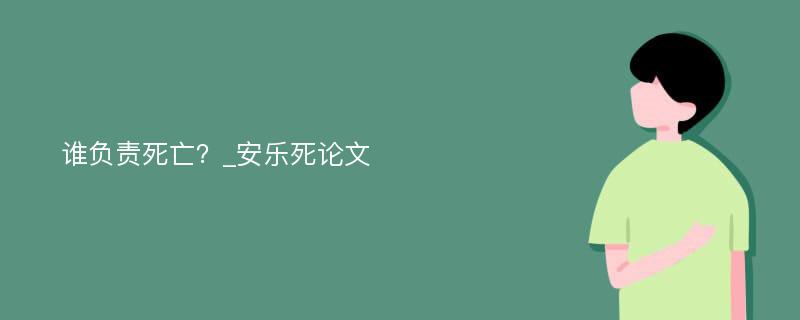
走向死亡 谁说了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谁说了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一位争取安乐死合法化者的临终呐喊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的这句隽永诗自从发表以来,就一直是众多读者的理想人生追求目标。然而,如夏花之绚烂的生不易,如秋叶之静美的死尤难,因为生命的辉煌可以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正大光明合理合法地实现;而死之愉悦却暂还不能由自己随心所欲地选择。纵观茫茫人海、古今中外,真正寿终正寝安然而逝的有多少?倒是处处都有惧死等死者的那种呻吟恐慌、眼神呆滞、精神受压、了无生趣的面孔。
纵横三国的枭雄曹操,在临终前曾无限感慨地提笔写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可见“死”与“生”同样是一个亘古不衰的话题。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除关注“优生”,也开始关注“优死”,即“安乐死”。长期以来,“安乐死”就已成为全社会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引起医学界、法律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高度重视。
安乐死浪潮席卷全球
“安乐死”一词原意为无痛苦死亡,尊严的死亡,中文直译为“安乐死”。早在1902年,挪威就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安乐死”属于特别犯罪,罚与不罚由法官裁断。南美洲的乌拉圭,对安乐死的看法则是全世界最开通的,1933年,该国修订刑法时,特别减免了安乐死的刑事责任,成为世界上最早赞成安乐死的国家。
荷兰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安乐死的国家。荷兰参议院1993年11月30日以37票对34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根据这部法律规定,申请安乐死必须具备五大项共20个条件,只有全部符合方允许执行。这些先决条件严谨、周密,可完全杜绝误杀或致人枉死之弊端,因此引起西欧和美国司法、医学、社会学者的普遍关注,至此安乐死在荷兰经过70年的争论终于获得合法地位。
在丹麦,1992年10月颁布并实施了一项有关安乐死的新法,受到许多人的欢迎。新法规定,凡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因中风瘫痪或大脑受损而无望存活下去者,只要他们事先立下遗嘱,医生就有义务停止治疗。这个600多万人口的国家,迄今已有四五万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接受新法规。
在加拿大,虽然法律规定任何人帮助他人结束生命都是犯罪,但现实生活中,安乐死事件却接二连三地发生。特别是去年,罗德里格斯太太挑战法律,为自己和其他同样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人争取在医生的协助下,保留着人的尊严去结束自己生命的斗争后,罗德里格斯太太的死又一次轰动政界和司法界,再次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去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加拿大有77%的人赞成安乐死。
在澳大利亚,安乐死事件屡见不鲜,维多利亚州加强了安乐死立法,同意病人可以拒绝治疗。新法令规定:如果违背病人意愿而给予继续治疗则是违法,在病人失去行为能力后,还可以指定代理人为他作出是否继续治疗的决定。在维多利亚州带动下,奥大利亚南部和北部两个地区也出台了“自然死亡法”,以尊重病人的选择。为此,澳大利亚“人和生物伦理中心”对维多利亚州的2000名医生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是:869人支持安乐死,1/3的人承认自己至少对病人施过一次安乐死。
日本属于东方民族,在观念上趋于保守,但他们也正在坦然接受安乐死的方式。1991年4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收住了一名肾衰竭病人,住院4个月后,病人病情恶化,最后只能靠饲管和呼吸器维持生命,家人多次请求医院中止治疗,医院都以无法律根据为由拒绝了。此后家人又单独找到负责病人治疗的一位34岁大夫,希望结束病人的生命(病人也同意),责任由家人负。这位大夫没有征询其他医生的意见,便停止了对病人的治疗,并在病人亲属在场的情况下,给病人静脉内注射了一针冬眠灵,病人当晚无痛苦辞别人世。此事一经披露,震惊日本,当地警视厅立即立案调查这一“谋杀案”。但许多人认为医生是无罪的。日本的安乐死组织“尊严死亡协会”主席阿基大认为,应当立法允许人们安乐死,至少可以允许被动安乐死,因为这么做至少是尊重一个人的意愿,也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据日本医学会最近的调查,四分之三的医生说只要病人患不治之症就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
中国尚未开绿灯
“地球村”上安乐死之风劲吹,作为村中一员的中国当然不可能成为安乐死的真空地带。安乐死虽然不再令人谈之色变,但仍然是法律的禁区。
1968年,著名演员,《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赵太太”的扮演者金彦章,因不忍儿子受病魔摧残而苟活,在一番“儿子,不是我不爱你,不是我不管你,实在是因为爱之极也是恨之极,你活着,于世无用,一生痛苦,于我们家也是一种磨难……”的祈祷后,终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了,随后抱着尸体直奔公安局投案自首。当时,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金彦章死刑缓期执行。
十年前,在湖南省衡阳县发生了一宗请求安乐死的典型事件。死亡请求人袁长青,男性,1961年生,因患脑神经肿瘤先后于1969年和1972年在长沙市一全国有名医院手术治疗未愈,后不久便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母亲和在法院工作的父亲没日没夜,精心照顾。为解除自己的痛苦,也为了不拖累父母,袁曾几次自杀未遂。1982年起,袁开始不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及省市等有关部门写信,请求安乐死,但均被婉拒,并劝他勇敢地生活下去。随着病情恶化,袁的上肢也开始瘫痪;进而双目失明。袁在极度痛若中,仍恳求安乐死但因无法律规定,同样无法实现其请求。1992年8月,袁开始绝食和拒绝治疗,不久,他便带着无限痛苦和深深遗憾告别了人间。
1989年,浙江省金华市一位叫曹进之的病人身患绝症,痛苦万分,自愿要求安乐死,也给医院和法院提出了一道难题。虽然在病人的要求下,其妻子、儿子和三个弟弟联名写了要求让曹进行安乐死的“申请书”并签了名,但医院认为要经法院签署意见,否则他们要负刑事责任,可法院接到申请书后觉得无法可依,不能签署意见,因此,问题最终未获解决。
1994年3月,苏北某县谈庄村村民陈莉,在丈夫患上绝症,多方医治无效后,为使丈夫早日解除痛苦,亲手将丈夫杀死,法院调查审理后,认为陈莉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同时有其特殊性,因为死者无可疗救,本人有提前死亡的请求,加害人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较小,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尽管如此,最后,陈莉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995年2月初,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安乐死”的特殊杀人案,刘沙波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54岁的刘沙波与其妻吴秀云结婚30多年来,感情一直很好。1993年12月,吴秀云在北京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情不断恶化,使她常常疼痛难忍,她多次求丈夫去找安眠药给她服用,让她安乐死,但都被刘沙波拒绝了。1994年9月8日,吴秀云又疼得在床上打滚,再次央求丈夫。刘沙波看着妻子痛苦欲绝的表情,实在于心不忍,就含泪用茶杯盛了半杯“一六零五”农药,递给妻子。吴秀云一口将药全部喝下。刘沙波将妻子紧紧抱在怀里,呜咽着看着妻子撒手西归。
实行安乐死,人心所向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在两千年前就认识到:“不要去治疗那些已被疾病完全征服的人,须知医学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散·培根说:“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
1978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安乐死国际讨论会,发表了“应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的宣言。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宣告成立。
人有生老病死,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我国古代的医书中,就有着关于安乐死的论述。《内经·五脏别论篇》曰:“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也。”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扁鹊的“六不治”思想,其中“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思想,在为齐桓公诊病时,前再次提出治疗方案,但他第三次见到齐恒公时,一句话不说,便匆匆离去。齐桓公派人追问何以如此。扁鹊答:病入骨髓,不可救药。
实行安乐死实际上也正是人道主义所要求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1992年,上海肿瘤医院共有9例晚期癌症病人自杀,占同期住院病人死亡数的0.42%。它让人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求死者”避免选择自杀这种残忍的方式?从掌握的材料看,如果自杀者懂得安乐死,法律也允许安乐死,那么自杀者会选择安乐死这种“优死”的方式,而避免自残致死。这从上海一位绝症病人的心态中得到了证实:病人为女性,54岁,晚期直肠癌合并乳癌,经过多次治疗和手术,病情仍恶化,杜冷丁也缓解不了利刃剜心般的剧痛,病人渴望安乐死,并向医生和子女提出。子女虽无数次念及让母亲安乐死,但出于种种顾虑,又无数次抹掉这种念头。病人痛苦地表示:“如果我现在还有一丝力气的话,我一定会翻下床,爬到阳台上跳下去,我再也熬不住了,这日子绝对不是人过的。”
实施安乐死对社会公有资源也是一个合理的保护。美国丘吉尔教授最近指出:“在美国,大约有一万人靠公众的钱昼夜不停地用药物用人工饲养的方式来维持其无价值的生命,他们每年所花掉的费用,大约是15亿美元。”
美国一家保险公司曾作过调查,结果是:对于癌症患者,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中,医疗费用急剧增长。某肺气肿病人最后一年的医疗费用20万美元,其中临终前34天中,就花掉6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却有900万儿童得不到常规医疗服务,有将近3300万人得不到企业和政府的保健补助。以效用原则来衡量,这种分配是极不公平的。更不要说濒临垂危的少数病人却需要无效占用医护人员更多的劳动了。
我国有12亿人口,其中约有20%享受公费医疗,国家卫生资源极其有限。根据有关统计,我国1982年人均卫生事业费仅为4元。而全国却有相当数量靠公费维持“无生命价值”的人。如上海某制药厂一副科长,1980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医生判定此人没有苏醒的可能,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8年后,他还“活着”,全部治疗费已达7万元以上;每月仍拿全额工资,另有单位每月负担210元护理费,实行每天24小时护理。现在,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高级病房里,一位脑死亡植物人已经在那里睡了5年多,每天光床费就大约200元,医疗费用难以计数。
试问:这于国家、于社会、于个人,何益之有?
目前,安乐死在很多地方都已获得了公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去年,北京有关方面对500人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安乐死可行者达399人,占79.8%。北京地区还对从事各种职业的10000人作问卷调查,其中91%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可以在我国推行安乐死。上海曾对122位老人作问卷调查,有79.8%的老者患有不治之症,又伴有无法忍受的痛苦,要求安乐死,亲属也表示同意,还有67.8%的老人表示,当病人无法救治时,亲属可以作主提出安乐死。江南某医院临床统计,在563例死亡病人中,有28%的死者亲属因不忍患不治之症的亲人遭受痛苦折磨,而根据死者要求,请求医生停止抢救而让其逝世。华北某医院也曾对600例50岁以上的癌症患者、老年病患者作调查,其中有22.8%的患者,因要求安乐死受阻,结果绝望地跳楼、自缢而去。
走向死亡,谁说了算
安乐死辩论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人是否有死的权利。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这是一条不可违背的首要原则,因此杀死任何无辜的人都是不允许的,生的权利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前提。而主张安乐死的人则认为:与人有生的权利一样,人也应有“尊严死”的权利。生的权利虽然及为重要,但它只是许多重要权利之一,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如患不治之症且又极端痛苦时,病人完全有选择死的权利。
1988年,邓颖超同志致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开展讨论,我很赞成。我认为安乐死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又委托秘书向中央报告:“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话虽不多,可体现了邓大姐的现实和开明。
三年后,当邓颖超同志病危时,她反复对周围的人们说:“我这么难受,还拖累了你们这么多人,再也不要抢救了。”她的崇高的愿望,终因没有法律的保障,未能实现。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短短的几句话,问得委员会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德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1993年,布兰德安乐死案轰动英伦,布兰德的父母在知道变成植物人的儿子毫无康复可能后,向公众表示:“我们爱自己的儿子,是爱他的尊严,而不应只是爱他没有生命意义的呼吸。我们的儿子有生的权利,但也应有死的尊严。”
1994年11月下旬,英国高等法院判定已陷入植物人状态3年半的安东尼·布兰德有权死亡。
这一判例由于赋于医生停止与布兰德类似病例的生命维持系统的合法权利,在英国各界引起了非常重大的争议。医学界和法律界专业人士大多赞同这项判决,认为这一判决符合人道和人权。英国高等法院的判决理由何在呢?据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家事法庭庭长斯蒂芬·布郎表示,22岁的布兰德,在1989年4月15日的一场足球赛中,因人群拥挤,胸部被挤压受伤后,胸部功能已经丧失。基于这一情况,在英国历史上创下先例,允许其医生不再喂食布兰德,让他“在最大尊严和最小痛苦中平静地安息。”
从最终意义上说,安乐死应该是必死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小段时间里所实现的变被动为主动,变痛苦为愉悦,从而对其自身生命本质的一次全面占有和自由主宰,是对自身生命能量的最后一次释放……
法律不应继续沉默
安乐死在我国还是一个尚未降生的“婴儿”,虽然实际上已成事实,但法律依然沉默。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曾联名提出“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尽快拟定‘安乐死’的立法”议案。对此议案,1994年6月30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给予的答复是:“对‘安乐死’立法涉及到法律、医学和伦理学等各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虽然有的国家制定了有关法律,但为数还很少,多数国家对此持慎重态度。目前可以促请有关部门积极研究这一问题。你们的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广东代表对此答复不太满意,所以决定今年继续提此议案。
1995年两会期间,广东74名全国人大代表再次联名提出“请尽快尽早为‘安乐死’立法以利国利民”议案。该议案对有人认为实行“安乐死”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宜暂缓立法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的初步草案。
当然,安乐死事关重大,有关部门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法律不应长期回避。可否从以下几方面制定法律规定:
其一:“安乐死”的实施前提,应该是患者本人不受任何人指使,按自己的意愿,清醒地、真挚地提出这一要求,以法定的形式记录下来,或有自己的手迹做为合法的根据。对那些隐瞒真正病情,利用诱导或胁迫等手段催其“安乐死”,从中获得遗产和好处的做法均视为违法。
其二:对“安乐死”必须有如下限制:第一必须经市、县以上医疗部门确诊为不可救药的绝症患者;第二必须处于极度痛苦无法继续忍受下去者;第三必须是绝症晚期、濒临死亡者。
其三:实施对象必须是患绝症的危重病人。对那些先天性瘫痪,以及活着的“死人”、残疾婴幼儿不能实施安乐死。任何随意剥夺人生存权力行为都是违法的。
其四:必须有家属认可。安乐死者的父母、配偶、儿女等直接共同生活者,必须对申请安乐死作共同认可,并在安乐死者的申请书上签名盖章。
其五:必须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安乐死不是自然死亡,为防止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必须经住所地县、区以上公证机关公证。
其六、必须由指定医院施行。安乐死应体现“安乐”,给死者一个愉快的意境,因而这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此,安乐死必须由地市级指定医院施行。在施行时,医院应严格审查上述材料,认真做好登记;并由申请人及其家属签名盖章;施行时必须有死者家属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