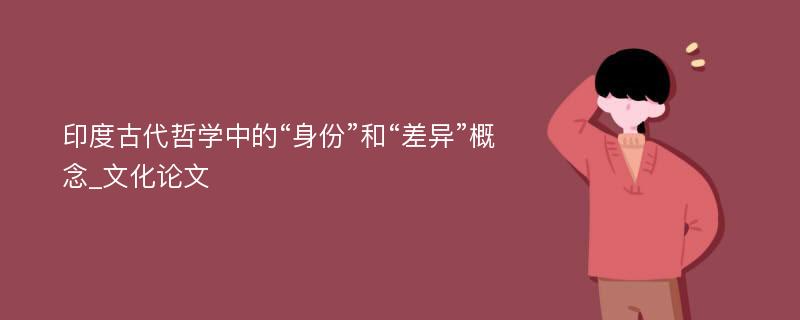
印度古代哲学中的“同”、“异”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与“异”是印度古代哲学中经常讨论的观念,它们涉及事物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别性,涉及事物的基本形态和事物的本质问题。无论在印度上古的宗教哲学典籍中,还是在印度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哲人们在这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代印度哲学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征,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思考。
一、吠陀、奥义书中的相关思想
吠陀是现存最早的古代印度文化历史文献。虽然多数吠陀文献主要论及的是宗教方面的内容,但其中也有一些赞歌具有明显的思辨性成分,被称为“哲理诗”。在这些哲理诗中,就涉及了事物的“同”与“异”的问题。
一些哲理诗提出了“太一”(tad ekam)的概念,认为世界最初是“太一”。如“无有歌”(《梨俱吠陀》10,129,1-2)中说:“那时,既没有无,也没有有;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它外面的天。什么被包含着?在什么地方?在谁的庇护下?是否有深不可测的水?那时,既没有死,也没有不死。没有夜与昼的标记。太一靠自己的力量无风地呼吸。在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Macdonell,pp.207-208)这里说的“太一”自然是没有差别的状态,因为在它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
但在另外一首称为“造一切者之歌”(《梨俱吠陀》10,82)的赞歌中,“太一”被认为是包含一切事物的东西。该赞歌6中说:“那(胚胎)安放在无生者的肚脐之上,那是太一,其中住有一切存在的东西。”(Radhakrishnan and Moore,p.18)这一赞歌中的太一或胚胎中有一切东西,这些东西自然是有种种差别,但它们也有着共同点,即都在相同的胚胎中。此处,所谓“一切存在的东西”涉及差别(异)的概念,而“太一”或“胚胎”则涉及相同(同)的概念。因为一切东西不是一个东西,自然属于“异”,而一切事物包含在一种东西中则是这些东西的共同性,自然属于“同”。
奥义书是吠陀中较晚出现的一批文献。奥义书中提出了大量的哲学理论,是印度系统哲学体系形成的开端。这些理论中的主流思想也涉及了“同”与“异”的观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梵”与“我”关系的理论。
所谓“梵”(Brahman)在奥义书中一般指一切事物的本体,宇宙的最高实在。如《歌者奥义书》(3,14,1)中说:“这整个世界都是梵。”(Radhakrishnan,p.391)《剃发者奥义书》(2,2,12)中说:“梵确实是这不朽者。在前是梵,在后是梵,在右在左亦是梵,梵在下和在上伸展。梵确实是这一切。”(ibid,p.685)在这里,梵被等同于一切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梵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所谓“我”(Qtman)一词音译为“阿特曼”。它在梵语中有多种含义。但在奥义书中,这一词一般是在两种意义上来使用:一是指小我(个我),即是在作为人的身体诸器官的主体或人的生命活动的控制者这种意义上来使用,如《广林奥义书》(3,7,23)中说:“它不被看却是看者,不被听却是听者,不被认知却是认知者,不被领悟却是领悟者。除它之外没有看者,除它之外没有听者,除它之外没有认知者,除它之外没有领悟者。它就是你的阿特曼,是内部的控制者”(Radhakrishnan,pp.229-230);二是指大我,如《歌者奥义书》(6,9,4)中说:“一切以它为自我,它是实在,它是阿特曼,它就是你。”(ibid,p.460)《歌者奥义书》(7,26,1)中则说:“气息产生于阿特曼,希望产生于阿特曼,记忆产生于阿特曼,空间产生于阿特曼,火产生于阿特曼,水产生于阿特曼……确实,一切都产生于阿特曼。”(ibid,pp.488-489)这里所用的“阿特曼”即是大我,它的含义实际与“梵”没有差别。
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的“我”有多个,因为每个人或生命物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我”,这些“我”及其所属的生命物是多样的、有差别的。而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我”则只是一,因而它没有差别,这种“我”是唯一存在的梵。
奥义书中关于梵与“我”关系的主流理论是所谓“梵我同一”(“梵我一如”)。这种理论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梵和作为人或一般生命物中主体的“我”是同一的。如《广林奥义书》(3,7,15)中说:“它位于一切存在之中,没有什么能认识它,它的身体就是一切存在物,它从内部控制一切存在物,它就是你的自我。”(ibid,p.228)此处的“我”不仅被认为是生命物中的主体,而且还被认为是与各生命物相关的各种事物。因此,所谓“梵我同一”的含义就不仅仅指大我与小我同一,还指大我(梵或最高实体)与一切事物同一。
奥义书的这种梵我关系理论中直接包含着“同”与“异”的观念,也包含着关于“同”与“异”的虚幻和实有观念。从小我有多个的角度说,或从有多个与小我直接相关的生命物或事物的角度说,存在着所谓“异”;从一切小我在本质上就是梵的角度说,或从一切生命物及相关事物都以梵为根本的角度说,存在着“同”。而如果从离开梵不存在真正独立的“我”或其他事物的角度说,事物或生命物的“异”就是现象上的,是虚假不实的,而“同”则是本质上的,是实在不虚的。《迦塔奥义书》(2,2,12)中说:“那个控制者,一切事物的阿特曼,使一种形态呈现为多种。”(ibid,p.640)而且,奥义书中的主流思想把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梵或大我(阿特曼)视为是摆脱痛苦的最高境界。如《慈氏奥义书》(6,17)中说:“最初,这世界是梵,是无限的同一,在东面是无限,在南面是无限,在西面是无限,在北面是无限,在下面和上面是无限,在各个方面都是无限……最高我是不可理解的,无限的……最高我是一。那认识到这的人达到一中之同一。”(ibid,pp.829-830)《伊莎奥义书》(7)中说:“在认识到所有的事物都是阿特曼的人那里,在看到了这同一的人那里,还能有什么迷误和痛苦呢?”(ibid,p.572)《歌者奥义书》(7,25,2)中说:“阿特曼(梵)确实就是所有这一切。看到这的人,想到这的人,领悟到这的人就在阿特曼中有快乐,在阿特曼中有高兴,有阿特曼中有同一,在阿特曼中有欢喜,他们就成为自制者,就在一切世界中具有无限的自由。但那些不这样想的人,就将依他,就将存在于可灭的世界中,就没有自由。”(ibid,p.488)在这里,实际上把认识到现象上的“异”在实质上是“同”的观念,视为一种达到解脱的最高真理。
奥义书中的这种“同”与“异”的观念虽然表述得还不是很明确或很直接,但它直接影响了印度后世哲学中的同异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对印度后来主流哲学思想中的同异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婆罗门教主要哲学流派中关于“同”、“异”的典型思想
婆罗门教主要哲学流派包括胜论派、正理派、数论派、瑜伽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这些派别中直接或较多论及“同”与“异”问题的是胜论派和吠檀多派。
胜论派的哲学体系是所谓“句义论”,用“句义”(与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来分析或说明世间事物的基本构成。在胜论派提出的诸种句义中,有所谓“同句义”、“异句义”和“俱分句义”,这三个句义是直接论及事物的“同”与“异”问题的。
所谓“同句义”,主要指事物的相同性。胜论派的重要文献《胜宗十句义论》把“同句义”限定在事物的存在(有性)上,认为存在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或最普遍的相同性。如说:“同句义云何?谓有性。何者为有性?谓与一切实、德、业句义和合,一切根所取,于实、德、业有诠智因,是谓有性。”(高楠顺次郎,第54卷,第1263页)
所谓“异句义”,主要指事物的差别性。《胜宗十句义论》把表明某一物的独特性或与其他物相区别的东西称为“异句义”。如说:“异句义云何?谓常于实转,依一实,是遮彼觉因及表此觉因,名异句义。”(同上)该论还把这种“异句义”视为事物的最终差别,称为“边异”。
所谓“俱分句义”,指事物中相对的同与异,如胜论派的“实”(实体)句义中包含地、水等,“德”(性质)句义中包含色、味等,“业”(运动)句义中包含取、舍等。这里的“实”、“德”、“业”各自对于胜论派的“句义”总体来说是下位的概念,是“异”,而对于其各自下属的地、水或色、味,或取、舍等来说,则是上位的概念,是“同”。这里涉及的“异”与“同”是相对的,称之为“俱分”。如《胜宗十句义论》中说:“俱分句义云何?谓实性、德性、业性及彼一义和合,地性、色性、取性等,如是名为俱分句义。”(同上)在胜论派中,“俱分句义”主要是《胜宗十句义论》中的提法,在印度其他的一些胜论派文献(如《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中,所谓的“同句义”和“异句义”既包括存在与最终差别的含义,也包括相对的同与异的含义。
吠檀多派是印度哲学中的主流派。此派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奥义书中的梵我关系理论,并在其理论中表明了本派关于“同”与“异”问题的看法。
吠檀多派中有不少分支,各分支中影响较大的有“不一不异论”、“不二一元论”、“限定不二论”和“二元论”。这些分支对梵我关系的见解不同,因而在同异问题上的观念也就不同。
“不一不异论”主要是吠檀多派根本经典《梵经》中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梵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或世界的根本因,与其部分、属性或被造物——“我”(现象界)是不同一的(此为“不一”),而从“我”(现象界)都具有梵性、一切事物离开梵都不能存在的角度看,梵与“我”又是同一的(此为“不异”)。《梵经》(3,2,27)中将二者的关系比喻为“如同蛇和它的盘绕状一样”;《梵经》(3,2,28)还将二者的关系比喻为“如同光和发光体一样”(见姚卫群编译,第318-319页)。从《梵经》的以上表述可以看出,它认为梵与“我”的关系在表现形态上存在“异”,而本体则是“同”。
“不二一元论”主要是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等人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梵或大我是万有的根本,一切事物在本质上是梵或大我的幻现,真实存在的仅是梵。乔荼波陀认为,没有独立于梵或大我的存在,小我既不是梵的部分,也不是它的变异。他在《圣教论》(3,4)中说:“犹如瓶等中之空,瓶等遭到破坏时,其空悉归于大空,众我汇入我亦然。”(乔荼波陀,第108页)这也就是说,小我(众我)与大我(梵)的关系就如同瓶中的小虚空和瓶外的大虚空的关系一样。即:瓶中的小虚空与瓶外的大虚空本是一个东西,仅仅由于瓶子的限制,它们才显得不同。与此情形类似,作为人生现象的无数小我与大我本是一个东西,仅仅由于身体的限制,它们才显得不同,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物。商羯罗认为,梵在本质上是唯一不二的,梵作为大我与众多的小我等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商羯罗在其《梵经注》(1,4,22)中说:“个我与最高我的差别是由限制性因素,如身体等造成的。它们(身体等)由无明幻变出来的名色构成。差别是不真实的。”(见姚卫群编译,第278页)这也就是说,在商羯罗看来,众生的身体等事物之间的“异”仅仅是由于人的错误认识或错觉而产生的,“异”并不实在;作为表面现象的众我在本质上就是大我或梵,这种“同”才是实在的。
“限定不二论”主要是罗摩努阇等人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小我(现象界)与最高我(梵)之间的关系是属性与实体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小我与最高我虽密不可分,但二者又不相同。罗摩努阇在其《梵经注》(2,3,45)中说:“个我是最高我的一部分,就如同从诸如火或太阳那样的发光体上所射出的光线是那发光体的一部分一样。或如同一头牛或马的一般特性一样,着色事物的白色或黑色是(事物的)性质,因而,这些性质就是其依存事物的部分……最高我与个我有不同的性质。因为这就如同发光体有不同于其光线性质的性质一样。因此,最高我与作为其部分的个我不同。”(同上,第305页)在罗摩努阇看来,小我是最高我的属性或部分;属性或部分尽管隶属于实体或整体,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实。同样,作为属性或部分的现象界虽然隶属于作为实体或整体的梵,但并不能由此认为现象界不真实。作为实体而存在的仅是唯一的最高梵,现象界是“限定”客观实在的属性或部分,但万有的最终实体是“不二”的。罗摩努阇反对商羯罗等人关于世界是虚幻或无明产物的观点,也反对他们否定事物差别的观点,他在《梵经注》(1,1,1)中说:“那些主张实体没有一切差别的人无权断言这或那可证明这种实体,因为一切正确的认识方式都以带有差别的事物为对象……现量仅以有差别的标志的事物为对象。比量亦如此。因为比量的对象也仅是被区分的事物,这种区分通过与由现量和其他量认知的事物的关联实现……有人认为,在我们认识中所呈现出的一切差别,如罐、布等等,是不真实的,因为这种差别不能持久。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同上,第246-247页)因而,在同异问题上,罗摩努阇与商羯罗的看法是不同的:商羯罗否定“异”的实在性,只承认一切事物在本质上即梵这种“同”,而罗摩努阇则既承认一切事物都隶属于梵之“同”,也承认事物之间及与梵之间存在的“异”。
“二元论”主要是摩陀婆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梵虽是根本,但梵与小我不同一,二者是分离的。小我也有实在性,小我与梵之间有差别,它们是二元的关系。摩陀婆在其《梵经注》(1,3,7)中区分二者时说:“主宰者被认为安住并发出光辉,而个我则要接受其业的结果的经历。”(同上,第266页)这也就是说,小我要接受业报,而作为一切事物主宰者的大我则不用,二者是不同的。摩陀婆在《梵经注》(1,2,3)中还说:“一个相同的我(同时)存在于所有的身体中是不可能的,这是与事实及情理相抵触的。”(同上,第258页)这实际上是从逻辑上反对大我与小我完全同一的观点。摩陀婆也反对商羯罗等人关于世界是虚幻或无明产物的观点。他在《梵经注》(2,2,28)中指出:“不能说世界自身是非存在,或非存在自身是世界,因为这世界实际被感到,还因为世界是准确知识的对象。”(同上,第292页)在《梵经注》(2,2,30)中他又说:“世界并非仅仅是思想的一种样式,因为没有人根据其经验而感到是这样。”(同上,第293页)摩陀婆的这些观点与其肯定事物差别的立场是一致的。摩陀婆并不因为承认梵为事物的根本因就认为二者完全同一,他在这个问题上否定那种绝对的或真实存在的“同”,并特别强调世间事物之间及事物与梵之间的“异”,认为这种“异”是实在的,而由于梵与世间事物之间有实在的“异”,所以它们是二元的。
三、佛教中的“同”、“异”观
佛教的理论体系庞大,其中也有不少论及“同”与“异”问题的内容。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中都有相关表述。但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思想与佛教产生时就确立的一些基本观念有重要关联。
佛教产生于婆罗门教之后,它反对婆罗门教关于人生现象或世间事物中有一个唯一实在的根本因的思想,而认为世间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主张所谓缘起论。既是缘起,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东西,至少要有两个以上成分的相互作用才可能有“缘”;因而在逻辑上就要讲事物间相对的差别,即要在一定程度上讲事物的“异”。但佛教又认为差别不是永恒存在或绝对的,诸缘(诸事物)会不断变化或转变,而且可能会是同一个事物的组成部分;因而诸缘又有其相同性,这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事物的“同”。
在大乘佛教中,缘起的思想依然受到重视,而大乘佛教突出讲性空的理论,讲缘起性空,讲什么都不能执著。因此,大乘中无论是“同”还是“异”都是相对的,都不被认为具有实在性。这在中观派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龙树在《中论》卷一分析事物的因缘时就提出“不一亦不异”(高楠顺次郎,第30卷,第1页)。这里所谓的“一”指相同,“异”指差别。汉译本《中论》中包括青目的注释。在解释“不一亦不异”时,青目说:“若一则无缘,若异则无相续……问曰:若尔者万物是一?答曰:不一。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一,如谷不作芽,芽不作谷。若谷作芽,芽作谷者,应是一,而实不尔,是故不一。问曰:若不一则应异?答曰:不异。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异,若异者,何故分别谷芽、谷茎、谷叶,不说树芽、树茎、树叶?是故不异。”(同上,第2页)这意思是说,诸法既不能说是“同”,也不能说是“异”。如果说“同”就否定了事物中诸缘的存在,如果说“异”就否定了缘起事物的相续发展。说“同”和说“异”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有关现象。如若说“同”,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世上有谷和芽的区分;若说“异”,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世上有谷芽、谷茎、谷叶一类事物,而不把它们称为树芽、树茎、树叶。中观派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思想倾向,即认为从缘起角度讲,作为缘的事物间有差别,但各种缘在发展中又会变化,可以归为同一个种类;绝对地说“同”或说“异”都有问题,不能将概念的实在性绝对化,任何概念都有其局限性。不过,《中论》在这方面的思想表述得还不是特别明确或清晰。
《十二门论》中亦论及了同异问题,该论中主要是联系事物表现出来的特性和事物自身之间的同异来谈的。如该论“观一异门”中的偈颂说:“相及与可相,一异不可得。若无有一异,是二云何成?”此偈颂后的释文说:“是相可相若一不可得,异亦不可得。若一异不可得,是二则不成。是故相可相皆空。相可相空故,一切法皆空。”(同上,第164页)这里的所谓“相”指事物的特性,所谓“可相”指事物自身。按照中观派的看法,无论是说二者“同”还是说二者“异”都不能成立。而如果对于“相”与“可相”不能说它们是“同”还是“异”的话,那么就表明它们不实在;如果事物自身和其特性不实在的话,那么事物也就是“空”的了。在这里,中观派通过分析事物的“同”与“异”来论证一切事物皆空,事物的“同”与“异”概念自然是不实在的。
佛教中一些部派也有这方面的理论。一些部派提出了“同分”(众同分)的概念,较突出的是说一切有部。如《俱舍论》卷五中说:“有别实物,名为同分,谓诸有情展转类等。本论说此名众同分。此复二种:一无差别,二有差别。无差别者,谓诸有情有情同分,一切有情各等有故;有差别者,谓诸有情界、地、趣、生、种姓、男、女、近事、苾刍、学、无学等各别同分,一类有情各等有故。复有法同分,谓随蕴、处、界,若无实物无差别相名同分者,展转差别诸有情中,有情有情等无差别,觉及施设不应得有。”(同上,第29卷,第24页)这里说的“同分”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共同性,它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有情的“众同分”,还有一种是关于一般事物的“法同分”。“众同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差别的同分,另一种是有差别的同分。无差别的同分是指一切有情都具有的共同性,而有差别的同分是指不同的有情又可以分为更小的类别,这不同类别中的有情又具有本类别中的共同性。所谓“法同分”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各类事物中存在的共同性。
《俱舍论》中有关“同分”的论述实际上既涉及“同”的概念,也涉及“异”的概念。因为它既肯定了事物之间的相同,也肯定了事物之间的种类差别或事物之间的差别。也可以说,这种同分的论述中既讲了“同中有异”,又讲了“异中有同”。
《俱舍论》等有部著作中一般认为有实在的“同分”,但佛教中不同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也有不同。一些派别不承认“同分”的实在性。如《成唯识论》中就记述了瑜伽行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于有部的观点。该书卷一中说:“复如何知异色、心等有实同分?契经说故。如契经说,此天同分,此人同分,乃至广说。此经不说异色、心等有实同分,为证不成。若同智言因斯起故知实有者,则草木等应有同分。又于同分起同智言,同分复应有别同分。彼既不尔,此云何然?若谓为因起同事欲知实有者,理亦不然。宿习为因,起同事欲,何要别执有实同分?然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差别,假立同分。”(高楠顺次郎,第31卷,第5页)瑜伽行派在这里的主要意思是说,不存在独立实有的同分,佛经里就没有这样说过。如果有情共同的智力和言语是来自实有的同分,那么草木等也应有有情的这种同分,而且同分还需要另外的同分,这是不可能的。有情相同的行为愿望等与相同的前世行为的业力有关,而不是同分产生的。所谓同分是根据有情的身心相似、进一步的分类差别而假立的,并无实有的同分。瑜伽行派与说一切有部在同异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显然直接来自于二者不同的基本哲学立场。
佛教对于其他派别在同异问题上的观点也有批判。如《成唯识论》中就破斥了胜论派的这方面理论。该书卷一中说:“彼所执有,应离实等,无别自性,许非无故,如实、德等。若离实等,应非有性,许异实等故,如毕竟无等。如有非无,无别有性,如何实等有别有性?若离有法有别有性,应离无法有别无性,彼既不然,此云何尔?故彼有性唯妄计度。又彼所执实、德、业性,异实、德、业,理定不然。勿此亦非实、德、业性,异实等故,如德、业等。又应实等非实等摄,异实等性故,如德、业实等,地等诸性对地等体,更相征诘,准此应知。如实性等无别实等性,实等亦应无别实性等。若离实等有实等性,应离非实等有非实等性,彼既不尔,此云何然?故同异性,唯假施设。”(同上,第3页)此处瑜伽行派所批判的是胜论派的作为最高同的“有性”(即《胜宗十句义论》中的同句义),以及相对的同异观念。瑜伽行派认为,胜论派中的“有性”离开实句义就是没有自性的,而且其他句义也不需一个“有性”来确立其存在。胜论派中说的同异性(即《胜宗十句义论》中的俱分句义)也不实在,因为所谓既可作为同又可作为异的实等性(类)或地等性(类)不可能独立于实等或地等的个体而存在。因而这种同异只能是假设。
佛教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同异问题的论述,此处所举的只是一些较突出或基本的观点。
四、综合评述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同异观念在古代印度很早就已萌发。在后来形成的主要哲学流派中,这方面的问题更是受到高度重视。从印度历史上的同异观念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认为一切事物在实质上都是一种根本因的显现,只承认事物的“同”是实在的或根本的,不承认事物之间的“异”的实在性。这是奥义书和吠檀多派中的主流同异观念。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论”和吠檀多派中的“不二一元论”都认为事物的差别是不实在的,而认为一切事物都可归于根本的梵,这种同一是实在的。
第二种类型认为“同”和“异”都是实在的,而且其中既有绝对的,也有相对的。这是胜论派中的观念。胜论派文献《胜宗十句义论》中的“同句义”主要指存在(有性)这种最高的同,“异句义”主要指最终的差别(边异),二者都是绝对的。《胜宗十句义论》中的“俱分句义”指相对的同异关系。
第三种类型是在论述“同”时涵盖“异”,但认为二者都是实在的。这是佛教中说一切有部有关理论中表露出来的观念。说一切有部分析“同分”时涉及了事物的不同种类,此派的“同”与“异”的观念是交织在一起的,“同”与“异”的实在性都未被否定。
第四种类型认为“同”与“异”都是相对的,并不实在,仅仅是人们的假立。这主要是大乘佛教中的观念。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都持此观点。中观派认为实在的“同”与“异”的观念将直接否定佛教的缘起论。瑜伽行派认为无论是表现为有差别的事物还是所谓的“同分”都是不实在的;一切唯识,但识最终也不能执著。因而同异观念在此派中自然只能是“假立”的。
以上几种不同类型的同异观念与各派哲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奥义书和吠檀多派中的主流思想是梵的唯一不二理论,它们要突出梵的本体地位,因而在同异观念方面自然要强调“同”的绝对实在与“异”的不实在。胜论派是一种自然哲学,它侧重分析事物的构成要素,对各种自然现象都认为是实在的,因而对于各种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是不加否定的。说一切有部是佛教中强调“法有”的派别,“同分”是此派对世间现象分析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因而此派对于事物之间的“同”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异”的关系的实在性自然是加以肯定的。大乘佛教在理论上强调较彻底的空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无自性,一切概念都不能执著,因而对其他派别提出的概念自然要否定;即便佛教内的种种概念也只是达到佛教最高境界的方便手法或假名,因而都是要否定其绝对实在性的。“同分”概念尽管在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中一些派别中经常使用,但依然要被大乘佛教视为“假立”,与各种事物直接相关的“异”的概念的实在性则更是不可能得到肯定。
印度古代论述“同”与“异”的观念较多的派别多为印度哲学中的主流。这些派别在印度古代文化发展中占有显要地位。它们的同异观念与其核心理论紧密相关,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示了这一文明古国哲学思想形态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