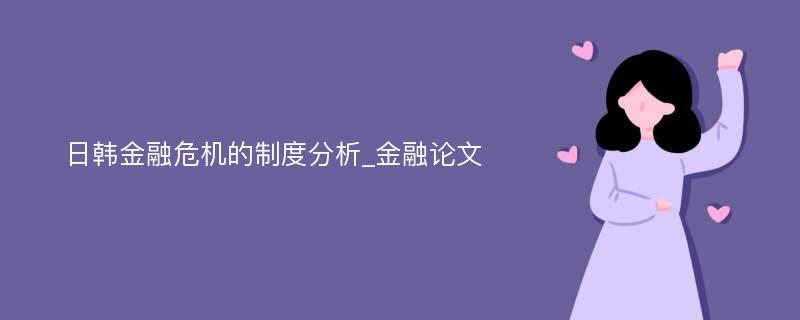
日韩金融危机的体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韩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持续半年、一波三折的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被称为经济危机,更多地着眼于这场危机对东亚未来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袭击了东南亚诸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并由最初的贬值危机发展到韩、日两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倒闭风潮。这场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东亚国家的财富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影响到某些国家的经济主权。那么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呢?除却“热钱”炒作这一共同诱因外,现有的分析实际上是将危机区分为两种不同形式来看待的。一种是东南亚的外部冲击式,即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由于宏观政策失误所导致的债务、外贸、投资结构失衡与僵化的汇率机制之间的矛盾,而给投机留下了缝隙。因而一经冲击即表现为恶性的、循环式的货币贬值。另一种则是日、韩两国的内部积累式,主要是在其发展战略下所形成的整个经济体制内在矛盾长期累积,最终从内部爆发的结果,外部冲击只是加剧了危机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可以通过日韩倒闭事件在时间上先于贬值风潮而得到证明。应该说,上述分类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还是找出了各自的主要特征。当然这两种形式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并有着最深层次的共同根源(如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影响),但鉴于对东南亚危机成因的论述颇多,而日、韩金融危机的确又有其独特性,因而我们在本文中仅以这两个国家作为考察重点,主要从体制入手考察其危机的成因,以期对这场危机的根源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高负债率:风险放大型的财务结构
这一问题不仅限于日韩两国,在东南亚各国也同样存在,只是发生的层面略有不同。东南亚主要是债务结构不合理,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的比例过高;对于日本来说,主要是产融一体化下的间接融资方式所带来的企业高负债经营(据统计,日本企业界的负债率高达80%以上);而对于韩国来说,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例如,韩国30个大企业集团1995年负债金额占资本总额的比率高达427.7%。 而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又有大量的企业和金融公司对外举债,导致了整个国家外债在短期内的激增,从而一举成为目前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债务国。为什么日韩企业“偏爱”高负债率的财务结构,而东亚国家又“偏爱”高外债式的发展道路呢?高负债的财务结构又是如何加剧了日韩(包括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呢?原因非常复杂,它涉及到发展战略、政府作用和历史成因等一系列因素,但仅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资本结构和杠杆原理已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应当看到,企业、金融业和政府虽然在各种收入与支出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其财务结构仍具有同构性,即都存在预算约束,要求其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这种同构性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类型的经营活动都要表现为货币金融的运作。在这种条件下,财务结构的原理,无论对于国家一级的宏观帐户,还是企业一级的微观帐户都同样适用。下面我们就以企业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先看公式(1):
Q(P-V)
DOL=───────
Q(P-V)-F
EBIT变动的百分比△EBIT/EBIT
(注:DOL=─────────=──────
销售量变动的百分比△Q/Q
△[(PQ-(VQ+F)]/[PQ-(VQ+F)]
=─────────────────────
△Q/Q
△Q(P-V)/[Q(P-V)-F]Q(P-V)
=────────────────=────────
△Q/Q Q(P-V)-F
在这里Q为销售量,P为单位售价,而V为单位变动成本,F为固定成本。熟悉财务理论的学者都知道,这一公式表示的是公司盈利,即EBIT[EBIT=Q(P-V)-F]对销售量变动的反应程度。这被称为营业杠杆作用。由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固定成本F 越高,DOL的数值就越大,即营业杠杆的作用越大。 这表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其销售量的小幅度变化会引起营业盈利的大幅度变化。因而高营业杠杆通常伴随着营业利润的较大不确定性和较大的经营风险。下面再来看财务杠杆。根据资产平衡公式,企业资产来源于负债和股东资本,通常情况下,对于债务企业必须按时支付固定利息费用,因而这类费用被称为财务固定成本,它是财务杠杆作用的支点,而股东资本(普通股)的收益则是根据盈利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财务杠杆衡量的是一个企业运用固定财务费用融资时,公司息前税前净利(营业利润)变动所引起股东每股盈余变动的幅度,用公式(2)表示为
EPS变动的百分比△EPS/EPS
(注:DFL=────────=───────
EBIT变动的百分比
△EBIT/EBIT
△(EBIT-I)(I-t) (EBIT-I)(I-t)
──────────/───────────
N N
=──────────────────────
△EBIT/EBIT
△EBIT
─────
EBIT-IEBIT
=───────=────):
△EBIT/EBIT
EBIT-I
EBIT
DFL=────(2)
EBIT-I
由上式可知,企业如果多以负债方式经营,那么其利息支出必定较高,而I的数值越大,DFL的数值也越大,从而较小百分比的营业盈利的变动,必然会导致较大百分比的股东收益的变动。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个杠杆作用合而为一,就得到了综合财务杠杆作用。将上述公式(1 )、(2)相乘即得
Q(P-V) EBIT
Q(P-V)
DOFL=DOL·DEL=──────·─────=──────=
Q(P-V)-F
EBIT-I EBIT-I
Q(P-V)
─────────。
Q(P-V)-F-I
这就是综合杠杆作用公式,它直接衡量销售变化对业主收益的影响。由公式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越大,利息支出的数量越多(即负债越多), 综合杠杆作用也就越大。这一杠杆说明,市场占有份额(无论是单个企业销售量的变动,还是整个国家的出口规模与变化速度),通过营业杠杆和财务杠杆对企业或国家的收益将产生成倍的放大或缩小作用。当经济繁荣、销量大增、出口增加时,高营业杠杆可以大大提高收益,高财务杠杆更是锦上添花。但当企业产品滞销、积压和国家出口急剧减少之时,杠杆作用却会雪上加霜。繁荣时,企业收益和国家经常项目收入递增很快;但当衰退时,则加速递减,如果企业负债率过高或国家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过多,那么企业的连续倒闭或整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就在所难免。实际上日、韩企业和银行的连锁倒闭,以及泰国、韩国陷入债务危机正是与此有直接关系。
我们先来看营业杠杆。由于欧美国家产业升级,东南亚和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80年代有很大增长,而韩国和日本的汽车、电子、机械等重化工业在西方转向信息产业的条件下,其竞争力也迅速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国家大力推行技术引进和改造策略,其经济结构中固定成本的比重迅速提高,这样在出口顺畅时,高固定成本使其收益增长快于销售量增长,因而“东亚奇迹”得以呈现。但进入90年代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有走出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下降波的迹象,美国经济连续七年持续增长就是一个信号(注:1995—1997年,美国经济空前高涨,已达到60年代的高水平。增长率从1995年的约2%提高到平均4%的水平。失业率从5.7%降到4.9%,达1973年以来最低水平。1995—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分别为3%、2.6%和2.4%,1997年度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利润跃升了14%。(引自[美]曼德尔等《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商业周刊》中文版1998 年1/2 月合刊,第74、75页)。),信息革命的成果开始在欧美的传统产业(即东南亚、韩国的出口产业)中得到应用,主要表现是传统产业中的工序革新,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导致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注:1995年以后,美国公司以比在其他资本货物的投入快一倍的速度,增加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支出。在1997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除小型企业和金融服务机构外)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达到了2.4 %(引自[美]曼德尔等《经济增长能持续多久》,《商业周刊》中文版,1998年1/2月合刊)。),因而上述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便受到了挑战。而与此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全体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了产业结构趋同和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注:尽管1996年动态随机进入存储器蕊片(DRAMs )的价格暴跌了82%, 但台湾仍计划在6个月内把半导体生产能力提高一倍。汽车生产能力全球过剩,在美国,1996年旅行轿车价格下降了2.1%, 在欧洲则有 300 —400万辆汽车过剩,1996 年欧洲轿车的平均价格下降了500—10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大宇和现代公司仍在为扩大出口增加生产,而三星集团也投资100亿美元进军汽车业 (参见《紧缩危机迫在眉睫》,《商业周刊》中文版,1998年1/2月合刊,第35页;《是正视亚洲现实的时候了》,《改革》1997年第3期,第124页,译自[美]《商业周刊》1996年12月2日)。)另外, 拥有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南亚、拉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出口也在崛起,这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威胁。而上述国家的工资成本却上升得很快(注:韩国的工资水平在过去3年内增加了将近一倍。 三星电子厂工人平均工资已达到12.7美元/小时(引自汤敏《东亚经济从此就日渐式微了吗》,《改革》1997年第 4期,第117页)。),在未遭到衰退袭击时, 大幅度上升的工资成本实际上已变成经营成本中的固定成本,这诸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出口增长缓慢,甚至大大低于进口增长。以韩国为例,在繁荣阶段大企业不断增加生产设备投资,并依靠高负债和政府支持来进行腕足式的扩张。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有利的贸易环境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而进入90年代,贸易环境一发生变化,韩国过度投资、生产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生产方式的弊端便一一显露出来。根据营业杠杆原理,出口的大幅减少(实际上是企业销售量减少)使营业利润以递增速度下降。而由于东亚地区国家在出口产业上的同构性和生产能力过剩,又导致了在贸易条件恶化条件下的竞相削价,甚至亏损出口的奇特现象,其结果是当出口销售量成等差数量减少时,出口收益却接近于成等比数量递减,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企业收益大幅减少,而且是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急剧恶化。韩国的经常项目从1990年开始出现赤字,1990年为22亿美元,1991年为87亿美元,1992年为45亿美元,到1995年已猛增至100.61亿美元,而1996年则为203.79亿美元。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营业杠杆过高难辞其咎。
然而如果仅是营业杠杆过高,还不致于发生大规模的连锁倒闭,可以说对这场危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这些国家从企业到金融机构,直到宏观经济帐户各个层面上负债率过高的财务结构。这种高负债不仅来自国内企业间和银企之间的拖欠和借贷,而且包括在短期内大量举借的外债。例如,我们已提到,韩国的30个大企业集团1995年的负债金额占资本总额的比率竟高达427.7%,这个数值较上市公司平均值高出4倍以上,而1997年初倒闭的真露集团负债比例竟高达3619%。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发生时,大企业首先倒闭的原因。根据前述财务杠杆原理,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货币贬值带来出口收益减少,通过固定财务费用,使其投资收益呈加速数递减,资不抵债的企业只好宣布破产,而当破产企业无法归还他人的欠款(供应商等)时,本来尚能维持的企业,由于不良债权的影响,其经营也出现了危机。企业支付链条中断引起一连串反应,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财务基础,如韩国1997年底金融业坏帐比剧增,已占GDP的16%—18%,接近泰国20%的水平。 韩国最大的九家银行,其坏帐金额1998年初已高达其资本额的94%— 376%,这些银行实际已到了破产边缘。再来看外债问题,据韩国财政经济院统计,截至1997年9月底, 韩国外债总额为2270 亿美元, 在最近到期的就有400亿美元,可是其外汇存底仅223亿美元,到12月,外汇储备只剩下了73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在债务结构上韩、日两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当局更犯了“短借长贷”的大忌。如韩国在实行金融自由化后,许多投资金融公司都转变为综合金融公司。在增长神话的刺激下,它们大规模扩大海外营业,借进1个月到1年的短期外汇,然后以3至5年的长期贷款贷出,结果在起亚事件发生后,借进新的外汇资金十分困难,而贷方却不断收回短期贷款,从而将这些金融公司逼上了绝路。到1997年11月底,这些金融公司所掌握的200亿美元外汇资金中,有64.4%(129亿美元)为短期资金,但却把168亿美元(占资金总额的83.7 %)作为长期贷款贷出,在短借长贷的同时,这些公司还对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的“危险债券”进行巨额投资,平均每个公司投入高达4亿美元。 这种债务和投资结构若想维持,只能靠企业出口的高增长和投资的高回报,而由于今年以来大企业倒闭,“危险债券”大幅下跌,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等一连串打击,导致这些公司陷入了严重的外汇危机(注:参见《综合金融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何在》,韩国《朝鲜日报》1997年11月25日。)。可见,正是整个国家从产业到金融投资收益的下降,才通过高财务杠杆这一风险放大机制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从而才有了韩圆的大幅贬值,而内部和外部信用链条的中断最终引发了倒闭风潮。
总地看来,用综合财务杠杆原理可以较好地说明韩国(也包括东南亚)的危机为何呈现一种反馈式的放大状态。那么运用这一原理能否说明日本的金融机构倒闭风潮呢?日本不同于上述国家之处有三点。首先, 日本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到1997 年10 月底, 日本外汇储备已达2281.1亿美元);其次,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海外金融净资产高达一万多亿美元);第三,日本的经济不是“过热”而是“过凉”,泡沫破灭带来的不良债权的影响,问题严重(注:据大藏省1995年11月公布数字,日本不良债权总额为37.4万亿日元(日兴调查中心推算为55万亿日元,美国议会调查局推算为70—80万亿日元(转引自刘玉操《当前日本金融面临的问题探析》,《国际金融专题研究》1997年第5期,第29、24页)。)。第一点说明日本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仍然很强。据日本制造业1996年9月中期决算表明,制造业平均出口额占总产值的22.9%,比1996年增加2.7%,而其中精密机械行业达40%以上。 这说明企业不存在出口问题所带来的营业和财务风险,因而没有发生像韩国那样的大企业倒闭风潮。第二点说明从企业到国家,不存在对外的财务、债务风险。那么日本的金融倒闭风潮只能通过第三点来说明。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股价、地价高涨,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高利吸收存款,另一方面又将巨额资金投入房地产领域和股市,而从1990年金融、地产双泡沫破裂至今,日经225种股票价格指数已从1989年底的39000点暴跌到了1997年11月14日的14966.12点;从商业用地来看,仅大阪、东京两市的地价就比1990年分别下跌了40%和60%(注:转引自《当前日本金融面临的问题探析》,《国际金融专题研究》1997年第5期,第29页。)。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及证券业失血过多,手上持有的股票、地产价格只跌剩两至三成,大量的贷款被“套牢”,形成了呆帐。如果把银行看作一个经营货币商品的企业,那么这些巨额呆帐实际上就转化成为一种固定的财务费用(支付存款利息)。由于日本金融机构以相互控股作资产计算,有人估计,当日经平均指数跌至16000点,最大的20 间金融机构中,只有8间尚可符合国际规定的资本充足比率;当日经平均指数跌穿15000点,则仅余下两间。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经济低迷,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国内投资增长乏力,造成了不良债权无法通过产业投资来消化,而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房地产融资机构和依靠交易佣金生存的证券机构,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依赖政府和同业的“输血”(如政府动用财政和中央银行资金来消化“注专”的不良债权)。实际上早在危机爆发之前,金融界已是不堪重负了。从1991年东洋信用金库出现经营问题开始,到1996年11月大阪三福信用组合被清理为止,已有21家金融机构先后破产。由于日本金融界之间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关系(大银行与中小银行、银行与证券机构及其各自内部之间)存在“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整个信用链条已经相当脆弱时,东南亚和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成了最后一击。由于上述地区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贷款最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货币贬值、股市暴跌、企业倒闭会产生集中的支付危机,使金融机构的负担更为沉重。这时由于杠杆作用会导致资金周转失灵,从而触发了倒闭风潮。信心动摇和危机的加重,使政府已无力维护“二十家大银行不会倒闭”的神话,不得不最终放弃了消化不良债权的作法,这样长期积累的矛盾便“聚变”式地爆发了。
二、风险放大型的财务结构源自金融体制的缺陷
实际上在整个东亚国家,尤其是日、韩高负债型的企业财务结构是其特殊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而这种金融体制又是服务于政府的“赶超”意图,从而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美国《经济学家》评论说:“没有一个国家像韩国政府那样如此严重地干预银行业务,把银行视为政策工具之一,命令银行必须贷款给某些信用不佳的大财团和企业。”日本《时报》在谈到韩国银行体制“不透明性”时说:“政府高级官员直接参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活动……企业再把巨额利益输送给政府的这些高级官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管理金融”的弊端。
最大的弊端是金融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韩国,金融市场发育很不完善,股票市场规模很小,重要原因就在于韩国公司宁愿通过借贷而不是证券契约来获取资金,它们历来对和别人分享所有权犹豫不定,主要是害怕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被“他人”知晓。在日本,企业和银行的财务状况也是绝密情况,不仅自身隐匿实情,而且还得到政府支持。如山一证券的巨额帐外债务,大藏省早已知晓,却不向社会公布,甚至不向其他政府机构通报。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问题十分严重,而大藏省却一再宣称影响不大,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加上“捂”字为主的“鸵鸟政策”,导致了矛盾的累积。由于封闭和排他性,整个国家的财务系统处于不透明状态,监督机制流于形式(注:以美国为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货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总数,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分别达到3700人和2500人。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大藏省银行局的职员仅有131人,其中经验丰富者不过15人(参见马洪、 刘中一主编《中国发展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资金流向不明,乱帐坏帐叠出。长期以来,日本金融界丑闻不断,贷款过程中“走后门”现象屡见不鲜,往往涉及到政府官员。一些金融机构甚至同黑社会(如“总会屋”)勾结,出现了许多幕后贷款。韩国这种情况更为严重。90年代以前,为了高增长目标所需的资金支持,不问来源地鼓励储蓄,金融假名制的存在为各种违法和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假名制的存在还使信号失真,导致宏观调控的失灵。这种体制危害极大,比如偷漏税现象普遍,国家财政的不记帐交易可能达到30%以上;地下经济与高利贷盛行, 有人估计地下经济规模可能占国民收入的8—40%,这种体制还带来了众所周知的“韩国病”——即“政经勾结下的政治、企业和社会腐败”,政府为了获得经济和财政上的支持,就从政策上支持财阀,提供优惠贷款;反过来企业从互惠角度出发又为政府提供政治资金和个人贿赂,这成了政治腐败的根源。而政经勾结又反过来加强了财务系统的封闭与不透明性。实际上韩国早在1982年和1990年就曾两次想实行“金融实名制”,但终因阻力太大而作罢。金泳三上台后,于1993年8月12日发布“紧急命令”实行“实名制”, 力度不可谓不大,但阻力仍然不小。据韩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从8月12日到8月底,通过对韩国19家主要银行的私人帐号检查,发现实名帐户确认额仅占这些银行总额的38.8%,真名存款户头只占总帐号的16.9%,假名户头转为真名的仅占总数的9.8%。由此可见,韩国的财务、 金融系统之混乱状况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廉洁总统”金泳三的儿子,竟在韩宝事件中充当贷款“掮客”,这表明韩国的金融改革还远未完成。在此条件下,金融自由化的推行只能是“乱上加乱”,危机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韩金融体制的弊病还有诸多其他表现,如缺乏独立的中央银行监督系统,在日本,中央银行的人员任免受到大藏省的很大影响,实际也成了政府意图的实现者,不利于客观公正地监督整个金融运行,韩国中央银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日本;再如政府保护下竞争不充分而带来的效率问题等等。实际上我们透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体制的各种特点无不与这两国的发展模式和政府行为紧密相关,应该说这才是风险的最终来源。
三、发展战略、“政府替代”与金融体制
日、韩两国财务金融体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回顾历史,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追赶先进”的过程。早在60年代,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通过对东南欧国家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就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其工业化速度往往比发达国家快,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本国的剩余劳动力来“浓缩”工业化进程,日本在战后初期的起飞和韩国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得益于此。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起飞阶段正是西方的“黄金时代”,从而利用了庞大的国际市场。格氏的另一结论是,后进国家倾向于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工业组织结构,经济落后程度越高,政府作用就越大,银行作用也就越大,政府替代银行和企业职能程度也就越大。而日韩通过外向型战略,由政府制定发展计划,然后要求中央银行以统制方式提供资本动员,强制性“浓缩”工业化进程的作法似乎也正符合这种规律。
这种由政府推进的“浓缩型”经济增长,一方面为日、韩带来了骄人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却是以放慢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为代价的,而其中最为扭曲的就是金融制度。先来看日本,财阀的势力在美军占领期虽然被严重削弱,但直至今天仍有残余。金融业一方面服务于赶超战略,为大企业充当“护送船队”,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政策目标的推行导致金融机构的效益不高,而政府出于“培育”企业考虑,长期将金融机构视为“准公有机构”,并对国内金融予以封锁和保护。日本金融制度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和主银行制相结合,从而使信贷配给、关系融资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政府、银行与企业结成家庭,这是日本大企业高负债率的根源,这一方面为政经勾结和“幕后”行为提供了便利,同时又导致了银行对企业不良行为的纵容。就上市公司来说,如果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股价下跌,银行作为持股者必然蒙受更大损失,因而导致了在贷款企业出现种种问题,甚至陷入财务危机时,银行却往往对外隐瞒这些信息。即使在银企关系无法维持之时,按照惯例也会通过政府斡旋来得到同业“搭救”。这种救援机制使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和影响深广的银行,在局部周转不灵时得以渡过难关,从而令人产生日本大企业和银行不会倒闭的印象,这就造成企业放松风险自律,而银行又敢于进行风险投资或放出不良贷款,帐面上的高利润带来了股价上涨,其他银行又不惜风险购入上述有问题银行或企业的股票以求一搏,其结果必然是不良债权的累积与扩大,这样一旦发生全面的信用危机,救援机制也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韩国的金融制度形成于1961年军事政变之后,新政府准确地发现经济发展可以使政变合法化。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便承担起制定发展计划,实施对重点产业投资的职能,银行系统被严密控制起来了,1962年军政府修改了《韩国银行法》,将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同时通过没收“非法财富”把商业银行的很大一部分流动资金转到了政府手中。这种变革的实质是由政府完全掌握货币信贷政策,即所谓“开发金融”,实际上是用于控制企业的官办金融。到了70年代这种制度又有所强化。1972年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支持大企业,推行“抓大放小”。70年代早期的产业目标和1975年推行的综合商社制度,在10年内形成了一大批由家族所有的纵向联合企业(注:参见[韩]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版。)。为支持重点产业发展,70年代中还采取了“保险单贷款”制,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的信贷和外资配给,这种作法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了政府,当投资失败时,政府就向“不健康企业”输送救援贷款。这一系列作法一方面鼓励了政经勾结,另一方面又使企业不择手段地争取贷款,盲目地扩大规模。企业界普遍认为,企业越大,越能从政府获得优惠贷款的资本,贷款越多,越不可能倒闭。其结果使韩国大企业的负债率达到了绝无仅有的400%, 还带来了大集团之间的产业趋同和腕足式的无序扩张。由于银行被剥夺了风险鉴别、控制功能和放贷权,政府的上述作法必然造成不良贷款积压。但银行并不担心,他们从货币当局那里得到的实际是无限制的保证,由此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大额贷款人一直不能也不想偿还贷款,而银行又不敢宣布这些贷款为不良贷款,政府官员受贿后,把更多的贷款输入不健康企业,而企业却想通过借更多的钱而得到以后更多的贷款,企业向银行举债,银行又向国外举债,以债养债,整个经济陷入了投机活动的恶性循环之中,蓬勃增长的经济背后暗藏的这股潜流在90年代后半期终于以“突现”形式爆发了。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日、韩从内部爆发的危机反映的是高速增长时期累积下来的体制缺陷,因而实质上是经济体制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日、韩模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但此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日、韩经验的得失。其中迫切需要研究的有以下问题。第一,高负债率是导致此次日、韩乃至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高负债率问题目前也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大问题。负债率多大为好?两大银行体制在负债率高低上的不同对金融体制的不稳定究竟有多大影响?我国采取什么措施来降低负债率?此次金融危机说明了,从长期来看,健全的财务结构不仅对工商企业,而且对金融业,乃至一国的经济活动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第二,我国“抓大放小”与韩国70年代支持大企业的产业政策有何本质区别,我们是否能避免韩国私人家族企业控制下大企业所产生的弊端?我国企业规模小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措施促进企业规模的成长?如何促使大、中、小企业的均衡发展,产业政策如何制定?第三,我国“主办银行”改革与日本的主银行制有何区别?主银行制在支持日本高速成长时期功不可没,但其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了,成为此次危机的祸首之一。日本“金融大爆炸”式的改革会使其发生什么变化,经过此次危机如何评价其利弊?我国主办银行制度是否可行?对商业银行改革的意义究竟如何?是否会加剧目前的坏帐问题,导致金融市场割裂?主办银行制如可行与日本又有何不同,如何避免其弊端?如果放弃主办银行改革,我国银行体制又如何构建?拉柬及香港的肖耿对主办银行制持有异议,但日本的青木昌彦却认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效的选择,澄清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第四,金融改革深化任重而道远。日、韩迅速发展的经济掩盖了金融业严重落后之弊端,此次日、韩金融危机说明拖延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太大。金融市场割裂是此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日本且不说,韩国受控制的无主权的商业银行与规模相当可观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并存,不仅加大了企业的负债率,也使中小企业依赖在黑市上集资,风险加大不说,经营处境也很艰难。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状况表明,非正规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国家对它的监管又是最薄弱的,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我国金融改革深化意义非常重大。虽然我国金融业发展很快,但却有畸重畸轻、制度建设不够之弱点,我们应从此次日、韩危机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在以上诸多问题上,我国正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日韩的危机,来的可谓正是时候。警钟长鸣,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对体制的选择和未来的发展如履薄冰,需要多一些警惕,少一些乐观,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复杂和动态系统的角度,把握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旦一种体制和发展模式被选择,它自己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身惯性,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从这种体制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就会强化这种体制,以致于再改革,难度就很大。例如,韩国扶植大企业的改革形成于70年代初,70年代末即已认识到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开始逐渐取消这些政策,80年代中期试图抑制大企业的势力,但成效甚微,最后造成1997年以大企业连锁倒闭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韩国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建立起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符合长期发展要求的体制虽然决非易事,但我们无法避免这种历史的选择,重要的是不要锁定在既定的框框之中,如何从日韩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无疑对于我们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签:金融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经济杠杆论文; 资金杠杆论文; 杠杆交易论文; 金融杠杆论文; 日本银行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负债融资论文; 负债结构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杠杆原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ebit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