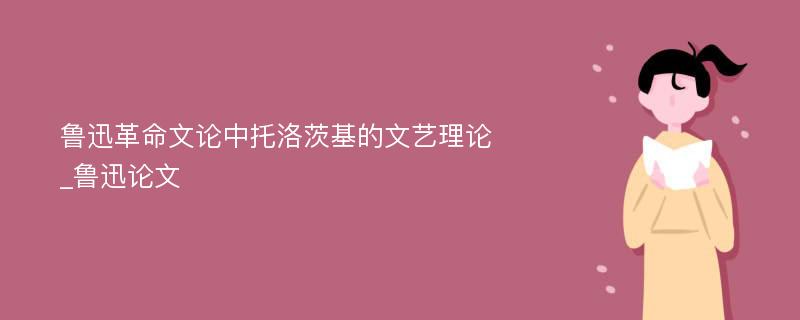
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鲁迅论文,文艺理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独特的表述有“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人“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以上两篇均于1927年发表,收入《而已集》)等。鲁迅的这种表述以及“革命人”一词本身,实际上来源于托洛茨基的著作《文学与革命》(日文版)①。在购买该书(1925年8月26日)②约半年后的1926年3月,鲁迅初次引用托洛茨基的观点写成《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收入《集外集拾遗》),如果把此文与《文学与革命》相对照,就可清楚鲁迅与其的关系。③以往还没有见到从积极的角度研究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的文章,不得不说这一课题受到了轻视。④但是,如果“革命人”的提法及其用语本身源于托洛茨基,那么就难以认为鲁迅革命文学论中与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相似仅仅是偶合,或者完全是鲁迅独自创建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本文暂且把焦点放在1927年前后的鲁迅革命文学论上,探讨其所受托洛茨基的影响。1927年,能够得到确认的鲁迅看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除了《文学与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⑤因此,这一时期的鲁迅革命文学论所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能以比较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前提下,也可以考察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对这一时期的鲁迅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从与“革命人”有关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来讨论。
一、《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与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
《革命时代的文学》是鲁迅在四·一二反共政变前夕的1927年4月8日,于黄埔军官学校所做的有名讲演。这里首先把讲演分为三段⑥,逐段论述与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关连。
1.《革命时代的文学》第一段研究
鲁迅首先从三种观点提出“文学无力说”。第一种观点,追溯讲演数年前他在北京的经历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所触发的如下感慨: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⑦
这就是面对权力(具体的武力、军事力)而言的“文学无力说”。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一版引言中有这样的话:
艺术的地位可以用下面一般的理论来决定。
假如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不曾创立自己的军队,劳动者国家许早就死了,那我们现在不会想着经济问题,更不会想着知识和文化问题了。(李霁野、韦素园译《文学与革命》,1928年“未名丛刊”之一)
据此推论,艺术的地位在军事之后。的确,把鲁迅前面的话与托洛茨基高度抽象的理论相比,可能会有无的放矢之感。但是,鲁迅于1926年3月10日写成《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引用托洛茨基的革命艺术论,论证孙文是永远的革命者⑧。八天后,眼见三·一八惨案发生而感到文学之无力的鲁迅,不能断言他此时没有想起《文学与革命》卷首第一行的这篇《引言》。
第二种观点应称之为“革命文学无力说”,可概括为对主张以文学推进革命的“革命文学者”的批判:
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⑨
《文学与革命》也主张,艺术家对于表现对象如果不是内在兴趣与精神的一致,就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⑩或者不应对艺术家下命令或强迫做某个题目。(11)而且鲁迅在1928年4月执笔《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收入《三闲集》)时写到“托罗兹基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包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12)这种文学不顾利害的主张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关联。
这一思想显然还与鲁迅1924年积极翻译介绍的厨川白村的文艺论相似,即“一受到功利思想的烦拢或心为善恶的批判所夺的时候,真的文艺就绝灭了”。(13)在强调文艺的独立性上,托洛茨基与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是共通的,二者对鲁迅的影响难以分清经纬。但是,附加了革命命题的还是托洛茨基。
第三种观点立足于革命与文学关系的直接考察。鲁迅主张不是文学影响革命,而“正是革命影响文章”。(14)这里,鲁迅的立论与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相关连,因此,根据《文学与革命》先简单概括一下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
革命时期,文学(艺术)沉默了。艺术是余裕的产物,因为革命时期已没有余裕。以无产者革命为例,革命中间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力和智慧主要倾注于政治方面,此时文艺领域革命的实现不得不作为例外。如果把革命艺术作为内在地表现革命的艺术,那么,使之成为可能的“革命人”忙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无暇创造革命艺术。因此,革命艺术的出现是在革命成功、社会出现余裕之后。而且,革命艺术之后能展望的不是无产阶级艺术,而是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艺术。因为,与革命前就掌握财富与文化的资产阶级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在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过渡期,必须从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中获取文化素养。这数十年间的过渡期,无产阶级还没能创造自己的阶级文化,社会已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旨在最终消灭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过渡期,解除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而代之以强化面向无产阶级社会的人类的联合。这样,无产阶级文化(艺术)不能成立,经过过渡时期的混和文化,可以展望社会主义艺术了。
一般认为,除无产阶级文化(艺术)否定论之外,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特征也可以说是以“革命艺术迟到论”这一独特的思想为其基调的,他的同路人作家论也是这一理论的必然归结。
那么,结合托洛茨基这一“革命艺术迟到论”,来解读鲁迅“正是革命影响文章”的主张,其逻辑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托洛茨基把革命时期的艺术分为单纯以革命为素材的艺术和革命艺术两种。前者由“同路人”来承担,从外部描写革命;后者由“革命人”负责,从内部来描写革命。于是,托洛茨基这样描述革命与革命文艺的关系:
诗的夜莺,像那智慧鸟——猫头鹰——一样,在日落之后才被人听闻。白昼是活动的时候、但是时至薄暮,感情和理智就要来估计已经成就的事。(15)
借猫头鹰来比喻艺术之神密涅瓦,欲言革命艺术在革命成功后安定的社会才会出现。从这种理论推论,革命艺术不会影响革命,相反,革命在使艺术窒息的意义上会影响艺术。如序言所提到的,鲁迅依据托洛茨基的理论创建了所谓“革命人”的思想,“革命人”之后提出的“正是革命影响文章”的论点,依据的也是托洛茨基的看法。托洛茨基还说:“艺术显出怕人的无力自持的样子,如在每一个大的时代的开端常显示的一样。”(16)
形成鲁迅“文学无力论”的三个观点中,至少第三种观点的中心思想与托洛茨基是相似的,由此可见其文艺理论的直接影响。回过头来看,实际上第一种观点也难以完全否定来自托洛茨基的影响。
2.《革命时代的文学》第二段研究
这里,鲁迅分革命前、革命中、革命成功后三阶段考察了革命对文学的影响。而后说,革命中,人们忙于革命没有文学,革命成功后,社会有了余裕,革命文学才会产生。这与上述托洛茨基的理论完全一致。关于“革命文学迟到论”的理论前提——文艺是余裕的产物这一命题,两人分别是这样讲的:
革命は潤沢と余裕とを必要とする(日文版《文学与革命·序言》)
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17)(《革命时代的文学》第三段)
显然,两人的基本思想具有共通性。(鲁迅认为革命前的文学是鸣不平、不满,这种论点在《文学与革命》中也有对应的说法)鲁迅把革命成功后出现的文学分为两种,一是讴歌旧社会灭亡的,二是凭吊旧社会崩坏的。而且说“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18),他认定第二种是逃亡外国的俄国作家的文学。关于第一种文学,则这样说道:
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19)
鲁迅把第一种文学分为高兴去破坏旧时代的“同路人”文学与讴歌新社会建设的“革命文学”,各自又与“怒吼时期”、“讴歌时期”的文学相对应。由此可见,鲁迅认为在苏联常常迟于革命到来的“革命艺术”已经出现了,苏维埃社会已到达了有余裕的阶段。可以说,《文学与革命》(1923年初版(20))认为革命艺术已有了萌芽但还未出现,而到1927年的鲁迅则向前一步,承认了苏维埃社会已有革命艺术的存在。
3.《革命时代的文学》第三段研究
鲁迅在第三段中预言革命后苏维埃文学的方向是“平民文学”,又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21)当时,所谓的“平民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相等的概念。鲁迅说: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22)
认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原因在于文学需要金钱与空闲。在这里又重复了鲁迅也是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艺术是余裕的产物”。鲁迅认为,中国既然还没有革命,平民没有解放,艺术的前提余裕还不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平民文学”。仅就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容易理解,但鲁迅说的是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世界”当然包括苏俄,可那里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革命。这里,如果不借助托洛茨基的话,就很难理解鲁迅的说法。(23)托洛茨基说:
革命艺术只能被劳动者所创造。这事是不真确的。正因为革命是劳动阶级的革命、它放开——重述以前已经说过者——很少的劳动阶级的精力,去从事艺术。(24)
而且,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假如可能有无产阶级艺术,那也是在迟于革命到来的革命艺术后才可展望的。因此,既然无产阶级为革命艺术只解放了一点点力量,那就还不到能谈论无产阶级艺术的阶段。在俄共党内主张这一理论的也是托洛茨基。(25)不得不承认,鲁迅的苏俄也不存在“平民文学”的认识仍然来源于托洛茨基。鲁迅谈及中国的文学状况时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26)托洛茨基认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有它的政治文化,在足够保持它的专政的限度内,但是它没有艺术的文化”。(27)因此,革命时期、过渡时期的文学不得不依赖“同路人”(读书人)。两人的认识互为响应。
进而,两人都没有把以下两种作品当作平民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即单纯以平民为素材来描述的作品和作者并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托洛茨基把文化定义为“知识与能力的有机的总和,它表现全社会的,或至少统治阶级的特性”,(28)认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的名,就是给予劳动阶级个人代表的最有价值的收获,也是太轻率了”。(29)而且说,所谓“无产者诗人”的作品“我们有天才的与能才的无产阶级者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30)可以认为,鲁迅所说的“平民文学”与托洛茨基基于其文化定义的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文学之“无产者文学”(以及“农民文学”)几乎是相同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20年代,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两人都不以素材及作家的阶级属性为断定是否“无产者文学”的基准,而是在全阶级真正的解放=阶级文化的确立这一地平线上来展望“无产者文学”的。
最后,来看讲演的结束部分:
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31)
这也可看作是鲁迅特有的自我韬晦的表现。但是,如果从鲁迅接受了革命时期艺术将沉默这一托洛茨基理论所强调的上面的文字,事情就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里反映了希望真正之革命到来的鲁迅内心的焦躁。这一部分,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或是韬略,或是讽刺,不允许夹杂诸如此类的主观因素,而应该看作是鲁迅考察文学与革命关系后得出的客观认识。如此,可以认为,鲁迅在把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当作自己经营文学之手段的同时,也以此作为批判中国状况的论据。
4.《革命文学》与托洛茨基文艺理论
《革命文学》是在《革命时代的文学》讲演半年之后,即1927年10月发表的。丸山升指出(32),鲁迅的意图在于批判反共政变后吴稚晖等国民党系“革命文学者”。不过,托洛茨基提出的“革命人”一词开始在这篇文章中出现,而且以托洛茨基的理论为中介,才会明白鲁迅为什么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到叶遂宁和梭波里。鲁迅说: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33)
革命中没有革命文学,反过来看鲁迅的这一理论就会变成革命文学(者)陆续出现的时代是没有革命的时代。在这里鲁迅也援引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以上,讨论了两篇有关“革命人”的文章。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对鲁迅的影响已显而易见。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很难说以往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因此,在下部分,我将继续分析1927年前后鲁迅的革命文学论。
二、1927年前后鲁迅革命文学论与托洛茨基文艺理论
1927年12月,鲁迅发表了以下3篇文章:《在钟楼上》(收入《三闲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收入《集外集》)、《文艺和革命》(收入《而已集》)。下面,笔者将对此进行逐一的考察。
1.《在钟楼上》中的《文学与革命》
《在钟楼上》发表于1927年12月17日《语丝》第4卷第1期。拉狄克有感于叶遂宁、梭波里的自杀,写了一篇文章,鲁迅的真意可能是要表达对这篇文章的感想。本来,应首先陈述鲁迅与托洛茨基对于“同路人”叶遂宁的同情,他们几乎同出一辙,令人吃惊。不过,论述两人在人品、文学方面的相同性,只能另文再谈。(34)在此,我只想把讨论集中在与《文学与革命》有关的部分。先从引用勃洛克的话来看吧。鲁迅在文章开头插了一段,说厦门时代他的朋友因写长信而被视为反革命,不禁失笑。接着,就引用了勃洛克下面一段话(引号内为勃洛克的话):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35)
引号内勃洛克的话与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第二章《革命文学的同伴者》(日文版同书第62页,李、韦译中文版69页)的引用部分完全一致。以下是茂森的译文,引号内的部分与鲁迅文中的引号部分相对应:
ナジェージュダ?パヴローウイツチの彼(ブロ一ク——長堀注)に關する思い出の中にこんな句がある、——「ボルシェウイキ一は詩を書く事を少しも妨げない。しかし彼等は自らを作家と感ずることを妨げている……その作家は自己の全創造力の流れを感じ、自己の中に韻律を持つ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在潘夫罗维奇(Nadezhda Pavlovich)所著的对于他(勃洛克——长堀注)的回忆中,有下面的句子:“布尔雪维克不阻止作诗,但是他们却阻止你觉得你是主人;觉得自己创造力的中枢,并在自己里面把持着韵律者,是一个主人。”
毫无疑问,鲁迅是从《文学与革命》转引的。从译文来看也不能说仅仅依据了茂森的译本。例如,茂森译的“作家”鲁迅译为“大作家”。仅从结论来看,鲁迅也参考了片上伸所著《文学评论》(36)以下的部分:
彼の女自身詩人で、晚年のブロクと同棲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るナデジュダ?パウロウイツチ女史の書いたブロクの思い出の記の中に、ブロクの言葉として、——「ボルシェウイキは詩を書くことを邪魔はしない、しかし自分が大家だと感ずることを妨げる……大家といぅのは、自分のすベての創造の核心を感覺し、自分のぅちに律を保持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といぅ文句がある。之はトロ一ツキ一が文學上の『革命の道づれ』を論じたもの(『文學と革命』—のぅち)の中に引いてあるのだが、……」《文学评论》所收《現實觀の動搖》)
巴比罗维奇自己是诗人,与晚年的勃洛克同居,她写的关于勃洛克的回忆录中写了勃洛克下面的话:“布尔什维克不妨碍写诗,但是,于觉得自己是大家有妨碍……所谓大家,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这些话,托洛茨基在论述文学上“革命的同路人”中引用过。……
鲁迅译文(37)的细微之处较之茂森的译本更与片上的译本接近。另外,鲁迅明确介绍引号内是勃洛克的话,而在茂森的译本中这是不明确的,也可以看作是巴比罗维奇的话。鲁迅1927年9月购买的英文版《文学与革命》(38)其情形也是一样的。只有片上明确断言那是勃洛克的话。据《鲁迅日记》所记,他购买《文学评论》是在1927年11月7日,而《在钟楼上》发表于同年12月17日。执笔日期不清楚,应是购买该书后马上或是稍后的事。也可以认为执笔写作《在钟楼上》时“想起”了勃洛克,或者依据片上译本的可能性很大,而并没有参考茂森的译本。不管怎样,鲁迅是据《文学与革命》而间接引用了勃洛克的话的,这一点当无异议。
鲁迅想“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认为“我不过说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39)照例援引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即文艺是余裕的产物。“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40)由此可以推断,鲁迅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时,脑海中出现的这个“人”的具体形象也是托洛茨基。
2.《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艺和革命》与“文艺先驱论”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是鲁迅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讲演。因为内容亦有关联,所以首先简述其标题取材于收入鹤见佑辅著《思想·山水·人物》(41)中的《文学与政治的歧路》。
据《鲁迅日记》及《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记载,鲁迅于1925年2月13日购买该书,同年4月14日起开始断断续续翻译并登在报纸、杂志上。1928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该译本的单行本。发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讲演的时候,鲁迅正在翻译鹤见书中《断想》一章,并在《北新》半月刊连载。这一时期,鲁迅当然看到了鹤见《文学与政治的歧路》一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与《文学与政治的歧路》,字面上相似,一目了然。顺带提一下,1928年2月暨南大学秋野社所刊《秋野》第3期上刊登的章铁民所录鲁迅演讲的标题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42)。而且,鹤见认为处在“无路可走之社会”的政治家“没有真正能施展文学才能的环境”(43),涉及政治与文学的矛盾。鲁迅在此次演讲中,则根据托洛茨基革命时代文艺将沉默的论题,论述了政治与文学的矛盾。两者的论点大致相同。鲁迅此次讲演的标题取自鹤见的这本书,这样判定当不会有错。
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首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对立。关于“革命”与“文艺”,则叙述了其共通性: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44)
接着,谈到政治以社会统一为第一,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且多样的思想所产生的文艺,会使社会分裂。在这一点上,鲁迅认为较之政治,革命与文艺更为接近。另外,“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45)鲁迅的这种文艺观与托洛茨基的如下记述也互为响应,即“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那些造成或经验这些事件的民众的生活”(日文版《文学与革命·序》第5页,中文版《引言》第5页)。可是,接下来所展开的是需要注意的“文艺先驱论”。
他(文艺家——长堀注)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46)
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47)
鲁迅的这种口吻似乎使人感到有其翻译厨川著作时受到的影响,但必须留意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时的鲁迅,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反复论述了革命艺术晚于革命(社会现实)的观点。因此,这里鲁迅的“文艺先驱论”就并非受厨川而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了。否定革命艺术先于革命的托洛茨基虽然也认为“诗人即预言者之论”,但与厨川“文学比政治之类先进一二十年也不足奇,有时还至于早五十年或一百年”(48)的无限乐观论不同,乃是控制在这样的命题范围之内,即“心都是在现实之后跛行的”(49)。
只有说诗人和先知是同样纡缓地去反映他的时代,传统上把诗人看同先知的说法才可以承受。假如有先知和诗人,可以说是“在他们时代的前面”,那就是因为他们不像他们的同类一样迟缓地表示出社会演进的某些种要求就是了。(50)
托洛茨基的意图是说,一个社会性的要求在成为整个社会的要求之前,诗人只不过稍先于他人而表现出来。换言之,在社会的一部分还没有成为问题时,诗人也不可能认识并表现它的。“革命所需要的观念学的前提,是在革命之前造成的,从革命得来的最重要的观念学的推论、在多时以后才出现。”(51)托洛茨基这些话也源于同样的思想。鲁迅在这里用的也是“不过”、“一点”,与托洛茨基同样是有限的“文艺先驱论”,这便与厨川的观点划开了界线。应该看到,鲁迅并不是积极主张文艺的先驱性,只不过是作为事实认识到了其有限的先驱性。否则,这一篇讲演就不会作为1927年前后一连串的鲁迅革命文学论的一环了吧。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半部分,我们放在后面讨论。先来看看这篇讲演三天后写就的《文艺和革命》,因为这是一篇集中论述“文艺先驱论”的小品文。
显然,在《文艺和革命》中,鲁迅的真意也在于批判四·一二后中国的状况。他用“文艺先驱否定论”来批判国民党系的“革命文学”。鲁迅说革命的先驱,一是革命军,二是人民代表,三是文学家。第三位的先驱当然就不是先驱了。的确,鲁迅后面马上举出了卢梭与珂罗连珂的名字,意在说明也许在中国以外的国家里“文艺先驱论”是成立的。但是,这里虽然倾向于“文艺先驱否定论”,可并未排除纯理论上的“文艺先驱论”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估计,也只是有限的“文艺先驱容忍论”。
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以及《文艺和革命》的一部分所看到的“文艺先驱论”,并不像厨川所认为的那样乐观而全面,倒是与托洛茨基的有限论相像,这样看当更符合鲁迅的一系列革命文学论。
3.《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与鲁迅“同路人”观
回到《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后半部分。这里,以下两个论点独具特色。
第一,依然是那个革命时期没有革命文学的观点:
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52)
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的关连,已如上所述。
第二,是叶遂宁、梭波里之死所象征的革命前之理想与革命后之现实相背离而引发的“同路人”的苦恼问题。关于这两人的自杀,鲁迅在1928年以后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可见对此相当的关心。这是鲁迅与勃洛克的相通且产生共鸣之处,同时也与他们都自称为“同路人”有关。我不知道鲁迅在哪篇文章中宣称自己是“同路人”,这里依据的是增田涉、竹内好两人的证言及记述。(53)但是,即使鲁迅没留下自认是“同路人”的文章,也不足为怪。因为,说起来构成“同路人作家论”的是来自革命家的定位,而不会是作家自己声称自己为“同路人”的。鲁迅在《〈竖琴〉前记》(1932年9月9日作,收入《南腔北调集》)中曾介绍“同路人”之称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并定义如下:
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54)
从这样的理解来看,“同路人”一方面是不会有彻底革命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傲慢地宣扬与革命同行的英雄主义。那么,鲁迅对可以无所不谈的外国青年增田涉谈到这样的认识,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相关的词句,也并非不可思议。
在这篇讲演中,鲁迅还说道:
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社会)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55)(括号内为长堀所加)
也就是说,所谓“同路人”不外是一边被燃烧着自己的身体,一边也深深地感受着社会的存在而参与其中去的人。在这一部分的后面,鲁迅把等待同伴者的悲剧其原因归结为“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一“注定的运命”(56)。如果没有革命,理想就会依然那样地存在着,而有了革命,理想反倒会因与现实的背离而破灭。叶遂宁、梭勃里“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57)结尾部分鲁迅说的这些话,等于证明了当时革命已经存在。而希望中国发生真正革命的鲁迅,则已然觉悟到若希望得以实现,那时自己也将接受“同路人”这种悲剧性的命运。仿佛说给自己听一样,他谈到了叶遂宁的死,这也显示了他希求革命的程度。
直到1930年代初,鲁迅都将自己规定为“同路人”。比如,关于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说“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58)另外,针对有人讽刺他是被人踩踏的梯子的社会舆论,鲁迅说:“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59)他在回忆革命文学论战的时候又说:“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60)的确,这是一种不为革命而彻底战斗,充其量希望与革命同行的“同路人”的态度。这一时期的鲁迅,几次提及叶遂宁、梭波里。如果不考察他自认是“同伴者”的这一自我认识,就不可推测其分量与意义。而且,所谓“同路人”,如鲁迅在《〈竖琴〉前记》中所说,是托洛茨基的用语。(61)
关于1927年前后鲁迅革命文学论的探讨,就到此为止。最后看一下竹内实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评论:
11月在苏联,发生了托洛茨基被除名事件,我想鲁迅已经知道了。(62)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钟楼上》以后鲁迅革命文学论中所见托洛茨基的影子,则会多少增加些分量的。这意味着,托洛茨基虽被除名,但鲁迅仍认为他的理论是有效的。
三、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于鲁迅的意义
1927年鲁迅革命文学论中所见到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影子在1928年以后的著作中依然存在,直到1932年,他还曾提到过托洛茨基以及“同路人”作家的论说。(63)关于1928年到1932年这段时期所涉及的托洛茨基及“同路人”作家论的问题,将作另文探讨。本文考察1926-1932年这段时间鲁迅援用托洛茨基的情况,包括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对鲁迅具有怎样的意义。在此,笔者将以第二章第三部分所述的鲁迅“同路人”观为前提,通过比较其与有岛武郎的文学观、革命观以及对现实(革命)的态度,来明确其意义。因为,有岛与鲁迅是同时代人且资质也相通的作家,鲁迅翻译有岛作品时,正是他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时期,从两位文学家所选择的道路之不同,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于鲁迅的意义。
1.关于鲁迅对有岛武郎作品的翻译
在1923年出版的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64)所附《关于作者的说明》中,鲁迅通过翻译其作品《四件事》(65),介绍了有岛武郎的创作态度。文中认为有岛的创作动机在于“寂寞”和“爱”。鲁迅还说: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创作总根于爱。(66)(《小杂感》,写于1927年9月,收入《而已集》)
在《生艺术之胎》(67)中,有岛武郎也强调了相同的内容,鲁迅也曾翻译过此文(1926年5月)。可以说,有岛基于“爱”的创作论给这一时期的人类主义者鲁迅(68)以强烈的印象。
革命文学论战初期,鲁迅还翻译并发表了有岛的另外两篇作品《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69)(1928年1月)与《伊孛生的工作态度》(70)(同年8月)。前一篇是论述易卜生最后的戏剧《死人复活时》的小品,作为艺术家的态度问题,有岛提出了美与爱的矛盾问题。这篇作品同时具有“为艺术之艺术”与“为人生之艺术”两种倾向,对鲁迅来说无疑意味深远。后一篇赞扬了易卜生在文学上的苦斗。自“五四”以来一直关心易卜生的鲁迅,无疑是对有岛的评价产生共鸣,才把它们翻译出来的。
仅从以上极为粗略的概述,也可以看出鲁迅与有岛武郎在文学观上的共通性。接下来,围绕《宣言一篇》的问题,来比较两位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只限于对革命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的方面)。
2.《宣言一篇》(71)与阶级转变问题
如标题所示,《宣言一篇》是有岛武郎发表于1922年的论战宣言。在俄国革命等的影响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大逆事件”以来的“冬季”,再次迎来高涨期。1920年代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1922年,日本共产党秘密结成。《宣言一篇》就是有岛对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文学领域无产者文学主张的一种表态。在一系列论争中,他的基本立足点是承认无产阶级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自己属于不同的阶级,不能与无产阶级站在同一立场上参与其运动和文学(有岛不相信阶级的转变,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时,他也曾拒绝参加)。但是,有岛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也没有停留于这样的客观认识上。他愿意积极地接受意味着自己所属阶级将没落的无产阶级的胜利,而且说他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使非无产阶级者认识、觉悟并接受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然性。有岛所依据的大概是确信无产阶级革命将自然发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对于有岛武郎的这种主张,片上伸、广津和郎、堺利彦、河上肇等都给予了批评,可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在1923年6月选择了自杀之路。有岛实践了所谓的“生活革命”,他欲率先体现自己阶级的没落,似乎已经以自己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勇猛的革命思想家”(72)有岛武郎直到最后仍拘泥于自己的知识阶级出身,不曾承认阶级转变论,结果走上了自杀的道路。1961年丸山升已经指出,革命文学论战时期的鲁迅也与有岛这种态度相通的地方:
鲁迅凝视着自己在内的既成文学家站立在人民立场的可能性近乎无望这一困难,从而批判提倡“为革命的文学”过于浅薄。更确切地说,他是从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坚持尖锐地批判专制君主制的托尔斯泰(73),以及因革命不得不自杀的俄国同伴作家们的生存状态,看到文学家是如何发挥主体性与革命相结合的。……因此从这一立场来看,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当然会引起鲁迅相当强烈的共鸣。(《鲁迅与〈宣言一篇〉》,载中国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研究》,1961年4月第1号)
可以说,鲁迅与有岛不仅文学观,而且在革命观上也有共通之处。
3.“同路人”作家论之于鲁迅的意义
正如日本的现实迫使有岛武郎形成这样的态度,中国的现实逼使鲁迅接受了文学与革命的问题。但是,两者虽有着共通的文学观与革命观,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外在的原因当然在于日本与中国在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
有岛武郎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有自己阶级的基础,但同时,这一阶级对他来说也是思想上、感情上的敌人。有岛否定阶级转变论,考虑到知识阶级与无产阶级没有联合的可能,而说“我对于自己的阶级只能自唱挽歌”(74),并切实以自杀奏响了“挽歌”。说得极端一点,对有岛而言,他所面临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下面临国家生死存亡危机的中国,于讨论阶级转变问题之前,迫切要求知识阶级也参加战斗(鲁迅把阶级转变作为问题是在此后的阶段即如何好好战斗的阶段)。对鲁迅来说,民族解放斗争本身首先是当然的前提,眼前的敌人无疑首先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内势力。
引起两人走向不同道路的内在因素之一,是“同路人”作家论。鲁迅认识到他自己骨髓里是一个知识分子,与有岛武郎一样,虽承认第四阶级的未来,但并没有轻易相信阶级转变论,而目前中国的现实使其不得不与第四阶级联合战斗。填补其空隙的理论就是“同路人”作家论。托洛茨基从考察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而得出的这一理论,在一个时期里被用于革命俄国的文艺政策。可以说,给鲁迅指出活着为自己的阶级奏响挽歌而又能走向革命道路的,就是被俄国革命现实所证明的“同路人”作家论。从1927年前后起,他就较深地介入到了文学与革命的问题中。这一时期,他已经翻译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亚历山大·勃洛克》(75)一章,而熟悉了这一理论。之后直到1930年代初,鲁迅不断提及托洛茨基与“同路人”作家论,很可能他根据这一理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他并没有片面地翻译介绍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就是有力的佐证吧。
另外,有岛武郎在否定阶级转变的可能性之后,没有可以使其有机会摸索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的理论、组织、运动做参考。与其说没有“同路人”作家论(76),倒不如说没有如鲁迅那样可以成为其自己存在之否定性(在为所属阶级奏响挽歌而又参加革命这一意义上)根据的理论。有岛的批判者们没能给他提供那样的理论。
由此看来,托洛茨基对于鲁迅的意义是以“同路人”作家论为轴心的。而且,由此可以得出与以往不同的鲁迅理解,也就是“同路人鲁迅”。竹内好曾提出“启蒙者鲁迅”与“文学者鲁迅”的图式,后来,丸山升用“革命人鲁迅”扬弃了竹内鲁迅像中的政治与文学的对立(77)。然而,“革命人鲁迅”尽管作为瞿秋白、毛泽东从重视鲁迅革命一面的立场而提出的历史性客观评价是妥当的,但与这一时期鲁迅的自我认识相背离。至少从1920年代后半期到1930年代初期,还是“同路人鲁迅”更符合实际以及鲁迅对“同路人”的理解。说起来,丸山升讲“革命人鲁迅”时的“革命人”形象,与鲁迅自己所谓的“革命人”相重合,它来源于托洛茨基,可以说是鲁迅的理想。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鲁迅曾自比为托洛茨基所说的“革命人”。加之,否定革命时期革命文学的可能性并由此得出“同路人”作家论的托洛茨基文艺观,给予这一时期的鲁迅及其革命文学论以相当根本的影响,而且根据“同路人”作家论鲁迅暗自承认自己是“同路人”等等,如果考虑到上述拙论中已阐述过的情况,那么“同路人鲁迅”自然而然地将会成为焦点而确立起来。这一鲁迅像未必完全扬弃了政治与文学的对立,它不是政治性地掩饰革命与文学的矛盾,而是在承认矛盾的存在同时革命性地统一起来并体现于矛盾之中(是“同路人”作家论使其成为可能的),可以说这一鲁迅像是在鲁迅生存的时代中得以把握到的形象。而且,这个“同路人鲁迅”的说法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冯雪峰在与鲁迅相熟之前参与翻译的托洛茨基中文版《文学与革命》出版后(78)的1928年5月提出的(79),虽然后来他又撤消了此种说法(80)。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对《革命与知识阶级》表示了不满,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也否定了“同路人”的定位。
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及其文艺理论,尽管否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但如鲁迅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它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优秀的精华之一,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可以预期,通过引入托洛茨基的这一文艺理论,可以把对鲁迅的讨论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鲁迅的政治与文学或者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等问题,将会更加清晰明朗起来。
而且,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意义并不只限于鲁迅研究的领域。托洛茨基主张文学作品有批判的自由,强调作家在支持革命的前提下其内心精神自由的重要性,斥责党对文艺的过渡干涉。回顾苏联与中国有良心的作家们长期苦斗的历史,听到他们在公开化与开放政策下的发言时,更觉得托洛茨基的主张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1988年 初稿
2010年12月 改稿
作者按:该稿的日文版曾刊载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集(1988年10月)。中文版除删掉日文版的补注外,还补充了若干注释。本稿引用鲁迅原文依据《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
①茂森唯士译,日本:改造社,1925年版。以下有关《文学与革命》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中文则根据李霁野、韦素园译《文学与革命》。
②《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625页。
③拙稿《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日本:《猫头鹰》,1987年9月第6号。中文版见《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④1987年1月以后,看到以下两篇相关的中文论文:一丁:《鲁迅与托洛茨基》,《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巴黎: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87年版;迟玉彬:《鲁迅与托洛茨基》,北京:《鲁迅研究》第1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总之,中国国内发表的论文,经常感到有这种倾向存在,即从托洛茨基即是反革命这一斯大林主义的大前提出发来限定乃至缩小托洛茨基对于鲁迅的意义。另一方面,上述一丁的论文与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香港周纪行出版1977年版)认为鲁迅是亲托洛茨基的,非常反感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内容及毛泽东对鲁迅的绝对赞扬,而对托洛茨基对于鲁迅的影响却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
⑤这一时期鲁迅可能看过卢那察尔斯基的两本书,即《新艺术论》(茂森唯士译,日本:至上社,1925年版)、《实证美学的基础》(马场哲哉译,日本:人文会出版部,1926年版),但这两本书的内容以及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鲁迅在1927年之前的著作中没有提及,因而忽略不计。
⑥《鲁迅全集》第3卷收入该文的从开篇到第419页第1行为第一段,到第421页第19行为第二段。
⑦《鲁迅全集》第3卷,第417页。
⑧托洛茨基的“永久(续)革命论”与鲁迅在这里用的或一般常被引用的“永久革命者”,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词。
⑨《鲁迅全集》第3卷,第418页。
⑩《文学与革命》第31页,中文版第40-41页。
(11)《文学与革命》第226-227页,中文版225页。
(12)《鲁迅全集》第4卷,第112页。
(13)厨川白村:《走出象牙之塔》,《厨川白村全集》第3卷,日本:改造社,1929年版,第76页。此处使用鲁迅自己的译文。《鲁迅全集》第13卷,1973年版,第231-232页。
(14)《鲁迅全集》第3卷,第418页。
(15)《文学与革命》第1页,中文版第14页。
(16)《文学与革命》第7页,中文版第19页。
(17)《鲁迅全集》第3卷,第423页。
(18)同上,第421页。
(19)同上。
(20)指俄文原版。
(21)《鲁迅全集》第3卷,第421页。
(22)同上,第422页。
(23)注4的迟玉彬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24)《文学与革命》第293-294页,中文版286-287页。
(25)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日本:南宋书院,1927年版。
(26)《鲁迅全集》第3卷,第422页。
(27)《文学与革命》第273-274页,中文版269页。
(28)《文学与革命》第268-269页,中文版264-265页。
(29)同上。
(30)同上。
(31)《鲁迅全集》第3卷,第423页。
(32)丸山升:《鲁迅与革命文学》,日本:纪伊国屋书店,1972年版。
(33)《鲁迅全集》第3卷,第544页。
(34)例如托洛茨基:《为了已故的塞尔该·叶遂宁》,《革命的想像力-托洛茨基艺术论》,金井毅译,日本:拓植书房,1978年版。
(35)《鲁迅全集》第4卷,第29-30页。应该注意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政客的论断,当时国民党也主张他们是“革命”。参见注32丸山升的著作。
(36)日本:新潮社,1926年版。
(37)《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里没有她回忆录的中译本。可以认为是鲁迅自己从日文翻译的。
(38)《鲁迅日记》1927年9月11日。参看英文版《文学与革命》第58页(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5,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25)。
(39)《鲁迅全集》第4卷,第30页。
(40)同上,第35页。
(41)大日本雄辩会,1924年版。
(42)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翻译出版了鹤见这本书,但没收录该篇。
(43)《思想·山水·人物》,第247页。
(44)《鲁迅全集》第7卷,第113页。
(45)同上,第115页。
(46)同上,第116页。
(47)同上,第117页。
(48)《走出象牙之塔》,第164页。《鲁迅全集》第13卷,1973年版,第323页。这里使用鲁迅的译文。
(49)《文学与革命》第1页,中文版第14页。
(50)同上,第2页,中文版第14页。
(51)同上,第209页,中文版第211页。
(52)《鲁迅全集》第7卷,第117页。
(53)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日本:角川书店版,1970年版,第62页;竹内好:《文化移入的方法》,《竹内好全集》第4卷,日本:筑摩书房,1980年版,第118页。鲁迅确实没有说过自己是同路人作家。
(54)《鲁迅全集》第4卷,第434页。
(55)《鲁迅全集》第7卷,第118页。
(56)同上,第119页。
(57)同上。
(58)《鲁迅全集》第4卷,第209页。
(59)《鲁迅全集》第12卷,第8页。
(60)《鲁迅全集》第4卷,第236页。
(61)顺便一提,黄继持在《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香港:《抖擞》,1981年9月号)中认为,用“同路人”而非“同伴者”译语的,最初似乎是鲁迅。
(62)《资料世界无产者文学运动》第2卷,日本:三一书房,1973年版,第241页。《申报》1927年12月20日报道《俄共党对反对党之议决案》:“路透社18日莫斯科电共产党在此开大会,已通过驱逐反对党领袖特罗资基、凯米尼夫、赖柯夫斯基等七十五人,而萨卜罗诺夫党员二十三人亦被消除共产党籍。”鲁迅的演讲《文艺与政治之歧途》就是作于这篇报道的第二天。鲁迅至少这时应该知道托洛茨基被苏共开除的情况。
(63)一般认为,1931、32年后鲁迅从对“同伴者作家论”在中国之有效性的怀疑,进而转变了“同伴者”的自我规定,同时,随着与瞿秋白的交往以及第三种人论争的展开,而改变了肯定性的托洛茨基观。参见拙稿《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中国文学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1987年12月号。中文版见《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6期。
(64)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65)收入《有岛武郎全集》第7卷,日本:筑摩书房,1979年版。
(66)《全集》第3卷,532页。另外,关于这一问题,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曾指出过。
(67)收入《有岛武郎全集》第7卷。
(68)藤井省三:《〈故乡〉的风景》,日本:平凡社,1986年版。
(69)收入《有岛武郎全集》第8卷。
(70)同上。
(71)收入《有岛武郎全集》第9卷。另外,关于本节的有岛以及围绕《宣言一篇》的争论及文学史问题,依据平野谦编《现代日本文学论争史》上卷(日本:未来社,1956年版)、《日本现代文学全集别卷日本现代文学史(二)》(日本:讲谈社,1979年版)所收久保田正文:《大正文学史》、《现代日本文学大系第35卷有岛武郎集》(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版)卷末解说等。
(72)厨川白村:《有岛的最后》,《来往于十字街头》,日本:福永书店,1923年版,第173页。
(73)鲁迅这种托尔斯泰观(这大概与鲁迅的自我认识也有关)与托洛茨基也有共通之处。
(74)《想片》,《有岛武郎全集》第9卷,49页。
(75)据《鲁迅著译年表》,翻译该篇是在1926年7月。
(76)《文学与革命》俄文初版于1923年秋,有岛不可能知道同伴者作家论。即使能知道,他有伦理性的洁癖症,是否能接受还是个疑问。
(77)伊藤虎丸:《鲁迅与终结论》,日本:龙溪书舍,1975年版。
(78)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冯雪峰论文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从本文依据托洛茨基的理论及前后文关系可知,冯所用“追随者”一词即“同伴者”之意。
(79)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能发现冯用的“追随者”意味着“同路人”。
(80)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冯在该书中说鲁迅对《革命与知识阶级》表示了不满,但这并不等于鲁迅也否定了对“同伴者”的定位。
标签:鲁迅论文; 文艺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革命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