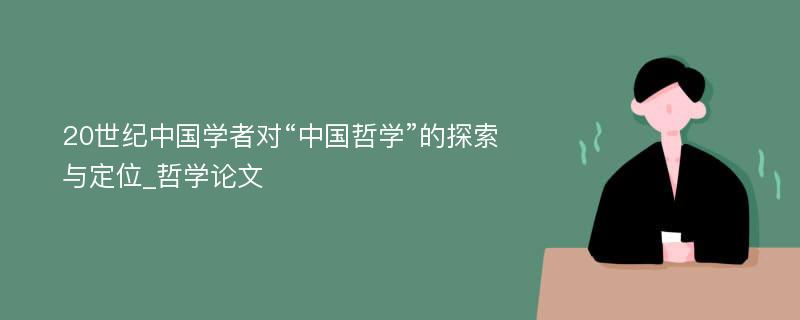
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对于“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人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从势所必然到理有必至
清末日人造“哲学”一词以翻译西方之philosophy,① 其词传入中国后,中国思想界随即有“中国哲学”一概念的提出,及后更演为一门崭新学科。到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已逾一个世纪。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的出现实为中国旧有学术观念的解体并代之以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结果。必须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旧有的学术若不能重新装置于现代西方学术的框架内,则只有随着传统文化的失序而式微。经学的衰落则是典例。用传统的话说,这是势所必然者。但倘使我们仅从势的一面着眼,自难免觉得旧酒之必须装以新瓶并不意味旧酒味酸注于新瓶始能救之,此中似无必至之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尝比较撰作“中国哲学史”与“西洋义理之学史”的可能,其言正隐约表现出这种理无必至的感觉。他说: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②
实则理有无必至的问题应分两方面来看:一是传统学术的衰落,一是新兴学术的出现。前者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未易遽下断语,且亦非本文所要讨论者。但后者却与本文的讨论直接相关。中国哲学的出现固是历史形势所使然,但它本身存在的理由、价值与意义则须另作安顿。借用劳思光对“发生历程”与“内含品质”的区别,③ 我们绝不应将对中国哲学出现的历史解释与对其内容特性的测定混为一谈。显而易见,我们只有将眼光从势所必然转至理有必至,从发生历程转至内含品质,才能真正展开对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定位。
但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似乎仍是众说纷纭。或谓中国有自己一套的哲学,凡说中国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的哲学性不够,皆是昧于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完全无视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或谓中国过去有无哲学并非关键的问题,盖哲学之反省方法乃人类思想的公器,没有理由说它不能用来处理中国的思想,故重要者乃在于处理后中国究竟有无好的哲学。近时更有学者提出中国哲学的研究有偏重文献方法与偏重哲学方法的不同趋向。这些纷纭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要将其中的道理解说清楚,并求能比较评论彼此的得失,则必有待于论者进一步反省厘清其所使用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哲学”这些概念的意谓为何。劳思光说得好:
但当我们想将“中国哲学”当作“哲学”来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必须对于自己的主张所依的理据有一定程度的自觉;究竟我们主张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呢?为甚么要持这样的主张呢?回答这些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对哲学的功能如何了解的问题,也牵涉到我们对“哲学”这个词语如何使用的问题。④
换一个角度看,论者的中国哲学观其实正是他们对传统思想、西方哲学以及哲学这三方面所作的相互理解的结果。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可能引起的误解,则迄今为止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仍言人人殊绝不表示过去的研究者对自己主张所依的理据都缺乏自觉。相反,我们只要检读一下20世纪用心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的文字,便不难看到发乎真诚的探索清晰可见。⑤ 问题只在于这些探索与定位中国哲学的努力并未受到恰如其分的关注。此盖凡学人自觉对其所意谓的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提出理据时,此理据实际上即同时成为此学人的一种哲学观点。于是,人易以一家之言视之,而反不见其本为对中国哲学本身的探索。结果自亦缺乏总结这些探索的文字。当然,研究者皆有权力选定他的研究取向,我们不必亦不可能达到一种关于中国哲学的统一定义。但假若连最基本的共识都阙如,则恐将大不利于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此所以清理前辈学人探索定位的工作,指出其中牵涉的各种问题,思考已有答案的理据,评论个中的得失,适足以使后来者避免重蹈无谓的争论,而能更自觉其主张背后的种种理据,并时与别人之见互相观摩。久乎辩驳竞胜、激浊扬清,则学人关心的问题及研究的结论虽仍尽可不同,但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则必会形成某种对“中国哲学”此一概念、学科的共同认识与方向,引领中国哲学的研究于21世纪更上层楼。在这个意义下,本文清理20世纪中国学人对于“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定位便只能算是个初步的尝试,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希望的只是不自量力的抛砖最后能引出有心人的美玉。⑥
扼要来说,20世纪中国学人对于“中国哲学”的探索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格义时期;(二)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三)对中国哲学底特殊性的探求;(四)统摄性“哲学”概念的建立。⑦ 以下即就此四阶段分别作一考察。
二、格义时期
稍涉猎过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魏晋时代中国思想界最初是借着所谓“格义”的方式来了解吸收传入的佛教思想。如以道家的“无”来比附佛家的“空”。这种格义方式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面对“哲学”这一新概念时亦曾一度发挥作用。此即径直以传统的道术、理学等观念解释哲学。王国维在1903年发表的《哲学辨惑》中说:“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⑧。1913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诸子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两门课的陈黻宸在他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亦写道:“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⑨。于是他的诸子哲学主要是解说《老》、《庄》,中国哲学史则自伏羲讲至姜太公。以现在的理解水平言,这些看法当然失之错陋,但这却是当时学人极其视域所能达至的理解。须知能格义者亦必已粗涉西学而绝非固步自封之徒所可为。然既囿于所知之限,则于附会之余难免心存疑惑,下面一段陈黻宸的文字正生动地说明了这点:
瀛海中通,欧学东渐,物质文明,让彼先觉。形上之学,宁惟我后,数典或忘,自叛厥祖。辗转相附,窃彼美名,谓爱谓智,乃以哲称。按《尔雅》云:“哲,智也。”杨子云:“《方言》亦曰:‘哲,智也。’”我又安知古中国神圣相传之学,果能以智之一义尽之欤?虽然,智者,人之所以为知也。人之有知,自有生以来非一日矣。其所以为学者,我无以名之,强而名之曰哲学。然则中国哲学史之作,或亦好学深思者之所乐于从事者欤!后必有能正其谬者。是篇也,讲义之云尔,史云乎哉!史云乎哉!(《中国哲学史》,第414页)
此处以西学所先觉者为物质文明,而谓彼之形上学则逊于中国,正清楚透露出陈氏对西方哲学缺乏认识。但碍于形势又不得不窃彼哲学之美名,故难免有“安知古中国神圣相传之学,果能以智之一义尽之欤”的疑问。故对于自己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陈氏遂谓“是篇也,讲义之云尔”,而有待“后必有能正其谬者”。
又陈氏后必有乐于作中国哲学史者的预言并未落空。因为假若中国哲学只是旧学的变换名目,则根本无法消融西学的冲击。可知思想界之不能久安于格义阶段而必有谋为中国哲学正名之要求。而一个自然不过的发展方向乃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定义哲学,并以此规定界划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哲学”一词的使用本身亦早已透露出其不能免于受西方观念影响的消息。其具体的结果则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现。
三、以西方哲学为参照
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得失,近人已有不少的评论。如金岳霖谓其是以一种成见来写的中国哲学史,故缺乏对古人思想的同情了解。⑩ 劳思光评其为“全未接触到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并且几乎未接触到任何哲学问题”(11)。但无论如何,大家都愿意承认胡书有开风气之功。此所谓开创新纪元之功,主要应是指胡氏能突破格义,正式援用西方哲学为参照来重新界划中国哲学的研究。他在〈导言〉中定义哲学为:“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他继而把哲学的门类分为: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又接着大谈世界上的哲学概分为东西两支的发展,由此以定“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12)。胡氏以这样富于系统的西方参照来写中国哲学史,自非格义阶段的理解所可比拟。这也是为何蔡元培在为胡书写的序言中,会盛赞是书解决了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形式问题的困难。因古无哲学之名,“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中国哲学史大纲》,〈序〉,第1页)当然,今天我们尽可以质疑胡适对哲学的定义太宽泛,门类的区分不全面,所谓世界哲学两支发展的说法亦多可商榷。但他最大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以为一经援引西方哲学为参照,中国哲学的涵义就自然清晰明白。事实上,冯友兰在这方面的思考比胡适仔细得多。他虽然也是依傍西方哲学来规定中国哲学,但其较细密的反省却充分暴露出以西方哲学来界划中国哲学这一构想背后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而冯氏之想得更透彻,又正可见出其无论在西洋哲学或传统思想上的造诣均有过于胡氏之处。
在《中国哲学史》的卷首,冯友兰开宗明义地表示是书之作乃是参照西方哲学为标准来界划中国哲学的研究。他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第1页)
冯氏继而以内容来定义哲学,分哲学为三大部:宇宙论(中复可再分为本体论与宇宙论)、人生论(中复可再分为心理学与伦理学)、知识论(中复可再分为知识论与论理学)。这种参照西方的做法,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效用,就是能建立一个标准来决定旧有材料中哪些可以归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其言曰:
哲学一名词,中国本来无有;一般人对哲学之范围及内容,无明确的观念,几以为凡立言有近于旧所谓“经”“子”者,皆可谓哲学史之材料。但依以上所说,吾人对于哲学之内容,既已有明确的观念,则吾人作哲学史于选取史料,当亦有一定的标准。(同上书,第25页)
是以“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同上书,第7页)而传统的兵家书则顺理成章地被驱逐出中国哲学的研究外。(同上书,第27页)仅就厘清确定研究范围这一点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是有必要的。问题只在于参照后是否需要作出调整,并进而为此调整提出理据。一成不变的生搬硬套将出现不少困难。事实上,冯氏自己也注意到在所谓“约略相当”的背后,中国哲学不以知识问题为哲学中的重要问题;逻辑不发达;宇宙论的研究亦甚简略。更严重的是,中国哲学讲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其中特重的修养工夫却在西方哲学的架构中找不到适当的对应,故“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虽则冯氏知道“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同上书,第10—11页)。结果,他在哲学史中也不能持守自己定下的准则而对中国传统的工夫论着墨甚多。
尤有进者,当我们从内容转至方法来看西方哲学这个参照时,困难就更加明显。冯先生十分强调哲学方法是必须讲求论证的,这与直觉之能得到一种经验应严加区别。他说:
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荀子所谓“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是也。孟子曰:“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辩即以论证攻击他人之非,证明自己之是;因明家所谓显正摧邪是也。非惟孟子好辩,即欲超过辩之〈齐物论〉作者,亦须大辩以示不辩之是。盖欲立一哲学的道理以主张一事,与实行一事不同。实行不辩,则缄默即可;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者。(同上书,第6页)
冯氏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仍坚持哲学方法乃“理论思维”。(13) 假若我们将此理论思维视为哲学的本质特性(essential characteristic),并与其所研讨的内容不可分割地构成哲学之所以为哲学者。则持之以视中国传统思想,前述所谓约略相当便顿成疑问。盖冯氏亦知建构理论,“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痗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书,比较少数”。(《中国哲学史》,第9页)大多数著述皆为杂凑学人平日的书札语录而成,“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之简略零碎”。(同上书,第6页)冯氏解决这个中国哲学在形式方法上不合乎普遍哲学的困难的方法(14),乃提倡取法西哲,替中国哲学底“实质上的系统”“讲”出和“补”出其“形式上的系统”。只有这样借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来适当地“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参看《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35—39页)研究者始能“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中国哲学史》,第13—14页)自冯氏悬此讲出和补充形式系统以揭示实质系统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任务后,几成研究者的共识。冯先生这种主张本身并不错,问题是他在这里并未进一步追问中国传统思想重实行轻思辨的缘故。中国古代学人视著述建构理论为不得已而后为之的最倒痗事,其理安在?其与彼等的主张倘有本质相干的关系,则今人反其道而行而美其名曰替其形式系统补强,则此中有否扭曲的危险在焉?简略来说,凡此皆示冯先生在参照西方哲学并以之为普遍哲学的标准时,对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仍缺乏足够的关注。张岱年在冯书出版后数年完稿的《中国哲学大纲》在继承冯氏的一些主张外却特重申明中国哲学的特色(15),正是上述分析的最佳佐证。
张书的取径本亦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张氏定义哲学为:“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1页)。据此以观中国旧有学术,则先秦时所谓“学”、诸子之学、魏晋玄学、宋明道学、理学与义理之学等,“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同上书,〈序论〉,第1页)。他亦支持冯氏提倡加强中国哲学底形式系统的主张,而谓“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同上书,〈序论〉,第4页)。然当张氏一触及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时,便必须在中西哲学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但这却与完全以西方参照为唯一标准的立场迥不相侔。因为划界的标准不能来自中西任何一方,而必须建立在一个既超越双方且又能统摄双方的“哲学”概念上。张氏说:
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换言之,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作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2页)
毋庸讳言,张先生在这里要分辨中西哲学,已接触到需要建立一具统摄性的哲学概念的问题。但他试图以类概念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问题则不能算是成功。盖依西方哲学为特例以建立一类名,其所依于西方哲学者究为何?再以有相似点来收纳中国哲学于哲学之类中,则此相似点究要相似至何种程度方可合符归类之要求?本质之相似乎?家族之相似乎?凡此张先生皆未作详细的交代。大抵他心目中所想的相似即跟随冯友兰的说法:谓中西哲学在问题及对象上相似,而相异处则在所谓彼此的态度方法上不同。然这一异同之辨稍一细想仍不易成立。尽管中西哲人都关心宇宙人生,但若所谓的态度方法不同,则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及处理方法均可大异其趣。于此说彼此在问题及对象上约略相当似乎意义不大。且过分强调约略相当而未能正视此约略相当实可大不相当,则正易于流为强我以就人。冯友兰向被诟病以新实在论的立场来解读宋明理学,未能把握中国哲学重视主体性的特质,实与他这一对中国哲学的反省定位不无关系。
其实金岳霖在冯书的审查报告中早已指出,以西方哲学作参照来规定中国哲学的研究,必较强调中国哲学底普遍性一面。其言曰:
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第5页)
金氏接着说“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16) 这是十分精确的论断。不过金氏的分析也暴露出当时流行思想的局限:即以为研究中国哲学要么以中国哲学为旧学的变换名目;要么以西方哲学为定夺中国哲学的唯一标准。实则在这两条路中间还有第三条路,此即一方面借西方哲学为参照来建构中国哲学,一方面仍不失对中国哲学底特殊性的探求。关键只系于如何调整西方哲学这参照并对这些调整提出充分的理据。毕竟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底普遍性),并不必排斥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底特殊性)。
四、对中国哲学底特殊性的探求
由援借西方哲学为参照而迫出关于中国哲学底特殊性的探求,正标志着思想界对于中国哲学的探索转入一新的阶段。但有趣的是,在这阶段中尽管学人们都肯定中国(哲学)思想有其特殊性并分途探索,然却出现了对哲学这一概念的“迎”与“拒”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梁漱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讲求亲证离言,故与强调理论思维的哲学不类,乃坚决反对用中国哲学一名来称谓传统思想。与此相反,熊十力亦指出儒学的归宿在求与本体实证相应,但却主思辨不碍实证;且儒学能由思辨以通实证,不沦为戏论,故甚或可将哲学之名据为己有而反视儒学为哲学之正宗。双方曾有书信往复辩难,争持不下。(1 7)
梁漱溟早年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亦曾随成说而分说中、西、印三支哲学。但在他的文化分析中实已隐然有将哲学、道德与宗教分别归为西、中、印三支文化所重不同的产物。(18) 到了《中国文化要义》以理性与理智分判中西,则严辨中(或东)西的想法已大体定型。(19) 扼要而言,梁漱溟拒绝用哲学之名的理据有三。一、视“哲学为西洋产物,对于宇宙根本问题揣测卜度”,故全属出于佛家唯识所谓第六意识作祟的戏论。(20) 二、中国儒释道三教均强调亲证离言,即使假设它们其中有理论思辨的成份,亦不过是人生实践中“无意而有的一种副产品”。“在东方古书中被看作是哲学的那些说话,正是古人们从其反躬向内的一种实践活动而来,而皆有其所指说的事实在,不是空话,不是捏造。”(21) 三、由是倘“随俗漫然以哲学称之”,将“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中国学术的特征,“失掉自家立场”(《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755页)。值得注意的是,梁氏这种立场在当时是不乏同道唱和的,如马一浮亦严“玄言”与“实理”之别,(22) 谓“然书院所讲习者,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与今之治哲学者未可同日而语。贤者之好尚在治哲学,若以今日治哲学者一般所持客观态度,视此为过去时代之一种哲学思想而研究之,恐未必有深益。”(23) 其虑亦在哲学徒呈思辨恐有碍发明自性。
关于梁氏的三个理据,其一斥西哲为揣测卜度,深于西方哲学者自难免觉得这是不称理的批评。但倘作同情的了解,则梁氏当时所面对的是20世纪西方重认知的哲学主流。此重认知的哲学所能成就者固不可谓只是揣测卜度,然其能否紧扣人的存在生命而施予引导变化之功则亦大成疑问。故梁氏这里的真问题其实是理论思辨是否有碍自我实践。自梁、马二氏的立场看,答案当然是有碍。至于第二个理据,则牵涉到对中国“为己之学”(姑以此名来统称讲求亲证之学)的理解。在中国为己之学的传统内虽无哲学之名但有否哲学之实?我们当然很难想象追求生命的完成可以完全不需要亦不表现任何理论思辨,故问题是理论思辨在其中所占的位置为何?梁氏以无意产生的“副产品”作答恐有不称理处。必须知道,为己之学中的理论思辨成份主要表现在学问讲明上。而学问讲明之“学”(相对为己之学可名为狭义的学)虽被强调为不能离乎追求生命转化之“宗”(此宗即最高目标义、宗旨义)而独立讲论,但却是实践工夫之“教”(教乘义)之一种。甚至严格来说,乃“宗”与“教”赖以传承所必须具备者。故实非所谓无意而有的副产品。此所以熊十力认为思辨并不一定妨碍践履相反还有助成之功,虽或有启于唯识转识成智之论,然衡之于为己之学的传统亦非无据。至谓传统为己之学是否哲学,则又端视乎我们如何使用哲学一词。如依20世纪西方重知哲学之主流来规定哲学一词的涵义,则传统为己之学自不能谓之哲学。最后,梁氏的第三个理据乃认为以重思辨之哲学来重新命名传统的为己之学将使为己之学的殊胜处模糊不清甚或泯灭不存。这种断定当然又是顺着思辨有碍实践的想法而来。可见梁氏的三个理据说来说去都是环绕着思辨有害于亲证的问题。诚然,传统为己之学确有悬胜义离言、亲证离言为最高鹄的之说,但此中离言之实义仍须加以简别澄清。梁氏有时为了贬抑思辨的作用,不免把离言的意义极端化了。
与梁氏相反,熊十力虽然亦肯定证会,但却认为思辨在追求证会的过程中有其必要的作用。在1944年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熊氏仔细交代了证会与思辨的关系:
证会,才是学问的极诣。思议,毕竟是肤泛不实的。或有问言:“如公所说,思议遂可废绝否?”答曰:“我并不曾主张废绝思议。极万有之散殊,而尽异可以观同;尽者,穷尽。察众理之通贯,而执简可以御繁;研天下之几微,而测其将巨;穷天下之幽深,而推其将着。思议的能事,是不可胜言的。并且思议之术日益求精。稽证验以观设臆之然否,求轨范以定抉择之顺违,其错误亦将逐渐减少,我们如何可废思议?不过思议的效用,不能无限的扩大。如前所说,穷理到极至处,便非思议可用的地方。这是究玄者所不可不知的。”“……本来,证会是要曾经用过思议的工夫,渐渐引归此路。唯恐学者滞于思议之域,不复知有向上一机,所以说不可思议。不可者,禁止之词,戒其止此而不更求进,故言不可,以示甚绝。常途以不可思议一语,为莫明其妙的神秘话头,若作此解,便非我立言的意思。”(24)
熊先生是以追求证会那穷极万化之源的本体为学问的极诣,所以他对西方哲学底本体论、宇宙论等概念分解极表赞同,认为大有助于中国为己之学的重释。依熊先生的观点,哲学的核心即本体论,亦即证会本体之学。故从他这种对本体论的特殊定义看,西方哲学昔谈本体遂只是驰逞思构的戏论;至近世罕言本体而转重知识,则更使哲学无涉于人生。故真能极成本体论的乃是儒家躬行实践之学。明乎此,则熊氏以儒学“当为哲学正宗”的说法便不难理解。(25) 当然,这绝对是熊先生个人的一家之言,不必人人都能同意。且人若囿限于此以观熊氏,则反不易正视其论在近世中国哲学的探索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此即通过对中国哲学重视实践之特殊性的把握,进而求融通西方哲学之思辨于一炉,来修改或扩大“哲学”此一概念(此义对近世西方重知识之哲学主流而言尤显)。熊氏这意图,在〈再答张东荪〉一书中明白透露:
弟则以为中国思想之优点亦正在此,特如何以保留此种优点而仍能卓然自立于西方文明大昌之今日,则颇为问题。诚以东方之自得之乐与西方之驭物之智,如何融合并存,不得不大费苦心矣!弟极思有以解决之,而深感一人之力有限,此则非区区短笺所能尽述者也。(26)
最后熊氏提出的答案是哲学乃“不遗理智思辨,要不当限于理智思辨”(27);哲学是始乎思辨、终乎切己的学问。有思辨而不切己,则哲学沦为戏论;相反,有切己而乏思辨,则切己之学亦终不能畅达而衰落。由是观之,近世儒学之遭受西方哲学的冲击实焉知非儒学之福。在〈再答张东荪〉中,熊氏说:
儒家注重践履,此其所长,而由此不务敷陈理论,则了精义宏旨者,仅少数哲人,而大多数人乃无从探索,而不见其有何物,此亦儒术所以衰也。(28)
在〈答君毅〉中,又说:
体会之功,所以自悟。论辩之术,虽为悟他,而自悟亦资之。此土儒道均尚体会而轻论辩,其得在是,失亦在是也。(29)
这样一来,则中国哲学此一新概念、新学科的出现便不仅是势所必然,且亦是理有必至。熊氏这种探索定位中国哲学的努力,后来完全为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所继承。熊氏曾在一通给牟宗三的信中写道:“宏斯学者,吾不能无望于汝与唐君毅。大事因缘出世,谁不当有此念耶?”(30) 诚有先见之明。
五、统摄性“哲学”概念的建立
由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探求而引发的有关思辨与实践的辩论,后来确实成了定位中国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熊氏的两位高弟唐君毅、牟宗三对此均有进一步的演绎发挥。关于思辨与实践之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牟先生尝以“哲学的悲剧”与“圣人的悲剧”两观念畅发其义:
因此,能不落在一定形态下,而单从名理以辩之哲学家,则可拆穿圣人之浑一,而一一予以辩示,而畅通其理理无碍,事事无碍之途径。哲学以名理为准。名理凌空,不为生命所限。圣证以生命为贵,不能不为其所限。无生命之圣证,则道不实。无名理之凌空,则道不开。哲学辩而开之,显无幽不烛之朗照。圣证浑而一之,示一体平铺之实理。然哲学家智及不能仁守,此是哲学家之悲剧。圣证仁守而封之,此是圣人之悲剧。两者永远在开阖相成中,而各有其独立之本质,藉以观人之所以为人,精神之所以为精神。(31)
圣人若仅有实践而无思辨之功以畅通之,则实践将无所持循甚或无由展开而反使其自身有窒息之虞,此所谓“圣证仁守而封之”的悲剧。反过来说,哲学家徒呈思辨而脱略实践,则面对人生种种实存的困境与苦难时,则只益显哲学之无力感,此即思辨“智及不能仁守”的悲剧。然我们若考虑到哲学本是以关怀人生为目的而根本不会甘于沦为纯智构作的戏论,则可知近世西方哲学之重知倾向实为一偏之见,(32) 而哲学必应为能统摄实践与思辨两面之学。
唐、牟二氏有时是纯从名理思辨以言哲学,则此哲学观念可谓西方(尤为现代西方)所特有。在这一狭义上用哲学一词,故牟先生会说:“中国传统学问是道德、宗教,不属于哲学。”(33) 唐先生亦说:“说儒家思想只是哲学,明不合西方所谓哲学之本义。西方所谓哲学,明重在理论系统的构造,大多是只重思辨与批判,而不重信仰的。而近代之哲学尤然。至儒家之思想,则明要导向道德上之行为与实践,而一切道德上之行为与实践,都要依于一信仰的。”(34) 此处唐先生以哲学之本义“只重思辨与批判”容或有可商榷处,但若范限于“近代之哲学尤然”则是大体合符事实的论断。若仅从上引的文字看,唐、牟二氏之不以(狭义的)哲学命名儒学的立场好象反近于梁漱溟而远于熊十力。但深究之下其实不然,此盖唐、牟二氏终以为思辨与实践可相融不悖。并且由此相融不悖之理想,乃可建构一既超越中西亦复能统摄中西的“哲学”概念。唐君毅在《哲学概论》中所做则是明证。唐先生在《哲学概论》开首界定哲学一词的涵义时,则通过将人类的学问概分为“以行为主之学问”及“以知为主之学问”,而谓哲学则是反省贯通二者之学。易言之,哲学乃“以贯通知行之学为言”:
哲学是一种以对于知识界与存在界之思维,以成就人在存在界中之行为,而使人成为一通贯其知与行的存在之学。(35)
此一统摄中西的“哲学”概念既立,则复可在此概念下分别定位中西哲学的不同传统。如唐先生便尝以历史文化的分殊通孔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而谓“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36)
从上述的析论看,可知自熊十力以降至唐君毅、牟宗三的这一条定位“中国哲学”的线索,主要是通过融通思辨与实践来建立一具统摄性的“哲学”概念。熊十力以为思辨可以引归实践;唐君毅亦谓思维可以成就人在存在界中之行为;牟宗三也曾以桥来比喻概念思考与分解方法而谓“哲学活动(按:指思辨活动)是在教的范围内帮助我们的一种疏通,是一道桥,尽桥的责任就是它的界限。”(37) 然而我们于此仍可追问思辨引归、成就、疏通实践等说法的实义为何?是指实践需要借助于思辨始能展开?但若仅是如此,则思辨非能产生实践者,实践与否最终仍得取决于思辨以外的因素,而所谓引归、成就等义遂不显。因此熊、唐、牟三先生的想法应是以为思辨能引发出或曰转化为实践。上引牟先生的文字谓思辨是在“教的范围”内的一种疏通正隐含此消息。在这里紧接着的问题是,倘若思辨是指概念分解与逻辑推演的活动,则这些活动如何能转化为实践的动因?解答的关键实已指向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述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略作分疏,此处暂不多说。
最后,要全面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定位历程,则劳思光所作的贡献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劳先生对自己研究哲学的方法所经常怀有的反省与自觉在20世纪的学人当中可谓无出其右。是故他在撰写其巨著《中国哲学史》时实早已究心于“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在三卷《中国哲学史》的序言、后记、附录中这些探索思考的痕迹清晰可见。后来他更将所思发而为文,写成〈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探讨及建议〉、〈由儒学立场看人之尊严〉等文字直接表述他对中国哲学的想法。(38) 假若仅从结论看,即劳先生以哲学应具认知与引导两种功能来统摄及分判中西,似乎与唐、牟两先生融通思辨与实践的看法大有可资比观的地方。不过唐、牟有时喜欢将彼所建立的统摄性“哲学”概念说成是直承中国先哲知行合一之说,(39) 则与劳氏较强调从普遍性哲学的立场出发来进行思考颇不相侔。且劳氏探索与定位中国哲学并不随熊、梁辩论的线索下来,而是独立运思,另辟蹊径。要之,此亦正反映出他对中西哲学的理解与同时代学人有不尽相同之处。
劳先生首先指出要为哲学寻找一本质定义固不可能,但我们总不能不对“哲学能做甚么”作某种决定。由是他建议从“哲学功能”入手。而顺着哲学底反省思考的性质(区别于经验思考)在文化世界中表现出的作用,他把哲学功能概分为“认知功能”与“引导功能”。(40) 前者提供“强迫性的知识”,后者则提供“主张”。(41) 而“中国哲学作为一整体看,基本性格是引导的哲学”(42),此即这一哲学提出各种主张,目的乃在促使人的自我转化。复次,不管是认知哲学抑或引导哲学,劳氏均认为我们应该定出一个有关“理论效力”的标准来衡量其中各种说法的得失。对引导哲学而言,这衡量标准即为“指引效力”:
中国哲学的主要学派——如儒道学说,原本以指引人生为主,或说以“自我转化”为主。在这个目标下,许多哲人又提出各种主张;而支持主张的又有一套套的理论。我们研究这些理论或主张时,可以处处测定其“理论效力”。即如宋明儒有种种工夫论;其中皆包括确定主张及支持主张的理论。我们如果弄清楚这些主张落在实践生活上会引人去怎样生活,然后即可立出一些设准,来衡量它们的理论效力。这样不仅可以在评判前人学说时,可以使我们的判断意义明确,而不陷入门户意气之争,并且也可以由此遥遥显出这种哲学思想对人生问题的普遍意义。(43)
面对西方近世重认知哲学的主流,劳先生则强调哲学活动在最根本上原是以引导功能为主。因为人“最基本的关怀或需要,是在目的方面,而不是在知识方面。”(44) 故此尽管引导哲学不能提供有关经验世界的知识,但却可以提供我们自觉生活方面的启示。所以劳先生最后总结说:
倘若谈教育,谈德性发展,以及谈社会进步并非无意义,则这种引导性的哲学将继续成为一门重要学问。(《思辨录》,第155—156页)
在定位中国哲学后,劳先生进而指出学人努力的方向应在于对这个传统进行清理工作,去掉其中“受特殊的历史、社会、心理等等条件约制”而在时移世易的情况下已经失效的“封闭成分”,复提炼出其中较具普遍意义,“有长久的功能,又可以在不同的特殊条件下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开放成分”。(45) 唯其如此,中国哲学才能通过展示它的时代相干性来恢复其生命力。
析论至此,人或会怀疑劳先生自始是以一种后设的解析语言来把中国哲学定位为引导哲学。但以后设的解析语言解释引导哲学与引导哲学的建构本身应有分别,盖二者属不同的层次。对引导哲学的后设解释我们似乎很清楚,但对引导哲学本身则恐仍有疑问待解。此则引导哲学如何建构?是否也是以解析语言建构之?但中国过去的学术思想中似乎并没有发展出很强的解析语言传统。又解析语言是否能够发挥引导的功能?凡此皆指向引导哲学的语言表述问题。其实这也正是前面曾提及过的思辨如何转化为实践的问题。对此劳先生曾有一回答:
哲学语言原应有一种“引导功能”(Orientative Function)。即在西方世界,古代欧洲的希腊哲学仍重视这种功能。不过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哲学家一直想将哲学变得像某种科学,由此而逐步转向“认知功能”的强调,因而遗忘了哲学语言原有的引导功能。(46)
但此处劳先生因未举例,故所谓哲学语言原应具有的引导功能仍语焉不详。从过去一个世纪研究中国哲学的文字看来,则似全属以解析语言来解释评断已有的各种思想而非属引导哲学的建构。倘从传统思想表述的用语来看,则类比、寓言、佛道两家的诡辞以至大量诗化语言(poetic language)的运用,是否就是具引导功能的哲学的表述语言?若然,则在今后中国哲学研究中此种语言应扮演甚么角色?其与现今被广泛应用作研究的解析语言的关系又为何?这一连串的问题恐怕是中国哲学研究者未来仍得费心着力的地方。
六、结论:兼谈建立两层论述的初步构想
总括而言,我们可以将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探索“中国哲学”的努力从以下几点来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发挥。一、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传统的为己之学在近百年来一变而为中国哲学其实正表征着一次典范的转移(paradigm shift)(47)。那么所谓的中国哲学无疑便是要运用哲学方法(概念分解与逻辑推演是其中主要的方法)来重新整理表述传统思想的研究工作。而此中必须借取参照西方哲学传统中各种观念架构乃题中应有之义。易言之,拓展比较哲学的视野显然仍是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所不可忽略的一环。二、当然,借用西方哲学为参照仍是需要加以调整并对此调整提出充分理据的。盖比较哲学亦非削足适履、牵强比附即可为之。三、通过对参照的调整,我们乃可以一方面凸显出中国哲学底特殊性,另一方面借着展示其时代相干性来透露出中国哲学底普遍意义。四、过去对中国哲学底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把握多落在转化生命的践履层面。诚然,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确是中国哲学的特色甚或殊胜处,但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清理与开发却绝不应自限于此。劳思光区分“封闭成分”与“开放成分”实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指引意义。五、由对中国哲学底特殊性与普遍性两面的衡定,我们实可进而建构一统摄性的“哲学”概念来分判中西以至不同民族文化的哲学。
最后,关于思辨如何转化为实践,引导哲学如何发挥引导功能的问题,正如前述的分析已约略点出这乃牵涉到哲学语言的表述与功能问题。因这问题若要充分展开则极复杂,以下我只能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粗浅的思考:即通过所谓两层论述的建构来使中国哲学的语言本身具有一种引导功能。唯其如此,中国哲学才能在典范转移的过程中继承发挥传统学问那能转化自我生命的胜义。两层论述的第一层我们可以称之为(诠释)系统内部的论述。其底子虽仍是思辨分解的,但在表述语言上则要力求吸纳消化传统为己之学在学问讲明上的种种概念用语。如体会语、训诫语、指点语以及那些近乎诗化的语言表述。盖传统为己之学中学问讲问的部分之所以能作为教,作为实践工夫,正是因为它的表述语言绝非那些冷冰抽象的概念,相反乃是极富于引导效果、能启发触动受教者心灵的一套用语。以佛家的“诡辞”为例,尽管以哲学分析底明晰性的要求来说,它实际上只是伪似的诡辞,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表述方式在语用上确实可以产生洗涤人心的效果。如果我们毫不保留这种表述方式,而仅在概念分解的号召下力求将之翻译、解读为所谓明晰的概念,则中国引导哲学的语言将无异于现代西方认知哲学的解析语言,其引导功能之丧失乃不言可喻。
不过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不能只有系统内部的论述这一层,因系统内的论述往往给人一种自圆其说的印象。并且若只有这一层,则中国哲学便不免有裹足不前、固步自封甚或无法跟别的思想传统对话交流的危险。所以在系统内部的论述外,我们还必须有后设反省的论述。而此即可以是概念分解、逻辑推理等思辨方法大派用场的地方。显而易见,这两层论述是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的。(48) 盖缺乏前者,中国哲学就无由继承为己之学的生命智能及其引导人生的功能,而后者亦将失掉汲取丰富思想资源的源头活水。(49) 相反,若缺乏后者,则中国哲学亦无法开展以与不同的哲学思想互相攻错来求更进一步善化自身。假若我们在将来仍想宣称中国哲学是一套“活的哲学”,则起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学术世界内对于理论底精巧性的要求,而另一个则是哲学对实际世界与人生能否发挥作用的问题。(50) 于此可见,两层论述中的后设论述将可满足第一个条件而使中国哲学得以逐步跻身世界哲学的舞台,而系统内部的论述则可满足第二个条件而使中国哲学仍能保持那份让学习者受用的吸引力。
“中国哲学”一词自20世纪初流行于中国思想界,并演为一门崭新学科,发展迄今已逾一个世纪。其间,“中国哲学”这概念的合理性一直备受质疑。现在或许已是个成熟时机,让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认真地去面对、反省“究竟甚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反省之所资,自然是过去前辈学人已作的思考成果。这亦正是本文清理20世纪中国学人对“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定位的用心所在。戴卡琳(Carine Defoort)曾经在其文章"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究竟有无中国哲学”)中提出一个四分架构来探讨这问题,有助于厘清关键。兹先概括其要点,再略作辨析,以清眉目。
依戴氏,对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这问题可以有四种态度:(1)根本不存在中国哲学。盖中国传统思想根本缺乏哲学那种系统性、反省性与分析性,而哲学研究的主要门类如形上学、知识论及逻辑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亦乏善可陈。从这个立场看,坚持有所谓中国哲学者,多为民族自卑心理之表现,故鲜能提出有力的理据。(2)存在中国哲学。代表人物如胡适、冯友兰,彼以为即使以西方哲学传统作标准,中国传统思想中仍不乏哲学的成分。胡适重视墨辩、冯友兰主张为中国文本本身具有的“实质上的系统”补上“形式上的系统”即是典例。(3)从(2)的态度进一步引申,认为中西文化的相遇适足以让学人藉此重新反省何谓“哲学”,并由此扩大“哲学”的意义以包容中国传统思想。而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将成为西方哲学一个虽相异却极有价值的参照。持此一态度的学人,戴氏举的例子为Herbert Fingarette。(4)乃是(1)的态度的激化,质疑哲学的价值,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有其自身的价值,不把它当哲学看待不仅毫无损失,反倒使人更能正视其自身实有不逊于哲学的价值。易言之,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绝不需要通过取得(西方)哲学的牌照才能证明。戴氏对上述四种态度的优劣均有所评骘,但却建议取一非本质主义的立场,从“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观点来理解“哲学”这观念,以求平息争议。戴氏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思想均可在某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加入“哲学”的大家庭,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出现亦当作如是观。虽则中国哲学或仍迥异于西方哲学,且仍未广为西方哲学家所接受,但这并无伤于中国哲学,因为根本上就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接受的哲学的本质定义作为确认身份资格的标准。
诚如本文开首已指出的,回答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哲学,端赖于我们对“哲学”一词采取怎样的理解,并自觉对这种理解提出理据。显而易见,持态度(1)者,实以经历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态来定义哲学,把“哲学思虑”(philosophize)完全窄化为概念分析、逻辑推演的思考方式。无怪乎以此衡量中国传统思想会得出没有中国哲学,或即使有也是不够哲学的哲学的怪论!持这种态度的学者,当然有责任反省以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态来定义哲学是否恰当。须知依现代西方哲学作标准,传统西方哲学中很多丰富的内容及多样化的哲学思虑形式(different modes of philosophizing)实际上亦已被扫除在哲学的门槛外。(51) 持态度(2)者,因不自觉仍以西方哲学作为定义哲学的唯一标准,即使承认有中国哲学,甚或呼吁不应囿限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态、回归丰富的西方哲学传统,以发现更多中西哲学可资比观攻错的地方,(52) 但毕竟未能正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殊性。戴氏所提出的第(3)种态度,从本文的观点看,正是20世纪中国学人探索及定位中国哲学的努力的主要方向。持此态度者,一方面承认“哲学”起源并大盛于西方文化,所以必须以西方哲学作为定位中国哲学的参照。但另一方面亦不排除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以改写“哲学”的定义:此即着力于寻求一统摄性的“哲学”概念,并为重新界划“哲学”的意义与内容提出理据。当然这一取径难免有本质主义的气味,不易为反本质主义者如戴卡琳所认同。但采取戴氏的建议,又怎样避免流于相对主义的窠臼:各种均以哲学自居的不同的文化思想传统陷入各自为政、无需甚至无法彼此沟通对话的困境?要之,这已牵涉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辩论,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说。最后,持第(4)种态度者,倘若真如戴氏所言,或是有激于中国学者久扣西方哲学家庭之大门却不得其门而入所造成的反弹情绪,固无足深论。但若持此态度者的立场是欲转而另辟蹊径来安顿中国传统思想,则是个值得讨论的真问题。必须知道,西方文化在保持其学术思想传统方面即有所谓“经典研究”(classics studies)的学术门类。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在20世纪初反传统的大气候下解体,支离破碎者只能求庇荫于西方学术的分类下始得延续生机。然而时移世易,今天倘若我们恢复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亟思有以经典研究之学术门类保存之、发扬之,则未尝非可取之道。不过这里必须补充一点可能引起的误解,即提倡经典研究者仍不能反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盖深思之下,便知经典研究永远是一返本开新的诠释过程,它无可避免地需假途于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文献的考证训诂方法、历史的如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方法、甚至西方学术中可为我用的研究方法。此处我们恐怕找不到什么很好的理由去把哲学方法排拒在外。
注释:
①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毅的考证,始造“哲学”一词以翻译philosophy的,是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姓西名周,读作Nishi Amane)。西周尝用音译“斐卤苏比”、意译“希哲学”(希冀成哲之学)之名翻译philosophy,后于1866年始用哲学一词。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造哲学一词时,原想藉以指出西学中一种有别于日本传统国学与儒学的学问。但此词一流行,日本学界随即有“儒教哲学”的提法。于此可见现代西方学术的分类,随着现代西方文化的扩散,如何冲击着其它民族的学术传统。参看小岛毅著、廖肇亨译:〈“儒教”与“儒学”涵义异同重探——新儒家的观察〉,收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第202—06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再版),第1章〈绪论〉,第7—8页。
③参看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97增订九版),第1册,〈后记〉,第407页。
④同上书,第3册下,〈答友人书——论中国哲学研究之态度〉,第893页。
⑤本文清理20世纪关于“中国哲学”的探索,只限于中文学术世界的研究。对欧美学界如何定位“中国哲学”则需另文处理。
⑥我们通过清理关于“中国哲学”的探索,实可进而据此以考察这些探索的结果(即对“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的定位)如何塑造了学人的研究方法及影响着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而得一通盘详尽的哲学史的清理。职是之故,本文的确只是这庞大的清理计划中的一个初步尝试。
⑦此四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依探索的理路发展来划定,盖若以历史时间的先后言,则阶段与阶段之间实颇有重叠之处。
⑧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卷。
⑨陈黻宸:《中国哲学史》,收《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上册,第415页。
⑩金岳霖:《审查报告二》,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第6—7页。
(11)《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第2页。
(12)参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4页。
(13)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三版),第1册,第16—25页。
(14)金岳霖在其审查报告中亦注意到此一难题,他说:“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同前注,〈审查报告二〉,第5页。
(15)张书提出的中国哲学的特色共有六点:一、合知行;二、一天人;三、同真善;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六、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参看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序论〉,第5—9页。
(16)《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第7页。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却反对这种做法:“‘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细读冯氏在《新编》的〈全书绪论〉,撇开其中的官方学说色彩及重复早年观点的部分不谈,他对中国哲学的探索有进于前书之处,乃在于分别从人类精神的反思、理论思维、锻练思维和提升精神境界三方面来理解哲学的内容、方法与受用。将哲学置于文化精神的层面来理解确有助于正视中国哲学底特殊性一面。参看《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25—28页。
(17)关于这一辩论,可参看陈来:《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念》,《人文论丛》2002。
(18)参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收《梁漱溟全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卷。
(19)参看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收同前注书,第2卷。
(20)梁漱溟:〈致某先生〉,同前注书,第8卷,第315页。
(21)梁漱溟:〈读熊著各书书后〉,同前注书,第7卷,第757页。
(22)马氏云:“若有言者,未必有德,只是其言亦有中理处,娓娓可听,足以移人,及细察之,则醇疵互见,精粗杂陈,于此实理,未尝有得,而验之行事,了不相干,言则甚美而行实反之,此为依似乱德之言。其有陈义,亦似微妙,务为高远,令人无可持循,务资谈说,以长傲遂非,自谓智过于人,此种言说,亦可名为玄言之失。盖真正玄言,亦是应理。但或举本而遗末,舍近而求远,非不绰见大体而不能切近人专,至其末流,则失之弥远,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也。”〈玄言与实理之别〉,《复性书院讲录》第2卷,收《马一浮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第1册,第157页。
(23)马一浮:〈答许君〉,《尔雅台答问》卷1,同前注书,第1册,第527页。
(24)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收《熊十力全集》(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卷,第146—147页。
(25)熊十力:〈与梁漱溟〉,同上书,第8卷,第649页。
(26)《十力语要》卷2,同上书,第4卷,第174页。
(27)〈与梁漱溟〉,同上书,第8卷,第649页。
(28)《十力语要》卷2,同上书,第4卷,第173页。
(29)《十力语要》卷2,《熊十力全集》,第4卷,第173页。
(30)《十力语要》卷2,〈与牟宗三〉,同上书,第4卷,第296页。
(31)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第283—284页。
(32)事实上,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近世西方哲学之重知传统所引致的偏颇亦已有深刻的反省批判。参看Charles Taylor," Preface" & "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in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p.vii-xii; pp.1—19.
(33)牟宗三:〈访韩答问录〉,收氏著:《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第204页。
(34)唐君毅:〈儒家之学与教之树立及宗教纷争之根绝〉,收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74),下册,第462页。
(35)唐君毅:《哲学概论》(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大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1961),上册,第18页。值得注意的是,唐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中谈中国哲学研究之新方向时,虽把哲学定义为“对统摄性、根原性之义理之思想与言说”,好象仍偏重哲学底思辨的一面。但他接着却以实践为标准来区分“圣哲”、“哲学家”与“哲学研究者”,可见贯通知与行的“哲学”乃其持守之信念。参看〈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收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册,第374—375页。
(3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北:学生书局,1983),第15页。
(37)〈访韩答问录〉,第204页。
(38)此两文均收氏著:《思辩录——思光近作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39)唐君毅在《哲学概论》的〈自序〉中写道:“本书对哲学定义之规定,以贯通知行之学为言,此乃直承中国先哲之说。”第4页。
(40)劳思光:〈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探讨及建议〉,《思辩录》,第17页。
(41)《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册下,〈答友人书〉,第894页。
(42)〈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探讨及建议〉,《思辨录》,第18页。
(43)〈答友人书〉,第895—896页。
(44)〈由儒学立场看人之尊严〉,《思辩录》,第152页。
(45)〈答友人书〉,第896页。
(46)〈由儒学立场看人之尊严〉,《思辨录》,第154页。
(47)典范转移的概念乃借用自孔恩(Thomas S.Kuhn),参看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必须补充的是,孔恩原以典范转移来说明科学革命的性质,但其说甫提出即已招来不少诘难,最后连孔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典范这概念的定义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并且他强调新旧典范间的不可通约性也屡被批评为过分忽略了科学传统发展的连续性,是错把科学发展中渐进性的中断扩大到彼此不可衔接的地步。不过尽管典范这个概念本身有很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它是个富于睿识的提法,故很快便在其它学术领域内不胫而走且被改造为一较宽松的用法。此处我们视从传统为己之学到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一典范转移,故重在强调两者间的巨大转变,但却绝不认为两者间是完全隔断与不可通约的。
(48)若我们把两层论述中的表述语言都视为哲学语言,正足以恢复哲学语言的丰富性,而恢复哲学语言的丰富性其实亦正是恢复“哲学思虑”(philosophizing)这概念的丰富性。
(49)必须澄清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一套所谓中立性的后设论述语言可以藉此来讨论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后设论述的语言其实亦是从所论述的对象中提炼出来的,是以后设论述所能达至的深度乃完全取决对所论述对象之理解程度。但反过来说,对所论述对象之理解程度亦端赖于后设论述能否提供更多更新的理解视角。可见两层论述的关系是一种诠释学的循环(hermeneutic circle)。
(50)这两个要求是借用自劳思光先生的说法,参看劳思光:〈中国哲学研究之检讨及建议〉,收氏著,刘国英编:《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第1—24页。
(51)参看Robert Solomon," ' What is Philosophy? ' The Status of World Philosophy in the Profession" ,Philosophy East & West,51(1)(2001):100—104.
(52)1995年法国哲学家Pierre Hadot的著作(英译本)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出版,曾引起一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关注,以为此实足证中国传统思想多有与古希腊哲学相通者故足可当哲学之名而无愧。这正是第(2)种态度的典例。参看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nold I.Davidson,trans.by Michael Chase( UK: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