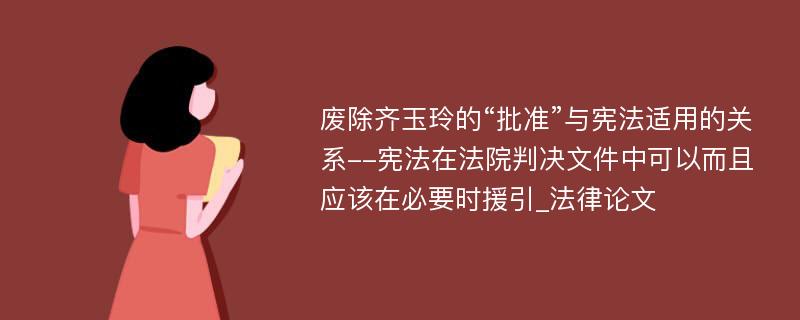
废止齐玉苓案“批复”与宪法适用之关联——法院裁判文书必要时可以并且应当援引宪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裁判论文,文书论文,法院论文,齐玉苓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法院的裁判文书援引宪法是由宪法作为根本法的特点决定的
要理解法院的裁判文书能否援引宪法,就必须对我国宪法的内涵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宪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也即宪法典,是指集中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职权及其相互关系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另一种是指作为部门法的宪法,也即一系列调整人民在行使“当家做主”权力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如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国务院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作为部门法的宪法,属于公法的范畴,而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却是所有法律的“母法”,其调整领域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①
我国部门法教材,如民法教材和劳动法教材都是将宪法作为民法和劳动法的渊源表现形式。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固然有许多都属于公法领域的,如选举权、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及取得国家赔偿,但是也有一些权利与义务,明显涉及私法领域,如人格尊严、劳动权、财产权、继承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因此,在私法领域,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碰到上述有关权利,以及可能进行法律分析的,法院应当援引宪法。
我国许多学者引用西方宪法的流行理论,如“第三者效应”理论、“国家行为”理论等,认为宪法对私法案件仅具有辐射效果,宪法如果进入普通的民事案件,就会侵犯私法的意思自治。因而,法院不能轻易援引宪法。然而,西方的宪法理论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我国。这是因为西方学者所理解的宪法主要是指作为部门法的宪法。
以英国、美国和法国宪法为例。英国是宪法的发源地,但是英国的宪法是由一系列的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性惯例构成,这就是作为部门法的宪法,而且到现在为止,尚未产生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美国宪法主要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上,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产生、运作和相互关系,后来增加的人权修正案亦仅仅限于政治类权利,没有规定自己具有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而是国家“最高法律”的其中一种。②美国宪法高于国会法律,且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起来的。法国1791年和1793年宪法都只规定了自身的严格修改程序,以避免大革命成果被篡夺,但没有规定自身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近代最早产生的宪法,是指作为部门法的宪法,最初并不是指作为根本法的宪法,这种观念深深支配着西方学术界对宪法的认识。③
我国的宪法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上。毛泽东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时候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④彭真在1982年宪法起草报告中指出:“它将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⑤我国的宪法实际上是在这样一种观念上制定的。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是我国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法院审理案件,裁断法律纠纷,恰恰就是治国安邦的具体体现。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当然是可以援引宪法的。
二、法院的裁判文书必要时可以并且应当援引宪法
列宁说:“宪法是什么?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⑥因此,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有权援引宪法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内在必然要求。笔者认为,不能将当事人在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时援引宪法视为“阴谋”,视为是引诱法院上当,进而炒作自己。相反,这是当事人的权利。
笔者认为,法院必须在说理部分援引宪法进行法律分析。这是因为既然当事人在主张诉讼请求上提出通过援引宪法来加强理据,法院就必须根据宪法进行分析说理,来达到支持或反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目的。即使当事人在法庭上没有援引宪法来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法院为了更好地进行说理,可以从宪法的角度进行推论说理,而且只能在宪法的高度上,才能加强说理部分的说服力。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人认为,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并不包括宪法在内,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适用宪法;宪法不能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法院即使援引宪法,其也只能出现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而不能出现在依据部分。⑦这种意见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宪法》第126条所指的法律,只能将其理解为合宪的法律,而不应当将其理解为还包括违宪的法律在内。《宪法》第126条恰恰就是法院审判案件的根本依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法院在审理案件的依据部分,必须引用《宪法》第126条,正如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明确指出是根据宪法行使立法权一样。而且,这还有助于在作出判决结果的关键时刻提醒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法院援引宪法,不等于宪法的适用。法院裁判文书对宪法的援引分为两种:一种是遵守性援引,一种是适用性援引。⑧所谓遵守性援引,是法院本身遵守宪法;所谓适用性援引,是指法院根据宪法本身来裁断当事人的纠纷。只有出现裁判文书的依据部分,才是适用性援引,而没有出现在依据部分的宪法援引,属于遵守性援引,不是适用性援引,不属于宪法适用的范畴。
不能机械地理解判决书的格式要求。我国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必须出现“依据某某法律第几条,判决如下”的所谓依据部分,这是因为我国法院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不注重说理甚至是没有说理所造成的。因此有所谓的依据部分,写明法院是根据某某法律的第几条才判决如下的。如果根据上述的遵守性援引和适用性援引的两分法,法院的裁判文书只能在说理部分援引宪法进行法律分析,相关条文反而不能出现在依据部分,这不仅是不自然的,反而割裂判决书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院的裁判文书里,并不存在所谓的“依据某某法律第几条,判决如下”的格式要求,它们通常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写到“因此,本合议庭判决如下”或“因此,本法庭判决如下”就可以了。判决结果只能是说理部分的必然结论。
三、法院援引宪法不等于行使违宪审查权
有一种意见认为,法院援引宪法,就会导致法院有权解释宪法,进而行使违宪审查权,判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进而造成一个县级基层法院就能挑战和否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局面”,⑨这与我国宪法已经确立的违宪审查机制不合。我国《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而我国宪法没有规定法院解释宪法,也没有权监督宪法实施。因此,法院不能援引宪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宪法在判决书中的地位缺乏进一步的观察。
不过,法院援引宪法,确实存在着解释宪法,进而判断法律无效的可能性。因此,笔者在此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法院拥有合宪判断的权力,但没有违宪判断的权力。笔者认为,这种合宪判断的权力隐含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是我国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我国法院现在在其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就是以所依据的法律是符合宪法为前提的。但是,如果当事人在主张诉讼请求的过程中,提出法律违反宪法的问题,法院该怎么办?法院不能说,你当事人不能提,你提了,我也置之不理。所以,法院应当拥有一种宣布法律符合宪法的权力。即在法院可以援引宪法的社会,其虽然不能拥有宣布法律违宪的权力,但是可以拥有作出合宪判断的权力。
譬如,甲乙皆为同性,他们或她们到婚姻登记部门要求登记,婚姻登记部门予以拒绝,根据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婚姻必须为异性结合,因此,同性不能登记结婚。当事人不服,因此提起诉讼,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只是婚姻自由,没有规定婚姻必须是异性的结合。又如,有甲乙丙三个当事人,甲乙为同性,丙为异性,他们到婚姻登记部门要求登记,婚姻登记部门予以拒绝,根据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婚姻必须为异性结合,而且必须是两个异性的结合,即必须是一男一女。当事人不服,因此提起诉讼,因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只是婚姻自由,没有规定婚姻必须是两个异性的结合。在这两个案件里,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显然,我们的法官只能判决当事人败诉,法院在说理的过程中,必须阐述《宪法》第49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的内涵,进而判断婚姻登记部门所依据的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是符合宪法的。
在此,马上会出现一种意见认为,即使法院拥有合宪判断的权力,但在作出合宪判断的过程中,对宪法的内涵作出阐述,就是在解释宪法,而我国宪法已经将宪法的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已经没有宪法解释权了。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与其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宪法》第67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不能排除其它国家机关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如《宪法》第6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这就包含着国务院在行使这些职权的过程中,对宪法可能有一个理解和解释,然后根据这个理解和解释去行使职权。因此,也不能排除法院在援引宪法的过程中,本身就自然而然地拥有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的权力。
笔者认为,法院援引宪法,不等于法院就行使了违宪审查权,法院最多行使的是合宪判断的权力。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认为所争议的法律是违反宪法的,如在上述的两个例子中,认为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违反了宪法上的婚姻自由原则,就应当停止审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如果认为没有违反宪法,可以通过一个司法批复,确认该法律是合宪的,公之于众,统一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思想。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法律违宪,则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解释宪法,确认违宪或合宪。
如果法院在援引宪法的过程中,判断法律违反宪法,进而直接根据宪法作出判决,那么应当怎么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应当追究法官的错案责任,同时根据审判监督原则对案件予以再审,如同洛阳市的种子案,“严厉打击”,公之于众,就会在全国法官的心目中形成无权根据宪法,判断法律无效的宪法观念。
四、最高人民法院废止齐案“批复”不等于法院就不能援引宪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宣布废止齐玉苓案“批复”,这是否意味着法院就不能援引宪法了呢?笔者认为,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只是意味着齐玉苓案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事实不清及定性不准等问题,不能认为法院的裁判文书就不能援引宪法了。
第一,齐玉苓案的核心是受教育权被侵犯。然而,二审法官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滕州八中已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齐玉苓本人,但从情理上判断,一个考生应当非常关心自己的考试结果及当地的录取分数线才是,何况考生齐玉苓第二年又重新进行了复读。如果齐玉苓的成绩单被他人领走,那么,她应当拿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成绩,或者应当听说过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成绩,而这个不属于自己的成绩又是怎样呢?所以,本案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合理怀疑。
这个合理怀疑引出了齐玉苓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侵犯受教育权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滕州八中已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了考生本人,同时,还认定齐玉苓未曾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缴纳委培费用,认定齐玉苓已放弃委培机会,其诉请被侵犯受教育权不能成立。因此,只以侵犯姓名权结案。二审法院改变了定性,认为受教育权被侵犯,但是这样的认定,必须对笔者提出的合理怀疑作出解答。
第二,在齐玉苓案中,侵犯姓名权和侵犯受教育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齐玉苓案“批复”指出,陈晓琪是以侵犯姓名权为手段,侵犯齐玉苓宪法上的受教育权,这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笔者在这里还想讨论的是,陈晓琪以齐玉苓的名字在银行工作,这是否还构成以侵犯姓名权为手段,侵犯了齐玉苓在宪法上的劳动权?在劳动过程中,可能还以齐玉苓的名义进行请假,这是否构成以侵犯姓名权为手段,侵犯齐玉苓在宪法上的休息权?因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这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理论上有待进一步论证。此批复被废除也在情理之中。
注释:
①我国许多宪法学教材都是建立在不区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部门法的宪法的观念基础上的。在分析具体案例时,有时候使用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概念,有时候使用作为部门法的宪法概念。因而,有些教材对宪法是母法的理论提出质疑(如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有些教材明确将宪法学定义为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如肖泽晟:《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利控制的学说》,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不一枚举。宪法学本身对宪法概念存在着重大分歧,如曾繁康指出:“何谓宪法?则以宪法发生长成,其所经历时间之悠久,与其规定内容之不齐一,复以各国情况不同,而每有其特殊意义之宪法,故无法归纳,加以简括之定义。因之,宪法学者乃每从其个人所持之观点不同,或就宪法之某种特征,以说明其所谓宪法,于是所谓宪法云者,其意义繁多,转而莫衷一是。”(参见曾繁康:《“中华民国宪法”概要》,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3页。)我国关于法院能否援引宪法的讨论,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在不同概念的宪法本身各说各理。笔者所主张的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并且应当援引宪法,是建立在区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部门法的宪法的基础上的,法院所援引的宪法是指作为根本法的宪法。
②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与依照本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及以合众国的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条约,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有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
③奥托·麦耶说:“宪法消逝,行政法生长。”这里的宪法就是建立在作为部门法的宪法观念之上的。他的意思是说,近代以来,由于行政权扩张,公民权利受到行政权越来越多的侵犯和威胁,而宪法作为调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已经初步建立人民主权、法治和分权、选举政治和责任政治等原则,宪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行政法作为防止和限制行政权的法律,在保障人权的作用中越来越重要,进一步生长起来,行政法“吸纳”宪法。我国许多法学院将宪法与行政法合并为一个专业,实际上是给奥托·麦耶的想法提供了注解。正是建立在作为部门法的宪法概念上,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只能是针对国家而设定的,不能适用于私人领域,因此,提出了诸如“基本权利第三者效力”理论和“国家行为”理论来理解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些理论也是众说纷纭,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西方宪法能否适用于私人领域的问题,必须转移到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概念上。
④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⑤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⑥《列宁全集》第1版,第9卷,第50页。
⑦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⑧同上注。
⑨同前注⑦,童之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