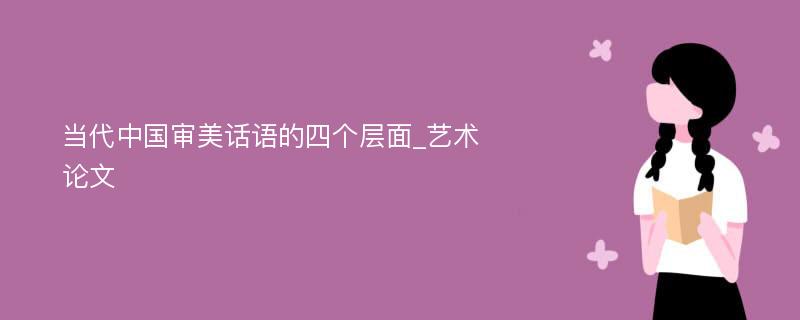
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四个层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层面论文,话语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尼采、叔本华、康德、席勒等西方美学大师的审美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激活了中国当代学者言说审美主义的渴望。但庞杂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着一条清晰的内在演进线路。综观近年学界的相关论文论著,其对“审美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比较混乱。因此,我觉得无论是从总结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而言,还是从推动当下审美主义研究来说,对其进行归纳梳理都显得相当必要。
一
在阐述和理解文学(文艺)本质和文学(文艺)研究重心时,从本体论的层面突出文学(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这是当代中国学界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的一个重要层面。
王元骧先生就是在捍卫文学审美本性的意义上,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近几年文艺理论界围绕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主张开疆拓土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与坚守阵地强调文学审美本性的学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王元骧先生的《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显然是回应这一论争的。该文指出,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在我国出现了一股消解文艺的审美属性,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相混同,并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抵制审美文化的“文化主义”。在王元骧先生看来,这种“文化主义”立场一味俯就人的感官、欲望,只会进一步助长当今社会人的物欲化倾向,并指出把文化研究看作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形态”,不仅是一种认知错觉和思想误导,而且也有悖于文艺理论的品格①。王先生对文化研究派消解文艺审美属性的指责是否有失偏颇,已超出本文的论题,这里不作辨析,他以“审美主义”来对抗“文化主义”的意图却是相当明显的,或者我们可以说,王先生之所以要这么坚定地表白自己的审美主义立场,正是为了与他不满的“文化主义”相抗衡,以捍卫文学的审美本性。章长城先生在对王国维审美主义思想的阐释中,也是这样理解审美主义的,他认为,王国维强调“重文学自己之价值”,奠立了文学审美自律体系的基石,他先是用艺术,最后是用生命践行了对审美独立的伸张,并认为王国维的审美主义思想对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怎么褒扬都不为过的②。
陈吉猛先生虽然对囿于审美谈文学的固守阵地做法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文学之为文学是多种规定的综合,是多方面本质因素协同合作的结果,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不是一个审美就能限定的,审美并没有特权,强以审美以制文学,只会遮蔽文学,钳制文学,寻求对于文学的全面性、整体性的理论掌握,对于推进我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指出,新时期文学理论审美主义倾向在争取文学独立、使文学摆脱束缚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的意义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而在文学理论研究拓展深入的今天,应该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局限,但是,在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倾向的概括中,还是不难看出,他所认为的审美主义主要是对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的强调③。这从他以审美主义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审美体验论、审美感性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和审美本质论这一理论主张中,我们清楚地看出陈吉猛所谓的审美主义,亦是从对文学审美属性的维护和坚守来理解的,即便他本人并不主张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狭隘地维护和坚守审美这块阵地。
董希文先生《矛盾与悖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论发展滞后探因》中所谓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论发展滞后,其实说的就是中国现代文论缺乏注重艺术自律强调审美本性的传统④。肖鹰先生之所以把在现代性批判中往往被视为截然相向的科学和审美主义捆绑在一起来探讨,强调的是科学和审美一样坚持宇宙的内在和谐和完整秩序,并且要求科学本身从理论形态到内容都表现这个宇宙的和谐和完整⑤。从肖鹰对科学的审美主义的阐述,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审美主义对审美纯粹性的情有独钟。
陈学祖先生和黄卓越先生则在阐述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陈学祖先生认为:中国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与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儒家伦理主义诗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经过汉代谶纬之学以及后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庄禅玄学为基础、中间以通过人物品藻和言意之辨向诗学转化的魏晋玄学为过渡、终以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的某些审美思想和钟嵘《诗品》“滋味”论的产生为标志的另一诗学传统,是以艺术的“美”为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陈学祖先生把后者称为审美主义诗学传统。这种命名强调的是,与儒家注重事功的诗学传统不同,道家(包括玄学和佛学)拒斥礼法观念和政治功利,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审美立场来观照诗学现象,并以其所崇尚的生命本真和自然性情、追求精神超越的价值向度作为评价诗学现象的尺度,树立了与儒家诗学截然相反的审美感性立场⑥。黄卓越先生在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时,与陈学祖颇为接近,但与他侧重从精神超越来理解审美主义之精髓稍有不同,黄卓越更侧重从形式感的加强这一方面来理解审美主义倾向。黄卓越所谓的“审美主义倾向”,指的是与永乐年间的重事功、重义理的台阁体文学所显示出的尚质论文学观相比,明弘正间的茶陵派与前七子派为代表的文学力量对尚质主义的诗学理念构成冲击,诗文创作中的审美要素得到了大幅度增强。该文没有对“审美主义”这个概念作任何的阐述和界说,但通读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我们不难看出黄卓越在尚质主义对立面的意义上使用审美主义这个概念,几乎把审美主义视为“文学性”的代名词⑦。他之所以从审美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弘正年间的文学,主要在于这期间的文学与“载道”说及“世用”说盛行之时的尚质主义、义理主义通行而诗道沦陷不同,大力倡导文学性,显示出强劲的审美独立性。
当代艺术家李强先生《重申审美主义》一文,虽然已防御性地把自己的立场与唯美主义的“纯艺术”倾向划清界限,但其中对审美纯粹性、独立性的捍卫亦是旗帜鲜明。李强先生之所以要重申审美主义,缘于他对当前艺术过于社会化、哲学化倾向的不满。他表示,大量的艺术家变成了社会学家、政治家,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政治思潮的运动之中,艺术被完全作为了社会批判的武器,重申审美主义,就是让它对无聊的生活和艺术现状起到一点消毒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制’之中,在人被异化的‘后工业社会’之中创造一片净土,世界自身不能生产这样的地方,而艺术可以。”⑧
徐贲先生的《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一文,也是沿着审美的超越性和独立性这一路向,从审美的纯粹性这方面确立审美主义之要义。该文认为,批评界将“艺术”和“非艺术”这一至关重要的区别引申为一系列其它的区别,如“雅”和“俗”、“精英”和“大众”、“高级”和“低俗”等等,并利用这一类对立二分定势和等级差别,使大众文化成为高等艺术的反面陪衬,从而形成了对大众文化真实面貌的遮蔽;而且,从本质上说,以审美为核心的主流美学是一种理想型的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理想美和理想艺术的原则,由此而确立的所谓“真”、“伪”艺术之间的区别,这种理想型的美学和实际的批评活动是脱离的,因为实际的批评永远必须面对一个非理想型的现实,批评的任务是讨论那些与理想境界有距离或相当距离的文化产品,实践批评不是超然的审美鉴赏,而是一种由解读和评价构成的、目的性的释义行为⑨。徐贲先生把大众文化所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归之为审美主义批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里所谓的审美主义批评其实和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当中与“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相区别的“审美批评”并没有实质的不同,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是在审美纯粹性方面在程度上作了更绝对地凸显。这从徐贲先生在提到审美主义的时候,往往在之前加上“狭隘的”这个修饰语这一细节就可以看出其用心之所在。朱庆福先生则认为,审美主义及其理论依据也并不是都错了或过时了,关键在于审美主义不能用错对象,审美主义批评以及所依据的理论若是用来针对精英文化的话,并没有太多的不合适,然而一旦用来批评大众文化,就难免产生误读。从朱庆福所谓审美主义批评只可用于精英文化而不可用于大众文化就可看出,他明显是在审美的超越性、独立性、纯粹性层面上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的⑩。
二
从功能论的角度,突出文艺的审美救赎功能,将审美视为一种生存态度,这是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第二层面内容。
由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儒家、道家和禅学均以不同的方式开辟出了走向审美生存的理路,这个层面上的审美主义话语,首先来自对中国古代美学审美人生观的建构。就儒家美学思想来说,孔子不仅以“吾与点也”的人生理想描绘出完全与天地自然相融汇的审美人生境界,还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个步骤指出了通向审美人生的具体道路;就道家审美思想而言,庄子不仅提出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乘物以游心”的体道方式,还以讲述“庖丁解牛”、“偻者承蜩”、“津人操守若神”、“吕梁大夫蹈水”、“大马之捶钩者”、“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等寓言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批匠人、船夫、游泳高手、射箭高手超越了世俗束缚而达到的不为物累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境界其实就是一种和谐愉悦的充满诗意的审美境界;就禅学来看,禅宗美学倡导“本心即佛”,既不讲苦行,也不讲坐禅,更不讲读经,一切外在的戒律、神圣的偶像、经典的教条都是多余的,追求一种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这种古代美学审美人生观与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界掀起的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反省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相结合,在学术界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观: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去挖掘审美主义的宝藏,于是乎,传统中国被研究者叙述成了一个审美的国度。在这方面,在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的李泽厚先生是当然的代表,刘小枫先生曾指出,李泽厚通过三种话语策略推进了汉语审美主义的理念系统化:一、将整个汉语思想传统审美化;二、在哲学上将心理主义本体论化——所谓心理即本体;三、明确主张审美性可以代替启示宗教(11)。对中国当代学人的古代审美主义研究,我已有专文进行评价(12),不再详细展开,这里我只是要借此指出,中国当代学人突出文艺的审美救赎功能,将审美视为一种生存态度的审美主义言说,似乎更多地从中国传统美学中寻找依据。
综观当代中国学人的王国维研究成果,在把王国维作为一个审美主义者来阐释时,更多的也是在审美救赎的层面上理解审美主义。在这方面,单小曦先生和陈鹏先生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单小曦认为,20世纪初王国维在介绍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审美主义引入了中国,也形成了他本人的早期审美主义思想,而从审美超越到审美慰藉再到审美救赎是王国维早期审美主义思想的主脉(13)。陈鹏则指出,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艺术理论不同,王国维建立的是以“审美”为核心的文艺美学解释体系,他把人生的痛苦与解脱视为人类所应共同面对的问题,视为他全部文艺美学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同时,认为美的艺术具有“解放”的功能,只有美的艺术才可以给苦痛的人生带来现实关怀,美的艺术以其纯粹的、超脱功利之念的、“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之特质,帮助人们从欲望利害中解脱出来,显示出积极的审美救赎功能(14)。
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的相关论著中,从审美救赎的层面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的,也比较普遍,刘悦笛先生和周仁政先生的观点可视为代表。刘悦笛先生认为,从美学家思想场域看,吕澂等人建构的是“唯识学的美学”,审美主义只是知识论的功用与衍义,而朱光潜思想体系中,知识论与审美主义则形成逻辑起点与价值终向的两端,到了宗白华的生命美,审美主义与美学知识论基本是叠合与交织的;从对生命的理解来看,吕澂等人只将生命视为“认知者”,强调审美是一种生命的认知活动,朱光潜的美学知识论虽也以近代认识论为基础,但他的审美主义却将生命视为“静观者”,执着于以生命的静观求解脱,宗白华虽把静观作为是一切审美生活的起点,但却更倾向于审美中“飞跃的生命”;从审美主义的逻辑构成看,吕澂、陈望道、范寿康以“移情”为环节,建构成“生命——移情——审美化”的结构,朱光潜以“情趣化”为桥梁,建构起“生命——情趣化——艺术化”的模式,宗白华则以“生命化”为纽带,建构起“宇宙图画——生命化——艺术化”的审美主义构架,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三部曲。通过这样一番梳理,刘悦笛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审美主义围绕“生命艺术化”这个核心渐次展开、步步深化,即从生命只作为起点(吕澂、陈望道、范寿康),到生命主动参与情趣而艺术化(朱光潜),到生命本身成为审美化的枢纽和灵魂(宗白华),中国审美主义得以渐次成熟,日臻完善(15)。这里刘悦笛之所谓生命本身成为审美化的枢纽和灵魂是中国审美主义成熟的标志,虽然他出于构建“生命艺术化”发展轨迹的需要,最终把重心落在了生命上,但仍不难看出其中的潜在逻辑:在突出文艺审美救赎功能的层面上理解审美主义。周仁政先生也大致沿着这个思路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他在《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一文中指出,审美主义所代表的是以艺术实践主体性与艺术自由化原则相标榜的文学认识和实践行为。根据这一认识,周仁政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诠释为审美理想主义,即一种自我精神的理想主义作为物质化社会的理想主义的对立面被标举出来,以文学的方式或者艺术的名义,“审美”或者艺术化生存被视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宗教”,个人化的审美主义变成了社会化的“审美理想主义”(16)。
王本朝先生在分析“京派”的审美主义思想时指出,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17)。事实上,这里显然把“京派”的审美主义视为一种生存态度。
郭定国先生把审美主义作为与“动物主义相对”的一个概念,这种看似诡异的对比中,不难看出他是把审美主义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救赎良方。他认为,人的生命体是美和丑、人性与兽性、心理性和生理性、审美主义和动物主义、审美的人的自我和动物的人的自我的对立斗争与矛盾统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一种是动物主义的弱肉强食论,一种是审美主义的和谐发展论,所谓“审美主义”是一种拯救人类与拯救教育的地球村人们的最高理论,也是人类为了快乐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高理论,只有信仰审美主义才能战胜动物主义,创建一个和谐发展美的人类新世界(18)。
事实上,诸多对审美主义的救赎功能持怀疑甚或批判的学者,在理解和阐释审美主义思想时,更是有意无意地突出审美主义的救赎功能。在这方面,杨霓先生和李茂增先生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杨霓指出,现代审美主义的思想核心是艺术对现实的否定与反抗作用能使个体产生一种内驱力,去质疑现代异化文明,寻得精神救赎并重新确立自我,但发轫于现代性中的审美主义却要消解现代性,审美主义变成“精英”空谈,陷入故步自封、“自恋”的怪圈,丧失了对大众的救赎功能,艺术的泛生活化和货币化颠覆了审美主义艺术救赎的主旨,这就注定了审美主义无法实现救赎,现代人在寻求精神自由时无奈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19)。李茂增认为,审美主义作为克服现代性症结的救治方案被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审美主义自身却隐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审美独立性与社会功利性的矛盾、审美多元性与审美一元性的矛盾、审美主义的人本特色与虚无主义的矛盾等,他通过托马斯·曼早期的艺术家小说对审美主义自身矛盾性的揭示,宣告了审美主义的幻灭(20)。
三
从价值论的层面,在审美与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中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这是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第三层面内容。
如果从词源去考溯,审美主义与感性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据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英文aestheticism(审美主义)的词根aesthetic的词源最早就来自希腊语aisthesis,“在希腊文中,aisthesis的主要意涵是指经由感官察觉其实质的东西,而非那些只能经由学习而得到的非物质、抽象之事物。”(21) 美学史上一度将“美学”(aesthetics)直接称为“感性学”,还有学者甚至直接把这个层面的审美主义命名为“感性审美主义”(22),很大程度上都跟这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艺术领域对感性生命和自由的肯定和放纵,福柯甚至有了“艺术疯癫”的理论。福柯指出,动物界没有疯癫,人类社会中的疯癫是人的感性本能受到文明的过度压抑而不能承受这种压抑的结果,疯癫的命名又变本加厉地为文明进一步压抑感性生命提供合法化理由,而将艺术家视为疯子并非一时戏言,而是文明逻辑早已把艺术与感性视为一体,“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的险恶因素”(23),“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24) 可以说,福柯的“艺术疯癫”理论于“片面的深刻”中对审美与感性、自由之间关系的揭示令人警醒,无论你是否认同,它至少为我们从感性、自由的维度理解审美主义竖立了一杆无法回避的相当刺眼的标杆。当然,更多的学者并不像福柯这么犀利,但诸多学者于平和冷静之中亦异曲同工地表现出了类似的思想,就审美主义问题域而言,在审美与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中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与从感性维度理解审美主义的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对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刘小枫先生用力甚勤,他在专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以一章近4万多字的篇幅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刘小枫先生首先关心的是审美性与现代现象在理念上和社会文化制度以及生活质态中的实质性关系,他通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为什么审美感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来厘清这一关系。与前述的对审美超越性、审美救赎功能的强调迥异的是,刘小枫借用韦伯的脱魅过程来描述现代社会质态,认为审美性作为现代生活的形态和质态,当指现代市民的感觉样态、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凡俗”成了理解审美主义的关键词。刘小枫对作为话语的审美主义与作为日常生活样态及质态的审美性作出了区分,他更关心的是后者,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感觉并非只体现于文学艺术之中,它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之中。刘小枫先生显然对后者更感兴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沿用本雅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方略,而是采用西美尔的社会感觉学的分析方略,以时装表演为个案,深入剖析了现代感觉的质态。另外,刘小枫还指出,汉语思想的审美主义特质,不仅在于用欧洲审美主义的论述资源和概念工具改塑汉语思想,而且它以民族价值优位论对西方思想的批判代替了现代性批判,这就意味着,审美性不是中国智慧的特质,它亦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一个或潜在、或凸显的实质性结构要素。也就是说,他以意味深长的笔法曲里拐弯地对中国审美主义是否具有独特性这个问题作了否定性回答(25)。
当然,在审美与现代性的关系上,更多的学者还是从作为反抗现代性的力量这一层面来理解和阐释审美主义。
赵彦芳女士就明确指出,审美主义是在现代性境遇中生长起来,反感工具理性的物质气息,反感客观化、科学化的理智性思维所造就的理性人、机器人,所以提出了感性人,张扬感性化生存,强调对世界持审美态度,视艺术原则、审美原则为最高的价值准则。事实上,审美主义延续了文艺复兴下释放出来的人的感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承接了价值理性的功能,为人提供目的和意义的源泉,这样,人就不是作为机器、工具,而是以一个丰富的感性者生存于世(26)。
林功成先生认为,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它既是现代性的建构因素,又同时充当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己力量,一方面它与整个现代性的目标相一致,表达了人企图确立自身心灵的准则,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行动,而不是按照外在的、来自神启或来自传统的指令来行事的强烈愿望。审美问题不仅已成为现代性问题的核心部分,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将现代性的实质定义为“审美的”,而不再是“理性的”或“现实的”(27)。在林功成看来,审美所涉及的问题,并不只是某一个特定文化中的问题,不只是对一般艺术现象和审美趣味的评判和鉴赏,而是一个以审美的逻辑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秩序,以之与旧的精神秩序相抗衡是否可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审美中心主义的出现就是对理性中心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否定。
吴晓东先生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反抗现代性的独特方式。吴晓东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同质性、整一性的理念作用于现代世界的历史叙事的时候,容易导致一元论价值体系的生成,而“美学现代性”是现代性知识体系自我解构的重要力量,具体到文学领域,“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视域与现代性问题有着盘根错节的内在关系。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吴晓东深入分析了沈从文小说《新与旧》和张爱玲小说的挽歌情调:沈从文的小说以新与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以及超越于传统—现代之外的更具兼容性的审美视角,消解了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性图景;张爱玲艺术直觉和美感意向的复杂性来自于“古中国”的情调与现代都市美感的混合,这种挽歌的美感来自于张爱玲对已逝与将逝的传统与现代文明形态的荒凉体验,正是这种荒凉体验最终超越了新与旧、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峙和分野,使张爱玲的文学想象汇入了地老天荒般的人类具有的原型性质的经验世界之中(28)。宋妍先生也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分析审美主义的要义及其多重矛盾性,她指出,审美主义产生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又在后现代性语境的影响下呈现出了泛审美的倾向,并把“审美主义”置于无论在历史分期还是精神气质等方面都迥异其趣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历史语境下剖析其复杂内涵(29)。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审美主义的局限性进行反省的研究者,其锋芒所向亦是审美主义理论中对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的高扬。赵彦芳认为,审美主义试图超越艺术、感性的范围而将自己上升为整一的“神话”,或者将美的范围内的原则扩展到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生活中时,就具有“审美帝国主义”的意味和自我中心的倾向,审美主义将感性存在定为本体性的存在,预设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审美主义中隐含着个体至上的逻辑,会走向个人中心主义(30)。与其说这是表示了对审美主义的隐忧,不如说表示了对审美主义话语中无限度地夸大感性、自由的警惕。
林功成和陈鹏对这审美主义也表示了类似的隐忧。林功成认为,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启蒙现代性的“他性”存在时,这种“他性”脱离前者的关照就失去了意义,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激情,但单凭激情无法解决现代性问题,审美如何与理性再度联袂,一如像早期的启蒙主义者那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的现实任务(31)。陈鹏认为,审美现代性不是只有积极性维度的单维存在,必须注意到作为其对立一维出现的理性的重要作用,把它放在感性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的张力结构中加以运用,如果用审美现代性原则来代替其它原则,不过是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中置换了一个主导思想坐标而已,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彻底的变化,现代社会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解放了感性,导致了非理性生存方式的“高扬”,另一方面也有审美泛化,感性沦落的趋势,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在理性的王国中提出审美的一维,提出审美的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的新地位,同时,在积极与消极之间寻找审美现代性的最佳位置(32)。
对审美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研究者,在我看来,也是“放大”了审美主义高扬感性、自由这一面。在这方面,李育红《人民性的缺失——当代文学审美主义问题的反思》(33) 最具代表性。该文把审美主义看成是一种肯定感性审美价值,并将人生价值归结为感性审美价值的思想倾向和观念,并认为审美主义问题是造成当前文学创作存在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以审美、感性、艺术性为文学艺术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价值,审美主义就造成了艺术中审美维度与现实、道德、政治、文化等维度的紧张关系,甚至使这些维度在其艺术中消失,这种直接的审美主义文学创作的枢纽就是绝对自我和自由的主体性,写作主体将世界消解成触发审美情趣和自我表现的机缘和机遇,而这里的自我和主体就是现代个人主义的个体自我和主体。顾梅珑先生在讨论审美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时,也延续了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建立在反抗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审美思潮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在置换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之后,它以极端的感性对抗极端的理性,将启蒙时代确立的个人主体性推向了顶峰,并且在多元、扩张和庸俗化进程中走向了价值的虚无,面对审美的危机,现代哲人提出的反本质论、主体间性、新理性精神等现代理念为重建审美提供了可能。审美可能是自我拯救的天堂,也可以让人更为迅速地坠入地狱,超越审美主义的困境将引领人类攀登新的生存高峰(34)。在这里,李育红先生和顾梅珑先生显然都把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理解为审美主义之主旨。
四
除以上三种情况外,我们还可看到审美主义这一术语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被使用着。有人指责卫慧、棉棉等“美女写作者”为审美主义者时,所谓审美主义成了宣扬享乐、追求快感、放弃责任、游戏人生的代名词;而当一个电子商务的策划者把商品交易网站命名为审美主义网站时,这里的审美主义成了一种高品位的象征;有人欣赏宗白华先生的人生境界,而理由是宗先生是审美主义者;而有人原谅顾城杀妻,其理由竟是顾城是审美主义者;还有眼下流行的“男人是审美主义者,女人是实用主义者”等等。这说明审美主义这一术语已走出审美城,成为一个生活用语,或者说,审美主义不仅仅作为一个理论术语,还作为泛审美化时代里一个非常富有小资情调的世俗世活中的雅词。
从“五四”启蒙文学那一代作家开始,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审美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上,似乎更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观念:日常生活是庸常的,缺乏审美特性,文学(艺术)之所以是美的,更重要的是对日常生活进行提炼和升华。对日常生活庸常性的不屑,在鲁迅那里就表现得很明显,这一点从他的小说《伤逝》的相关细节描写中就不难看出来: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35)
我引用这段原文,首先要表明的是,鲁迅事实上在他这篇充满诗意怀想的小说里,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曾经意气风发的“五四”青年子君,在饲油鸡喂小狗的日常生活中变得多么庸俗,而对庸常的日常生活表示出鄙夷和不屑的涓生则有着强烈的优越感。然而,日常生活的庸常性是不证自明的吗?卢卡契曾指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36) 刘怀玉先生也曾指出,“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保守性这些普通平常的特征,但同时也具有超常的惊人的活力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37) 这样的看法,在长期浸淫并服膺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中的人们来说,或许并不好理解。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然也表示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但它强调的是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对生活进行概括和提升以达到揭示生活本质之目的。这里对“典型”、“概括”、“提升”、“本质”的强调,明显包含着这样的逻辑:日常生活本身只是生活的表象,只有用典型的方法对其进行概括和提升才能揭示出生活的本质。沿着这样的逻辑往前走,或许就不难理解这样的创作景观了:既然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并不是要表现日常生活本身,而是要揭示日常生活背后的本质,那么作家无视日常生活所具有的“超常的惊人的活力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而想方设法以“去芜存精”的典型化手法“提升”日常生活,事实上以浪漫情怀把所谓的现实主义“折腾”得远离了现实生活。其中的吊诡,在“高大全”式的主要英雄人物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典型的时代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对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反拨,“新写实主义”显然是看到了对日常生活的漠视就无法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搅扰得风生水起的池莉、方方、刘震云等等新写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强调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反对人为地粉饰和拔高现实,真诚直面现实和人生,放逐理想,解构崇高,在题材上注重对庸常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与操劳庸碌的小人物成为作品的中心,这种对“毛茸茸”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相比传统的现实主义无疑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日常生活焕发出了充满诗性和创造性的活力。就如人生的幸福与希望应该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到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求一样,无论何种主义的文学,日常生活都是其不竭的最有活力的源泉,我想我们应该回到这样的文学常识中来。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倡导及引发的相关争论不仅将审美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还使这个问题成为理论热点。早在2001年周宪先生就开始探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当时他还没有把来自韦尔施(周宪译为威尔什)和费瑟斯通的概念“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译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将其译为“日常生活美学化”。他认为,消费社会时代“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已经崛起,其显著的特征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趋向于美化,视觉愉悦和快感体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我们越发地感受和追求视觉的快感,也越发地体验到外观的视觉美化成为主流,能否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日常生活的美学化阶段?这个阶段和艺术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文化是否有本质的不同?”(38) 在这里,周宪先生虽然相当谨慎地用了探询的语气,但那宣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已然到来的用意却昭然若揭。我觉得,国内学术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关注,大的学术趋向上看与文化研究的崛起有关,更具体地看,与2000年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先生的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译本的出版(39) 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费瑟斯通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三个含义:第一是艺术亚文化的兴起,包括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第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是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泛滥。他明确指出:“这种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位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40) 陶东风先生则将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意味着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这一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41) 金元浦先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审美性不再是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惟一特征,社会出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向非艺术领域扩张的局面,“在当今社会中,原先被认为是美的集中体现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经典的(古典的)艺术门类,特别是以高雅艺术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精英艺术已经不再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经典艺术所追求的审美性、文学性则从艺术的象牙之塔中悄然坠落,风光不再,而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则蓬勃兴起,”“美不在虚无缥缈间,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诗意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42) 类似的观点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随处可见,“我们经验中的‘文艺’很可能、甚至已经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进程中找到新的栖身之处,获得新的形态。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活动不一定非得在文学艺术那里开展不可。”(43)“以文学为例,它的华丽辞藻游走在电视的广告词中,它的浪漫激情出没在时尚杂志和报纸的专栏文章中。”(44)“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街头、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生活场所。”(45)“人在日常生活里的视觉满足和满足欲望直接相关的‘视像’的生产与消费,便成为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核心。”(46)
鲁枢元先生则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加以严格区分,反对“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他认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观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渡,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47) 从鲁枢元先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导中可以看出,他不赞成将审美泛化为日常生活的润滑剂,而是在“高贵”、“精神”等层面强调审美对日常生活的提升。
以上对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现状作了一个粗略的综述,将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概括梳理为四个层面内容:一是从本体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二是从功能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救赎功能,将审美视为一种生存态度;三是从价值论上,在审美与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中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四是作为泛审美化时代里一个非常富有小资情调的世俗生活中的雅词。当然,审美主义这一术语在当代的运用,要比我这样条分缕析的分析复杂得多,即便以上梳理出来的四个层面,在实际的理论运用中也常常是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的。
注释:
① 王元骧:《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章长城:《试论王国维审美主义思想》,《龙岩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③ 陈吉猛:《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倾向论略》,《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④ 董希文:《矛盾与悖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论发展滞后探因》,《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⑤ 肖鹰:《科学中的审美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陈学祖:《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⑦ 黄卓越:《明弘正间审美主义倾向之流布》,《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
⑧ 李强:《重申审美主义》,《艺术家》2005年第5期。
⑨ 徐贲:《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⑩ 朱庆福:《审美主义视角下大众文化批评的反思》,《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1)(2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9—351页。
(12) 叶世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再论现代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3) 单小曦:《王国维早期审美主义思想——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理论的肇始》,《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6期。
(14)(32) 陈鹏:《理解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5) 刘悦笛:《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审美主义思潮论》,《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
(16) 周仁政:《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7) 王本朝:《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8) 郭定国:《论审美主义和动物主义——两种全球化的理论思潮谁战胜谁?》,《美与时代》2008年第6期。
(19) 杨霓:《现代审美主义救赎刍议》,《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
(20) 李茂增:《审美主义的幻灭——托马斯·曼早期艺术家三部曲解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1) [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22) 余虹:《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3)(24) [法]福柯著,刘北成译:《疯癫与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6页,第269页。
(26)(30) 赵彦芳:《审美主义辨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7)(31) 林功成:《现代性与审美主义》,《湖北师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8) 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29) 宋妍:《审美主义要义及其多重矛盾分析——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进行探讨》,《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
(33) 李育红:《人民性的缺失——当代文学审美主义问题的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34) 顾梅珑:《审美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35)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36) [匈]卢卡契著,徐恒醇译:《审美特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7) 刘怀玉:《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见李小娟主编的《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38) 周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39) [英]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版。
(40) 同上书,第97-98页。
(41)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媒》2005年第1期。
(42) 金元浦:《别了,蛋糕上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43) 阎景娟:《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44) 朱国华:《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45) 蒲震元、杜寒风:《美学前沿》,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46) 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47) 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标签:艺术论文; 美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王国维论文; 艺术与审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