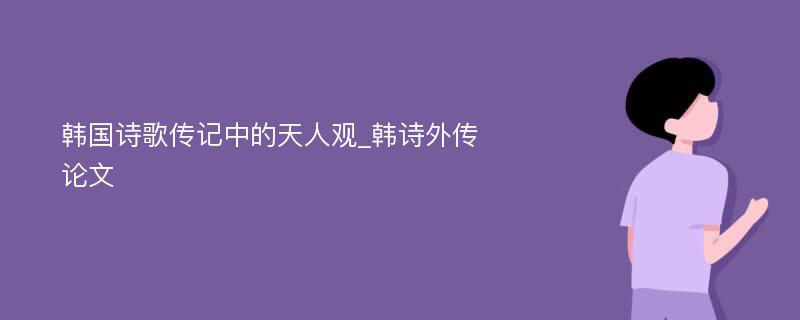
《韩诗外传》的天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道论文,外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4)02-0045-04
西汉韩婴传授的《诗经》即是齐、鲁、韩今文经“三家诗”中的韩诗一派。目前,“三家诗”的其他著作都已亡佚,只有这部《韩诗外传》传世至今。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韩诗外传》的研究甚少,对其评价亦甚低。其主要原因是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时代,“韩诗颇与齐鲁间异”[1](P1083)。在士人把经书奉到至尊地位并且“皓首穷经”的风潮中,《韩诗外传》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
就《韩诗外传》本身来说,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线,但同时吸收道家及其它各家思想,各家学术杂糅捏和的痕迹斑斑可见,表面显得非常“驳杂”,而且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这应该是其不被世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作为汉初儒家学者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婴与汉初的叔孙通、陆贾、贾谊一样采获各家,共同构造了汉代的“新儒学”。他们的思想都是以儒为宗,本同而异末,各自代表了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而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努力从理论上拓展原始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并且将其付诸于社会实践,但其论证往往限于仁、礼本身。韩婴则将这些理论与其构建的有意志的“天”结合,为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的真理性寻找“天命”依据。韩婴的天道观是汉代儒学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环。至董仲舒,儒学便发展成为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完成了儒学的学术整合。也就是说,韩婴吸收改造了《周易》、《诗经》等经典中的天命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为董仲舒构建系统完整的“天人感应”理论起了先驱的作用。
一、“同类相动”观点
中国古人强调阴阳五行与四时四方的相互配合。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别与春、夏、秋、冬相配置,东、西、南、北、中相互呼应,结成一体,相互生克,动荡不息,故“沧海为之桑田,别迁于天命,而变乎人事。”用系统论的观念来看,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每个系统都具有相同的一部分物性(元素),因此具有通达或蕴含等关系,系统与系统之间就可能互相演算。古人笼统地称之为“同类相感,同类相动”。
《韩诗外传》认为自然界中的人和其它事物都有着“类”的划分,“君子洁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类者应焉。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2](P13)。人类中有着“君子”类,“善者”类等,动物中的牛马也是各归其类,并且能“同类相动”。《韩诗外传》卷一借助钟鼓乐器的感应和作用说“此言音乐相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2](P16)在这里也提到了“物类相感”。
秦汉之际,随着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自然界中的一些联系,如声音共鸣的现象,天气的变化对人们身体的某些影响等。韩婴利用这些自然界中人们已知的科学知识,将自然界中的事物按照“类”划分,这首先为其“同类相动”、“物类相感”找到了“科学依据”,增加了人们对其学说的信任,这也就顺理成章地为其后面提出天人能“感应”,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上天”能作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前期的理论铺垫。
二、天人感应思想
天人关系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议的重要哲学课题,也是儒学内部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孔子的“天”基本上是自然性的,如“天何言哉,是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是有规律可循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并认为天以“天命”的形式作用于人,人应当“知天命”,“畏(敬)天命”,遵循天命行事。在这里,天和人是一种亲和关系。但是他又说过“天丧予”,“天厌之”,似乎天又是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神。此后,出于对孔子言论的理解分歧,因而在儒家内部,出现人格之天和自然之天的分野。
《韩诗外传》继承和发展了《诗经》和孔子赋予“天”以情感及人类道德属性使其具有无上权利意志特点的理论。韩婴主张“人格之天”的观点。天之人格是通过“谴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谴告”是指通过灾异和祥瑞来表达“天”对君主的爱护、关心和惩罚。如果“国无道”,则会让“上天”非常生气,并且通过各种异常现象表现出来,如水旱灾、火灾、虫灾、地震、日月蚀等等。“天”不仅有意志、有情感、有目的,而且全知全能,有主宰一切自然变化和人世祸福吉凶的无限权威和能力。
《韩诗外传》卷二曰:“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2](P74)国君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正确的做法,就会有旋风猛烈疾速地刮起来,天降暴雨使树木都折断,阴阳会错乱,夏天寒冷而冬天温暖,春天很热而秋天却开花;太阳月亮没有亮光,天上的星辰运行位置错乱;百姓很多人染上疾病;一切生物都提早死亡,各种粮食作物也都没成熟就死了。自然现象中的这许多异常情况韩婴都有所列举,并把它们定义为“天谴”,由此说明上天的意志。
如果君王能够顺势而行,行为与天道合一,那么上天就会对其嘉奖,这以“祥瑞”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成周之时,阴阳调,寒暑平,群生遂,万物宁。故曰:其风治,其乐连,其驱马舒,其民依依,其行迟迟,其意好好。”[2](P74)和平时期阴阳调和,呈现出一片风调雨顺的景象。
《韩诗外传》卷五曰:“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满车,长几充箱,民得而上诸成王。成王问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几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下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与是来也。’周公乃敬受其所以来。”[2](P180)
周成王时,有三株禾苗穿过田边的桑树枝高高地长出来,共同结出一个大稻穗,大得几乎装满车厢。这种“天瑞”、“三苗同一秀”预示着国家即将统一,果然过了三年越裳氏的使者就来送礼物,国家统一。这种把某些罕见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说成是帝王受命之符的说法即所谓的符瑞说。符瑞说认为帝王统治的和平时期,会有各种祥瑞降临。“三苗同一秀”即是这种祥瑞。另外,在当时的传说中还有凤凰、麒麟等祥瑞。
《韩诗外传》卷八曰:“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2](P277)即只有凤凰能在上与天降的福气相通,在下与地上的灵气相应。如果“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2](P288)治理天下的办法,有一点得到凤凰的赞许,它就会飞过这地方;有两点得到凤凰的赞许,它就会在那里盘旋飞翔;有三点得到凤凰的赞许,它就会落在树上歇息;有四点得到凤凰的赞许,它就会春秋两季都要降落到那片土地上;有五点得到凤凰的赞许,那么凤凰就永远住在那里。黄帝面对铺天盖地飞来的凤凰,两次下拜并行稽首礼,说上天降临福泽,我哪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凤凰就止歇在黄帝东园的梧桐树上,吃黄帝的竹实永远也不离开。
“谴告”说的实质是人间政治上可感天,“国有善政,天乃出祥瑞以奖励之;国有恶政,天乃出灾异以谴告之;尚不知改,乃生祸乱以丧败之。”这一思想发展到西汉末年便形成了虚诞无稽的谶纬神学。但是,“谴告”说在当时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在封建大一统的社会中,上天的儿子即“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子代表“天”的意志,因此也就受到“天”的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腐败,有了“天谴”也就使“天子”的行为受到了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天谴”内容正是对《诗经》中的“天命靡常”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天谴”正是“天命靡常”之“天怒”在人间发挥作用的表现。这其中有愚弄人民的一面,但是同时也对国君的权力有所制约,在人间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子”要受到“上天”的监督和惩罚,这是对“君权神圣”的封建思想的一个挑战。
三、以德配天思想
尽管天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人们在“天”的面前并不是消极地顺从自然命运,被动地接受一切,人的作用可以影响“天”的意志,这是始终贯彻在《韩诗外传》中的思想。这是对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德配天的思维方式,并不忽视天的作用,但却十分强调人的主观努力。这就必然冲淡天作为人格神的神圣性,动摇了人们对于天的绝对依赖性。既然天命转移的根据是人的行为,那么人只要把握好自己的行为,也就等于把握住了天命。
《韩诗外传》卷曰:“昔者周文王之时,莅国八年,夏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者君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是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又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移之。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遂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践妖也。”[2](P81)
文王得病卧床不起并且又发生地震,君臣上下一致认为这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群臣的主张是通过征发徭役、动员民众来加高首都城墙的办法来转移地震,而文王却认为这样会加重自己的罪过,他采取的措施是更加谨慎地对待礼仪法度,挑选质量好的皮革来和诸侯交往;更讲求交际言辞和聘礼,来以礼相待国中的杰出人士;颁布爵位、等级、田地来奖赏大臣们。于是文王的病好了,而且地震消除。因此,韩婴在这段话最后总结说,这就是文王用来镇压妖异现象的做法,并且用《诗经》的话为自己作论证说:“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即畏惧上天的威严,设法保守住自己的国家。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韩婴对“天”的极度敬畏,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人为,突出强调的是《诗经》中的如何“保”自己国家。人们可以“自求多福”,而且实行的措施都是儒家的仁政主张,即人与天可以靠着儒家的德统一起来。在天命与人为的关系中,《诗经》重点突出“畏天之威”,要求人们对天有敬畏之心,而韩婴把重点转移到提醒人们如何“保”,这就把对人们要求的重点从“畏”转移到“保”,标志着韩婴已经把天所赋予人的“命”转换到人自己的手中。这样,人就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命,而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地为自己“立命”了。同时,韩婴主张“天德”的内容即儒家的仁政,从而为儒家的仁政理论找到了天命的根据。这样也就为其规劝统治者实行德治进行了合理性论证。
《韩诗外传》卷三记载了“不吉之物”榖树的出现。伊尹说:“臣闻妖者祸之先,祥者福之先。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臻。”[2](P81)伊尹认为虽然妖异是灾祸的先导,而吉兆是福事的先导,但是见到妖异就做好事,那么灾祸就不会到来;反过来,见到吉兆后如果干坏事,那么幸福也不会降临。所以,“汤乃斋戒静处,夙兴夜寐,吊死问疾,赦过赈穷,七日而鈆亡。妖孽不见,国家其昌。”[2](P81)因此,不吉之物的消失,国家的重新昌盛还是由于皇帝汤努力的结果。当鈆树出现以后,成汤就进行斋戒,自己安静地住着,不与妻妾同房睡觉。他起早睡晚地勤劳工作,对有丧事的人家表示哀悼慰问。看望有病的人,赦免有过错的人,救济穷苦的人。这样过了七天,鈆树就自己死了。妖孽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更加昌盛了。有意志的上天的确存在并且能作用于人,但人的行为也会对上天的行为产生影响,人的力量可以在“德”的自我约束中参与“天”的运作。
《韩诗外传》卷二认为“星附木鸣”等自然现象,都是“物之罕至者也”。人们对它们“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因为如果“上明政平,是虽并至无伤也;上政险,是虽无一无益也。”世界是否太平,社会是否安定,关键取决于执政的人是英明还是昏庸。因此说“夫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2](P38)
人们对于天的理解,从殷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由神秘莫测的占卜对象变成了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可以掌握的对象,人作为天命的执行者,也就从对天的盲从迷信中解脱出来,人靠着自我的主观努力,追求永远的天人合一。在《韩诗外传》中已经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在自然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视。
四、结语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韩婴生活于文帝、景帝、武帝时代的燕地,即今北京,年稍稍长于董仲舒。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论辩于汉武帝前,史称“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1](P1083)二人都在为影响皇帝、复兴儒家思想而努力,他们之间的哲学思想虽有许多相异的方面,但其一致性也应当注意,这在天人感应理论上尤为明显。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有专门的一章“同类相动”,并且有“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3](P286)的原话,可见在董仲舒建立自己的系统理论之前,韩婴在这方面已经先有了初步的思想。韩婴在《韩诗外传》中借助钟鼓乐器的感应和作用说:“此言音乐相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2](P16)在这里也提到了“物类相感”。董仲舒的“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3](P286)的说法,也是利用共鸣原理来说明“物类相感”命题。
董仲舒在其天人感应哲学思想体系中,提出了“天人同类”作为天人感应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他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P267)他认为天既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3](P242)从人的身体结构和道德情感看,人和天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天的“副本”,这叫做“人副天数”。在这方面,韩婴也有类似的思想,但他没有构筑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如他也同样利用共鸣、共振、天气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等自然规律提出“同类相动”,然后大量地论证了“天人感应”。但是“同类相动”为什么能推导出“天”与“人”的相互感应?这中间缺失了“天人同类”理论,就使他的整个逻辑推理过程失去了中间环节,因而最终没能形成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
“从陆贾到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作一种持续不断前后相继的发展,一种有着共同目标和倾向的思想运动;一方面又可以看作一种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新体系的建立)的‘飞跃’。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是飞跃和质变的完成。由于它以新的基础和面貌出现,从而使儒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4](P109)韩婴与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前承周秦之季,后开董子之风,是汉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儒学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环。韩婴的天道观思想在这个承转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4-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