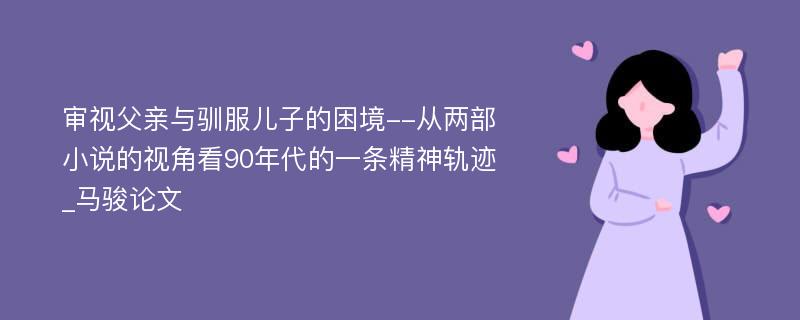
审父与驯子的两难——从两篇小说看九十年代的一种精神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篇论文,轨迹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坛每每会出现一些巧合的现象,却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苏童于九十年代末写出了中篇小说《驯子记》(《钟山》1999年第4期),令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九十年代初,王朔曾发表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收获》1991年第3期),恰恰也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驯子记”。两篇小说都以父子之间的种种冲突和情感对应为主要内容,仔细读来,却透露着不那么相同的气息。文学作品中的父子角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血缘关系上的父与子,在具体性的父子冲突背后往往蕴含着超越性的结构:伦理的、历史的、文化的。父/子,成人/小孩,启蒙者/被启蒙者,历史/现实,现实/未来,传统/现代之间的同构关系,使父亲的脸上永远重叠着含义丰富、模糊不明的面影。《我是你爸爸》中的父与子,暗含着现实与未来的关系,《驯子记》中的父与子,则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时代之初的前瞻与世纪末的回望,倒也暗合了两位作家惯常的写作姿态。
新时期大多数表现父子之间的作品往往都是站在儿子的立场审视父亲,审父一直是当代小说一个隐蔽的主题。审父主题的小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带有明确社会历史文化批判内涵的小说,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等;另一类是父子角色身份暧昧的带有寓言性的小说,主要是先锋作家的作品,如余华《呼喊与细雨》、《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苏童《一九三四年逃亡》、《米》、《舒农》等。但是这两类小说似乎都缺少父子之间的直接面对,主要是“父亲”的几乎不在场。而正是在父子对应互视这一点上,《我是你爸爸》与《驯子记》具有了可比性。
有别于早期那些玩世不恭、散发着“破坏”气息的小说,《我是你爸爸》是王朔作品中较为真切和沉重的一篇。小说有点新写实的味道,虽然依旧带着一以贯之的对类知识分子的刻薄和调侃,但对父子两代人角色的细腻入微的探讨却意味深长,从而使父子角色超越了个体性的具体形象而具有了普泛性的抽象性,也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马林生曾是一个自命不凡、专制霸道的父亲形象,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没有两样。当他觉察了儿子的对抗和拒绝姿态之后,试图有所改变,于是,表面上维持稳定的既定规范和秩序随之破碎。
小说是在父亲对儿子的交流-压制这一不断更替的过程中展开叙述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父亲的马林生屡屡受挫。他第一次试图与儿子交流是因了少年世界那片无拘束自由天地的诱惑,马锐与夏青毫无保留的密切交谈勾起了他对往昔真纯岁月的深切怀恋,但他无从介入,对于孩子们而言,他是一个粗暴的不合时宜的侵入者。然后发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挑战成人世界的事件,马锐上课指摘老师的错误被视为目无尊长,而他还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是“尊重真理”。马林生又愤怒又担忧,以过来人的经验,他知道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放弃个性,认同正统文化和接受现行规范、权威和法则的过程,他预见了一个行为与世乖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现实命运,他必须无情地干预,必须让儿子为成长付出代价。这一次驯子生动地演绎了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注: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使马锐深受伤害,也使马林生面临更深的拒绝。于是马林生第二次痛下决心与儿子交流,他决心放弃为人父所有的特权和地位,与儿子平等相待,做同志和朋友。但他一方面心理时时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民主姿态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他放弃了赖以存在的功能性符号指征,也就丢失了自我,“他过于依赖儿子了,甚至超过了儿子对他的依赖”,当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并未换回他所期待的回报,他又愤怒又伤心。王朔在这里灵机一转,让马林生发现了子辈的残酷的同时,又让他借助儿子的立场发现了这种残酷恰是生命的本质,无可更改:父母生出子女当然算不了有恩,前前后后,今日之父是昨日之子,今日之子是明日之父,大家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这是进化意义上的残酷,正如后浪推前浪,新枝催老叶。父母只有自爱,才能爱子,只有自己独立,才能“完全解放”孩子。然而“父亲”这一类的文化角色对自我的狭隘和限制视若无睹,反而极力维护已有的特权。马林生第二次驯子集中了成人世界所有的丑陋和蛮不讲理:勾结串连,偷翻书包,掏衣服兜,抄捡抽屉,强看信件和日记。他的名言:“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包括你的生命!人权?你还少扯这个!”但这次发作伤害更深的其实是他自己,在反思中,他想起了多年前那种初为人父的喜悦和激动,那个为了孩子幸福可以舍弃自己的誓言,这些都不知不觉间在粗糙的生活中丢失和遗忘了。经了这两次大起大落,马林生看破红尘,“我哪儿是为自个活着的呀?我净尽责任了。你没想到我是这么个人,那是我把自个扭曲了!……”他要活回自个,然而丢弃责任、只为自己活着的人生是多么虚浮无着,放弃了生命的尊严,父辈在孩子的眼里是多么可怕,而这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马锐对于支配着正统文化也被正统文化所支配的成人世界和既定的社会规范始终怀着本能的抗拒。他保持沉默也好,唯唯诺诺也好,或是胁肩谄笑、曲意奉承,这些表象背后始终隐伏着反抗和否定。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拒绝有可能成为新一代成长者普遍的态度。他们最不屑于成人的虚伪,他们对一个人最轻蔑的评价就是“假得厉害”。作为儿子的马锐其实对父亲看得很分明:自命不凡,蛮横狂暴,志大才疏,怯懦无能,委琐自卑。但对父亲最犀利最无情的审视还是这一段:马锐恍然大悟,“其实他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能折腾会玩,也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为具体的苦恼或巨大的忧患所困扰,他的悒郁更多的是来自无聊,无以排遣空闲的时间。他根本不会玩也没有培养出任何别致的情趣,只对吃熟悉……除了吃还是吃!”对父亲和成人世界的反感和失望,更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马锐遭受了成长过程中难忘的深创巨痛。离开了社会的既定规范和“合法化”系统,注定要大吃苦头,但是立意否定和拒绝的理性一旦产生,再也冲刷不去,“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别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血缘亲爱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当然是永远不可否定的,但是深远绵长的文化所强加给符号的角色功能则遭到了断然的拒绝。
在成人世界和少年世界的对比中,在父与子不断的精神冲撞和互视中,作者于否定现实的同时,似乎对未来前景满怀希望。断然的拒绝之后,是否意味着从此可以挣脱以往一切文化神话的粘附,是否可能出现新的天地和新的气象?
《驯子记》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香椿树街的市井故事。国际海鲜城陪酒员马骏为了帮助前妻推销如意发财酒,因喝多了这种用工业酒精兑制的假酒而中毒身亡。但这显然仅是作者设置的象,从小说题目可知,作者意在表现事件发生前后日常生活中父亲马恒大和儿子马骏屡次冲突背后所隐藏的意味,现实生活中的父子冲突也还是象,而在关于这些冲突的话语叙述背后所潜在的,才是作者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马恒大与儿子的第一次冲突缘于马骏背着他偷偷更换了职业,由凤鸣楼的厨师变成了国际海鲜城的陪酒员。陪酒在马恒大的眼里意味着吃大户,是没有廉耻、丧尽人格、丢祖宗脸面的事,他差点被气死。于马骏闭着眼承受父亲巴掌的联想中可知,马恒大从小就对他家教极严,在所有的过失中,没有骨气是最受痛恨的一种,是要招致最大的惩罚的。马恒大这一次驯子的功绩是打到了儿子的要害(喉管),让他吐了个七荤八素,差点废了他陪酒的武功,导致了不久之后马骏在海鲜城地位的下降,为儿子“新前程”的断送打下了基础。
父子之间的第二次冲突是因为马骏看黄色录像。马骏一时说漏嘴,争辩道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外面的小姐要多少有多少,而且很便宜,用不着靠老婆。儿子在工作方面不务正业,在婚姻方面又走歪门邪道,这一次把马恒大气得进了医院。受罚跪在母亲遗像前的马骏也在潜伏于灵魂深处的幻觉的浮现中恐惧地预见了只有死亡是自己最后的逃脱地。父亲带给儿子的身心压抑已达到了极致。不过马恒大的这一次驯子还是有所成效,至少马骏在陪酒中拒绝了台湾林老板漂亮的女秘书的诱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马恒大最后一次驯子是在濒临死亡的儿子的病床前。他训斥马骏因喝酒进医院纯属活得多余,但当他敏感地触摸到死神的阴影时,强大的父爱随之迸发。马骏提出最后的遗愿是要打还他一巴掌,他在沉默的反思中意识到自己平生也有打错的时候,于是答应了儿子的请求。马骏死后,马恒大当然是伤心,但镇定之后,他要求与儿子同归于尽,不是因为伤心,而是为了在死后继续教驯儿子。
这三次驯子都是马恒大主动挺身而出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有没有马骏主动挑起的父子间的战端呢?有。马骏因酒量下降而与总经理表弟发生龃龉,在龃龉中一向强硬的他自觉放弃了抗争,这意味着他对金钱这个当下世俗生活主宰的臣服,也意味着他历来心理优势的丧失,尤其是前妻蒋碧丽在表弟面前的刚烈、有骨气,更对比出了这一点。自信的丧失导致了他在与前妻的较量中威严扫地,反招致了蒋的沉重一击。追根溯源,所有这一切都是马恒大第一次驯子造成的后果,而他还在四处奔走,干涉马骏目前的生活方式,竭力要把儿子拉回过去的日子中。马骏忍无可忍了。作者不失时机也不无所欣然(带着重操旧业的熟练)地来了段“夺宫”前的心理铺垫,但是小说并没有出现我们阅读经验中的“杀父”场面。在年老力衰又瞎了眼的父亲面前,马骏不孝的勇气莫名其妙地随着时间流逝一点点消失。他再一次体会到了在父亲面前那种宿命般的逃亡感,父亲是永远不可抗拒的。他的稍稍有点不逊的姿态,也就是用手指的上半部分推了一下父亲的肩膀,就被父亲看作是用刀子捅他,这与其说是父辈的狡智和无赖,不如说是父亲的心理感应,他所要求的是长幼有序、恪守伦常的规范,儿子敢于动一根手指头都是对权威的侵犯,对他的大逆不道。马骏只有臣服。但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当他终于走上命定的逃亡之路,摸到了死亡这个对抗父亲的唯一武器,他可以反抗了,他终于可以要求打还父亲一巴掌了,他终于可以在精神上与父亲平等对视了,可是,“不能打,你是我爸爸”。马骏最后在空中划了一下的也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这个手势满含了儿子对父亲的所有复杂感情。于是,一切过往的挣扎奔突和斗智斗力,都在刹那之间尘埃落定。
父亲马恒大的形象显然深具象征意味。他一出场便与众不同,他是盲人,但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心知肚明,他能听出现在的时间过得比原来快,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也的确有别于传统的过日子。他对马骏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甚至马骏心里想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所谓知子莫如父,这也是他教驯儿子的根据。他驯子的方式虽然粗暴,却最终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些是否暗示了父亲、权威、历史、传统等虽然有盲目的一面,却决定着现实的方向,并且不可否定?民间向来与意识形态具有同构性,赞赏长幼有序的香椿树街正如鲁迅笔下的未庄,正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儿子马骏的反抗始终较为隐晦和软弱。他一直试图在父亲的规范之外干点什么,但无一成功,顶多在自己打自己巴掌时稍稍占点便宜,类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一生中最大的反抗是更换职业,试图借助商业文化的介入走出父亲给他规定的老路,但这恰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步入商品社会便要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这里无所谓“六亲不认”,无所谓“见利忘义”。用宗法社会的人情对抗商品社会的经济规则,他逃脱不了被炒鱿鱼的命运。正是预见了自己不得不走回父亲的屋檐下这一点,他悲伤而愤怒地喝掉了自己的性命,有意无意地踏上了最后的逃亡之旅。离开了父亲的制约和引导,子辈究竟会走向何方?又能走向何方?
细细回顾起来,一切似乎都有迹可寻。审父曾是先锋小说的一大主题,在先锋作家的笔下,父亲这一“菲勒斯”形象往往被作为“传统”、“规范”、”制度“或“权威”的象征而遭到拒绝和颠覆。审父乃至弑父在余华和苏童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父辈们被夸张扭曲地呈现并遭到无以复加的亵渎。作家笔下那种竭力摆脱丑父阴影的精神逃亡充满了对已有文化价值的怀疑和拒绝:“我象父亲。我一路奔跑越过夜色迷离的城市,父亲的影子在后面呼啸着追踪我。那是一种超于物态的静力的追踪。我懂得,我的那次拼命奔跑是一种逃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然而转变不久就开始了。陈晓明在《无望的救赎:从形式到历史》一文中指出:1989年3月号《人民文学》推出一组“新潮小说”,包括格非的《风琴》、余华的《鲜血梅花》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这几部小说恰如其分地完成了先锋派一个类似仪式的写作;尤其是《鲜血梅花》,“缺席的父亲”被记忆唤醒,“为父报仇”不过是“寻找父亲”主题的变种,对“父亲”(历史)的忧伤记忆及讲述历史颓败的故事成为无父的子们又一次的祈祷。余华恰当地写出了找不到父亲的历史命运,但却象征性地预示了弑父仪式的终结。(注: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中国的作家骨子里缺少不了父亲,缺少不了精神和价值导向。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作家笔下似乎也流露了这种精神端倪。曾被作为1987年后的“后新潮小说”作家与余华、苏童、格非等人归为一类的陈染,她笔下的那些有着恋父倾向的女主人公身上不正打上了作家自己的精神烙印。寻找精神之父,寻找漂泊的灵魂最后的皈依地,也就是寻找精神家园,这种焦灼的呼唤却被淹没于一片“身体抒写”之中。之后,先锋作家纷纷转向历史(家族)故事的叙述,如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正如形式写作强烈的话语欲望背后不乏对文化精神的焦虑思考,从形式遁入历史也并不意味着作家对现实的冷漠。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面目渐渐明晰。传统意识形态对精神抑制的威胁依旧存在,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来自商业文化的挑战。在商业文化的熏染下,人的存在集中明确地被指归为物质性的生存,精神遭到无情的嘲讽和侮弄,竞争日益加剧,世俗性的成功成为独尊的价值标准。一方面是记忆深处对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延续的习惯性的怀疑和拒绝,另一方面是步入新环境遭遇的无可避免的心理受挫和失重,这一代作家究竟何去何从?于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次决然的满负着绝望和不甘的逃亡,到九十年代末这次犹疑的带着无奈和惶然的逃亡,便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总之,苏童在这里不无悲观地道出了“父亲”是中国人的宿命这一历史现实悲剧。从五四到现在,所有对“父亲”的反抗无一成功,“菲勒斯”中心不可打破,中国人只能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苍老的婴儿,他们不是臣服于权力,就是臣服于金钱,独立人格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这样的父亲只能出产马骏这样丑陋的下一代。给马骏这一形象打上阿Q的精神烙印,也许更深地传达了一种悲凉情绪。作者在这里再一次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发出了世纪末的深长喟叹。他在现实的叙述中不知不觉揉进了自我话语,使市井故事的讲述掺杂了寓言的色彩。而在对父/子,历史/现实,压制/反抗的暧昧态度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用形式写作残酷肢解历史的先锋作家为自己的“文化救赋”或曰“自我救赋”作了一个无奈的定格。
如何处理儿子和父亲、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困境。这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父亲”的存在大致有这样三种类型:“五四”新文学中的家庭和家族伦理,“他”遭到了启蒙精神的颠覆;延安文学至文革文学中虚拟的革命英雄和政治乌托邦,“他”得到了政治理性的重塑;新时期文学中作为“根”被寻找的文化,“他”受到了非理性精神的审视和怀疑。但在实际的情形中,作为他律机制的“父亲”和作为自律机制的“儿子”(自我)之间,有着太多复杂的情境,绝非颠覆、重塑和怀疑那么简单。自我一方面反抗压制,追求自由,而获得自由与感到孤独是同一个个体化过程的两个方面,人获得的自由越多,滋生的“个人无意义感和无权力感”便越强,因此,为了克服孤独感,他们“逃避自由”(埃里希·弗罗姆)。在“五四”新文学的表层,人们对传统的反叛确实很彻底,反传统因素在不断成长壮大,但传统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他”也在不断演化,在人们的意识深层处,“他”顽固地存在着,而人们也借此与周围达成某种默契。延安文学和文革文学时期,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式的民族国家建构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类型之一的话(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显然也存在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之间的问题,而在文学实践方面,他律机制和自我之间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相一致的关系,延安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整风之前的一些文学现象(如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在医院中》,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等)以及文革后反思、伤痕和改革文学从政治和制度上对“父亲”进行清算便是明证。新时期文学中,传统文化这个被寻找的“父亲”,遭到了先锋作家的审视和怀疑,但他们拒绝了这一个,却寻找不到理想中的另一个,于是如何对待这一个“父亲”便成为他们心中的两难。九十年代出现的“游走的一代”,以及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类”(卫慧、周洁茹、金仁顺、朱文颖等),他们也许是真正在精神气质上远离父亲的一些人,但他们患有精神贫血症,散发着世纪末的颓废气息,如何对待父亲的问题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王朔《我是你爸爸》和苏童《驯子记》都写出了作为他律机制的“父亲”和作为自律机制的“自我”之间的复杂情境,写出了现代伦理的两难选择。体现在文本中的对父辈的不同态度(拒绝或逃亡),显示了两位作家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对历史文化的不同理解。王朔《我是你爸爸》虽发表于九十年代初,但它其实是八十年代的精神成果,带着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气质;苏童《驯子记》则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精神的一个总结。王朔《我是你爸爸》主要表现父子伦理和观念的冲突,描写更多地集中于现实生活层面,因其体察的入微及描述的深刻而具有了文化的内涵;苏童《驯子记》则更具形而上的意味,不经意间散发着他的作品常带的宿命气息。王朔于日常生活语境中探求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不无乐观的向往;苏童于商业文化语境中反思历史与现实,却流露出悲观的世纪末情绪。在王朔《我是你爸爸》与苏童《驯子记》的互读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用不同方式立意反抗的一代作家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所走过的精神轨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注: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一种理想的未来,关键是现在。看清楚了以后,在马骏迟疑的逃亡之后,会不会有鲁迅式痛切的承担,在悲观的九十年AI写作作之后,新一世纪的文学能否实现超越?我们只能等待。
标签:马骏论文; 苏童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我是你爸爸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父亲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