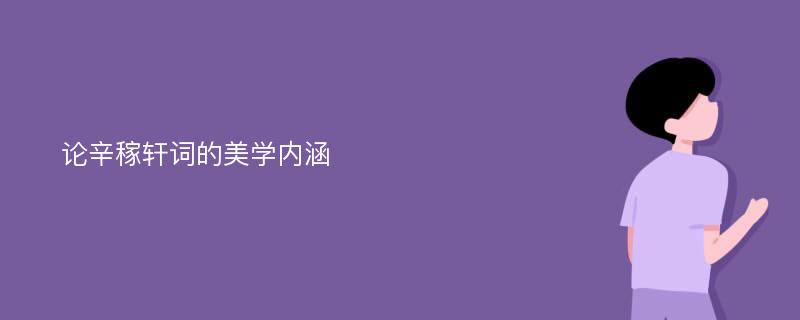
于永森[1]2010年在《论豪放》文中研究说明“豪放”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民族特色、反映着一种积极刚健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美学范畴,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生、思想精神和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古至今,对“豪放”的研究基本上都局限在词学的领域之内,而对其前期的发展嬗变及内在的深厚内涵,则很少有人研究。把“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来进行全面探讨的,更属阙如。本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力图从美学范畴本体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豪放”的发展、嬗变的历史,根本思想精神、哲学辩证法精神和诗学精神,内涵和生成,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等等内容;一是集中研究了“豪放”范畴涉及到的主要理论问题,探讨了“豪放”和“婉约”(及与此有关的“本色”、“中和”等范畴)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而确立“豪放”的价值及其在古代诗学、美学中的地位,为中华民族新的审美理想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参照。文章共分为十个部分:导言:主要探讨了“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美学及范畴中的地位及本文选题的由来,关于“豪放”范畴研究的情况综述及研究“豪放”的逻辑起点,阐明了本文研究的方法和逻辑思路。第一、二章:主要探讨了“豪放”的形成和嬗变。“豪放”萌芽于先秦中国传统文化奠基的历史时期,是社会礼法制度逐渐加强、腐朽并形成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的产物。其中“放”的一面最先起步发展,并在老庄思想中得到体现;而“豪”的生成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理想。“豪放”在魏晋人的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过南北朝及隋代的酝酿,在唐代的文学艺术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和体现。宋代是“豪放”发展为一个基本美学范畴的时期,尤其在词这种文体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趋于成熟,但是它在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中并不占有正宗的位置,且为正统的审美意识所排斥。元曲之中则是以“豪放”为特点的文学作品占据了主流地位,曲本身的形式即有着“豪放”的特点。而随着诗歌——即很大程度上是以主体的抒情为主的文学体式——在封建社会后半期的衰落,代言体的戏曲和小说的兴起,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和缺乏创造创新精神,“豪放”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豪放”的根本思想精神、哲学辩证法精神和诗学精神三个方面。“豪放”范畴的根本思想精神是指儒、道互补、取长补短、意在现实的积极人生境界;哲学辩证法精神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民族审美意识对“中和”之美的偏离和歪曲,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易传》美学为代表的刚健积极精神;诗学精神是指诗“可以怨”的精神,在传统的偏于柔弱消极静态的审美意识影响之下,以“温柔敦厚”为特点的传统诗学对于“豪放”进行压抑和排斥,“豪放”范畴成熟于宋代并与“婉约”相对待,是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豪放”概念的义界、内涵及内在结构合成。“豪放”在义界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作为审美范畴的“豪放”,主要体现在其狭义上,其核心内涵是“不受拘束”;广义上的“豪放”是“壮美”的象征,它和其他一系列“壮美”范畴一起构成了“壮美”的风格,而在宋代以后“豪放”成熟为一个基本美学范畴之后,则成为这些“壮美”范畴的核心范畴。“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内涵涉及三个层面:内在精神层次的意义,表现为人对于腐朽礼法制度的反抗和超越;艺术表达层次的意义,表现为作者主体对于过时的规律和相对真理的超越;风格层次上的意义,表现为对“婉约”和“优美”风格的突破和超越。“豪放”的内在结构是由“豪”和“放”两部分按照“中和”之美的规律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结果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的规律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豪放”的生成,可以用“‘志’(理想,包含‘小我之情’→‘大我之情’的生成过程)→‘气’→‘豪’→‘放’”这样一个流程来阐释。“豪放”生成的主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人的志意理想促成了内在的“气”的积聚,而客观方面的原因则主要是和地域、社会、时代、心境及其他物质因素——尤其是酒联系着的。第五章:以具体的故事或文学作品为例,阐述了“豪放”在文学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及其主要美学风格特点。“豪放”之美集中的文学艺术,主要是诗歌和绘画、书法等等领域。“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主要有三个特点: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性精神特征;盛大而充沛的内在气蕴和外在气势;直抒胸臆、淋漓尽致的表达方式。第六章:主要探讨了“豪放”和一些容易混淆的美学范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至于明显与“豪放”区别开来的范畴,则不在探讨范围。“豪放”和“中和”之美的辨正,主要论述了“豪放”是“中和”之美的一种形态,而且是其较为健康和积极的一种形态,它在哲学的高度上秉承并代表着《易传》刚健积极为主的“中和”之美一路。和“壮美”的辨正,主要论述了“豪放”是一种最富有主体性精神的“壮美”。和“崇高”的辨正则主要指出“豪放”可以被主体以外在的形式上直接表现出来,而“崇高”只能在主体或审美对象的内心产生;“豪放”产生的根源是主体的“志”(理想),是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儒”、“道”两家思想互补的一个结晶,而“崇高”产生的根源则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命运和虚无的思考,最终达到对“有限”和“无限”的超越;“豪放”的主体通过积极介入现实社会生活而得到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崇高”的主体则往往是通过悲剧性的毁灭来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综合比较起来,“豪放”更具有现实性,而“崇高”则往往带给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对现实生活并无多大的改变。和“浪漫”的辨正主要是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来进行的,指出两者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不同,“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个性解放,其主体资产阶级最终推翻封建制度而成为统治阶级,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地位,仅仅兴盛于十九世纪初数十年的时间,而“豪放”则是以主体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心进行变革和创新的一种体现,它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脱出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的控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基础。第七、八两章:主要研究了“豪放”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豪放”范畴成熟之后的宋代以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和“豪放”的对立范畴“婉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部分研究的六方面的问题,都以这个问题为基础。具体的观点有:“豪放”是对“婉约”的突破与发展;“豪放”词可以兼有“婉约”词之长,反之“婉约”词要兼有“豪放”词之长则甚不易,这是由于受到主张“婉约”为词的正宗或本色的观点的限制,研究历史上的词人词作,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这一点;“豪放”和“婉约”一样,既能在词这种文体中具有“本色”的地位和性质,同时在元曲中,又具有独一无二的“本色”的地位和性质;用“诗化词”来贬低“豪放”词并非词这种文体的“本色”的观点,并不能成立,相反,词只有在一种向大诗学(即诗、词、曲同为一种诗歌体裁的阶段性形式)发展的趋势上,才能提升其文学境界和思想境界;“豪放”和“婉约”二分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近、现代一些认为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单的观点,其实并未认识到这种二分法的独特贡献,即它对于“豪放”范畴成熟的关键意义的揭示;“豪放”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内在的推动着从诗到词、从词再到曲的文体变化历程,在各个文体阶段上,“豪放”都有自己独到的特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九章:主要阐述了在民族审美意识重建的宏观视野下,“豪放”美学范畴研究的现代意义。“豪放”和中华民族新时期文化复兴和审美意识大方向的重建,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时代需要建立一种积极进取的以“阳刚之美”为主要风貌的审美意识,以促进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全面创新和发展,而其中所具有的“豪放”精神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豪放”是我们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新时期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前提条件,它对于人的发展,对于发展人从而使之达到更高的层次和理想境界,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林坡[2]2000年在《论辛稼轩词的美学内涵》文中认为辛稼轩是两宋词坛上“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大家。他在苏轼开拓词境的基础上,一变主要表现女性缠绵悱恻的柔情之词为表现血性男儿激昂豪迈的豪情之词;由于本人坎坷的人生经历,他在词中尽展自己的豪迈气概,词中军事化的审美意象频频出现,为宋词的发展又开拓了另一类虎啸生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的审美风格既有沉郁之致,又不乏豪迈气概,在审美形式上,则一变柳永的“以赋入词”和东坡的“以诗入词”而“以文入词”,为扩充词的容量,开拓词境,丰富词的表现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于永森[3]2007年在《论豪放》文中提出“豪放”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民族特色,反映着一种积极刚健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美学范畴,它在中国古代的人生思想和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古至今,研究“豪放”一般是局限在词学的领域之内进行的,而对其前期的发展及内在的深厚内涵及意蕴,则很少有人研究。本文从范畴研究的角度出发,力图系统而全面的探讨“豪放”的内涵和特征,生成、发展、嬗变的历史,以及历史文化基础和审美意蕴等各个层面。文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分析了“豪放”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从范畴研究的角度确立了“豪放”这一范畴的逻辑起点,即“收”和“放”的关系。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豪放”概念的义界和内涵、“豪放”的生成和特点及“豪放”与相关范畴的辨正。“豪放”在义界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作为审美范畴的“豪放”,主要体现在其狭义上;广义上的“豪放”是“壮美”的象征。“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内涵涉及三个层面:内在精神层次的意义,表现为人对于腐朽礼法制度的反抗和超越;艺术表达层次的意义,表现为人对于过时的规律和相对真理的超越;风格层次上的意义,表现为对“婉约”和“优美”风格的突破和超越。“豪放”的内在结构是由“豪”和“放”两部分按照“中和”之美的规律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结果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的规律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豪放”生成的主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人的志意理想促成了内在的“气”的积聚,而客观方面的原因则主要是和地域、社会、时代、心境及其他物质因素——尤其是酒联系着的。“豪放”和“中和”之美的辨正主要论述了“豪放”是“中和”之美的一种形态,和“壮美”的辨正主要论述了“豪放”是一种最富有主体性精神的“壮美”,和“崇高”的辨正则主要指出“豪放”可以在外在的形式上直接表现出来,而“崇高”只能在审美对象的内心产生。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豪放”的形成和嬗变。“豪放”萌芽于先秦中国传统文化奠基的历史时期,是社会礼法制度逐渐加强、腐朽并逐渐形成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的产物。其中“放”的一面最先起步发展,并在老庄思想中得到体现;而“豪”的生成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理想。“豪放”在魏晋人的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过南北朝和隋的酝酿,在唐代的文学艺术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和体现。宋代是“豪放”发展为一个美学范畴的时期,尤其在词这种文体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逐渐趋于成熟,但是在人的审美意识中它并不占有正宗的位置,且为正统的审美意识所排斥。元曲则是以“豪放”为特点的文学作品占据了主流地位,曲本身的形式即有着“豪放”的特点,而随着诗歌——即很大程度上是以主体的抒情为主的文学体式——在封建社会后半期的衰落,代言体的戏曲和小说的兴起,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和缺乏创造创新精神,“豪放”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豪放”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和审美意蕴,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哲学辩证法基础和诗学基础三个方面。社会历史文化基础是指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格局,哲学辩证法基础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民族审美意识对“中和”的偏离和歪曲,诗学基础是指在偏于柔弱消极静态的审美意识影响之下,以“温柔敦厚”为特点的传统诗学对于“豪放”的压抑和排斥。“豪放”的审美意蕴大体包含四个方面:以“活”为辩证法的人生境界;天真、朴素、本色的人格本真架构;自信热烈、一往情深的心灵世界;诗酒缠绵、琴剑炫异的人生意态。第五部分:结语,主要论述了“豪放”的现代意义:“豪放”和中华民族新时期文化复兴和审美意识大方向的重建,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豪放”范畴中所具有的“豪放”精神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豪放”是我们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新时期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前提条件;“豪放”对于人的发展,对于发展人从而使之达到更高的层次和理想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国正[4]2006年在《南宋孝宗词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宋孝宗词坛群星璀璨,既出现了像辛弃疾、姜夔这样的词坛巨匠,也有陆游、陈亮、范成大、刘过、韩元吉、张镃等名家,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宋词的高峰,孝宗词坛完全可以与北宋元佑词坛相媲美。本文即希望对形成宋词高峰之一的孝宗词坛作出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解释和描述。全文分外编和内编、各四章。 外编着眼从词坛外部因素探究词坛内外的互动。首章交待孝宗词坛的历史背景,但摒弃全面的描述方式,而以孝宗为观察点分析他的恢复之志的时代意义和他的治效形成的盛世局面。这两个方面都与词坛的风气以及题材内容的选择有密切的关联。第二章论述孝宗时期的文艺思想,仍是作为词坛的背景来描述。第三章从词人的生活模式出发,探讨他们的生活与词的关系,传统的隐居生活在南宋获得新的意义,而江湖生活则更为找不到出路的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三种生活模式对词人创作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时又受共同的时代潮流所左右。第四章试图在宋词和理学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这便是“性情”。理学家和词人分别用自己的方式充实其含义,并因而获得沟通。 本文内编主要研究孝宗词坛的词人之组合及其词学观念、艺术探索。第五章研究以辛弃疾为中心的词人,而辛弃疾本人则作为一条线索而存在。与辛弃疾接近的许多词人确实有着与他相近的风格,但这既有生活体验相似的因素,也有东坡词风的遗泽所在,而非完全追随的结果。辛弃疾本人既不排斥豪放之外的风格,他的朋友中也不乏与之异趣者。除了辛弃疾为中心的这一群词人,本文对孝宗词坛的其他词人选取了宫廷与帅臣豪门这两个角度,它们都是权势所在,词的享乐性恰好是它们的形象体现,同时又呈现出精英文化的特征。此后一章转向词学观念的探究,孝宗时期词人在词体观、创作观与功能观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心理,但它不仅无妨于词人的创作,反而使整个词坛具有一种不可羁勒的活力。最后一章讨论孝宗词坛在词的艺术追求上的努力,南宋词被认为“极工”,就是其艺术形式上的深化所致,然而它又不仅仅具有形式上意味,同时也预示着词人心理的蕲向。
周炫[5]2005年在《稼轩词用典与宋词的“雅化”进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稼轩词用典的定量统计和分析,了解辛弃疾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了解传统文化在辛弃疾身上的渗透,深入理解稼轩词用典在宋词“雅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宋词的“雅化”指的是宋词的“诗化”和“散文化”。辛弃疾以“才学为词”,以“诗言志”的精神写词,借典明志,使词进一步“诗化”;在表现方式上,辛弃疾以散文的气、叙、议等方式运典为词,又注重比兴寄托,使词进一步“散文化”。稼轩词用典,使词进一步“雅化”,成为与诗、文并列的“雅文学”,也使词进一步弱化了俗文学的体性。
王毅[6]2006年在《南宋江西词人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梳理中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体”和“派”的内涵入手,对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江西词派”的说法与现象进行了辨析,认为用江西词人群体的概念来界定更符合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和当代的文学理论,更加准确和科学。 南宋江西词人群体分为稼轩时期的江西词人群体和须溪时期的江西词人群体两部分。后者在词的创作和词学观念上对前者有所继承外,又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表现为词作内容上的以词存史和艺术手法上的以词叙事。 稼轩时期的江西词人群体包括洪适、洪迈、韩元吉、赵彦端、赵善括、赵善扛、杨炎正、赵蕃、韩淲、徐文卿、徐安国、赵晋臣、刘过、姜夔等人,他们之间互有交往和酬唱,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词学审美理想和创作风格,而是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在对词人群体的交往酬唱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发现,稼轩词风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与众多江西词人的相互唱和中逐渐呈现的。他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在与不同词人的唱和中有意无意的受到影响,而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稼轩词风。这一点是为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的。 须溪时期的江西词人群体包括刘将孙、文天祥、赵文、赵功可、邓剡、罗志仁、姚云文、詹玉、滕宾、彭元逊、颜奎等人。他们之间互有交往和酬唱,但是并不密切和频繁。词人群以刘辰翁和文天祥为中心,江万里和欧阳守道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刘过、刘辰翁通常被视作辛派词人,词风受辛弃疾影响很大,但这种作家之间共性的描述并不能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作家的特点和真正的创作个性。因此第四章即是揭示刘过、刘辰翁等江西词人在与稼轩词风相似的同时还存在哪些差异,其异于稼轩的创作个性何在,从而让他们在稼轩词风的笼罩下重新走出来,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从而进一步细化文学史研究,展示作家创作的丰富性。 南宋江西词人有很多也是江西诗派中人或受到江西诗法的影响,这种诗与词横向上的联系,在过去的研究中却很少提及,但其实二者之间确有影响,本文在第五章给予了揭示。 《名儒草堂诗余》是一部江西地域色彩浓厚的词集选本,过去一般认为此书所选皆南宋遗民,整体风格是稼轩风的延续,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书中所选作者为当时名儒,整体风格是清丽雅正。 最后,从江西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南宋江西词的发展特质给予一种文化上的关照,江西文化中重气节、尚节义、以及隐逸传统和理学风气的盛行熏染,是南宋江西词总体上以气为胜、偏于豪放的外在环境因素。
程继红[7]1996年在《七百年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文中研究说明梳理1188年至1908年共720年的辛弃疾研究进程,表明了因时代不同、审美趣味的变化,词学批评大势的走向不一,对辛词有推崇亦有贬抑,辛弃疾的地位因此在历代呈升沉涨落的动态性,从而为今天的辛词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系统、动态的历史参照体系。
杜运威[8]2017年在《抗战词坛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1931至1945年的抗战词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该时期的词学理论、题材内容、词艺风格、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其研究范围主要是:第一,1931至1936年间,与“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相关或表达抗日救国情绪的作品。风格方面批判梦窗、倡导苏辛者也应重点关注。第二,1937至1945年间所有词作皆应纳入考察范畴,不管任何题材,也不论多么偏离“抗日”中心,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战争的历史烙印。第三,1946年后,指那些庆祝抗战胜利,追忆抗战历程,回顾个人身世之词,此类作品暂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抗战词坛是亟待深入开发的学术富矿。首先,它是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边缘”文体,词体创作受政治牵绊较小,情感抒发十分自由,文学独立性很强,且其历史经验丰富,有着悠久的“诗词史”传统。至于音律和谐、雅俗共赏、交游娱乐等范式及功能更是新文学不具备的品质,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其次,它是百年词史的精彩一页。大批作家于抗战中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创作水平逐步走向成熟。彼时梦窗风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环境下的群体诉求,豪放词风成为各界拍手欢迎的新宠,词坛陡然兴起一场席卷南北的词风转变。第三,“十四年”时间创作力量十分强大,粗略统计有300余词人,近8000首作品。然目前相关研究仍徘徊于个案多、群体少,专题较深、宏观缺失的基本现状,还有很多值得拓展的空间。为便于清晰地反映词坛创作情况,本文采取“文史互证”和“微观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有利于对主流文学风貌的强化,后者则可加强非主流文学关注,还原词坛纷繁复杂的多元化面目。自列强入侵中国以来,词坛格局和词史发展已经悄然改变,尤其稼轩接受群体及其所作“战争词”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从“鸦片战争时期的薄弱跳动”,至“太平天国间的集体性吟唱”,再至“中法战争的停滞徘徊及庚子事变的转型”,俨然构成一条独立于浙、常二派之外的发展脉络。庚子之后仍有前进,但影响不大。直至抗战的爆发,才真正开启续写词体“御敌抗侮”的新史程。彼时整个文坛亦迎来全面复兴的契机。抗战词坛是一个风云激荡、裂变新生的时代。文学生态十分复杂,有的词人不畏艰险,投笔从戎;有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以隐士自居;还有的投奔日伪政府,成为推进“和平文学”的帮凶。各角色之间多有交叉,甚至集于一身。战乱中不同处世心态及生存方式创造出题材各异的作品,进一步拓宽了词体叙述广度和深度。另外,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对文学思想、群体意识、内容风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以期刊为中心形成的文学流派最值得关注。三十年代,龙榆生提出“别建一宗”的理论主张,矛头直指词坛“四声競巧”怪状,发起反对梦窗,倡导苏辛的变革运动。并以《词学季刊》为平台,聚集起有着共同审美倾向的百余名词人,正式宣告抗战词派成立。他们反对过于专注声律技巧,倡导苏辛词风,恢复韵文抒情本质,并抬高词体言志批判功能,力求有益于现实社会。全面抗战后期刊的停办及1940年龙榆生的“入伪”阻断了词派正常发展历程,但并未就此消失。“别建一宗”理念被卢前主编的《民族诗坛》选择性的接纳继承,他们提出建立“民族诗歌”的新口号,其秉承的“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的创作宗旨与中国面临的战争处境及人民大众内心的期望达到高度契合。于是,以卢前为新领袖,以“诗坛”为新平台,再次聚集起一批更偏向于“稼轩风”的新词群,抗战词派由此进入后期发展阶段。这是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第一个严格意义的“期刊型”文学流派,它的发掘将改变当今百年诗词史的基本格局。基于以上宏观生态及词学理论的考察,结合“词史”意义、艺术水平、词坛影响三大维度,我推出此期成就突出的三位词人,分别是卢前、刘永济、吴眉孙。卢前《中兴鼓吹》将前线英雄事迹辍为长歌,声调铿锵,振奋人心,成为战区难得的畅销词集,影响深远。学人词代表刘永济和“词人之词”典范吴眉孙,分别引领词坛两大群体的创作方向。前者驱使学识入词,典博厚重,言语老辣,坚守声律本色,艺术成就颇高;后者较为浅近,然亦强调音韵谐和,注重一己情怀的宣泄,个性十足,评论时政犀利大胆,又不似“以诗为词”者那般粗率。三人各自占据不同领域的制高点,成就卓著,堪誉为词坛“三驾马车”。此外,还有20位名家共同撑起词坛璀璨星空,他们是张尔田、夏承焘、詹安泰、汪东、仇埰、唐圭璋、陈匪石、吴白匋、龙榆生、王陆一、苏鹏、杜兰亭、顾衍泽、汪曾武、廖恩焘、郭则沄、章士钊、林思进、沈祖棻、丁宁等。据作家分布及“十四年词史”时间短、地域广的现实情况,本文选择以词人群体为中心,并引入期刊、社团、地域、性别等多元视角,以期对词坛形成立体化观照。当然,各“视角”之间多有穿插、互利互补。因此,以上所述坐标个案根据需要分别打入相关视角之下。比如汪东、陈匪石、唐圭璋、吴白匋、仇埰等置于第五章“雍园词群与午社”;龙榆生、张尔田、汪曾武、廖恩焘等于第六章“沦陷区生存策略与复杂心声”集中讨论;而沈祖棻、丁宁等则以“女性词人群”独立成章。雍园词群和午社是抗战词坛成就突出的两大团体。前者是一批远离故乡、避居西南的伤心词客,生活经历的相似使其作品蕴含共同的抗战血泪、家国情怀和忧虑彷徨,而词学观的共性则锻造出“温柔敦厚”、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稳稳占据抗战词坛的艺术高地。后者是一群既不受国统区承认又被沦陷区严格监控的孤岛词人,国破家亡之痛与身世的压抑处境非偏重技巧声律的“清真、梦窗”能够疏解,对情感内容、比兴寄托的强烈要求本能的促使他们改革民初以来的“梦窗风”,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作为词体美学的优秀继承者,两大团体分别代表了战争影响下不同区域的风格取向和文学成就。沦陷区的特殊处境孕育出与国统区不同的艺术风貌。作家一方面要承受来自日伪政权的生命安全压力,以“复古倒退”的典雅诗词配合伪政府“和平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要扛住伦理道德压力,于典故比兴之间寄寓批判抵制。这与国统区词人的“慷慨”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抗战词坛另一番别开生面的文体特色。《同声月刊》和《雅言》两大诗词刊物是认识南京、北京一带词人生存状态及其作品风格的独特窗口。《同声月刊》通过倡导“诗教”,实现了“在朝”与“在野”文人的统一,成为沦陷区影响最大,聚集作家最多,作品成就亦最高的旧体文学刊物。《雅言》则通过文体“雅化”策略,成功斡旋于政权压制和个人反抗的博弈之间。无论是诗教理念,还是文体雅化,都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特殊地域空间的生存策略,同时又是生存与反抗的统一表现。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二者都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
谢水华, 何黎明[9]2003年在《辛弃疾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初稿)》文中认为前言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安抚使。善长诗词,与苏轼并称"苏辛"。著有《稼轩词》、《美芹十论》、《九议》、《南渡录》等。近十年来,对辛弃疾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同时也推出了一大
朱丽霞[10]2007年在《继承与新变——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理性思索》文中研究说明辛弃疾是中国词史的巅峰作家,空前绝后。自从其步入词坛之日起,人们便开始了对辛词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以来,围绕辛弃疾及其词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本文拟从清末民初、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建国初至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四个时段对百年辛弃疾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和文化考察。百年辛弃疾研究与每一时段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密切相关。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辛词研究反映了二十世纪词学嬗变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论豪放[D]. 于永森.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2]. 论辛稼轩词的美学内涵[D]. 陈林坡. 郑州大学. 2000
[3]. 论豪放[D]. 于永森.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4]. 南宋孝宗词坛研究[D]. 金国正.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5]. 稼轩词用典与宋词的“雅化”进程[D]. 周炫. 华南师范大学. 2005
[6]. 南宋江西词人群体研究[D]. 王毅.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 七百年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J]. 程继红. 上饶师专学报. 1996
[8]. 抗战词坛研究[D]. 杜运威. 吉林大学. 2017
[9]. 辛弃疾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初稿)[C]. 谢水华, 何黎明. 2003中国上饶辛弃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
[10]. 继承与新变——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理性思索[C]. 朱丽霞. 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7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辛弃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宋朝论文; 宋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