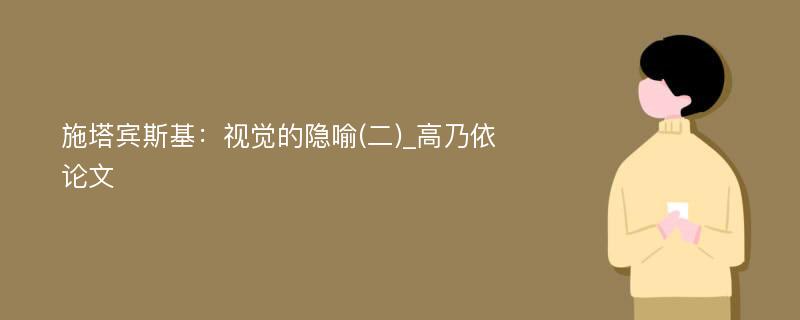
让#183;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斯塔论文,目光论文,罗宾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让·斯塔罗宾斯基以主题学研究开始了他的批评事业。他往往从词源入手,然后扩展到整个文本,反复倾听词语的声音,例如他对“注视”的研究就极具代表性,并因此而发展出一种批评的理论。
1961年,让·斯塔罗宾斯基出版了论文集《活的眼》,题目取自让—雅克·卢梭的小说《新爱洛漪丝》,小说中有一正直的无神论者德·伏尔玛尔先生,他是女主人公于丽的丈夫,他对于丽和她的情人说:“如果我有什么主要的激情,那就是对于观察的激情。我喜欢阅读人们心中的思想。因为我的心没有给我什么幻想,因此我冷静地和不带兴趣地进行观察,而长时间的经验给了我洞察力,我的判断不会欺骗我;因此在我连续的研究中,自尊心的全部报酬就在于此,因为我不爱充当角色,但只爱看人家演角色——社会对于我的可爱之处在于可以观察而不在于参加进去。假如我能改变我的本性和变为一只活的眼,我很愿意这种交换。这样我对于人们的不关心并不使我独立于他们;我虽并不努力于被他们看到,我却需要看到他们,我虽不对他们成为可贵的,但他们却是我必需的。”(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20页。引文见《新爱洛漪丝》第四卷,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1-212页。译文略有改动。)伏尔玛尔先生怀着观察的激情,见证了小说主人公的爱情的微妙变化。论文集取了《活的眼》这样的名字,表明了作者的“观察的激情”和“洞察力”,题目以下统领着五篇文章:《波佩的面纱》、《论高乃依》、《拉辛与注视诗学》、《让—雅克·卢梭与反省的危险》和《使用笔名的斯丹达尔》。《波佩的面纱》实际上是一篇序言,以下四篇文章分别研究了四种通过看与被看达到的迷惑或蛊惑的目的,例如,高乃依作品中的颂扬的目光,拉辛作品中的发愣的目光,卢梭的裸露癖和观淫癖所流露出来的对于迷惑的追求,斯丹达尔通过使用笔名而达到对于他人目光的躲避,这一切透露出作者的用意——研究人看世界、人与人互相交换的目光,研究看与被看,从中引出某些阅读的原则和育人的目的。他从一个词出发,从词根开始,溯流而上,直到源头,再顺流而下,囊括所有的支流,编织了一张文本之网,这张网的纲就是:“被隐藏的东西使人着迷。”(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
且以高乃依和拉辛的戏剧为例,看看斯塔罗宾斯基如何以“注视”为源分析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他们令人“眼花缭乱”或“沉入黑夜”的爱情。
高乃依一生写有30多部喜剧、悲喜剧和悲剧,以悲剧最为著名,号称法国“悲剧之父”,其剧作以贵族的“责任”、“荣誉”战胜个人的感情为主题,主人公勇敢、坚定、富于牺牲精神,称为“英雄悲剧”。拉辛继高乃依之后登上法国剧坛,把法国古典主义悲剧推上顶峰。他的戏剧简洁凝练,尤其善于塑造女性形象。他写过悲剧、喜剧10余部,《安德洛玛刻》、《费德尔》、《贝蕾尼斯》等是他的代表作。
斯塔罗宾斯基这样概括高乃依的喜剧和悲剧:“一切都始于眼花缭乱。”“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他为自己造出来了的不起的命运:在普天下的人的眼中,他一出世就是胜利者。他最高的幸福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看的行为中,甚至也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做的力量中,它存在于使人看的复杂行为中。那么,什么样的丰功伟绩、什么样的意志才有能力产生并传播一种不可磨灭的眼花缭乱呢?惟一有效的努力,其效果可以保证的惟一的努力将是自我牺牲,这是一种行动,人通过这种行动将全部力量反转来对着自己,完全地否定自己,以便在作为证人的人类世代的注视中获得重生。”(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喜剧《梅里特》的主人公提尔西一见“美丽的面孔的光辉”,立刻就改变了原有的一切,放弃了誓言,转眼间变成了“目光一瞥”的俘虏。“光辉”、“炫目”、“眼花缭乱”等,都是高乃依喜欢用的词语,在这些词语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光辉’一词在高乃依的作品中如此频繁地出现,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这种主动的辉煌。那是一种胜利的惊讶,一种令人震惊的征服,一种不经过斗争的凯旋。就像路易十四的胜利一样:‘路易只要出现就行。’城墙倒塌了,骑兵队逃跑了,人民低头了。极端地说,个人的在场不再是必要的了。一句话,一个命令就代表了君主的存在,使他不必亲自出现。……在场的魔法很容易地变成了远距离的行动。……很明显,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从很原始的感情借用武器的修辞术:面对神圣的事物及其光辉的一种震惊。如果思考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拜倒于权力,那就应该找出某种强迫我们的超自然力,就应该使王公贵族们相信他们的豪华和炫目的光辉使我们发呆,失去抵抗。既然我们一见之下就被征服了,我们就不再需要讨论他们的权威的理由了:那是强加于我们的。”(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于是,爱与恨,生与死,一幅肖像就行了,一瞥目光就够了,仿佛一剂看不见的毒药使人迷惑或死亡。看与被看,迷惑与被迷惑,都是不由人自主的,人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操纵,这神秘来源于“看的力量”:“这是一条从诱惑到真实、从瞬间的惊奇到永久的胜利的道路。”(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力量与软弱,坦率与遮掩,非但不互相排斥,反而相互融合。使人看与隐藏,承认与压制,往往结合为同一种行为。在《熙德》中,罗德里格与施麦娜压制着他们的爱情,但不是为了消灭它,而是为了掩盖它,仿佛它并不存在。荣誉的观念,礼貌和责任的规矩,迫使一个人分裂为“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分为秘密的我和呈现在众人目光之下的我。一种对亲情的尊重使施麦娜对她的父亲隐瞒了她的爱情,她的爱情不能拥有“大白于天下的甜蜜的自由”。在她得到父亲的决定之前,她必须压制着她的任何表白。一个人外在的表现符合荣誉和责任的规矩,和一个满怀激情但不能表达的人,是同样真实的,因为这里分裂为二的,并非真实的存在和虚幻的表象,而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的一部分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展现,而另一部分则非得隐藏起来不可,这两种权利都受制于一种反映出价值选择的“社会监督”。没有障碍,没有对障碍的克服,就不可能区分“外在”和“内在”,一个完整的存在(一个人)就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斯塔罗宾斯基的结论是:“高乃依的悲剧几乎总是结束于眼花缭乱的‘感谢’的时刻;人们看到个人的骄傲的结局和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其存在和幸福决定于王公的辉煌的闪光。因此,高乃依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幻象的诗人,这个幻象的全部的能力恰当地充满了光明。……主人公的意志力靠一种外力得以增强,这种由赞赏的目光形成的外力转向他并赋予了他——高乃依式的结局就存在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之处。此外,主人公不言自明地知道,他怎么表现人们就怎么看他,既不变形,也不减少。人们看他的目光在他的存在中证实了他,全部地接受了他,认可了他。表象和他人的主体性并未使真实成为问题:误解始终被排斥。表象给英雄的我带来了证明,如果不被众人看,则英雄的我就不会有这个证明。因为我只有出现,才有完整的存在。如果他不断地请普天下来作证,那是因为他只有在证人面前出现,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
在拉辛的剧作中,目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价值和意义不同。“这是一种不乏强度但少圆满的目光,它不能阻止目标的逃避。对拉辛来说,看的行为总是被不幸所纠缠。……目光不断地表现出饥渴和怨恨。看是一种悲怆的行为,总是一种对觊觎的对象的不完美的捕获。被看并不意味着光荣,而意味着耻辱。在他激情的冲动中出现,拉辛的主人公不能自我证明,也不能被他的对手承认。他经常试图躲过众人的目光,因为他觉得事先就被定罪了。总之,他不得不接受着目光,他永远也不能在完全的明显中出现。”(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拉辛在欢乐的目光的映照下创造了黑夜的目光,这目光具有某种诱惑力,也具有某种羞耻感,例如,安德洛玛刻忘不了庀吕斯在特洛伊城的大火中闪闪发光的眼睛,尼禄在火把的照耀下第一次看见居妮的“泪痕点点的眼睛”,贝蕾尼斯看见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提都斯,告诉他不能娶一个外邦的女王,费德尔第一眼看见希波利特的时候,她的不幸就开始了,……。“拉辛的人物知道,一切都开始于夜间遇到的事物。决定他们的命运的是看见了这些眼睛,从此不能摆脱它们的形象。”(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看的行为虽然具有控制的力量,但是包含着弱点或对于弱点的意识;相反,被看几乎同时在他人的眼中是有罪的。拉辛的人物所等待的,是一种爱抚的眼光,然而他发现的却是一种犯罪感。他的人物的罪恶在一个先验的审判者的目光下展现,这个审判者就是太阳,就是上帝。斯塔罗宾斯基说:“弱点和过失永远存在,几乎是彼此相融,这就是拉辛给予看的人的行为和被看的人的处境的意义,惟一不具弱点的目光是先验的审判者的目光,它或者不及或者超出了悲剧的世界。人永远也不能走出悲剧世界,也就是说,不能走出弱点和过失。他不能从任何地方得到救助。如果他感觉到了审判者的俯视的目光,那只是增加了痛苦,而不是得到了疗治。对于睁开双眼的人和知道自己被看的人来说,没有平静。”这就是拉辛的“目光诗学”。(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斯塔罗宾斯基还对注视做了具体的解释:“注视表达了对于一种贪欲的痛苦的警惕,这种贪欲事先就知道占有等于毁灭,然而它既不能放弃占有,也不能放弃毁灭。在拉辛那里,悲剧性不单单与情节结构相联系,也不单单与结局的不可避免性相联系,而是全部人类命运从根本上被判决了,因为一切欲望命定地陷入注视的失败之中。……于是人们在欲望的中心、在视觉贪欲的残忍的闪光中猜到一股绝望的火,这股火追逐着它自身的死亡——由于不能得到希望的东西,它就只能通过选择灾难和沉入黑夜来克服它的痛苦。当英雄们沉入深渊时,无情的神则在充满光明的天上宣布,他们是一场颂扬其全能的灾祸的绝对见证。”(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
对高乃依和拉辛的分析,包括对卢梭和斯丹达尔的分析,是为了引出批评对作品的关系,即批评注视作品。那么,注视的结果是什么呢?注视的过程中又有什么发生了呢?
四
让·斯塔罗宾斯基在论奥地利批评家列奥·斯皮策的风格学时指出,纯粹的语言学对他来说是一种“源知识”,是一切评论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与斯皮策是一样的,他的批评从考察词源开始,例如对“注视”的研究。
斯塔罗宾斯基发现,法国语言表示定向的视觉使用的词是名词le regard,动词是regarder,有“看、注视、注意、面向”等义,其词根是gard,然而这词根最初并不表示看的动作,而是表示等待、关心、注意、监护、拯救等,如果加上表示重复或反转的前缀re则表示某种“坚持”。因此,作为名词和动词,“注视”表示的是“一种重新获得并保存之的行为”。(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这是一种持续的冲动,一种重新获取并加以保存的欲望,一种继续深入并扩大其所获的意愿。“‘注视’具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它不满足于已经给予它的东西,它等待着不断运动的形式的静止,朝着休息中的面容之最轻微的颤动冲上去,它要求贴近面具后面的面孔,或者重新接受深度所具有的令人眩晕的蛊惑,以便重新捕捉水面上光影的变幻”。(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这是对人的注视的描述,他面对的是他人和世界,他之所对可能是有声的和嘈杂的;这也是对一种批评的描述,他面对的是文学艺术作品(文本),他之所对是无声的和沉默的。但是,一部作品在没有被阅读的时候,是无声的和沉默的,是一个客观的、没有生命的存在,如果有人阅读,特别是批评的阅读,那么作品是有所回应的,因为它被批评的注视激活了。“注视,为了你被注视。”斯塔罗宾斯基这句话说得实在是精辟、深刻,它包含了正反两方面的力量,即注视和注视注视的力量。一个人注视另一个人,如果这另一个人毫不理会,则这个人的注视就少了交流,对另一个人的认识就仅限于他之所见,而他之所见就不会全面深刻而往往浮于表面,如果另一个人报以回眸一笑,甚至开口说话,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批评对作品的注视也是一样,如果批评家只把作品当作冷冰冰的存在,那就只好满足于注视;相反,如果批评家把作品看作活生生的人,把一口生气灌输给它,让它活跃起来,那两者之间就有了交流。所以,这两种注视,批评对作品的注视,作品对批评的反注视,都是主动的,又都是被动的。主动的时候,注视就是探询;被动的时候,注视就是应答。因此,“注视”乃是眼睛这种感觉器官的有意向性的行为。
“注视”的对象是一个被遮蔽的文本,遮蔽与去蔽遂成为文本与批评之间的最基本、最经常的关系。枫丹白露派的一位画家画了一幅古希腊美女萨比娜·波佩的画像,靓面白臂,风姿绰约,浑圆的乳房隐约可见,但是,她罩了一重薄薄的纱,挡住了观者的目光,使其处于见与不见之间。蒙田早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让波佩遮住她那美丽的脸?是为了让她的情人们觉得她更美吗?”斯塔罗宾斯基接过了蒙田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被遮蔽的东西使人着迷。……在遮蔽和不在场之中,有一种奇特的力量,这种力量使精神转向不可接近的东西,并且为了占有它而牺牲自己拥有的一切。”(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这就是说,波佩的面纱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而“神秘的特性是使我们必须将一切不利于接近它的东西视为无用或讨厌的东西”,其“唯一的许诺是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命运。日内瓦学派对批评的一致要求是始则泯灭自我,终则主客相融,而贯穿始终的是批评主体和创造主体的意识的遇合。斯塔罗宾斯基对批评的见解,就其出发点来说,是与日内瓦学派的其他批评家完全一致的,波佩的面纱要求于“注视”的,正是忘掉自我,超越肉体,在可见之物后面的神秘空间中“耗尽自身”。文本要求于批评的,也正是超越文字的表面,探求掩藏在阴暗的深处的“珍宝”,即“被隐藏的东西”。“为了一种幻想就丢掉一切!为了生活在一种毁灭性的迷狂中就让人抢走现时的世界!鄙视可见的美而爱不可见的美!”这乃是一种“对于被隐藏的东西的激情”。这其实就是批评的原动力。有人指责它是魔鬼的诱惑,有人指责它是上帝的诱惑,总之是一种欺骗,其实,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这种激情”。波佩的情人们“并非为她而死,他们是为她那不兑现的诺言而死的”。这就是“注视”的命运,也是批评的命运。
斯塔罗宾斯基对“注视”的描绘,处处与批评有关,让我们想到批评的特性。他指出,“注视”的特性有六:(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
一、“注视很难局限于对表象的纯粹确认。提出更多的要求乃是它的本性。实际上,所有感官都具有这种急切性。习惯上的通感之外,每一种感官也都渴望着交换权利。”歌德在一首《颂歌》中说:手想看见,眼睛希望抚摩。斯塔罗宾斯基补充说,注视想变成言语,“盲人的夜充满了固定的注视”,因此,在不具备视觉的情况下,人也可以借助补充的通道,例如听觉或触觉,在自身与外界之间建立“有意图的联系”。斯塔罗宾斯基在这里“更多的是将‘注视’称为建立联系的能力,而非拾取形象的能力”。视觉具有进取性,注视在视觉与视觉的对象之间建立了主动的联系。
二、在所有的感官中,注视最具急迫性,其表达方式也最为明显。“一种神奇的、从来不是完全有效的、但也从不气馁的微弱意愿伴随着我们的每一眼:抓住,剥去衣服,使人呆立不动,深入进去。”在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时,“注视”仿佛本身变成了一种物质的力量,跃跃欲试。瓦莱里说:“如果注视能让人受孕,那该有多少孩子!如果注视能杀人,街上将满是尸体和孕妇。”因此,人的每一道目光都伴随着某种意愿,“蛊惑,就是让隐藏在一个不动的瞳人中的东西发出光亮”。
三、“注视假使不为过量或不足的光所出卖,就永远也不会餍足。它使某种不会缓和的冲动得以通过。”注视(看)为欲望打开了全部空间,然而这并不能使欲望得到完全的满足,同时又使欲望留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人们知道充满欲望的目光是多么的悲哀”,因为人的注视可以发现一个崭新的空间,可是人却无力到达,徒唤奈何而已。
四、“看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极力想使注视所及更远,心灵就要盲目,陷入黑夜。”兰塞、蓝胡子的妻子、俄尔甫斯、那喀索斯、俄狄浦斯、普赛克、美杜莎,或死亡,或化为水仙,或变成石头,或跌进沙漠,或犯下弑父娶母之罪,其原因就是想看到真相,“在这一点上,神话和传说出奇地相互一致”。
五、“注视保证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身体所占据的地方之外有一条出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奢侈。……诸感官中,视觉最易犯错误,天然地有罪。”视觉最容易体会到各种诱惑,也最难抵制诱惑对虚荣心的满足,因此,“奥古斯都觉得拒绝看马戏的快乐简直是最大的痛苦”。教会的神甫对“注视”持最严厉的态度:“勿将你们的眼睛盯在一件使其愉悦的东西上”,超过了孔子关于“非礼勿视”的教诲。“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都能俘获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精神迷失方向,远离拯救之路”。
六、“无论在肉体好奇的意义上,还是在精神直觉的意义上,看的意愿都要求使用一种第二视觉。”那是一种朝向“彼岸世界”、朝向“理念”的注视,是一种“精神的、肉眼不可见的”超越了视觉的注视。第二视力是一种超越表象、直达本质的洞察力,它可能开始于直觉,也可能成于经验的累积,总之,它离不开现象力。
综上所述,“注视”天然地包含着某种愿望和要求,不可避免地要对视觉的原始材料进行“全面的批判”。(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所谓批判,乃是判定第一视觉所看见的表象是虚假的,是一种“假面具和伪装”。然而,第二视觉的境界又是“与表象相协调的”,并且认可表象本身所具有的诱惑力,例如波佩的面纱。因此,注视在穿过表象深入实质之后,又必须“返回直接的明显之物”,一切又从这里重新开始。例如蒙田,他的智慧是建立在对假面具和伪装的批判之上的,然而这种智慧又“在自反的注视的保护下,相信感觉,相信感觉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斯塔罗宾斯基的注视是一种历险的开始,是认识世界和他人的开始。这意味着对主体间性的承认,承认其存在既是实在的,又是不连续的,两者互为前提。“注视”有一种奇妙的作用,既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促使人与人相互接近。注视的这种作用于主体间的功能揭示了表象和真实之互为表里的关系,进而达到对于表象的全面的把握。萨特也极为重视“注视”,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使之成为“他人是地狱”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在萨特看来,“人也是这样一种生灵,他不能看到某一处境而不改变它,因为他的目光使对象凝固,毁灭它,或者雕琢它,或者如永恒做到的那样,把对象变成它自身”。注视是意识的搏斗,是进攻,是评判,是敌意,是企图占有,是自欺的遮盖。显而易见,这与斯塔罗宾斯基的看法大异其趣,尽管萨特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斯塔罗宾斯基关于“注视”的描述包含了他关于文学批评的隐喻式的描述。这就是说,如果对象是一部文学作品,那么“注视”就是阅读,而阅读就是批评的“注视”。批评家面对文本,既是被动的,又是独立的,他一方面“接受文本强加于他的迷惑”,一方面又“要求保留注视的权利”。他的注视说明他预感到在明显的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意义,他必须“从最初的‘眼前的阅读’开始并继续向前,直到遇见一种第二意义”。“注视”引导精神超越可见的王国,例如形式和节奏,进入对意义的把握。它使符号变成有意义的语句,进而推出一个形象、观念和感情的复杂世界。这个潜在的世界要求批评的注视参与并加以保护。因此,这个世界一旦被唤醒,就要求批评家全身心地投入。它是一种呼唤,要求批评家给予回答。它要求接触和遇合,它加强自己的节奏和步伐,并强迫批评家紧紧跟随它。意义就在语言符号之中,而不在语言符号之外的某个“深层”。
在这种对于意义的追寻中,批评的“注视”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指向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要求批评家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使他感觉到的那个虚构的意识之中,所谓理解,就成了逐步追求与创造主体的一种完全的默契,成了对于作品所展示的感性和智力经验的一种热情的参与。然而,无论批评走得多远,他也不能完全泯灭自身,他将始终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无论他多么热烈地希望,他也不能与创造意识完全地融合为一。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忘我,那么,结果将是沉默,因为他将只能重复他所面对的文本。因此,要对一个文本说出某种感受和体验,与创造主体认同是必要的,但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要做出某种牺牲。
另一种可能性正相反,就是在批评家和批评对象之间拉开距离,以一种俯瞰的目光在全景的展望中注视作品,不仅看到作品,也看到作品周围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诸因素,以便“分辨出某些未被作家觉察的富有含义的对应关系,解释其无意识的动机,读出一种命运和一部作品在其历史的、社会的环境中的复杂关系”。(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然而,这种俯瞰的注视将产生这样的后果,即什么都想看到,最后什么也看不清楚。作品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的无数表现之一”,终至消失。因此,“俯瞰的胜利也不过是一种失败的形式而已——它在声称给予我们一个作品沉浸其中的世界的同时使我们失去了作品及其含义”。(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
阅读的经验证明,斯塔罗宾斯基提出的这两种对立的可能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批评家固执地追求此种理想境界,必将导致批评的失败,即形成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批评。那么,完整的批评如何能够形成呢?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完整的批评也许既不是那种以整体性为目标的批评(例如俯瞰的注视所为),也不是那种以内在性为目标的批评(例如认同的直觉所为),而是一种时而要求俯瞰时而要求内在的注视的批评,此种注视事先就知道,真理既不在前一种企图之中,也不在后一种企图之中,而在两者之间不疲倦的运动之中。”(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活的眼》,伽利马出版社,1961年,第9、18、33-34、43、72、73、80、88、21-22、11、12、9、12-15、15、26、26、27页。)这里提出了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方法论的核心,即阅读始终是一个双向的动态过程,而其目的则是:“注视,为了你被注视。”这就是说,阅读最终要在批评主体和创造主体之间建立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两个主体都是主动的,同时又都是被动的,都是起点,又都是终点,一切都在不间断的往复的运动之中。因此,批评最好是认为自己永远是未完成的,“甚至可以走回头路,重新开始其努力,使全部阅读始终是一种无成见的阅读,是一种简简单单的相遇,这种阅读不曾有一丝系统的预谋和理论前提的阴影”。(注:斯塔罗宾斯基《批评的关系》,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第13页。)批评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往复运动,有可能上升为一种文学理论,走向批评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定。
注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意味着一种距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为了看得、理解得清楚和深刻,主体和客体之间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距离,太远则模糊,大而无当;太近则一无所见,同样是模糊。斯塔罗宾斯基说:“对于人们清晰地分开的存在的事物,首先要有一个距离。”“距离对于思想的展开是不可缺少的,对于物质的东西也是一样。这种距离打开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乔治·布莱说,距离是斯塔罗宾斯基“最自然也最合理”的立场:“对于人们清晰地加以分开的存在的事物保持距离,而存在的事物并无遮盖,是让·斯塔罗宾斯基对于他所选择的事物的最初的立场。”(注:乔治·布莱《不确定的思想,Ⅲ》,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距离并非封闭了注视的空间,而是从一个中心开始,打通了向四面八方延伸的道路,道路的长短、曲直,以看得清楚和深刻为准,这个中心就是批评家及其批评意识。
萨比娜·波佩的肖像陈列在日内瓦美术馆里,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在她面前驻足,被她吸引,然而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是被一袭轻纱遮住的脸和乳房,他们的目光显然有进一步的要求和欲望。然而,斯塔罗宾斯基的分析并非要揭去这重纱,而是揭示这重纱的各种作用,可以说,他的解读也是一重新的纱,批评的纱。波佩的眼睛望着那些想要看她的人,她在想:她要呈现在什么人的面前?她装作还是希望人们冒犯她?她要诱惑谁?她在欲推还就的姿态中体会到什么样的快乐?她期待着与人共度美好的时光?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她的观赏者那里。然而,问题是无穷的,解答也是无穷的,波佩的“不兑现的诺言”使问题和解答永无尽头,这也正是批评的魅力所在。
让·斯塔罗宾斯基在结束《波佩的面纱》的时候说:“(批评)在许多场合中,更应该忘记自身,让作品突然抓住自己。作为回报,我将感到作品中有一种朝我而来的注视产生:这种注视并非我的询问的一种反映,这是一种陌生的意识,从根本上说是另一种意识,它寻找我,固定我,让我做出回答。我感到我暴露在这个问题面前。作品询问我。在我为自己说话之前,我应该将我自己的声音借与这种询问我的力量。于是,无论我多么驯顺,我总是有偏爱我创造的令人放心的和谐的危险。睁大眼睛迎接寻找我们的凝视,这是不容易的。也许不仅仅对于批评,而是对一切认识的行动,都应该肯定地说:‘注视,为了你被注视。’”批评并不单单询问作品,它也要接受作品的询问,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才能达到批评的最高境界。批评本身应该成为作品,阐释应该成为一种创造。这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注视美学”的本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