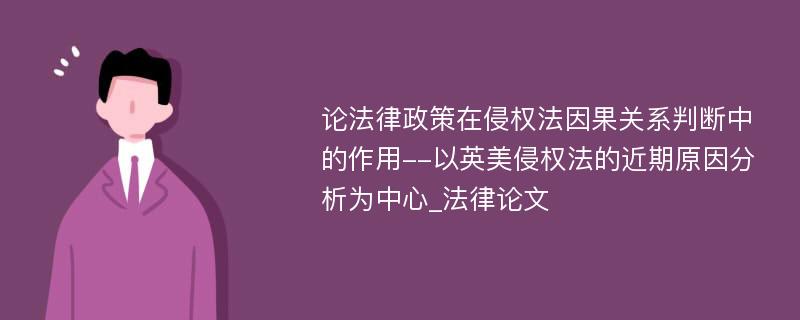
论法律政策在侵权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作用——以英美侵权法之最近原因的分析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果关系论文,英美论文,作用论文,原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1—6914(2007)04—0059—(12) 中图分类号:DF522 文献标识码:A
按照英美侵权法上考察因果关系的二分法①,在运用but-for测试②或重要因素测试等方法,将不属于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的其他环境条件和促成因素排除在原因的探究范围之外,就从对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考察进入到对最近原因或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考察阶段③。不同于事实上原因与事实的密切关系,最近原因概念更多的是同政策、便利和正义感等这些非事实因素联系在一起,与人们日常基于因果律和一般因果法则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很难扯上关系。既然最近原因同政策、便利和正义感等这些非事实因素如此密切地相关,那么以最近原因之名实现法律上的归责,同直接以法律政策为由进行归责,有何区别?究竟是哪些具体的法律政策在左右着最近原因的判断?在这背后是否包含着影响整个侵权法的政策因素的考量?本文旨在通过对法律政策在最近原因判断中所起作用的论述,管窥法律政策在侵权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作用。
一、最近原因及其判断标准
(一)最近原因概念
“最近原因”(proximate cause)也称为法律上原因(legal cause)、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源自于法律谚语“in jure non remota causa sed proxima spectatur”,意即在探讨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仅仅指出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原因)是不够的,还应探讨因果关系的法律目的。[1]86—87英美法上继受了此种观点,将因果关系考察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两个阶段,其理由是因为“在事件之间复杂多样的联系之网中,法律应该仅仅基于实际原因而不是纯粹逻辑上原因来提取某些相关的结果”(“逻辑上原因”即“事实上原因”),[2]107 在哲学意义上,逻辑或事实上因果关系链条向前向后可延伸至无穷,这就意味着一个事件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类事件之初。显然毫无限制地对最初原因的追溯将导致对违法行为归责的无限性,不仅对“遥远”的被告不公平,也增加法院的讼累,不利于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作为一个实践中的问题,对法律责任必须要有所限制,最近原因就是法院限制被告责任的概念工具之一。正像美国法官Andrews在:Palsgraf v.Long.Island R.R.Co一案[62.N.E.99(N.Y.1928)]中对最近原因意义的概括那样,最近原因的意义,“是基于便利(convenience)、公共政策以及粗略的正义感情,法律恣意地不再追溯一系列事件至某一特定点以外。这种判断并非逻辑,而是实际的策略应用。”对最近原因的上述理解也反映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该词典将最近原因界定为“法律上足以产生责任的原因”。[3]213
作为责任限制的概念工具,最近原因的“最近”并非指时间和空间上的接近,而是指在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可有太多其他新的原因介入其中。[4]633 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其他足以中断因果链条的介入原因,就成为判断最近原因的关键,主要表现为直接结果说和可预见性说。
(二)最近原因的判断标准之一:直接结果说及其式微
依据直接结果说,只要被害人所受损害是加害人违法行为的直接结果,加害行为就构成最近原因,加害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要成为加害行为的直接结果,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其一,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别无其他独立介入原因;其二,即使被告加害行为后有独立原因介入,但因为该介入原因是由于被告的积极行为引起,被告行为的积极作用事实上是借着第二次原因仍在持续中,那么无论损害结果是否为加害人可得预期,被告行为仍构成最近原因,加害人均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换个说法,除非被告积极行为的作用力必须持续到直接导致结果发生时,或者被告行为之作用力引发新的积极危险,进而由其他原因促使结果发生,否则损害只是行为的间接结果,而非直接结果,加害行为也就不构成最近原因。 In re Polemis一案{[1921]3 K.B.560(C.A.)}是法院采用直接结果说作为判断最近原因存在的标准的典型例子。被告租用轮船载货,在卸货的时候,由于工人过失厚木板跌落到船舱,因之前油气桶漏油,木板撞击引起火灾,导致轮船沉没。本案被告抗辩认为,虽然可以合理预期木板跌落可能造成某种损害,但是引起火灾却不在合理预见范围,因此其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没有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判决认为,既然原告损害是被告过失的直接结果,即使损害不可预期,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案件认定最近原因的关键在于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是否存在独立的介入原因,以及该介入原因是否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链条。此处的独立的介入原因,是指在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发生的足以让在先的加害行为免责的原因,它在加害行为造就的条件上发生作用,但并不是加害行为的结果。[3]212 显然该案中并没有发生足以中断被告过失行为同损害结果之间因果链条的独立的介入事件。依据直接结果说,只有损害是加害人行为的直接结果,加害人方要承担责任,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加害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间接损害而言,加害行为只是损害发生的条件,而不是法律上原因,因此不需赔偿。显然,运用直接结果说认定最近原因,进而确定赔偿责任,对被告是有利的,但不利于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也是英美判例法上,直接结果说日渐式微、最后被可预见性学说代替的主要原因。
(三)最近原因的判断标准之二:可预见性学说
随着欧洲启蒙运动弃用超自然存在观念,急需找到构建社会秩序所必须的道德价值的其他途径,Mill的功利主义哲学给出了他的答案:一个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该行为可预见到的结果:是否美丽、是否可爱,或者相反,同时还取决于其作为证据的性质。[5]349 之后,可预见性学说被用于法律领域,成为为那些可以预见的损害设定义务的依据。普通法上最近原因认定的可预见性说就是以此功利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点。
普通法上的可预见性说是通过Wagon Mound No.1一案[Privy Council(1961) A.C.388(SATL 403)]确立的。被告因疏忽将熔炉中的燃油排放到原告的码头附近的水域,原告工人倒掉的熔化金属恰好点燃了码头水面上漂浮的燃油,随后大火烧毁了整个码头。上诉法院认为,如果行为人须对其轻微过失行为造成的所有直接后果承担责任,而不论行为人能否预见到这些后果及后果的严重性,则有悖于公平观念。行为人对其行为后果承担侵权责任,应取决于行为人能否合理预见到实际发生的损害。本案中,既然被告无法预见到水面上燃油可能引发火灾,被告无须对码头毁损承担责任。[6]123 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法院以损害结果太过“遥远”且不可预见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请求。在Ryan 诉New York Central R.co.案中[35 N.Y.210(1866)],被告过失引起火灾,导致26家房屋被烧毁,法院认为被告只对其行为的最近结果,也就是第一家被烧毁的房屋负责,因为它是“失火的正常而自然的结果”,而其他房屋被烧毁不是失火的自然且可期待发生的结果,而是因为其他同时发生的环境条件,诸如温度、风向、临近建筑物的材质等被告无法控制的因素促成,不应由被告负责。
可见,依据可预见性说,侵权行为人的责任须以其在事件发生时对损害可得预见者为限,而且只有当损害在加害人违法行为制造的危险范围之内,加害人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何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呢?主要存在两个标准。一是主观预见标准,即站在行为人的主观立场,看其在事件发生时是否预见到损害的发生。二是客观可预见标准,也称为合理可预见性标准(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即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事件发生时能否预见作为确定行为人能否预见的标准,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能够预见,即使行为人其时不能预见,也应断定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成立法律上因果关系。
至于可预见的对象和范围,一般认为不包括损害发生的方式、损害的程度、范围,但损害类型必须是可预见的。依据普通法上的蛋壳头盖骨规则(the eggshell skull rule;thin skull rule),无论原告多么脆弱,被告因过失行为引起的损害,即便一般人无法预见损害发生的方式和损害的程度,被告仍然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124 普通法上还将原告纳入考察被告可预见对象的范围,只有那些可以被合理预见的被害人的损失才能得到赔偿,这就是所谓的“可预见原告”学说(unforeseeable plaintiff)。
在Palsgraf诉Long Island R.R.一案中[162.N.E.99(N.Y.1928).],一名火车站保安将一名携带一个包裹的旅客推上火车,结果包裹落地,因包裹内装有烟花,烟花爆炸后引起的冲击波使站台上放置的梯子倒下,砸伤了原告。审理该案的Cardozo法官认为,被告过失行为责任,仅对其危险范围内合理可预见的被害人,始得成立。可预见原告学说还被用于第三人救助被害人受损害案件,比如路人救助被被告车辆撞伤的受害人的时候,不幸被其他车辆撞伤,虽然救助者不在被告肇事行为的危险范围内,但法院以救助者属于被告违法行为对他人产生危险的可预见的被害人为由,认定被告应对救助者的损害承担责任。[5]350—351 可预见性学说在普通法上不仅是最近原因的判断标准,而且也正日益成为侵权责任的判断标准,侵权责任的认定越来越依靠对某事件或行为的“预见性”来定。但尽管如此,对于作为最近原因判断标准的可预见性学说,学界仍是毁誉参半。赞成者认为,依据一般的社会经验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可以预见并藉此来界定因果关系的界限,从而确定应赔偿损害的范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可预见性”标准的“一般社会经验”较为抽象,不易把握,且例外情况较多;可预见性学说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观点,无非是把因果关系同主观过错揉为一体。[8]199 普通法上,美国的Green教授对可预见性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划出可预见与不可预见之界限,其困难与划分太空、外太空的边际同样困难”,因此他主张用“义务——危险”分析代替合理可预见性说。[9]1412
二、法律政策及其对最近原因判断的影响
(一)法律政策概述
既然普通法上一般认为最近原因问题是法律政策问题,那么我们在探讨最近原因和法律政策之间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法律政策的概念、法律政策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有概括的了解,为进一步讨论法律政策同最近原因的关系以及影响侵权法和最近原因的具体法律政策提供讨论的基础。
法律政策(policy of law)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同义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律政策是指立法机关或者法院在考虑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根本性问题的时候,被视为原则和标准的东西。此种意义上的法律政策常被法院作为判决的正当化理由,比如对于违背公共利益的合同否定其效力。而狭义上的法律政策则专指“每个人都不得随便做伤害公共利益的事情”这一原则。[3]1245 可见,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法律政策概念,都同公共利益和社会根本问题相关,本质上反映了社会或团体的总体目标,目的是使团体成员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福利得以整体提升,即使这样可能会导致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政策也会被贯彻。[10]22 广义的法律政策在立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政府的执政党或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总会试图将反映其团体目标的政策通过立法反映到法律规范中,以获得法律的强制性。这并不是说,体现在立法中的法律政策都是执政党或利益集团的一己之私,为了其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阶层利益的考量也是必需的,所以体现在立法中的法律政策必然兼顾了对各种社会利益的不同权衡和评价,反映出公共秩序的要求。因为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在大陆法系上鲜有成文法规范,而普通法上判例的形成又与司法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对于法律政策对于立法的影响不作详论,而重点强调其对司法判决的影响⑤。
法律政策对司法过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可被法院援引作为判决的正当化理由。霍姆斯就曾经将“对——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公共政策的直觉”看作“比演绎推理作用大得多”的影响司法判决的因素。[11]1 特别是当法律规定出现漏洞,或者一些基本原则、条款的适用需要解释方能适用,或者遇到像“因果关系”、“义务”等这样的语义模糊不确定的概念,公共政策往往会成为法官填补漏洞、进行法律解释的工具,并向那些语义不确定的概念藉由一定的判断标准注入政策的内容,最终实现对判决的特定化。
我国有学者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提出了三条原则: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力只能限于填补法律漏洞的需要;对公共政策的适用必须不会构成对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法治价值的威胁和损害;公共政策只有在不违背现有法律规范,以及法律授予其自由裁量权目的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12]61 对此观点,笔者不完全同意。其一,笔者赞成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予以限制,否则公共政策将可能成为法官恣意裁判的借口和工具,损及当事人利益及社会正义价值。事实上,现在法官判决中使用公共政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公共政策作为一种非正式法律渊源,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在实在法表示出模棱两可或沉默时法官方可适当地使用。但如果执行公共政策与正义的基本标准发生冲突,那么法官应有否决的权力。[13]422 上面引述的我国学者的第二条原则与此义同。其二,将法律政策的适用空间仅仅限于填补法律漏洞,并不符合司法裁判的现实,也不能涵盖法律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所有功能。拉伦茨认为,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也就是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14]249 按照拉伦茨对这个法律漏洞的界定,实际上,即使法律规定本身不存在漏洞,法律政策也有适用的空间,而且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在特定情形下,还可以以法律政策的名义对合法行为或合法权利进行限制。这从上面对法律(公共)政策概念意义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乃是法律政策概念的当然之义。
(二)最近原因判断与法律政策考量
目前普通法上的主流观点认为,最近原因既非因果关系问题,也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依据法律政策决定被告是否应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应对损害结果负责的问题。⑥ [15]95 我国有法理学者也认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概念不是一种自在的性质,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一种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建构,其中隐含的是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公共政策判断或价值判断。[16]22
从最近原因的语言表达上,也不难窥探到其作为法律上原因的实质,而同事实上原因有根本区别⑦。一些与最近原因有关的词比如“重要的”、“有效的”、“介入力量”(intervening force)等之前,往往会有“法律上”(in law)这个定语。另外,最近原因往往借助隐喻的表达形式比如“介入力量”、“技术上的力”(technical force)等术语间接反映对法律政策、正义或者便利的考量。用事实的、政策中立的术语来界定最近原因只是个虚假的幌子,某事件作为损害的最近原因,必须是“在法律上”的损害的原因。在Henningsen v.Markowitz(1928)[132 Misc.547,230 NYS 313]一案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禁止将危险武器卖给16岁以下人士,将一支手枪和指弹卖给一个13岁男孩。男孩的妈妈让男孩将武器还给被告并要回买武器的钱,被告拒绝收回该枪,男孩的妈妈就将武器藏起来不让男孩找到。6个月后,男孩发现了该枪,让他的一个玩伴拿来玩,结果射伤了原告,使原告一只眼睛视力受损。法官用隐喻的形式,认为被告违法将危险武器出售给13岁男孩的行为是一种“积极力量”(active force),如果在其行为后出现其他“新的力量”并造成了损害,那么结果就同被告的行为之间是“遥远”的,被告行为就是损害产生的条件,而非最近原因。但本案中,孩子母亲的介入充其量只是一个无效的阻挠行为,并没有让被告的“积极力量”停止作用,被告行为仍停留在一个明显“安全”的位置,不用同其他任何“新的力量”结合就足以造成损害。被告行为同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未因孩子母亲的介入行为而中断,其仍是损害的最近原因,需承担赔偿责任。
最近原因受政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还表现在同一个类型的案件,由于决定最近原因的法律政策的差异,以及对“损害”、“介入因素”的不同界定,最终作出的关于最近原因和法律责任的决定很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并不存在作为上述决定基础的一致的客观事实。一个事件发生后,不同人因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差异,很可能对事件造成的损害以及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存在差异,于是事件或者案件事实就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在一幅面孔下,损害是可以预见的,因此被告应承担责任;但当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述这些事实的时候,损害就可能变成不可预见的,被告因此可以免责。可见,并不存在一个关于事实应该如何描述的权威的方法。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并不存在最近原因判断的一致认同的事实和客观标准。下面的判例是这一论断的很好例证。一个载着汽油车的火车司机因过失同轨道上的障碍物发生碰撞,车翻了,溅出的汽油着火并流入河流,并顺流而下一英里并点燃了干草,火势蔓延点燃了原告一英里开外的房屋。在新泽西州,原告的诉讼请求获得满足,理由是司机的过失是原告损害的最近原因。但是几乎同样的事实,在宾州,原告却败诉,因为损害太过“遥远”。[Kuhn v.Jewitt(1880)32 NJ Eq.647;Hoag v.Lake Shore and Michigan S.R.Co.(1877)85 Pa.293.27 Am.Rep.653.][1]101
(三)法律政策与最近原因责任限制功能的趋同
既然法律上因果关系传达的是非因果关系的法律政策的内容,那么为何不直接以政策名义反而是借因果关系之名来实现归责目的呢?两者对责任限制所起的作用是否完全一样,抑或是存在某种区别?目前普通法上的趋势是两者的作用正日益趋同。
传统上的因果关系学说区分基于便利、公正及法规目的等政策考量进行的责任限制与基于最近原因进行的责任限制,这种不同可以在司法语言不同的表达习惯以及运用特别的技术将两者做不同的分类中体现出来。[1]91 但是现在学者们趋于将两者合二为一,在美国的教科书中,两者均放在最近原因的标题下进行阐述。两者关注的焦点都在于第三人的故意介入行为或者异常事件是否中断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除了与事件发生的事实上原因存在某种关联外,最近原因的其他方面涉及的都是法律政策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官根据他们对什么样的责任限制才是公正的且符合理性及法规目的的理解,最终作出责任认定。无论是直接以法律政策的名义还是以最近原因的名义,决定法官作出责任认定的实质影响因素并无不同。前面举到的纽约失火案就很说明问题,该案中法官既可以以保险政策为由,如考虑到房屋保险的普及,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损失比由被告来承担损失更为现实和公平,也可以以其他房屋的毁损与被告行为之间关系过于“遥远”因而不构成法律上因果关系为由,判决被告仅对第一家被烧毁的房屋负责而不需对其他房屋的毁损负责。虽然是两种判决理由,但判决结果上并无区别。
可见,普通法上的最近原因概念虽然名列因果关系之下,但实际上承载的却是法律政策和价值的内容,最近原因的判断必须借助于特定的政策考量和价值判断才能实现。
(四)最近原因与其他法律政策载体功能的趋同
虽然最近原因传达的是“非因果关系”的法律政策的内容,但是最近原因只是法律政策实现责任限制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工具。法律政策并不一定要以最近原因的名义才能实现归责目的,有时候义务作为政策工具也起到了跟最近原因同样的作用。目前发展的趋势是政策对义务和最近原因的影响愈益混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影响义务和最近原因判断的政策类型是不同的。
在普通法上,对于作为一种侵权类型的“过失侵权”(negligence)而言,对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判断至关重要。这其中政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为了“实用目的”(pragmatic purpose)偏离现有的法律原则。著名的:Donoghua v.Stevenson案就明显考虑了政策因素,从而确立了“邻居原则”(neighbor principle),即一个人必须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以便根据合理预见避免有可能伤害其邻居的行为或不作为。这里所称“邻居”是指易受某人行为或不作为直接而密切影响的人,正因为存在如此密切关系,所以一个人在行为时,应合理地把邻居纳入考虑范围⑧[7]3[17]163 而随后的Murphy v.Brentwood DC案[(1991)A.C.398.],则将注意义务的考察分为“合理可预见”、“最近性”(proximity)以及“公平、公正、合理”(fair、just and reasonable)三个阶段,从而进一步把政策因素混入其他因素一并考虑,如“最近原因”、让被告负有义务是否“公平、公正、合理”等[18]475[7]6。
除了上述判例法上政策对注意义务和最近原因的影响愈益难以区分外,还有学者提出某种学说,直接将对义务的分析和对最近原因的分析等同起来,认为对影响两者的政策类型进行区别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美国学者Leon Green提出的“义务——危险分析”理论(duty-risk theory)。
Green认为,所谓的法律上因果关系问题就是义务或者义务范围问题,因此应该运用政策考量方法通过对危险的认定和排除,来划出被告义务的范围,从而回答原告的利益是否应予以保护或者被告责任范围的问题。具体而言,Green的“义务——危险分析”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被告是否对受害人的损害负有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原告利益是否属于法律保护的对象,被告违法行为是否是法律所要避免的;被告行为是否违反了上述义务;被告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过失。只要满足了上述三个步骤的要求,被告就要承担责任。[19]1761—1762 一言以蔽之,“义务——危险分析”理论就是要求法官在每个案件中通过具体的政策考量,判断是否损害属于被告应该负责的危险类型,并结合其他的促成因素,最终决定被告是否承担责任。
Green提出“义务——危险分析”理论,同他对最近原因的独特分类是分不开的。Green将最近原因问题细分为“事实上原因”和“义务”两个具体问题,前者是科学的、物理的、事实上原因,也是他认为的真正的因果关系,后者则是社会政策主导的义务分析,不属于因果关系考察的范围,事实上原因应优先于对义务和责任的考量。[1]104—105 Green对最近原因的上述分类采用政策主导的义务分析,避免在判断法律上因果关系时使用诸如“最近性”(proximity)和“遥远”(remoteness)这些意义模棱两可的字眼,也将因果关系概念限定在事实上因果关系范围之内⑨[19]1761—1763。
基于对最近原因所作的上述区分,Green拒绝将被告在案件中是否对原告拥有义务同最近原因问题做出区别。他认为两者同是政策问题,要对两者涉及的政策类型作出宽泛的区别是不可能的,而且两者所起到的责任限制作用并无不同。但是侵权法学者Prosser却不同意Green的观点,认为“义务”、“最近原因”名下的政策类型是不同的,应该予以区分。Prosser认为,在过失侵权领域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政策:一类是在“义务”和“被保护利益”名下的政策,比如在原告不可能预见到危险的存在而其他人却可以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再比如是否应该给予“精神困扰”(mental disturbance)、“恐惧”(fright)和“惊吓”(shock)以赔偿,就涉及到政策对“被保护利益”范围的看法。另一类政策考量是在“最近原因”名义下进行的,法庭认为是因果关系的问题,其实存在着独立的不同于“义务”名下的政策因素。[1]106 即使:Prosser对影响义务和最近原因的政策类型作了区别,但因为他使用的政策原则范围相当宽泛,很难区分出哪些政策是在“义务”名下贯彻的,哪些又是在“最近原因”名义下得以体现。
笔者认为,随着侵权法上客观过错说的兴起,过错不再是主观过错说所主张的那样指行为人具有的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20]68 而成为“义务违反”所引起的“行为不当”;[21]143 并且判断过错的方法也由心理分析方法变为以通常有理性之人,日常生活中“当为”或“不当为”作判断标准。[22]259—260 与过错判断的客观化倾向相反,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则出现主观化倾向,如将合理可预见说作为最近原因的认定标准。无疑,无论是理性人标准还是合理可预见标准,均渗透着法律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身是很难区分的,法律政策有时选择义务作为政策的载体,有时却选择最近原因作为载体,但目的都是要实现归责和责任限制。如在前面提及的:Palsgraf v.Long Island R.R.Co一案中,Cardozo法官就是从义务角度来说明被告铁路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即便是对最谨慎的人而言,本案中也没有任何情形能让人想到一个纸包裹会使整个车站遭难”,“可以合理地觉察或预见的危险确定了当事人应当负有的义务的范围”,而审理本案的另一名法官Andrews则是在最近原因的名义下讨论让被告承担责任的公平性问题。[6]73 虽然方法不同,但异途同归,政策在不同的载体中起到的作用并无不同。
三、影响最近原因判断的主要政策性因素
探讨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法律政策因素,应首先从探讨法律政策对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影响开始。因为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影响侵权法的政策因素必然会渗透到对因果关系、特别是最近原因问题的判断中。
(一)法律政策对侵权法影响概述
虽然法律政策首先是作为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出现的,但正像英国的Dennis Lloyd认为的那样,英国侵权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英国法官对什么是公众利益的要求的感受而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也认为,法庭在判决侵权案件的时候,不能也不应该逃避对“人民大众”(we the people)的最大利益以及属于社会秩序利益的某些重要群体的利益的考量。“义务”、“违法性”、“过错”、“可预见性”、“遥远性”这些语义模糊的词语,成为侵权法上政策的最好的栖息之地。[2]43 法律政策对侵权法的意义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在侵权法中进行法律政策的考量是实现侵权法目的的必然要求。侵权法的主要目的是赔偿受害人损失并对社会上不特定人起到吓阻和威吓作用,因此在传统的自己责任原则下,要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让加害人为他人损失负责,侵权法要提供归责的理由。从宏观政策言,就是要在受害人权益保护与加害人行为自由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权衡,“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就在于如何平衡行动自由和权益保护”,[23]67 权衡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政策考量的过程。如果考虑到侵权法还具有的惩罚目的,特别是是否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是直接体现了法律政策的选择。
其次,法律政策在侵权法中主要起到责任限制的作用。法院在寻求政策因素使其判决正当化的同时,主要是要在个案中实现对侵权责任进行限制的目的,而不是去扩大责任范围。也就是说法院更倾向于在意欲限制责任而不是扩张责任的时候求助于政策因素。因果关系和过错等侵权责任要件作为责任限制的工具的角色远远要重于作为责任扩张工具的角色。从下文的讨论我们将看到,普通法上的法律上因果关系和德国法上的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正是作为以限制责任为核心的法律政策的载体存在的,它们的主要价值也在于此。政策对责任限制的作用不仅在普通法中日益得到验证,比如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因为政策因素,被告得以全部免责,继而可能影响到原告特定权利、损失的救济⑩。德国的许多案例也一样。法国在侵权责任概念上,已经较普通法和德国法更加宽泛,在使用政策理由扩展其侵权法方面走得更远。[2]43—44
最后,法律政策对侵权法的影响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问题和四个具体环节。两个大的方面问题是:立法上应如何规范侵权行为法的原则及其构成要件;在法律的解释适用上应如何使其适应变迁社会中的需要。此二者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国家侵权行为法的形式、内容和风格。[23]69 四个具体环节是指:法律责任的不同理由、限制责任的因素、诉讼中因果关系问题的构建以及证明责任的分配。[1]xliii 由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侵权法立法体例和构成要件上有明显不同,比如普通法上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有不同的要件,而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法国民法典则规定了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因此,可能上面列举的这些受法律政策影响的问题和环节,在一些国家并不存在或者只有微弱的影响,但无可否认,法律政策在构成要件的取舍、归责理由、责任限制以及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具有普遍性的。
(二)影响侵权法和最近原因的具体政策因素
法律政策对侵权法以及因果关系的影响,必然体现为具体的政策因素,下面就对这些政策因素择其要者进行分析,重点分析这些政策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11)。
1.行政管理因素(administrative factor)
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的容量、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普通法国家,由于法官数量稀少,如果对起诉条件不加以适当限制,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动辄为了很小的纠纷就提起诉讼,将造成社会的法律和经济成本畸高,案件出现积压,形成讼累,整个司法系统将难以承受。法院对“精神困扰”案件(nervous shock;mental harm)的判决,正是政策上因对滥讼的担心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很好例证。
所谓“精神困扰”案件,是指因受惊吓致精神受侵害者,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案件。假设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非常悲惨。很显然,在现场看到事故发生或者看到有关新闻报道后产生精神困扰的人数要比事故的实际受害人要多得多,因此,如果法院判令所有这些受到精神困扰的人都可以从交通事故肇事者处获得赔偿,一方面肇事者将承担不合理的过重的责任,另一方面法院也会因此受案无数,司法成本巨增,而司法效率则锐减。正是基于这些政策因素的考虑,在英国对于精神困扰案件,法院的一般做法是区分严重精神困扰和轻微精神困扰,前者给予救济,后者则不予救济(12)。[2]46—47 实际上,这一区分并作出不同判决的过程是通过法律上因果关系这一概念工具实现的,严重精神困扰被认为同加害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而轻微精神困扰则不是加害行为的结果。
2.价值层级因素(the superior value factor)
任何法律制度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有形或无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事物提供法律保护,不同事物对于人的价值并不相同,当受到侵犯的时候,法律总是对那些处于价值层级高端的事物提供更好的保护。问题是如何排定不同价值的优先性。
拉伦茨将民法上的价值判断问题归结为自由及其限制问题,“自由及其限制问题是民法的核心问题,民法的价值判断问题大多也都属于自由及其限制问题”。[24]98 拉伦茨所说的“对自由的限制”实质上就是对他人权益的保护。具体到侵权法领域,著名侵权法学家Fleming教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整部侵权法的历史充满着个体利益的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安全利益(interest in security)和行动自由利益(interest in freedom)”。安全利益要求不管加害人出于何种动机,都要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责任,甚至是无过错责任。而行动自由利益却要求只有在加害人出于故意或者对他人缺乏应有的关照的时候,才承担过错责任。[18]6 在具体案件中,对加害人行动自由和被害人安全利益保护这两种价值形态何者占优的判断,就决定了被害人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赔偿。然而在种类繁多的侵权案件中,“行动自由”和“安全利益”会化身为众多的具体的价值形式,而这些具体价值形式之间的层级关系往往并不清楚。如何确立具体的价值层级的判断机制就非常重要。
既然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5]406 价值判断是关于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什么的判断,[26]616 因此,判断价值层级高低、地位优劣的标准只能是看事物满足人的需求的程度。一般而言,当权利价值互相冲突时,如果有基本公认的价值序列,就要优先适用被判断为处于优先地位的权利价值。具体表现在:当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冲突的时候,优先考虑人的价值;当生命权与人格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优先考虑生命权;当生存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优先考虑生存权;当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以公正为主,等等。[27]78 具体到侵权法领域,自由比财产、人的完整比财产的完整、财产或人身损失较单纯金钱损失更能满足人的需求,在价值层级上居于更高位阶,因此,在特定案件中,法院更倾向于对这些优位价值予以保护。
然而应该看到,现实中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价值层级,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价值对于人的意义和重要性又会发生变化。以西方社会历史演变为例,在18、19世纪,价值的天平倾向于财产和财产的自由使用,目的是不给土地所有人附加沉重的因预防他人侵入其土地而遭致的负担,而现代社会则更倾向于对因土地所有人无限制地使用土地造成其损害的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保护。另外应当看到,对不同价值层级的判断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判断,不同判断者可能会对同一个事物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适的价值层级供人们借鉴比较。
综上所述,因为立法和司法上对民法不同价值层级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到具体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能否获得损害赔偿,所以价值因素对侵权法的影响非常之大。由于价值因素对案件最终判决的影响要通过对具体的责任构成要件的认定的影响来实现,所以因果关系、特别是法律上因果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必然也是对具体案件中存在的不同价值目标层级关系和冲突的反映,体现了司法裁判者的价值倾向。
3.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
环境因素同前面的政策因素虽然有重合,但它并不过多涉及道德和价值的考量,而是强调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虽然法官和学者尽量避免公开提及这些因素,而是选择用抽象概念和法律学说来支持自己的论证,但这些因素仍然存在。普通法上著名的严格责任案件:Rylands v.Fletcher[(1868)l.r.3 h.l.330]所确立的原则中,就包含了环境政策因素对侵权法以及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
依据Rylands v Fletcher原则,只要能证明被告在其土地上堆放了有毒物资,并且该有毒物资泄露造成伤害,不管被告是否有能力阻止泄露的发生,他都要承担责任。该原则规定了那些工业土地使用者对其土地使用中产生的危险类型要承担严格责任。而对于“原告的损害是否是由于泄露造成,抑或是其后因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亦或泄露本身是由陌生人的行为或者不可抗力造成”这些因果关系问题并未作为具体责任要件加以规定。笔者认为,法院在此采取的是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强调了土地的工业使用者在土地使用中的注意义务,加入了对环境政策因素的考量。
环境政策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从日本环境侵权案件中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也可见一斑。疫学因果关系说源自日本侵权法,是为了在公害诉讼(13) 中减轻受害人在因果关系上的证明责任。所谓疫学方法“是指依据计量方法,观察分析某种疾病因素之集团现象,如发现某因素之作用,对于某种疾病之生灭消长,具有牵连关系,且其生物学上说明,未见矛盾,即可认定因素与疾病间,具有因果之连锁”。[21]223—224 显然运用疫学方法判断因果关系,可以更容易实现对环境侵权者的归责,从而遏制环境污染,减少污染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另外,伴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因人为因素致使环境对人特别是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类型和程度也将日益增多和加深,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因无力证明过错或因果关系的存在而不能获得赔偿的情况也会增加。所以将环境因素纳入对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考量,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利用环境,并有效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4.责任保险因素(liability insurance factor)
责任保险制度对侵权法产生了很大冲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传统侵权法上由加害人个人承担赔偿责任转由参与保险的多数人来分担,案件的实际加害人在诉讼中成为一个名义上的被告。责任保险制度的出现对传统侵权法的一些功能和原则提出了挑战。首先,责任保险制度的出现削弱了侵权法的威慑和遏制功能。因为有责任保险存在,当事人小心行事的动力减弱,从而可能引致道德风险。其次,传统侵权法上在判决被告承担责任的时候会考虑被告的赔偿能力,而有了责任保险制度,就没有了如此顾虑,所以责任范围有扩大趋势,并且在一些强制责任保险的行业,严格责任的适用更加普遍。最后,因为某种意义上讲,保险为责任铺平了道路,因此保险的存在成为判决承担责任的一个潜在的理由。[21]18
虽然目前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法律理论仍坚持认为责任保险的存在与否不应该影响法官对责任的判决结果,[2]64 但无可否认的是责任保险的存在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法官对具体案件的裁判,特别是对如何进行损失的分担、如何判断谁是较好的危险承担者产生影响。比如在前文提及的“纽约失火案”中,保险因素可以用来说明后25家被大火烧毁房屋的原告为什么在法官眼里,较被告是更好的损失承担者,因而仅判决被告对第一间房屋的毁损承担责任。
5.其他政策因素
除了上述政策因素外,还有一些政策因素对侵权责任以及因果关系的认定产生影响。比如随着工业化时代而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将个人安全视作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代价这样的政策的产物。而在现代,随着工业危险物的不断增加,以及对个体价值和劳工权利的强调,严格责任出现并有扩大适用的趋势。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的演变,反映了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权益保护的侧重点的转换。体现在因果关系方面,为了能够给予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如消费者、劳工、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人在举证方面的便利,使他们不会因为证据信息不对称而举证不能导致败诉,法院会采纳证明责任倒置、推定、事实自认制度等手段,放宽受害者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以便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弱者以救济。这其中显然渗透着法律政策的影响。
四、政策因素影响最近原因判断的实证研究
前文论及影响侵权责任及因果关系认定的一些主要的政策因素,但这些政策因素难免抽象和宏观,在具体案件中,这些政策因素以怎样的形式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载体又是什么,却并无定式。只是在一些特殊类型案件中,政策对因果关系的影响更为明显,是我们洞察因果关系和法律政策的关系的更直观的途径。
(一)被害人过错案件
被害人过错(fault of the injured party),同普通法上的与有过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大致同义,不仅包括被害人造成其自身伤害的过错,而且还包括了他没有及时将损害程度控制到最小的过错。一般认为,在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情况下,加害人得以有条件免责或者减轻责任。具体而言,如果被害人过错是损害的唯一原因,那么可以构成免责的抗辩理由,而如果是混合过错的话,加害人则可以要求减轻责任。[28]218 然而,由于强制保险领域的不断扩大,加害人因被害人过错而免责的情况正日益减少。
从因果关系角度看,被害人过错的存在并不就当然地引致被害人的自己责任,首先被害人行为的“原因力”对于损害而言必须是关键性的;其次只有当加害人能够证明被害人未能减少损失是不合理的,才能要求被害人承担一部分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现在存在普遍的强制保险的情况下,法庭总是更热衷于去发现被告的过错,而对于原告的过错则比较宽容。此类案件最典型的例子是交通事故侵权案件,由于机动车第三人责任险属于强制险种(14),所以无论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中,都表现出对被害人过错的某种程度的宽容。在这些案件中,要确定损害发生的原因,必须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另外,除了保险政策的权衡之外,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人的生命安全价值的倾斜保护,也是被害人过错案件中,在认定被害人行为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时候趋于采取较严格标准的理由之一。在我国之所以有些地方出现的“撞了白撞”的规定遭到的强烈批评并最终流产,正印证了政策对于人的生命安全价值的优先性的肯定。
被害人过错案件是典型的法律政策通过影响责任构成要件的认定从而影响责任分配的案件类型。由于强制保险的日益普遍存在,增加了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的渠道和可能性,在此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法庭倾向于去发现加害人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存在,以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假设没有保险制度的存在,法庭仍要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和加害人行为自由这两种价值目标进行平衡,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结果。
(二)救助案件
所谓救助案件(rescue cases),是指被害人在对他人进行救助时受伤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涉及到被救助的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侵权行为人和作为受害人的救助人三方当事人。一个路人在救助一名交通事故伤者的时候被其他车辆撞伤,这时候他是否可以从初始的侵权行为人处获得赔偿呢?对此问题的回答,既可以从过错或者普通法上的注意义务入手,也可以从因果关系角度来审视。
侵权人对直接受害人负有注意义务,这并无争议,但是否对向直接受害人施救的救助者也负有注意义务,却不无疑问。在美国,纽约州的Wagner v.International Railway Company一案[232 N.Y.176,133,N.E.347(1921)]确立的原则肯定加害人对救助者负有注意义务及赔偿责任。该案中,原告为了救助被火车事故抛出车外的侄子,却因天黑失足掉落受伤。Cardozo法官的判决理由有很深的政策影响痕迹:“危险招来救助,痛苦呼唤解困。”[23]210—211 “虽然此案中法律政策是通过让加害人承担注意义务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实际上也肯定了最近原因的存在。
除了从义务角度探讨救助者是否应获得赔偿,从因果关系链条是否中断进而判断救助者所受损害同侵权人行为之间是否过于“遥远”,并据此作出责任认定,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既能体现政策对救助行为的鼓励,又能给予判决充分的正当化理由的好的思路。在德国,实务上支持这种观点,认可为他人合理地避免和减少损害的企图不属于过错,除非救助者的行为属于蛮干,否则救助行为并不中断初始的因果关系链条,救助者损害同侵权人行为之间仍然存在因果关系,救助者应该获得赔偿补偿。[15]105
对于救助案件中,判断救助人是否可以从原始侵权人处获得救济的关键,是认定侵权人的行为与救助者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不因救助行为的存在而中断。虽然侵权行为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第一受害人的损害,而救助者的损害是因实施救助行为而引起,看似不是侵权行为的直接结果,但出于鼓励救助行为的道德风尚和政策考量,仍然给予救助者以救济,反映了政策因素对最近原因、侵权责任的认定所起的作用。
(三)涉及被害人特殊体质天性案件
因被害人特殊体质天性(predispositions)导致的伤害案件,是指在某类侵权案件中,因为原告固有的某种体质特征和倾向(主要是指生理的和心理的弱点,比如具有某种疾病),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程度和范围,可能超过了被告的预期。[15]105 比如被告因过错划伤了被害人的手臂,其并不知道原告是血友病患者,后被害人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否要对被害人死亡负责,涉及复杂的政策考量。
对于涉及被害人特殊体质和天性的案件,无论是普通法上还是大陆法上的德国,其采纳的原则都是一致的,即加害人必须赔偿被害人的所有损失,而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和天性作为内在的超越原因(internal overtaking cause)并不足以“超越”加害人的行为成为损害的原因。[2]108 德国法院认为,给身体有缺陷人士造成伤害的侵权人无权要求假设受害人是健康人那样的对待。[29]66 法国最高法院也认为受害人的体质天性并不足以中断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链条。[30]55
以因果关系理由让给具有特殊体质天性的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加害人承担责任,实际上蕴涵着政策方面的考量。表面来看,让加害人承担所有的损失,因其对被害人的特殊情况并不知情,对加害人来讲有些严苛,但是考虑到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无上价值,法律政策上应尽可能多地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这特别对于鼓励残障人士可以安全地参加社会交往,至关重要。如果让加害人只承担假设受害人是健康人所可能出现的损害责任,那么就等于强迫生理上有弱点的人反倒要在生活中处处小心,为自己的柔弱体质面临日益增加的危险而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法律政策对人的生命健康及残障人士的特别关注。
(四)追逐引起的损害案件
所谓追逐引起的损害案件,是指追逐者在追逐他人的过程中发生伤害的案件,涉及案件的核心问题是,逃跑者是否应为追逐者所受损失承担责任。此类案件多涉及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追逐中受伤的情况。
一名警察在追逐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受伤,如果嫌疑人增加了追逐风险的话,那么就认定他是警察受伤的原因。比如由于嫌疑人选择通过梯子逃跑就是增加了追逐者的风险,所以他要对追逐者追逐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承担责任。而在另一件案件中,逃跑者经过一个刚刚割过的草坪,追逐者扭伤了脚,法院判逃跑者免责,原因是刚刚清理过的草坪,应该一般不会增加追逐者受伤的风险。在这些案件中存在的潜在政策因素是:如果逃跑者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逃跑路径因此增加了追逐者受伤的风险的话,就应该由他来承担赔偿责任。[29]66
五、普通法上因果关系的事实与法律政策之争——代结论
侵权法上因果关系概念涉及的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政策考量、价值判断问题,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普通法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法律实在论者(realist)的观点。Green为其代表人物。实在论者认为因果关系就是事实上因果关系,只同事实相关,与政策、价值判断无涉,因此因果关系考察应集中在被告的行为是否实际上导致了原告的损害上。他们认为法律上因果关系充满着“非因果关系”的政策判断,意在对已经具备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适当的限制。基于上述理由,实在论者主张政策问题应该放在“义务”、“被保护的利益”、“损害赔偿”的名下进行讨论,而不应纳入因果关系范畴。[31]1523—1525 其二、以Wex Malone为代表一派反对实在论者的观点,认为因果关系问题并非纯粹的事实问题,认为即使是对“如果没有被告的行为是否损害会发生”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可能是事实的或者政策中立的。比如法庭怎么知道如果船上配备了适当的救生设施,溺水的人就一定不会溺水而死呢?他们认为上述问题的主要决定因素不是对盖然性的事实估计,而是要发现被告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受到的损害类型是否属于被违反的规则所要禁止的类型。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受政策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31]1535—1537[19]1808—1809 其三、关于因果关系概念的另一派观点是由Hart和Honoré提出的常识因果关系概念。他们从日常语言分析着手,认为无论是事实上因果关系还是法律上因果关系都蕴涵在对因果关系所作的日常语言陈述中,应该用常识的因果关系概念来架构关于事实的调查,不仅包括了事实上因果关系的问题,还包括了绝大多数法律上因果关系的问题。侵权法上因果关系问题无所谓事实问题和政策、价值问题之分,因为“造成损害是赋予责任的最通常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1]27—44 应该说,Hart和Honoré更多成分上是从事实角度来看因果关系的。
可见,普通法上对侵权法上因果关系概念内涵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强调因果关系的事实属性,不承认因果关系的规范属性,还是用政策的规范属性来涵盖吸收事实属性。笔者认为,普通法上因果关系考察二分法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不同的因果关系考察阶段实现不同的功能,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概念也不是严格意义上因果关系概念的种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地存在共性的东西。从根本意义上讲,笔者更认为,虽然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都用了因果关系这个语词,然而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因果关系在内涵上更接近因果律和一般因果法则,因此具有更多的“因果关系性”(causality)。因为认定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过程搀杂了人主观的选择和假设因素,因此它并不同于因果律和一般因果法则本身,在具体案件中,只是与同类的一般因果法则相若而已。至于“法律上因果关系”或“最近原因”,作为语词,其所指称的对象同“事实上因果关系”所指称的对象,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两者实际上是在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要描述的是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前后相继、并前者引起后者的关系,判断的标准从根本上讲是拿案件中的现实关系同人们对世界万物彼此联系的认知成果即对因果律的把握相比照,如果符合则成立事实上因果关系,否则不成立。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无论是可预见说还是直接结果说,它们本身就是以人的主观视角为出发点的判断标准,况且在判断过程中,特定的法律政策因素起主导作用。虽然主观视角并不必然意味着最近原因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远近,但从我们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作为归责基础或原因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更多地体现的是法律政策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对不同价值层级的判断,也包括了对于规范目的的看法。
收稿日期:2007—02—28
注释:
① 普通法上的二分法是将传统上“损害是否是被告行为的结果”这样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问题分成以下两个问题:“如果被告的行为没有发生,损害还会产生吗?”“为了法律目的,有什么原则和理由可以排除将损害作为被告行为的结果进而使被告免责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因果关系(actual causation;cause-in-fact)问题,第二个问题称为法律上因果关系(legal causation)或最近原因(proximate causation)问题。
② 所谓“but-for”规则(“若无,则不”规则),是普通法上认定事实上因果关系的主要规则,其方法是假设没有该事件或加害行为,考察损害是否还会发生;如果损害不会发生,则该事件或行为就是损害的原因,相反,如果损害依旧会发生,则不是原因。“but-for”规则是一种所谓的“全有全无”方法(all-or-nothing approach),即假设一个事件要么是要么不是损害的原因,通过but-for规则可以在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构建起某种事实上的关联。
③ “最近原因”、“法律上原因”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在本文中作同义词使用。
④ 公共政策本质上就是法律政策。“有时候它(公共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完全就是法律演变过程中,立法或司法功能上,最根本的伦理、治理和社会等诸原则和概念;而某些时候,它本身就是一法律名词,而意谓着‘公共利益的好处’。意即任何合法行为,若有侵害大众或违反公共利益之虞时,即应加禁止。”参见邓衍森:《法律哲学上司法造法的若干问题》,台湾《法律学报》第4卷第2期,第166页。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美国学者博登海默也认为,“在所有法律部门中,与审判有关的唯一类型的公共政策乃是法律政策”。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421页。基于此,本文后面引述的关于公共政策的观点,即关于法律政策的观点,两者不做区分。
⑤ 德国法上在适用规范目的说认定因果关系的时候,对于规范目的的考察,会涉及到对立法政策、目的的考量,但这一过程是在司法过程中实现的,不同于此处所讲的政策对立法的影响。
⑥ 与将最近原因问题视为政策问题的主流观点在表述上稍有不同,有英国学者回避用“政策”这个词,而是将最近原因问题等同于责任问题(responsibility),但实质上都是将最近原因作为归责工具。Hart and Honoré,Causation in the Law,p.106.
⑦ 在英美法系,不仅仅认为最近原因属于法律政策衡量问题,而且还有学者认为即使是事实上因果关系,本质上也是政策考量问题。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Malone,他认为事实上因果关系问题并非是纯粹的事实问题,其中也包含着政策的考量,因果关系对政策具有依赖性,因果关系判断从本质上讲是评价性的和有目的性的(evaluative and purposive)。“我发现即使是关于简单的原因问题,政策和事实之间的神秘关系也可能是最显著的问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问题有待解决的时候,政策经常成为一个因素,就像最近原因问题一样”。Malone,“Ruminations on Cause-In-Fact”,STAN.L.REV.vol.9(1956),pp.61—62.
⑧ 该案中,Donoghua女士与一位朋友去一家咖啡厅,在喝了一杯姜啤酒后,她发现啤酒瓶中有一只腐烂的蜗牛。最后法院判决制造商具有注意义务。Atkin法官在该案中对邻居原则作了陈述。A.c.562 at 569 Per Lord Atkin.
⑨ X以高车速开车撞到了P,在撞到的瞬间,他并没有踩刹车。x不知道,其实他从D处买的该车辆,刹车本身就有毛病,D明知这一事实却未告知X。依据Green的观点,X和D的行为和P的伤害之间有明显的因果联系。D将车卖给X,即使不考虑其明知刹车有毛病的细节,也是P受伤的促成因素。责任认定问题变成了义务范围和是否D和X对P存在过失问题。对于此案件,法院的看法则是x对P和所有路上没有超速的其他人来说存在义务,另外X对P还存在适时刹车以避免撞伤P的义务,陪审团无疑会得出结论,X对P违反了其义务,表现在超速和没有使用刹车。Green认为如果X履行了上述义务,就不存在义务和过失,因此就不用承担责任。关于D是否要承担责任,Green认为D对P和X及其他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人员来讲存在义务,即不应该在明知刹车有问题的情况下,不披露实情,将车卖给X。无论X存在多大的过失,Green认为D都要对由于X驾驶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因为可以推定如果知道刹车有问题,X不会冒险驾驶一辆刹车有问题的车辆上路。对于Green的上述看法,美国学者Richard W.Wright进行了反驳。Wright认为。在侵权法中,X的超速或者未使用刹车行为是典型的因果关系问题。要回答的是“X的超速或者未使用刹车(行为的过失方面)是否是P伤害的原因”这样的问题。D的责任问题实际上也是被义务问题遮蔽的因果关系问题(but-for),虽然D未披露刹车的问题存在过失,但是并非P伤害的原因。Green用义务分析替代了对因果关系的考察,而因果关系问题是很难用关于义务的表述和对义务的分析说清楚的。
⑩ 比如在上文提及的纽约失火案中,之所以让被告对于其他25家被烧毁的房屋免责,其中就有对保险政策的考量。
(11) 以下对法律政策要素的分析主要参考了Lawson and Markesinis,Tortious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Harm一书。
(12) Alcock v.Chief-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ne Police一案[(1991)4 All ER 907]是英国法上一个典型的精神困扰案件。在1989年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因人多看台倒塌,致使95人死亡,超过400受伤。16名原告因在球场或电视转播中看到或听到自己的亲人遇难,造成精神困扰和生病。于是起诉主管警察局长请求损害赔偿。审理本案法官认为,只有具备以下条件,原告才能获得赔偿:1.原告与被害人之间具有足够的亲密关系;2.原告与侵害事故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足够的密切关系;3.原告耳闻或目睹侵害事故或其直接结果。最后法院认为16名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上述条件,因此驳回赔偿请求。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13) 主要是指环境污染造成群体性病患案件。
(14) 我国国务院颁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涵盖了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15) Hart和Honoré的因果关系学说参见Hart and Honoré,Causation in the Law,PP.2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