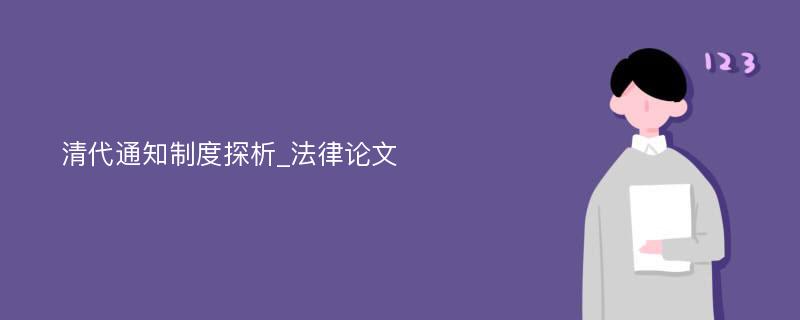
清代抱告制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清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9)01-0036-05
根据清代司法档案及官箴书等史料来看,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官吏、生监、老幼废疾及妇女为原、被告时应用抱告呈诉基本是各地通行的做法。①本文将综合利用官箴书、司法档案和清末诉讼习惯调查等史料对抱告制度作详实考察,弥补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足。
一
虽然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官吏、生监、老幼废疾及妇女为原、被告时应用抱告呈诉是各地通行的做法,《大清律例》中与抱告制度直接相关的规定仅有寥寥二例一律。②抱告制度与其说是法定的制度,毋宁说是习惯的做法。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为编纂诉讼法典的需要而开展了诉讼习惯调查,其中即多涉及了抱告制度。以下为笔者搜集的直隶、山东、湖北三省拟定的抱告习惯调查问题:
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拟定《诉讼事习惯调查书》“抱告”目[1]:
一、凡民事诉讼何项人得用抱告?
二、凡充当抱告是否必系亲属或家丁?有无随地雇用者并有无年龄限制?
三、用抱告之呈纸式?
四、所遣抱告以何为凭据,是否但凭其自称?
五、凡抱告一切行为及供述是否即视为原告所自为?
六、何种事仍需经原告自己之许可?如经断须赔偿或费财失权之事抱告能否承认?须具结者抱告能否代具?
山东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拟定《调查诉讼习惯条目·调查民事诉讼习惯调查条目》“庚”项[2]:
未成年者(按:未成年制度中国向无一定规则,兹所谓未成年者,即幼时依赖父母为生活而无独立营生之资格者)及有夫之妇诉讼之习惯如何?系自己为诉讼行为抑系抱告人代为诉讼行为?又,官绅及一切有身分之人凡遇诉讼往往自不到堂而遣抱告对质,其抱告人资格权限若何?
《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调查诉讼习惯问题》第四项“迅断”[3]:
……(七)抱告到案如供词支离或所供与原控不符,是否须令本人到案覆讯抑得照所供断结?(八)抱告遵结之案本人尚得呈请覆审否?
显然仅仅根据《大清律例》中的直接规定,我们难以回答上述大部分抱告习惯调查问题。幸好清代保存下来的大量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等史料可以为我们提供抱告制度更为丰富的信息。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二《遂溪书牍》“收状规条”中共有六条涉及抱告制度,为笔者所见官箴书中对抱告制度记载最为详实者[4]:
一、妇女家有夫男,子侄者不准出名具呈;违者,除责惩外,原呈掷还。二、生员非事关切己,不准具呈;具呈时虽准用抱告,仍须本人亲来。三、年七十以上者准用抱告;初词初审及旧案未经本县亲鞫者亦须本人随堂候讯。四、妇女除六七品以上曾膺封典之命妇及现任官员命妇与曾受旌奖之节妇如果家无丁男子侄准用家人抱告,优免亲自取供外,余虽准用抱告,初词初审及旧案未经本县亲鞫者均随堂候讯。五、绅士除曾作现任文职知县以上、武职都守以上,丁病休养回籍,并非降革罢黜者,准用抱告,优免本身取供外;余如曾任首领、佐杂等官及文武举人、正途贡监虽准用抱告,初词初审及旧案未经本县亲鞫者均随堂候讯。六、以上优免取供之现任职官命妇节妇如告人及被告罪名至杖一百以上者,仍须亲身到县,录取亲供。
根据徐赓陛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1)抱告在司法实践中除代原、被告呈递诉状外,亦代原、被告到堂接受讯问;(2)虽然妇女、生监、年老者、职官、绅士等人在诉讼中均准用抱告,但除其中身份地位较高者优免本身取供外,其余人等于初词初审及旧案未经现任县官亲审者均应亲身到县,随堂候讯。
为从当时具体司法运作中了解清代抱告制度,笔者特从陕西省档案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中随机抽取了同治、光绪年间100件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存在适用抱告现象的案例共30件,其中原、被告为老人者16例,原、被告为妇女者8例,原、被告为生监者11例。③(2)16例老人适用抱告的案例中(实为15个案件),抱告为老人之子者8例;孙1例;甥1例;婿1例;侄2例;侄孙1例;雇工1例。16例案例中经州县官堂断结案者6例,抱告一并到堂者3例。虽然紫阳档案“计开条款”中规定:“年七十以上及有残疾并妇女生监无抱者不准。”16例案例中,适用抱告的老人年龄最低者为61岁,70岁以下者共8例。(3)8例妇女适用抱告的案例中(实为7个案件),抱告为妇女之子者3例;夫弟2例;堂弟1例;侄1例;娘室兄1例。8例案例中,经州县官堂断结案者2例,抱告一并到堂者1例。8例案例中,孀妇为7例;有丈夫者1例,但据呈词称其夫“愚懦患病”。(4)11例生监适用抱告的案例中,抱告为雇工者7例;侄1例;姨侄1例;孙1例;弟1例。11例案例中,经州县官堂断结案者5例,抱告一并到堂者无。上述统计结果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充当抱告者主要为原、被告的亲属或雇工,其中老人、妇女以亲属充当抱告者居多,生监则以雇工充当抱告者居多;(2)抱告主要是代原、被告呈递诉状,有时亦与原、被告一并到堂接受讯问;(3)老人适用抱告的年龄不以“计开条款”所规定者为限;(4)适用抱告告状之妇女一般为孀妇,或有其他特殊情况者。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其抱告习惯报告部分可以回答我们不少疑问,也使我们对抱告制度的考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省一级的视野(时广西共设县四十九、散州十五、散厅七,州县一级政府合计七十一)。[5]
第二章 诉讼当事者
……
一、关于原被告之习惯
(甲)原被告之制限 左列诸人为原被告时非用抱告呈诉不为受理
(一)有举贡生监以上之出身者
(二)职官
(三)绅士
(四)年满六十以上者
(五)未成年者
(六)妇女
(七)废疾者
……
右所述乃一般之惯例,其他一二州县中尚有特例于左:
(一)太平府之养利州无论何项起诉均无用抱告之例。
(二)梧州府怀集县惟重罪事件不用抱告,余均得用抱告,不以前列诸人之诉讼为限。
(三)庆远府之河池州、南宁府之新宁州,惟生监职官及老幼废疾起诉用抱告,其绅士及妇女之诉讼鲜有用抱告者。
二、关于抱告之习惯
(甲)抱告之资格。抱告非有左列资格不能充当:
(一)亲属
(二)雇人
(三)服公役者
凡职官起诉多用雇人,其他多用亲属。关于地方重大案件则用服公役者。此种习惯亦与各国法律所定诉讼代理人之资格同。惟各国裁判所有调查资格确否之职权,故诉讼代理人无不合格者。广西抱告资格虽有制限,事实上多未实行。若桂林府之兴安、灌阳、义宁;平乐府之信都、富川、贺县;梧州府之怀集;南宁府之新宁;浔州府之贵县等处抱告不惟不拘资格,且填写伪名,官吏亦无从调查。此又特别之例。
(乙)抱告之权限分为二种
(一)有呈递诉状之权 凡应用抱告之案,其诉状均由抱告呈递。惟抱告供词递与呈词不符时,则须本人到堂呈明,此通例也。至若桂林之兴安;梧州之怀集;庆远之河池、天河;浔州之武宣;思恩之迁江;南宁之宣化;太平之崇善等处但以抱告供词为据,无本人到堂呈明之例。
(二)有赴公堂对审之权 此非抱告绝对之权利。凡原被告年老不能赴案或系职绅不愿赴案者始以抱告赴审。如未成年及妇女废疾则与抱告同时赴审。抱告所提出之意见及提出之证据均与本人有同一之效力。惟桂林之全州、灌阳;平乐之昭平、修仁;柳州之融县;太平之永康等处抱告只呈递状词,无赴案对审者。
作为一种诉讼习惯,抱告制度在各地之间颇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官吏、生监、老幼废疾及妇女非用抱告呈诉官府不予受理是普遍的惯例;抱告多由原、被告的亲属或雇工充当,原、被告身份地位较高者如职官等多用雇工充当抱告,其他人则多用亲属充当;抱告一般代原、被告呈递诉状,有时亦代原、被告赴公堂对审。
二
法制史学者在述及抱告制度时,常称其为“中国古代的诉讼代理制度”。从形式上来看,在近代以来的诉讼代理制度中,诉讼代理人代诉讼当事人为各种诉讼行为;在抱告制度中,抱告代诉讼当事人呈递诉状乃至代为出庭受审,二者颇为相似。然而即使清末诉讼习惯调查者也已发现中国的抱告习惯与各国的诉讼代理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指出“此种习惯与各国法律所谓无诉讼能力者同。惟无诉讼能力者只限于幼年、妇女、废疾诸人,因其无辨别是非之智识,不能不设人以辅助之。至举贡生监职绅年老者其识力本属完全,然必用抱告者,乃纯然身份上之关系,非智识上之关系,此与各国法律之异点也。”[5]诉讼代理制度与抱告制度背后各自的理念存在巨大的差异。简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诉讼代理制度是基于法理上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分立的法律关系主体制度而作出的制度设计,其内容是对无诉讼行为能力者特设诉讼代理人制度予以辅助,以维护其法律上的合法权利;同时对有诉讼行为能力者亦允许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诉讼上之辅助,以补自身智识之不足,以利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抱告制度则是中国古代“无讼”理想追求下对讼争现实的妥协性制度安排,实际上体现了国家限制诉讼以维持社会风俗教化的理念。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更是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除正面赞美无讼的理想境界外,还从另一方面制造为讼之害的舆论。如《周易·讼卦》说:“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等。“在古人眼里,兴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威胁,是陷人心于不古的权利之争和使人格与族望扫地的恶行。”[6]以下为笔者对清代诉讼惯例中几类主体应适用抱告诉讼的原因的分别考察。
(一)官吏
《大清律例》“官吏词讼家人诉”条明确规定:“凡官吏有争论婚姻、钱债、田土等事,听令家人告官对理,不许公文行移,违者,笞四十。”《大清律辑注》“官吏词讼家人诉”条律上注谓:“听家人告理,所以存其体;禁公文行移,所以抑其私也。”律后注谓:“官吏词讼,私事非公事也,故听令家人出名告官理对,不许官吏自以公文行移。”[7]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下,官僚阶级较之于平民享有很多特权。法律规定官吏在与他人争讼户婚、田土、钱债等事时,应令家人代为告官理对,乃是法律赋予官吏的特权,是“存其体”,即维护官吏的尊严。同时,法律规定官吏对涉己民事案件只可由抱告代告,而不可以公文行移,也有抑制官吏滥用权势,防止官吏干扰正常司法秩序之意,即“抑其私”。此外,还有一点也不应忽视,即,在当时社会中,官吏在道德上被视为平民的表率,规定官吏涉讼应由抱告代告,亦有避免官吏诉讼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的考虑。
(二)生监
《钦定礼部则例》卷五十七载:“生员当爱身忍性,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诉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大清律例》并未明确规定生监涉讼应由抱告代讼。
清代实行科举取仕,生监是官僚集团的预备人员,在社会中有着高于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在诉讼中要求生监须用抱告呈诉,事实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其尊严的维护,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当然也有维护社会良好风气的意愿。同时作为现实层面的考虑,亦可以尽量限制生监利用特权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
(三)老幼废疾
《大清律例》“现禁囚不得告举他事”附例规定“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此条例乃是对正律“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的规定的修正。这一规定大致是司法实践中老幼废疾涉讼须由抱告呈诉的渊源。
《大清律辑注》“现禁囚不得告举他事”条律后注谓:“名例内人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之人,犯罪者,勿论,……不准告,以其罪得弗论、收赎,难以反坐,因得诬告害人也。”例上注谓:“律不得告而例许代告者,恐实有冤抑之事,限于不得告之律,致不得申辩。故立此代告之例,则有冤者可以辩理,诬告者亦得反坐,所以补律未备也。”[7]中国古代追求“无讼”,对遇有纠纷轻易诉讼者已动辄斥为“健讼”、“刁民”,予以压制,对诬告者更是严惩不贷。同时,在儒家“矜老恤幼”思想影响下,法律对老幼废疾的犯罪行为一般予以宽免。为防止老幼废疾等人借法律的优待诬告害人,法律特对他们的诉权作出严格限制,最终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即老幼废疾涉讼须由抱告代告,如所告之事不实,由抱告承担责任,以追求“有冤者可以辩理,诬告者亦得反坐”的良好效果。
(四)妇女
从司法档案及其他有关史料来看,这里的“妇女”一词主要是指“寡居无依,及虽有子男,别因他故妨碍,事须论诉者”。④
在中国古代,妇女无独立人格,必须依附于男子。所谓“妇人,伏于人也”,“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8](本命)在中国古代,妇女在家有男子的情况下抛头露面,出入公堂进行告状,实属违反“三从”、破坏“三纲”、违背天理的行为。⑤故在法律上妇女原则上并无告状权。然而对“寡居无依,及虽有子男,别因他故妨碍,事须论诉者”之妇女,法律如不予救济,使其有冤不得伸,显亦于情理不合。《大清律例》即明确规定妇女于“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在法律实践中,一般允许有特殊情况的妇女遣抱告代告,以使其冤抑得伸。这将妇女抛头露面出入公堂的次数降至较低的必要限度内,既维护了礼教、风俗,也保存了涉讼妇女个人的颜面。此外,与老幼废疾的情况相似,要求妇女告状适用抱告也有防止妇女滥用法律优待诬告害人之意。⑥
总之,在清代民事诉讼中,虽然官吏、生监、老幼废疾及妇女告状须用抱告的具体原因各异,但均体现了“无讼”的价值追求。正因此故,在清代民事诉讼中抱告除代原、被告为代递呈状等诉讼行为外,也必须承担原、被告诬告的责任;能够充当抱告的人也仅限于与原、被告有亲密身份关系的亲属或雇工。这均与近代以来的诉讼代理制度不同。近代以来的诉讼代理制度下,诉讼代理人仅代诉讼当事人为各种诉讼行为,并不因此而代当事人承受实质的法律后果;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选择亦不以与诉讼当事人存在亲密的身份关系为前提,而注重于诉讼代理人的法律知识及技能。
收稿日期:2008-10-12
注释:
①如黄岩档案“状式条例”中规定“凡有职及生监、妇女、年老、废疾或未成丁无抱者,不准。”清雍正十年祁门县“告状不准事项”中规定:“绅衿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及虽有抱告年未成丁者,不准。”巴县档案“状式条例”中规定:“有职人员及贡监生妇女无抱者不准。”陕西省档案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计开条款”中规定:“年七十以上及有残疾并妇女生监无抱者不准。”黄六鸿所立状式所载“状式条例”规定:“生监及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者不准。”《大清律例会通新纂》“越诉”条所附同治十二年通行“计开条款”中规定:“生监、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者不准。”“状式条例”或称“计开条款”是当时诉讼状纸上所载的告状不准条款,当事人告状时应予遵守,否则官府不予受理。
②即“越诉”条附例:“军民人等,干己词讼,若无故不行亲赍,并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女、家人抱赍奏诉者,俱各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壮丁问罪。”“现禁囚不得告举他事”条附例:“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的实之人代告。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官吏词讼家人诉”条:凡官吏有争论婚姻、钱债、田土等事,听令家人告官对理,不许公文行移,违者,笞四十。
③分类统计时,如原、被告均适用抱告,则按原、被告类型分别统计,重复计算。在30件案例中,原、被告均适用抱告者5件:原告为老人,被告为监生者1件;原告为妇女,被告为老人者1件;原告为监生,被告为老人者1件;原、被告均为老人者1例,原、被告均为妇女者1件,故各项之和并非30件,而是35例。另有1件,原告为监生,虽年龄亦已79岁,笔者在分类统计时仍归于生监类。
④《元典章》“妇人不许诉”。《大清律例》中虽无此规定,但从有关史料来看,实沿承了元代的做法,如黄岩档案“状式条例”中规定:“现有夫男,教以妇女出头混控者,不准。”巴县档案“状式条例”规定:“夫男现在,令妇女出头者,不准。”《大清律例会通新纂》“越诉”条所附同治十二年通行控诉条款中亦规定:“妇人有子,年已成丁,即令其子自行出名呈告,如仍以妇女出名,以其子作抱告者,不准。”
⑤如《元典章》“妇人不许诉”谓:“妇人之意,唯主中馈,代夫出讼,有违理法。此等侥幸,在在如是,不加禁约,败俗弥深。以此参详:凡妇人代替男子经官告辨词讼,合准所言通行禁止。”
⑥《大清律例》“工乐户及妇人犯罪”规定:“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受刑,余罪单衣决罚,皆免刺字。若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大清律辑注》“现禁囚不得告举他事”律上注谓:“囚在禁而许其告人,恐奸徒恣其诬枉”,“此条唯重在‘恐有诬告’上,盖老幼废疾,妇人,与禁囚不得告之意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