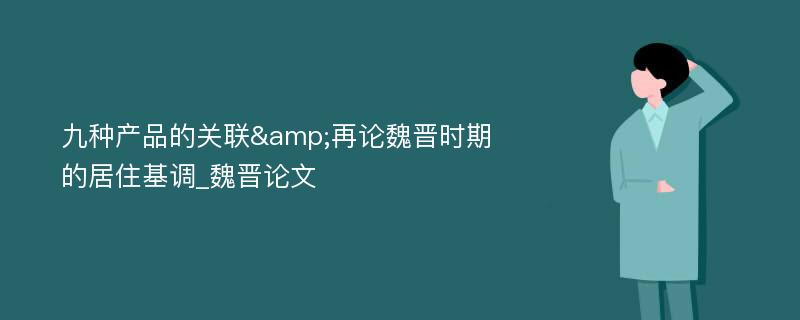
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九品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的租赋征收体系中,其主要的内容虽然可以归结为田租、口算赋这两大块,但事实上是多头的。作为农业收益税的田租,原则上按三十税一的税率征收谷物(事实上定额租的可能性极大);作为田租附加税的有刍藁税,除实物以外还可以用粟谷、货币代纳;人头税是按年龄征收货币的口算赋。此外,还有代替徭役的更赋钱、财产税以及其他一些临时课调。汉代的这种赋税体系,到了建安年间曹操执政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按田亩征收定额田租的方法取代了三十税一的定率田租;作为田租附加税的刍藁税消失了;按人头征收的口算赋、财产税、临时课调变成了按户征收的户调;代役的更赋钱也消失了。对农业社会的征收体系就简化成了田租、户调这两大块。建安以后的征收体系,通常被称为租调制。这一征收体系为不久以后成立的曹魏政权及继之而起的西晋王朝所继承,并一直影响到了唐代中期。
从两汉的租赋体系演变为魏晋以后的租调制,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重大改变也意味着社会性质的重大改变,这一点通过前人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明确了。然而,同样是租调制,魏晋时期的租调制与北魏施行均田制以后的租调制,虽然在名称、征收内容等方面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制度的理念上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租调制历史上的阶段性变化,同样也意味着社会性质在朝着新的方向蜕变。
如果说按一夫一妇(一床)或丁为单位征收租调是北魏均田制以后历代租调制的特征的话,那么,按户征收户调,按田亩征收田租,就应该是魏晋租调制的时代特征。魏晋租调制的这一时代特点,又可以用当时的“九品相通”这一用语将之概括。
“九品相通”也称“九品混通”,是魏晋时期征收户调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在征收户调时,对一定范围内的民户进行资产评估,按资产的多寡将民户分成九等,然后再按九等户的上下分担户调的总额。其实,“九品相通”的原则不仅仅只限用于户调的征收,由于评定资产的主要依据在农业社会里应该是田亩,因此,“九品相通”的原则又与土地的审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通过对“九品相通”的探讨,可以从中发现魏晋租调制的性格特征,并以此来进一步认识魏晋社会的性质。关于魏晋时期的田租,笔者已在多种场合作了探讨(注:参见拙稿《试论曹魏租调制度中的田租问题》,《史林》第81卷第6号,京都,1998年;《再论西晋的占田、课田、租调制度》,《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1号,京都,2000年;《论东晋的“度田税米”》,《中国史研究》第8辑,韩国大邱,2000年2月。),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以下,我们想通过“九品相通”这一征收原则来思考一下魏晋户调的性质问题。
魏晋户调制的研究及问题之所在
关于魏晋户调制的研究,以往的学者大多将精力集中在这一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上,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不用说,在户调制研究上,这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日本学者野中敬在《魏晋户调成立考》一文中,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止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整理和评述(注:野中敬:《魏晋户调成立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第14集哲学、史学编,东京,1987年。)。据野中敬的整理,关于户调制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大类意见。
1.主要从东汉末年以来的战乱历史来说明户调制的产生。持这一类意见的主要有松本善海(注:松本善海:《以邻保组织为中心的唐代村政》,《史学杂志》第53卷第3号,东京,1942年。后载其《中国村落制度的历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曾我部静雄(注:曾我部静雄:《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第二章《晋代土地税役制度》,东京讲谈社1953年版。)等人。
这一类意见认为,东汉末年以来的战乱,导致了人民的流亡和土地的荒废,政府无法彻底进行人口和土地的调查。而与人口、土地相比,民户的调查则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以户为单位的户调征收就应运而生了。
2.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来探讨户调制的产生。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唐长孺(注: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载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西岛定生(注:西岛定生:《曹魏的屯田制——尤其是其废止问题》,《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十,东京,1956年。修订后载其《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田中整治(注:田中整治:《关于曹魏的户调制》,《北海道学艺大学纪要》第一部,第九卷第一号,1958年。)、高敏(注:高敏:《曹魏租调制拾零》,《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后载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主要内容又见其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人的论说。
西岛定生认为,户调源于汉代的口算赋,在征收形式上,以户为单位征收实物绢绵取代了汉代按人头征收货币。从按人头变为按户,这意味着国家对一个一个的人的直接统治,即所谓的“个别人身支配”弛缓了。从征收货币改为征收实物绢绵,则意味着东汉以来货币经济的衰退和实物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扩大。
从汉代的赋税体系内部来探求户调制的产生,在这一点上,唐长孺的着眼点与西岛是一样的。但唐长孺更注重被称为“调”的这种汉代的临时征发制度,认为:这种临时性的征发到了曹操时代开始普遍化,吸收了算赋而产生了户调制;户调征收实物绢绵的做法是受到了汉代用布帛折纳算赋的影响;至于放弃人头按户课税,则是由于布帛无法按人头裁断交纳,因此,作为生产单位的户就自然地成了课税的单位。
高敏的意见与唐长孺一致,只是从《续汉书》百官志所记“啬夫”按民户的贫富之差调整税额这一执掌中,认为资产评定的单位“户”代替人头成了课税单位,补充了唐长孺的意见。田中整治也同样是从汉代的算赋中来探讨户调的产生的。
3.力图从货币经济的消长上来解释户调制的产生。藤元光彦是其主要论者(注:藤元光彦:《户调的产生——尤其是从其与货币经济的关系来看》,《立正史学》第61号,东京,1987年版。)。藤元认为:由于算赋征收货币,导致了农民的没落和破产,为了阻止这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国家出于无奈,促使布帛的流通,使之起到通货的作用,并以此来抑制商业阶层在市场上的势力膨胀。
针对以上三种意见,野中敬作了评述,并提出了一些疑问。对第一种意见,野中指出,战乱时期,如果人民流亡,脱离土地,那么,户口比人头容易把握这样的说法就很难成立。对第二种意见中西岛定生的看法,野中指出,虽然西岛从货币经济的衰退和国家权力对人民的控制弛缓这两方面探讨了户调制的产生,但是,如果是因为泰汉帝国的崩溃、国家权力的弱化而使得人头税变成了户调,那么就存在着与第一种意见同样的疑问。至于唐长孺的意见,野中认为是纯制度史的研究,汉代临时征发的“调”为什么到了曹操时变成了“正税”,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回答;至于不能裁断交纳的意见,野中认为有可能采取像唐代那样邻里数户合成匹端交纳的方法。针对第三种意见,野中指出,因货币流通的衰退而不得已采用的实物征收应该是一种消极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因这种消极的理由而施行的“调”能够延续六百年,在国家权力强大的隋唐时代仍有着它的地位呢?
在整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野中敬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基于“任土作贡”原则的布帛征收,是在黄巾起义以后强制人民生产布帛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恢复生产;又因为户调的课税对象是“男耕女织”的小农,因此,以户为课税单位,反映了魏晋国家扶持小农的意图。
但是,野中的观点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其论文中的两根支柱,一是“任土作贡”的贡赋原则,一是“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任土作贡”的目的,野中认为是使人民安于土地,通过劝农政策,恢复农村的生产秩序。但是,同样是战乱以后恢复生产期的西汉初年,为什么就没有采用“任土作贡”的原则实行实物征收呢?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征收货币的人头税制度得到了完善。至于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是中国两千年来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而并非魏晋时期所特有。因此,野中敬的新论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战乱后政府无法对农村的人口进行准确的把握;由于东汉以来货币经济的衰退而导致了货币流通量激减;东汉时期临时征发的“调”逐渐普遍化最后取代了算赋;征收实物绢绵是基于“任土作贡”的贡赋原则;以户为课税对象是基于“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这些具体的理由不用说都是户调制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又似乎都不是户调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的各种意见中,有一点其实是具有启发性的,这就是西岛定生的意见。西岛将户调制的产生与秦汉帝国的政治构造——“个别人身支配”结合在一起,主张户调的出现是“个别人身支配”这一统治体制衰退的一个表现。这就意味着户调制的产生是与秦汉社会性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户调制产生的背后,体现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外,永田英正《汉代人头税的崩溃过程》一文也意识到了汉代人头税的崩溃与秦汉帝国的崩溃之间的关联性。(注:永田英正:《汉代人头税的崩溃过程——以算赋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18卷第4号,京都,1960年。)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对汉代社会性质的变革和魏晋社会性质的探讨,才能真正找到户调制度产生的原因。
汉魏社会的变革与乡村“豪族共同体”原理
关于东汉时期社会性质的变革以及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特征,经过中外学者近一个世纪的探讨,其面貌已渐渐地清晰起来。尤其是宇都宫清吉、宫崎市定、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人,对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对魏晋租调制的研究极富启发性,笔者与他们的观点之间有许多着许多共鸣。以下,主要想利用前人的既有成果,对两汉、魏晋政治社会的基本性质作一个概观,从中来探讨户调制产生的社会基础。
两汉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征,宇都宫清吉曾经作了扼要的阐述(注:宇都宫清吉:《掌握中国古代、中世纪历史的一个视角》,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与文化》,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第17~39页。)。对汉代历史的特征,宇都宫是这样认识的:始终贯穿于汉代历史的是“皇帝”与“民”这一对关系(加了引号的皇帝和民在这里特指两汉政治社会中皇帝与民这一对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在“形式”上通过二十等爵制将两者自上到下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种“机能上的秩序”。对于这种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显著特征,宇都宫用“一君万民”这一词语作了概括。另一方面,从政治或者权力的统治这一侧面来看,在“皇帝”与“民”之间,存在着“官僚”这一大机构。官僚是将“皇帝”的政治意志贯彻于“民”的,从这个意义上,官僚是“皇帝”的股肱,是“皇帝”的分身。而产生这些官僚的母体,就汉代而言,不是别的,正是“民”(即所谓的“乡举里选”)。官僚的这种性质,与魏晋时期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接着,宇都宫又分析了汉代“皇帝”统治“民”的特征。他认为,在汉代,“皇帝”的权力贯彻到了全“民”之中,“皇帝”对“民”的统治可以延伸到每一个人头,这就是所谓的“个别人身支配”,而作为人头税的口算赋就是这一统治体制在制度上的显著表现。为了推行这种人头税,必须对一个一个的“民”进行具体的把握。因此,通过行政手段,依照“民”的基本组织——家族——编造户籍,调查人口。所谓的“八月案比”,就成了两汉四百年始终厉行的严格的制度。宇都宫认为,汉帝国之所以为汉帝国,其制度上最大的特征就在于这一点。
但是,在汉代这种专制体制下,又不应该是“皇帝”单方面对“民”的统治,即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强权世界”,与“皇帝”处于对极关系上的“民”也应该有自己的秩序原理。汉代以乡村为舞台的“民”的秩序原理,宇都宫认为是以家族为中心通过儒家“孝”的伦理结成的“自律性世界”。这两种“世界”是潜藏在汉帝国内部的一对矛盾,其变化发展的结果,是“皇帝”不得不变身为儒家式的皇帝,原来代表“强权”、法律的文吏也不得不转向代表乡村要求、心意、伦理秩序的儒生,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礼教世界”。这样,以基于儒学精神的乡村社会为背景进入政界的官僚们,又因其出身于“民”,所以自身也就带有乡村社会的许多矛盾。
另一方面,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生活,由于受到气候等各种条件的影响,社会、经济上的沉浮是相当激烈的。因此,乡村社会整体上趋于阶层分化。在这种形势之下,乡村的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具有经济优势和文化传统的人家——豪族——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代表者及支配者,新型的乡村秩序关系产生了。宇都宫将这一时期在乡村发生的这种秩序关系上的变化称为“乡村的豪族化”。这种新的支配体制与“皇帝”的支配体制完全不同,这种乡村支配体制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汉帝国将失去乡村社会这个重要的经济基础乃至军事基础。原来通过国家权力——行政手段征收的人头税、田租、力役、兵役等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宇都宫认为,汉帝国的彻底崩溃,其根源就在于“乡村的豪族化”。
随着乡村豪族化的进展,帝国的官僚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具有自由意义的来自于“民”间的“乡举里选”也被豪族层独占。这样一来,本来应该是“皇帝”股肱的官僚机构,不但无法彻底贯彻“皇帝”的权力,反而将官僚制全盘变成了门阀豪族层的公共财产,皇帝的地位如果没有以门阀、豪族集团为首的所谓“天下士大夫”的共同承认就无法确立。到了公元2世纪末,这种矛盾达到了顶点,汉帝国终于彻底崩溃了。汉帝国的崩溃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世纪。
针对汉代社会内部的这种矛盾变化,宇都宫清吉以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之作了详细的考察(注: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著很多,笔者主要参考了以下几种: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纪社会与共同体》第一部第二章《中国的中世纪——六朝、隋唐社会与共同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部《贵族制社会的形成》所收的各篇,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狩野直祯:《东汉末期地方豪族的动向——地方分权化与豪族》,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第43~68页;稻叶一郎:《汉代民间秩序的形成》,载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版,第243~274页。)。笔者也曾以这种激烈的社会变动为背景,从汉代赋税制度内部潜在的矛盾以及汉代赋税制度的崩溃这一角度来探讨曹魏租调制度产生的必然性(注:参见拙稿《试论曹魏租调制度中的田租问题》,《史林》第81卷第6号,京都,1998年;《再论西晋的占田、课田、租调制度》,《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1号,京都,2000年;《论东晋的“度田税米”》,《中国史研究》第8辑,韩国大邱,2000年2月。)。
魏晋时期通常被称为“门阀豪族制社会”或“贵族制社会”。门阀当然是指豪族中有着特定的家世、历世高官的那一批贵族。在门阀贵族之下,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够不上门阀的一般豪族层。这些大小豪族在社会上、文化上,也即在权力、经济、精神以及人格上,对乡村的农民有着有形无形的支配能力,乡村社会的秩序也正是由他们来维持的。豪族与乡村农民之间结成的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笔者所理解的乡村豪族共同体关系。
那么,维持魏晋南北朝乡村秩序的豪族层,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的呢?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两人关于“豪族共同体”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魏晋以后的豪族,川胜认为,豪族并不等于贵族,贵族是“有教养的豪族”(注:参见前注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3~22页。又见其《六朝初期的贵族制与封建社会》,载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研究》,第3~52页。)。“豪族共同体”这一用语中的“豪族”,应该赋予川胜所说的“教养”这一内涵。对魏晋南北朝豪族的性质谷川道雄作了更加详细的探讨。贵族的形成及其累世不衰的基础,比大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要素。这种精神方面的要素就是谷川所谓的“士大夫伦理”。而这种“士大夫伦理”又是通过“轻财重义”、“轻财好施”的救济精神,“恭俭”、“累世同居”的生活理念以及“乡党支配”的社会伦理等表现出来的。(注:参见谷川道雄《北朝贵族的生活伦理》,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后收进其《中国中世纪社会与共同体》。又《贵族制与封建制》,载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研究》,第53~69页。)在皇帝权力无法完全贯彻到社会基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村的生活是以这一批大小豪族为中心展开的。对于这样的时代特征,谷川用“地方的时代”这句话作了概括(注:谷川道雄:《“共同体”论与六朝乡里社会——答中村圭尔氏的疑念》,《东洋史苑》第54号,1999年。)。豪族与乡村自耕农民之间的这种新型的乡村共同体关系不同于汉代以行政手段为基干的“里共同体”。而以“九品相通”为原则的户调制度就是这种地方自治性质的共同体关系的显著表现。
“九品相通”与乡村共同体原理
萌芽于汉代社会内部的“调”,原来是一种临时性的征发(注: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载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而且从一开始就有按家资多少课税的迹象(注:高敏:《曹魏租调制拾零》,《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后载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主要内容又见其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调的征收,到了东汉初期在史籍中已经有很明显的反映(注:例如,《后汉书·刘平传》谓刘平“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刘平是东汉光武帝、明帝时人,此事发生在光武帝时期,表明东汉初期已经有这种按赀定赋的做法。《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五年(93)二月条中也有平赀的记载,“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鬲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又《续汉书·百官志》载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即按民户贫富的不同确定其课税等第。)。然而,殇帝延平元年(106)七月诏中称:
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中略)二千石长吏其各实覈所伤害,为除田租、刍藁。(注:《后汉书》卷四《和殇帝纪》,殇帝延平元年七月条。)
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汉赋税征收中按田亩征租(包括附加税刍藁),按人口征赋这一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将这一时期按家资等级征收的“调”理解为临时性赋课是妥当的。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豪族化倾向的不断发展,加上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行政机能无法挽救乡村,货币经济的衰退等各种因素,政府在乡村的行政机能逐渐后退。基于严格的户口调查之上的人头税的正常征收势必受到影响,而立足于乡村秩序(乡村内部按贫富之差进行自我调整)和乡村生产形态(以小自耕农家族为单位的实物绢绵布麻生产)、本来作为临时课税的“调”的比重越来越大,建安五年前后在曹操的主持下将“调”的征收制度化(注:“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所谓曹操的《令》,虽初见于建安九年平定冀州以后,但据吉田虎雄(《魏晋南北朝租税研究》,大阪屋书店,东京,1943年)、唐长孺(前注)、高敏(前注)等人的研究,包括户调在内的曹魏租调制度,至迟在建安五年十月已经开始实施。),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洪传》注引《魏略》称:
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曹洪)耶!
又卷十五《贾逵传》注引《魏略列传》杨沛事称:
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县令杨)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
曹操为司空是在建安元年十月,《通鉴》对“平赀”事无系年,所以此事发生的具体年月不详。但从“每岁发调”的记述来看,按家赀高低征收户调似乎已经成为定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司空曹操在内的高官高位者也逃脱不了户调的征收,而且谯县令杨沛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不法的曹洪宾客进行处罚。这是否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建安元年前后的户调制还保留着一些汉代的气息。汉代,尤其是西汉,即使是承相之子,原则上也逃脱不了负担算钱、兵役(包括代役钱的更赋)的义务,魏晋贵族制社会的那种免课免役的贵族主义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还没有确立。(注:参考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二编第一章,京都,东洋史研究会刊1956年版。)东汉以来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豪族走向贵族化,或者说贵族主义从产生走向确立的过程。不过,从上引曹操、曹洪的事例中可以窥知,建安初期这种贵族主义似乎还没有制度化。另外,从中也可以看出户调制与汉代口算赋、更赋在制度上的继承关系。
通过评定家资征发户调萌芽于东汉时期,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于曹操时期,但是,是什么时候将户调分成九品的,这一点目前还无法确定。成立于魏末晋初的西晋诸侯分食制度的规定中,“其余租及旧调绢二(衍字)户三(二之误)匹绵三斤,书(或是“尽”之误)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注:《初学记》卷二十七《宝器部·绢第九》所引《晋故事》佚文。关于这一段史料的考证以及西晋诸侯分食制度的研究,参见拙稿《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规定中所谓的旧制,指的应该是曹魏的制度。因此,“九品相通”的原则在曹魏时的运用是无疑的。九品相通原则的制度化,与“九品官人法”等一系列贵族主义法规的制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曹操时期制定的户调额是“绢二匹绵三斤”,西晋时期的户调额是“绢三匹绵三斤”,户调增额的理由不是很清楚。野中敬认为是为了补偿因屯田的废止所造成的财政损失,这或许是理由之一,但并不能排除在废除屯田之前的某个时期户调额已经增加的可能性。
在论及户调时,往往有这样一种错误,这就是将魏晋户调视作定额课税,将之与汉代的口算、更赋在钱额上进行数量比较,或与北魏以后均田制下一夫一妇的床调在匹丈上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汉与魏晋、魏晋与北朝隋唐赋税制度、征收体制的差异。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以上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性质和“九品相通”原则缺乏深刻的认识。“绢二匹绵二斤”也好,“绢三匹绵三斤”也好,都是政府制定的交给地方基层组织(县的可能性很大)的一个征收标准,绝对不是每一户都得负担的数额。至于每户所负担的户调数额,则由共同体内部通过评定各户赀产,在总额不变的前提下按九等进行调整。例外肯定是有的,但总的来说,主持这类工作的人无论地方行政官吏还是乡村豪族,仁德、人望、教养等人格上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郑浑传》中记载他建安年间在京兆尹任上,
(郑)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者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资贼止息。
从郑浑的事迹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郑浑是积极地有意识地在建立乡村共同体社会,“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者为比”,通过这种互助关系来勤稼穑,明禁令,发奸者,达到维护乡村秩序的目的。这个新建立的共同体社会,虽然是在京兆尹郑浑这样一个地方长官的主持下形成的,形式上似乎是在行政手段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这种共同体关系应该是出身于“历世名儒”的郑浑式士大夫的理想模式。建立之初,虽然成员都是因各种原因新集到一起来的民众,但是随着生活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其中的“兼复者”(多丁户)或“温信者”(教养者)发展成为大族、豪族的可能性极大,乡村秩序的维持最终会落到这些人的头上,而不再是行政长官。“九品相通”的户调征收原则就是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晋书》卷七十《刘超传》记刘超东晋初,
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迄,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
太康元年(280)以后,江左的句容一带被纳入西晋王朝的统治之下,按“九品相通”原则征收的户调也开始施行。可能由于这一带的乡村共同体的自治程度还不是很高,因此,每年评赀时,由行政机关派人四出主持,效果看来并不理想。东晋建国后,刘超为句容令,采取了上述的方法,结果增加了户调的收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超的“大函”是“村别付之”,而不是户别。这意味着给予乡村共同体更多的自治权。这既是魏晋以来中原地区共同体支配的经验,又是魏晋贵族制社会这一时代的必然之路。因此,刘超的行为受到了赞扬。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刘超“推诚于物”的品德与人望。
按“九品相通”原则征收户调的具体事例,可以从《张丘建算经》的例题中找到。例题如下:
今有率户出绢三匹,依贫富欲以九等出之,令户各差除二丈。今上上三十九户,上中二十四户,上下五十七户,中上三十一户,中中七十八户,中下四十三户,下上二十五户,下中七十六户,下下一十三户。问:九等户户各应出绢几何?
答曰:上上户户出绢五匹,上中户户出绢四匹二丈,上下户户出绢四匹,中上户户出绢三匹二丈,中中户户出绢三匹,中下户户出绢二匹二丈,下上户户出绢二匹,下中户户出绢一匹二丈,下下户户出绢一匹。
《张丘建算经》三卷,被列入唐代国子监算学博士的十一种教科书中,成书于北朝时期,钱宝琮将成书的年代具体到了466~484年间(注:参见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又《算经十书·张丘建算经提要》,中华书局1963年版。)。题中的“率户出绢三匹”的说法,反映的很可能是西晋时期的情况。题中的总户数是386户,这是一个在较大的范围内实行的九品相通。从户等间的比例来看,也比较合乎现实,可见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数学题目,而是有着它的可信性的。郑欣先生甚至指出,这段资料很可能源于两晋的官文书,前一部分的上上户至下下户的构成应是官府估计的地方上的大致情况,后一部分上上至下下各等户的纳调数就是晋中央规定的比额(注: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年第1期。后载其《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处于九品中间的中中户户数最多,这一等户实际负担的调绢是三匹。可以推想,西晋户调制法规中规定的户调额三匹,就是以九品中的中中户的负担能力而定的,各户等之间的差额是二丈(半匹)。也由此可以推测,曹操制定的“绢二匹、绵二斤”这一户调额也应该是建安时代相当于中中户的民户实际负担的额数。
综上所述,魏晋的户调,绝不是定额课税,而是在家赀评定的基础上按“九品相通”原则征收的,是可变的。户调从生产时的一种临时性征收发展成为国家的正规税制,是乡村豪族化的结果,是贵族制社会自治性乡村共同体原理的体现。户调制的产生和确立,其步伐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以及孕育于古代社会内部的中世纪社会的产生、确立是一致的。
兼论北魏前期的征收体系
这里所说的北魏前期,是指北魏建国至孝文帝太和九年(485)施行均田制以前这一历史阶段。
北魏建国后不久,实行了解散部落,“息众课农”,又在平城和大宁河一带对被称为“新民”的被掠人口实行给牛、给农具、“计口授用”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推测只限于地广人稀的朔北,而且还多少具有屯田的性质,与华北传统农业地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息众课农”及新附民“计口授田”下的征收体系,因史料的阙如难以明了。而对广大的华北地区的乡村农民,北魏政府采取的征收体系依然是魏晋以来传统的租调制度。相关的史料并不少,以下择数条以明其要。
1.《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398)正月:
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
天兴二年八月:
除州郡民租赋之半。
2.同书卷三《太宗纪》神瑞二年(415)三月诏:
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后怠惰,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征发于民。
3.同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四年(443)六月庚寅诏:
今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
4.同书卷五《高宗纪》太安四年(458)五月壬戌诏:
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以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县,咸有逋悬,(中略)在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
上引史料中的“赀调”、“赀赋”很明显是按赀征收的“调”,“赀租”、“租赋”则是租、调之合称。“田租”是按田亩所课之租,与户赀无关。从《世祖纪》太延元年(435)十二月甲申诏书中的“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的文句来看,户调仍然按“九品混通”的原则征收。按赀征调、按田课租的基本理念在制度上与魏晋是一致的。
北魏前期的租调征收,可以见到《太宗纪》明元帝泰常三年(418)九月“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高祖纪》孝文帝延兴三年(473)七月的“诏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以及同年十月“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等事例。但是这些事例都应该是备战时的临时征发,不能视为制度内的征收。北朝前期租调征收制度上的规定,见于《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食货志》记的是太和八年(484)制定百官俸禄时的规定,“至是”以后的部分是太和八年新加的,以前的部分应是北魏前期较长的时间内施行的制度。户调额是帛(绢)二匹、絮(绵)二斤、丝一斤,与西晋的绢三匹、绵三斤相比,绢、绵虽然各减少了一匹、一斤,但增加了丝一斤,在总的负担上基本是一样的(北魏前期的度量衡与西晋时期基本上没有变化),加上调外之费,比西晋略有增加。田租为二十石,按平均一户耕种五十亩算,亩租四斗,与魏晋时期相比也没有变化。(注:关于魏晋时期田租亩收“四斗”,贺昌群(《升斗辩》,《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周国林(《曹魏亩收租四升辩误》,《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增刊。又见其《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先后作过考证。笔者赞成两人的意见,并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考察,见前注①《试论曹魏租调制度中的田租问题》。)因此,可以说北魏前期的租调制基本上是魏晋制度的沿袭。
对于《食货志》中所记的北魏前期的租调制度以及上面所引的三条临时征收租调的史料,笔者的理解与以往的研究之间有着一些差异。以往的研究对《食货志》中的租“粟二十石”及《太宗纪》的“租户五十石”、《高宗纪》的“租三十石”、“户收租五十石”的高额田租表示难以理解,因此,往往用北魏前期“户”的特征来加以说明。北魏前期的户,往往用“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注:《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和“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注:《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来加以说明,认为租“粟二十石”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定的。这种大户在十六国北魏时期确实是一种突出的存在,并且由于这些大户“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损风毁宪,法所不容”(注:《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因此也成为政府制压的对象。但是,这样的大户不应该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更多的仍然是自耕农民。政府的租调政策不可能只针对大户,而必定是以广泛的乡村自耕农层为基础的。否则,为什么租额增加了五倍(过去通常认为西晋田租为四斛)而户调额却基本上没变呢?这一点是以往的研究无法回答的问题。究其原因,仍然在于对魏晋甚至汉代田租额的错误理解上。
太和九年(485)北魏施行均田制以后,均田制下的征收体系中,“租”和“调”的名称虽没有改变,但是,制度的基本理念及内容与魏晋租调制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均田制在制度规定上和现实中的乖离以及均田制与这一制度下的租调体系之间的不一致性,已被频频指出,笔者也深有同感。由于篇幅关系,对均田制施行后的租调体系的重新探讨,留待以后展开。
标签:魏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三国论文; 汉朝论文; 东汉皇帝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人头税论文; 经济学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