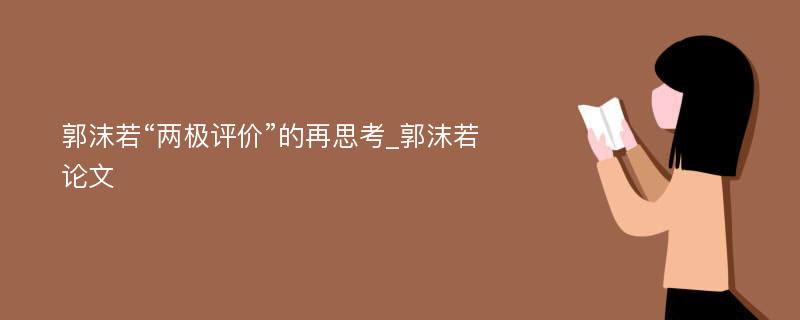
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两极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6-0006-06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非但未能盖棺论定,反而是认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大大超出了郭沫若的生前。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呈现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评价反差之大,在对20世纪中国文人的认识中是极为少见的。温儒敏先生曾著文称之为“两极阅读现象”[1]。这一现象首先是郭沫若研究的重要问题。它反映出对郭沫若作为历史人物跨越时空、跨越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对于研究郭沫若与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对话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外,这又不仅仅是郭沫若评价本身的问题,还是一个当下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对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长时间地存在南辕北辙的相反认识?笔者通过本文想回答的是,在这一巨大的认识反差背后究竟有哪些未知的、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一、怎样的“两极评价”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郭沫若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称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此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第一个郭沫若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的中期。从当时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以看出,大陆中国学术界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科学和文化建设事业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这期间只有极少数论文对郭沫若的某些作品或某一类创作的评价与主流评价不一致,如萧涤非对郭沫若著作《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的质疑[3]、曾立平对郭沫若历史剧反历史主义的批评[4]等。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认识都应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没有改变大陆中国学界对郭沫若的基本评价。
在大陆中国学界出现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现象主要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源于海外的观点陆续进入大陆郭沫若研究者的视野。“两极评价”最初的表现集中体现在两本观点相反的著作上。先是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达凯的《郭沫若总论》[5]一书出版。此书对郭沫若的人品、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等无不予以否定,把郭沫若说成“是东抄西凑,见异思迁,前后矛盾的文学机会主义者”[5](P369)。书中一些歪曲历史事实的论述,尤其是对郭沫若大量的人身攻击,引起大陆学界多数学人的极度反感。于是,有了1992年《百家论郭沫若》[6]一书的问世。此书收录了从1920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以及外国人士对郭沫若的代表性评价,基本上都是选择了肯定性的言论。《百家论郭沫若》一书明显是针对《郭沫若总论》而编选并出版的。
此后助推“两极评价”的是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的论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在大陆中国出现。余英时的文章指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这篇文章很早就在海外发表了,但一直没有引起大陆学界的关注。1994年,此文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推波助澜者有之,激烈反驳者亦有之,莫衷一是者更有之。挑战余英时的有翟清福、耿清珩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7]、方舟子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8]等文章。这些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和细致的辨析说明,余英时所说的“抄袭”“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7]。这一场对郭沫若的批评与反批评,虽然围绕的是具体的“抄袭”问题,但双方观点都直接指向对郭沫若的评价问题,并且双方都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由于事实比较清楚,所以这一场关于郭沫若“抄袭”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但争辩背后的问题远没有结束。到了1999年,又是两本书的出版将郭沫若的“两极评价”推向高潮:一本是丁东编的《反思郭沫若》[9];另一本是曹剑编的《公正评价郭沫若》[10]。《反思郭沫若》的编者丁东在《编后记》中申明:“本书编选的基本上都是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对郭沫若进行学术商榷的文章,赞扬郭沫若成就的文字本书基本上没有收入。实际上,对郭沫若歌功颂德的文章要远远多于反思郭老的文章。我不否认这类文章的价值,但这种文章和书籍已经出得很多了……所以我索性只收一面之词。”[9](P418)而《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完全是针对《反思郭沫若》而出版的。前者集中了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后者则是对郭沫若的充分肯定和对前者的批驳。
从文学史的评价来看,在195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初期约40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据笔者所见)中,郭沫若都是仅次于鲁迅的“二号人物”。1988-1989年,《上海文论》设立的“重写文学史”栏目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学术争鸣,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作家评价问题。有一大批论文贬低甚至否定了既有文学史著作所充分肯定的人物,主要是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些“体制内”作家。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重排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座次”现象。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王一川、张同道主编),封面上赫然打出了“重论大师,再定座次”的旗号,挑战此前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已成定论的“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地位:其诗歌卷的前六位大师是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没有郭沫若。紧接着,钱理群和吴晓东在《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1]第八篇“新世纪的文学”中,也进行了新的作家地位排序:鲁迅、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也没有郭沫若。“重排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座次”之后出版的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地位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要么依然高高在上,要么悄然隐退。在海外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这种差别更为明显,如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与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都对郭沫若做了较大篇幅的历史评判。前者对郭沫若基本是否定的,说“他不过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对《女神》中代表诗作的评价是,“把这种浪漫主义手法和态度拿来混用,自然可以把当时没有读过西洋诗的读者弄得目迷五色。这种诗看似雄浑,其实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内在的感情:节奏的刻板,惊叹句的滥用,都显示缺乏诗才”[12](P70)。后者对郭沫若基本是肯定的,顾彬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在五四中国人自我和激情如何“承担了合法化的功用”以及“现代性作为自我提升、自我指涉、自我褒扬和自我庆典的实质”,继而说“《女神》(1921)的《天狗》也许是现代性作为‘自我显灵’的最好证明”。他还特别强调:“轻视他(郭沫若)是不公正的。”[13](P44)
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仍然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如:主流评价认为郭沫若开了现代中国一代诗风,反对者引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认为他“诗多好的少”;主流评价认为郭沫若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新史学,反对者认为郭沫若开创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历史研究;主流评价肯定郭沫若的与时俱进,反对者则认为“他通过对自己的背叛来适应时代,通过背叛来不断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主流评价认为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创者与成功者,反对者认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席勒式”倾向……
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撇开对郭沫若的评价先不论,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呢?我以为,所谓“科学的认识”应该包含三个要素: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评判。要完全实现这三个理想是很困难的,但相对的科学化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如果说“科学的立场”难以实现,那么,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历史人物应是能够做到的;如果说“科学的态度”难以实现,那么,抱“了解之同情”态度应是不难做到的;在科学立场和科学态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历史人物作出相对科学的评判。
二、“两极评价”原因探析
导致郭沫若“两极评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对郭沫若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受到非科学性因素的干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性和片面性影响了学术评价应有的科学立场
如上所说,要想做到对历史人物的科学认识,首先要采取科学的立场,至少要采取客观的立场。客观立场是什么?就是价值中立,就是全面地看问题,与之相反的就是主观和片面。而学术界对于郭沫若评价的一些不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郭沫若的赞美者和诋毁者各自都带着强烈的主观偏见。其中最极端的是带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如金达凯所著的《郭沫若总论》就是政治偏见干扰客观立场评价的典型代表。怀着政治偏见看待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以,研究任何历史人物,无论前人的褒贬毁誉差别多大,我们首先要选择客观的立场,先不要带着主观的好恶看取研究对象。
科学的立场不仅要求研究者超越主观性,还应该超越片面性。郭沫若是具有多种身份、多重角色、多方面影响和跨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多侧面人物。因此,对郭沫若的认识应力求全面,这是客观公正评价的前提。表面来看,“两极评价”是对郭沫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分歧。仔细考察,其实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为面对身份不断变换、思想不断变换的郭沫若形象多面体,评价者只能看到有限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这就使得对郭沫若的评价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两极评价”的对立,往往是以一种片面性对抗另一种片面性。最不应该出现的就是以偏概全的肯定与否定。例如,余英时依据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所引用材料的相同,就得出了“抄袭”的结论,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尤其不应该如他文中所说,“对他(郭沫若)的一切学术著作都保持怀疑态度”[14]。
对郭沫若历史叙述的“放大”,也影响到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一旦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历史名人,哪一个不是是非缠身?所有的杰出人物几乎都是复杂的存在,褒贬毁誉,古来不绝。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中国的孔子到西方的歌德,莫不如此。其实,所谓“名人”几乎都是被历史着重叙述出来的人,好比用照相机“聚焦”拍摄的人物,在他的优点被放大的同时,他的缺点也被放大了。对郭沫若的认识同样如此。我们在看到郭沫若博大的同时,也看到了他某些东西并不精深;在看到他屡屡创新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的浮躁和片面;在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时候,也看到了他的好走极端;在看到他大胆无畏的同时,也看到了他有时随意树敌;在看到他冲动、热情的同时,也能看到他缺乏坚韧和冷静。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是非、长短、贡献与局限常常是统一体,矛盾的双方都是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的。比如,郭沫若过于张扬自己的所长,以至于不免暴露出自己的所短;而他在忏悔自己的所短时,往往又体现了自己的天真之长。他的许多突出的贡献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局限,而在他明显的缺点里却又渗透着积极的时代意义。他的趋时和善变,与他追求的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相关;他的某些偏激的举动,与中国新文化矫枉过正的运行规律相连。他的某些“创造”不无幼稚的色彩,但在当时的中国,究竟是多了创造,还是多了因袭?他的有些行为近乎天真,但在当时的中国,究竟是多了天真,还是多了虚伪?所以,科学评价不能是简单的是非判断,而应是客观、全面的历史价值考量。
2.漠视历史人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中外史学大家都主张抱“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了解之同情”就是设身处地地了解,就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每一个人都有作为生命的尊严。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对于历史人物,如果你喜欢谁,就尊重谁;不喜欢谁,就不尊重谁,那么,尊重生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研究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必须贯彻尊重生命的原则和设身处地的原则。而在大量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中,明显看出对个体生命独特性与历史复杂性的漠视。
“了解之同情”首先应包括对历史人物个性的理解与同情。研究郭沫若首先要了解“这一个”人的独特性并宽容这种个性。遗憾的是,一些即使不带着政治偏见的评价,对郭沫若的浪漫性格也缺乏理解。例如,许多学人喜欢比较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比较的方式却是“以鲁视郭”,即用适用于鲁迅的观察眼光去审视郭沫若,甚至是以鲁迅之长量郭沫若之短。一些学者比较“五四”时期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时,思考的前提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背景(这是鲁迅研究范式的背景),思考的对象主要是郭沫若相近于鲁迅的东西。这就使得他们研究《女神》的目光总是聚焦于鲁迅式的社会批判、个性解放等思想内涵,却相对忽略了属于郭沫若的高扬青春和激情的生命内涵。
充分认识郭沫若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对郭沫若评价的分歧。郭沫若的血管里原本流淌着冒险家的血液,因而郭沫若具有超出常人的勇气、胆识和开拓精神。别人不敢想的念头,他敢想;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正是这种个性,成就了郭沫若非凡的想象力,推动了他观念上的领先,也帮助他不断开拓新的创造领域。当然,他的这种个性和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却能出奇制胜的成功经验也铸就了他好走极端、做事不够谨慎等缺点,养成了爱走偏锋、好做“翻案”文章的习惯,有时翻案翻过了头或说话说过了头,留下了一些被人攻击的把柄。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还应包括对一个人矛盾性和复杂性的理解。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主体。贤如世界级大文豪歌德,也不能避免“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5](P256)。郭沫若也是这样,有时很伟大,有时也很平庸。他既有许多非凡的成功业绩,但也确有许多凡人之举。比如,他写过一些很好的诗篇,也写过一些很不好的顺口溜。赞美郭沫若的人拿他的杰作说他的诗如何好,贬低他的人以他的顺口溜为例说他的诗如何不好。“两极评价”的双方往往是一边抓住了郭沫若的伟大,另一边抓住了他的渺小。
3.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也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性
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除以上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对立之外,还来自研究者时空错位的对话。任何历史人物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对历史人物的科学评判必须放到个体与特定历史的联系中来知人论世。而一些对于郭沫若的简单化评价,恰恰割裂了郭沫若与特定社会历史的关联。例如,一些对1949年建国后郭沫若的评价,无视他作为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变化。这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郭沫若的后半生确有一些过失,但那是不止一代中国人自觉或未必自觉的抉择。现代中国成就了郭沫若,现代中国也改造了郭沫若。它让文人郭沫若陷进中国政治漩涡,陷得很深,陷得很久,不能自拔。这有郭沫若自身的原因,更有社会历史的缘由。
由于极左时代的黑白颠倒,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以往官方肯定的东西受冷遇甚至被唾弃,以往官方否定或冷落的东西往往受热捧。尤其是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文化名流几乎全部遭受迫害的时候,郭沫若却经常在各种大会上讲话,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美化“文化大革命”的诗词,如《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庆祝“九大”开幕》、《歌颂“九大”路线》、《庆祝“九大”闭幕》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多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郭沫若却频繁地出现在报端和纪录片《新闻简报》上。人们很容易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怀疑,甚至误以为他是“四人帮”的同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对郭沫若的评价无以复加,却难以改变人们对郭沫若的不良印象,甚至会出现评价越高、接受效果反而可能越低的现象。
对郭沫若形象更为不利的是,大约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价值取向开始向远离政治、思想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靠拢。这是中国知识界在官方话语之外建构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新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建构中,自由主义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徐志摩等人越来越热,而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体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体制内”作家越来越冷。因此,变化了的时代及其价值取向,是强化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客观原因。
总之,郭沫若一生的贡献也罢、局限也罢,都不完全属于他自己。透过这一个“人”,我们可以观测到现代中国复杂、深刻的人生。
三、历史价值评价与当下价值发掘
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存在,并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研究应当摈弃相对主义。因为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目的主要是对其所蕴含价值的发掘。历史人物的研究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价值;二是当下的价值。
所谓历史上的价值包括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郭沫若“两极评价”,无非是肯定者强调其正面价值,否定者强调其负面价值。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没有标准吗?我们今天能解决的问题,难道一定要留给后人吗?其实,对历史人物历史价值的评价,不仅是有标准的,而且从来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永恒标准之一就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是必须肯定的,因为“原创性贡献”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郭沫若对现代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在以下五个方面应是绝大多数郭沫若研究者的共识:一是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作为现代中国开一代诗风;二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历史学论著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新史学;三是以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卓越成就使中国的古文字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四是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古器物学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新体系;五是现代中国历史剧文学的开创。
如果一个历史人物只具有历史上的价值,那他就真地“作古”了。历史人物是否具有生命力,主要看他是否能提供对今天的人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当年五四时代的中国人知道郭沫若的时候,他就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可是,当今中国的人们都被物欲主义包围着、异化着。精神的家园、高蹈的浪漫、彼岸的理想都变得那么空洞而遥远。实利化、物质化的生命压迫,让我们越发怀念青年郭沫若那无边的想象、那浪漫的理想、那天真的诗心、那酣畅淋漓的生命状态。只要生活中还有物欲横流的现象,郭沫若式的理想主义就有存在的意义。
不过本人认为,郭沫若对于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价值是他作为“球形天才”榜样的力量和这种榜样给我们的启示。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都不缺少精通一门的专家,唯独缺乏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一般人都认为,郭沫若一生有两个高峰:一个是五四时期,以《女神》为代表的新诗创作开一代诗风;二是1940年代,他的史剧和史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笔者认为,郭沫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是在这两个高峰之间,具体说是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这是郭沫若真正的创造高峰。一般人之所以不以为然,是因为对郭沫若的研究被分割在不同领域,搞文学的只看到文学,搞历史的只看到历史,搞考古的只看到考古,搞古文字的只看到古文字,搞翻译的只看到翻译。综合起来看,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成就最高。仅1928年至1932年四年间,郭沫若共撰写和翻译了20多本书(不包括未出版的)。这些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译著(如《战争与和平》等经典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生物学、美术考古史的翻译,历史学著作,古文字研究著作等。郭沫若写的这些书不光绝对数量多,涉及的领域多,而且质量也很高。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史学界称为划时代的著作,《生命的科学》被今人称为“不该遗忘的科学巨译”,《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被赞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最伟大之巨著”。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从接触甲骨文到发表成果用了9年,王国维用了6年,而郭沫若只用了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成果给我们找回来一个失去了3000年的商王朝、一个立体的遥远的古代中国社会。
然而,郭沫若为什么能够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古器物学、政治、艺术、翻译、外交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创造力和创造的潜力?在他变成“球形天才”的过程中具有哪些我们可以汲取的经验和可供后人效仿的东西?这其中具有多少现代科学尚不能回答的人类创造的秘密?这一切不仅对于当今中国乃至对于世界,都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东西。因此,研究“球形天才”的郭沫若,具有不可多得的时代价值。
综上,通过对郭沫若“两极评价”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出现见仁见智的对立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科学研究,长时间地存在“两极评价”是不正常的。因为科学研究是有标准、有规范的,科学的历史人物评价应当是建立在成熟的科学研究成果之上的共识性结论。长时间地存在“两极评价”,只能说明直至今日的郭沫若研究依然停留在科学含量较低的学术层次。因此,郭沫若研究(也包括其他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亟需建构包括价值中立、“了解之同情”、历史原创性评判等价值观念在内的一整套历史人物评价的科学话语和学术规范。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尊重。
谨以此文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
标签:郭沫若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历史人物评价论文; 女神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余英时论文; 十批判书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