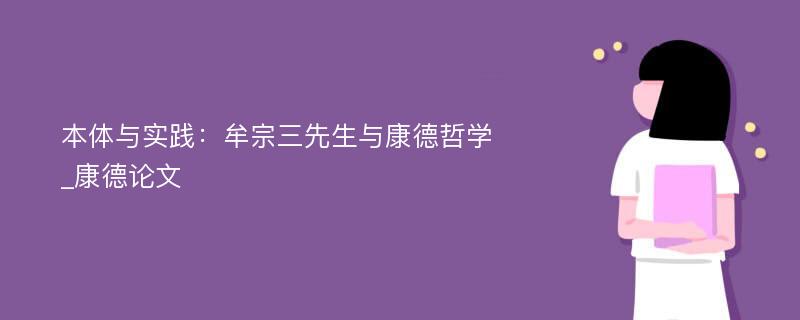
本体与实践:牟宗三先生与康德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本体论文,生与论文,哲学论文,宗三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野与关联:本体论与道德形上学
一般言之,“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根本概念。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深刻而丰富的。它不是单单的“本质”或静的结构,它也不是单单的“过程”或动的变化,它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实质的个物,不是人格神的上帝,也不是非人格神的物质。甚至它也不是海德格的基本形上学的主客不分的“个别存有”(Dasein)或隐显自如的“一般存有”(Sein)。事实上,一个形上学的对形上实存的理解本来就不可能范围在一方面或一个概念的语言之中。“本体”唯有中国哲学的“道”与“太极”的意含可以表达。“本体”这一概念可说就是融合了“道”和“太极”的概念而形成的。《易·文言》中就有“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系辞下》有“复,德之本也”的原始反终的“本”的概念,而《易·乾文言》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坤·文言》也有“君子黄中通理、政位居体”,《易·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系辞下》有“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等可为人所体察的实体之“体”的概念。“本”与“体”连用虽晚至魏晋玄学阮籍(其《乐论》曰:“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经王弼《老子注》中以本为体、以末为用对道的解说,而固定于宋明理学的朱熹,此一辞所含的原初意思却是从《易传》中就决定了的。“本体”即有“本”与因本而生之“体”,体含体性、体质、形体、气体等义,故不离具体的自然宇宙,也因而为宇宙万物之根源。又因此一“本体”概念的所缘与所指可以为人体知,故具有超越(包含)而又内在(被包含)的涵义。我们如再因其生化为万物的体系而给与整体与体系的涵义,则“本体”的涵义更形周全与明确了。我们用此一辞不可不察它的所指与所蕴涵,就不必把“本体”一辞等同西方传统哲学的形上实体或超越根源,而应就其具有万物创造的根源与能为人之心智所体察的涵义进行理解。
由此观之,传统中西形上学中的“根本存在”与“真实”的概念就是根本不同的。事实上,中国形上学就是“本体论”或“道论”或“太极论”。西方形上学自柏拉图以来意指有关超越的理型的或抽象的原型存在或第一原理的理解。更因亚理斯多德以“不动的动者”(unmoved mover)为第一因的概念把形上的根源存在看成纯静态的动因,是与儒道之道的生生不已、太极的静极而动、动极而静的看法迥然不同的。因而西方的形上学侧重存有论(ontology)的研究,同时又把宇宙发生论看为上帝创物的理论或气质宇宙因果演化的理论,与存有论划分为二。但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真实与现象、本源与宇宙,都是不可以截然划分为两物的,故本体论是基本体察本体之道所以发生为宇宙万物之论,而宇宙万物之论也必须追溯本体论的范畴。此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朱子在《近思录》一书中首列“道体”为第一章的意思也在此。由于此,西方的“存有论”与中国的“本体论”可说是对立的。牟宗三先生以“只存有而不活动”来说明存有论,而用“即存有即活动”来说明中国形上学的特质是有真知灼见的。此一真知灼见的精神即在表明西方哲学中的真实与现象之间基本有隔,而中国哲学中的本体与宇宙之间却基本无隔。
本体的道包含一切,自然也包含了人之存在,而人的存在的本体就是道的本体。为了理解此点,我们必须面对中国本体之道的发展历史,并用以说明中国哲学中人性论有关人性的根源。所谓人之性,一则是天命之谓性,另则是生生之谓性。性故应为“天之所生”与“天之所命”合而为一的。但天又统率于整体的动态的道之中。如此方能了解道体即性体、性体即心体、心体即意体、意体即诚体的内在的创造发展。[1]内在的道即是德,老子所谓“道生之,德蓄之”,从道的形上学言,表明道德之不可分,德即道的分享于万物,构成物的性,是为德。人之性得之于道,而为性之最灵明者,性又朗显为活动之心。性与心具有道的创造性固不待言,故牟宗三先生所谓的“道德形上学”应为“道的形上学”或“道与性的形上学”,而非他所用英文所称的"moral metaphyics "一辞所可真正涵盖与表达。此一英文译文显然把一个较为宽广的概念狭窄化了,即是把道与德限定在狭义的人文与人伦道德实践上面。我不认为这应是牟先生真正的意思,但牟先生是因批判康德的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而导向此一用法的,此又不可不知。以下再就人际道德与本体道德的区分进行探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第1部,第3节)
道与德的实践本体学:本体的认知问题
牟宗三先生从批判康德“道德底形上学”发展到“道德的形上学”,这是他专注道德实践的理由。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旨在说明人的纯粹理性的实用能够成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基础。纯粹理性的实用在于把理性与善的意志合而为一,一方面经理性形成普遍而必然的律法,另方面意志只命令此律法的实践与执行以实现善的目的。康德先予设了道德行为的绝对性,提出了绝对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回答此,故也必须推设理性的立法是无条件的,而意志的命令也是无条件的。但意志能够无条件的执行无条件的理性律法,则是因为它是自由且是以善为目的的。于是,又有自由的保障与根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的整个努力在建立道德行为的先验综合前提,即是理性的自我立法,意志的无上命令以及两者的合一与自由活动。事实上,理性与意志必须合一,意志必须是自由的,而其行为或实践必须是以善为目的的。在理性意志(此处就其合一的形态言)的实际运作与应用中,显然我们还要考虑或要求理性对具体行为目的的认知以及对相关背景与环境的认知,这就涉及到理性的理论与事实判断能力的要求了。由于此一要求,自由意志在自我理性立法的实践中却有可能不一定能够恰如其分的实践具体的善。这自然是康德哲学中后一段的问题。但目前我们所关注的是前一段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道德行为所假设的先验前提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必须表现为一个真实的定然命题,这就是道德命令的本体基础及其认知问题。
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在发掘知识与道德行为的主体性如何实践其所知的先验条件。此一方法本身就有两个限制:一是先验条件只是逻辑的有效性说明,并不能代表一个独立客观真实的存在。此点康德也甚为理解,故在知识上否定对自在之物或物之本身(物自身,ding-an-sich/thing-in-itself)有任何认知的可能;在道德行为上也只能假设上帝的存在、意志的自由与灵魂之不朽以确保道德行为及其实践的价值,故先验条件的说明的作用在理性化道德,而非在存有化道德。据上所言,道德也不可能存有化;二是先验条件的说明与阐述分析对具体知识与行为的形成只有回顾的规范性,而无前瞻的发现性,故只是一种合理化逻辑(logic of justification)的建立,而非一种发现性逻辑(logic of discovery)的探索,也就是对未来的知识形态与道德行为方式不能作出具体的硬性的决定。牟先生不满意康德的是前一点,对第二点则似未能加以发挥。
我们能确知道德的本体之原为何吗?对于这个问题牟宗三先生就陆王心学的“本心”、“良知”来说明道德的本体为何。此是极好的见解,不但合乎孟子陆王一系知行合一的思想,而且也合乎道德是以心的意志为起点,以行动为终点的一以贯之要求。由此来印证道德的本体的存在似为最佳途径。本来人之有性、性之有心、心之能知、知而能行、自然显现了道德之行的存在根源。如就此道德之行的自律自主的特性言,此正是“独立不拔”的主体性,表述了所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的典型。故牟先生名之为良知本体的“具体的呈现”。良知本体如非自我规定,如非自我表现,它又是什么呢?可以说本心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实现,也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中本心才能呈现。因之对本心自然呈现的直接经验就是本体的经验。问题是对这一经验又是如何来把握和描述呢?牟区分为形而下的感受亦即气的感受,与超越的道德感情表现为孟子四端之心的“理义之悦我心”。也许牟要说的是心既为气也为理,故应同时表现为心之气感与心之理感。因而道德的心性本体既是心的昭明灵觉也是心的主宰自觉。若更进一步的反思,则更能发挥为心之创造体验,达到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本心具有创造性体验是循着本心即性即理而理即道即行的路数发挥的。在心之明觉、心之主宰、心之创造性体验的基础上,可以继续发挥心性的创造性,也可以建立心性的创造性之知。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知事实上是一种信念,一种不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一种行为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虽然知可以是行为的基础,但却不一定非是行为的基础不可。只有信必然联系于行为,因为信就是潜在的行为。事实上,这又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反思推理,是在对行或实践的丰富涵义的体验基础上的细密深思而来的。
实践本体学的哲学背景
有关本体的实践涵义,我们可以从三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中看出端倪:第一项是从易的本体宇宙观的发展来看。第二项是从孟子人性论的建立的发展来看。第三项则可从禅宗的悟觉本心本性来看。
第一项:易的宇宙观是由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长期观察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的现象而发展出来的。伏曦观天察地、远取物、近取身的观察活动就是具体的表明了易的宇宙观的起点与终点:以观察宇宙万物为始,以人的行为作用于宇宙为终。观察的内容是变易不居的天地万物。如何从变易的直接体验中掌握宇宙的整体性、差异对立中的统一互补性、发展循环性、层级创生性、人的创造参与性等等的理解,都是基于人对宇宙的变化与人与宇宙有机性的交相互动性的关系的观察而来。这种观察显然导向了天地变化观、人天互动观、人我互动观、自我内外互动观、知行互动观。所谓“互动”也是一种变化关系,可称为交易的变化关系。万物人天之间既是交易互动,自然形成有机的一体,这一体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影响作用,最后在人的心中呈现了整体宇宙与其内含的阴阳互动的创生的原理,并呈现了宇宙本乎一源的辩证展开,可名之为宇宙发生论,人物发生论,因而引申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能参与宇宙的人生创造观。前两者可定名为本体宇宙论,后者则可定名为本体人生论。基于此一发展,发明出来的占扑决策与预测以及对人生的忧患意识,事实上,都可看成是本体宇宙论中的天人互动论的一项延伸。本与体的涵义则已如上述。
在这一分析说明中,观察与实践显然是导向与建立本体、本原概念与意识的根据与原由。固无论《易传》出现多晚,这一意识的含容深化的发展脉胳却历历可呈。但无容讳言的是:此一宇宙观是否即是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与掌握却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西方近代哲学所说的“物自身”与对物自身的认识只是西方发展出来的概念而已,并不适用于中国哲学所开辟出来的本体宇宙观。甚至也不适用于西方古代的本体形上学与上帝神学。但它却与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有关。此一对象性的物自身的概念模型基于不断的应用乃成为现代西方知识论的根本问题。这是由笛卡儿开其端,康德致其极的。但这也是知识论走到最近代必须面临价值实践论的大力批判的命运。
中国古代周易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思)观(view),最后演化为宋明理学中的(知或理)解(understanding),并不是对什么物自身的认知(knowledge)中国哲学在一个意义上是超越了笛卡儿与康德哲学,但根本上却是不同于笛卡儿、康德哲学一路。说它是超越了笛、康,是我们对笛卡儿、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本体意识与物自身的概念重新理解与诠释的结果。
第二项:孔子在对周礼、周文的深度反思中获得对人性所蕴涵的仁心的理解与信念。这是一种悟觉,一种发现,当然也可看成是一种心体、性体的呈现,但说为从对人之仁心的信念与理解则似更为踏实。这是由于仁心还要表现为仁行方可称为仁,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如人无仁心的直觉能力,仁之来何能如此无隔、如此神速!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孔子是把仁与自由意志结合在一起的。孔子并没有限定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意欲仁,孔子的意思反而是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可以求仁得仁,只要我意愿,仁就在目前,因而仁的实现也就是自由意志的实现。在《论语》113个仁字的应用中,绝大多数的仁字指的是仁之行、仁之德,事实上所有仁字都可以解说为仁行或仁德,但有二三处显然解说为仁心较为合理,如上述的我欲仁、仁者静、仁者寿、依于仁等处。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孔子是把仁定义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基础上。“克己”是内在的心的修持,但“复礼”却必须是行为上的要求与实践。作为德行,仁自然是一种自我的体验。“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正表现了仁性可以界定一个自我,可以作为人所欲实现自我的理想目标。(《孟子·离娄下》)这种由身体力行界定的自我本身就是善的典型,也是行的主体与本体。迨至孟子,基于自反的体验对仁心作了深刻的考察与理解,并从直感上抉发了仁心的端始,以恻隐为仁之端。他更进一步考察与体会其它德行与价值的情感之源与感发之端,不但为各种德行找到感情的基础,更综合的统一了这些德行的感情之源,建立了人性为善的理论。很明显的,性的概念既可分析为反思创见的结果,又可看做由情而心、由心而性的自然感悟,甚至也可以说为一种人性直觉。
总之,人性理论与人性为善的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德行的整体的体验而来。在这个体验下,孟子也提出了对天的感受,他谓之“知天”。显然此处的天不是形质之天,而是义理之天,也就是义理的具体化身。所知之天的一个内涵是天之所命之为性,表现为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如果天是一超越的实体,显然“知天”就是同时体验超越的内在与内在的超越,体验到人的生命的内外统一。孟子所说的“尽心而后知性”、“知性而后知天”都可以从这一个体验的角度理解,而不必说为康德的认知物之自身。“知”此处作体验感受讲,而非孤立的对象之知。中国哲学中用“知”字均有此一意思,如《易传》所说“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就是把乾之“易知”形容为“有亲”“可久”的“贤人之德”。这说明此知是是从乾德之变化之有亲可久中体会到的,[2]因而知也就是自然之信与行的基础,故言“体仁”。
第三项:老子《道德经》指出恒长的“道”是不可道的,佛经中的“真如”也是不可言说的。“道”和“真如”都是本体概念或可视为本体的代名词。但它们是不是等同于“自在之物”或“物自身”却值得怀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道和真如是被认为可以体验于人心智慧之修持中而为修持的最高境界。从这个意义说,道与真如绝对不是物自身,因为物自身是不可以用修持来达到的。从修持中知道或达到真如就是所谓悟或悟觉。但如何来说明或描述悟或悟觉呢?撇开渐悟与顿悟之辩,我们对悟是如何理解呢?显然,“悟”是体现本心、本性的活动,也可以说是本心、自性的呈现,但它同时也是本体、真实的呈现。在本体的悟之中主客之间已无隔阂或可说主客之分已不存在,因为任何分别或分割主客的概念与情素都已剥落,只留存原始的主客共享的存在根据,但从一个严格的大乘佛学观点,即是两者的存在根据也要剥落完尽才算得上了悟本体,因此佛学的悟是一个一切俱空而空亦空空的境界。当然它也是要用直接的体验去理解的不可说境界,甚至于是“非想非非想”的境界。这种体验的理解事实上是对已得或已发体验的观照与反思,而不是体验的本身。体验如同呈现是一种发生,但不同于体验的是呈现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也就是呈现的真实结合了主体的经验的丰富感受。对这一体验的观照可以引发现象性的或形象性的描述,而对其反思则可以引发抽象的论说。无论描述或论说,都可说是对此一体验的理解,也都是可以用语言的方式表达的。因之,对体验真实的理解就是对这个体验的语言表象化;不可说的或非想非非想的体验,作为一个穷致本体真实的终极结果,就可以在理解中认定或解说为本体,甚至也被赋予了一个论说中概念的结构。但这个语言中的解说及概念,虽有意象性的所指,却无实际的可指的对象,因为体验或呈现,或体验的呈现或呈现的体验,是没有对象的,因为没有依对象而立的主体。即使在思虑中对象化了,也不能对本体有所指,因为在对象化中已无体验的反思或观照相应。但透过个别个人的体验与经验背景,一个语言化的本体体验也可能发挥启示或启发提示,甚至引发本体呈现与体验本体的作用。
道之为道是体验的结果,但我们对道的理解则是语言表象化的结果,语言表象化却非对象化的结果,而是象征性的(明喻性的或隐喻性的)语言表述。如谓道如水、如朴、如谷等等。同样的,在中国佛学中的真如本体也往往要透过形象语言或抽象语言来表达的。抽象的说,真如本体是空、是寂灭、是无相法身、是如来藏、是菩提法性、是般若智慧、是无念无相无住等等。但形象的说,真如本体可以经由比喻和暗示的方式来作更多的语言表述,如《楞伽经》中有谓真如本体为“明镜水净眼,摩尼妙宝珠,于中现众色,而实无所有”(《楞伽经》卷二),《坛经》比喻菩提为树为无树为明镜为非明镜,又如谓诸法在自性中,“天常清,日月常明…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坛经》忏悔品第六)永嘉玄觉《证道歌》中的“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中国禅宗大全》第71—73页)更是生动的描绘出理学中“理一分殊”的原理。自唐代禅学宗风形成,有更多的褐句与禅诗运用隐喻或明喻来表达本体意识或本体真如的体验。甚至禅宗公案的问答题材与内涵也是一种反映本体真如与导向本体之悟的语言使用方式。[3]
道德理性三义及其批判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牟宗三先生在他的巨作《心体与性体》第一册中运用“云门三句”来陈述他的对康德的批评与表明他的道德性体、心体的理悟与发用。首先他肯定道德主体即性体心体的主宰性,并用“截断众流”句来刻画性体心体的挺拔自主自律与通体是“仁心德慧”。这是牟说的道德理性的第一义;其次他肯定纯正的道德行为直透“至其形而上的宇宙论的意义”,可说彰显了天地之性、生化之理,甚至说它为“宇宙万物底实体本体”。他用“涵盖乾坤”句来形容之。这是道德理性的第二义;最后,牟先生指出道德法则必须通过实践工夫做具体真实的体现。他用“随波逐浪”句来表示此一“践体”的道德理性的第三义。他做结论说:“这是儒家言道德理性充其极而为最完整的一个园融的整体,是康德所不能及的。”(以上所述,见牟著《心体与性体》第1册综论,第三章,115-190页。引言见138页)基于上节所作的背景分析,我想对牟先生有关道德理性三义的见解,提出几点我的看法。
第一点: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是从孔子树立起基础的。但如无更早期的周礼文化与周易的宇宙哲学与思维方式,儒学也不可能提出与获得持续而充其极的发展。这个过程反而接近“云门三句”原来表达的秩序,也就是先要“涵盖乾坤”才能“截断众流”,然后才能“遂波逐浪”。这是一个发生学的观点,但牟先生强调的是道德心性自我的突出挺拔以相应康德的道德自主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个突出是要到孟子才真正完成的。即是孟子与《中庸》的心性的宇宙论或形上学的意涵可以说是先行已予设与呈现的,并非先有道德意识才有宇宙意识。《中庸》所称“天命之谓性”说明了性体心体的自觉是与其形上根源的自觉同时进行的。道德意识只是宇宙意识的一个突出的面而已,而非宇宙意识是道德意识的延伸。甚至也不能说道德意识潜含了宇宙意识。
“道德的形上学”如被理解为道德意识就是宇宙意识、宇宙意识就是道德意识,似乎太局限了形上学的宇宙论。如果能理解为道德意识开显了宇宙意识、宇宙意识转化成道德意识的辩证的探讨则更能表达中国道德伦理学与本体宇宙论的实际关联。因而“云门三句”的相应理解可以有另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先谈宇宙意识再谈道德意识及其发用;另一种方式是先就实际的道德伦理经验来抉发道德主体,进而开展道德的宇宙根源与宇宙境界。显然,牟先生的方式是康德模式的;后两种方式则是非康德模型的。最后的一种是经验论的,但也不全同于休谟与弥勒。较后的一种反是符合中国道德意识开展的历史实际,也符合易、孔、学、庸、孟、荀次第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这一个方式的理解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宇宙的道德哲学”概念及其理解与研究,这是在上面讨论“道德的形上学”时涉及到的。如果肯定“云门三句”之间的循环理解,我们自然也可以就本体宇宙论与道德行为哲学两者的贯串、相应、互基、整合与园融此两项提法与观点,甚至也可以把最后一种提法与观点融入,这一可能正是恢复了“道德”与“德道”两辞应有的意涵。
第二点:牟先生在论证儒家哲学道德主体的三义时,他指出的道德主体意识所呈现的意义与境界事实上并非实体的对象;无论性体与心体,无论天道与性命,都是在一个生活世界与文化网络中呈现的概念,因而具有丰富的经验与体验内涵,但它们是不是具有客观认知的意义,亦即是否具有对象化或对象性的知识内涵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必把意义等同于知识,意境或境界等同与于对象。但我们也不必认为一个呈现的意境必然带来对象知识或决定对象知识。因之,牟先生说的“性体与心体,宇宙万物实体本体”并不就是一个客观的独立自在的对象之物。相反的,它乃是经过人的体验反思与观照的存在与境界的理解。故可以为人的自身实践的发展来体现的。如把它看成是本来就与人的体验与人的存在完全无关的,然后人以其知的能力直觉或感觉此一外缘超越之物,则它又如何来为人所开发所修持甚至所利用呢?我们又如何确立它对人的意义呢?如果知的过程在排除我们对真实的体验和价值的需求来建构我们的感觉经验为可控制可解释对象,这个对象又如何成为本体呢?如果我们把本体完全对象化或完全超越化我们又如何认同他的本体性呢?[4]总言之,牟先生的阐明儒家的道德本体或心性主体是在界定另一个语境、另一套生活体验、另一种生活世界与另一种组合经验的方式与思维方式。他的矛盾乃是:如果他用康德的思维典范,他是不能把本体对象化而又言智的直觉的。因为这样的对象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对象都需要建构出来,不是经由感觉经验的范畴化,就是经由价值理想及其体验的语言化;不是形成一个理论理性的个别对象,就是形成一个价值理性的整体境界。两者是不可以外在的转化的,不然就是一种知识的约化或价值的约化。但透过人的内在的知与性的融合,在一个整体意识中取得一定的调和和相互补充,达到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的体验,并永远的开放的调节知的挑战及意的坚持,才能逐渐使个人的生活境界趋向圆熟与圆融。
第三点:从康德哲学的观点,牟宗三先生对实践理性未能呈现本体之真的批判,会有如何的回应呢?他能不能接受或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证得道德的性体与心体,而放弃以设订或假设态度对待自由意志、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回答是:康德是无法接受牟先生“呈现”之说的,因为他并无此一“呈现”的体验。再说,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因而也无法掌握中国哲学所基础与展现的生活世界,从而深入的感受中国哲学的旁通感应的义理。更重要的是,康德有他的哲学义理与批判方法,而他的哲学义理与批判方法是深刻的根植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理性与理代科学的知识重建精神之中。他继承了笛卡儿理性重建知识的精神,又面对牛顿的系统的物理学的有效建立,更受到休谟怀疑论的刺激,因而从事如何系统建构与界定任何知识理性化的条件以及其基础。他建立了“超绝自我”(transcendental ego),以理性为形式、以感性为内涵的知识结构。但“超绝自我”能够建构其自身吗?在能、所/主、客的对待与对立的关系中,能与主永远不能化约为所与客,但如果不能化约为所与客,“超绝自我”也不可能成为对象化的存在。反言之,如果“超绝自我”成为了对象化的存在,“超绝自我”也非“超绝自我”了。主、客与能、所的关系显然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排除逻辑,而非此彼兼取的包含逻辑。后者的可能在建立一个厘定与界说主、客,能、所的整体系统,亦即一个超越主客而又有效界定主客的关系。但康德并没有发展此一整体系统,因为他并没有此一超越而有内在的体系。相反的,超越的不可能内在而内在的也不可能超越。不但如此,超越与内在甚至既不能同时主体化也不能同时客体化,而必须以纯然的客观与纯然的主观的对立方式出现。这种对立是抽象概念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内在的主体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形成对外在的客体的认知,但又不能取消他的概念的存在,因为主体自身概念的存在是在此对立中自反的界定的。于是,纯然概念存在的超越对象就成为所谓的“物自身”(ding-an-sich)。
“物自身”就其界定而言就是不可知的。而所谓知就知的界定而言也是不及于“物自身”的。故从康德的思考逻辑来看,牟先生按照宋明理学界定的心性本体并非“物自身”,而是宋明哲学的内在体验所构造出来的非对象化的实体。这种构造如前所述,是取消了主客的对立以及主观的超越了主客的活动所形成的,也是取消了知的意义所形成的,因而也内在的取消了“物自身”概念性的存在。如仍用“物自身”一辞,则此“物自身”已非彼“物自身”,而对此“物自身”的知亦非严格的知,而是知的拟似而已,它是针对主体的超脱主客对立思考方式的体验的概念塑造,并非知的对象,只是思的对象,只是为某种需求设定的对象。从这个关于“物自身”概念的逻辑的分析来看,“物自身”本来就是不可知的,知本来就排除“物自身”的。因而也就无所谓“智的直觉”了。如果“智的直觉”所指的是纯理性对“物自身”的认知,以上的分析已说明为不可能。既无知的建构,又皇论脱离感觉经验的限制用纯理来构造纯然的客体超越物呢?又焉知此一纯理的构造不内涵(一如康德的四个“对立名言”即antinomies所示)概念的矛盾呢?
如就实践理性而言,为了行的善的目的,为了保证必然普遍的理性法则,为了说明道德责任,假设意志自由甚至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朽都是逻辑上必要的,但这并不能逻辑的推出它们的本体性的存在,因此也不能就实践理性、认知意志自由等的本体性,而只能说明它们的假设的必要性。当然康德不能否定心性本体作为体验的存在,但他必然坚持体验并非认知,而心性作为本体概念,我们则无权也无法推引出它们形上的实存,正如我们无权也无法自上帝的概念推引出上帝的实存一样。上帝本体论证的错误说明概念(不管来自理的建构或来自体验)与存在(实存)间的鸿沟是不能跨越的。此一论证,从康德的立场,是一样可以用在心性本体的概念上。[5]
结论:两套典范的融合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康德与牟宗三可说是完全独立的系统。两者并非没有交叉点,但两者对所谓本体、所谓物自身、所谓智、所谓智的直觉、都有不同的定义与解说,因而得到不同的结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是外在的,其要点在以体验对应认知,以呈现对抗设定,以说明对本体的把握的可能性与其在中国哲学中的实际典范。但毋容否定的是,康德仍可用其知识的批判来论证本体之知或直觉的不可能以及任何对本体或物自身的建构的理性的限制性,从而构成对中国本体体验哲学的外在的批评。此一相互批判的研讨对我来说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意义,也提示了一个重大的思考课题。代表的重大意义是:康德的逻辑理性与科学理性与牟宗三的道德理性与本体理性(这是我的名词)可以是对立的,甚至是不相容的(incommensurable),这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性与中国古典性的不相容。提示的重大意义是:康德与牟宗三的不相容正是西方现代性与中国古典性的不相容,但我们应如何创造的转化两者为相容并进一步向融,以达到中西融合的世界性的目标,这无疑是一项兼具高度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工作。两者的向容与相融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正如两者的对立与矛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一样。当然,两者的向容与相融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正如两者的对立与矛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一样。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能否建立一个包含两者的理论也正是人类智慧综合的考验。
从康德哲学的眼光来看,未尝不可以“体验”与“呈现”之论为人的行为的根本基础之一,因之在行为实践所需要的信的基础上肯定体验与呈现之说。从牟宗三的立场,也未尝不可在知的理性基础上肯定科学理性对形上学甚至对“道德的形上学”的批判性,并面对不同的形上信仰可以产生同样的或不同样的实践与行为效果与后果的事实予以肯认,亦即认识到不必非在心性本体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导致必然与普遍的纯正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只是人的创造活动知一端,故不必有待于心性本体之唯一之发用,而对心性哲学的理解也不必仅限于纯正道德行为的实践上。基于体验与呈现以及对其所作理性的反思与信念,我们可以深入的探索心性本体的广泛的创造性。在这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架构中,我们结合理论与实际来融合康德与牟宗三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在这个对立的批判中,我看到一个兼容并包相互转化的逻辑的可能性,也由于此,我认为从一个整体但却是开放的本体论的建构中,我们可以视康、牟为一体之两用、一元之两端、一极之两仪、一心之二门、一事之两行,就其知识建构、道德实践与价值创造的需要定其体用、决其两端、建其双仪、开其门路、明其行止,从而还其本体太极创化阴阳二端的本色,而不必强纳一端为另一端、或强饰一端为另一端。[6]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当代开放的新儒学可以也应该发展的方向。
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建立体验与呈现的本体形上学的过程中,无论就体验说或就呈现说,主客的对立均会消失,因而主体的说体验了本体,客观的说本体呈现了。但如何获得本体的体验与本体呈现,从儒家看乃是一个心性修持的问题,先秦儒家与宋明理学对此极为关注。牟先生在其《现象与物自身》中却选择用大乘佛学的执与无执的概念来说明“无执存在论”所彰显的本体性。但我认为无论是尊德性或道问学,无论是穷理或尽心,无论是执与无执,其终极目标均在见体与现体。有关此点,我在这里有两点意思要表明:一是尊德性或道问学、穷理或尽心、解蔽或去执,均在成就德行、体现人性(也就是成圣成贤成佛)。因之,对朱熹的哲学的理解也不应排除此一方面的考虑。朱熹的理气哲学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学也可说在一个实践的人生(《论语》与《大学》中所示者)中获得充分意义。只是他的实践的模式与陆、王的实践模式有很大的差异而已,但两派在实践的终极意义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异。[7]二是本体的体验与呈现需要对性理与心理两方面的掌握与修持,因而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本体的理解与本体对实践的启发与影响的理解的误差。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必须在两个极端的全面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性的本体概念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体验与呈现,也包含了认知与设定以及两方面的平衡与互动关系。然而这是离不开考虑两方面的实践目标与实践意义的,也就是离不开知识与行为或知识与价值的机体互动、互创的关系。只有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本体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合理化的基础,而实践的要求也能改变或重建本体的概念与系统。总言之,我们必须在知行的统一中解决主与客的对立问题,也必须在主、客的对立中探索知行统一的实践意义。[8]在这一个知行合一与主客对立而又超脱的整体建构中,心灵对本体呈现的体验是以超脱主客而又包容主客为基础的,就其能超脱说,是一个“智的直觉”;但就其能包含主客而言,却当称为“仁的直觉”或“仁的直感”。这是由于我们可以以“万物皆备于我”、“天地与我合一、万物与我并存”、“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作为我们体悟或体验本体的进路、标示以及其实际情状的描写。在此一意义下的“智的直觉”中,主客可以俱非,而在此一意义下的“仁的直觉”中,主客可以俱是。在此仁智双重的意义下,仁与智可以在本体的体验中合一,正如天与人在此本体的体验中可以合一一样。但这种仁智合一、天人合一的本体的体验绝不是康德哲学中或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的“智的直觉”或纯粹理性的认知。[9]
注释:
[1]在我的思路中,心体兼涵意体与思体,意体体现于诚体而思体体现于知体,各言其体只是加重自成体系可以体察之义。
[2]这就是墨经说的“亲知”,而墨经说的“说知”往往也是以“亲知”为基础的,而非为现代科学的抽象假设。
[3]禅宗语类或语录中尽多用明喻或隐喻的语言来描述或表达对本体的了悟或体悟,如问如何是涵盖乾坤句,答为:天上有星皆拱北;祥云弥宇宙等等。问如何是截断众流句,答曰:横身三界外;不通凡圣;猛虎踞当途等等。问如何是随波逐浪句,答曰:春生夏长;有问有答;春煦阳和花织地,满林初啭野莺声等等。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临济四料拣所表达的四种境界: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答曰: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答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问如何是人境俱夺,答曰:并汾绝信,独处一方。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答曰:王登宝位,野老沤歌。请见《校补增集人天眼目》巴壶天、林义正校补,台北名文书局,1982年出版,238-240页;26-27页。
[4]犹太教的耶和华原来只是祖先神,但耶稣的作用一方面是把耶和华上帝化或超越化;另方面成为上帝与人的拯救媒体,也就是把上帝内在化或人间化了。自中世纪后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是愈来愈人间化与内在化,用此来克服超越化,但又有反动的思潮如巴斯(Barth)企图用超越化来克服内在化与人间化。基督教的发展因之也就在超越化与内在化之间徘徊。
[5]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自黑格尔以来一直是一个错综复杂扰人思虑的哲学问题。思维活动是因存在的创造性而起,但不能离开存在创造新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不因上帝的概念而起,但上帝概念却可因不同的存在原因而生。
[6]如此我们也就无须如牟先生所说“良知的坎陷”以成就科学知识与民主政治。对于这一点我已有论述。此处我只是强调肯定两行及结合两行的重要。请参考本文(下文)中所举拙文。
[7]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不但我们可以从实践的要求中体验本体,也可以透过实践创造价值与文化。后面这一点正是唐君毅先生的慧见。至于徐佛观先生说的“天的人文化”固是事实,但人之下学上达却是自然的发展。故帝化解为天、天又化解为道、道又呈现为理,但并不因此必然消解了形上学甚至神学。
[8]我们要理解固然王阳明阐发了“即知即行”的知行统一哲学,但这只是知行统一的一个模式。在现代科学中,所强调的刚好相反:“非即知非即行”,但这并不表示知行不可统一起来。
[9]有关我所说的“仁的直觉”,请参考拙文:《现代新儒学建立的基础:“仁学”与“人学”合一之道》,在《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内圣篇》一书中,1992年,台北鹅湖出版社出版。113-145页。
标签:康德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文化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道德论文; 哲学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