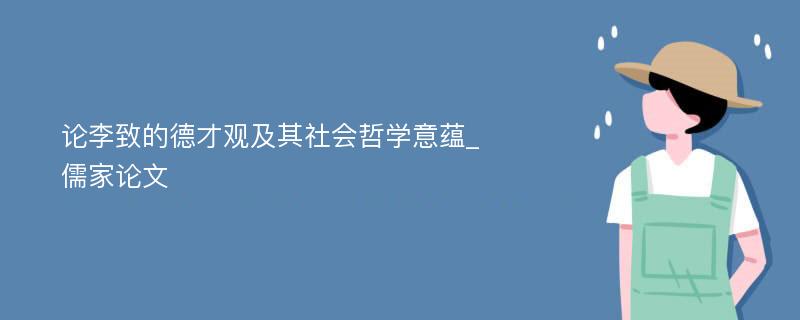
论李贽的德才观及其社会哲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才论文,意蕴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3)04-0006-06
从明末一直到现代,李贽(1527—1602)被大多数人视为儒家正统之外的异端。这种看法虽有少数人反对,但还是成立的,因为李贽的一些重要观点的确偏离了儒家的传统立场,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根据我的理解,李贽对儒家传统的偏离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在人生哲学上,李贽把佛教对来世的价值追求嫁接到儒家的人生观上,换句话说,以佛教对超验的永恒的个人价值关怀来扩展儒学的纯粹现世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这一点在《焚书》《续焚书》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见到。除此之外,李贽对儒家传统的偏离集中体现在他的德才观上。德才观本身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其意义还不限于此:由于德才观往往是某种社会哲学的产物,具有社会哲学的意蕴,因此德才观上的变化反映着社会哲学的差异,至少是社会哲学上的某种不同倾向。据此,阐明李贽的德才观及其背后的社会哲学,不仅有助于理解李贽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后期儒家哲学所面临的某种困境。
广义的德性是把才能包括在内的,比如《中庸》讲的“三达德”(知、仁、勇)和古希腊人所说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都是这样。但在德才观的讨论中,德和才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德性是取较为狭义的用法,即仅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与理智德性相对而言的伦理德性①;此种意义上的德性概念,虽然不可能完全把理智的成分排除在外,但更多地涉及情感因素。而才能是指以知识、经验等为基础的做事能力,涉及的不是情感,而是知性因素。
关于德性和才能性质上的不同,伦理学家有过很多论述,不过,就德才观这个术语而言,更多地是指人们对德性和才智各自功能的看法,即它们各自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以及——更重要的是——这些功能使它们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具有怎样的地位。显而易见,德性和才智各自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在个体行为方面,德性使主体在不同的行为方案中选择善的、正当的行为而拒绝恶的、不正当的行为,才智则使主体采取有效方法来达到某种或善或恶的目标;在整体性的社会效应方面,德性主要关乎社会的秩序或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性,而才智主要关乎社会各领域的活动效能或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力量的总量。对于德才功能的这种不同倾向性,人们一般不存在重大分歧;实质性的分歧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德性和才能二者当中哪一种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把培养广大社会成员的德性和发展他们的才智当作社会决策者需要统筹安排的两项基本任务,那么,究竟哪一项应该被置于优先位置?
从总体上估量与比较德性和才智的社会价值,确定何者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根本上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哲学观念,而不仅仅取决于德才这两种因素本身。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哲学观念,是从社会价值目标的结构来谈的。一个社会的价值目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分析;我们在此只采取一种最简单的分析方法:把社会秩序和力量增长作为两项基本的社会价值目标。这样,社会价值目标的结构不外乎三种可能:(1)秩序优先,增长后置;(2)增长优先,秩序后置;(3)秩序和增长并重。第一种是以秩序为主要取向,第二种以增长为主要取向,而第三种以和谐发展为主要取向。这是三种有明显差异的社会价值目标结构,也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哲学观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秩序和增长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我们仍能够大致分辨开来: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利益分配的合理(这种合理性当然就具体的社会伦理和法律标准而言)以及政权的稳定等;增长则是指一个社会的总体实力的增强,主要包括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的扩张以及行政效能的提高等。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广大社会成员的优良德性对某一社会的总体实力的增长来说是宝贵的“社会资源”②,同时,社会成员的良好才智也可能有利于社会关系的调节。但就功能的基本倾向而言,德性主要与秩序相联系,而才智主要与增长相联系。因此,以秩序为主要取向的社会哲学更关注道德问题,关注社会成员的德性培养问题,而把社会成员的知性发展放在次要位置;与此相反,以增长为主要取向的社会哲学,更加强调各种社会活动的效能,更加关注相关社会成员的才智发展。所以我们说,德才观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与社会哲学紧密相关:德才观既是某种社会哲学观念的衍生物,又是社会哲学观念的反映。
李贽的德才观大大提升了才智的地位,使才智的价值地位达到了在儒家德才观中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关于德才问题的论述,在李贽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中都能见到,但最集中的阐述则是在《藏书》当中。所以,我们以《藏书》为基本材料,辅以李贽的其他著作,对其德才思想做一概括和分析。
我们需要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德才观以及由此表达的社会哲学观念,是李贽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李贽一生勤于著述,留下的著作达几十种之多。不过,在后世影响最大的,只有《焚书》《续焚书》《藏书》和《续藏书》等几种。而在这几种当中,《藏书》的重要性又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李贽之所以被视为儒家的“异端”,主要证据就是《藏书》所阐发的理论观点③。再就是李贽本人对《藏书》的评价。他在给焦竑的一封信中说道,此书史料方面的讹误尽可改正,但自己所作的论断不能改动,因为这些论断反映了自己的重要而成熟的理论见解。[1]7-8他还对此书的社会价值和未来命运颇为自信:“盖此书乃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1]325据此,我们可以断言,《藏书》是李贽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包含的思想观点是李贽最重要的理论成果。那么,这部被作者自许为“万世治平之书”的著作,其理论着眼点究竟在哪里呢?该著开篇有一篇短论,讲了一通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大旨是说:千百年来,人们都是以孔子的意见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人们可以甚至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哪怕自己的见解与孔子有所不同;理由是,不同的是非标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标准本身是因时而异的。李贽还表示,他要在该书中确立自己的标准,根据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孔子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毫无疑问,这篇短论包含着非常激进的主张,而后世的读者可以从这些主张中绎出某种一般性的结论来。不过,我们要知道,李贽对抽象的或一般性的是非标准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整部《藏书》此后再也没有涉及一般性的是非标准问题;开篇讲这番话,只不过是为自己要在该书中阐发的实质性观点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而已。李贽要阐发的实质性的观点,就是其德才观和社会哲学观念。
众所周知,《藏书》在形式上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记载了自战国到元末约八百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实际上,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作者表达自己德才观和社会哲学的纯粹的哲学著作。李贽重才轻德的德才观和对儒家秩序取向的社会哲学的质疑,在《藏书》中通过多种途径表现出来。
第一,在传主的选择上。世纪部分的传主选择表现得尤其突出。《藏书》分为“世纪”和“列传”两大部分,世纪部分记载的是一些领袖人物,主要是历代君主,外加一些农民起义的首领。对这些人物,李贽区别对待的态度很鲜明:有的浓墨重彩,列为专篇,大多数则几笔带过,仅附带提及。如西汉一代,被列为专篇的只是汉高祖、文帝、武帝、昭帝和宣帝,其他如惠帝、景帝、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等不过附骥而行。更有甚者,唐代只有唐太宗列有专篇,其他诸帝被称为“唐子孙”附在其后而已。如此处理所依据的标准,很明显是看这些人物是否具有雄才大略,是否有历史作为,至于他们是否具有儒家推崇的德性,是否遵循了儒家的治国理念,那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在人物的分类上,尤其是列传部分的人物分类上,李贽也表现出同样的观点。列传部分记载的是除领袖之外的历史人物,李贽把他们分为八类,即“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和“外臣”。其中,武臣是指将军;贼臣包括了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奸逆”(这也是李贽与正统史学家最吻合的一部分);亲臣是指宗室、外戚之类;近臣包括了一些宦官、嬖幸;而外臣是所谓的“隐处之臣”。以上这几类人物的划分,基本上接近正统史学标准,至少不构成严重对立,因此,这种划分本身(不包括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评论)没有反映出李贽思想的独特之处。但李贽对前三类人物(大臣、名臣和儒臣)的划分却体现了与正统史学截然不同的观点。什么人是大臣?按照李贽的界定,大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有不同的资质和策略,但“随其资之所及,极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辅危乱而致太平”。什么人是名臣?按照李贽的观点,名臣比大臣要低一个档次:“大臣又不可得,于是又思其次,其次则名臣是已”。不过,名臣也能够为国家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倘得名臣以辅之,亦可以辅幼弱而致富强”。所谓儒臣,是指学习和掌握了儒家的典籍,接受了儒家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李贽认为,三类当中最差的是儒臣:“名臣虽未必知学而实自有学。……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亦无怪其嗤笑也。”总之,儒臣是一群“不可以治天下国家”[2]61的无用之辈。可见,对于大臣、名臣、儒臣,李贽是有明显的褒贬态度的,而这三类人物得以区分的标准,是看他们有无治国安民的才干,是否为国家的富强做出了贡献,而是否具备儒家所鼓吹的德性,是否遵循了儒家的政治哲学理念,对于评定人物的历史地位只起次要作用。
第三,在具体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在评价具体人物和事件时,李贽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观念在其价值尺度中还是有所反映的,如把大多数农民起义领袖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分子列为“贼臣”,在“大臣”、“名臣”中列有“忠诚”、“直节”等名目对德性突出者以示表彰,等等。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李贽高度推崇才智的价值,他对人物事件的很多评价就大大偏离了儒家的传统看法。譬如,秦始皇历来被儒家指斥为暴君,李贽却誉之为“千古一帝”;[2]3李贽还称赞随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有眼睛”,能够“忍小耻而就大计”。[2]625他对武则天也赞誉有加,主要理由是她知人善任:“试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夫所贵乎明王者,不过以知人为难、爱养人才为急耳。”[2]941更加激起争议的是他对谯周、冯道二人的评论。前者是蜀汉降晋的主谋,后者是五代时期历仕数朝、不以改朝换代为意的政坛“不倒翁”,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二人都是典型的没有立场、不讲节操的“贰臣”。但李贽将他们归类为“外臣”,极力为其辩护,多加揄扬。理由是这二人“皆有一定之学术”,[1]225从而使“百姓卒免锋镝之苦”。[2]1142而对于历代儒者所推崇的“圣贤”,如孟子、董仲舒和包括程颐、朱熹在内的绝大多数道学家,不仅列在“儒臣”,而且多有微词。如他批评朱熹,在宋王朝举步维艰之时,只会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谈,并无使宋室“危而安,弱而强”的“奇谋秘策”。[2]603
李贽重才轻德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而且还有更直接的表述。他说:“士之有智谋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谋,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贵正直久矣。余谓惟智谋之士不用,而后正直之臣见,节义之行始显耳。节义者,败亡之征也。……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予以谓智谋之士可贵也。若夫惇厚清谨,士之自好者亦能为之,以之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是亦不足贵矣。是故惇谨之士于斯为下。”[2]343按照李贽的这种说法,“惇谨之士”是在国家败亡之际才出场的,假如国家事先就重用“智谋之士”,国家就会免于走向败亡,“惇谨之士”永无出场的必要。这里面的“智谋之士可贵”和“惇谨之士于斯为下”两句话,是李贽德才观的最清楚最简洁的表达。
对于德性和才智的价值比较,儒家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德性的价值地位是首要的,才智固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与德性相比,其价值地位只是第二位的。孔子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3]《论语·宪问》一匹马之所以被认为是好马,不在于它有力量,而在于它有驯服的“德性”。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项专长当中,德行被排在首位。[3]《论语·先进》因此,德性培养是第一要务,各项才能的发展是其次的工作,这就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论语·学而》后世儒家一直没有背离这一根本立场。
如前所说,这种德才观不是孤立的,而是以秩序为取向的社会哲学的产物。以秩序为取向,这是儒家传统社会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这项特征早在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已经形成。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3]《论语·季氏》这一著名命题,就是这种社会哲学观念的重要表述。《孟子》开篇记载的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也表达了同样的主张: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如何调节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增强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这种社会哲学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职业观、学科观等等。在以实现和谐秩序为首要政策目标的社会里,最受重视的职业是那些服务于调节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的职业,如行政职业和培养后备行政人员并从事道德宣传的教育职业,同样,最受重视的学科是能够直接服务于调节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的学科,如政治学和伦理学。德才观是受这种社会哲学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很明显,德性而非才智是与社会秩序更加契合的因素。普遍的才智发展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各种活动的效能的提高、社会利益总量的增长,的确也可能有助于调节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稳定,但在传统社会各种条件制约下,最现实的手段却是广大社会成员尤其特定社会群体、特定个人的德性培养。从改造德性(儒家通常强调的是士大夫阶层和君主的德性)入手,实现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合理化,进而实现和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儒家德治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④
以秩序为取向的社会哲学和德性优先的德才观,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得到了系统阐述。仅以朱熹为例。我们知道,宋代长时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不仅国内存在种种矛盾和困难,外部还面临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理学家仍然恪守以秩序为取向的社会哲学和道德优先的德才观。朱熹认为,宋代社会当然需要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如提高封建国家官僚系统的运行效率,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他甚至承认“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乃是“腐儒迂阔之论”,[4]1055要求人们要具备认识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他同时指出,这些都不是根本性的。对宋代社会来说,根本性的任务是改造整个士大夫阶层尤其是君主的德性,只要这个任务完成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比如谈到宋金之间的对峙,朱熹说道:“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虑国事者大抵以审彼己、较强弱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尝及中国治夷狄之道也。盖以力言之,则彼常强,我常弱,是无时而可胜,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则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国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当议也。”[4]1270宋王朝战胜金政权的关键,并不在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在于社会内部关系的调节,在于统治阶层的道德状况。这也是他批评王安石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活动和陈亮的事功思想的理论依据。
儒家的这种社会哲学和德才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然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它又有明显的偏颇和局限,即为秩序而牺牲增长,为突出道德的社会价值而不恰当地贬低了才智的重要性。这种理论上的偏差会导致许多严重的消极后果,如整个社会缺少足够的增强实力的意志,各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智力资源无法投入到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经济当中去,各种社会活动专业化程度低下⑤、效率不高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后果尚可以保持在封建国家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这些后果会变得特别突出。
李贽的德才观和它反映出来的社会哲学,除受到泰州学派的某些影响之外⑥,主要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刺激,表达了李贽对儒家思想制约下的社会状况的某些方面的不满。这些方面主要集中在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行效能的低下上。李贽生活在明代嘉靖(1522—1566)到万历(1573—1620)年间,而这一时期,明王朝虽然还未显败亡的征兆,但它已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李贽的视野里,两方面的问题最为扎眼:一是士大夫阶层日益腐败的道德状况,二是统治集团的无能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机器运行效能的低下。而在这两方面当中,李贽把后一方面视为更关键的问题。这种效能的低下,表现在封建国家的各个领域,如财政、法律和军事等等。比如,李贽曾谈到这样一个事例:在东南沿海,当时有一股以林道乾为首的盗匪,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今幸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1]155国家机器运行的效能的低下,被李贽直截了当地归因于人的问题(而非制度问题),即官僚集团的无能,而后者又被归因于儒家传统的德才观。他曾就林道乾之事发表了一段有名的议论:“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1]155)
毫无疑问,与正统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对比,李贽的理论在主题上发生了转移。理学家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士大夫阶层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力图通过统治集团的自我道德改造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化,最终实现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而李贽似乎意识到,这种以秩序为取向的社会哲学会造成德才观上的偏差,进而带来社会管理的效能问题。因此,李贽强调要为知识、才干、谋略等等这些德性之外的因素确立一个更高的、更适当的价值地位,而不能一味地强调道德,重复天理人欲的老调。
综观从先秦到清代中叶之前的中国思想史,关注社会经济、军事等各种实力的增长,重视各方面具体问题的解决,强调与德性相对的才智因素的社会价值,这种思想观念作为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正统的社会哲学和德才观相疏离甚至相对立的支流,在整个思想史上时隐时现。先秦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东汉末年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南宋陈亮、叶适的事功倾向以及从明末兴起而盛行于清代的实学思潮,都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虽然这些思想观点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与儒家以秩序为取向的社会哲学和德性优先的德才观构成了某种对立。我认为,李贽的观点就属于这一支流,而且是这一支流当中较为激进的一种。
不过,同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偏离,就其主要根源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思想家之所以强调社会实力的增长,推崇才智因素的社会价值,主要基于社会的外部环境。我们看到,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激烈角逐、东汉末年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宋政权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对峙,尤其是两宋政权和明王朝的覆灭并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取代,这种“国际”竞争的局势如何严重地刺激了上述思想的发生发展。另外一些思想家提出相似观点,其主要动因与此有别:不是外部环境带来的竞争压力,而是社会内在问题的积累,刺激了这种观点的产生。明清倡导实学的许多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明陈子龙于1638年编著《皇明经世文编》,魏源以贺长龄的名义于1820年编著《皇朝经世文编》,虽然部分动机是应对外患,但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社会内部问题。与这些人相比,李贽思想的提出在这一点上更加典型。当李贽于1602年去世时,努尔哈赤还只是受明朝廷册封的地方官,后金政权的建立是十多年之后的事情,更不用说它对明王朝构成真正的威胁了。至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在李贽看来也算不上真正的外来威胁。因此,李贽之所以强调国家实力的增长,强调才智因素的社会价值,完全出于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虚弱、效能低下的不满。不必等到这一社会与外部力量相碰撞而遭受重创,或者爆发严重内乱而走向覆灭,而在这一切到来之前,能够透过其四海升平、安定强大的外表察觉到它的无能和脆弱,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李贽的远见卓识。
但无论是李贽还是其他异端思想家,都没能真正颠覆儒家德才观和社会哲学的统治地位,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几乎始终处于主流之外。在中国,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以增长为取向的社会哲学观最终获得主流地位,乃是所谓“反应性民族主义”⑦的副产品,而包括德才观在内的一系列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又是这种副产品的结果。近代以来,由于外部力量的威胁和一连串失败的厄运,中国社会才形成了比较普遍的民族意识和国际竞争意识,才产生了发展国家总体实力的意志。无论此后是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还是出于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考虑,抑或出于“文明”间竞争的需要,国家力量的增长始终是一个确定不移的目标。与此相应,整个民族的知性(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等)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这种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体系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的近现代进程使李贽的主张获得了胜利——只是这种胜利比它应该到来的时间晚了大约三个世纪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重才轻德的德才观和以增长为取向的社会哲学,并不就是绝对正确、积极的观念。它们对缓解传统社会中片面强调道德和秩序的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顺应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趋势,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没有人敢保证这不是以一个极端取代另一个极端,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或许,我们应该确立的是一种德才并重的德才观、秩序与增长兼顾的社会哲学。
注释: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科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卷第13章、第2卷第1章。
②关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当然包括在内)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原因应归功于研究和宣传“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可参见曹荣湘选编的文集《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③1602年李贽被指控的理由,除所谓的个人品行不端外,就是集中体现在《藏书》中的理论观点。从当时朝臣对李贽的劾状(顾炎武《日知录》卷18、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都有引录)就可看出。李贽死后不断遭到理论上的批判,这些观点也是主要内容和起因,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和“叙论三”。
④所谓德治主义,一方面是把道德与法律相比较,讨论的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问题,另一方面是把道德与才能相比较,讨论的是增长和秩序的价值取向问题。
⑤对于中国古代甚至迟至晚清的行政系统的非职业化、非专门化,M.韦伯有过很多论述。可参见其《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0、298页。
⑥李贽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很大,对该派中的许多人如王艮、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表示推崇。而自王艮之后的该派成员,大都有一个特点,即多有胆识才干,较少顾及道德约束。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卷32)这种人格特征在李贽的思想中想必留下了印记。如他所刻画的“豪杰之士”,颇带有该派人物的特征。可参见《焚书》卷1《与焦弱侯》。
⑦这是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的概念,见澳大利亚经济学家H.W.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二章。意思是指,一个社会或国家因遭受外来打击而产生的民族意识和增强民族力量的意愿、思想与决策等。
⑧正是在李贽生活的16世纪,西欧社会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相互间的竞争,一方面,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成为一种明确的政策目标(见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13~14页),另一方面,军事、财政和法律领域的专业化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专业官吏体制”得以确立(见M.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68页)。
标签:儒家论文; 李贽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价值观取向论文; 读书论文; 焚书论文; 社会价值论文; 藏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