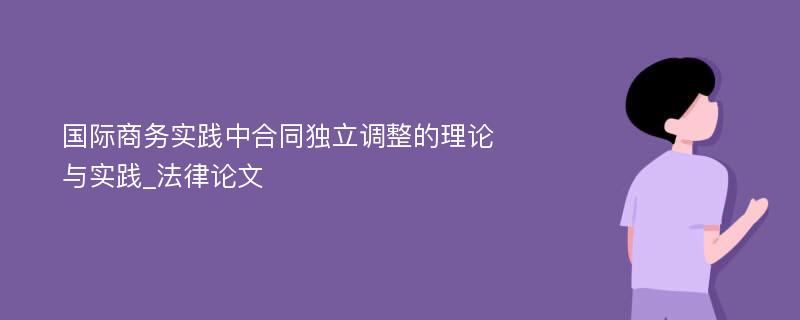
国际商业惯例独立调整合同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惯例论文,独立论文,合同论文,理论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08)01-0121-08
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日渐频繁和深入,对跨国性商事纠纷处理的适当与否成为推动或阻碍国际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跨国纠纷的传统法律适用方法是通过设计“指示器”的方式在不同国内法之间寻找适当的法律。随着国际商业的日益发展,国内法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不适当性越来越明显,①一些国际法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可以取代国内法调整国际合同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商业惯例便成为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际商业惯例取代国内法的依据何在,国际商业惯例能否担负调整合同的功能,国际商业惯例可以何种方式取代国内法,等等。本文试通过对相关理论争议以及国际商业惯例适用的实践和发展前景的评述和考察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立法有关国际商业惯例法律作用规定的积极意义和不足。
一、国际商业惯例的含义
国际商业惯例通常又谓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国际贸易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得到普遍接受并具有确定内容的做法和规则等,自发性是这一传统概念的核心。但随着旨在调整国际商事交易活动的各种自觉性立法活动的增多,国际商业惯例概念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Roy Goode在论述跨国商法的渊源时,将“国际贸易惯例”界定为完全自发的产物,以与国际组织等自觉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进行严格的区分[1]547,前者是在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具有普遍约束性的习惯做法,其对当事人的约束不以合同选择为前提;而后者则具有统一权利义务和行为的目的,既可能是对既存国际惯例的编纂,也可能存在为推动贸易实践而对现状的一些偏离,而这种偏离只有在被广泛获悉和采用后才可能创造新的惯例。[1]550-551
而作为商人法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施米托夫则主张作为商人法渊源之一的国际商业惯例是指“由诸如国际商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法协会或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商业习惯性做法或标准”[2]266,而非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商业惯例则被称为国际商业习惯性做法(usances),“有时就是商业惯例的雏形(in statu nascendi),即导致最终形成的商业惯例的最初的或试验阶段的形式”。[2]50
显然,Roy Goode的“国际贸易惯例”概念强调其形成的自发性及其约束力的普遍性,强调对贸易实践的真实描述,因此更侧重于惯例的事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合同而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2]266而施米托夫的“国际商业惯例”概念则侧重于惯例作为法律规则的意义,通过对国际组织制法功能的强调将国际商业惯例界定为“一种造法渊源”。[2]150从为国际商事交易提供调整规范的角度看,以自觉制定性为其核心特性的“国际商业惯例”显然更符合本文的写作目的。只是,施米托夫将“国际商业惯例”的制定主体限于“国际组织”未免过于狭窄。事实上,除了国际组织的制定活动之外,包括各主权国家所独自制定的国内立法,由各主权国家参与制定的国际商事公约等,也可能或者部分或全部反映了国际商业实践中被广泛接受的习惯性做法②,或者因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而成为习惯性做法。而施米托夫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商业惯例的唯一制定主体,显然“抑制了各种形式的试图去统一各国商法的努力”。[3]319-320
因此,本文所称的“国际商业惯例”是指为调整国际商事交易的目的而制定的,反映国际商事实践中的既有习惯或在实践中被广泛接受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商业规则或标准。至于规则或标准的制定主体为何则在所不问。
二、国际商业惯例独立调整合同的效力依据
从现实的角度看,国际商业惯例因其实践来源性、针对性以及统一性而比国内法更能适应国际商业共同体的利益需求。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国际商业惯例在多数情况下既非由国内立法机关制定,又非各国共同意志的产物,因此其取代国内法独立调整合同的依据何在是困扰着国际法学者以及国际商业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反对国际商业惯例作为合同适用法的学者最根本的理由在于:国际商业惯例不是法律。在反对者看来,“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是能够去独立的解决国际商业纠纷所必需的。”[3]286因此,国际商业惯例要取代国内法独立调整合同的必要前提是其应归属于独立的法律体系。根据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法律主要有三个一般的和重要的特点,即规范性,制度化和强制性(normative,institutionalized,coercive)。而国际商业惯例不完全符合为法律体系所特有的制度化和强制性[4]152-53,因此它不是法律,而只是一种贸易原则(principia mercatoria)[5]108,不能够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
而一些支持者们从法社会学的角度主张国际商业惯例的法律性。例如,法国学者卡恩(P.Kohn)认为,按法社会学的观点,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均可制定法律,因此,国际商业社会的自治规则,如惯例等,也可以视为适用于国际贸易活动的法律规范。[3]215-216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避开有关国际商业惯例是否是法律的争论,主张“如果‘法律规则’能够为纠纷提供适当的解决,就没有必要考虑他们是否构成了一个法律体系”[6]。例如Jenks指出,国际商业惯例“能否作为合同适用法并不依赖于关于什么构成法律体系的先入为主(preconceived)的观念,而是依赖于他们是否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合同适用法的功能以及实际上被基于那种目的而适用”。[6]704显然,上述学者们都将国际商业惯例的效力依据建立在商业共同体自发制裁和自动执行的基础上。但对国内司法而言,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强制力仍只是事实上的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因此仍难摆脱实证主义者的质疑。
与上述学者的立场不同,兰度则认为,国际商业惯例是否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并不是其取得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其法律约束力的有无取决于商业社会和国家权力机关承认它为一种自治体系的事实[7]。换言之,国际商业惯例独立调整合同不以符合实证法的要件为前提,只要其规范功能得到国内法强制力的保障即足够了。这一观点显然正确地抛弃了前述反对者和支持者各自片面和对立的立场,为国际商业惯例的事实效力与法律效力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由此可以断言,国际商业惯例得以独立调整合同的效力依据在于国内法的认可,其事实上的约束力本身不能为其提供取代国内法的依据,而只是决定国内法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其自治性的影响因素。
三、国际商业惯例独立调整合同的可适用性
除上述有关效力根据的争论外,国际商业惯例在现实中能否担负独立调整合同的作用也是引发各种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按照美国学者哈赫特(Keith Highet)的观点,[5]624能够独立调整合同的法律规则或者“法”必须符合这样的标准:即,一般可适用性;权威性和连贯性;相对可预测性;明显的公平性。而对国际商业惯例的可适用性表示质疑的学者指出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难以符合上述要求:
首先,不具有一般可适用性。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惯例必须以某一共同体为依托,在时间与空间的制约下,方能成立。[8]而现代世界的商业社会并未构成一个共同体,所以从法的观点来看,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惯例”[3]228。
其次,缺乏可预测性。导致国际商业惯例不可预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确定性,而对国际商业惯例的最普遍的批评也正在于此。③[9]182有学者认为,国际商业惯例所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都是“以牺牲确定性为代价的”。[10]536
第三,在利益平衡和保护方面不完善不公平。法国学者巴迪福尔在论及非国内规则的适用条件时认为,在解决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时,必须考虑诸如公益、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方利益及第三方利益的保护问题。[11]而国际商业惯例往往只反映商业团体自身的利益追求而忽视国家、社会利益与私益之间的平衡;[10]535另外,因国际商业惯例缺乏强制性规定,适用其调整合同将导致“合同有效性的问题,误述,不正当影响,惩罚性条款以及对弱方利益的保护都处于真空状态”[12]。
针对国际商业惯例的上述缺陷,一些国际法学者也试图从理论层面予以补救。例如,为弥补国际商业惯例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方面的不足,法国学者哥德曼提出“跨国公共秩序”的概念,[13]691④主张国际商业惯例应受“跨国公共秩序”的限制。[3]215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其所界定的“跨国公共秩序”不仅过于笼统而难以操作,⑤而且也不足以排除不公平的国际商业惯例的适用。而施米托夫则寄望于国际组织的制法活动,强调作为商人法渊源的国际商业惯例必须是“由诸如国际商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法协会或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商业习惯性做法或标准”[2]266。只是其将国际商业惯例严格界定为国际组织的制法成果,又过分限制了国际商业惯例的范围,可能“抑制各种形式的试图统一各国商法的努力”[3]319-320。
事实上,从现有的状况看,不仅国际组织对惯例的编纂活动已经大大提高了国际商业惯例的可预测性,而且一些国际商业惯例因被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纳入而更加确定和公平。⑥而在与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范畴内,对国际商业惯例忽视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批评也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将目光放诸于未来,从各种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者对确定、统一和公平等价值的重视态度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会有更具可适用性的国际商业惯例出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所起草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不仅对一些模糊概念规定了确定的内容,甚至比国内法的规定更为详尽和确定。⑦另外,《通则》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强制性规定,反映了其在保障特殊利益方面的努力。⑧尽管《通则》目前尚不是国际商业惯例,但其规定的合理性使其被广泛接受和适用的前景值得期待。
因此,针对有关国际商业惯例可适用性的质疑,似乎可以借鉴塞尔登(Selden)的观点[14]来予以答复:国际商业惯例现在是否已经足够明确和公平以致可以被用来取代国内法来规范国际商事合同?今天的答案是“不”,但这一前景是可以预见的。而目前,一些发展成熟的国际商业惯例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已经足以承担这一功能。因此,现在应探讨的不应是现有的国际商业惯例是否具有可适用性,而应是基于国际商业惯例现有不足的存在,为国内法认可哪些国际商业惯例以及在哪些领域认可国际商业惯例确定一个现实的标准。
四、国际商业惯例调整合同的理论模式
基于对国际商业惯例的性质及其重要性的不同认识,主张国际商业惯例作为合同适用法的学者对其取代国内法的方式设计了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的合理性、现实可行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也是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自动适用论
即国际商业惯例可直接自动调整其范围内的国际商事合同,而无须国内法冲突规范的指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国际商业惯例视为一种超国家的规范,Sir Michael Kerr更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一种独立的“漂浮在跨国上空”的法律规范(legal norm "floating in the transnational firmament"),[1]548因此其存在使“法律选择规则以及原则就变得多余了”,[15]哥德曼则认为以国际商业惯例为主要支柱之一的现代商人法是一种自治法律体系,是本身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正式法律渊源,它不仅有自己的实体法,而且发展了自己的冲突规则,即跨国性实体规则(substantive transnational rules)。[13]660根据这种规则,商人法可以无须借助各国内法的冲突规范而直接凭借该体系内的“实体跨国规则”予以适用,从而使国际商事交易完全摆脱国内实体法和冲突法的影响。Lord Justice Mustill则更明确地主张“可能有一种专门的只有一种规则的冲突体系——即所有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纠纷在仲裁时都被商人法(国际商业惯例)所调整”。[4]154但他进一步认为,国际商业惯例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适用其他法律的情况下才具有自动适用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适用国际商业惯例“意味着重写了合同”,不论动机有多好,都将对当事人构成伤害,从而导致对交易自由的干预。[4]168
自动适用的观点与我国法学界所主张的国际统一实体法理论相近[16],其核心在于国际商业惯例无须经国内冲突规范的指引可直接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这与传统上所主张的国际私法规则的作用是相对立的。根据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跨国合同的适用法应根据国内冲突规范来确定,这“反映了地域主权为了其存在而控制具有涉外因素的私法关系以维护其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需要”;[6]682而自动适用论则力求摆脱国内冲突法的约束,实际上将跨国范畴内的私人利益置于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更宽泛的共同利益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商业社会对“自我管理”的要求日益增长的需要相一致。
由于自动适用论将国际商业惯例完全置于国内法,包括国内冲突法和国内实体法之上,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将很难为国内法所接受。因此,有学者认为自动适用论是“理想主义”的。[17]但是,在某些国际惯例发展成熟并且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关系较少的领域,认可国际商业惯例的自动适用地位也不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奢望。如西班牙和伊拉克的法律规定,西班牙的一切进口交易和伊拉克的所有进出口交易,都必须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约束。[18]尽管实践中对这种模式的接受情况尚属罕见,但随着国际商业惯例日益发展成熟,在与国家和社会利益无关的领域内认可国际商业惯例的自动适用性并非没有现实的可能。当然,国内法在接受自动适用模式时,仍有必要在追求国际商业交易调整规范的一致性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二)替代适用论
替代适用论主张国际商业惯例是一个规则体,可供合同当事人将其纳入合同,或明示或默示选择适用以摆脱本应适用的国内法的约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当事人自治是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首要宗旨,因此,除非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国际商业惯例,否则国际商业惯例不能自动适用于调整国际商事合同。[19]也有学者主张,在当事人未明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情况下,适用国际商业惯例比适用国内法更接近当事人的意愿。[20]
替代适用论的提出突破了“以主权国家或政治实体为本位”[21]的传统法律适用方法理论。根据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当事人意思自治是通过选择某一立法管辖权从而获得具体的国内法作为准据法。这种“扎根于中央集权以及实证主义(in statism and positivism)之中”[22]203的传统理论,在替代论者看来“在现代已经过时了”,因为“商业行为正被从国家干预中解放出来”。[22]203因此,替代适用论的学者抛弃了适当国内法必然是适当法律的这一理论假设,主张径直寻找实体意义上适当的规则作为商事交易准据法,从而使当事人合意不仅仅起定域功能,而是直接指向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这样不仅可以免除当事人在不同国家法律之间进行抉择的困难,而且可以降低适用外国国内法的诉讼成本。[1]545-546
替代适用论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接受,一些国内仲裁立法、国际公约和仲裁示范法等都不再将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限于“法律体系”,而是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规则”(rules of law)。相反,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的冲突法明确准许国际合同当事人选择国内法之外的其他法律规则。更多学者主张在处理选择了国际商业惯例的合同的纠纷时,国内法院只应在“其不会影响适用法中的当事人不得以协议减损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适用该惯例。[23]
尽管如此,仍有学者从国内法院的表述中窥见了其接受非国内法调整合同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国上诉法院支持国际商会在DST v.Rakoil案⑨中根据非国内法所做的裁决后,Mark Garavaglia指出,[24]“既然上诉院的判决明确拒绝了传统的‘法律体系’的主张而认为当事人有权不将其合同限定于单一的国内体系”,那么对非国内法律体系的适用是在仲裁还是在诉讼中的区别将“仅具有表面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也许Peter Nygh的观点将对国内法院接受国际商业惯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该不该承认当事人在国内法之外的选择权,而是如何合理地划定选择非国内法的权利和国内法必要地介入之间的界线。[9]173
(三)补充适用论
补充适用论主张国际商业惯例至多可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规则被用于纠纷的处理,[6]733其不是“革命的”,而只能被用于“阐明和弥补个别国家法律的缺陷,以及减少根本不是为国际交易而设计的个别国家法律的特殊性的影响。”[25]因此,国际商业惯例只是本应适用于合同的国内法的补充,国际商业合同最终仍摆脱不了国内法律体系的约束。
与自动适用论和替代适用论相比,“补充适用论”对国际商业惯例法律作用的界定显然最为狭窄,有学者认为这过分贬低了国际商业惯例实际的法律作用,[17]226更有学者将具有补充作用的国际商业惯例等同于“法律漏洞补充的工具”而否定其法律性质。[13]645但不能否认,补充适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简化法律选择排除国内法适用的作用。在适用分割理论的情况下,根据国内冲突规范所确定的国内法对所涉案件没有规定时,以国际商业惯例作为补充可能省却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继续确定准据法的麻烦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充适用论仍具有一定的价值。而由于“补充适用论”对国内法地位的冲击最小,这种理论被国内法接受的程度也更高。⑩
从上述分析可见,三种有关国际商业惯例的适用模式各以不同的理论假设为前提,分别从一个角度关注了国际商业惯例的一种特性,表面上看似乎各不相容,但正是由于其各自的片面性,三种模式反倒各有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孤立地评判某种模式比其他模式更为合理和完善似乎不够恰当,(11)正确的态度应是全面地分析三种模式各自的适用条件和范畴,从而在国内立法中适当地选择采纳。
五、中国有关国际商业惯例法律地位的立法实践
自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首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做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之后,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1992年《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1995年《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以及2004年《票据法》第九十五条也都沿袭了这一做法,规定在涉外法律关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2)类似的规定在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也得以保留。(13)
另外,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1999年《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都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对于可以选择的“法律”是否包括国际惯例,立法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最高院1987年《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的二(三)中也只规定“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可以是中国法,也可以是港澳地区的法律或者是外国法”,但不包括国际惯例;1989年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时,各法院则一致认为“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适用的国际惯例,只要不违背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作为解决当事人间纠纷的依据”;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颁布的《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中更明确地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选择的准据法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外国法或者有关地区的法律”。《民法典草案》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第四条也明确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经过协商一致以明示方式选择适用国际惯例”,第五十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在涉外合同当事人未明示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根据相关规定,法院仍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的准据法,而非直接适用国际惯例。
但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则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该条显然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是对当事人明示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的认可;其二,是对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时国际惯例自动适用性的认可。
从上述立法实践看,我国立法对国际惯例法律效力的认可兼采了三种理论模式,其中以补充适用论最为突出,通过《民法通则》和《海商法》等各单行法以及《民法典草案》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于国际惯例对我国国内法的补充作用不仅给予了一般性的认可,而且有继续予以保留的趋势。至于替代适用模式的采用虽然在现行立法中还没有得到明确的体现,但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倾向于认可当事人合意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民法典草案》中的规定更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趋势。因此,似乎有理由相信,我国国内法准许涉外合同当事人选择国际惯例的立场是较为明确的。另外,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我国法律也认可了有关信用证的国际惯例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可自动适用。
中国法对三种模式的逐步接受的过程反映了中国立法对国际惯例的逐步放宽态度。从最初的以补充适用论为主到现在对国际惯例的替代作用的基本认可以及对国际惯例自动适用的有限接受,国际惯例在中国法下发挥法律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立法对国际惯例的这种宽松态度反映了我国有关涉外商事交易的立法正逐渐向减少对跨国商事交易管制的方向转变的趋势,对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方无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有助于提高中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影响力。但同时,中国法对于国际惯例的适用仍保留了“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必要的限制,(14)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因国际惯例的内在缺陷所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法对于国际惯例的态度仍是较为理智的。但是结合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我国现有立法有关国际惯例的规定仍不乏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首先,就国际惯例的补充作用而言,现有立法只明确认可国际惯例作为我国法律的补充,即只有在我国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且缺乏相应规定时,法院才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而在外国法为准据法且缺少相应规定时,能否以国际惯例作为外国法的补充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可以将国际惯例的补充作用扩大及一切本应适用的准据法,即只要就案件相关问题存在国际惯例而合同准据法没有规定时,可直接适用该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的补充,这对于降低诉讼成本以及确保审理结果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都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从我国立法实践看,有关国际惯例适用的限制规定尚欠完备。如前文所述,一方面,现有国际商业惯例所具有的不完善性决定了分割理论的适用是认可国际惯例作为合同适用法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大量国际商业惯例存在的不确定和不周全性决定了国内法认可的国际惯例应限于内容确定、合理且与国家和社会利益较少冲突的领域。而我国有关法律适用的相关立法(包括《民法典草案》)都没有明确采纳分割理论,从而可能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无法对合同进行全面调整时合同部分处于法律真空的状态。另外,仅以公共秩序保留作为适用国际商业惯例的防范工具显然不够充分。虽然作为适用外国法的安全阀,公共秩序保留为各国国际私法的理论和立法所广泛接受,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发展,这一原则一般仅被作为“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例外地排除外国法的适用的手段和措施”。[26]如果对我国立法中的“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也做如此严格解释的话,不仅立法有关国际惯例具有合理性及确定性的要求的缺失将可能增大适用国际惯例的风险,而且对当事人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的一般性认可也将对现有立法的利益保护体制构成冲击。由此可见,在立法相关配套规定仍不完善,并且对可适用的国际惯例未进行严格考察的情况下,一般性地准许合同当事人选择国际惯例作为准据法未免过于仓促。
收稿日期:2007-09-30
注释:
①如美国学者劳恩费尔德认为:“法律选择程序所指引的国内法规则,与国际商业的需要和习惯是不协调的。各国自行制定国内法规则,本是为了调整国内事项,而非国际范围内的事项。”见Peter Nygh,Auonomy in Intnernational Contracts[J].Clarendon Press,1999:178-179.
②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被认为是对海上保险领域习惯性做法的集合(见Donald M.Waesche.Choice and Uniformity of Law Generally[J].66 Tul.L.Rev.,1991:293,297-300.);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中的一般原则和条件被普遍视为是贸易惯例的证明。
③在由跨国法中心所发起的世界性调查中,大多数回答者认为,作为国际律师,他们强烈反对选择商人法(包括国际商业惯例)作为准据法。
④又为“真正的国际公共秩序”或“第三种公共秩序”。哥德曼认为其规则包括自然法则的规则、普遍的公平原则、国际公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和为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
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国际公共秩序”的根据仍然是国内的,其成立与适用仍需国内法的认可或作出解释。所以,这种区分在目前似乎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在实践上很难实行。(详见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347-348)
⑥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中某些惯例被认为比国内法更为公平。例如:在国际商会的某一仲裁案中,仲裁小组认为,“卖方营业所在地的国家的法律对买方因货物缺陷而向卖方发出通知规定了极短的期限和特别的要求”,而CISG中所规定的两年期间对缺陷产品的买方提起诉讼更为有利,该国内法的规定“看起来偏离了反映在CISG中的被普遍接受的贸易惯例”。(ICC Case No.5713,as reported in UN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ases on UNCITRAL Texts",A/CN.9/SER.C/ABSTRACTS/3(1994).)
⑦《通则》对一些被承认的概念增加了确切的定义,如善意,不可抗力以及终止权。
⑧如第1.7条关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规定,第三章关于实质效力的规定,第5.1.7条第2款关于价格的确定的规定,第7.4.13条第2款关于对不履行协议的支付的规定和第10.3条第2款关于时效期间的规定。
⑨DST v.Rakoil(Deutsche Schachtbau-und Tiefbohrgesellschaft mbH v.R'as A1 Khaimah National Oil Co) ,2 Lloyd's Rep.246 (1987)
⑩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民法典都赋予“惯例”或“习惯”以补充法律的地位。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如本法无相应规定的,法官应依据惯例;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者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在前款情况下,法官应依据经过实践确定的学理和惯例。”我国台湾民法第1条也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围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⑾我国有学者主张替代论比另两种理论更为合理,并主张我国立法应抛弃补充适用论而采替代适用论。
⑿《票据法》规定的是“本法”而非“中国法律”,从而使国际惯例成为票据法的补充性渊源。
⒀《民法典草案》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于该涉外民事关系的争议事项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⒁除了《民法通则》以及其他单行法中有关适用国际惯例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之外,《民法典草案》第十一条也同样规定:“依照本法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标签:法律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实践合同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商事主体论文; 社会法论文; 商业论文; 海商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