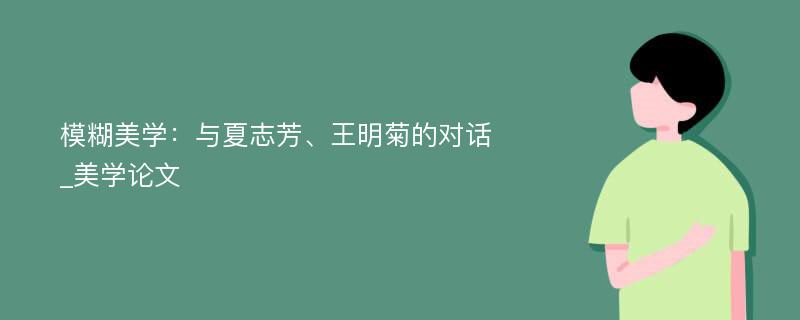
关于模糊美学——与夏之放、王明居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模糊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二十年代前后,当玻尔等人因为在量子力学方面的贡献而一个接一个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却受到爱因斯坦等人的猛烈攻击。玻尔、海森堡等人对爱因斯坦进行了可以说是科学史上最顽强的抵抗。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大多数物理学家倾向于测不准关系,爱氏只好去责备量子力学理论的完备性,而玻尔则获得了物理学的伦勃朗称号。伦勃朗与玻尔都强调不确定性①。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都在向模糊论位移。
大约在一九八二年左右,中国出现了有关艺术的模糊性的探讨②,后来王世德、徐宏力诸先生都有论文面世③,特别是王明居先生《模糊艺术论》、《模糊美学》两部专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夏之放先生在一九九三年《文艺研究》第三期上著文批评了其中某些观点。
首先夏之放先生否定了模糊理论自身的哲学意义。夏先生认为现代科学如模糊数学、耗散结构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验证。因此似乎是模糊美学只要以唯物辩证法做为基础就可以了,“舍此之外再去寻找什么物理学的、化学的、数学的理论依据,是没有必要的。”
这里夏之放先生有两个常识性的错误,一是唯物辩证法是在大量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数学的理论依据”上产生的,没有这些理论依据,就没有唯物辩证法。而夏之放先生却让这个后来者取代了自然科学的几乎全部哲学意义,似乎人们研究模糊美学只要研究唯物辩证法就行了。
夏之放先生的第二个常识性错误在于,他一方面把实践做为理论的唯一基础和依据,但却又把唯物辩证法做为耗散结构论的理论依据。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之内就难以自圆其说。其实马列主义者早就说过,理论也是可以做思想的基础的。毛泽东就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可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可以产生精神分析的美学,在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可以产生实用主义美学,在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可以产生存在主义美学,在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可以产生结构主义美学,如此等等。那么为什么不能在模糊数学的基础上,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在耗散结构论、在相对论的基础上产生模糊美学呢?
王明居先生在反驳这些观点时,他认为耗散结构论和模糊数学可以做为模糊美学的理论基础,这没有什么不对,未必一定要从唯物辩证法作为出发点。王明居先生还把耗散结构论、模糊数学的一些具体原理推演到模糊美学,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论确实从最抽象的形式中说明了模糊理论的一些本质特征,可以做为模糊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但王先生似乎忽略了模糊数学的哲学意义,因为美学本身就是模糊性很浓厚的学科,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向模糊数学学习,死搬硬套模糊数学的方法。
二
王明居先生没有注意到东方艺术比西方艺术、现代派艺术比古典艺术具有更大的模糊性,所以夏之放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王明居先生的模糊美学肯定了无限的宇宙的模糊美,可书中引用的例证大多为中外经典著作,同时关于典型性与模糊性的论述也在逻辑上产生了矛盾。我认为这说中了王先生的弱点。王先生在他的模糊美学研究中,至少对两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是就整个世界的文学艺术而言,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现代派文学艺术比以前具有更大、更多、更加丰富多彩的模糊性;二是东方的文学艺术比西方的文学艺术具有本能的或自觉的模糊性。王明居先生忽视了第一点,所以夏先生说他是“前此已有的所谓传统美学著作和传统艺术作品,几乎包罗无遗地全都变成了论述和验证模糊美学的资料,这就势必造成论述逻辑上的严重错位。”王先生忽视了第二点,所以有时在典型性与模糊性之间先造成了对立。如果我们注意到东西方文艺观的差异,我们就会认识到做为西方艺术几乎是最重要的范畴的典型也是具有模糊性的。而做为东方艺术几乎是最重要的范畴的意境则具有更大的模糊性。
忽略了这两点,就使得王先生在他的两本著作中,对古典艺术和现代派艺术平均用力,那么这样一来,模糊美学与模糊数学、混沌学、耗散结构论、模糊思维以及现代派艺术之间的联系就似乎不存在了。同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讲,西方现代派艺术之所以具有了更强的模糊性,与其向东方艺术中借鉴有关。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与其主要是一味模仿吸收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有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沈从文、钱钟书、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赵树理、郭小川、丁玲等人,如果说是他们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的话,那么大多是十九世纪以前的陈酿。所以,他们的作品极少具有现代派的模糊性,同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非常可惜地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含蓄与意境。
在关于逻辑的错位这一问题上,王先生引用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无论是王先生还是夏先生,他们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都并不是太得心应手。例如在宇宙学方面,在关于时空的有限与无限方面,他们的知识都限于十九世纪,甚至没有超出哥白尼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水平,好像马克思以后的爱因斯坦、德西特、弗里德曼、勒梅特、哈布尔、盖莫夫、彭各阿斯与威尔逊等人都没有存在过似的。
三
关于美学本来是不是模糊的问题,我认为夏先生的论点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也就是说,传统美学对模糊性的研究,与今天的美学对模糊性的研究,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异。只不过是现在的模糊美学研究变得自觉了。抛开中国的传统美学不说,就拿西方美学来说,早在二千多年前,对于美的模糊性问题已经有所认识。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一开始就继承了古代时期对精确的追求。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的和谐、比例以及秩序是美的,否则就是丑的。不过当时的艺术家并没有像毕氏这样追求绝对的精确。④这为后来的赫拉克利特的美的相对性⑤和德谟克里特对暖昧感觉的推崇⑥,做了重要的暗示。
与此前的科学家不同,苏格拉底第一个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美的问题,于是美善相乐,美与善的统一成了苏格拉底美学观的重要特色,柏拉图继承了美善同流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美的相对性的观点。在《大希庇阿斯》中我们似乎已分辨不出那些是苏格拉底的观点,那些是柏拉图的观点,但有一点,像“美是难的”“美是圆滑的”“漂亮的小姐比神也是丑的”等这些观点至少是柏拉图没有反对的。也就是说,在美的模糊性讨论这方面,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是大致一致的。而后来“更爱真理”的亚里斯多德则较少论及美的模糊性。亚氏对科学的博大精深影响了他对美的模糊性的探讨,他似乎更加肯定现实、经验,而诗人的想象就有翼而难飞了。
在中世纪,上帝代替了柏拉图的理式,人们把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绝对化和神秘化,从而重复着完整、和谐的希腊古调,只有到了但丁时代,才真正想出象征诗学。康帕内拉的《诗学》更把美的相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⑦,而这时中世纪已经结束了。
就像爱因斯坦时代唯一的一位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物理学家是玻尔一样,在牛顿时代唯一可与其相提并论的数学家就是莱布尼茨⑧。我不明白何以维柯、弗洛伊德可以成为大美学家,而莱布尼茨作为一个大美学家的地位却从未有人提及。我认为莱布尼茨在美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单子论,这不仅具有了模糊数学的思想⑨,而且从哲学上暗示了模糊美学的存在;从而,其次提出了意识的朦胧性与明晰性⑩,最后莱布尼茨提出了美的和谐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近代美学(至少是一个主要流派)是从莱布尼茨开始的。
与经验主义哲学同时,当时代表新柏拉图主义的夏夫兹博里及其学生哈奇生却站在了莱布尼茨这一边。尊敬的朱光潜先生曾经认为在笛卡儿时代维柯是孤立无援的,但这似乎并不符合事实,至少在研究美的模糊性方面,维柯是以新柏拉图主义和莱布尼茨做为先锋和同伴的。他的关于人类早期形象思维的观点,关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的观点,关于诗性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界说,从一个方面肯定了美的模糊性。
就在这时启蒙运动开始了。狄德罗等人部分地接受了莱布尼茨、夏夫兹博里的思想,使启蒙主义的美学带有一些模糊性质,这一点在莱辛美学中有独到的表现,于是德国美学的伟大时代到来了。
在鲍姆嘉通之前,莱布尼茨的信徒伍尔夫把莱氏的和谐发展为“快感的完善”,这种强调感觉的理论被鲍姆嘉通继承下来,于是他用感性学(Aesthetica)来定义关于美的科学。感觉从许多意义上就不如理性清晰,从此美学正式研究模糊性了。
首先站起来反对近代科学的完善无缺性的大哲学家是康德,然而这种反对是不彻底的,但康德毕竟指出了审美判断的许多不确定性(11)。
这时出现了同时兼有诗人和哲学家两种气质的歌德。他的作品显示出极为丰富多彩的个性。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就闪耀着模糊思想的光辉。黑格尔似乎对模糊性并不感兴趣,在他身上好像有一种类似科学家的哲学精确性,但黑格尔认识到艺术典型是“守一而应万”,是无定性的普遍性和有定性的特殊性统一到完美的无限,这又在事实上肯定了美的模糊性。黑格尔的《美学》,实际上可以看作他的辩证法在明晰与模糊关系中的应用。
从莱布尼茨到康德到黑格尔是西方古典美学的主流。此外,在黑格尔以后,还有德、意的叔本华、尼采和克罗齐,他们对现代派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现代派文学从主题、形象到语言、时空都比较模糊。
而俄国的别林斯基,特别是他的形象思维的理论,也闪耀着模糊美学的光彩。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著名的美学定义--“美是生活”,其具体内涵无疑也是模糊的。
再往下说就是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艺术有直接影响的四大美学家。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与卢卡契,弗洛伊德与柏格森,前二人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艺清澈如水;后二人为现代派文艺奠定了哲学与心理学基础,使现代派艺术模糊如云。清澈如水者,主题突出易懂,形象好坏分明;模糊如云者,主题多义难解,形象真假朦胧。
综上,我们通过对西方模糊美学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出,模糊美学并不像王明居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与传统美学有那样鲜明的对立,只是现代美学更能自觉地研究美的模糊性罢了。
注释:
①丹纳《艺术哲学》:“他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眼睛来说:有形的物体主要是一块块的斑点;……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受别的斑点影响的一个斑点;因此一幅画的主体是有颜色的,颤动的,重叠交错的气氛,形象浸在气氛中像海中的鱼一样。伦勃朗把这种气氛表现得好像可以用手接触,其中有许多神秘的生命;……他感觉到一大批半明半暗,模模糊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他的油画和版画上像从深水中望出去的海底世界。”(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页。)
②《雪莲》1982年第1期发表了阎萧的《试谈文艺作品中的“模糊成分”》,《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陈胜民、肖梅的《模糊思维在艺术中的表现初探》。
③王世德《美学新趋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有模糊美学方面的论文4篇。
④“在实际应用中,希腊人并不严格遵守这些数学规律,而是根据效果有所改变。”(参见李思孝《西方古典美学史论》,1992年南开版,第33-34页。)
⑤“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最聪明的人与神相比只是一只猴子,犹如最漂亮的猴子与人相比也是丑陋的一样。”(《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⑥“可怜的理智,你从我们这里获得信赖,又想抛弃我们吗?我们被抛掉了你也就垮台了。”(同上书。)
⑦“曼德里卡尔多说,他的摩尔人朋友们身上的伤是美的,因为这些巨大的伤口表明了刺伤者罗兰的伟大力量;圣奥古斯丁把在圣文琴佐(SanVicenzo)身上的剥皮和肢解痕迹也称为美,因为表明了它的忍耐力;相反,它们也丑的,因为这是暴君达蒂亚诺(Datiano)和刽子手残暴的标志(符号)。……任何东西都同时是美和丑的。”(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⑧〔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莱布尼茨(1646-1716)是牛顿同时代的人,在智力上是可与牛顿相匹敌的。……他不是牛顿的引力理论的赞同者,虽然这个理论在经验中得到了成功。但他不予赞同,因为他导致了一种运动绝对论。莱布尼茨发展了一种根据运动相对性观念的空间理论,在这种理论里他预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逻辑原则。……这证明他的唯理论思想并不肯在经验论的真理标准之前屈服。”(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版,第87页。)
⑨莱布尼茨关于单子连续排列的理论与现代模糊数学的隶属概念几乎是有着惊人的吻合。关于他的组成物质的单子没有大小而只有能量,与现在人们对基本粒子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这似乎更加可以说明他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超越了人类几个世纪。
⑩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莱氏提出了类似后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还有千千万万的征象,都使我们断定任何时候在我们心中都有无数的知觉,但是并无察觉和反省;……因此这种微知觉,就其后果来看,效力要比人所设想的大得多。……这种感觉不到的知觉之在精神学上的用处,和那种感觉不到的分子在物理学上的用处一样大。”(中译本,第8、10、12页。)
(11)罗·乔治:“康德认为,感觉是纯粹主观的,的确也是不可传达的:‘既然感觉不能被传达……’感觉就不许可有任何检验标准;关于感觉,每一个人在自身面前都是正确的”。(《国外康德哲学新论》,1990年求实版,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