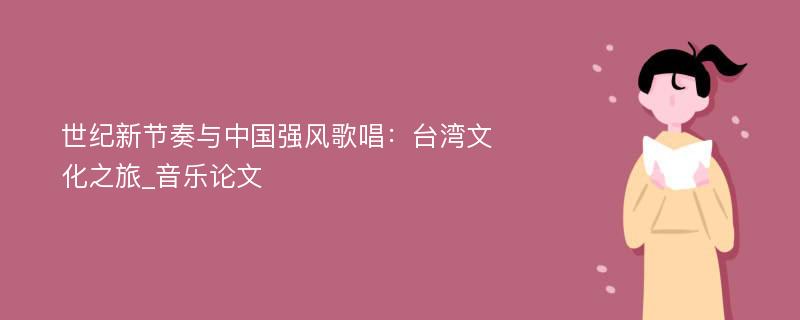
世纪传新韵 中华唱大风——台湾文化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台湾论文,中华论文,大风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鹅銮鼻,三面环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与浩瀚的太平洋水天相接,渺无涯际。海风扑面,海涛盈耳,携裹着世界风云五洲潮汛一齐奔来眼底。这,实在是一块最能启动艺术遐思的滩头。
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陈澄雄团长,把96华裔音乐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文化新韵,世纪展望”,其内蕴的象征意义确实耐人寻味。
作为由大陆应邀赴会的21位代表之一,我有幸以音乐评论工作者的身份参与盛会。然而我也没有忘记,作为记者,有责任将海内外音乐家对华夏音乐所作的“世纪展望”形诸笔墨,以便与广大关心中国音乐前途的朋友们互通心曲,共享忧乐。
一、渴望“合唱”
特定的时间(世纪之交)和特定的主题(世纪展望),使这次会议带有几分神圣的色彩,从世界现代音乐的角度观照华裔音乐,自本世纪初,由萧友梅、沈心工、李叔同诸位先行者发轫,从涓涓细流到潺潺小溪,如今已汇成浩浩江河。然而,现代音乐(尤其是交响乐)毕竟是从西方发源的,在世界音乐的大格局中,西方还处于君临天下的主导地位,而中国音乐家的声音还极其微弱。尽管近年来已有百多位华裔音乐家在世界各地陆续创出骄人的佳绩,但是,却像散珠碎玉,难成大势。多数华裔音乐家还只能靠加入“欧洲军团”或“美洲军团”来展现自己的才华,而华人乐团所经常演奏的曲目也很少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许多音乐家心目中的“华夏新韵”还远没有在世界乐坛上引起相应的回响。
来自加拿大安省华人音乐协会的陈其本女士,历数了他们在多伦多艰苦创业,宏扬与推介中国音乐的历程。在近20年中,他们荜路蓝缕,先后组织起华人爱乐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以演出中国音乐作品为己任:1983年他们公演了《黄河大合唱》,在海外引起轰动;1990年又成功地主办了中国音乐周;1991年还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专以介绍非华人作曲家所写的中国音乐作品的“东风西渐”系列音乐会;1994年,又邀请台湾省陈澄雄团长,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将中国作曲家黄安伦的交响名曲《巴颜喀拉》和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杰作《梁祝》,奏响在太洋彼岸……陈女士在回顾了这20年奋斗历程之后,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华人的音乐天赋,已经在西方得到了承认;但是,我们华人的音乐作品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形下,全世界华人音乐家,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也包括分居海外各地的华人音乐家,真该认真想一想如何携起手来,让中国音乐真正走向世界!
来自美国的廖英华女士,是现任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在茶叙时与我谈起了海外奋斗的艰辛。原来她的先生就是活跃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廖女士把一盘新近出版的田浩江专集《彼岸》赠送给我,她说,田浩江把他对祖国的全部思念都溶进了这盘歌曲集中。可是在海外,华人音乐家总感到势单力孤,什么时候,整个华人音乐界能够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气候就好了。
或许正因为人同此心,本届华裔音乐家学术研讨会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吧——旅美女作曲家陈怡,为了不误会期,不惜转机韩国,绕到台湾,于会议开幕的第二天深夜赶到了鹅銮鼻,按时发表了演讲;新加坡歌唱家林丽获得开会的消息较晚,但她依然要求自费赶来听会。来自各地的音乐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各有自己的看法,但在这一点上却可以达成共识:台湾省交响乐团能够不惜心力筹办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华裔音乐家盛会,进行“世纪展望”,确是具有远见的大手笔。人们渴望多有一些这样的“大合唱”的良机!
二、百年回眸
人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必然要回溯一下过往的路程,作一次深沉的“世纪回眸”。
许常惠教授是当今台湾音乐界的“大佬”,他从事音乐创作与研究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台湾现代音乐史的缩影。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显示了他在台湾音乐界的特殊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他演讲的论题恰好也是世纪性的《从百年来台湾音乐的传统与走向,试论传统音乐的维护与世界音乐的认识》。这位台湾音乐老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只是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情:搜集和整理台湾地区“原汁原味”的民歌,他把这些流传千百年的民间音乐,视为珍贵的宝藏。经他与同事收集到的民歌竟多至七八千首。其中绝大部分是台湾土著民族(现统称为原住民)民歌,汉族民歌只有二三百首。这些土著民歌记录了原住民的历史、社会和感情生活的丰富内容。在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部落里,这些民歌也就成了人们传递信息、保存历史记忆和进行传统教育的重要手段。当现代文明闯入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之后,许多民歌便迅速消亡了。而许教授当年不辞辛劳保存下来的民歌,许多成了“孤本”
与许常惠教授异曲同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梁茂春教授则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展开了对本世纪华裔音乐发展历程的“百年回眸”:从萧友梅、沈心工、李叔同在日本的早期音乐创作,到青主、杨仲子在德国、瑞士的开拓;从赵元任、黄自、李抱忱在美国的杰出探索,到马思聪、唐学咏、郑志声在法国的艰苦奋斗;从台湾作曲家江文也在日本崭露头角,到冼星海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写下的壮丽乐章;直到40年代谭小麟、萧淑娴在欧美,丁善德、张昊在法国所创出的佳绩。一个个沉甸甸的名字,一段段或柔美、或激昂、或轻快、或悲壮的旋律,把人们不由自主地牵引到中国老一辈音乐拓荒者在彼时彼地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听着梁教授条理分明的剖析和不时插入的音乐录音,我仿佛沿着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长河,见到他们步履沉重的身影。这些中国乐坛的先行者背负着重大的民族责任,求学于异邦,靠着勤勉与坚韧,用心血与汗水在异国他乡浇开了一朵朵中国音乐之花。尽管他们的早期作品中还留有明显的模仿西乐的痕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分明感觉到民族风格在渐行渐强在赵元任的《卖布谣》、江文也的《台湾组曲》、萧淑娴的《怀念中国》、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丁善德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在众多华裔作曲家的旋律中间,民族意识在觉醒、民族风格在形成,这是中国音乐在国际乐坛上奏出的第一组交响乐章。
就在梁茂春教授发表演讲的第二天凌晨,我约他结伴到海边去看日出。途中,我向梁教授发问:“您昨天讲到的只是本世纪前半叶华裔音乐的发展历程,那么,您对本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的华裔音乐前景,作何评价和预测呢?”梁教授略沉思后,慨然作答:“我对21世纪的华裔音乐充满信心。因为,本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大陆搞了改革开放,一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登上了世界音乐舞台。这批年轻的音乐家,足以同30年代到欧洲去的那批人相媲美。而且,这批音乐家的创作心态也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了。过去的华裔音乐家是去人家那里学艺,西方的音乐语言往往占着主导地位,即使作曲家采用一些中国音乐语言,音乐思维方式也还是西方的。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学生在国内已经学有所成,他们出国之后的创作,主要是在抒发民族情感,强调中国风格,表达的也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这种创作心态可以说是前人所没有的。这种变化看起来简单,其实很深刻,这是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
三、盛世忧思
百年沧桑的回顾,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华夏音乐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已超过了本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中国音乐家在乐坛上创造的优异成绩,被写进了高水准的国际音乐大赛的记录;一座座被公认是音乐殿堂的神圣舞台上,首次响起了华人音乐家的歌声和琴韵——这是几代中国音乐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啊,如今终于变成现实。然而,当人们从鲜花与掌声中逐渐清醒,一些有识之士却陷入了更深层次的困惑与忧虑之中……
当今的乐坛,“欧洲中心论”依然占有主宰地位。中国音乐的所有成功,都是以皈依(或曰服从)西方音乐的价值准则、美学标准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西方获得的成功越大,距离东方的、本土的音乐价值准则就可能越远。而就中国本土音乐创作与演出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君不见,众多的华人乐团(无论海内外)整天演奏着西方的音乐,而对中国音乐却不屑一顾?君不见,连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民乐,都在尝试依照西方交响乐队的编制重新排列组合,并以能改编演奏比才的《卡门序曲》或穆索尔斯基的《图画音乐会》为归依……
陈澄雄,这位毕业于音乐之都奥地利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对西乐有着深厚造诣的指挥家,同时又是一位曾作过7年国乐团团长、对中国音乐有着深刻领悟的民乐专家。这种特殊的经历给了他特殊的视角,使他有可能在五音乱耳的嘈杂声中,洞若观火,一次次地发出震聋发聩的警世之言——他说:“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交响乐团,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中国的艺术精神缺乏研究,甚至缺乏了解。比如指挥,我们的指挥大部分要到国外去学习,即使在国内,学的也是西方的那套理论。结果就造成一个怪现象:许多中国的指挥家,不会、不敢、也不情愿指挥中国的乐曲。他们指挥西乐如鱼得水,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全行;可是一遇到中国音乐就不知所措。这能算中国音乐家吗?”他说:“中国音乐人才,从小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和训练,把耳朵也训练得只会听西方音乐,而不会听我们老祖宗的音乐了。他听老祖宗的旋律,也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就说不准,其实是他的耳朵不灵了。我在台湾排演中国乐曲,有的演奏员就说,演中国曲子,就好像进了沙漠,渴死了。也有的团员要求我少演点中国曲子。我说,少演一点可以,但是不能不演,这是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作为一个中国的演奏家,你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一味地追求西乐,你在世界上就会漂泊不定,只有跟在西方人的后边做跟屁虫,永远也超不过人家!”
他说:“未来的21世纪,我们的乐团再不能一味地去做西方音乐的拷贝机、复印机了。中国的乐团要有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作品。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办交响乐团,难道就是为西方人做嫁衣裳吗?我的回答是不行的!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中国人的自尊。我们中国人的好作品,要争取先由自己的乐团来演奏。而且只有中国人的演奏,才会比外国人更好。因为中国作品的那种韵味,那种内涵,那种亲切的、血浓于水的感情,外国人终究是理解不了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外国乐团都在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可是我们中国的乐团却扶不上轿。难道让我们再去买外国人演奏的中国作曲家的唱片吗?那岂不是太丢人了吗?正因如此,我才不厌其烦的对大家讲:一定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认识和演奏中国的乐曲,这是关系到中国交响乐未来前途的大事啊!”
在我的印象中,陈澄雄的确是在不厌其烦地发出这样的警策之音,在北京、在深圳、在台北,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的忧思、他的焦虑,他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静与深邃,着实令人感佩。我时常想:或许正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音乐的深层矛盾,他才如此不遗余力地邀集全世界的华裔音乐家来作这次“世纪展望”吧?如果说,陈澄雄的“盛世危言”只是源自一位杰出艺术家的敏感直觉的话,那么,大陆理论家罗艺峰的思索则显得更加缜密更富于理性色彩。罗艺峰教授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其为人温文尔雅,其为论却峥嵘卓荦。他在会上的发言因时间关系差一点被取消,只是由于另外一位学者临时请假才又获准。然而,当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论点稍作铺排,其理论的穿透力立即令会场肃然。在这里,我只需依照现场录音摘出他的结束语,便足以窥见一斑了——
“我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危机,远比今天人们看到的要深重得多。无论是原先处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宫廷音乐、文人音乐,还是处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宗教音乐,以及被压抑到亚文化地位而只有潜历史的民间音乐,均已失去其生存、发展的条件。不请自来的西方音乐凭借其强势文化,移入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而西方音乐易于操作的知识体系,已在音乐制度和器用层面占据了话语权力的中心地位。因此有人指出,中西音乐实际上已经错位,并深入地影响到许多中国的音乐观,比如,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音乐教育及音乐文化中,已占有权威性的主流地位,这套理论体系不仅包括其具体的音乐声学、创作、奏唱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再如,中国的主体音乐史观还没有来得及与西方音乐史观进行公平或平等的对话,就被纳入了西方音乐进化史观的理论框架内,使中国音乐史观失去了自主地位……
而更深层的危机发生在中国的民间,尤其是农村。自本世纪初以“学堂乐歌”为开端的中国音乐西化运动,从政治、教育、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的层面,推向了任何一个穷乡僻壤,使这种保持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纵深处——一个战略性的文化后方——已在发生颠覆、发生质变,真正的本土民间文化愈来愈难以生存,人们的音乐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令人骇异的变化:陕北农民汇演中出现了电子琴伴奏的“信天游”;寺里用卡带播放佛教伴乐经文以充功课以及到处可见的卡拉OK大赛等等。这到底是谁的OK?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西方文化跨国复制的最佳工厂,我们实际上已经被当做“角色”来训练。当今后再没有人能唱苦音并欣赏苦音的时候,秦腔还能存在吗?当最富于中国文化色彩的不确定性操作再无人能理解时,几千年的古琴音乐还能生存吗?当中国民间无比丰富的音乐韵味、音色、音律、结构乃至抑扬顿挫,都被冷冰冰的midi机廉价地大批制造出来的时候,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活的生命其实已奄奄一息了!”
当罗艺峰先生用平静得近乎冷峻的语调,发出这一连串设问的时候,整个会场都像是陷入了沉思——是的,就当今的华夏音乐而言,眼下还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陶醉的时候!
四、溯源寻根
中国音乐向何处去?面对新世纪的呼唤,中国音乐家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才不至于迷失自己?中国音乐怎样才能在世界乐坛上争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每个华裔音乐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鹅銮鼻的会场上、海滩边,无论茶叙小憩还是晚间聚谈,大家谈论的中心总离不开上述话题。令人欣慰的是,许多音乐家不光停留在思考阶段,而且已经开始用创作实践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了。
年轻女作曲家陈怡是位引人瞩目的人物。她1986年从大陆赴美,数年之间写下了大量富于中国韵味与中国气派的交响乐作品,在西方获得包括美国国家文学艺术院作曲家大奖在内的十几个奖项,成为美国妇女爱乐乐团等四家乐团和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顾问。在会上,她向同行们介绍了在西方奋斗、探索直至获得成功的心路历程。我记得最真切的一句话是:“到了西方,同中国拉开了一段距离,才突然发现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是那么丰富,那么优美,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个音乐家能生在中国是多么幸运。”她讲话的声音很平静。而她当场播放的作品片段,则清晰地传递了中国民间音乐所给予她的丰富营养。她的管弦乐《歌墟》直接取材于广西壮族的传统歌节,并采用了苗族飞歌和彝族跳舞的原始素材,用管弦乐模仿出山歌的演唱风格和民族吹管及打击乐的演奏特点,其旋律与配器都令人耳目一新。而她为几家合唱团所作的《中国民歌大合唱》、《中国神话大合唱》及《唐诗大合唱》,更显示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浓郁风格。陈怡曾任广州京剧院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她对中国京剧音乐也十分熟悉,在她的代表作《第二交响曲》中,她就将京剧的曲调和打击乐融入交响乐语言中,使交响乐这种纯西方的音乐形式,平添了一股浓郁的中国古典情调。
老一辈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同样是位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七十高龄而拒绝守成,锐意创新,近年来创作出一些颇具前卫色彩的音乐作品。有人称他是西方现代派音乐在中国的代表,而朱老却说:我的音乐是真正中国的“土产”。在这次研讨会上,朱践耳先生在题为《兼容并蓄、立足超越》的专题发言中,演示了他的许多音响、旋律、乃至乐器的真正来源:原来都是直接采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瓦釜钟盘——最原始的往往就是最现代的,最土的其实正是最洋的——朱老的音乐实践,刚好为这一美学观念作了最好的注解。
大陆作曲家鲍元恺、王西麟与台湾作曲家阿镗都是中壮一辈的实力派人物,他们在交响乐的民族化方面都作了探索。鲍元恺的《中国汉族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发端而形成了他的《炎黄风情》系列,以原汁原味的中国民歌为素材,以正宗的交响乐为形式,中西融合,中乐西奏,不但令海峡两岸的华人如醉如痴,而且令外国人品味到了真正的中国风韵,他的探索无疑是为交响乐的民族化,走出了一条新路。而王西麟教授早年以一曲《云南音诗》饮誉全国,近年来,又在管弦乐融入中国西北民间戏曲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在会上,他为大家播放了他的近作《铸剑》的片段,雄浑、悲怆,其中的吟唱部分借鉴了山西上党梆子的音乐旋律。王向麟由此提出了他的一家之言:“中国交响乐的前途埋藏在中国戏曲音乐的大海里边!”
阿镗的音乐作品充满古典情怀。他为中国古典诗词和古代圣贤谱写的大量乐歌,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如他将《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岁老,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十字真言谱成大合唱,用最艰深的赋格技法,对此层层演绎,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宏大的架构。而他的另一首合唱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取自《易经》,以西方的复调技法,赋予简单的词句以回环往复的旋律,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阿镗的成功,与其说是单纯音乐的,莫如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成功。
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曲家从各自的立足点出发,探索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的途径,结果却殊途同归,都回归到中国民间的与传统的音乐源流上来,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它反映出中国作曲家溯源寻根的自醒与自觉。
记得五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为《寻找背景》。其中讲到这样一个观点:“一个艺术家要想成功,必须寻找自己的创作背景。”同样的道理,一个民族的音乐要想获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的权力,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创作背景。这个背景便是钟灵毓秀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上面提到的这些音乐家,无论从何处起步、从哪里取法,他们的成功,归根到底,全都得益于这个文化之“根”。
五、世纪展望
在中西音乐的对话中,西方的强势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展望未来,那么,东方的弱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成了特有的优势。譬如,西方音乐已有百年的历史,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其音乐资源的开发也近乎饱和。从技巧、旋律到音响、配器,都已很难找到一片无人涉足的处女地。本世纪上半叶,当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发现了流传于本国农村的农民歌曲时,他只须稍作开发便震惊世界,被赞誉为“联合起两个分裂的半球”(柯达伊语)。如今,在西方再想重复巴托克的奇迹,已经很难了。然而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30个省份,56个民族的民间音乐,基本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虽然如罗艺峰先生所说,近年来西方音乐文化已开始污染这片净土,但是比之于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这里的音乐纯净度显然要高出许多。这不啻是上帝为中国音乐家留下的最大幸运。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樊祖荫教授是著名的民歌研究专家。他在研讨会上播放了数十首由他和助手们采集到的中国民歌录音,以第一手资料否定了一直流传于中外音乐界的一种论点,即:中国音乐一直是单旋律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没有复调音乐。事实上,中国民歌、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民歌中,多声结构早已普遍存在,有些民歌已复杂到三、四个声部的混声合唱,表现出相当稳定的多声结构形态。这些凝结着劳动者世世代代音乐智慧的民歌,无疑为专业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音乐源泉。而这正是西方音乐所望尘莫及的。
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童忠良教授,本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对西方音乐具有深刻的领悟。然而他向大会宣读的论文却是绝对的“国粹”——《论曾侯乙编钟的对称乐学》。他告诉大家,这套制于2400多年前、共有65件编钟的大型乐器,竟然同现代钢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将全部编钟所发出的乐音按半音排列,中间三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全。由此可知,这是中国古代乐器中音域最宽、最完整、最早具有十二半音音阶的特大型定调乐器。而编钟上分别镌刻着的铭文(共3700余字),则准确地记载着各音的固定音名及其在不同调中的转换,涉及到大量的音乐理论学问题,因而有人称它是一部2400年前的古代乐学大全。我在音乐学上的无知,使我无法听懂童教授那一番极其深奥的“对称乐学”分析,然而,对他的结论却完全能够领悟——“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常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习惯于用现代普通乐理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传统乐理,致使我国某些特有的传统观念被生硬地纳入欧洲体系。这不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中华民族早在2400年前就能够制造像曾侯乙编钟这样精密、高妙的乐器,说明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大国。我们完全有能力、有理由建立起自己的音乐体系,来和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而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的音乐宝库,对于我们今后的音乐发展,其意义同样是无法估量的。”
童教授的一番话赢得了全场的掌声。在座的音乐家们不但从古代编钟上找回了民族的自豪,而且看到了一条通过研究开发古代音乐资源,走向世界乐坛的新思路。
作为本届研讨会的发起者,陈澄雄团长也对我谈起了他对21世纪中国音乐的预测和展望。他最先强调的是中国的乐器——“我想,音乐家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乐器了。我们的作曲家还没有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老祖宗留下的乐器注入新的生命,让它们发挥到最高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对世界乐坛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测——到了21世纪,国际乐坛上讲的就是光怪陆离的音响,而西方的乐器已经被赤裸裸的用光了,再也造不出阴阳鬼怪的音响了。只有中国的乐器有可能创造出来。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新音乐,势必要借助中国乐器的很多特殊音响效果。可惜的是,现在许多中国的作曲家还没有掌握它们。因此,我认为,作曲家要想走向现代,必须先回过头来认识自己民族的古典乐器,把自己的乐器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西方的乐器已经搞过头了,他们已经在向东方、向中国寻找新的音响了:你看,现在西方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有三分之二都是中国的乐器,像大锣、大镲都是中国的。可是我们自己手里端着金碗,却还向人家讨饭吃,这怎么行呢?”
陈澄雄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艺术的“纯种化”趋势——“我的另一个预测是,到了21世纪,地球将变成一个‘地球村’,一切都将国际化,不仅地域的界限、国家的界限将谈化,甚至连人种都很难保持纯正,因为国际通婚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到了那个时候,最珍贵的是什么?对了,是纯种——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包括音乐,都将以纯种为上。因为人类已经在国际化上走得太远了,势必要回到文艺复光时期。民族的艺术、原始的艺术必将重新抬头。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一定会标榜自己原土著原民族的特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这个音乐,别人没有,独此一家,好啦,你就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佼佼者,没人能和你比。若论音乐的民族色彩和保持的原始风味,中国真是得天独厚。在我们这里保存着最丰富、最原始的民族音乐,同时又保留着许多没有开发的古老乐器,这两者都是我们打天下的利器。如果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我敢肯定,21世纪的世界乐坛,绝对是中国人的天下!”
诸位音乐专家的滔滔宏论,给人以信心,给人以鼓舞,昭示着中国音乐的灿烂前景与光辉未来。我自叹自己的笔是拙涩的,无法尽录智者之言;我更恨自己的音乐知识是残缺的,无法悟透深邃乐理。然而,我庆幸自己能够跻身其间躬逢其盛,并且能够以笔作证——若干年后,当华夏音乐终于能够在世界乐坛上辉煌地奏响,当华裔音乐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徜徉于国际舞台之上,我们再来回视今朝,便足以欣然地自慰地讲:这一切不是早在那一年那一刻的鹅銮鼻上就已经展望到了么?
标签:音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台湾论文; 西方音乐史论文; 作曲家论文; 古典音乐论文; 民谣论文; 交响乐论文; 美国华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