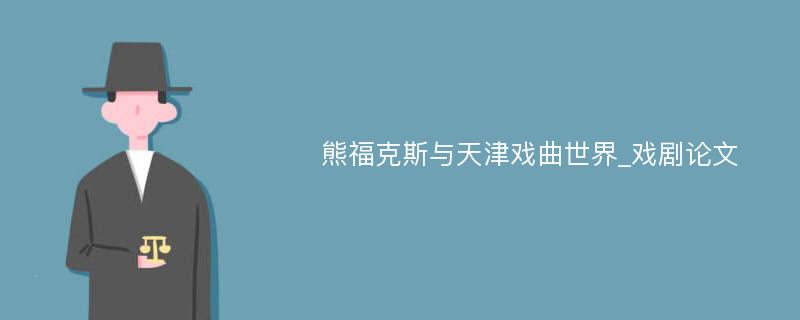
熊佛西与天津剧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天津论文,熊佛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戏剧家熊佛西(1900—1965),是我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批剧作家之一,有“北方剧坛泰斗”之誉;在二、三十年代,通过剧本与演出、文章与演讲,对天津剧坛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20年代初,现代话剧正处于从无到有的拓荒时期。熊佛西自“五四”以后,就奋笔创作,陆续写出了一批既有一定社会意义、又适于舞台上演的话剧剧本,适应了当时话剧演出的需要。1924年1月,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青春底悲哀》,是“文学研究会”编的“通俗戏剧丛书”第一种,它辑收熊佛西于1921—1923年间发表的4 个剧本:《新闻记者》、《这是谁的错》、《新人的生活》和《青春底悲哀》。它们以不同的题材,反映了作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而且“都是在北平及其他地方表演过而得成功的”(郑振铎:《青春底悲哀·序》);有的还传到天津,搬上舞台,如《新闻记者》等。独幕剧《新闻记者》是第一个在津上演的熊编剧本。首演此剧的则是邓颖超等领导的进步妇女团体“女星社”。1923年10—11月间,邓颖超等为创办妇女补习学校,特组织社员演剧筹款,选演的剧目之一就是《新闻记者》;此剧表现记者胡天民以“新闻”谋私,胁迫女青年马啸兰嫁其为妻而遭坚拒的故事,评击卑劣的强迫婚姻,赞颂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择偶,其题旨涉及男女婚恋与妇女解放,且剧本也写得颇有情趣。邓颖超很看重此剧,亲自主持排练,并串演剧中男角“周超群”(女主角马啸兰的表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她还请著名教育家马千里(也是南开新剧团的元老之一)到场指导。此剧先在达仁女校(邓颖超时在此校任教)试演,再行排练后于11月上旬在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正式公演。当月10日的《华北新闻》曾报道说,演出者“排演已三星期,极为纯熟,表演亦甚佳”。后来,南开(中学与大学)师生,也曾先后三次演出过这个独幕剧。
1929年9月,时任国立北平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的熊佛西, 亲率该系首届毕业同学演出组(包括章泯、王瑞麟等6 名毕业同学和特邀的几位女士共13人)来津公演;剧目有熊编的《一片爱国心》、《醉了》(又名《王三》)和丁西林的《压迫》等,皆由熊执导。这次演出,由于剧作富有时代气息,演员男女同台,并注重演技,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天津的大公、益世等大报,皆辟专栏、发专评。同年10月,熊带剧组回到北平之后,特在他主编的《戏剧与文艺》(1卷6期)上,刊出了一期《第一届毕业同学公演专号》,辑收文章30余篇;其中,有熊佛西写的3篇:《我们来津公演之意义》、 《我们的戏剧与天津民众》与《我们不是文明戏子》,着重说明开展新兴话剧运动的意义以及剧组到津演出的目的,并对天津观众的踊跃观演与热情支持,表示欣慰与感谢。“专号”中还收了天津报刊上的几篇剧评,对剧组的演出颇多赞赏之语;尤其是三幕剧《一片爱国心》,通过唐华亭一家围绕是否签订向日人出卖矿山权益的密约一事所展开的争论与冲突,谴责卖国行径,颂扬爱国精神。此剧一年前由南开女中部师生演出时,就受到好评:“诚佳剧也”(见1928年10月29日《南开双周》2卷3期)。这次由熊亲自指导,演出更为精彩,大公报的一篇剧评称赞说:此剧“句句说白,能打动观众心坎,处处动作,能触发观众热情,演到紧张处,真能叫人迸出泪珠来,这是何等高妙的艺术啊!”(聊止:《看了〈一片爱国心〉以后》)这次公演,对于熊的学生,是一次有益的艺术实践,而对于天津的新兴话剧运动,是一次积极的推动。
到了30年代,话剧演出从学校走向社会,演出团体日渐增多,剧目也更为丰富;而熊佛西则是其剧本被当时津门剧团选演最多的一位剧作家。在1931—1937年间,天津舞台上演出的熊编剧本就有10余个,有的还被几个剧团多次演出,如《艺术家》(“三八”女中学生剧团,1933年12月;南开中学学生剧团,1935年6月;咪咪剧团,1935年12月; 春笋剧团,1936年6月)、《王三》(孤松剧团,1934年11—12月间, 演出3次;喇叭剧团,1936年1月)、《喇叭》(喇叭剧团,1935年7月; 津市部分剧团联合演出,1936年1月)……这些剧目, 大多以城市生活为背景,描画不同阶层人的人世相;有的以“趣剧”的形式,讥嘲崇尚金钱、亵渎艺术的不良行径(如《艺术家》),有的以隐晦的笔触,剥露封建军阀的丑恶嘴脸(如《王三》),有的则直捷表现男女真情,激励青年勇于去打破旧礼教的“万恶牢笼”(如《青春底悲哀》)……,它们以互异的艺术手法,从诸多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时在津上演的,还有几部熊编“农村剧”。30年代初,党领导的左翼戏剧界大力倡导“戏剧大众化”,熊佛西热情响应,倾力实行;自1932年起,他辞去国立北平艺术学院的教职,到河北定县进行长达5年半的戏剧大众化的“实验”;除组织农村戏剧协会、 开展农村演剧活动外,还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民疾苦与抗争的“农村剧”。熊的“实验”与新编农村剧,受到津市传媒的关注:《国闻周报》自11 卷1期(1934年1月1日)起,分数期连载熊的五幕剧《牛》(又名《王四》),写农村破产与农民苦难;《大公报》1936年1月11 日出的一期“艺术周刊”,登载文章与照片,介绍了定县农村剧团公演熊编导的《过渡》(表现农民团结斗争,反抗地主压迫)的情况。而在剧界,熊编农村剧也一时成了“热门戏”。1934年4月28日, 天津青年会的联青社在该社礼堂演出《锄头健儿》,描写青年农民“健儿”破除迷信、烧庙除虎,抗击恶势力;1935年12月21日,津市部分剧社联演,剧目就有熊编的《屠户》(又名《孔大爷》),揭露农村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1936年10月18日,永生剧团在新新影院再演《屠户》……熊编剧本的多次演出,活跃了津门话剧舞台,也使参演者得到有益的艺术实践。在当时的参演者中,就有几位后来成为知名表演艺术家的,如谢天(即谢添,喇叭剧团)、孙坚白(即石羽,孤松剧团)和李保罗(鹦鹉剧团)等。
熊佛西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一生共编剧40余个),而且在戏剧理论上也颇多建树;天津的话剧工作者从他的论著与演讲中也获得启示与教益。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的“戏剧研究会”,在津市剧界颇有影响,它在1936年12月间的校刊《市师周刊》(37—39号)上,集中推荐了一批话剧剧本与戏剧理论著作。其中熊佛西编著的最多,除14个剧本(收于1930—1933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佛西戏剧》1—4集)之外,还把他的戏剧论文集《佛西论剧》(1928年北平朴社出版)列为戏剧理论的重要“参考书”。在30年代的天津报刊上,还刊登过熊佛西的多篇戏剧论文,如《单纯主义》(载1930年10月8日《大公报》)、 《再论戏剧批评》(载1934年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1卷2期)等;其中,有几篇文章,如《新生》(载1936年1月11日《庸报》)、 《从解放到新生》(《载1936年11月11日《大公报》)等,是作者对定县“实验”所作的理论总结,着重阐述了戏剧大众化的目的与意义,论说了自己从学院走向农村、面对大众的切身感受,读来感人,发人深思。熊佛西的定县“实验”以及关于戏剧大众化的见解,在津市戏剧界引起反响与共鸣。1935年,天津《庸报》副刊“另外一页”,自3月起,开辟专栏, 登载文章,开展关于“戏剧大众化”的专题讨论;有好几位剧界人士在讨论文章中肯定熊的“实验”与主张。司徒珂强调指出,戏剧能够“交给大众”,因为“现在已经有定县戏剧协会农村剧的演出给予我们一个大的证明”(《关于“戏剧与大众”问题的检讨》,载1935年3月4—5 日《庸报》)。有的论者更借熊的言论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如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出:要戏剧“大众化”,“首先应该明了的,自然是‘大众’的‘爱’与‘恶’”,接着引用了熊的“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定论”,即“农民不愿意听长篇的对话,喜欢听一个完整的故事并用动作表现出来……少说话,多动作!”进而申述说,“我以为凡从事于剧运的,都要先认清这个定论,然后,话剧才逐渐的大众化”(《对于戏剧界的一个苛求》,载1935年8月19—20日《庸报》)。
熊佛西在定县期间,还曾数次到津演说或参加座谈,讲授现代戏剧知识,推动天津剧运发展。1933年11月4日, 熊应邀到天津扶轮中学与女子师范学院发表演讲,讲题是《戏剧的表演》;他结合自己的实际体验,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话剧表演的理论与技巧,受到听众的欢迎。1935年3月,熊先于6日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作题为《中国话剧的前途》的演说,纵论中国剧运发展的趋势,提出繁荣话剧事业的建议;又于14日出席春草剧社专为他举行的茶话会,并在会上发言指出:“办剧社必须有毅力,要不怕挫折,应付一切阻力,坚持到底。话剧公演要有充分准备,公演就要成功。”熊还应聘担任春草剧社的顾问,指导该社的演剧活动。1937年3月31日,熊再次应春草剧社之邀,到津演讲, 题为《戏剧在文化上的地位》;是晚,又在该社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讲话,对津市剧运提出三点意见:大家要团结;工作要有计划;努力推行戏剧大众化运动。熊佛西曾在国外研习现代戏剧,又在国内从事戏剧工作,具有很高的艺术素养与丰富的编、导、演经验,因而他的几次津门之行,既“传”(授知识、谈经验)、又“帮”(出主意、作指导),这对于提高剧团的演艺水平,推进津门的话剧事业,无疑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通过剧本的上演、著述的传播以及亲身的宣讲,熊佛西已在抗战前的天津新文苑留下深深的印迹;而他在津城以外的戏剧活动,也成了文艺报刊的注视点而时予报道。如天津的《北洋画报》,在1286期(1935年8月22日)上, 以彩照与文字介绍了熊与杨村彬(熊的学生)导演的《伪君子》等剧在北平几家剧场演出的情况;1532期(1937年3月23 日)刊出题为“熊佛西编导的《莫里哀》之一幕”、“熊佛西与《赛金花》演员”两幅照片,并在1534—1535期上连载了熊编剧本《赛金花》。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大公报》在1931年的一期“艺术周刊”上,登出过一帧熊佛西的影照,其下题“老佛爷”三字(熊的名字中有一“佛”字),这是当时剧界人士对熊的一种亲昵的戏称;另一是,1936年7月,《北洋画报》社趁该刊创办10周年之际, 特邀几位文化名人分别撰写总结10年来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的专文,其中《十年来的话剧运动》一文,就是由熊佛西执笔,并载于该刊1422期(1936年7月7日)。由上可见熊佛西当年在津门文化界不凡的声誉与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