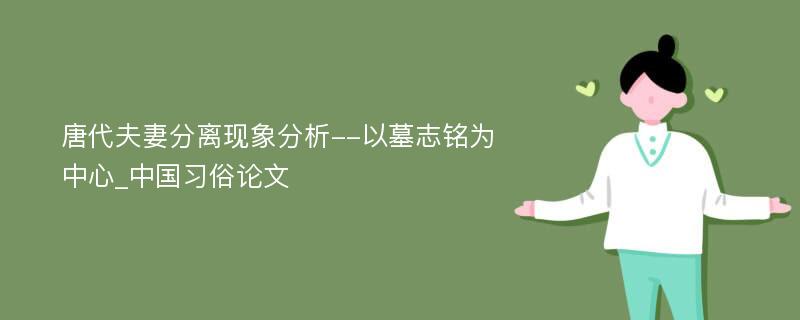
唐代夫妻分葬现象论析——以墓志铭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铭论文,唐代论文,现象论文,夫妻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2-0011-05
夫妻合葬是唐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纳入到了“礼”的范畴,所谓“生有异室之和,死遵同穴之礼”[1]。《唐律疏议》也云:“伉俪之道,义期同穴。”[2] 然而,我们在阅读墓志时却发现了不少夫妻分葬的现象,为何在合葬这一主流趋势下会出现一些相反的社会现象——夫妻分葬?是何原因让这些夫妻不愿死后同穴?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唐代的丧葬文化,而且有助于从另一层面来解析唐代的夫妻关系。
运用墓志材料来研究唐代丧葬,学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学者们一般集中在合葬、归葬和招魂葬方面的研究①。有关唐代夫妻分葬现象,焦杰、严耀中、陈弱水等先生也都注意到了佛教信仰对合葬习俗的冲击②。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影响唐代夫妻分葬的因素实际上并非佛教一项,而是多元的。本文欲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唐代夫妻分葬的其它文化因子,如道教信仰、妇女无子或早死、再嫁、占卜和时辰禁忌等。
一、道教信仰
唐代妇女以佛教信仰为由,常常拒绝与丈夫合葬,这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除了佛教这种异域文化对唐代夫妻合葬习俗的冲击外,我们还注意到本土宗教——道教对于唐代夫妻合葬习俗的干扰。如卒于神龙三年(707)的郑道妻李氏:
及诸子冠成,遂屏绝世事曰:吾平生闻王母瑶池之赏,意甚乐之,余可行矣。是乃受簶,学丹仙,高丘白云,心眇然矣。晚年尤精庄老,都忘形骸,因曰:“夫死者归也,盖归于真;吾果死,当归于真庭,永无形骸之累矣。”神龙三年七月,终于河南之私第,时年七十七。夫人有遗训曰:“合葬非古,始自周公,淳真之道微矣。汝曹无丧吾真。……即以景龙元年(707)十二月廿六日窆于北邙之平原,奉遗训也[3]。
李氏遗言,因为自己信仰道教,要与丈夫分葬。尚舍直长薛府君妻裴氏,丈夫亡后, “聿备三善,腾心八解,金仙圣道,味之及真,外身等物,不竞以礼,放迹远俗,谓为全生,凝神寂冥,块然而往。春秋五十有九,以开元十三年(725)五月廿三日考终于通利之里第。……先是遗付不许从于直长之茔,以其受诫律也”[4]。从志文描述的内容看,裴氏信仰道教,遗言与丈夫分葬的理由是已受戒律。安国观女道士虚明,丈夫去世后,“遽捐俗累,归于道门”;以大中十三年(859)卒于安国观精思殿西隅道院,“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景业村,不祔于柳氏,盖从教也”[5]。也因为道教信仰而不与丈夫合葬。
由此可知,道教信仰仍然对夫妻合葬习俗构成了一定冲击。结合佛教影响下的夫妻分葬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宗教信徒在死后的世界里,追求的不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自己的精神信仰,她们的选择超越了夫妻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宗教教义有关。佛教、道教反对结婚③。因此,这些信徒死后,要继续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应该保持单身形象,而不能违反教义——死后仍然与丈夫或妻子保持夫妻关系。如前述女道士虚明,不与丈夫合葬的原因就是“盖从教也”。宦官韩国信不与妻子合葬,也是“以君遗命,茔域攸同,封穸云异,遵释氏也”[6],即遵从佛教教义。还有一些墓志直接云,因为“戒行”而不能夫妻合葬,如赵璧,丈夫死后,“归依法门”,临死前,“以府君倾逝年深,又持戒行,遗嘱不令合葬”[7];卢璥妻李晋,“崇信释典”,临终遗言:“不须祔葬,全吾平生戒行焉。”[8] 以上事实表明,无论佛教信徒还是道教信徒,宗教教义是导致他们夫妻分葬的深层原因。
二、妇女无子嗣
没有子嗣也是干扰唐代夫妻合葬的因素之一,因为女人与男人不同,男子无论有无子嗣,死后都可以葬在自家族莹。而女子则不一样,她长大后要经历一个出嫁过程,离开本家。因此,一旦在夫家没有生育子嗣,这有时候就可能影响到她在夫家的地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子嗣甚至成为男子出妻的正当理由,唐令将之列在七出的首位[9]。社会观念和唐令的规定,使没有子嗣这一情况自然而然地成为阻碍夫妻合葬的因素之一,墓志中也有相关事实的反映。
卒于贞元十二年(796)的蔡州司法参军翟氏妻萧十九娘,卒后,“权窆于县南郭。以无子息,至永贞元年(805)十月十九日,归葬于偃师县石桥店东北本家大茔之侧,礼也”[10]。卒于会昌元年(841)的薛公妻董夫人,临终“有遗言曰:吾无子承继,勿葬吾于夫之茔。卜地于我家先茔之侧”,故死后家人按照其遗言,将其灵柩安葬在本家坟茔[11]。卒于大中二年(848)的郑德柔,丈夫司马鱼君“雅有词学,每悼其嘉配倏然,不克有嗣。会离荣谢,宛如一寐,伤神之苦,几不胜怀。以其年十一月十日,从郡君灵车,葬京兆府万年县崇义乡白鹿原。未归夫族,附女氏之党,礼也”[12]。这是丈夫根据其没有子嗣的情况,主动将其灵柩送回本家坟茔的。张国刚先生认为,“按照古礼的规定,如果新妇不庙见,将不算完成了成妇之礼。没有通过庙见的儿媳妇,如果突然夭亡,就不能葬在夫家墓地里,而必须回本家落葬”[13]。但是这种新妇,一般仍然没有子嗣,如张先生所举崔攀的例子,其“年十有九,归于荥阳郑宾,未及庙见,而婴沉痼”[14]。崔攀同样没有子嗣。
可见,部分没有子嗣的妇女,有时会导致她们死后回归本家坟茔,与夫家脱离联系。而且,这一举动在唐人看来是一种“礼”的行为,故志文结尾常云“礼也”,而不是无所根据的举动。当然,我们要看到这只是构成阻碍夫妻合葬的因素之一,而不是说没有子嗣的妇女必须夫妻分葬。
三、早死下的亡灵禁忌观念
古人对于死后世界有一番特殊的想象,认为亡灵世界与现实人生差异不大。故而在埋葬死者尤其是进行合葬时,唐人有一定的观念禁忌,就是尽量不要打搅早已安寂的亡魂。如果违背此原则,他们就可能会主动放弃合葬的意图。如卒于开元廿五年(737)的李勖,夫人卒于宝应元年(762),二人死期相隔近25年,家人“以其年扶护归都,卜地迁合,爰择吉日,用启旧茔,伏见玄堂之中,根蔓萦覆。时有阴阳人卢皓云:久闻贤达所传,此则神理保安,不合惊动。遂以其年十一月十四日祔葬于旧茔之右”[15]。这是家人在安葬夫人灵柩时,发现李勖墓已经长满了植物,这是“神理保安”的征兆,不能惊动,于是家人放弃了合葬的想法,将夫人葬于李勖墓侧。张氏,丈夫左骁卫将军独孤袆之“早世”,夫人卒后,天宝八载(749)“十一月十八日归葬于高陵奉政原,去羽林府君之茔四里,盖以远日非便,近祔从宜”[16]。所谓“远日非便”,无疑是指独孤府君早死,合葬不宜。卒于天宝十载(751)的崔夫人,丈夫去世时年仅二十九岁,“初府君之殡也,近在洛阳,距夫人之丧卅余年矣,虽鲁人之祔,宜恭行于典礼;而滕公之室,惧多历于岁时”[17]。也害怕打开这些埋葬时间久远的坟墓,故实行分葬。卒于宝应元年(762)的宦官高力士,正妻吕氏,“天宝中封齐国夫人,方贵而逝。封树已久,安而不迁”[18]。齐夫人因为去世时间久远,坟墓“封树已久”,因此,高力士与其分葬。卒于会昌六年(846)的军器使推官赵文信,“夫人辛氏,贞元十二年(796)而殁,先公谢世五[十]年矣。公尝曰:合葬非古也,况年代深远,鬼神好静,不须开发。今别茔焉,遵遗命也”[19]。赵文信留下遗命,因为妻子辛氏去世已有五十年之久,“年代深远”,不与之合葬。
上述事例表明,如果夫妻一方早死,埋葬时间过久,在另一方死亡后,出于打搅亡魂的观念禁忌,就可能放弃合葬,而实行分葬。
四、再嫁
再嫁之女子,由于其一生不止一个丈夫,因此,死后该如何埋葬?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然而,有关唐代再嫁女子的墓志材料极为有限,大概有十方④。在这十方墓志中,只有一方墓志,即《大唐故江王息故沣州刺史广平公夫人杨氏墓志》其题名署的是前夫,其余全是署的后夫。志文载:
属唐祚中缺,宗族播迁,公谪南陬,敕降西掖,爰及外氏,命离夫人。夫人赴镬道亡,从义守节。父恭荷造,旋乃迫离,胁夺志怀,改醮胡氏。君父之命,难以故违,闵夏之礼,或释其道,因兹遘疾,久积缠痾。返香无征,暮华有限,呜呼!以开元十九年(731)六月六日,薨于鼎邑殖业里私第也,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其年月十九日葬于洛阳县清风乡北邙山之原。二氏各男,绝浆泣血,卜远申议,别建封茔,拜享之仪,俱得其礼[20]。
杨氏前夫是皇室成员,因政治缘故被迫离婚,故夫人死后墓志题名归属前夫,可以理解。但是最后的埋葬地点上,子女们却给她选择的是独葬——不与任何一位丈夫合葬,或者葬在任何一位夫家的墓地,显示出对于这样一位再嫁母亲墓葬的独特处理。
其余9方墓志显示出来的信息是,再嫁之女子,归属后夫,死后与前夫分葬。如卒于天宝十载(751)的郭班,“年甫十六,适于常山阎府君,有一子焉。不幸府君中年早逝,叔父夺志,更醮张门”。郭班改嫁后,没有给后夫家生育孩子,死后,“嗣子仅等号天泣血,叩地摧心,永惟同穴之仪,未卜归祔之典。即以其月廿二日权殡于洛阳县平乐乡之原,礼也”[21]。此“嗣子”指郭班前夫之子,为何阎仅伤痛母亲不能与父亲合葬,无疑母亲改嫁是原因的关键所在,但是他也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习俗。又卒于会昌四年(844)的刘夫人:
笄年适南阳张公讳闰。有子一人曰勍。夫人夙著内则,方勤中馈。未几,府君先世,……无何,父兄悯其稚,遂夺厥志,再行乐安孙公讳伯达,有子曰毅。不幸良人复早亡而嫠居,待养者久之。南阳之嗣,卒以善积庆钟,年甫弱冠,惕然有游艺依仕之志,□壮室负书西去,举学究一经科。会昌元年(841),擢登上第。既□走□洛师拜省夫人,惧孙孤不能慰安于晨昏。乃拜迎以归,□其就养。今则迩于宦,屈指而荣禄将及。夫人□□□于戏!夫人生之辰艰阨如是,孤子勍号痛不得以夫人祔于先人者,拘其典礼之谓也。乃于邙山之趾相土而得吉兆,即河南县平乐乡王寇村也[22]。
刘夫人先嫁张闰,后改嫁孙伯达,为前夫生下一子张勍,为后夫也生下一子孙毅。张勍后来科举及第,将母亲迎回家赡养。但是当母亲去世时,其“号痛不得以夫人祔于先人者”,即刘夫人的前夫,志文云是“拘于典礼”,即当时的社会习俗——再嫁之女子不能与前夫合葬。因为女子再嫁,便表明她已经“移天”,也就意味着与前夫恩断义绝,便永远地丧失了与前夫合葬的机会。那是否意味着她应该葬在后夫家,或者可以与后夫合葬呢?墓志材料中,我们见到了一则葬在后夫家的实例,那就是卢全寿夫人陈照,其先嫁东海徐文公,后改嫁卢氏,死后以天宝四载(745)十月廿五日“归厝于河南之邙山卢氏先茔。以域内更无坟地,遂卜兆于平乐原”[23]。传统文献中的一则实例也表明再嫁之女子当葬在后夫家。安定公主:
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龙时,又嫁韦濯。濯即韦皇后从祖弟,以卫尉少卿诛,更嫁太府卿崔铣。主薨,王同皎子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铦曰:“主义绝王庙,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将拒诸泉。”铣或诉于帝,乃止。铦坐是贬泸州都督。[24]
夏侯铦强调安定公主再嫁是“义绝王庙”,而最后嫁与崔氏便“恩成崔氏”,因此,死后的归宿理应是崔家,而不是与第一位丈夫合葬;而且崔铣也就此事向皇帝诉说,最终,王同皎与安定公主合葬之事以失败告终。可见,在时人眼里,再嫁之女子是没有资格与前夫合葬的。但是,她们可以选择回归本家坟茔⑤。
这些事例表明,再嫁之女子与前夫分葬,已经成为世俗普遍接受的观念,在实践中也是严格遵守的。这与男子不同,再次娶妻的男子,他的所有妻子一般而言都葬在他家的族莹,尽管不一定每一位妻子都与之合葬。然而女子一旦改嫁,便丧失了与前夫合葬的机会,也不一定能够与后夫合葬。这一埋葬现象的差异,反映出男女性别等级上的不同,即女性地位明显不如男性,女性最后的归属只能是一位男性,因为她的“天”只有一位,而不能同时有两位。一夫多妻的男性则不一样,他可以与多位妻子合葬,因为他是这所有妻子的“天”。
五、占卜和时辰禁忌
唐人在夫妻合葬时,往往要先行占卜,寻求一个指示性的吉凶意见;然后再选择吉日,进行夫妻合葬。如果卜相显示出一些不吉利的兆头,则会保持暂时分葬的状态。如卒于天宝八载的高琛,前妻杜氏和继室杨氏都比他先亡,高琛死后,“今以五胜相推,六甲躔次,询于卜筮,以定月时,而由象有差,合祔非吉,且仍旧贯,以俟他年”[25]。由于卜相不吉,因此,家人未敢实行合葬仪式。终于乾元二年(759)的陈府君夫人韩氏,以其年二月朔十七日,“归葬于清风乡原大理正之茔侧,爰考龟筮,未从祔礼”[26]。也要等待占卜后,才能实行合葬。卒于贞元四年(788)的监察御史裴涚,“夫人兰陵萧氏,先府君而殁。卜不云吉,合祔未期”[27]。因为占卜不吉,无法选择合葬时间。卒于大和二年(828)的杨士真,“夫人太原王氏,不幸早终,蓍龟所占,合祔未便,同茔异穴,以俟通时”[28]。也是因为占卜结果不良而保持分葬状态。卒于咸通十三年(872)的郭克全,夫人宋氏,先公而死,“公及夫人,岁月非宜,未遂祔葬,且异窨焉”[29]。这是没有择到吉日而分葬的例子。
唐人在丧葬中如此关注占卜和择日,这一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唐朝中央官僚机构设有太卜署,归太常寺管辖,太卜署有“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丞为之贰。其法有四:一龟,二五兆,三易,四式。皆辨其象数,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凡国有祭祀,则率卜正、占者,卜日于太庙南门之外”[30]。唐代,翰林院还供奉着一批相工、占星之人[31]。这些占卜机构的设置,以及皇帝周围也聚集着大量占卜人员的本身,对于民众的方术信仰提供了一个榜样和示范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普通民众的方术信仰,这是当时丧葬中流行占卜择日的文化大背景。
综上所述,影响唐代夫妻分葬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思想信仰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约定已成的社会习俗和实际生活中的观念禁忌。在以上诸因素中,占卜和时辰禁忌不是夫妻分葬的决定因素,因为,一旦占卜吉利,并择得吉日,便可以实行合葬大典。宗教信仰往往让妇女做出一些超越夫妻关系的理性选择,将精神信仰作为她的亡灵归宿。无子嗣死后回归本家坟茔、早死分葬、再嫁与前夫分葬,这些社会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仍然是一种社会习俗和观念。可见,在主流文化——夫妻合葬的大背景下,唐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一些次文化的潜流,它们不停地对主流文化构成冲撞。而正是这些次文化,才让唐代的夫妻关系呈现出多元性,丧葬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注释:
① 太田有子《古代中国にゎける为夫妇合葬墓》,《史学》49.4(1980年3月);加藤修《北魏から唐代の墓志に见る夫妇合葬の分析》,《女子美术大学纪要》31(2001年3月)。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年第4期;朱松林《试述中古时期的招魂葬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四章“琴瑟之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段塔丽《从夫妻合葬习俗看唐代丧葬礼俗文化中的性别等级差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② 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97页;严耀中《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481页;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第187-188页。
③ 郑显文先生认为:“道士、女官、僧、尼等在唐代被称为出家人,属于特殊的阶层,依佛、道戒律,不合婚娶。唐代律令中没有关于禁止出家人结婚的规定,但是在唐代关于佛教、道教的法规性文件《道僧格》中,却有这方面的内容”。作者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见郑显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④ 分别见于《汇编》长安037,开元047,开元306,开元327,天宝074,天宝108,天宝183,元和139,会昌035,大中160,转载于苏士梅《唐人妇女观的几个问题——以墓志铭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4页。
⑤ 如《汇编》开元047中的李夫人,第1186-1187页;《汇编》元和139中的赵氏,第2047-20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