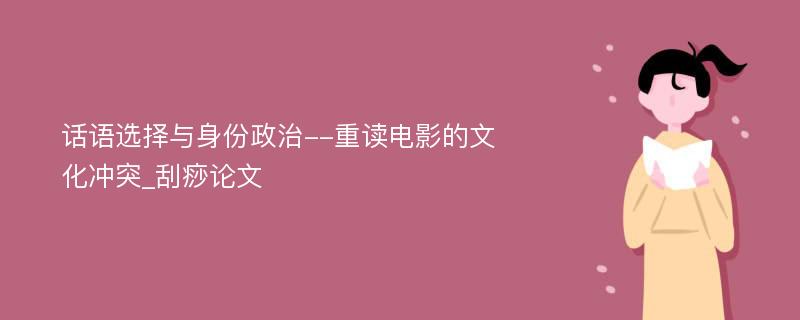
话语选择与身份政治——重读电影《刮痧》的文化冲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冲突论文,身份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产电影《刮痧》,作为2001年度国产精英电影之一,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主题,传统的叙述手法,引发了国内学界对跨文化主题讨论的热潮。影片展示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对美国文化不甚精通,但事业小有成就,并决心融入美国生活。大同之父,一位传统中国老人,在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引发了一场中美文化关于刮痧的冲突。影片中明显的文化冲突主题受到了国内评论界的追捧,据中国期刊网统计,2002年至2004年期间,全国各类期刊共发表《刮痧》评论文章20余篇,但几乎都是围绕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展开。比如,思齐指出影片展示了中美文化关系的冲突[1];而张伯存认为影片在全球化背景下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情感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冲突[2];张江艺则坚持文化冲突是由于对人权的文化差异造成的[3] 等等。文化主题的市场热销,不必要地牵制了批评的视角,使得学界对于《刮痧》的理解仅局限在文化冲突。因此,本文从分析刮痧疗法的文化意义出发,运用当代西方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理论,超越对文化和文化差异的传统理解,挖掘刮痧在身份政治中的神话意义,探讨文化选择与身份政治的关系,为影片提供一种文化身份阅读的全新视角。
一、刮痧与文化冲突:解读刮痧的文化神话
影片中文化冲突的焦点就是刮痧疗法的合法性问题。从始至终,刮痧问题就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刮痧是中国传统的医疗方法,但是所有美国人就是无法理解刮痧,而将其视为暴力和虐待。随着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美国人可以理解或宽容中国文化的异质部分,比如,美国辩护律师为许大同对医院先救生产困难的爱人的要求做辩护;大同的美国老板虽然无法理解,但至少可以容忍大同当面教训儿子;控方律师可以认识并欣赏孙悟空形象,虽然他在法庭上不得不断章取义,有意丑化中国文化以图激怒大同并打赢官司;黑人法官对大同的中国式爱子呈述尤为感动,然而他们终究无法理解作为医疗方法的刮痧。许大同也无法从西方学界找到任何为法庭所认可的英语资料,用于证明刮痧的疗效。但是西方为什么就不能像对待其他中国文化符号一样理解并尊重刮痧呢?实际上,不是所谓的文化差异引发了刮痧的文化冲突,而是中西方的文化话语决定了刮痧的不可翻译性,使刮痧最终成为中美文化交流中不可逾越的文化神话。
“神话”,学者罗兰·巴特尔认为,是“一个纯粹的表意系统,其形式仍然由表征的概念所决定,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表征的所有可能性”[4]。由此看来,神话不仅是“意指”的符号形式,同时也是表征的意识形态,其意义不完全确定,也无法被穷尽。神话时真时假,“只有神话的读者个体才可能也必须解释其主要意义”[4](P127,P128)。然而,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即便是同样形式的神话,也会具有不尽相同的“意指”,表征迥异的文化意义。因此,刮痧作为文化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中国文化的常识性知识,而对于美国人来讲,却代表着文化他者的暴力与野蛮;对于中国移民而言,坚持其合法性和人道性,无异于认同和捍卫中国文化,对于美国人,忌讳和禁止刮痧,意味着排除中国异质文化的影响,巩固其“中心”和“权力”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中美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中美文化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比如说,中国文化崇“感”尚“度”,而西方文化重逻辑和推理,不是因为中国传统医学重视“阴阳调和”概念,而忽视西方的“解剖”和“外科”实践等等,而是中美两种文化对刮痧神话解释权的争夺,是美国“东方主义”话语和中国“汉化”意识在刮痧问题上的一次正面交锋。
美国文化对刮痧疗法的态度,似乎非常公正和理性,只要求许大同能从英文资料中证明刮痧的效用,便承认其合法性。实际上,对刮痧的指控过程中,毫无公正可言,只有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和彻头彻尾的话语运作。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福科解释道:“权力生产知识,并不是说权力以简单的方式鼓励知识的产生,而是由于知识侍候着权力,或者运用着权力;权力和知识直接关联;没有脱离相关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离开权力关系的任何知识形式。”[5](P127) 由此,刮痧的合法性便成了权力运作的焦点。刮痧疗法,用许大同父亲的话来说,在中国被用了几千年,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常识,但是为什么一来到美国就违法了呢?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国的医学实践,未曾为西方医界所承认;仅仅是因为无法从英文资料找到证明材料,而西方医学也未有刮痧实践,刮痧就被认定为非人道的虐待;只是因为刮痧在美国医学界没有知识记录,美国法律就认为刮痧不合法。事实上只要美国法律禁止刮痧在其境内的实践,刮痧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更不用说是合法地位。刮痧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必须要在深有成见的美国文化的规则和指导之下,这是典型的“军规22条”的逻辑,荒唐的逻辑,毫无逻辑的逻辑。
这种对异质文化的边缘化,在肖哈特(Shohat)看来,反映了“主流群体的一种幻想,认为其自身是普适或精英的美国民族,超越任何其他少数族裔”[6](P215)。为了将美国中心与文化他者区别,巩固中心的权威地位,美国主流文化早已从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对“东方”和“西方”做出明确的界定。多元文化政策,鼓励文化的多元发展,尊重个体的文化选择,但是无形之中,对文化差异的关注也得到了加强。尽管多元政策提倡主流和族裔文化的和平共存,但它并不能消除“中心”与“他者”的二元对立逻辑,也不能彻底改变族裔文化的边缘化状态。如果某些异质文化符号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理解并消化,它们就会改头换面进入并装饰美国文化;如果它们像刮痧疗法一样,超出美国文化知识范围,并对其文化中心地位造成威胁,那它们无疑会被驱除出境或遭到压制。回顾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西方主流文化总是在借助经济文化力量,介入知识系统的建构。东方主义意识便是其特殊产物。东方主义,源于区别“我们”和“他们”的方法论需要,演变成民族中心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特殊形式,成为西方中心统治并控制东方他者的知识工具。因此,怎样理解刮痧神话,决定了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建构。很显然,是美国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而决不是刮痧本身的含义或者文化的差异,决定了美国文化对刮痧神话的理解,对刮痧“虐待”情节的认定。在权利和知识的运作过程中,刮痧和中国文化作为“无力的”他者,根本不能给自己做实体的界定,只能成为一个浮动的能指符号,等待美国中心文化的知识介入;而美国主流文化,控制着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建构,像一个超级的能指符号,决定任何相关知识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然而,即使美国文化占据着中心和权力的位置,控制着知识话语权利,处于文化边缘的中国文化,却不会那么容易屈服于文化霸权,放弃其自身的种族话语体系。著名文化学者康拉德(Conrad,Kottack)教授就曾指出,“种族主义是一个普遍文化现象”[7](P96),也就是说,“中心”和“他者”的地位只是相对而言的,而绝不是先验的存在物。因此,类似西方文化,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同样存在着其种族话语,具有特定的标准判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野蛮。换句话说,中国文化也具有区分“我们”和“他们”、“中心”和“他者”的知识体系。华裔学者吴一湖(David Yen-ho Wu)解释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情节:“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定义简单而明确:那就是一种属于伟大文明的归属感,以知识精英的标准规范言行……‘汉化’意识是唯一可能的结果,野蛮的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8]。
显然,中国文化对“二元对立”思维并不免疫,中国移民的文化记忆更不会被美国文化轻易地给抹去。正如文化学者苏福朗(Sufran Williams)所言,“即使没有任何民族宗教,任何政治体制的认同感,没有统一的民族身份,甚至没有在中国长期居住的经历,但是汉化思维,作为对民族整体特性的确认方式,事实上已经是维系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灵魂的理想家园”[9]。对于许大同来说,刮痧文化冲突的发生,标志着他对文化记忆的回应以及对文化身份的体认,同时也迫使他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对他来说,“汉化”意识, 就“像所有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一样,可以为散居者、祖国、异国用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目的”[9]。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大同逐渐远离了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利用“汉化”文化逻辑,从“他者”地位挑战“中心”,或者用萨特的话来说,是“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在大同看来,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文化他者”,因为他们连刮痧这样简单的道理竟也理解不了,还毫无根据地指控自己暴力和虐待。刮痧的冲突,如果还没有让大同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对立,那至少已经让他意识到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他来说,那些不能理解刮痧和孙悟空形象的人,肯定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也是一无所知,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异己,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大同最后的心态,让人想起作家王蒙在《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与中国人》里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华人)和欧美人互为主体和他者,在许多代中国人眼里,中国才是主体,而欧美人正是他者异类……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永远是‘他者’”[10]。
因此,“二元对立”思维乃是普遍文化现象。在文化冲突之中,斗争的方向也是双向的,强势的美国文化掌握着话语权利,进行事实上的知识控制,而弱势的中国文化,脱离自身文化语境,只能进行玄学意义上的文化抵抗。在中美文化的对抗中,刮痧疗法成为无法翻译的文化符号,因为在文化冲突中,任何文化符号都必然是权力关系的承载物,必然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神话。神话的意义,不是简单体现了文化冲突中文化能力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西方东方主义话语与中国“汉化”思想的对立。由此看来,文化神话的形成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文化政治:不是刮痧原本无法翻译,而是因为文化权力的操纵下,刮痧变得无法翻译。刮痧不可翻译的文化神话中体现出了两种文化权力运作的斗争,但是从深层次来讲,也体现了文化神话与身份政治的共谋关系,这也就是刮痧不可翻译性的终结原因所在。
二、刮痧与身份政治:文化记忆与主体认同的冲突
中美文化差异中蕴含的权利政治创造了刮痧的文化神话,也造成中西文化种族话语的对抗。两种文化都试图垄断刮痧神话的知识建构,从而控制文化话语权力。对两者来说,刮痧本身具有的技术或医学意义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其文化和身份在玄学意义上的意指,也即刮痧神话对身份建构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刮痧神话不仅是两种文化种族意识的主战场,也是两种单一性集体文化身份对抗的直接体现,而对于移民个体来说,则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记忆与文化选择之间的冲突。
“集体身份”,根据哥劳斯伯格(Grossberg Lawrence)的理解,是指“人们属于某个单一群体的持久性标志”,包含“这样的一些共享的感情和价值观,认同于某个具有公共性记忆的延续性与共同的经历和文化特性的某个群体”。[11](P102—108) 集体身份起源于对“我们”和“他们”之间差异的历史性体认,但作为对文化他者的基本界定方式,其也是对文化差异的本质化结果。萨意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文化的发展和保持就必须有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性存在”。[12](P332)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同质效应的扩展尤其是移民群体的扩张,传统的地缘、血缘等身份传承模式几乎面临被颠覆的命运,国别身份、民族身份以及种族身份在某些移民国家已逐渐模糊和淡化,文化身份反而成为了归属感的最后家园。在身份建构中,文化不仅有其自身本体存在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刮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代表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之处,其神话内涵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表征。对许大同这一代移民来说,当他们踏上美国之时,便与中国文化相隔万里,在美国生活多年以后,过去的文化记忆变得越加模糊,身份也变得游离浮动,他们只能生活在破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选择的交叉地。用一个时髦的字眼来说,他们正在承受着被美国文化同化的“身份危机”,而无法正确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刮痧冲突的发生,一方面彻底打破了许大同对美国梦精神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身份问题,以及刮痧对在异国他乡回归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对于他来说,刮痧是解决其身份问题、回归中国文化的唯一途径:如果他放弃为刮痧做辩解、在法庭上接受西方知识话语的裁决,无异于背叛自己的文化记忆、放弃中国文化集体身份操守;而如果他坚持刮痧的合法性,则不仅是在捍卫刮痧疗法与中国文化,同时也表明了自身向集体身份的回归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在刮痧冲突中,移民身份与文化选择的复杂问题暴露无遗。
对于美国文化来说,刮痧对于集体身份的延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改变了国内的文化构成,造成了文化与身份的多样化现状。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理想可以实现,但“中心—边缘”的现实却无法改变。换句话说,美国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也受到了多元化的威胁,同样存在多样化和碎片化“身份危机”的困扰。因此,在对待异质文化的刮痧疗法时,美国文化固执地坚持其文化知识系统,断然拒绝接受刮痧的异质文化符号。如果刮痧被接受转而合法化,西方现有的知识系统的根基将被动摇,“中心”与“他者”的文化差异将被抹去,基于其上的各种文化身份将统统被消解。因此,在知识和权力的合谋运作下,主流的美国文化,设计了“军规22条”式的相关法律条款,消除了来自刮痧的异己威胁,暂时维持“文化熔炉”的现状,保持自身文化的纯洁和统一性,同时也对移民施加文化压力,迫使其放弃文化记忆,从此接受美国文化的引导和锻造。
刮痧神话,引起了中美文化的对立和两种集体身份的较量。在对抗中,两种文化不但致力保持各自的集体文化身份,而且试图控制移民主体的个体身份,强迫其在冲突中做出身份选择。中国文化,深藏于往昔记忆之中,要求大同为保卫祖国文化和延续文化身份而奋起抗争;美国文化,代表着现在或将来的归属,强迫大同忘却碎片的记忆,继而放弃对刮痧的努力,接受美国移民身份。而许大同处于中美文化两种身份政治左右之间,很难求得两种集体身份的平衡,从而顺利建构自我的个体身份。关于“个体身份”或是“自我身份”,史密思教授指出,其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生活和行为的标识”,而是“任何个体对某些共同的经验和文化特点(如习俗、语言、宗教等等)的主体性感情或价值观”[13]。相比较集体身份而言,个体身份更加重视主体情感,强调个人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处在主流文化的塑造之下,身份主体,尤其对于脱离母文化语境的移民来讲,不一定总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总是具有认同和选择的权力。身份认同的自由,一方面给予许大同多元文化生活的权力,同时也使得其在身份政治的阴影下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实际上,移民身份并不自成一种独立的身份标签,而只是个体身份的特殊形式。它并不维持某种恒定状态,也没有稳定的文化根基,只能是以两种文化集体身份为轨迹而浮动,并偶尔有所偏向。许大同似乎早已认识到移民身份的暂时性,了解自己并不能在美国当一辈子的中国移民。因此,他决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身份的跨越,通过事业的成功来做一个真正成功的美国人。只是刮痧事件打碎了他的美国梦,将他带回到两种文化身份的十字路口。接受美国文化的知识话语,成为美国人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只能永远作为文化“他者”而存在;回到中国文化,重新做回中国人也不大现实,因为“移民只是单程旅行”[14](P134—135),过去的一切早已是尘封的记忆。遥望多元文化主义的绿林,两种文化身份分了路;大同却只能选择一条,并且再也没有回头路;行路的他,久久地伫立,因为再也没有了回头路。
移民身份的“散居性”给许大同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他渴望融入美国文化,认同美国精神,但是刮痧的冷酷现实却将他拉了回来,提醒他的中国文化身份。然而,尽管刮痧事件让大同恢复中国文化的记忆,认识到自身的身份困境,它并未能提供给异国他乡的许大同以解决身份问题的最终办法,而只是留给其一个玄学意义上的“身份家园”。选择美国文化也好,回归中国文化也罢,许大同却只能处于想象的认同状态。这种尴尬的境界,正如萨意德所解释的,“你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回到国内的那种或许比较稳定的状态;天啊,你更不能完全地融入你的新地方、新状态”[15](P39—98)。对于许大同来说,无论他怎么努力工作,怎么事业成功,他在美国也只能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新移民”,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美国人”;而另一方面,无论他如何虔诚地为刮痧辩护,捍卫中国文化,他也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状态,重新回复到同一和稳定的中国文化身份。身份放逐的痛苦与怀旧思乡的苦楚,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移民来说,确实难以承受。
总的来说,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二元对立影响了中国移民身份的重构,并使其在两种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左右为难,无法维持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移民只是文化身份运动的节点,总在围绕两种文化身份的轨迹同时做公转,似乎运动轨迹也相仿,但始终却只能按照自己的轨迹同时做自转。这种移民身份自转的轨迹,或者趋向身份的放逐,或者倾向身份的杂体化。如果许大同能够突破对文化身份“二元对立”的理解,采取一种对待身份问题的“杂体化”新思路,他就会认识到移民散居身份中潜在的杂体性,相应地改变捍卫刮痧与中国文化的策略,从而可能会避免文化冲突的发生以及文化身份的对立。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刮痧文化冲突是中美两种文化身份及种族话语的一次正面较量。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捍卫刮痧的合法性,中国移民就可以重温母文化的认同感,并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延续中国文化的谱系;而对美国文化来讲,排斥刮痧就意味着排除潜在的异己威胁,保护自身文化纯洁性和身份统一性。对文化身份单一性的盲目崇尚,和对“文化杂体”的莫名恐惧,成了身份政治和文化冲突的终极原因。“文化杂体”的含糊性和多重性,拒绝接受任何简单形式的文化诠释,同时也否定了单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可能性。许大同利用“文化杂体”的共通性,通过孙悟空与美国超人两种文化符号的糅合取得事业的成功,但是“文化杂体”的复杂性却使他没有意识到其文化和身份的关联意义。一方面,杂体形式颠覆抵抗主流文化霸权和歧视;另一方面,对于移民群体来说,它也是解决文化脱节和身份分裂问题的有效途径。杂体身份,不仅在理论上是文化身份的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文化和身份发展的最终方向。
对文化纯洁性和身份统一性的狂热,让中美文化脱离了文化现实,造成了两种文化身份的严重对立。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中,“单一”或许只是梦想,“杂体”才是现实。在整个电影的剖析中,中美文化意识形态的对抗,两种文化集体身份的对立以及移民个体身份分裂的苦楚等等,无不表明一种崭新移民文化身份形成中复杂而又痛苦的涅槃过程。也许这就是主人公许大同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启示,也许这仅仅是对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世界的预言,我们无法判断影片真实的文化意图,但是在影片结尾大同的幼子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多元文化身份的杂体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