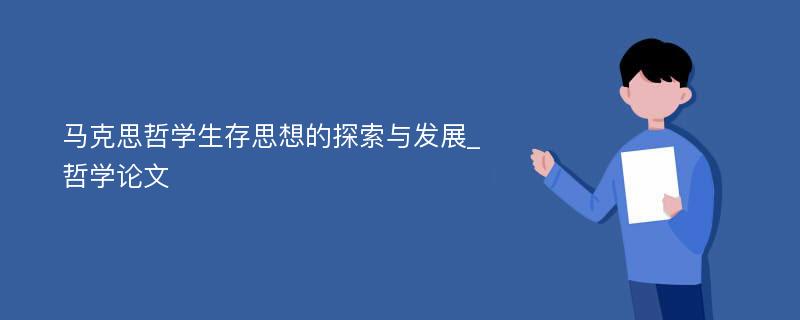
开掘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在新的世纪,马克思哲学是否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否继续成为我们思想的向导,为我们指点迷津?要弄清这些问题,关键要看马克思哲学的视域能否涵盖当代人类生活,它的思想资质是否具有透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的能力。我以为,当代人类生存实践与马克思哲学的互动业已凸显出马克思哲学中最为当代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存论维度,而需要我们做到的则是深入地开掘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思想。
哲学的生存论维度指的是人的生存在哲学中的自觉表达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自批判自超越的辩证思维及精神气质。这种思维和气质既不同于经验主义和单纯的感性直观,也不同于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因为它们虽然也都生发于人的生存活动,但却要么停留于生存的表层和边际,要么把人的生存抽象化、概念化,并因此与人的活泼生动的内在生命相脱离,成为从外面强制人的生存的实体性思维模式。而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则维系于人的生存的生命向度,以人的生存的自我创生、自我确证、自我理解为其理论坐标和视界。哲学的生存论维度表明哲学并不具有独立于人的生存的自足品格,因而不能“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哲学是“有待”的,这就是人的生存活动这一哲学的真正“本体”。如果说哲学的确可以超然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常识甚至不为所谓“时代潮流”所裹携,那正是因为它深入到了人的生存的腠理之中,捕捉到了人的生存的生命精神,从而作为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思想要素而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所需要。当然,再重要的思维或信仰也不等于生活本身。哲学“形而上学”的症结所在,就是以从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思维和信仰取代生活而不是将其实现于生活。所以,它只是“解释”了世界而无力“改变”世界。
马克思正是着眼于人的现实生活而批判地对待现有哲学的。由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一直是主流哲学,并且与宗教神学互为依托,俨然构成凌驾于人的生活之上的自足的观念世界,而事实上却执行着对异化现实掩饰和安慰的世俗功能,因此首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从人的生存出发,马克思发现“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例如,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实体”,其实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自我意识”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绝对精神”则不过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哲学“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把抽象化的“理念”作为人必须信奉和托付的绝对的、终极的“存在”和“本体”,在具体时空和境遇中展开的人唯有靠自己感受和觉解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人生便被吞没、消解掉了。诚然,人的生存并不完全封闭在个体之内,人具有类的普遍性,是社会存在物。但人的类属性和社会性并不能游离于人的具体的感性生活。马克思就此写道:“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为活生生的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的形态,但是在今天,普遍意识是撇开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物,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物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
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在方法论上主要是借助费尔巴哈一类唯物主义对人的“感性”存在的推崇和对人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揭露。但马克思通过这一“借助”却发现了在黑格尔抽象形而上学形式下所蕴涵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辩证法”,即人自我创生的劳动的辩证法。借助这一辩证法,马克思反转来又发现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另一种“抽象”:由于费尔巴哈只知凭借单纯的“感性直观”观照对象,人及其周围世界在他眼里就只能是类似于自然实体的“现成地”“直接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社会”和“历史”这一本来最容易为人所意识和领会的切己内容却成了他的盲点。费尔巴哈是有让哲学“进入”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良好愿望的,但这一愿望不幸落空了。
马克思则成功地实现了他关于“哲学与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期待,因为他发现了打开为种种意识形态所遮蔽、颠倒的人的生活世界的钥匙: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自在生存而可以名之为属人的“生活”,之所以不能归结为外在的客观性物质性存在或内在的观念性精神性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是人自觉展开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这一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力的表现,也唯有人自身才能体验;是人对对象世界即属人的生活世界的建构,也是人感受对象之属人意义而达到的自我陶冶;人由于这一活动而成为具有类属性的社会的人,也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由于这一活动而使自然界不断人化、美化,也因此而使人能够扬弃狭隘的功利取向而与整个自然界融为一体。对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强调使马克思一举确立了哲学的生存论维度。这一维度旨在于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的生存,揭示人与周围世界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并从而为人的整个生命机能的发挥和实现,为人的生存意义的无穷生发作出承诺。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极性思维和疏离人的生存的抽象性弊端,使哲学从认识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为哲学确立“此岸”生活世界的“真理”廓清了道路。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维度的功能在哲学理论上表现为对过时的旧概念的扬弃和具有丰赡的时代意蕴的新概念的提出,由此形成较系统的生存论思想。我以为,马克思对下述六大概念的新的界说初步形成了他的生存哲学的构架。
(1)实践
“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似乎只是指人们改造外部世界以求生的功利活动。马克思同样看重实践的“生产性”。但“生产”的根本旨趣不在于“功利”,而在于它是人的生命创生活动,是人的生命表现和感受的统一。因为实践作为人有意识地进行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由生命力量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这两个具有内在的整体性的环节构成的。人与自然与他人的对象性关系,本身就是生存论关系,因为“对象”所表明的正是人自身存在的对象性质,即人的真实存在并不是他的先天自身,而是在他和对象的可能关系中,他只有在自觉地对象化和扬弃对象化的自返式活动中才能生成并实现其自由无待的主体性。属人的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在这一活动中一体性地生成的。可以说,“实践”这个概念所指谓的,就是对象性的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向自我同时也是世界和未来而生的那种辩证生存方式。
(2)现实 人的现实不是抽象的思想,也不是现成、 现存的事体,那样看问题只能导致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外在化和实体性理解。现实就是人的实践——感性对象活动所创设并为人感受着生存意义的实际生活过程,是体现着人的生存“本质”的生存“现象”。诚然,人的异化生存也具有“铁一般”的现实性,但“铁一般”的既成事实却又是失掉现实性即经历着“抽象化”的“现实”,因为它的属人的性质正在被抽掉、淘空而物态化。所以,人的异化生存的“现实”本身就是“非现实”的。这从反面说明人的生存现实总是由于其内在否定机制(实践)而走向某种新的可能,从而呈现为自否定自超越的流变性。由此可知,现实的真理是可能,现实只有不断地扬弃自身才不致于停滞或退化为毫无生气的非人的物态化存在。
(3)自然 “自然”表面上是完全外在于人的物质实体,其实,人们在其生存实践活动中遭遇并给予观照的“自然”,无论在客观意义还是主观意义上,都不是现成地直接呈现在属人的存在物面前的。为人的意识和语言所中介着的自然对象,已体现了与人的某种特定的关系而成为一种生存现象。例如,只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自然”才作为无任何神秘性可言的实用物而存在;只有废除了私有制,人的需要和享受消除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不再是“赤裸裸的有用性”,才会真正成为人类“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才会敞开其自生自长、多姿多态、自然而然的真实本性。
(4)社会“社会”似乎与“自然”是正相反对的,其实, 社会是自然的“自然性”的自觉完成。因为这是自然的灵长——人的“自然”存在方式。所以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社会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亦决非与个人对立的抽象物,个人诚然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形态,但这只是意味着个人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其赖以生长和得到教化的族群,属于由许多彼此联系和交往的个人构成的生存共同体。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既形成类的普遍性,又获得独立和自由。马克思之所以将“类”改造为“社会”概念,就是因为“类”在德国的哲人们那里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亦即人的“抽象的普遍性”。而“社会”则是人的“具体的普遍性”的实现形式,是人获得自我规定而又能够自我解放的生存之域。
(5)历史“历史”是社会的运动过程, 因而也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联结和共生的过程,说到底则是人的生存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超越的历程。因此,历史并不等于时间的古往今来,而是人的自我相关、自我确证这种开放式循环结构的展开形式。人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解放作为人类实现自己的社会活动,其历史性表现必定是后代人以前代人的终点为起点并重构这个前提。诚然,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死交替。但个人的死并非冷酷无情的“历史”的胜利,没有完全外在于具体个人的所谓“历史”和“历史规律”。这样的“历史”和“历史规定”谈不上公正还是不公正、无情还是有情。历史属于个人,所以个人也是历史性的,“历史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生的螺旋式的上升与回归。历史性已经嵌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所以,人对个人生死的达观,其实来自他对人类生生不息的信念。
(6)异化 “异化”是对人的苦难现实的解释。 这个“解释”的深刻性在于它对生存现象学的“揭示”:人的苦难现实表现着又反对着人的生存本质。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就蕴含了异化的可能,这就是人作为活动主体与客体、活动目的与手段的矛盾结构。这个矛盾结构决定了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双向展开。如果对象是“物”,那么,人就有“物化”的问题;对象是“人”,那么,人与人就会互相规定。这可以说是在世生存的人的基本“境遇”或“宿命”。但这个“境遇”或“宿命”并不等于人的自我和自由的丧失,而只是意味着人要在特定的尺度上生存和发展,也必定为这个尺度所陶铸。人的生成就是不断地进入而又突破指定尺度,从而获得又打破某种确定性的生命流程。就此而言,人永远处在“人化”和“物化”的交互关系中,永远要不停地出“城”和进“城”。但是,如果人与对象的双向关系变成了为自己的对象所支配的单向关系,对象成为与他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那么,本属正常的人的生命“对象化”就成了“异化”。异化不仅意味着人的生存完全囿于一种“尺度”,而且意味着为这种“尺度”所主宰和榨取:人为它倾注的生命活力越多,他自己的生命活力便越少;人的生命的表现成为他的生命的丧失。人似乎由此完全陷入非人的“绝境”。然而,能系铃者亦能解铃。“异化”来自于人而又被人自己给出“异化”这一否定性价值评价,就说明人能够意识到并力图改变自己的异化处境。人的生命对异化的感觉本身就催促着人去克服异化。作为“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的人化的“感觉”(“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等等)是最难以被异化的,它因而总是充当着人反抗异化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内在的动力。而通过异化劳动创造的巨大的文明成果恰恰为异化的克服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异化和异化的克服其实走着同一条实践之路。
笔者认为上述六大概念构成了马克思生存哲学的基本思想,这也是他的基本的“人”论。康德的三大批判最终指向“人是什么”这一难题,在马克思看来,“人”并不能被归结为“什么”。人是他自己的最高真理,而作为自己最高真理的“人”又永远在生成中,即经由其“实践”而表现为人的现实、人的自然、人的社会、人的历史、人的异化及其扬弃。所以,人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人是永远向内在和外在世界生成着的存在者;人就是人的世界。
站在21世纪的入口处解读19世纪马克思的生存哲学思想,我们自然会有“时间”的跨度感。人类在21世纪的生存能力比其它19世纪不知高出多少倍,而生存问题的复杂性也远不在同一层面上。生态危机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是马克思的时代未曾面临的;人的心灵的孤独漂泊感荒谬感及精神疾病亦非马克思的时代的重大生成问题;生物工程和计算机对人的生存和身心所带来的改变更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而要求马克思为我们活在今天的人预备下一切解危济困的“锦囊妙计”,也只能证明我们作为马克思后人的无能乃至退化。我们只能自己拯救自己。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生存哲学思想已经过时,事实上,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辩证生存观,即从人的生存活动的自身矛盾及其螺旋式展开理解并批判地对待生存的基准和思路。以此观之,可以说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危机正是由于人的主体性自身的分裂所造成的。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资质仍然具有透视当代人类生存的能力。诚然,上述困境和危机的解决,有待于我们通过深入开掘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思想,认真地研究现实问题而得以达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