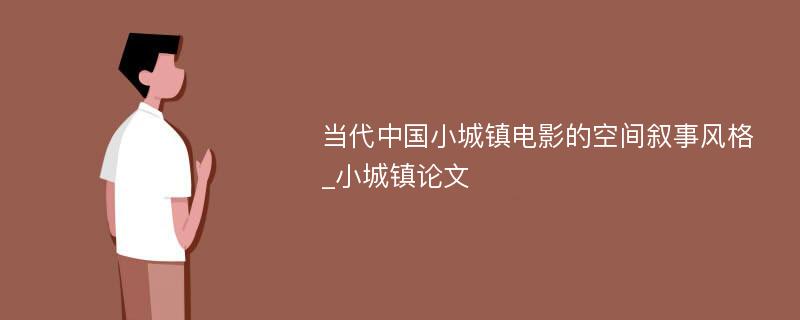
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的一种空间叙事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城镇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风格论文,电影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的美学风格非常鲜明,一种是写实主义风格,一种是形式主义风格。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在论及写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电影风格的区别时说:“排斥虚构剧情的倾向是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是表现赤裸裸的事实,一是表现纯粹的现象。前者的目的是只表现物象而不要形式,后者则是只表现形式而不要物象。”①写实主义风格强调还原“物象”真实,通过客观的电影语言来记录和表现社会现实,其特点是“遵循科学的精确性原则,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社会人生,不带主观倾向,忠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这是它的长处,也是写实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得以独立存在的原因。”②从贾樟柯、王小帅、王超、顾长卫等电影导演的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导演们在自觉地遵循写实主义的这些美学风格。形式主义风格则强调通过电影语言表达他们的“世界观”,如章明、陆川和张猛等导演的作品就倾向通过电影语言“形式”来表现心理真实和社会真实。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不但数量丰富,而且显示出小城镇电影的作者们已形成各自颇为自觉、成熟的电影美学风格,本文将重点论述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的写实主义风格及其在空间叙事方面的表现。 1897年,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曾在《玫瑰:一个社会性假定》一文中阐述了一种被命名为“寂静主义”的美学观:“革命,总是围绕着不平等的残余,如何频繁地一再上演。一个世纪以后,人们或许知道。但是,玫瑰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变迁。”③西美尔的这种“典雅、节制、有质感”的寂静主义美学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西美尔称赞的“令人欢欣的漠然”的外在表象,另一方面是针对现代社会的“对抗所有变迁”的本真态度。西美尔美学的这两个层面如今生动地体现在今天的小城镇电影里:一方面,贾樟柯、王小帅、王超、顾长卫等人平淡如生活流的镜头和段落富有“令人欢欣的漠然”;另一方面,他们对当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表现出“对抗所有变迁”的主观判断。对此,贾樟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如何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遭这种种变化,我觉得这对导演来说是一种责任。当然有些导演可以在作品中无视现实,但对我的美学兴趣来说,我没办法回避这些东西。”④可见,贾樟柯这样的导演之所以关注现实并采取写实的风格,说明其叙述目的和叙事方法一致,对叙事方式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具有自觉的美学追求。 作为美学实践,小城镇电影成为导演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介质,与此同时,其中的空间元素是作者们展示当代中国小城镇、表达其电影观念的主要叙事介质。本文将以顾长卫的《孔雀》(2003)和《立春》(2008)、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李玉的《观音山》(2011)、贾樟柯的《任逍遥》(2002)和《三峡好人》(2006)、王小帅的《二弟》(2003)等小城镇电影文本为例,探讨作者们如何通过不同的空间叙事类型描绘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小城镇生活,展现鲜明的写实风格,并呈现他们的自我观念。 虚构空间:死水微澜的封城 电影的写实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越了对纪录片或模仿纪录片的剧情片的认识局限,形成了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出现了本体的、虚构的、仿真的、描述的等多种写实类型⑤。其中,虚构的写实是和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界定的写实主义相去最远的,它并非完全像克拉考尔所说的那样忠实地记录和揭示现实,而是以虚构的方式还原和表现现实。许多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就采用了虚构的方式来表现现实,顾长卫的《孔雀》和《立春》是其中颇为典型的文本,作者将视线投向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北方小城镇,描绘独特时空中的独特人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实的向度。 《孔雀》和《立春》是顾长卫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创作的两部作品,尽管创作时间相隔五年,但是这两部电影的诸多相互关联之处让我们不妨将其视作顾长卫关于中国小城镇书写的上、下篇章。从叙事时间上说,《孔雀》结尾部分中弟弟的旁白说:“那一年冬天,爸爸突然去世了,妈妈变老了,我们还好。我恍惚记得,爸爸走那天,很快就是农历立春了。”《立春》除了片名之外,开头部分王彩玲的旁白也说:“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这两处时间结构上的互文性显示出,两部电影在叙事时间上先后关联。另外,《孔雀》通过弟弟的旁白明确交代了叙事时间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夏天开始至80年代,《立春》则隐晦地显示了叙事时间是在1990年⑥立春前后的十年时间,因而这两部电影的叙事时间被线性接续起来,跨越了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的20世纪70至90年代。从叙事空间上说,这两部电影是在不同地方拍摄的,《孔雀》是在河南安阳和开封拍摄,《立春》是在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取景,但在电影中它们都叫“鹤阳市”,表明作者意欲通过虚构形成叙事空间上的完整性。《孔雀》和《立春》在叙事时间上的延续性和叙事空间上的同一性表明,作者具有宏大的叙事目标和相应的叙事策略,将鹤阳市这个虚构的小城镇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标本,试图描述和呈现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近30年间中国小城镇的社会生态,其核心是小城人物的浪漫性和小城空间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 空间的封闭性是故事发展的原动力,两部电影的序幕便已建构起一座封闭的小城。《孔雀》的序幕是一个视点处于小城内部的俯视镜头,《立春》的序幕则是一组从远处观望鹤阳小城的空镜头,两处序幕从内至外构成了一组空间镜头,完整地向观众呈现了一座虚构的封城。这显然是一座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小城,富有生活气息的炊烟、低矮的建筑、缓慢的生活节奏都表明小城的传统特性。远景镜头包裹起封闭的城池,其向心性催生出具有桎梏性的小城秩序。与理想幻灭主题的同类电影不同之处是,它们不是以人物或情节,而是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小城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作为主导性的阻力因素,从而具有独特的空间叙事力量。《孔雀》和《立春》通过小城空间表现了小城两个方面的桎梏性,前者表现家庭关系的桎梏性,后者表现社会关系的桎梏性。 《孔雀》主要讲述了姐姐失败的人生,姐姐是一个追求理想、富有浪漫气质的小城人物,她和小城环境之间的冲突最终造成理想的幻灭。姐姐对繁忙、琐碎、平庸的托儿所和制药厂工作感到绝望,在遭遇征考伞兵、欣赏老人拉琴、草率结婚等一系列失败后,最终离婚返家。《孔雀》的主题集中在小城家庭生活的冷漠和粗暴,这一主题生动地表现在姐姐绝食时全家强行喂食、姐姐街头拉伞被父母按住打针、妈妈当众给鹅下药的三个段落里。这三个段落都反映出家庭秩序残酷的桎梏性,父母和姐姐毫无情感上的交流和抚慰,他们对待子女的方式简单而粗暴,要求子女和自己一样安守小城镇的生活秩序。《孔雀》有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姐姐骑自行车拉着自己缝制的降落伞,像一只盛开的孔雀,妈妈扔下菜篮追上姐姐,抓住降落伞揉成一团。这组发生在街道上的镜头几乎容纳了影片中冲突的所有层面,象征精神生活的降落伞和象征物质生活的菜篮、姐姐个人的梦想和路人的侧目而视、姐姐试图飞翔和妈妈扯住降落伞、路人的注视和母女的摔倒、母亲怀抱降落伞坐在地上和姐姐独自离去并置在一起,凸显出小城镇生活在精神与物质、梦想和现实、个人与社会、子女和父母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组镜头采取了典型的封闭式结构,运用长镜头开始和结束,前半段景别由远至近,表现个人对梦想的追求,后半段景别由近至远,表现空间对个人的封锁和钳制。最后的远景长镜头里,路人、妈妈和姐姐的动作表明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制约关系:社会制约家庭,家庭又制约个人。 不同于《孔雀》聚焦家庭对个人的桎梏,《立春》主要表现了小城社会环境的封闭性。《立春》中的王彩玲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性和戏剧性的人物,她长相丑陋但是拥有美丽的歌喉,和姐姐一样,王彩玲最终未能实现到大都市去演唱的梦想,困守在封闭的小城里。《立春》的空间叙事同样采取写实的美学风格,但它的空间比《孔雀》更为繁复。一方面,《立春》在小城内部描绘了多种象征暴力社会秩序的小城空间,包括师范学院封闭的四方院落、广场、公园和监狱等。对为小城秩序所不容的人来说,这些空间都具有规训与惩罚的功能,将王彩玲和舞蹈教师胡金泉牢牢地禁锢在这座封城里。另一方面,《立春》从外部突破了小城空间,通过小城和都市、乡村的对比来表现小城空间的封闭和制约。北京无情地拒绝了王彩玲并粉碎了她的梦想,乡村里的父母亲情则承担起慰藉的功能。王彩玲最终选择了向现实妥协,过上了小城人称道的生活。但是,影片结尾王彩玲和女儿在天安门广场唱歌的段落里,女儿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城里的学生,说明新的梦想在生成而桎梏还在,空间的冲突仍将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孔雀》和《立春》的美学风格采用了鲜明的寂静主义的写实方式,作者大量运用静止镜头或缓慢运动的长镜头来叙述这个虚构的故事。例如,《立春》中王彩玲靠着栏杆远看天安门城楼的静止镜头长度为30秒,带女儿在天安门广场唱歌的静止镜头也是30秒,结尾唱歌剧的长镜头则长达1分50秒,在这些镜头里王彩玲的梦想显得格外遥远而沉重。相对而言,《孔雀》的写实更加风格化。姐姐被殴打之后有一个全家一起做蜂窝煤的长镜头,画面用平视角度凝视大雨中徒劳无功的一家人,姐姐在雨中滑倒爬起来后走出了这个封闭的空间,长达2分36秒的静止长镜头将沉重的家庭关系渲染得令人窒息。影片结尾也是一个静止长镜头,这个孔雀开屏的镜头更是长达4分钟,笼中的孔雀像姐姐一样,美丽而寂寞的绽放,关着孔雀的铁笼则像姐姐所在的家庭和小城,冷酷而封闭。尽管《孔雀》和《立春》是虚构的剧情片,但它们表现的是小城镇“人的状况的真实性”。影片中小城镇社会在精神与物质、梦想和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通过空间叙事作者表明,彼时中国小城镇社会秩序的桎梏性牢不可破,个人死水微澜般的突围终被小城空间封锁。 仿真空间:底层绝望的伤城 “写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克拉考尔强调,电影的本性就是记录和揭示现实,这是写实主义最原初的功能。在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的空间叙事中,有一些电影文本遵循写实主义的原意,采用记录的形式来还原和表现小城镇,如王超的《安阳婴儿》、贾樟柯的《任逍遥》和李玉的《观音山》。这样的形式可称之为仿真的写实,其美学特点是淡化情节,用“生活流”的方式记录现实,同时“表现在时间中演进的现实”。 上述文本关注的现实聚焦于中国小城镇社会当下的社会阶层分化,作者们将镜头对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书写他们的伤痛与绝望,如《安阳婴儿》中一次次被剥夺的下岗工人、《任逍遥》中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和《观音山》中求死的丧子母亲。这些文本中的小城分布于中国的山西、河南、四川,地域不同,风土人情不同,但在导演的书写中显示出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给底层人物带来创痛和绝望的伤城。 在叙事方式上,这三部电影的仿真方式也有共同之处,即采用“生活流”的叙事方法将空间融入时间之中。克拉考尔认为,“‘生活流’的概念包括具体的情境和事件之流以及它们通过情绪、含义和思想暗示出来的一切东西。这意思是说,生活流主要是一种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连续,尽管从定义上来说,它也延伸到精神的领域。”⑦可见,仿真的写实是将物质的空间以时间的流逝和延绵加以呈现,以此来看,这三个电影文本包含了以下几种表现“生活流”的空间类型。 街道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因为“街道就其广义来说,不仅是转瞬即逝的景象和偶然事件的荟萃之所,而且也是生活流得到必然表现的地方。”⑧《安阳婴儿》中,街道是表现人物生存状态的主要空间:下岗工人大刚独自抱着婴儿行走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大刚和妓女冯艳丽抱着婴儿一起逛街、冯在街头被警察追捕、冯在幻觉中将婴儿交给路口的大刚,大刚和冯艳丽的悲惨命运始终和街道交织在一起。关于空间和人的关系,正如导演王超所说:“安阳整个的节奏,它整个的质感、质地,是有东西的,你能够感觉到在中国的底层有一股场,这股场是‘悲怆’,但它是有力量的。”⑨《任逍遥》同样借助街道来表现失业青年斌斌和小济的生活状态:斌斌在车站门外看着便衣警察抓人,包括斌斌在内的所有旁观者熟视无睹;小济和斌斌在街道旁说乔三之死,一列自行车载着花圈穿过,小济的“生命之轻”论调表现出年轻人的虚无态度。《观音山》中的年轻人具有类似的颓废街道生活:胖子在街头被抢钱、南风为胖子要钱砸破自己的头、丁波的摩托车被警察没收,这些场景同样表现了年轻人无所归依的漂浮状态。 和具有静态倾向的街道相比,交通工具是表现运动性质的空间类型,三部影片的动态空间各具特色。《安阳婴儿》是一部强调静态的影片,“它以几乎(除了影片结尾处的肩抗镜头之外)完全静止的镜头,冷静地‘凝视’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的人们,中国平民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聚集在这里:下岗工人、警察、妓女、黑社会、弃婴、监狱等。这里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⑩在静态的“凝视”中,公共汽车、警车的运动更具有视觉上的表现力。大刚抱着孩子坐在汽车上去找冯要抚养费,显示出一种静默的生存态度。冯被抓后像牲口一样被拉到车站,她沉默地和镜头对视表现出顽强的生存力量。《任逍遥》中最典型的是小济骑摩托车的镜头,他面无表情地骑着摩托车穿过街道、穿过废墟、载着巧巧穿过高速公路的工地,最终抢劫失败后骑行至城外的公路上坐巴士离去。小济骑车的镜头大多是长镜头,伴随《任逍遥》虚无的英雄主义音乐,长镜头中的小济凝聚了浓重的消沉感。《观音山》中的运动镜头也有类似的消沉、颓废的气息,南风、丁波和胖子骑摩托车奔驰在城里的街道、爬火车在铁轨上呼啸而过、用车祸中存留下来的汽车载着常月琴在公路上飞奔,无根的年轻人和悲伤的母亲呈现了地震后小城人茫然的生存状态。 此外,室内空间也是反复出现的、表现“生活流”的空间类型。《安阳婴儿》中,大刚狭窄的房间、夜总会的包房等空间和人物暗沉、绝望、逼仄的生存处境相对应。《任逍遥》中,车站的活动室、斌斌被经济困扰的家、小济缺乏亲情的家、将巧巧父亲赶走的医院、充斥皮肉交易的夜总会等空间容纳了小城镇贫乏而堕落的生活,父一代因金钱的匮乏毫无尊严,子一代因生活的虚无走向绝望。《观音山》中,混乱嘈杂的酒吧、常月琴狭窄的住房、令人窒息的车库、山上残破重建的小庙等空间将绝望的人们向希望引渡,然而常月琴的自杀表明人们最终无法获得救赎。 王超、贾樟柯和李玉的这三部电影具有很多共性:它们创作于同一时期(创作时间分别是2001年、2002年和2011年)、讲述同一时期的故事(影片的叙事时间分别是2000年、2001年和2009年)、均采取写实风格、反映小城镇生活,但最重要的共性是他们的主题都是书写底层人物的绝望。关于绝望主题,王超在谈到《安阳婴儿》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希望这是一份独特的中国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影像文献,构思和拍摄这部影片我都希望建立在我对他们现实生存状态之上的精神压力的触摸。是关于他们‘当下处境’的速写;是关于他们‘活下去’或‘死去’的诗;是他们扭曲而顽强的‘存在’,是他们绝望与希望的名字。”(11)贾樟柯在谈到为何选择大同作为《任逍遥》的叙事空间时说:“这城市到处是破产的国营工厂,这里只生产绝望,我看到那些少年早已握紧了铁拳。他们是失业工人的孩子,他们的心里没有明天。带着摄影机和这个城市交谈,慢慢才明白狂欢是因为彻底的绝望。”(12)李玉导演的《观音山》中,南风和父亲的无法沟通、丁波父子之间的封闭以及常月琴和南风、丁波建立母女和母子之情后仍然选择自杀的行为,将绝望情绪一贯到底。因此,无论是中部的历史古城、北方的工业小城,还是南方的震后小城,电影中的小城都是带给底层人物绝望的伤城。 静物空间:记录消失的浮城 除了虚构的封闭小城和底层的无望小城之外,当代的小城镇电影还描写了一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的小城,如王小帅的《二弟》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二弟》描写的是在人口迁移中被抛弃的海边小城,《三峡好人》描写的则是在社会变迁中被淹没的江边小城。 作为外来者的导演,无法迅速深入这些被抛离的小城的内部空间,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采用描述性的外部写实方法,用静物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变迁和人的变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英文片名是“Still Life”,意为静物,贾樟柯在导演阐述中解释了它的深刻寓意:“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镜头前一批又一批劳动者来来去去,他们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让我肃然起敬。”(13)可见,这部电影采用的写实方法是让“镜头前一批又一批劳动者来来去去”,这种方法可称之为静物的或描述的写实,其美学特点是让画面记录的每种静物意象都具有表现的功能。克拉考尔在论及写实主义的记录方式之一“静物”的特性时说:“凡是让静物仅仅作为本身完整的台词和孤立自在的人物关系的背景的影片,都是根本不电影化的。”(14)也就是说,静物的记录功能在于,它是作为一个显性要素来表现影片的整体感觉。《二弟》和《三峡好人》的叙事时间分别为2001年和2005年,在其写实的静物空间里,处于变动中的小城在静止镜头中消失在海平面或缓慢下沉江水中,这种巨变的速度被放大,人们对变动的感受也相应被放大,这正是这两部电影采用静物方式试图表现的整体感受。 《二弟》讲述的是偷渡客二弟的故事,影片背景是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这一时期内陆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沿海地区则涌现出出国潮。影片中有虚实两个空间,全片都是此岸的小镇真实空间,彼岸的美国是对应的想象空间。全片通过这两处空间的比较,用大量静止镜头表现海边小城镇生活的沉闷及其蕴涵的各种对立和冲突。 第一层冲突是传统宗法社会的血缘关系和现代契约社会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冲突。在二弟和岳父争夺孩子的叙事段落中,二弟父母的坟墓和岳父拿出的合同各自象征了血缘关系和契约关系,孩子最终被送回老丈人家,表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里以传统社会的溃败而告终。第二层冲突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镇领导请二弟用失败经验规劝年轻人放弃偷渡,讲座礼堂里悬挂的政治领袖肖像、国徽、红旗等象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询唤,而有较强经济意识的沿海小镇已经无法回避市场经济的到来。第三层冲突是友情、爱情、亲情和令人窒息的小城镇生活之间的冲突。尽管二弟拥有阿亮等朋友真挚的友情、小女无私的爱情和大哥大嫂的亲情,但影片中简陋的演出后台、昏暗潮湿的街道、光秃秃的房间、狭窄拥挤的小吃店等空间显示了他们的生活极为乏味,这是导致小镇人纷纷偷渡的主因,影片结尾偷渡船在海平面远处的天际线上变成小小的黑点,沉闷的小镇也消失在二弟的视野中。 《三峡好人》同样表现了社会迁移的主题,和《二弟》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选择不同,《三峡好人》是以整座小城的消失为代价进行的被动迁移,因而更具有一种无奈和悲怆的情怀。与《二弟》相比,《三峡好人》具有更明确和更主动的空间意识,它的空间叙事方法是用静物的方式去记录奉节这座正在消失的小城和被迫离开故乡的人们。关于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的写实方法,汪晖认为,“我觉得他要深描的是这个运动和变迁本身,从各个角度去呈现、逼近它,但落在具体的人和事上又是速写式的。”(15)上述评价所强调的记录形式和记录对象正是《三峡好人》空间叙事的两个重要方面,即静物的方法和消失的浮城。 《三峡好人》采用了大量静止或缓慢移动的长镜头,以类似绘画的视角呈现了一座即将消失的小城。影片描述了三明寻妻和沈红寻夫的过程,以外来者的视点全面展现了这座小城的空间。在外来者的视野里,小城的空间大致可分为正在破坏的空间和尚且残留的空间。正在破坏的空间包括拆迁办、工地、船厂和爆破的建筑等,这些写实空间的巨大破坏性和震耳欲聋的噪音在静态的镜头里具有一种安静的诗意,视觉上动与静的对比、听觉上响与静的对比使观者在大变动中沉静下来,静静体会变化和破坏的魔幻性和荒谬性。残留的空间包括客栈、渡船、游船、桥等,这些空间是暂时存留但也即将消失,生活于其间的人在变动中的当下保持着一种奇妙的淡然态度。他们家徒四壁,他们被迫接受永远不能返乡的残酷命运,然而小城人的感受绝不只是淡然接受那么简单,导演以外来者的视角通过诸多的细节写实表现这些既普通又独特的人物群像的日常生活,在他们平静的外表下掩藏着复杂的生活状态。 影片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发生在王东明所在的考古队的工作场景。这个场景除了作为寻找主题的叙事桥外,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揭示小城的社会迁移付出的高昂成本,提醒人们不应忽略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人、资源和历史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像考古,以写实的方式将小城和小城人的这段历史存留下来,提供了人们日后追忆和凭吊这座浮城的影像空间。 本文分析的写实主义风格的小城镇电影书写了一系列受制于小城秩序的电影群像:试图走出小城的梦想者、收养弃婴的下岗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退休并丧子的母亲、千里寻妻的农民工、离乡而去的游子等。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是因小城镇的空间局限和社会秩序而承受各自沉重的命运。在当代中国,小城镇的物质生活已卷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中,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之脱节,外面的世界冲击着他们却没有机会真正拥有,他们没有沐浴“现代性之光”却要承受“现代性之难”。对此,写实主义的小城镇电影秉持“寂静主义”的美学观,以客观的态度审视当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及其对人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通过虚构空间、仿真空间和静物空间等空间叙事类型,运用多元的写实方法已开辟出一条寂静主义的写实美学路径,兼具电影方法论和电影美学的双重意义。 注释: ①[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60. ②俞兆平.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2001.87. ③[德]西美尔.玫瑰:一个社会性假定.引自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106. ④[美]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7. ⑤如美国电影学者马杰声(Jason McGRATH)将电影的写实主义类型分为本体的(Ontological)、知觉的(Perceptual)、虚构的(Fictional)、似真的(Verisimilar)、描述的(Prescriptive)和否定法所得的(Apothatic)六种类型. ⑥除了片名《立春》之外,影片没有明确故事的时间,但从片中一个场景可以确定故事的时间,王彩玲去北京找人办户口,在列车驶过的桥洞下悬挂着十一届亚运会会标,墙上的熊猫吉祥物图案显示故事应该发生在1990年. ⑦[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56-83. ⑧同上,第99页. ⑨引自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172. ⑩同上,第165页. (11)同上,第163页. (12)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3. (13)同上,第167页. (14)[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2. (15)李陀等.《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读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