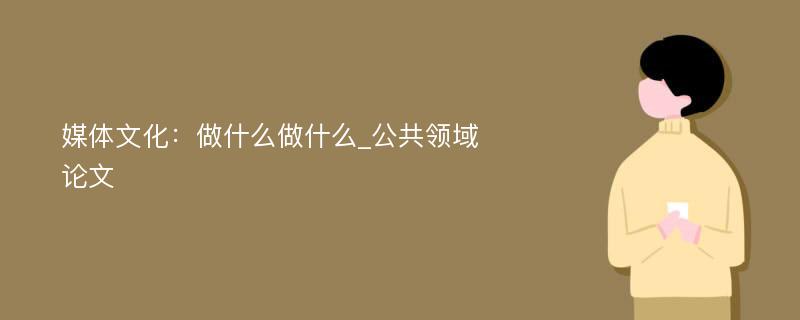
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做什么论文,怎么做论文,传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3-0005-06
关于当今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尽管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描述——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网络社会、技术装置社会、后工业社会、传媒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但无论用什么概念来描述,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经由各种不同传媒或“装置范式”(paradigm of device)——从电视到电脑,从卡拉OK到3G手机,从视频分享到名人博客,已经深刻地构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当人们着迷于各种传媒技术装置范式时,当人们通过这些装置在时空中延伸自己时,同时他们也被传媒及其信息所制约和征服。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传媒在社会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要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自我,就必须直面传媒文化,并反思传媒文化。
一、视觉文化的转向
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代发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minant)。只要翻开图书、杂志和报纸,就不难发现,传统的印刷传媒正遭遇视觉的征服。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可以亳不夸张地说,印刷传媒如果缺了视觉,既有缺憾,又失去了对公众的吸引力。图文书在市场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在都市甚至乡村,各式各样的广告随处可见,巨大的广告图像透过平面传媒、电视和印刷媒体扑面而来。打开电脑或电视,上网游弋或沉溺于家庭影院之中,影像无处不在地追踪着人们。以至于可以断言,今日传媒的视觉性高低乃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相互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从某种角度看,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可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传媒的市场占有率要求把节目或内容变成公众消费品,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视觉性——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对此,美国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总结道:
形象在竞争之中变得极其重要,不仅是通过识别名牌商品,而且也因为各种各样的“高尚体面”、“品质”、“威望”、“可以信赖”和“创新”。形象建构交易中的竞争,成了公司内部竞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成功就是如此明显地获取利润,以至于投资于形象建构(赞助艺术、展览会、电视制作、新建筑以及直接营销)就变得跟投资于新工厂和机器一样重要。形象服务于在市场上确立一种身份。①
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视觉文化转向,导致了许多复杂的“传媒视觉奇观”。所谓“奇观”,是指商品在当代社会日益转化为某种表意形象或影像,因此,“商品即形象”意味着传媒在电子文化时代其游戏规则的深刻转变。根据法国学者德波(Guy Debord)的看法,马克思所探究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特征呈现为物质的占有关系;但在晚近消费社会,商品本质已经从占有转向了展示或炫耀。②因此,商品本身就成为奇观。传媒作为一种消费娱乐性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眼下许多流行的传媒趋向,从国产大片到视频分享,从春节联欢晚会到各种选秀节目,从奥运会转播到时尚杂志,一个又一个当代中国传媒奇观被生产出来。
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显然具有压制对话的“独裁性”。这种“独裁性”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快感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难免会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正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在分析电视和电影这样的视觉传媒时所指出的那样,高度视觉化的传媒取消了印刷传媒所具有的读者与读物之间的距离,“随着新传媒的出现,交往形式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超过了任何报刊所能达到的程度。‘别回嘴’迫使公众采取另一种行为方式。与付印的信息相比,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实际上限制了接受者的反应。……剥夺了公众‘成熟’所必需的距离,也就是剥夺了言论和反驳的机会”。③只要对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各种走红的表征形式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这个趋向。单向性和平面化,成为这一发展的传神描述。
当我们进一步解析传媒奇观现象背后的意义时,就会注意到,传媒奇观不只是吸引眼球的商品推销,更是消费文化欲望和相应意识形态的双重再生产;不仅是特定的传媒内容产业的再生产,也是相关的社会文化体制和现实的再生产,更是人们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这里,我们不妨把传媒奇观视作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的话语。借用福柯的表述来说,传媒的视觉奇观在生产出权力的同时,更在传播和强化着权力。对视觉文化的受众而言,他既被视觉奇观的权力所宰制,同时又在宰制中扩大这一权力。形形色色的视觉奇观通过媒体传播,一方面把受众变成权力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建构为散播这一权力的主体,进而扩大了这一权力的生产性。正是在这里,我们观察到视觉奇观的高度生产性。
二、传媒公域对私域的入侵
当代中国传媒文化所凸显的另一个问题,是传媒公域对个人私域的广泛入侵。这一趋势我们可以在诸多领域看到。例如,在网络博客中,个人的隐私成为最具吸引眼球的网络资源,甚至有人不惜兜售出卖自己的个人隐私来制造卖点;在电视节目中,各种专题和访谈节目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并在其中寻找能够引发观众“窥私癖”的素材;在报纸和杂志上,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成为印刷传媒最具商业价值的“卖点”;在传论文学中,传主的各种爆料才是阅读兴趣的焦点,等等。高度娱乐化的当代传媒,其内容产业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对私人生活素材的征用,越是奇特、怪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就越有传媒的商业价值。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这个传媒立法尚不健全的国度里,传媒公域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入侵,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
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交往公共领域,大众传媒为个体、群体、社群甚至整个社会传递信息、分享经验、建构意义提供了平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独立领域,同时它又与公共权力构成某种相抗衡的关系。④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公共领域又是由私人构成的,它的功能就是介于私人与公共权力之间,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遗憾的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功能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的情境中,当代传媒公共领域却频频侵入私人生活,对个体隐私权和私人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公共领域成了社会力量的入侵口,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公共领域侵入小家庭内部。失去私人意义的内心世界领域受到大众传媒的破坏”。⑤
公共领域入侵私人领域的潜在威胁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方面是:其一,传媒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许多传媒节目中,人们津津乐道于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的暴露。尤其是电视,一些节目打着保护弱者、解决情感危机或家庭纠纷的幌子,不加限制地追问甚至逼问被采访人的隐私和秘密。表面上看是厘清问题解决矛盾,但实际上却是以兜售个人私生活的隐秘为节目卖点,不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被采访人在主持人一再追问和逼迫下,在镁光灯和现场观众的压力下,往往迫不得已地说出自己不情愿说出的隐私,因而从自主的被采访者沦为满足观众“窥私癖”的娱乐性资源。显然,这样的节目与其说是在保护弱者,毋宁说是在侵犯弱者。其二,在网络和视频中,由于这个公共空间缺乏必要的限制和严格的管理,因此,一些来自不同途径的视频或图像便成为公共浏览的对象。越来越多的这类事件成为网络视频热门浏览对象,从香港“艳照门”事件,到晚近某市公安部门在“扫黄”行动中将卖淫女裸照上网等。更有心理阴暗者报复他人,或窥探他人隐私放置网络公开,或造谣惑众败坏他人名誉。这些都严重混淆了公共空间的公共话语与隐私话语,带来了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其三,个人博客也成为出售个人隐私以博得高点击率的阵地。博客本是在公共领域中写给别人看的,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私生活的呈现,因此,博客的话语表述应有一定的尺度和界限。但博客的发展并非如此,一些极端的博主要么在博客中诋毁他人,要么贩卖个人隐私,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谓的“木子美事件”。这种公私话语越界的情况,扰乱了公众视听和公共领域的传播原则,大有猎奇和出风头的轰动效果。
当娱乐化和收视率成为当今一切传媒的生存法则时,个人隐私便成为各种传媒争夺的资源。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健康的传媒文化,应确立并恪守一些公私话语分界的原则,应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免遭侵犯,设立一些基本底线和边界。像今天这样疯狂地攫取个人隐私并直接转化为公众娱乐对象,不能不说我们的传媒患上了某种“传媒窥私症”,进而满足受众的“窥私癖”而导致受众文化的堕落。当一个社会的传媒文化专注于琐碎的个人隐私来提升收视率或点击率时,人们自然要问,这个文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毫无疑问,传媒公域对个人私域的入侵既是一个传媒文化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传媒社会伦理问题。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规则需要探索,许多法规需要订立,听任传媒本身去追逐收视率和轰动效果是危险的。
三、快感的非政治化
快感和政治的关联很复杂,既可以说两相无涉,也可以说关系密切。
在革命至上的年代,人们终日沉浸在革命的运动之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断革命”的快感遮蔽了人们冷静的眼光,压抑了人们的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思能力,使人处在一种情绪偏执化的革命快感之中。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从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从不断革命转向了消费娱乐,从人类大我的理想主义转向个体小我的生存方式,快感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形态——革命欣快感的追求转向了娱乐欣快感的生产。
诚然,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传媒娱乐化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娱乐欣快感的生产和再生产,放到一个特殊语境中加以考量,那就会解读出这一不断发展的文化趋向后面的复杂政治意味。
在中国当代传媒文化中,显然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它常常呈现为政治话语与娱乐话语之间的紧张。这一张力结构通常体现为中心化的政治话语与多元化的娱乐话语之间的平行和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当代传媒文化现象的经验性描述,同时也是对当代传媒文化加以运作的有效策略。我们知道,传媒是一个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社会中,传媒的体制面临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规制与市场化竞争的商业法则的双重压力。从前一个方面说,传媒正确的政治导向规制着传媒的政治话语及其场域,中心化的一元性指导显而易见;从后一方面来看,市场化的传媒运作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高度娱乐化的传媒甚至也可以影响到政治话语。显然,解决这个张力的简单办法就是将两者区隔开来,传媒的政治话语必须加以控制而中心化,娱乐话语只要不涉及政治话语尽可娱乐化。这就在总体上构成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政治与娱乐的二元平行结构——两者平行发展,互惠互利。这种相关性,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格局;同时,它也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一,传媒文化中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两极运作状态——传媒政治话语高度一致,而娱乐话语无所禁忌。在各种传媒载体中,大凡触及政治话语都有严格规范,比如新闻、报道、宣传、相关专题节目和栏目等;而不涉及政治话语的各式娱乐化“怎么都行”,娱乐快感的产品林林总总、丰富多彩。这就导致了两个彼此分离的传媒文化场域各有各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然而,表面上看似两个彼此独立的场域,实际上却通过种种潜在的方式实现彼此的互惠互利关系。
其二,由于这一分离的二元结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受众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传媒参与模式。一方面,由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化运作,使公众的广泛自发参与受到了限制,因而难免导致受众对政治话语参与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热心、不关心甚至不介入状态。另一方面,传媒文化高度娱乐化,又促发了受众对娱乐节目的高度热情和广泛介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传媒的快感生产、传播和消费功能。二元分立结构在限制受众政治参与的同时,也遏制传媒文化批判性和反思性,受众的传媒文化素养很容易流于片面的单纯娱乐化。在这种情形下,快感追求和政治冷漠成为当代传媒文化后果的一对孪生兄弟。所以,传媒娱乐化的商品生产变本加厉,并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地与商业结盟,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回报率,使得娱乐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花样翻新化,快感程度节节攀升。此时,被限制了的公众传媒政治话语的参与冲动,悄悄地转移到了娱乐化的快感体验上来。就像弗洛伊德解释艺术家和白日梦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人格结构中本我的冲动最终被自我所调适,由自我的现实原则转移到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中来。因此,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家的想象替代物,缓解了本我的冲动,带来某种替代性满足。如果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发自内心的冲动的话,那么,在当下中国传媒政治和娱乐二元分离的格局中,这种冲动在转移到娱乐性的快感满足时,政治参与冲动的压力就在暗中被缓解了。
其三,尽管娱乐化的快感生产和消费成为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主体,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还存在着某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参与冲动。形象地说,存在着某种间歇性的政治话语表征“歇斯底里”。虽然娱乐话语的常规形态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传媒受众的文化需求,但是政治冲动的能量仍然存在,一旦某个事件出现,这种冲动便会以某种瞬时爆发的形式凸显出来。这种“歇斯底里”的瞬时爆发有两个特征:一是空前热情但往往却缺乏成熟理性,尤其是在触及民族主义的情绪时,更是如此。因为平时常态的政治冷漠导致了某种政治疏离感,一俟某些事件出现便唤起了被压抑的政治本我冲动,但这些冲动却缺少深思熟虑的分析和理性的批判,很容易流于表面的激情参与。二是这种瞬时爆发的政治参与冲动和热情,一旦时过境迁,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重又陷入某种冷漠和怠惰状态之中,等待着下一次间歇性的爆发。其实,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公民政治心理状态。
其四,从快感本身的政治性来看,如何理解当下流行的传媒娱乐化快感生产本身?它是否具有解构当下政治话语刻板性的功能呢?从美学角度说,德国古典美学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在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宰制的社会文化中,审美的感性快感功能具有某种颠覆性,它把人从工具理性和道德的刻板压力中拯救出来,因而具有某种积极性。这个理论在韦伯(Max Weber)那里成为一种解决现代性内在紧张的办法。⑥当代文化研究也发现,大众文化的快感其实也具有某种颠覆现存社会文化霸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就是所谓“快感政治”的另一层含义所在。那么,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高度娱乐化快感生产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呢?很遗憾,中国当代传媒文化中的娱乐化快感生产和消费似乎缺乏这样的功能。传媒的快感生产与消费与其说使受众自觉地改变什么,不如说使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使现状合理化。这也许说明,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发展路向是一种彻底的快感非政治化。
四、认同建构的同一与混杂
传媒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所谓认同,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如何想象和确认自己。在当今世界,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都比不上传媒文化在认同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道理很简单,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传媒文化主宰的生活世界之中,几乎没人能逃避传媒的包围、追踪、诱惑和影响。
当代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后来的“话语转向”,清楚地揭示了传媒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是如何在认同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⑦显然,语言决不只是一个简单被动的传情达意的工具,它同时也是主体建构自我和社会的观念通道。掌握或使用一种语言,同时也就意味着被这种语言所蕴涵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塑造。因此,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是主张一种文化建构论;更进一步,话语的转向特别强调主体的话语表意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不同于“自然主义”的认同观,话语研究方法把认同过程视作一种通过话语实践来建构的过程,它是一个从未完成——总是在“进行中”——的过程。⑧换言之,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严格地说它是通过主体性的话语表意实践而被持续地建构起来的。⑨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预设了意义;但它也预设了前文曾提及的不断重述和重新阐述的过程。……在所有社会中,个人身份的维系以及个人身份与更广泛的社会身份的联系是本体安全的基本要素”⑩。传媒借助于各种视听语言来传达信息、提供快感,这个过程当然也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认同建构过程。
那么,今天的中国当代传媒如何在建构我们的认同呢?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其文化亦复如此,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各种元素挤压在一个当下的平面上。在当下中国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进程中,本土的和外来的各种文化错综地混杂在一起。社会文化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认同建构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总体上说,中国传媒文化的身份建构具有某种看似对立的特征——同一性和混杂性。
首先,从内部来看,传媒文化具有认同建构的同一性。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由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支撑的三元结构,又形成了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二元平行发展、互惠互利的局面。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不同文化的认同建构的目标其实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主导文化始终坚持政治和伦理导向优先,将个人、群体和族群的认同归结为一种对国家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体制认同的同一性乃是主导文化认同建构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各有自己的认同诉求,但在主导文化话语的支配性建构中,两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导文化的制约和渗透。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建构统一的具有高度向心力的认同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下充满了复杂冲突和文化差异的中国。但是,如何培育公民认同自我建构的反思性,如何在认同的宏大叙事建构过程中为认同的差异性留有空间,也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难题。
其次,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随着通讯、交通的发达和信息频繁的跨国流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互动愈加频繁。我们的认同建构实际上又处于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状态之中。(11)用马克思的话来描述,“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2)。传媒文化是一个高度流动性载体,在全球本土化的今天更是如此。不难发现,几乎每一种在西方传媒中叫好走红的节目类型或传媒创意,在中国传媒文化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克隆或拷贝(尽管它们会加入一些本土原素),更不用说在当今中国传媒中大量存在的国外传媒节目和信息了。在网络资源、建筑风格、饮食文化、时尚风潮、家居设计、网络文化、电影电视、广告节目等领域,大量的异质元素和资源持续渗入本土传媒的内容生产。在这样的高度交融互动的混杂语境中,中国传媒文化的混杂性,必然导致其受众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晚近认同建构理论指出,“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业已完成了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被建构和重构的过程。英国学者霍尔强调认同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表征的、如何影响到我们怎样表征我们自己的问题”(13)。“认同”在当下面临着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是认同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构成认同建构的传媒文化显得多元混杂,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是当代认同的混杂性。
当代传媒文化这种混杂状态,必然会产生某种焦虑甚至恐惧,就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的文化实际上是以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各民族和地区多样性文化的一种侵蚀,它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将遭到破坏”(14)。因此,如何在混杂的文化语境中保持一种本土的、本民族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认同的连续性,就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今天的青年亚文化(所谓“80后”甚至“90后”等),由于处于高度开放和混杂的传媒文化濡染之中,他们较之于前辈必然更加开放、更加多元也更加混杂,因而其文化认同也就更加复杂和更加混杂。
面对这种的认同混杂性,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回应。一种观点是主张回归传统,以本土传统资源的弘扬来抵御这种混杂和不确定性。另一种观点是强调混杂并非坏事,它倒是给传统发展和认同重构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对混杂性的不同评价。印裔美国学者巴巴对混杂性提出了非常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居间的”的“第三空间”,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抵御后殖民主义的策略。(15)阿根廷裔墨西哥学者加西亚·坎克里尼则注意到,混杂化就是把有所区分的文化层面整合到新的结构中去,这个过程导致了认同概念的相对化,因此混杂化也许是建构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16)
对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来说,混杂化究竟会导致何种后果还难下定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混杂中撤退到本真性的原教旨传统中去是不可行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积极面对混杂,探索“认同”建构的新路径。显然,在日益混杂的传媒文化情境中,“认同”的建构一定不同于以往,这是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状况。
注释:
①[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第360—361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Guy Debord,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1994.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96页,曹卫东、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④⑤[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89页。
⑥H.H.Gerth and C.W.Mille.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340—341.
⑦周宪:《从语言到话语》,载《文艺研究》,2008(5)。
⑧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p.2.
⑨参见[法]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英]霍尔主编的《表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两书。
⑩[英]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见《自反性现代性——现代社会制度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101页,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p.4.
(14)[美]詹姆逊:《全球化和政治策略》,见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第36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See Homi K.Bhabha,"Culture's In between",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
(16)Nestor Garcia Canclini,Hybrid Cultures: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Mi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p.xxv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