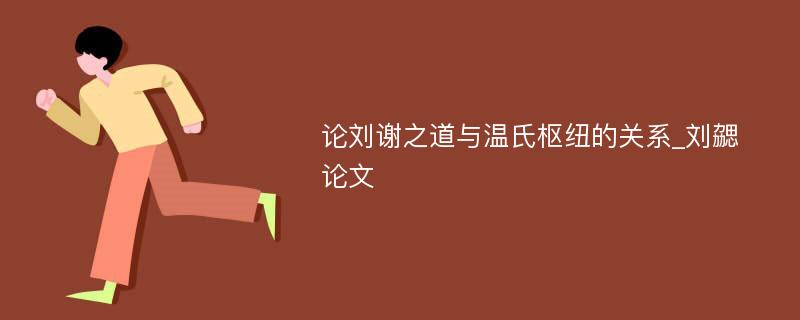
论刘勰之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枢纽论文,关系论文,论刘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等五篇是“文之枢纽”。关于《原道》篇的宗旨,笔者曾撰专文《〈文心雕龙·原道〉与〈易传〉之关系》(注:《漳州师范学报》1995年第3期。)进行了探讨,认为刘勰之道实源于《易传》,其基本内涵有两方面:一指文质相契互存原则,有其质则必有其文;二指文随质变的运动发展规律,强调创作主体或批评主体应善于观察对象之变,体知其内理,然后形诸文辞。因此,刘勰既强调文质相契原则的普遍恒常性,又讲求文随质变的随机变通性。这种从《易传》而来的道观,不仅是刘勰文论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他构设文论体系和进行具体评论的方法论工具。这在“文之枢纽”《征圣》、《宗经》、《正纬》及《辨骚》诸篇中就有充分的体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究。
纵观《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可以看出:刘勰正是秉持这种来自《易传》的道观方法去构设自己的理论体系。纪昀评《征圣》篇“抑引随时,变通适会”二语时认为:“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当道作为创作者共同遵循的普遍恒常之原则时,相当于后人的定格之说,即无论如何变异更新,都应持守“文”与事物之“质”相契合的规律;但道又以强调运动变化为另一重要内含,因此随事摛文、应物生变也就与后世的无定格之论相通。刘勰认为,圣人就是完整、周密地体悟、把握这种道的代表者。《原道》之后接以《征圣》亦是逻辑之必然。
《征圣》篇除“抑引随时”二句体现了刘勰道观思想外,还有另外两处可资佐证。其一是称引《易传·系辞下》中的“辨物正言,断辞则备”。就其原意说,这两句是讲一个卦名欲求圆满周备须由三部分组成,即辨别物类,言中其理,进而断定卦爻辞的吉凶。(注:参见《易学哲学史》上册第69页。)“辨物”是“正言”的前提,恰如“妙极几神”是“思合符契”的条件一样。“断辞”则是前二者结合所具有的功能。刘勰沿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在于说明圣人虽然处处贵文,但总是以切中具体事物之理为要务。所以,虽然“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刘勰却认为“虽欲訾圣,弗可得已”。其二是称引《尚书·(伪)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后两句。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九疏:“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又《尚书集说》引宋代夏氏撰云:“体则具于理而无不足,要则简而不至于馀,谓辞理足而简约也。”刘勰引用此语也是为了强调文辞应当适于事理。
就《征圣》篇论证过程看,从“夫作者曰圣”到“秉文之金科矣”一段,主要是以圣人经文之言为贵文理论提供证据,并且认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秉文之金科”。所谓“秉文之金科”实际上就是指具有普遍恒常性的为文之道,其内含有二:一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原则,强调的是制文须随对象之变而变;二是指“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的要求,强调言理、体辞之契合,相当于道观中文质相符原则。《风骨》篇曰:“《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所谓“文滥”就是指言胜理、辞胜体。因此,《征圣》篇提出,“抑引随时”,“辞尚体要”也就与宋齐以来崇尚藻饰之风有关。《宗经》篇亦本此而发。
罗根泽先生说,“圣人往矣,其人不可征,惟有征沿圣以垂之文,所以又作《宗经篇》”。(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一册第215页。)恰如《征圣》主旨在于弘扬圣人所秉持的为文之法则一样,《宗经》也是着重从经文中所蕴含的创作规律的角度发其精义。文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易传·系辞上》即认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将“三极彝训”释为“有关‘三极’、即‘三材’运动变化规律的训教”,并且认为此处之“经”等于《原道》篇所说的圣人所垂之“文”,是。又《易·恒卦·彖辞》:“‘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刘勰“恒久之至道”一说当本此,(注:在注释“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三句时,大多忽略了“恒久之至道”的来源及真实内含。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只对“经也者”出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亦同;《文心雕龙注释》亦未及“恒久之至道”的出处。)指的就是《易传》中事物变化生成的最高法则。《论说》篇的“圣哲彝训曰经”和《总术》篇的“常道曰经”,在取义上亦与此有关。
将《宗经》篇的“彝训、恒道”理解为以文质相符为内核的运动变化之道,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其一,《宗经》篇曰:“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在此,刘勰将经典中包含的“至道”视成圣人藉以“象、效、参、制”诸种事物之理的依据和原则,并认为是圣人用以洞达性灵之精奥和曲尽文章之义理的最重要方法。“至道”普遍地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正表明了道的恒常通久之特点;但各项活动又必须根据具体对象采取相应的形式,则又从广义上体现了道观中文质相契的原则精神。
其二,《宗经》篇又言:“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刘勰把经典中的具体伦理教义与为文原则分而论之。他指出,人们在修身立德方面都知道应向圣人学习,但在为文建言方面则不懂得去效法经书中蕴含的原理。这种原理即“至道”,也就是刘勰通过评论五经后总结出来的“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殊致”与“异体”正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原则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经典中所包含的道。提倡宗经,目的即在于标举这样一种依不同对象而敷辞制文的创作主张。
《正纬》篇云:“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芟夷谲诡,采其雕蔚”。“正纬”之“正”,除表明刘勰试图纠正世人以纬注经的方法外,还包含有刘勰力求摆正纬书之地位与功用的思想。通过对纬书的证伪,从“文”的角度确认了纬书“有助文章”的价值。这种态度和方法反映了刘勰道观思想,即善于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将对象置于它所应当置放的范围中去讨论。因此,刘勰在理清经书纬书之区别的同时,仍然认为作者应酌采纬书之“雕蔚”以丰富词汇。
《辨骚》之“辨”一作“辩”,与“原、征、宗、正”一样用如动词,具有方法论意味。在先秦哲学中,墨家论“辨”最为详尽。《墨子·经上》云:“彼,不可,两不可也。……辨,争彼也。辨胜,当也。”《经说上》:“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张岱年说:“所谓辩,即‘争彼’之义;所谓‘彼’,则是‘不可’之义。两方互谓不可,谓之争彼。对于一事,此认为是,彼认为非,便是争彼。”(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9页。)刘勰辨骚的方法正与此相类。
刘勰之前,刘安、扬雄、汉宣帝和王逸等人认为屈原《离骚》合乎经术,班固则“谓不合传”。这就出现了“此认为是,彼认为非”的局面。刘勰指出,这些评论都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辨骚》篇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具体分析辨明双方论点的偏颇之处,即“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其论”指刘安、班固等人的评论,“征言”则指征诸《离骚》作品本身的语言材料。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批评方法上,刘勰并没有像前人那样一味拘执于外在的经文标准,而是试图通过对作品自身特点的分析达到批评之目的。
刘勰既找出《离骚》中“同于风雅”之“四事”,又找出“异乎经典”之“四事”。这就以实例说明:如果片面地以外在的经文标准作为评断《离骚》价值的尺度,必然难以得出公正的结论。这同时还表明,刘勰例举“四事”的目的,在于否定刘安、班固等人的观点。(注: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第73页已经指出这一点。)刘勰对《离骚》的正面评价是:
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倘若将刘勰之评与刘安、班固等人的论断相比较,则可看出刘勰在批评方法上的两大特点:
第一,刘安、班固等人的评论,或仅仅注重《楚辞》中有关伦理品德方面的义理,或单单推崇屈原的辞采,刘勰则不同。他坚持文质并重的原则,从整体结构上揭示了屈原作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特点以及因此而体现出的艺术风貌。这种观点方法正是对道观中文质相契关系原则的具体应用。
第二,道观理论还要求批评主体应善于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具体对象而施以相应的分析评价。刘勰对楚、骚的评论,就是从作品的社会时代环境以及对前代艺术经验的继承的双重角度,确认屈原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一点,也是刘安、班固诸评论者所未能做到的。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楚辞》中曾指出:
按淮南王、宣帝、扬雄、王逸皆举以方经,而班固独深贬之。刘勰如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也。
这里的“折衷”即《序志》“唯务折衷”之义,指的是斟酌于屈原作品的内在之理,(注:张少康指出,刘勰的“折衷”论“是折衷于客观的‘势’与‘理’,而非折衷于圣道也。以客观真理为标准,而不是以圣人言行为标准。”见《文心雕龙新探》,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55页。)“不必以圣经列之”,反映了刘勰评文不拘成见的方法特点。
以上分析说明:刘勰运用道观方法正确地评论了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作品,同时又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体现了道观的原则精神。《序志》篇谈“文之枢纽”时提出“变乎骚”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刘勰之道的特性。这样,以文质互契为核心,以变化为运动发展规律的道观思想方法便始终贯彻于《文心雕龙》的理论纲领之中了。
应当顺带提及的是:刘勰以道观方法论文也集中体现在《通变篇》。该篇有这样一段文字: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刘勰以“常”、“变”两个范畴阐明了“文”的发展变化规律。具体地说,“常”指“名理相因”,即一种文体之所以成其为一种文体,应由“名理”双方符契才能成立。任何文体都有内在之理,也就是《定势》中提出的“势”。这就从文体的角度表现了道观思想中“文质”契合的原则。一物之“文”应有其“质”为内在依据,一物之“质”须有其“文”为外在表征形式。文体中的“名理”关系与此相同。刘勰在《序志》篇所批评的“文体解散”,指的正是由于辞人夸饰之风太盛,致使各文体的“名理”互存关系受到破坏,沦失了各自的基本特性。《定势》中说:“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基于这种看法,刘勰主张“体必资于故实”。“故实”指“足以效法的成规”。《国语·周(上)》:“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在《通变》篇,“故实”则具体地指“名理”互存的关系原则。该篇赞文中说的“参古定法”,所指亦同。
如果说“常”的观念体现了刘勰道观思想中“文质”或“名理”互存关系原则的恒久性特点,那么,“通变”观则体现了其道观思想中讲求运动变化的精神。客观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作者也应随着时空及表现对象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文体和文辞加以传达。所谓“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即是就这方面而言。应当注意的是,刘勰的通变观仍然建立在“文质”相符、“名理”相契的原则基础上。
刘勰的这一通变观,既是《文心》之道观思想的具体表现,又与《易传》之道有着直接渊源关系。刘勰认为通变应以名理之常为前提,然后才能通过“变”使“文质”互存之“道”得以通久无滞。《通变》“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物色》篇亦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同样,在《易传》作者看来,事物运动变化是一种必然,但必须建立在乾坤阴阳二元对立相存基础之上。《系辞上》曰:
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变之,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这就是说,乾为纯阳,坤为纯阴,有此对立之象,方有六十四卦之变易可言,六十四卦之变易不可见,乾坤两卦的作用也就止息了。(注:参见《易学哲学史》上册第75页。)这样,《易传》之道虽以乾坤两卦阴阳互立为基础,但又得通过其它卦象的演变来体现。刘勰之道亦如此。如果说乾坤构成了《易经》之道的基本元素并成为其它诸卦演变的基础,那么,文质或名理则构成了刘勰之道的基本范畴,并成为“文”变化发展的基本依据。《时序》篇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所谓“古今情理”、“枢中所动”指的是文质相契之道的恒常性,而“质文代变”、“辞采九变”、“质文沿时”则反映了“文质”互存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运动变化的特性。(注:所谓“枢中所动,环流无倦”,可与《原道》篇“旁通无滞,日用不匮”及《通变》篇“聘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相参看。又《封禅》篇:“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