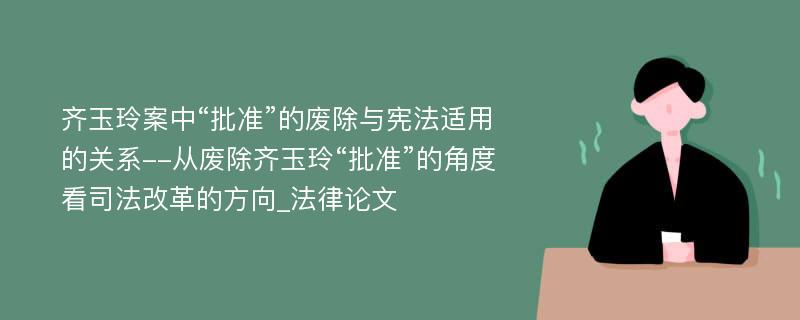
废止齐玉苓案quot;批复quot;与宪法适用之关联——从废止齐案“批复”看司法改革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方向论文,司法改革论文,齐玉苓案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们的热情期待、善意理解和恣意想象下,齐玉苓案“批复”曾经在我国一石激起千层浪。齐玉苓案“批复”并无惊人之语,然而,它的产生和废止均能引发许多人的关注,这实在是许多中国人长期期待宪法权威,期待通过宪法实践体现宪法权威,期待通过宪法诉讼实现宪法权利的强烈愿望所致。齐玉苓案“批复”虽然不曾代表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但废止齐玉苓案“批复”倒是有助于我们认清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有助于我们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推进司法改革。
一、司法改革不要尝试宪法司法化
曾几何时,有些人以为,齐玉苓案“批复”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该“批复”甚至被誉为司法改革的创举。但是齐玉苓案只是一个普通民事案件,不具有宪法案件的性质。“批复”虽然提到宪法上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但并未确认侵犯该项权利的宪法责任,而只是确认普通的民事责任。或许有人考虑待条件成熟时用“批复”这种形式分阶段或一次性地实现有关“宪法司法化”的重大突破,①但是,由于这种突破必然会涉及法院地位和职权的重大改变,非最高人民法院的自作主张所能实现。
宪法司法化涉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重新界定。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而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界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那种认为法院可以通过自主性的改革,扩张司法权,提高自身宪政地位的观点,是与我国的政治传统、根本制度格格不入的,对维护我国宪法权威也是有害的。
根据《宪法》第62条的规定,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宪法》第67条又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已经明确确立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主导地位,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形成更好的机制来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既定前提下,司法改革应该限于追求司法公正,而不是尝试宪法司法化。
从长远来看,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或许要寻求宪法的修改或宪法的解释,但是,在不改变现行宪法及寻求新的宪法解释的前提下,司法改革所要追求的是落实宪法所明确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以有效实现司法公正。宪法司法化明显超出了当前司法改革的范畴。
二、司法改革不要尝试宪法私法化
宪法本质上属于公法,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受宪法控制原则”。宪法可直接或间接地规范政府的行为,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宪法也约束个人,但是,宪法通常通过具体的法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因此,宪法主要是调节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私法则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齐玉苓案中,运用私法规范就已经能够满足案件的审判,而“批复”本身又没有给法院判决提供更多的实质性的司法资源,因此,该案原本就不是一个宪法私法化的例证。
虽然国外有宪法私法化的主张,但这一主张所要引发的问题,远远超过其所能解决的问题,宪法私法化在政治、学术及司法中远未达到广泛的认同。在某些西方国家,宪法私法化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带来了私法难以充分解决私人间权益冲突的新问题,以及宪法司法化带来的宪法效力范围的扩张要求。而在我国,市场经济才刚刚形成,宪法司法化也远远缺乏正当性基础。
我国是一个后发的法治国家,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效力的地位,宪法限制和规范公权力的权能,并未获得各级官员的普遍认同。因此,坚持宪法的公法本质,有助于培养各级官员的宪法责任感,维护宪法权威。同时,让私法解决私法问题,有助于私法健康的成长。宪法私法化,容易将宪法泛法律化,以致庸俗化,冲淡了宪法的特殊性,从而有损宪法的权威性。
三、司法改革不要尝试司法造法
齐玉苓案所涉及的受教育权,尽管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同时也是教育法里明确规定的一项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依照民法通则有关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和教育法的规定,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然而“批复”却不理会教育法的存在,而直接援引宪法,这多少有舍近求远,杀鸡用牛刀之嫌。
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本已通过教育法得以具体化,立法者在教育法中所形成的立法意志是法院依法审判的准绳,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必须予以适用。“批复”的制作者不可能不知晓教育法的存在,法院又无权审查教育法是否违反宪法,那么,在明显应当适用教育法的场合又不适用教育法,就只能推定是有意排斥教育法的适用。齐玉苓案“批复”虽未形成司法造法,但是,拒不适用现行法律而直接援引宪法,实际上也就用司法意志取代了立法意志,具有司法造法的嫌疑。司法造法一方面挑战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垄断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妨碍了宪法通过法律的具体化而得到有效实施的正常途径。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虽然只是针对疑难案件提出的具有很强指导性的意见,但长期以来,它对全国各级法院产生了普遍的、长久的指导意义,并在事实上与条款式的司法解释一起成为审判的法定依据。司法解释虽然由于人大的相关规定而获得合法性,但由于在事实上难以区分条款式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前提条件及形式特征,从逻辑上看,条款式司法解释完全有可能抵触立法或涉嫌干预立法。至于“批复”,更具有司法政策特性,不仅涉嫌干预立法,也涉嫌违反了诉讼程序,抵触了程序法有关二审及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也涉嫌抵触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监督不是指导,更不是约束。
四、司法改革需要整合政治资源
司法改革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司法制度建设是国家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司法改革必须充分运用我国现有的全部政治资源。靠一起齐玉苓案“批复”,或若干起某某案“批复”,甚至于靠一起或若干起某某案的判决,依靠法院单兵突进来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在观念上是有害的,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从未在国家权力中占据过中心地位,法官及其他司法专业人士也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核心影响作用。对于法院及法官自身力量的过度期待,是不理智的。最高人民法院不可能承担我国司法改革的领导任务,更不可能单凭自身之力或一个法院系统来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
就司法改革政治资源的整合来看,首先是执政党的力量,要充分发挥执政党在司法改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司法改革的重大方案,需要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研究规划,党中央决策。同时,也要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通过人民政协等途径,积极发挥各民主党派对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言献策。其次是国家机关的力量,要加强人大和一府两院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分工配合。司法改革绝非法院一个系统的事情,更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紧密合作与分工。全国人大应当通过立法手段统筹安排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检讨司法资源的利用、司法效率的提高与司法公正的实现,落实司法改革措施。国务院应负责落实司法改革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在司法人员的教育、培训上,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是其他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社会公众的力量。司法改革,还需要积极发挥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教育研究机构的力量。如发挥法学会、各学术研究会、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以及法学与政治学的各种教育与研究机构的作用,调动法律专业人士对司法改革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在法治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律生活,他们与司法改革的方向及结果密切相关。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新闻媒体,让全体民众同步了解我国法治发展的进程,及时征求他们对司法改革的要求和建议。
五、司法改革需要运用立法手段
司法改革的结果最直接的作用对象,虽然是司法机关,但是,司法改革的基本步骤却应该通过立法的手段得以完成。“批复”的出台和废止,不是也不应该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晴雨表。
司法改革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在宪法不修改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应当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来推进。我国《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九)诉讼和仲裁制度。”司法改革所涉及的体制、机制问题,自然包括司法机关的产生、组织、职权,也包括诉讼和仲裁制度。司法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是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总体上需要通过立法步骤来完成。
司法改革需要各种政治资源的整合,而要保证各种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一方面要通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机制,另一方面,就要依靠人大的法律决策机制。基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必须遵守和执行法律,同时,一府两院必须向人大负责和报告工作。因此,通过法律手段推进司法改革,能保证各国家机关的紧密合作,促进各政治力量的广泛参与,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改革的科学性、有步骤性和有效性。
六、法院的自主性司法改革应当限于技术性领域
严格划分政治性司法改革领域与技术性司法改革领域是不科学和不可能的,但是,司法改革的内容,有些政治性较强,有些技术性较强,倒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笔者将司法改革可能涉及抵触现行法律或涉及要求现行法律修改的,称为政治性司法改革领域;将司法改革不涉及抵触现行法律或要求现行法律修改的,称为技术性司法改革领域。政治性司法改革需要通过法律步骤,整合多种政治资源后才可进行,因此,必须在全国人大的统筹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所进行的仅仅是配合性司法改革工作。技术性的司法改革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在自己的法定权限内自主进行,是自主性的司法改革工作。
假定齐玉苓案“批复”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某种司法改革的意义,基于这一“批复”引发的有关法院职权的合宪性合法性争议,就可判断其显然不属于技术性的司法改革领域。
政治性司法改革,常常涉及政治权力的重新界定,权利的重新分配,这就非要充分酝酿、认真准备、统筹安排和全面配合不可,因此,只能由全国人大统一负责。至于技术性司法改革,就是在现行宪法法律框架内,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定权限内,在不涉及权力界定和权利分配的前提下,通过审判活动方式方法的改进,努力追求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法官决策机制,减少司法成本和减少司法延迟,减少审判不公,促进司法便民和执法为民。
“从政治制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应该目标一致,但应通过不同的程序发挥不同的作用。”②其实,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不仅性质不同,地位不同,工作方式和工作能力也不相同。涉及司法体制、机制的政治性司法改革问题,适合于全国人大这样的政治性机关来负责,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承担配合和落实的工作;而涉及司法方式方法的技术性司法改革问题,可根据司法经验和司法逻辑由最高人民法院自主开展和进行。法院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政治家,他们适合在法律的逻辑中思维,在经验的积累中探索。要求他们进行政治创新和领衔政治性的司法改革,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危险的。
当然,法院系统处于司法审判的第一线,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法院对于司法体制及司法权的配置有直接的感受,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和党中央就政治性司法改革及时地进言献策是很重要的,但这仅限于改革的研究和动议,而非改革决策。
七、司法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非切入点
对于齐玉苓案“批复”的许多溢美之词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领导地位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也反映了一部分学者视司法改革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的错觉。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及时调整党的执政方式的问题。在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中,立法改革和行政改革在传统和逻辑上也都要优先于司法改革。基于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司法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守成者,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创新者。司法改革需要在若干立法改革和行政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改革需要坚持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并要坚决抛弃“投石问路”的老办法。
齐玉苓案“批复”的出台,是有可能带有许多政治冲动的。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应该是有理智的,考虑成熟的。司法权的运行在我们国家道路坎坷,维护司法权的底线远比盲目扩张司法权重要得多。司法权的运行只承担有限的政治使命,负担过重,可能会引发“过劳死”的恶果。
注释:
①参见陈云生:《宪法监督司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9页。
②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