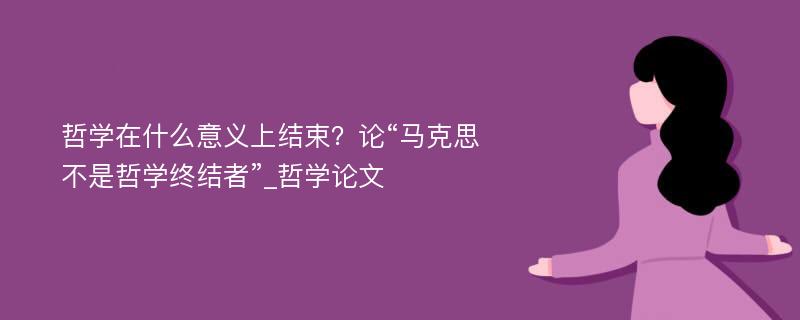
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兼与《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一文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论者论文,一文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8-0026-06
我国哲学界对“哲学终结”问题的认识,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在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引发“哲学终结”的问题上,我国哲学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分歧,大家一般都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正是以“颠覆”、“消解”、“终结”传统哲学为特征的。在此意义上,西方现代及当代众多的哲学家,从尼采开始直到海德格尔、罗蒂等哲学家为止,似乎都可称为“哲学终结论者”。问题在于,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哲学同样具有“现代哲学”的意义,那么,具有现代哲学意义或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不是也同样属于“哲学终结论”呢?对此,哲学界的观点就显出了分歧。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已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拒斥”、[1]“历史科学对传统哲学的拒斥”、“马恩宣告了哲学的终结”[2] 等观点。2004年10月,学界同仁聂锦芳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3] 一文,又表达了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认识的另一种观点。前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也包含或属于“哲学终结论”。这种观点并不带贬义,而是认为只有承认马克思的哲学也包含“哲学终结论”,才能显示其现代哲学的性质及其在哲学史上重大变革的意义。但是,这种马克思哲学是“哲学终结论”的观点,由于与我国理论界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存在一定矛盾,因而到目前为止,也就更多的是以“隐含”的形式出现在一些相关论著之中。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则否认马克思哲学是“哲学终结论”,同时强调马克思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中以聂锦芳的这篇文章最具代表性。然而,这篇文章的观点缺乏足够的历史与逻辑根据,并且还包含着一些矛盾而难以自圆其说。
聂锦芳文章提出“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其立意明确,而其论据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聂文指出那些认为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的论著是“到马克思文本中寻找依据,发现马克思也有‘取消哲学’、‘哲学的虚妄性’等提法,于是就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个‘哲学终结论者’”。[3] 聂锦芳特别批评这种“单纯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抽象出一句话,把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3] 的做法。但聂锦芳自己的文章又是怎样论证的呢?文章一方面“引用”马克思“诚然”说过的一些“取消哲学”、“消灭哲学”一类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引用”另一些“正面”的肯定哲学的“提法”。但“仔细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就可看出,聂文前一方面“引用”的“取消哲学”一类的“论断”主要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合著的著作,那时马克思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而后一方面的“正面”的“引用”则全是出自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例如:“离开哲学我一步也不能前进”出自《给父亲的信》,应是写于1837年11月间,那时马克思才19岁;再引用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1841年3月所写;赞赏“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文化的活的灵魂”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是马克思1842年所写;而提出“哲学是现世的智慧”等等“正面”论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也是写于1843年末到1844年初。由此看来,马克思只在“早期”才多有“正面”肯定哲学的论断,而在1845年以后则倾向于“取消哲学”、“消灭哲学”的否定论断了。可以看出,聂文自身也是在“把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并且在时间上是倒置的,即先“引证”马克思哲学形成以后对哲学的“否定”论述,然后再“引证”马克思早期对哲学的“肯定”论述,这样怎么可能使人得出真实的历史认识呢?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早期”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马克思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1845年春天以后才形成“马克思主义”。那么,到底马克思哪一时期、哪一方面的论断才算是聂锦芳所说的“正面的见解”呢?
其次,聂文在为马克思做出“正面”论述的同时,也描述了“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终结论者”的“反面”的形象与特征,如“对传统哲学的全盘否定”、“强烈的反本质主义意向”以及“相对主义特征”。与之对比的是,聂文提出“马克思不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令笔者困惑的是,什么才算“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呢?提出“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两个决裂”,[4](P293)算不算“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呢?聂文还提出“传统哲学成了他(指马克思)思想建构的重要源头和起点”,“在其一系列著述中,马克思极其详尽地评述了源自古希腊直迄他同时代的全部哲学历程”。这一不无夸张的论断委实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有“一系列”“极其详尽地评述”西方哲学的“全部哲学历程”的学术著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虽然可算“评述了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但那也只限于评述古希腊两位自然哲学家,而且是写于1841年,严格地说它也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著述”。这种“评述”是指《神圣家族》中“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吗?该章节写于1844年9—11月,但那也只是马克思对近代英、法等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所做出的一个极其概略的而并非“极其详尽”的评述。
再次,聂文还提出了马克思的“辩证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的区别。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文中提出的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的“谁也不具有真理的绝对占有权,一切都是相对的”一类思想,到底是属于“相对主义”还是属于“辩证哲学”?“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5](P320)本是属于黑格尔“辩证哲学”的思想,恩格斯也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阐述过“谁也不具有真理的绝对占有权”的辩证思想。至于提出这种“区别”何以就能证明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西方现代哲学才是“哲学终结论者”,也同样令人费解。
这样,通过阅读聂锦芳的文章,我们并没有体会出“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但该文的观点也不失一家之言,并具有启发作用,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终结”问题,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哲学变革与“哲学终结”的关系。
笔者认为,考察“马克思哲学”,准确地说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终结”的关系,不应只限于“马克思”个人,还应包括恩格斯的论述。我们知道,在1845到1895年的半个世纪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说,在对“哲学”及其“哲学终结”理念的基本理解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均为两人合著,恩格斯还把《反杜林论》全文读给马克思听,得到马克思的肯定。所以,恩格斯的论述不仅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问题的依据,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也因此,本文分析“哲学终结”问题的角度就与聂锦芳的文章有所区别,他只限于考察马克思,而笔者考察的思路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终结”。考察“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终结”的关系,必须注意到两方面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背景。
其一,要注意到在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欧兴起并流行起来的实证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年)在19世纪中期发表《实证哲学教程》,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推动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实证主义运动的胜利进军。哲学就是“实证知识”,哲学没有单独存在的权利,人类智力的发展在经过“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之后就要最终进入“实证阶段”。[6](P26)这些观念已经渗透到19世纪中期以后哲学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内部系统,恐怕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与科学理论的发展能够完全摆脱其重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念的形成(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正好与这种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发展同步,因而在事实上也就不能不受到其影响而带有“实证科学”的时代烙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而那种基于“实证科学”的“哲学终结”的思想影响与烙印,按照19世纪的思想标准来说,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哲学终结”的论述中,“实证科学”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所谓“哲学的终结”也主要是指哲学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考察“哲学终结”问题,自然不应遮蔽而是应该再现这一时代背景,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笔者把这一历史背景视为“哲学终结”的“大背景”,它映现、贯穿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对其哲学理念乃至科学理念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二,还要注意到在19世纪中期在德国出现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终结的深刻影响。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哲学研究时,正值黑格尔学派趋于解体并最终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之时。当然,两派都没能挽救黑格尔哲学终结的命运,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对宗教神学和“绝对精神”的批判中逐渐转向激进的无神论,施特劳斯揭露了基督教神话的世俗根源,费尔巴哈提出“人本主义”,马克思则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从而引起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导致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无论是黑格尔本人的哲学,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或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都带有那种特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特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终结”,在其最初意义或原初意义上也正是指同这种德国“思辨”哲学的“决裂”,亦即指“思辨终止”。[4](P73)这也如恩格斯所说的:“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5](P211)这种“决裂”与“清算”,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中,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直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与上述“大背景”相比,这一黑格尔主义思辨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表现为“哲学终结”的“小背景”。不过,这一“小背景”和“大背景”也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二者共同形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过程中“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正是在这两重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的作用、驱动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实现了与“思辨”哲学的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也就在与“思辨”哲学的分道扬镳中提出了与一般“哲学”分道扬镳的结论,即提出了哲学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亦即“哲学终结”的结论。
这样,与上述两重历史背景相适应,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的终结”就相应具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特定的德国“思辨哲学”的终结,另一重含义是指在实证科学的发展中一般“哲学”或“哲学”本身的消亡。这两重含义也相互联结、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内容与“哲学终结”的基本内涵。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哲学终结”的全部论述,都无一不是对这两重含义的论证,或者偏重于第一重含义,或者偏重于第二重含义,或者两重含义兼而有之。而从这两重含义的内在关系来说,“思辨哲学”的终结构成其“哲学终结论”的直接现实内容,而一般“哲学”的终结则构成其“哲学终结论”的长远历史内容,而后者作为“哲学终结论”的最一般结论,也就同时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一般本质内容。
还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终结”的两重含义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著作中是做出了不同表述的,但这些表述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矛盾,而只是体现出其“哲学终结”思想的一些历史特点。大致说来,马、恩有关“哲学终结”思想的发展历程表现出下述阶段性历史特点。
首先,在19世纪中期,即在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与形成“唯物史观”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与德国“思辨”哲学的决裂,同时也就在这一决裂的同时初步确立了自身“实证科学”的立场。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著作中得到体现。其中,下述论断最具代表性。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4](P73—74)
其次,在19世纪50—60年代,即在其理论活动的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于《资本论》的写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即关注于建构实证的“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因此,“哲学的终结”也就更多地通过建构实证的“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体现出来。或者说,这一时期,“哲学终结”的两重含义都通过其“实证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建构而体现出来。
最后,在19世纪70—90年代,即在其理论活动的晚期,在恩格斯的论述中,主要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4年)中,虽然恩格斯也还是关注、阐述其哲学见解与德国“思辨”哲学的见解之间的历史关系,但恩格斯论述“哲学终结”的重点却已完全转移到“实证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他开始更多地论述哲学将“消失”在“实证科学”的发展之中了。
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7](P375)
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批判思辨哲学的同时又一次重申了“全部哲学也将完结”的思想。
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5](P219—220)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这三个时期思想发展的轨迹,其“哲学终结论”的两重含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而两重含义之间也总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
当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认定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就一定会消失或终结呢?
首先,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犯有‘思辨’原罪的哲学同科学是根本对立的”。[1] 因此,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就将“失去生存环境”或“独立存在的理由”而“终止于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可以说,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主要思路。对此,恩格斯多次反复做了说明。除上述引文之外,在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也指出: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7](P738)
在一篇被收入《自然辩证法》的《〈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的文稿中,恩格斯又写道:
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5](P308—309)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定位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因此,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而被“驱逐出历史领域”。就是说,哲学将“终结”于实证的“历史科学”的发展之中,正如已“终结”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之中一样。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4](P66)在他们看来,自然与历史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实质上都服从于同样的辩证运动规律,而对自然与历史的认识也就都属于对现实世界发展的经验的认识。由于自然史研究即近代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已是发现、证明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因而历史的任务就在于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推广、贯彻到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去,以便建立严格的“历史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一建立“历史科学”的任务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就已宣告完成。
我们知道,恩格斯曾多次把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加以类比,认为这两者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7](P77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历史的“实证科学”是与“哲学”、“历史哲学”或“意识形态”根本不同的。据此,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把“唯物史观”定性为从实证研究中概括出来的不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历史科学”及其“方法”,另一方面也对“哲学的终结”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科学主义”立场被有关论文表述为“肯定历史科学、否定哲学的理论取向”,是“历史科学对传统哲学的拒斥”。[2] 这样,哲学在被从自然领域驱逐出去之后,也就紧接着被从历史领域这一“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哲学便无可挽救地走向终结。
现在的问题是,哲学在“实证科学”中消失之后,是否还能在其他领域残存下来?在上述两大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外,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哲学的其他安身立命之地?
哲学的这种可能的安身立命之地主要还有两个,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把“哲学”驱逐出去而促使哲学走向最终的完结。
首先,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也将消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把“世界观”和“哲学”区别开来,并一再以“世界观”的概念来代替“哲学”概念。这种“世界观”被他们称之为“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或“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他们从未把这一“世界观”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现代唯物主义”时指出:“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7](P48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的“世界观”不应有任何超验的成分,完全应该依靠经验的实证科学来建构,而一旦依靠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基本图景,那么,任何关于“世界观”的“哲学”即“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就必然消解。这样,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哲学也将终结。
其次,作为“逻辑学”的“哲学”也难以避免终结的命运。恩格斯一再申明,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即“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才是哲学能够保留下来的唯一领域。但事实上,单纯作为“逻辑学”或“辩证法”的哲学,也像单纯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一样,也“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逻辑学”。哲学,全部传统哲学,也正由于具有某种超验的、反思的、批判的、非经验与非实证的形而上学的本性才得以成为“哲学”,才得以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延续并发展起来,而一旦把哲学完全归属于“实证科学”、“历史科学”或“逻辑学”等等实证知识并认定哲学只能履行实证科学的任务,那么,哲学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关于哲学能否在“纯粹思维的领域”中“残存”的问题,当然也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能认识的历史范围,因为这是一个现代哲学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哲学中残余的部分及其在20世纪的历史性演变”问题。[1] 有的学者对此已做出专门分析,其主要结论是:在20世纪的“纯粹思维领域”也发生了“哲学终结”的现象。一方面,数理逻辑的建立标志着形式逻辑已经从哲学的王国中彻底分化出来,变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真正的科学”;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出现,也已把思辨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当作没有意义的“伪命题”扔掉,连认识论中的非逻辑部分也被排除在哲学之外。“这实际上等于彻底否定了哲学”。[1]
总之,提出“哲学终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进行革命变革的必然结论。这一对哲学的革命变革,一方面消解了哲学的形上意义,导致全部传统哲学的“终结”,另一方面也促使哲学走进经验的“现实世界”、走进人类历史“实践”,达到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融合,但这似乎也同样意味着哲学的终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断言,马克思、恩格斯也应当属于“哲学终结论者”,马克思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具有“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拒斥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与“实证科学”分离、对立的意义上,“哲学”必然“终结”。只有超越实证科学,哲学才能永生。
标签:哲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聂锦芳论文; 科学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