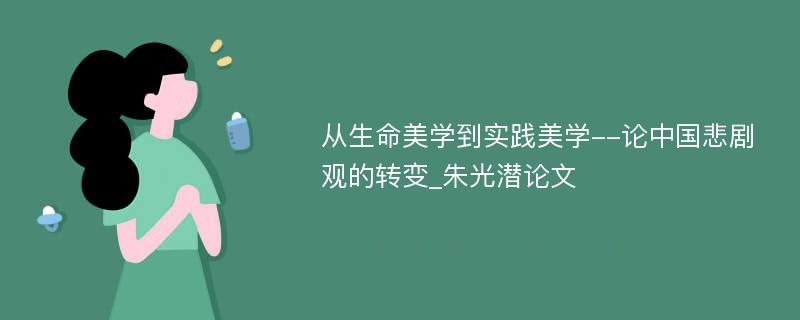
从人生论美学到实践美学——中国悲剧观演变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悲剧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4)01-0055-08
一
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里没有出现过“悲剧”这个范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没有悲剧,也不表明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于悲剧缺乏认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儒道释三家对人生的悲剧性困境都曾作过哲学的(包括美学的)和艺术的阐释,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悲剧意识,深深影响着历代文人的创作心态,他们所创作的大量带悲剧性的文学作品都明显体现着儒道释三家悲剧意识的弥散与聚合。儒家哲学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对建立中华民族悲剧观念,塑造民族悲剧精神起着主导作用。它与老庄、佛教哲学起着补充和互促的作用。它们各自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目的论都有其特殊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它们认识悲剧的出发点完全一致,首先是认识理解人生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把这种认识与对悲剧的认识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各自的悲剧意识。
(一)儒家
儒家哲学把《周礼》中的孝悌演化为“仁”,并从“仁”出发,发展出一系列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的范畴。儒家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形成了“仁、义、礼、智、信”和“忠、孝、悌”等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引导人们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当作生存实践活动之目的,并认为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是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重要保证,这与西方人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意志,并以此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标尺颇为不同的。所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则,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总体秩序之中,它是制约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并引导调整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力量。这样,人们在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情”与“理”的统一,个人的意志、行为是否有悖于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从而做出“善”与“不善”、“合理”与“不合理”的道德评判。因此中国古典悲剧如《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有关人物在苦难时的令人尊敬、振奋的表现,在灾难袭来时超乎常人的抗争。但往往更贯穿其中的是人物的儒家伦理人格,主人公往往是“忠”、“义”、“孝”等的化身,抗争精神也是基于人物自身的“忠”、“义”、“孝”等的信念上,故最能体现悲剧震撼力的人物本身在超凡苦难中显示的抗争精神与其强大的伦理品质相互融合,人物产生的崇高感由此而来,悲剧的精神亦由此而来。所以,中国古典悲剧冲突的基础重在伦理道德引发的矛盾,在悲剧审美过程中,人们对道德观的关注就大大超过了命运观,陶醉于惩恶扬善的情节和结局之中,缺少向更高人生境界的追寻和提升。
儒家认为“哀”(与“悲”同义)和喜、怒、乐一样,毫无例外都是人之常情。但儒家对于苦况的表现和悲情的宣泄,却力持“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论语·八佾》中说:“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哀而不伤”即是儒家哲学对人世悲情进行哲理思辨取得的思想成果。此种观念无疑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悲剧意识上的反映。《礼记·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排斥冲突、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渗透到悲剧结构中,就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理智对情感进行节制和引导,形成了悲中有喜、哀而不伤、矛盾调和的大团圆结局。所以中国古典悲剧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一悲到底以及在极度的悲伤和恐惧中达到“净化”的效果,而是在温和适度的气氛中实现道德教化之功能,使悲剧感得以调和与缓解。但同时这种悲剧结构很容易简化人类实践中悲剧冲突的复杂性,人性由剧烈的痛苦和矛盾方能掘出的深度被强烈的和谐愿望所淹没,现实的苦难和受伤的心灵被消解在团圆的虚幻欢乐中,削弱了悲剧的深层力量。
(二)道家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道家以其不同于儒家的思辨方式,提出了自己对于悲剧观念的哲学见解。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如庄子发出了洞察宇宙人生之后的哀叹:“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尔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灵魂)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庄子·齐物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当庄子把人的生存状况放在自然宇宙这样一个背景上,或者说从“自然之道”的高度来俯瞰人的生存状况时,“大化流行”于一气之中的“死”,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价值化为虚无,“人间世”中那本来只具有相对价值意义的一切,归根结底并无任何价值意义可言。所以,庄子以“自然之道”的价值尺度否定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和政治神圣性,对社会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但他又认为,“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他期盼一种“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自由生活,却又发现人生活在一种自然的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之中,“穷之有命”,“通之有时”(《庄子·秋水》)。这“时”,这“命”都是不可解释的,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庄子·达生》)的无原因的结果,而人又必须忍耐这种“求其为之者而不得”(《庄子·大宗师》)的无奈。
那么怎样面对这种无奈而又无价值、无意义的人生悲剧呢?庄子提出的方法是“忘”,也就是体道,从而得“道”成为“真人”。由于人不是栖息在世界之外的精灵,既然生而为人,就有人的情欲,人的需要,并且不得不为它而作无谓的挣扎。老子所说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正是此意。因此庄子强调那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式的“心斋”、“坐忘”,强调“至人无己”(《庄子·逍遥游》)。庄子论证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谓坐忘。”(《庄子·人间世》)“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庄子·天地》)“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庄子·达生》)道家所谓“体道”,也就是忘怀一切,从而合乎自然,排除内心的干扰,像镜子一样对“道”进行观照。通过“体道”,人们能够全真保性,独善其身,在虚廓宁静的状态中享受心灵的和谐,实现道家理想人格。
因此,道家虽然对黑暗的现实不满,重视人的个性自由,但并不以自我的努力去发挥人在现实中的作用,而是远远地避开社会,向内心求取精神的平衡,把“心斋”、“坐忘”作为超脱痛苦的现实世界,达到自由状态的途径,实现个体的超越。然而,道家的超越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反思和想象,是一种通过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识的沉重的逃避,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道家的安时处顺、超然出世的思想实际上回避、取消了悲剧的核心——事物的矛盾冲突和人的抗争。
(三)释家
从儒学产生到佛教东传,在这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悲剧意识一直在以儒、道两家为主要学派壁垒的中国本土的哲学思辨中被诠释。佛教的传入,及其与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相互辩难,相互渗透,使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升华,闪射出了新的异彩。释家认为人世间“乐是幻”,“苦是谛”,世人无不都因为“身(行动)、口(言语)、意(思想活动)”三“羯磨”(业)而沉沦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轮回”的“无边苦海”中生死相续,生堕不定。这“无边苦海”,即是释家体悟到的人世间的悲剧世界。
释家在悲剧的成因上提出了所谓“业”的概念,认为“业力将人处处经,随其作业受苦乐”(《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世尊偈言”),“业”在佛经中指“造作”,泛指一切身心活动,一般包括“行动”(身)、“言语”(口)和“思想活动”(意)三类(三业)。释家据此提出了“三业”是“因”,报应是“果”的观念,又进而系统理论化为佛教全部教义的总纲——“四谛”(四种真理):“苦谛”(关于人生苦难的真理)、“集谛”(关于积聚感招的真理)、“灭谛”(关于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一切原因达到脱生死的“涅槃”境界的真理)和“道谛”(关于达到涅槃境界的一切理论和修习方法的真理)。在这里,释家认为:人世间充满了苦难,所谓“三界皆苦,无可乐者”(郗超《奉法要》);若想“断除诸苦受”(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只有消除足以“集起生死苦”的各种烦恼“业因”(《俱舍论》),乘上佛教智慧的“慈航”,苦志修行,彻悟“因果业报”等“至理”,到达“涅槃”境界,方可脱离“无边苦海”。
在这里释家只不过是想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实际上“无边苦难”无疑都是“现实苦难”的折光反射;“因果业报”自然也是社会现实生活中遭受苦难的人们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愿被神学化了的反映,尤其是其中的“恶业得恶报”,更是人世间遭受苦难的众生希望制造苦难的恶徒们受到应有惩罚的由衷心愿,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而期望借助佛教法轮的运转付诸实施的对恶势力的一种抗争。然而,佛教哲学中所宣扬的出世论和涅槃说彻底否弃生命,弃绝尘世人生,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解脱,与注重抗争、直面人生苦难的悲剧意识一定程度上是不相合的,反映在悲剧观念上便出现了解脱苦难的空幻性大团圆结局方式,如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蝶得以团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化为鸳鸯等,从而把悲剧人物抗争与超越的毁灭转化为闲情舒适的解脱。
尽管儒道释三家有着不同的悲剧意识,但它们在对人的问题上,在对人的规范上都统一地指向人际关系的平和、统一,反对尖锐的冲突,消除决然的对立,达到世事的“有序”。也就是说,都是追求秩序、规范,厌恶矛盾争斗,反映、表达了农业宗法社会的生活理想。这样,在悲剧意识方面儒道释不同程度起着反悲剧性,反对尖锐矛盾冲突,淡化民族悲剧精神,调和对立的悲剧人物关系以致形成悲剧大团圆模式的负面作用。
二
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剧烈地碰撞,撼动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美学。在西方美学思潮冲击下,王国维、鲁迅、朱光潜和蔡仪等将目光转向西方悲剧理论并做出了自己的美学抉择。通过他们有关悲剧的论述,可以窥见中国近现代悲剧观念蜕变、深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王国维
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主要依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学说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悲剧观,成为中国近现代悲剧观念的开创者。
第一: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的结合。人的知识与实践这两个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只有“美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因其非“实物”,故能于人“无利害之关系”,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人对它也就“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种“艺术之美”,因其能“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故能减轻人类苦痛,因而也就优于“自然之美”。因此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一绝大著作”。因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1](P36)特别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解脱,不是“非常之人”的解脱,而是“通常之人”的解脱,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1](P36)王国维的悲剧美学思想是叔本华悲剧理论在中国的投影和回声,他用虚构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用短暂的美感代替一切,解释悲剧,最终只能走向宿命论。
第二,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由于剧中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P39)。这三种悲剧中,第三种感人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第一、二种。因为人们在面对第一、二种悲剧的时候,“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站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1](P39)就是说,这两种悲剧,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还是可以逃脱的。第三种悲剧则不然,“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所固有”[1](P39)。就是说,这种悲剧是必然性的,不可逃脱的。因此当人们面对第三种悲剧的时候,“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1](P39)而《红楼梦》“正第三种之悲剧也”,描写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1](P39)因此,王国维之所以肯定《红楼梦》正在于《红楼梦》不是通过偶然的事件,而是通过普通人的种种遭遇揭示了悲剧的必然性。
第三,王国维还依据新引入的悲剧观,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发出了肯定与吁求“彻头彻尾之悲剧”的呼声。针对中国崇尚“大团圆”结局的悲剧传统,他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1](P37)因为它是“他律的”、“政治的”、“国民的”和“历史的”,而《红楼梦》的解脱则是“自律的”、“哲学的”、“宇宙的”和“文学的”,因而它“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1](P38)在这里,王国维不仅发现、认定《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实际上,也是在否定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精神,大力吁求一种“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之精神,因而,极具开创意义。“盲目的乐天、廉价的大团圆,这确是中国文学的、戏曲的旧传统,也是普遍的审美心理。这是不敢正视人生,惯于听天由命的思想的反映,因而在近代反封建的先进人物如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都在文学戏曲领域给予尖锐批判,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但在这方面,王国维是先驱者。”[2](P117-118)
王国维是近代从西方引进悲剧观念到中国的第一位学者,他接受了叔本华悲剧理论的影响,否定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伦理主义、中和主义的“大团圆”模式,从人本身、从人的意志、欲望去寻求悲剧的根源,认为悲剧精神就在于拒绝生活之欲而走向解脱之路,显示了悲剧观念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深刻转换。但王国维把悲剧变成一种与社会毫不相干的个人命运的不幸,因而没有把握悲剧的真正意义,不能在生活本身之中看到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更没有找到改变人生悲剧的现实力量。
(二)鲁迅
鲁迅的悲剧观与王国维、朱光潜一样,直接受西方现代悲剧理论的影响,都很看重悲剧与人生的联系,但由于接受的方式和出发点不同,使他们的悲剧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鲁迅的悲剧观是为现实人生的,主张正义;而王国维与朱光潜的悲剧观则是为“过滤了的人生”,消解了正义。
鲁迅青年时代就倡导悲剧,他在日本期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十分重视悲剧,认为悲剧要致力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它会引导人们去思索产生痛苦与不幸的社会原因,如果悲剧作品能揭示出大家所未能觉察的社会原因,其思想内涵就深刻有力了。鲁迅曾经接受过尼采的美学思想,但并没有笼罩在尼采的思想阴影里,他把尼采的“超人”变成了社会的叛逆者和对抗者,终身致力于勾画和剖析国民的灵魂。鲁迅没有在尼采的思想面前止步,他接受了苏联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提出用“几乎无事的悲剧”表现社会最低层的弱者,最平凡和最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他们是不幸的,但大都是善良的。因此鲁迅的悲剧观体现的是“有价值”的小人物所遭受的毁灭,强调悲剧的正义,揭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激活人们为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而奋斗、抗争的悲壮精神。这样,鲁迅的悲剧观不是现实向审美的逃避,也不是现实的“距离化”,而是一切为了现实,完全表现现实,最终影响现实。
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大团圆模式率先发难,自有功绩,但是对于造成这种民族精神囹圄的更深层次原因,他却无力回答。鲁迅则用他的现代悲剧观念烛照历史的纵深处,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是中国国民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其病根在于我们身上的传统思想因子在作祟,几千年的封建名教历史,使妥协平和中庸的思想成为浸透中国传统文化骨髓的一种主导性精神倾向,它禁锢和束缚着人们的心灵,不敢正视由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或社会缺陷所生发的苦难,“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中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3](P284)所以鲁迅强调传统文化是人性压抑的罪魁祸首,中国老百姓沉默的灵魂“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悲剧就应该写出被黑暗的社会重压、毁灭了的有价值的精神悲剧,从而唤醒人们达到改造国民性,变革现实的目的。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只有鲁迅的悲剧观念才真正触及到了悲剧的实质或核心要素:悲剧并不是人生不幸与厄运的简单展示,相反,悲剧艺术美的深刻根源在于表现了代表正义、健康和善的精神力量的“有价值的毁灭”,唤起人们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与淋漓的鲜血,积极向旧世界宣战的无私无畏的抗争、革新精神。同时,由于鲁迅不是美学理论家,未曾将美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来研究,他对悲剧冲突缺乏论述,也没有从理论上揭示悲剧的根源,因而鲁迅的悲剧观没有上升到美学范畴和美学定义的高度,具有一定局限性。
(三)朱光潜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对悲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从总体而言,王国维的接受西方悲剧理论具有明显的单一性,他没有刻意地融合不同的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体系,重在以西学阐释中国悲剧;朱光潜则表现出折衷综合的倾向,注重在批判中选择,在批判中综合,试图在融合各家悲剧观念于一体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悲剧观。
朱光潜首先严厉批评黑格尔对悲剧人物苦难的忽视,他说:“黑格尔既然完全忽略悲剧中的苦难,自然也就完全不谈忍受苦难的情形。”[4](P118)所以朱光潜强调:“悲剧表现的主要是主人公的苦难。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中,……是俄狄浦斯突然明白自己犯过错,是越卡斯塔之死以及俄狄浦斯自己弄瞎双眼去四处流浪……通常给一般人以强烈快感的,主要就是悲剧中这‘受难’的方面。”[4](P118)与此同时,朱光潜称赞叔本华说:“黑格尔很少谈论悲剧中的受难。然而叔本华却把这一点变成唯一重要的因素。他说:‘对于悲剧来说,只有表现大不幸才是重要的。’他把不幸的来源分为三种。”并说:“叔本华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真理。……他对于我们认识悲剧至少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他比别人更能使我们生动地感受到悲剧悲观的一面。……强调悲剧中的受难,就填补了黑格尔留下来的一个空白。”[4](P140)同时,在朱光潜看来,悲剧中的痛苦绝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难混为一谈,悲剧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它与现实生活是有距离的。就悲剧主人公来说,“崇高”首先体现在地位的重要,“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和悔恨的痛苦,在一个农夫和在一个帝王都是一样地动人。这当然都对,但是也不可否认,人物的地位越高,随之而来的沉沦也更惨,结果就更具悲剧性。一位显赫的亲王突然遭到灾祸,常常会连带使国家人民遭殃,这是描写一个普通人的痛苦的故事无法比拟的。”[4](P120)这样,“崇高”意味着悲剧主角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无论善恶都超出一般水平,他的激情和意志都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心灵的伟大”正是悲剧中关键之所在。这个“伟大”绝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仅仅是指“英雄的宏伟气质”,即使是善良人,怯懦和屈从不能使他成为悲剧人物;即使是邪恶之人,只要表现了抗争和不屈,他便可以成为悲剧人物,因为他们在邪恶当中表现出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强烈的生命力。朱光潜认为悲剧与善恶无关,实际上也就与道德无关,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他是以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痛苦的人生,但这种“距离化”的人生,是虚妄的,非真实的。
朱光潜从西方传统悲剧理论出发,认为“崇高”是悲剧的主要美学特征,但是他理解的崇高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正义,而是尼采的生命哲学。由此,朱光潜批评了叔本华,并形成、提出自己的看法:“严格来说,叔本华说‘只有表现巨大的痛苦才是悲剧’,并不符合实际情形。……悲剧全在于对灾难地反抗……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4](P138)“悲剧正是描写悲剧英雄甚至在被可怕的灾难毁灭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自己的活力与尊严,向我们揭示出人的价值。”[4](P140)这样,朱光潜在对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有所继承、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悲剧不仅表现受难,还应表现反抗,悲剧表现的是受难与反抗。
朱光潜和王国维、鲁迅一样,严厉批评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方式。他认为大悲痛和大灾难,在一切伟大悲剧中是不可避免的。他借用尼柯尔教授的话说:“悲剧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并发挥道:“人非到遭逢大悲痛和大灾难的时候,不会显露自己的内心深处,而一旦到了那种时刻,他心灵的伟大就随痛苦而增长,他会变得比平常伟大得多。”[4](P207)但是,在中国“戏剧情境当然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4](P218)他认为,没有了大悲痛和大灾难的结尾,等于就没有了悲剧。“中国文学在其他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4](P218)论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他倾向于批判剧作家的“道德感”,认为是“他们强烈的道德感使他们不愿承认人生的悲剧面。”[4](P221)朱光潜关于中国“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的说法,已经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且还有待争论。但他对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方式严厉批评,是醒目而且有益的。
朱光潜的“受难”——“反抗”说,对王国维的“苦难”——“出世”说,是一种修正;对鲁迅的“毁灭”说,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朱光潜的悲剧观同他的美学思想一样以西方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具有过于强调悲剧艺术的非功利性,重视精神力量甚于社会实践等缺陷。朱光潜认为悲剧与善恶无关,实际上也就与道德无关,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他是以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痛苦的人生,但这种“距离化”的人生,是虚妄的,非真实的。同时,他对西方悲剧美学的折衷与综合,没有形成内在一致性的体系,仍然处于移植和运用的接受层面,没有达到自觉的创造性转换,提出自己的悲剧理论。
(四)蔡仪
在中国近现代悲剧理论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立场上来阐述悲剧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美学家蔡仪。蔡仪的悲剧观念,主要体现在其1947年出版的《新美学》中。
什么是悲剧?他认为悲剧“是表现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的美”[5](P270)。即是说,悲剧是表现社会矛盾的本质的。他解释说,冲突的社会事物,在它们冲突的发展过程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两种相反的社会力量的冲突:一方是正的力,另一方是负的力。而冲突的消解,或者是构成冲突的这两种相反的社会的力的一齐灭亡,或者只是正的社会的力的灭亡。他认为,负的社会的力的胜利,有它的存在的必然性;而正的社会力的灭亡,则是由于它的前途是必然的。他着重指出:“正的社会的力的必然性,在当前尚小于负的社会的力的必然性,所以它不免于灭亡。但它的前途是必然的,人们对它的必然的前途的期望,随它的灭亡而受挫折,所以是可悲的。”[5](P276)蔡仪对悲剧的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相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悲剧冲突的实质,指出悲剧冲突根源在于两种社会阶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的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不可解决,因而必然性地导致其代表人物的失败与灭亡。在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的启示下,蔡仪提出在悲剧中“正的社会的力的灭亡”和“负的社会的力的胜利”的“必然性”的观点,对悲剧本质和冲突进行了新的诠释并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力。
蔡仪对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与观念的深刻理解,更体现在对经典悲剧作品的唯物史观的阐释中。他首先对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所谓命运悲剧,按从前的说法是主人公对命运的冲突而终于灭亡。命运原是古代人假设的支配人们的一种神秘的必然的力量,而在今日我们知道事实上原无所谓命运,只有自然的必然和社会的必然。如《奥迭蒲士王》(今译《俄狄浦斯王》),可以算是命运悲剧的代表。他认为,主人公奥迭蒲士王设法要避免杀父娶母的命运而终于不能避免的悲剧冲突,实际“象征着由‘杂婚制’到进步的婚姻制的社会蜕变过程中的冲突。奥迭蒲士王的意欲是新的婚姻制的必然,而他的命运则是旧婚姻的必然。所以他的意欲和他的命运的冲突,其实就是社会的必然和必然的冲突。他的意欲失败了,而他的命运胜利了,也就是新的婚姻制失败了,而旧的婚姻制胜利了。”所以这是“社会的悲剧”[4](P277)。谈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性格悲剧,他认为也是有深刻的社会矛盾根源的。他说,《哈孟雷特》(今译《哈姆雷特》)的主人公悲剧的根源,从表面上看来,诚然是他的犹疑而不果敢、思虑多而行动少的性格所致。但是所谓性格,若只就生理的遗传的条件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就不是什么典型的东西。他认为,性格不仅由生理的条件所决定,而主要的倒是社会的条件所决定的,如社会的人群的关系和社会层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他指出,《哈孟雷特》一剧题材虽属于古代的丹麦,而哈孟雷特却是近代初期英国的产物。当时英国的封建制度已在动摇之中,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正要抬头,哈孟雷特的性格就反映着这两个社会的人群关系:他的“封建的复仇义务和完成这义务的力量之丧失。因为哈孟雷特已经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对于旧世界的封建关系已经在他心中瓦解了。”这样,“两个社会的人群的关系反映于一个人物身上,两个矛盾的必然反映于一个人物身上,这矛盾在他心里冲突不决,使这个人物犹疑而莫知适从,于是而有哈孟雷特一样的悲剧的性格。”[5](P278)在蔡仪看来,一切悲剧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但直到近代“才出现特别指出悲剧的社会根源的所谓社会的悲剧”[5](P279)。
蔡仪的悲剧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从而拓展了现代悲剧观念乃至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理论视野与研究天地,昭示了中国美学和悲剧理论的发展趋向,但是由于时代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上的简单化、片面化等原因,他的悲剧观也存在着忽视悲剧人物的主体作用等局限。
总之,中国近现代悲剧观念从形成历程看,它是从接受各种西方悲剧美学思想开始,发展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阐释悲剧的过程,但正是因为普遍处于移植和运用的接受层面,没有真正达到自觉的创造性转换,建构起自己的悲剧理论。
三
中国传统美学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之下,从先秦时代以来就造就了“向内求善”的审美品格,从人的本性和特质出发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了人生论美学的特征,同时相应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意识。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逐渐靠拢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探寻,王国维、鲁迅、朱光潜、蔡仪等在移植西方哲学美学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体系包括悲剧观,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艺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但人生论美学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仍然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期的美学包括悲剧范畴研究中曾经长期被中断或淡漠。
随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美学包括悲剧范畴研究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悲剧的本质是显示善与恶的冲突,在善的失败中显示善的价值,悲剧人物必须具备道德上的优秀品质,欣赏者从这些人物的毁灭中受到教益等。例如这一时期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李泽厚在写于1959年的《关于崇高与滑稽》中说:“艺术中的悲剧正是在情节或性格的发展过程中,以激烈的冲突形式将现实与实践的矛盾斗争集中地反映出来,以唤起人们积极的审美感受。”[6](F210)而“悲剧的审美感受有两个方面,有两种突出的心理动力:一方面,因目睹失败而同情或哀怜,但同时感到被摧残者的正义、勇敢而激励自己奋发兴起;另一方面因目睹失败而震惊而‘畏惧’,但同时感到人们(也是自己)必须更好地去认识客观规律(必然性)和掌握这规律,从而进行更有效的斗争。”[6](P218)李泽厚把悲剧放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考察,从实践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出发探讨悲剧的美学实质和审美感受,为悲剧范畴研究找到了一条正确途径。由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存在着美的物质性(或客观性)和社会性与美的精神性和个体意识性间的矛盾与对立,所以他对悲剧范畴的阐释存在理论缺陷,例如悲剧与个体生命、悲剧与现实人生的关系等成为其理论盲点。
这一时期的美学具有建国后扫除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带有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悲剧研究的论域与深度都是十分有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悲剧?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悲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悲剧艺术是否能够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曾经成为这一时期悲剧研究探索、争论的焦点。由于政治与文艺和美学的愈来愈不正常的关系,带来了把悲剧研究更加政治化、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以至于出现了照搬苏联美学理论对悲剧范畴进行偏狭理解,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悲剧,“文革”时期禁止悲剧创作,悲剧研究更是成为空白的民族悲剧。
“文革”结束后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西方各种现代美学理论大量涌入,美学研究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步形成,悲剧研究随之十分活跃,有了很多新的进展、突破。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视野比过去更宽广,视角趋向多元化,悲剧范畴的很多关键性问题研究也更为深入。在各种美学思潮中,实践美学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美学不可否认的主潮。这一阶段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尽管具体的美学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们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指导来研究美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并据此阐释悲剧观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对悲剧范畴的研究。以蒋孔阳为例,蒋孔阳在“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建立了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特色,以人生论为宗旨的完整的美学开放体系。蒋孔阳在《美学新论》中从他的这种美学开放体系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悲剧观:“在人生道路上,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在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悲惨的遭遇,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说悲剧性的命运,这样,悲剧性这一审美的范畴,虽然来自于悲剧,却又不限于悲剧。”[7](P387)“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们认为在社会历史关系中所形成起来的人的本质力量,总是希望自由地得到实现和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本质力量不仅得不到实现和发展,而且受到阻碍和摧残,以至遭到毁灭,造成悲剧。”[7](P396)蒋孔阳对于悲剧的论述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从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的视角把悲剧研究与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实现密切联系在一起,阐明了悲剧对于人类,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预示了悲剧研究的新方向、新视域。美学必须以人本身为焦点,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这个根基,那么美学就必定是一门“人学”,是为人生而美的学问,因此,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方向也就必定要走向以科学的人类学为基础的人生论美学。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人类的自然实现为根本目标,能够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真正阐明悲剧的内在根源和美学特征。
收稿日期:2003-10-23
标签:朱光潜论文; 王国维论文; 美学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红楼梦论文; 鲁迅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