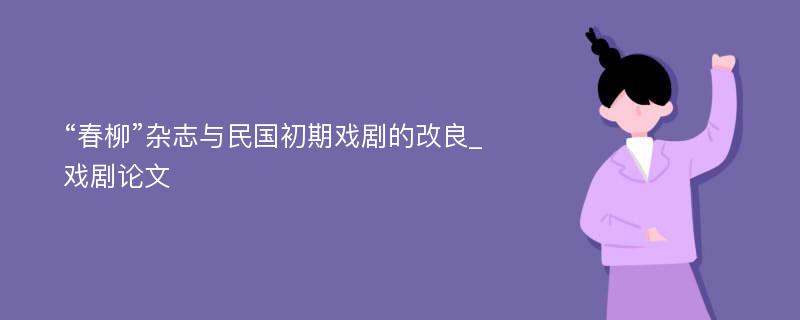
《春柳》杂志与民初之戏剧改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戏剧论文,杂志论文,春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民初之平津地区,《春柳》杂志据说是第一份戏剧专刊①,且影响颇大。以往之研究对这份刊物的关注多限于若干史料,如对春柳社之回忆、梅兰芳第一次东渡演剧之纪实等。但《春柳》杂志与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史之起点的春柳社之间有何关联?在梅兰芳第一次东渡演剧中,它扮演何种角色?在民初之戏剧改良中,又持何种立场?本文以《春柳》杂志为标本,通过《春柳》杂志之编辑、运作及相关话题,来探讨民初戏剧改良之某种情境。
一 《春柳》杂志之编辑、同人及影响
今之所见《春柳》杂志自1918年12月1日始,每月一期,但因社长随梅兰芳赴日,其间延误三月,第六期为1919年5月1日出版,第七期则迟至1919年9月1日才出版。1919年10月1日出版第八期,此期《春柳》并未宣布休刊,甚至还发布了筹备“梨园博物室”及投票选举“名伶”的“本社启事”,但其后之刊物即不见。1940年,《立言画刊》曾发表一篇小品文,作者追记《春柳》为民十之后休刊②,但该文所举《春柳》之事皆在《春柳》前八期内,因此无法依据此文判断《春柳》第八期后是否继续出刊。一般辞典记载均为《春柳》杂志出至第八期休刊。③
从这八期《春柳》来看,刊物的规模、栏目及风格大致稳定,创刊号有103页(含封面、封底等,以下计算页数皆同),此后除第3期为105页外,多维持在120多页的规模,第七、八期最多,分别为140页、150页。刊物售价为每册大洋三角,全年三元,并无变动。
《春柳》各期标明的“编辑及发行所”为“春柳杂志事务所”,前六期的地址为“天津河北公园后”,收信处为“天津河北建德里李宅”和“北京琉璃厂戏剧新报社”,第七、八期《春柳》上,“春柳杂志事务所”地址变更为“天津法租界四十九号楼上”,收信处则无。这意味着1919年7、8月间,《春柳》杂志可能有所变动。寄售处则一直标明为“北京天津上海各大书坊”,这标示了《春柳》杂志的主要受众范围。
《春柳》所登广告皆载于刊物正文之前后部分,“中国银行广告”仅出现在创刊号上,“天津造胰公司”、“铸新照相馆”则每期固定登载,至第七期。第二期开始出现“天津九州大药房自造人中血”广告,至第七期。日本“和合药水”广告,仅出现在第七期。第三期开始出现“国货玩具商品陈列所售品处”广告,此后亦每期登载。第六期有“介绍名医蔡希良先生”广告。因《春柳》申明为“同人杂志”,因此这些广告或多或少能显示《春柳》杂志同人之社会联系及阶层。如“中国银行广告”或许会令人联想起“梅党”,“天津造胰公司”广告为“所造各种国货胰皂群推为花妆最美之品凡演剧家皆乐用之”,“铸新照相馆”则强调有“现在京津名优肖相”出售,特别突出“演剧家”、“京津名优”亦标明该刊之目标读者群体。在“介绍名医蔡希良先生”广告中,则由“王琴侬王蕙芳朱幼芬姜妙香贯大元杨孝庭涛痕露厂”联名介绍,并言“先生医学渊深活人无算大有手到病除之神力同人等皆深知之谨此介绍”,这一推荐语则列出了《春柳》这一“同人杂志”的“同人”名单。
在上述《春柳》杂志“同人”中,“王琴侬王蕙芳朱幼芬姜妙香贯大元”为皮黄名角,“杨孝庭”尚待考,“涛痕露厂”之名则常见于《春柳》。“涛痕”即“李涛痕”,亦名“春柳旧主”,为《春柳》之社长,“露厂”名“李露厂”,为李涛痕之弟。李家兄弟几乎包揽了《春柳》的绝大部分评论文章。
李涛痕本名李文权,又名李道衡,1878年出生于北京,曾应乡试,参与变法,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后感于国事,放弃缙绅之路,改为“研究一致富之路,以为根本”,兴实业以救祖国。1906年去日本,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任中文教师,1910年10月,创办《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1912年改名为《中国实业杂志》,为该杂志的发行人兼总编辑。1917年8月回国,将《中国实业杂志》移至天津出版④,其社址与《春柳》杂志同。
在居留日本的12年间,李涛痕曾参与春柳社的活动。春柳社成立于1906年。在春柳社的第二次公演中,李扮演《黑奴吁天录》中的海雷、海留。在对此次公演的评论中,对于李涛痕的观感几乎是一致的,“涛痕的海留过分取乐观众,让人感到遗憾。但是作为普通的滑稽角色,其演技恐怕连我国新派演员也无法与之抗敌”、“其演技可能是社中最为熟练的,但可惜的是以熟练自居而无限度取乐的作派不敢恭维。看来还需再下些功夫。”“肆意发挥,使得前一幕(注:第一幕)中好不容易博得的好评付之东流”,从以上剧评中,可推测李涛痕颇有演剧经验,因此能以第一幕中所扮演的“海雷”博得好评,而在第二、三幕中扮演的“海留”为“滑稽角色”,他力图“取乐观众”,但这种“无限度取乐”的“作派”并不见好于日本的评剧家。此后,春柳社又排演了《生相怜》,李涛痕扮演“画家”,欧阳予倩此时扮演“画家”的“妹妹”。1908年,李涛痕又组织演出《新蝶梦》,登台演出者除李涛痕外,皆是初次上台。⑤其后,李涛痕继续倡导、组织春柳社的新剧演出,直至1917年回国,创办《春柳》杂志。李涛痕以《春柳》杂志为春柳社的继承者,自称“春柳旧主”,并叙述了一条从春柳社到春柳剧场再到《春柳》杂志的线索。⑥此外,从李涛痕的自述中,还可知其“酷嗜观剧”,至少有三十余年的观剧史。⑦
在《春柳》杂志上发表文章较多的,除李家兄弟外,还有齐如山、豂公、喃喃、袁寒云、罗瘿公等人,齐如山此时正为梅兰芳编戏,并研究改良旧剧。豂公即张厚载,时为北京大学学生,常有观剧文字见诸报端,并与胡适等《新青年》同人于戏剧改良发生争论。喃喃为春柳社成员,曾与李涛痕一起参与《黑奴吁天录》的演出。袁寒云、罗瘿公等人则为旧派名士、票友。从以上同人、撰稿人的构成来看,其群体熟悉旧剧,以致被认为是“票友同人”⑧,但某些成员对新剧有所实践并予以提倡。这一特殊背景决定其在民初戏剧改良中所持立场,并不同于《新青年》等新派团体。
这一点从《春柳》杂志的栏目设置亦可见出,封面为“题字”和“脸谱”,除广告外,栏目计有“翰墨”、“肖像”、“旧剧谈话”、“新剧谈话”、“名伶小史”、“名伶家世”、“名伶生辰表”、“戏场杂评”、“旧剧脚本”、“新剧脚本”、“文苑”、“小说”、“北京名伶演戏月表”、“戏剧词典”、“杂事轶闻”等。以上栏目,虽每期稍有增减,但其设置基本稳定。从性质上看,或可分作四类:一、“题字”、“脸谱”、“翰墨”、“肖像”栏目,按李涛痕之说⑨,为展示演员艺术才能之窗口,有展示、保存戏曲史料之功能。但有时亦会被理解为“捧角”;二、“旧剧谈话”、“新剧谈话”、“戏场杂评”、“旧剧脚本”、“新剧脚本”、“小说”、“戏剧词典”栏目,其内容为戏曲研究;三、“名伶小史”、“名伶家世”、“名伶生辰表”、“北京名伶演戏月表”栏目,虽是带有戏曲研究及提供演剧资讯之性质,但冠以“名伶”之称,或许亦有“捧角”之效果。四、“文苑”、“杂事轶闻”栏目,为文人、票友、伶人之间的唱和及八卦野史。
“四戒堂主人”谈及《春柳》为其时北京“颇为少见”的“专谈戏剧”的“定期刊物”,是“唯一之戏剧专刊”⑩。《春柳》创刊号上豂公之文亦提及:“余惟北京为戏剧鼎盛之地。评剧文字。亦汗牛充栋。独杂志之发刊。尚付阙如。诚为憾事。今春柳杂志出版。为之失喜。”(11)因为《春柳》杂志的这种独特地位,因此“发行时期销路极好”。尤其在举行“名伶”选举之后,“此种别开生面之‘菊选’,当时居然轰动京津一带,《春柳》销路亦竟因之陡增数倍。”(12)由此可略见《春柳》杂志影响之一斑。
二 建构“戏学”与新、旧剧之讨论
《春柳》杂志的宗旨为“改良戏曲”、“研究戏曲”。在其创刊号之“发刊词”上,社长李涛痕便以“答客问”的形式申明“春柳之目的非所谓改良戏曲针砭社会者乎”,而且,其致力的目标在于“研究戏曲”,“吾人须抬高戏曲之声价。俾人人知戏曲与文字有关系。戏曲与历史有关系。戏曲与美术有关系。戏曲与国家进化有关系”,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建构“戏学”,将戏曲作为一门学问,“抬高戏曲之声价”,并藉戏曲于大众之影响力,发挥其社会功用,“然后可以促进社会之程度。得以驾欧凌美焉”(13)。
《春柳》杂志诸多栏目的设置,如上文所分析,其实也体现了李涛痕所建构“戏学”之大略,既有史料收集与展示,亦有研究、批评与创作。各栏目的编者附言,处处皆以“戏”为标准,如“文苑”栏有“欢迎投稿以戏为限咏坤角者恕不登载”之语,“小说”栏有“小说以曾经演戏或能作脚本者为限不能演戏无关社会人心者不录”、“欢迎投稿凡小说之与社会有益而能编戏者本社极为欢迎”之语。当然,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将“新”与“旧”并列之举。如“旧剧谈话”与“新剧谈话”,“旧剧脚本”与“新剧脚本”,“名伶小史”中亦有对新剧、旧剧艺人之介绍,“新”与“旧”并行不悖。刊于《春柳》第二期的一段补白应是编者所言:“新旧水火自古如斯何以水火两派分歧孰优孰劣彼此不知。”此语可视为《春柳》杂志编者及同人对戏剧改良中“新”、“旧”对立之批评。
事实上,对于新剧、旧剧,《春柳》虽是分而论之,但绝非互不相干。如果细察“旧剧谈话”、“新剧谈话”二栏,就会发现,关于“旧剧”、“新剧”之“谈话”往往有所混杂,有时很难区分,譬如在前三期,齐如山共发表五篇文章,其中《论旧戏中之烘托法》、《论观戏须注重戏情》、《论编戏须分高下各种》发表于“旧剧谈话”栏,《新旧剧难易之比较》、《论编排戏宜细研究》发表于“新剧谈话”栏,除《新旧剧难易之比较》之外,其他四文其实很难将其内容截然区分为“新剧”或“旧剧”。同样,李涛痕等人的文章也常见于“新剧谈话”、“旧剧谈话”二栏。这也是说,对于“新剧”、“旧剧”之研究、批评,在《春柳》杂志的构想中,被放置于某种统一性或同一视野。
这种统一性或视野即是“改良”,在一文中,李涛痕谈到欧战后的社会趋势为“改良”,再具体到中国戏剧,“中国戏界之不可不改良者。亦甚多矣。然千端百絮,应自何处入手。曰当分新戏与旧戏。”(14)新剧和旧剧皆为需改良之对象。不过,因新剧、旧剧此时之状态、处境不同,其改良之道亦各有其方。
关于旧剧,话题较为广泛,既有齐如山对于旧剧之研究,又有李涛痕等人对京剧、昆曲、秦腔等声腔之介绍、演出之评论,以及对国外戏剧动向之译介。齐如山将旧剧定义为“由古时候传下来的”(15),主要从编剧、观剧角度予以研究,实际上谈的是旧剧的欣赏及写作方式上的“改良”。李涛痕则在“衣冠之宜研究”、“词句之宜研究”、“情节之宜审求”、“文唱之宜研究”四个方面,并针对“饮场”、“对镜理装”、“随意吐痰”、“跪拜后掷垫子”、“叫好”、“戏单”等现象(16),提出自己的方案。“戏场杂评”栏则对“喝彩”、“戏单”、“茶资”、“戏码”等各种戏剧旧规提出批评。
关于新剧,李涛痕、齐如山等人的论述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今日之新戏”,齐如山将其定义为“学的西洋样子”,并分为三类:“旧样子的新戏”,“仿电影的戏”,“仿西洋的戏。但是跟演说差不了多少。一点美术的思想也没有”。齐如山认为这三种新剧“要不得”、“不足为训”,因此在比较新剧与旧剧时,直接以西洋戏剧作为“新剧”来讨论。(17)这一表达与李涛痕相同,李涛痕认为“新戏之在中国,尚未有萌芽。”(18)而在另一篇讨论新剧的文章中,李涛痕认为“今日之新戏”并非新剧,“中国所谓之新戏可分两种。一为无唱之新戏。一为有唱之新戏。证以余所欲言之新戏。犹未可也。”(19)第二个层面为理想中的“新剧”,如前所述,齐如山直接将“西洋戏剧”当作“新剧”之样板来讨论,在曾亲身参与新剧演出的李涛痕看来,情形则较为复杂和具体:一方面,李涛痕极力阐明新剧之特质,“无唱之新戏。本为新戏之原则。是即Drama也。”但符合“无唱”这一原则的新剧,却往往过于随意,“惜乎今之自命为新剧家者。大抵未甚研究。在舞台上任意说话。三五分钟即为一幕,无一定之脚本。”因此,李涛痕提出“特别之布景”、“时与地之区别”、“讲求”“事实”等改良新剧之方(20),这些方案又与齐如山在《论编排戏宜细研究》一文中之表达相似。另一方面,李涛痕又举出昔日之“春柳社”与现今之南开学校新剧团作为理想中的新剧典范:“吾国新剧之兴。当然以春柳社为嚆矢。其后国内新剧团成立甚多。然较诸天津南开学校脚本而欲上之亦不可多得。”(21)在发表南开学校新剧团所编《一念差》脚本后,附言评价为“新剧脚本如此出所编之情节文笔曲折是足为近日中国新戏之杰作”(22)。
从上述讨论可知,关于“新剧”、“旧剧”之讨论,亦为《春柳》杂志所关注之重点,但由于《春柳》同人独特的位置,使得其虽亦以戏剧改良为目标,但其方案并非是以“新”换“旧”,而是将“新剧”、“旧剧”并置于“改良”这一视野之下,而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1919年9月1日,《春柳》第七期登载了一则启事,名为“梨园博物室启事”,曰“本社发起梨园博物室现正在组织中所望同志诸君匡予不逮切祷之至”,而且,社长李涛痕还计划“明年正月先行试办”(23)。虽然这一行动不知所终,但《春柳》杂志之运作及诸多实践仍能让人联想到十余年后齐如山等人所组织的国剧学会,这亦是中国戏剧界建构“戏学”之较早尝试。
三 制造“名伶”:《春柳》中的“梅兰芳”
随着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公共舆论空间渐次形塑,副刊、小报、杂志等传播媒介对于戏曲的影响亦是有增无减,在近现代戏曲史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名伶”的出现以及对于名伶形象的塑造——或曰制造“名伶”中,报刊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譬如,1927年《顺天时报》的一次“征集五大名旦新剧夺魁投票”的选举,便被认为与“四大名旦”之称号的出现有关。(24)而“四大坤旦”之称号,也源自《北洋画报》的一次票选。在《春柳》杂志上,冠以“名伶”的栏目颇多,作为一份销路极广的京津地区唯一戏剧专刊,其对于“名伶”的认定会有相当的影响力。刊登于《春柳》第八期的一则启事则提供了一个其对“名伶”之认定及其效果的反馈。这则启事是因《春柳》的固定栏目“北京名伶演戏月表”而发:
本杂志所列名伶演戏月表,其意有二:一以觇名伶演戏之成绩,一以备阅者诸君之查考。但于此有两难点:一为名伶之界说,一为排列之次序。夫所谓名伶者,必其技艺优美而能博一时之盛誉者也,然而顾客之心理不同,享名之途径或异,则甲之所谓名伶,乙未必从而名之;乙所谓名伶者,丙又未必从而名之。况以本社区区数人所鉴定者,又乌得尽合阅者之心理哉!此一难点也。由前之说进而言之,则所列诸伶之次序亦大有可以研究者,其实在吾人执笔纪录,初无一定之成见而有所轩轾于其间,然在阅者视之,或不免疑有爱憎究之,将以技艺之高下而前后之乎,抑以享名之隆替而抑扬之乎,此亦一难点也。(25)
启事中的这段文字述说的是在“名伶”认定上的问题,简言之,一位艺人何以入选“名伶”?在“名伶”中占据何等位置?虽有公认的标准,但这些标准难以确定,因人而异。《春柳》的“北京名伶演戏月表”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原因或许在于:在编者看来,这份“北京名伶演戏月表”本为提供演戏资讯而制,但在读者中却产生了类似于“名伶”“排行榜”的效果,因此对其标准及公正性发出质疑。正如《记〈春柳〉之名伶选举》一文所忆:“乃为时既久,阅者中竟有去函质问某人何以不列入‘名伶’之内?该社烦不胜烦,于是在民国八年之后的半年间,在《春柳》上注销启事,公开投票选举二十一位‘名伶’”(26),而举行“名伶”选举的效应则是“轰动平津一带”。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恰好展示了一个“名伶”制造的运作过程。
由于《春柳》杂志特殊之背景,在其所涉诸多“名伶”中,梅兰芳可谓是“出镜率”最高的一位:每期《春柳》皆会出现梅兰芳及与之有关的文章资讯,绝大部分栏目都曾不同角度地涉及梅兰芳。在引起争议的“北京名伶演戏月表”中,梅兰芳始终占据首位——无论这一“排行榜”是由《春柳》同人所选,还是公开投票“菊选”。梅兰芳第一次东渡日本演戏,《春柳》社长李涛痕及撰稿者齐如山随同前往,《春柳》亦延期三月。梅兰芳东渡前后,《春柳》均予以大篇幅的报道。事实上,《春柳》杂志上诸多的报道、批评、研究、轶闻,不但固定了梅兰芳的“名伶”地位,更重要的是,梅兰芳的“名伶”形象由此被塑造起来,并赋予意义,使其不仅晋级为“世界名优”,而且被视作戏剧改良之“先锋”。
在《春柳》创刊号上,当李涛痕谈论“今日之新戏”时,以“无唱”为新剧之原则,因而将梅兰芳的一系列新编戏定位为“过渡戏”,“至今日而梅兰芳之一缕麻邓霞姑牢狱鸳鸯等”,“非不美也非不可以改良社会也。然止可谓之为过渡戏。不得谓之为新戏。”(27)但在《春柳》的描述中,虽然梅兰芳所演并非新剧,但非为梅兰芳之过,“盖兰芳尚未尝演新戏也。不过演过渡戏而已。其所以然之故。非兰芳之不能演新戏,亦非无新戏脚本也。特患配角少耳。”(28)而且,登载于《春柳》第三期上的梅兰芳观看新剧的轶闻也透露出梅兰芳对于新剧的学习兴趣。
李涛痕给中国戏剧开的改良之方有两点,“一为就内部以改良。二为游外国以考求。上述之衣冠词句情节文场。是皆内部也。至于游历外国以考求艺术,噫,今之伶界宁有其人乎。”在两点中,李涛痕似乎更强调后者,“中国人不好游。于是无世界之眼光。由北京至天津。则以为出外矣。此种乡里之脑筋。市井之思想。又何能造就一世界名优也耶。然则欧战后亦不可无人提倡此事也夫。”(29)正当李涛痕呼吁“伶界”“游历外国以考求艺术”之时,梅兰芳东渡日本运作成功,因此,《春柳》第三期上,便立即登载了“梅兰芳将游日本”的消息,称“伶界人物当至外国游历。以期技术增进”。并赞美梅兰芳此举“是为伶界之创举。而中国戏之文明可发扬于海内外矣”。接着,《春柳》第四期又登载“法美争聘兰芳”之消息,从齐如山的回忆来看,应是并无其事(30),作为梅兰芳东渡之行的成员,李涛痕发布这一消息,或是为梅兰芳此行造势,以塑造梅兰芳“世界名优”之形象。
梅兰芳东渡的前前后后,《春柳》杂志予以全方位的跟踪报道及宣传,继第三、四期报道梅兰芳东渡及法美“争聘”消息后,第五期《春柳》涉及梅兰芳的篇幅更多,“肖像”栏载有东渡诸伶之剧照两桢“此次受聘往日本者梅兰芳姚玉芙姜妙香之断桥”“芙蓉草化身此次聘往日本演剧之一人”,“旧剧谈话”栏载李涛痕文《梅兰芳到日本后之影响》,“新剧谈话”栏载春柳旧主(即李涛痕)文《梅剧与新剧之区别》,“名伶小史”栏载梅兰芳之伯父梅雨田之小传,“文苑”栏载多首送梅兰芳东渡的赠诗,“北京名伶演戏月表”中梅兰芳仍然占据首位,补白处亦有特别预告“本社社长为兰芳东渡有关中国艺术之发扬亲赴日本调查一切下期当以见闻所得详为披露特此预告”。到第七期,梅兰芳东渡诸人已归,于是,“肖像”栏载梅兰芳在东京演《天女散花》剧照,“旧剧谈话”栏载《梅兰芳何以能享盛名》、《今岁剧界之活动》二文,“文苑”栏载赞梅兰芳东渡的赠诗多首,《北京名伶演戏月表》中梅兰芳依然名列首位,“杂事轶闻”栏则发表《梅兰芳东渡纪实》。
在《春柳》杂志的诸多报道、批评文章中,对“梅兰芳东渡”之意义的阐释,除扩大中国戏剧及梅兰芳之声誉外,主要集中于此次东渡对于戏剧改良之影响:
同业者虽未能人尽同游,然而闻归述之词,亦间接得许多参考,他日改良戏曲,决不能专靠兰芳及少数同游之人。希望同业者之对于兰芳等此行也不必羡之,亦不必忌之。当俟彼等归来,聆彼等之谈话,为改良之计。(31)
其大目的则尤愿研究新戏,他日归国而组织完全新戏也。故同行诸人,苟无此资格者殆不能同行,且同人中亦颇有研究新戏之志愿。抵东献技以后,不惟宜观新戏数日,以为一种参考。而尤宜多访各新剧家,一聆其言。则将来之梅剧,由过渡戏而首先诞登彼岸也。余日望之。(32)
在评论者看来,梅兰芳东渡之行的意义,一方面可促进旧剧内部的改革,因东渡演出之需,梅兰芳对一些戏曲旧规作了改革,“又此次东游。不饮场。不吐痰。不用检场之人。拜跪后不掷垫子之类。”(33)因梅之影响力,这些改革亦会促进国内旧剧之变化;另一方面,以梅兰芳为首的诸名伶在日本对新剧的观摩和经验,亦会影响他们实践新剧的态度。因此,在梅兰芳归国后,《春柳》杂志便立即宣布梅兰芳的三个目标:“设学校”、“建舞台”、“编新剧”。(34)
自近代以降,“趋新”为推进中国现代性之动力,影响于现代中国的各个领域。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新旧混杂及不均衡性,“新”“旧”之间有着相当错综复杂的中间地带,即如罗志田所言之“多个世界”(35)。在民初之戏剧界中,“改良”之议虽为大趋势,但具体到不同的社会群体,因地域、知识背景及立场的差异,其想象和方案则各不相同。《春柳》杂志及其同人之实践,则为我们理解和探索这一复杂样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
注释:
①春柳旧主《今岁剧界之活动》,《春柳》1919年第7期。该文称“从前虽有评剧文字,散见于日报或杂志,而刊行专门杂志以行世者,实自春柳始”。
②四戒堂主人《记〈春柳〉之名伶选举》,《立言画刊》1940年第6期。
③《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第36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第225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④《中国实业杂志》,《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第188~19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中村忠行《春柳社逸史稿(二)——献给欧阳予倩先生》,《戏剧》2004年第4期。
⑥春柳旧主《春柳社之过去谭》,《春柳》1919年第2期。
⑦春柳旧主《今日梨园之怪现象》,《春柳》1919年第4期。
⑧四戒堂主人《记〈春柳〉之名伶选举》,《立言画刊》1940年第6期。
⑨李涛痕《提倡伶界文学之必要》,《春柳》1919年第6期。
⑩四戒堂主人《记〈春柳〉之名伶选举》,《立言画刊》1940年第6期。
(11)豂公《菊部剧谈录》,《春柳》1918年第1期。
(12)四戒堂主人《记〈春柳〉之名伶选举》,《立言画刊》1940年第6期。
(13)涛痕《发刊词》,《春柳》1918年第1期。
(14)涛痕《欧战后应改良之剧界各事》,《春柳》1919年第3期。
(15)齐如山《新旧剧难易之比较》,《春柳》1919年第2期。
(16)涛痕《欧战后应改良之剧界各事》,《春柳》1919年第3期。
(17)齐如山《新旧剧难易之比较》,《春柳》1919年第2期。
(18)涛痕《欧战后应改良之剧界各事》,《春柳》1919年第3期。
(19)李涛痕《论今日之新戏》,《春柳》1918年第1期。
(20)李涛痕《论今日之新戏》,《春柳》1918年第1期。
(21)涛痕《〈一念差〉编者注》,《春柳》1919年第2期。
(22)《一念差》,《春柳》1919年第4期。
(23)春柳旧主《今岁剧界之活动》,《春柳》1919年第7期。
(24)吴修申《顺天时报评选“京剧名伶”》,《民国春秋》2000年3期。另,参见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第429~4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么文对《顺天时报》之选举与“四大名旦”之称号的关系提出质疑,或可推断,“四大名伶”之称与此次选举虽无直接关联,但应是这一习说被追溯的某个源头。
(25)标点为作者添加,原文无。
(26)四戒堂主人《记〈春柳〉之名伶选举》,《立言画刊》1940年第6期。
(27)李涛痕《论今日之新戏》,《春柳》1918年第1期。
(28)春柳旧主《梅剧与新戏之区别》,《春柳》1919年第5期。
(29)涛痕《欧战后应改良之剧界各事》,《春柳》1919年第3期。
(30)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第126~15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版。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谈及东渡归国后多方努力运作梅兰芳赴美之事,可见“法美争聘”并无其事。
(31)涛痕《梅兰芳到日本后之影响》,《春柳》1919年第5期。原文仅有句读,今改为标点。
(32)春柳旧主《梅剧与新戏之区别》,《春柳》1919年第5期。原文仅有句读,今改为标点。
(33)涛痕《梅兰芳到日本后之影响》,《春柳》1919年第5期。
(34)春柳旧主《今岁剧界之活动》,载《春柳》1919年第7期。
(35)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