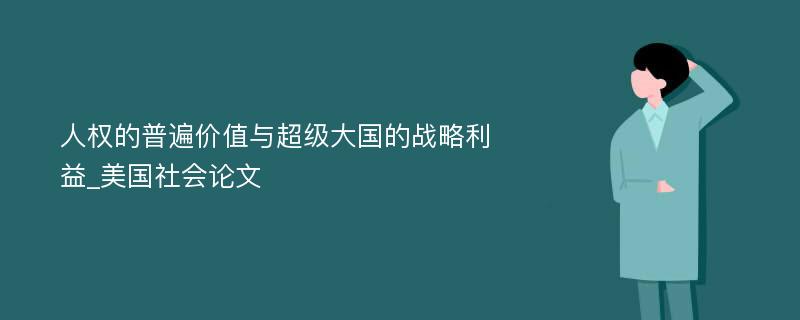
人权的普世价值与超级大国的战略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超级大国论文,人权论文,利益论文,战略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7年开始,美国国务院一年一度发布《各国人权报告》,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虽然受到《200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批评的印度政府将此称作只是美国国务院的“例行公事”,但是,谁也无法否定,这种持之以恒的“例行公事”已经产生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以此显示了自己导引人类政治文明的无以伦比的“软力量”。它就像一个有着巨大魔力的巫师一样,通过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的发布,向世界各国吹响了自己的魔笛。它颠覆、摇撼和敲打着各国政权的权力宝座,让世界各国无数的知识分子和人民随着它的魔咒的节奏而起舞。
人权报告的发布,以及针对报告中所谴责的行为,对美国强大的舆论、外交和军事力量的运用,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因而,如何切当地解读美国的人权魔咒就成为理解国际政治、把握世界精神和切实有效地推进发展中国家自由民主事业的关键课题。
一
《报告》的导言写道,美国之所以坚持人权外交,是“美国的立国价值观和我们持久的战略利益促使我们做出这一承诺。”(注:美国国务院2004年2月15日发布的《200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导言)。)美国人认为:“只要我们毫不松懈,通过编写人权报告并采取有计划的行动让人权报告不局限于罗列事实,就能促进美国的利益。”(注:美国国务院2004年2月15日发布的《200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导言)。)国务卿鲍威尔先生在《报告》序言中更是满怀豪情地宣称:“我坚信,我们坚持了准确、全面的高标准——正是这种标准给我们在过去带来了突破,使我们将来的成就成为可能。”(注:《200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序言)。)
我们承认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体现出来的,以保护个人权利作为政府目的的美国的立国价值观中,确实闪耀着普世性的光辉。我们也认识到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人权外交,对威慑滥用权力的暴政,促进各国的法治和民主化,包括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起的十分重要的正面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美国把人权的普世价值和自己的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将追求对整个世界的战略控制等同于为全世界人民谋求自由时,一种危险的僭妄已经出现了。就像个人宣称他就能代表上帝那样,当一个国家敢于宣称它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时,那么,它的国家意志中无疑已经附着上了恶魔性的因素。
当美国凭借其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喝令世界各国遵循它所制定的“规格统一”的“准确和全面的高标准”,并称不能容忍以文化差异和特殊情况为借口抗拒这个标准时,人们获得了一种印象,就是仿佛各国的主权不应该从其自身真实的存在处境中有机地生长起来,而应像世界各地无数的肯德鸡、麦当劳分店一样,完全按总部提供的一整套现存的精确和全面的标准化指令来加以构建。在这里,美国在精神气质上,是否已经和其所致力战胜的敌人,一种极权主义的致命的理性自负,变得极其相似?当美国满怀豪情地强制各国立即执行它所制定的“准确和全面的高标准”时,它表现得似乎完全忘记了,它自己达到目前这种令人羡慕的人权状况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表现得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假如目前世界上有一个比美国强大十倍的权力,强制它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先进国立刻全面执行所谓的“高标准”的话,也必然会给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带来巨大的,甚至致命的损害。
严复曾经说过:“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注:参见严复的《中俄友谊论》。)严复思想中的真理性,用更为准确的政治哲学语言来加以诠释的话,就是政府能够给予每个国民的自由只能是保护其免于他者伤害的消极自由,而每一种消极自由的实现,又都必然是以对某种相应的积极自由的强行限制作为前提的。要使国民有免于强奸伤害的消极自由,惟一的办法就是限制每个人强奸他人的积极自由;要使人们能够免于被侮辱和诽谤,惟一的办法就是限制个人和媒体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自由;而要使每个人能够有效地得到国家的保护,就只能限制任何个人和组织依凭激情和野心任意地颠覆和撕裂国家的自由。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而理性地加以使用的一种强制力,衡量这种强制使用是否正当的标准就是它是否为保护国民免于伤害的权利所必需。假如,它不是为保护人权所必需,那就构成了对积极自由的过剩压抑,因而对政府的这种过剩压抑的废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假如一种强制是维护主权和保护国民安全所必需的,那么,对它的废除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和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的加剧。而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为了达到有效地保护国民安全这个共同目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中,国家政权必须使用的强制力的力度和范围不可能是一样的。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有这么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由多个有着相互仇杀传统的部落组成,其中没有融合成一个有着统一语言的主导民族,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盲;而另一个国家则富裕、繁荣,有着数百年的法治传统。那么,怎么可能用完全一样的统治方式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中实现和平呢?简而言之,假如我们在一个卢旺达式的国家中,全套照搬美国式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除了是部落之间相互残杀的自由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二
事实上,目前人权状况比较好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其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无不使用过最血腥的暴力。美国社会的形成就是以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作为起步的,并且正是在其后一个多世纪的贩卖黑奴,强制黑人从事奴隶劳动,以及奴役亚洲劳工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现代德国则产生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日本在亚洲发动惨烈的殖民战争;法国则大肆抢夺非洲殖民地。我们仔细省察近现代世界史就会发现,这么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就是,目前人权状态最好的那些大国,恰恰是历史上人权纪录最糟的国家。现在的纯洁的“天使”,正是以前的最邪恶的“恶魔”。
美国和这些前殖民主义的大国是幸运的,因为它们犯罪犯得“恰当其时”。当美洲的白人放开手脚大肆杀戮印第安人,宣称“最好的印第安人是死的印第安人”时,并不存在什么人权NGO充满道德义愤地谴责他们的种族灭绝罪;在美国贩卖和奴役黑人时,还不存在一个联合国追究它的贩卖人口罪和蓄奴罪;在西方列强发动殖民战争,将整个人类推进血泊中时,也没有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它们的反人类罪。恰恰相反,这一切最令人发指的罪行,都是以最美好和最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1870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作为这场殖民主义事业的领导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满怀豪情的动员报告。一个多世纪后重温这个讲话,对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理解现代性中的野蛮性、残酷性和单边主义,依然有着重要启示。利奥波德讲道:“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全球惟一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战。”(注:刚果人在利奥波德的残酷压榨下,从1885至1908的20多年间,人口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这就是他冲破“黑暗”,带去的“文明”。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505页。)仿佛这些以“文明”的名义进行“圣战”的国家,正是依靠血腥的殖民主义,才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到现在的文明水平,因而有了资格和能力,来向那些以前被它们烧杀抢夺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一场以“人权”的名义进行的新的“圣战”。再次冲破笼罩它们的“黑暗”,为它们带来“进步”。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人权本身的重要价值,否定发展中国家切实改变自身人权状况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前殖民主义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然而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美、英等国对它们从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有过痛切的反省,有过像西德总理勃兰特为纳粹屠杀犹太人下跪赔罪那样的行为。相反,我们常常听到的倒是他们在自夸为我们带来了文明。因而,那些对自己的战争罪责还缺乏足够反省的前强盗国家向被它们侮辱和伤害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人权要求,并采取了一种单边主义的蛮横和傲慢的态度,怎么会不引起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强烈反感呢?这样的人权要求,由于有着太浓的历史讽刺意味,怎么能不亵渎了人权本身的神圣价值呢?
三
当然,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历史之中,而应该面向现实和未来。不管各国历史上的人权纪录如何,由目前人权状态较好的国家,对人权状态较差的国家提出批评,共同促进全球自由秩序的扩展和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首位的重要性。但是,要真正达到这样的目的,发达的大国在提出人权批评时,必须遵循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找到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权标准,而不是自我中心主义地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中具有特殊性的成份和人权的普世价值混为一谈;二是需要同情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三是要求他国做到的那些标准,也必须同时用来要求自己。总而言之,人权批评只有在真正是出于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政治文明水平的目的,而不是以人权为借口来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时,才可能是良善的,而非邪恶的。
然而在事实上,由于美国习惯于自我为中心地强行推销自己的人权标准,发展中国家在其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上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国民安全不得不对自由所作的那些必要限制,在美国的“准确和全面的高标准”的对照下,总是被看作不必要的过剩压抑,看作必须被立刻废除的专制和邪恶。因而,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种“高标准”的人权谴责之下,难以避免地在道德上成为可疑和邪恶的。可是,当这些不合标准的政府在美国的压力和支持下被推翻之后,往往并不能生长出一个健康的美式政府来,整个社会经常反而陷入动乱和倒退。像南斯拉夫,它的各个民族在外部势力的鼓励下争取独立,暴力反抗其原有的统一政府,导致了长时间的酷烈战争和种族灭绝事件的发生。而苏联在美国的人权魔咒下自行解体后,其大部分原加盟共和国除了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大倒退之外,也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和人权状况的退化;十多年来,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动乱和暴力犯罪。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因其东方文化背景全都出现了强权政治。在土库曼斯坦,民众和媒体已不能直呼总统尼亚佐夫的姓名,而必须称“土库曼巴什”(意为“土库曼之父”),室内、街头到处都是尼亚佐夫的画像或雕塑。在阿塞拜疆,总统开始在父子之间继承。而俄罗斯则因车臣战争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政治避难者输出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2003年头九个月就有2万3千多人逃离俄罗斯向外国申请政治避难。这一切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相比都是严重的倒退。
而且,即使是对那些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和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通过外部武力推翻其原有政权,除了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人道主义代价之外,能否真正有效地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依然是十分不确定的。我们看到,美国扶持的文官政府完全无力有效地管理阿富汗,一旦美军撤出,阿富汗将重新陷入军阀间的内战。而在伊拉克即使在大量美军占领的情况下,也没能有效制止反美武装力量的暴力反抗。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格鲁吉亚、海地等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不断革命”的现象。对熟悉毛泽东的七八年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理论的中国人来说,要理解在美国的人权魔咒下引发的激进自由主义的“不断革命”并不困难。当人民满怀对未来乌托邦的憧憬,推翻一个“不合人权标准”的政权之后,他们发现得到的往往是一个更加“不合标准”的政权,因为革命引发了各民族、各阶层相互对立的激情,摧毁了使人们能够和平相处的各种传统之后,新政权为了建立秩序,总是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去限制言论自由和镇压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同时,社会的无序也使官员变得更容易腐败。而这必然激起处于革命冲动中的人民的更大的愤怒,和美欧各国分贝更高的人权谴责。于是,一场新的更彻底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必须从自己的土壤中有机地生长起来,而不可能通过一种外部的强制力来机械地加以构建。假如我们把美国的主权看作是一棵在法治传统下生长了二百多年的参天大树的话,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仿佛是许多长得有点歪歪斜斜的中树和小树。现在,这棵大树用自己的尺寸度量了这些小树之后,充满蔑视地发出了愤怒的命令:“你们必须被连根拔起,按照我的模样重新生长!”但是,这些小树重新长出来后,却变得更加脆弱和更加歪歪斜斜。于是,又一次被粗暴地连根拔起。在这样的“不断革命”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政治文明水平变得日益恶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美国在竭力用人权来限制、削弱和颠覆各国主权的同时,对自己的主权却无比珍爱。美国是至今为止惟一没有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发达国家,即便是对《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它也一直不愿加入,直到1992年在作出实际上排除国内适用的保留后才勉强批准。(注:参见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页。)另外,对各种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全球环境的国际公约,它一贯持十分消极的态度。总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不愿意受国际法约束的国家,因为它希望能够完全自主地行使主权和自由地使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当这个超级大国依凭无可匹敌的军事、经济和理念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各国的主权时,这确实是完全符合它自己的“持久的战略利益”的。像苏联这样的大国解体,美国使自己不再有战略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了长久的军事安全;而在大量的小国所引发的激烈冲突,则为其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军事占领提供了理由。然而,在它通过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的人权外交追求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却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国家的人民以人权的名义推入战争和动乱之中。这不禁让人想起有些学者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精神导师列奥·斯特劳斯的显白教诲和隐晦教诲的区分。确实,这些目前主导美国政局的新保守主义鹰派政治家,他们向别国大力推销的是洛克,而自己的灵魂深处却隐而不露地深藏着一个尼采。
四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中,总是同时存在着保守和激进这两种力量。诚如J.M.凯恩斯所言,就像保守势力中总是存在一个顽固派那样,在激进势力中总是有着一个“破坏派”。“这个派别憎恨或鄙视现存制度,而且相信仅仅是推翻它就可以获益无穷,或者至少是把推翻现存制度看作是取得任何巨大进步的必要前提。”(注:J.M.凯恩斯:《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因而,它总是在竭力煽动怨恨和狂热的社会情绪。我们知道,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转型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英国和法国二种不同模式。前者是以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或称保守派的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它相信任何一种消极自由的获得,都是以对某种相应的积极自由的限制为前提的。因而,追求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扩展的精制的强制系统的构建过程;后者则以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为主导,它相信追求自由,也就是通过革命挣脱一切束缚来获得彻底的解放。历史告诉我们,在追求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前者比后者取得了远为卓越的成效。
发人深省的是,二百多年来美国始终是以稳健的英国模式来追求自由的,而现在它却以人权的名义,鼓励着各个发展中国家内部最激进的反叛行为。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那些激进的破坏派,高呼着空洞和狂热的口号,要求撕裂自己的国家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心生困惑:当一个人如此地缺乏自省和教养,在作出如此幼稚和不负责的行为的同时,为什么还会有那么一种根深蒂固的惟我独善的道德傲慢呢?这么一种道德傲慢在历史上我们只是在雅各宾派和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身上才见识过。但是,我们认真地研读了美国的《报告》之后才恍然大悟,才找到了这种道德傲慢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上的根源。这些激进的破坏派在痛斥自己国家时的语调和《报告》简直完全如出一辙,他们相信只是因为自己毫无反省地认同了美国提出的“准确和全面的高标准”就已经变得无比神圣。虽然他们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切实的建设性工作帮助自己的国家成长,却仅仅因为发现了这个国家和“高标准”之间的差距,就趾高气扬地认为已经找到了傲视生活在这个国家制度中的所有人的充分理由;他们的事业就是要将这棵“不合标准”的树连根拔起,并且陶醉在不顾一切,尽情破坏的勇气之中。
为了要提醒人们充分认识这样的破坏派的危险和荒唐,霍布斯和柏克曾经讲述过同一个希腊神话。塞撒里(Thessaly)国王柏利阿斯(Pelias)的女儿们,听信巫师美狄亚(Medea)的唆使,不顾一切,鲁莽地把自己年迈的父亲切成碎块,放到巫师的锅里去煮,希望用一些有毒的药草和疯狂的咒语就可以使父亲返老还童,恢复青春。对世界各国激进的破坏派而言,他们从美国这个美狄亚一年一度的人权魔咒中听到的正是同样的信息:“不要害怕把你的国家和人民推到战争和动乱的锅里去煮,只要你按照我的咒语而行,你的国家就会变得像我一样健康和强大。”
一般而言,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这样的激进的破坏派成不了大的气候。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越低,再加上外部力量的影响,就会使这种激进的破坏力量变得越强大。而一旦这种激进主义成为主流,一个社会的灾难将无法避免,任何有序的建设性的改革和发展都会被其冲断。而且,政治史告诉我们,一种卑贱的最具有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总是在一个社会产生真正的希望,在政府真诚地想要改革时,才变得具有最大的杀伤力。在一个严厉的独裁者面前,一个卑贱的破坏者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幻想,知道他会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自己;相反,一旦他感受到执政者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和仁慈时,就会开始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怨恨。随着开放和改革的深化,如何清理和化解我们民族文化意识深处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激进主义,以及分析它的国际文化背景,已成为目前人文知识界最为紧迫的课题。只有在遏制和化解了激进主义之后,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享受到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中的正面价值。
五
最后,有必要分析一下激进的破坏派对自己所在社会的现实和传统所持的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为了揭示这种态度的荒谬性,我们只须做这么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就是用他们那种惟我独善的道德傲慢,那种激进批评的摧毁性态度(注:“蒙迪卡罗协会”由杰佛逊的700多名嫡系后裔组成。2002年该协会的八十名领导成虽投票,结果74票反对,拒绝杰佛逊和其女奴海明斯的后人加入该协会。),反过来抨击作为他们傲慢的精神支柱的美国。这时,我们发现连美国也将变得一片漆黑。
所有的“人权斗士”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独立宣言》中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这段名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话庄严肃穆,所有的转述者和阅读者都会深受它的感染。然而,“人权斗士”们在引述这段话时,总是忘记了它被说出时的真实语境。这些豪言壮语是二百多年前美国的白人向英国人“要自由”、“要民主”时喊出来的,而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他们想把这些权利给予黑人。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人”,完全不包括现实中的黑人。因为发出这些豪言壮语的美国白人在此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即不仅仅终其自己的一生,而且终其子女的一生,依然泰然自若地捆绑、捕杀、鞭打和贩卖黑人,泰然自若地享受着强制数百万人从事非人的奴隶劳动而产生的丰裕的物质成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亲手写下这段文采斐然的神圣话语的托马斯·杰佛逊正是一个蓄奴者。他不仅仅在写下那段话之后的数十年中(1776-1826年)坦然地奴役着自己的奴隶,而且和自己14岁的女奴发生奸情,之后生下了一堆混血的私生子。(注:孱弱的中国人在其数千年历史中,始终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和高效的”奴隶制。因为他们相信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孔孟的说教,相信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仁”,在“不忍人之心”,在事事为他人着想的“恻隐之心”。正是因为深含着沦为“禽兽”的恐惧,中国人在其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将“蛮夷之族”变为奴隶。然而,令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创建了近代以来最现代和最庞大的奴隶制的美国人,他们非但没有沦为“禽兽”,反而站在数百万黑人的白骨之上,宣布了天赋人权的普世真理。而这些事情,正是同一批人,在同一段时间里完成的。而战战兢兢唯恐沦为“禽兽”的中国人,在以缺乏力量的名义遭受了第一次侮辱之后,现在,正在以缺乏政治道德的名义遭受第二次侮辱。)然而,正是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奴隶主,以一种庄严肃穆的神情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和自由权神圣不可剥夺的真理。上帝啊,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
谁都知道,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就捆绑、拷打和贩卖自己的同类,强制其从事绝望的奴隶劳动,这需要多么强健的神经,多么坚韧的意志,多么冷酷的理性。(注:我们看到,这完全违反了道学的“反身求诚”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尤其令人惊厥的是,一个人在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恶行的同时,还能够以一种天使般的纯洁发布“人人平等”的福音。这样的人究竟是以怎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呢?这是在追求现实利益时敢于担当最血腥的罪恶的残酷和满怀激情地向他人推销道德信念时丝毫不反省对照自身的无耻的混合物!这就是创建了美国的国父精神,这就是深深地蕴含在《独立宣言》中的美国的立国精神,这种精神绝不仅仅只存在于美国的过去,而是作为美国的立国之道,一以贯之地穿透于它的二百多年历史之中。它体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年年谴责别国的人权状况,却对自己的恶行始终装聋作哑的当代美国政府身上;尤其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年年屠杀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用武装暴力输出“人权”,泰然自若地将世界各国人民推进内战、动乱和经济崩溃深渊的新保守主义政客身上!
这种单边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存在于一切美国人所创造的事物中,存在于美国一切最伟大最纯洁的政治家身上,存在于一切美国人自以为最完美最神圣的制度之中。我们看到,它首先以最触目惊心的方式存在于林肯身上,这个被许多人打扮成神的、美国历史上最圣洁的总统,决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为了解放奴隶才发动南北战争,而是相反,为了捍卫统一,打赢战争,才解放了奴隶。所以,他签署命令时,宣布解放的只是自己敌人(南方各州)的奴隶,而自己人(北方蓄奴州)的奴隶则依然泰然自若地保存着。他的政治道德的逻辑是,我们的敌人蓄奴是邪恶的,所以必须解放,而我们自己人蓄奴则是正义的,所以必须保存,对于自己人和敌人绝不能使用同一个标准。它同样存在于美国人无比自爱的司法制度中,有些美国人和“崇美狂”(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统治世界时,全世界出现了一批“慕英狂”,他们竭尽全力要使自己的衣着穿戴、言行举止完全合乎英国绅士的标准,只要发现发型、服饰上和英国人有一点差异就自卑不已,羞惭得认为自己的生存已彻底丧失了意义。现在,世界各国又出现了一批“崇美狂”,他们以一种同样的激情,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自己国家的制度乃至生活方式改造得和美国一丝不差。)们对它的拜物教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认为必须用贫轴弹和子母弹向世界各国输出这种制度。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尽管已经经过了长达二百多年的进化和改良,目前的美国在这种司法制度下,普遍地看“犯有同样罪行的黑人和有色人种总是受到比白人重2至3倍的惩罚,而杀害白人被判死刑的黑人则是杀害黑人被判死刑的白人的4倍。”(注:数据来自联合国发表的调查报告,转引自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更不要说,由于富人能够请得起更好的律师,因而犯了同样的罪行之后,普遍地看富人总是比穷人受到较轻的惩罚。经过漫长的二百多年的实践,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美国跛脚的现行司法制度,根本没有能力抵制金钱、权势和社会偏见对司法公正的系统扭曲。相反,这个已经被邪恶所彻底渗透的制度,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美丽词藻的装饰下,将富人对穷人的阶级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完全制度化和合理化了。美国人和“崇美狂”们竭力推销这个制度的理由是“司法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所须考虑的首要价值究竟应该是公正,还是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彻底独立呢?假如司法独立仅仅被用来独立地进行制度化的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那么,这种“独立”难道不是世界上最野蛮的邪恶吗?(注:即使是一个最激进的“崇美狂”,也无法在中国的死刑判决中,统计出这么一个类似的数据来:藏族人(或维族人)杀死汉人后被判死刑的数字,是汉人杀死少数民族后被判死刑数字的4倍。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法官是对照标准统一的刑法来给罪犯量刑的。虽然也有不少贪赃枉法的例子,但偏差绝不会大到4倍这么夸张,连1倍也不可能。而金钱对中国现行司法公正的扭曲能力,也很难说比美国现行制度更大。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在目前中国的现状下,假如一夜之间全盘照搬美国的司法制度,那么,司法公正在富人与穷人,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扭曲,就绝不仅仅只是3、4倍的问题(这是这种制度进化了200年的结果)。它将无可避免地扩展到8倍、10倍、40倍,而这样的国家势必被下层人民的暴力革命所推翻,从而陷入不断革命的境地。2000多年前的法家,在挖苦那些想以三代之制求当下之治的教条主义者时,发明了“刻舟求剑”这个寓言。那些想原封不动地移植美国的制度,来追求中国的公正的“崇美狂”,恐怕比那位“刻舟求剑”的先生都不如,因为,那位可爱的先生至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弄清了剑是在船的什么位置上掉下水的。而我们的“崇美狂”们,连这套制度在美国的实践中造成了哪些邪恶和不公都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又遑论用它到中国来实现他们想象中的绝对正义呢?开玩笑地说,有时候我们倒想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假如,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反过来是美国的8倍,而中国每年的军费开支是美国的20倍的话,那么,届时也许真的会有人严肃地向美国推销中国式的行政主导的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届时也许在我们的社会中会涌现出大批博学和雄辩的理论家,来蛊惑天真朴质的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激进知识分子,起来颠覆自己搞了几百年依然不能“根治”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的“邪恶制度”。)
当然,我们深知,这种单边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尤其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现代性之中。而美国的精神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最典型和最集中的反应。这个民族在短短的二个世纪间爆发出来的现代性力量令人惊叹。所以,这个超级强权假如要向他人介绍自己征服、奴役、统治自然和人类的技艺和经验,我们确实只有毕恭毕敬,洗耳恭听的份。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它却偏偏热衷于炫耀自己政治上的德行,这种用尼采的精神向他人推销洛克的单边主义的把戏,又怎能瞒得过一个数千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反思平衡的政治道德的古老民族的眼睛?
我们对美国的批评,并非想要改变美国的精神传统。所有的创造中都包含着恶,但对创造者自身而言,创造往往依然是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人权外交也不例外,这个世界目前有美国人的领导和没有美国人领导相比,也许并不更坏。我们的批评所致力于解构的是世界各国的“崇美狂”头脑中已经被偶像化了的那个美国。他们已被美国鹰一般的目光所催眠,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只是它的强有力的情感、思想和利益的空洞和机械的回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伟大的。它在从事改变世界的创造的同时,并非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中的罪恶;它在向别国强行推销自身价值观的同时,坦率地承认这正是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细致地区别美国身上同时存在的洛克和尼采,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美国的人权魔咒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双刃剑,我们假如被其单边主义的道德傲慢所激怒,因而彻底摒弃人权的价值,那么,在追求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会走入歧路;反过来,假如我们完全被它的魔咒所催眠,亦步亦趋地按照美国制定的标准和提出的要求行事,那么,中国的必然结果就是跟苏联一样,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最后陷入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的境地。
世界各国人民都在追求自由,我们看到,有的国家,比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变得国家破亡、人民内战;也有的国家,比如美国,越是追求自由,国家就越是强大和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美国学习。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国家的强制力完全地建筑在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伤害为目的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像美国一样地无比珍爱自己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像美国人一样地充满同情地去理解和接纳自己“千疮百孔”和“充满罪恶”的传统以及创立这些传统的伟人,(注:我们非常赞同柏克的这个思想,一个人批评自己国家的错误时,应像用手去触摸父亲身上的创伤一样,满含畏惧、痛苦和虔敬之心。而不是以一种轻率的勇敢和无耻的傲慢。)像美国一样地无比关切和积极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真实的存在境况出发,走出一条自我主导的追求人权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这同时也是一条通向自由和繁荣的世界性大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