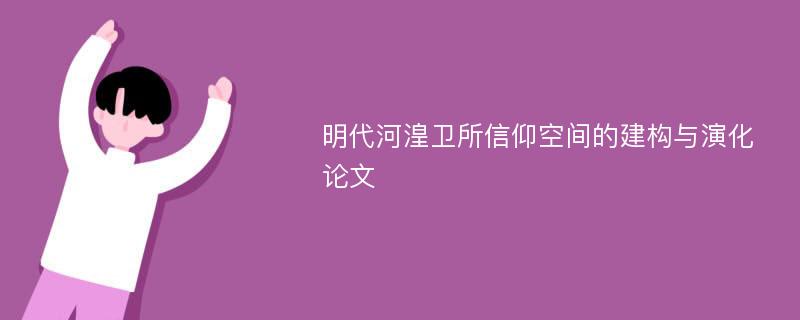
明代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建构与演化
何 威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明代河湟卫所形成了独特的卫所文化。通过聚焦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探究卫所民众的精神世界,在信仰层面研究卫所与中央、地方的互动关系。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建构下,在权力博弈与文化认同的动态发展中,河湟卫所形成了国家信仰体系、宗教信仰体系、民间信仰体系——“三位一体”的信仰空间。其中,湫神崇拜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国家祭祀向民间信仰转化的典型。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建构既是国家权力文化网络建构的主要内容,也是加强国家认同、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反映了多族群多文化危机下的调适策略。
关键词 :明代;河湟卫所;信仰空间;文化认同;湫神崇拜
卫所制度是明代军事制度的核心。对于西北边疆而言,卫所不仅是重要的军政机构,更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外籍人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嵌入了新的地理单元,形成了独特的卫所文化。军户移民来到边疆之后,必然要重塑自己的生活空间,信仰必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军事卫所也要努力建构自己的信仰空间。
在中国传统社会,信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它稳定地保存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所以,通过对河湟卫所信仰空间形成和演化的研究,可以从另一视角窥探河湟地区社会的历史演进、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央权力的整合过程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为我们展现一幅独特的西北边疆社会文化图景。
关于西北边疆卫所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涉及卫所制度、历史演变、军户军屯、文化信仰等诸多方面。如武沐的《明代河岷洮三卫戍边军屯研究》[1]、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2]、骆桂花、高永久的《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3]等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探究卫所民众的精神世界,在信仰层面研究卫所与中央、地方的互动关系。
一、信仰空间的建构——权力博弈与文化认同
明洪武三年(1370年),邓愈兵克河州,元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何锁南率部归降。第二年,明政府首先在河州设立河州卫。洪武六年(1373年)再建西宁卫。洪武十一年(1378年)、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相继设立岷州卫、洮州卫,形成了河湟地区军政合一的卫所体系。明代河湟卫所,既领兵,又管土,还治民,它不同于内地卫所,不是单纯的管理军士、领兵打仗的军事机关,而是统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机构。明初河湟地区亦曾设立州县,司民事,掌钱粮,然“寻罢之”[4],“自设州以后,征发繁重,人亦困敝,且番人恋世官,而流官又不乐居……仍撤州设卫如故”[5]。中间虽有短暂复置,但直到清雍正年间,河湟地区才正式建立起完备的府县制度。因此,河湟地区的卫所文化虽源于明代的军制,却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独特的综合性地域文化。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也不能仅局限于军士及其亲属所生活的卫城和屯堡之中,而是涵盖了整个河湟地区,并在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建构下,在权力的博弈与文化认同的动态发展中,形成了国家信仰体系、宗教信仰体系、民间信仰体系——“三位一体”的信仰空间。
1.国家信仰体系——中央权力的持续深入。朱元璋定鼎中原后,非常重视国家信仰体系和礼仪制度的建构,逐步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坛庙制度,对祭祀时间、祭祀对象、祭祀主持、祭祀什物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国之大事,所以为民祈福。各府州县,每岁春祈秋报,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诸祠,及境内旧有功德于民,应在祀典之神,郡厉、邑厉等坛。到任之初,必首先报知祭祀诸神日期、坛场几所、坐落地方、周围坛垣、祭器什物,见在有无完缺。如遇损坏,随即修理。务在常川洁净,依时致祭,以尽事神之诚”[6]。
有机酸类成分是中药中酸味的主要来源,中医五味讲“酸入肝”“酸收敛”,相关研究发现有机酸类成分具有抗炎、抗血栓、抑制血小板凝聚等多种药理活性[9-11]。据文献报道,枸杞子中含有草酸、酒石酸等多种有机酸[12],但目前其相关含量测定研究较少见。本研究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法对不同产地的枸杞子药材中水杨酸、香草酸、肉桂酸、咖啡酸、对羟基苯甲酸、阿魏酸、对香豆酸、富马酸、3,4-二羟基苯甲酸、酒石酸、丁香酸和原儿茶酸等12种有机酸类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并进行了成分含量差异分析,以期为枸杞子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城隍是传说中阴间的行政官员,与阳间的行政区划相对,有一定的辖区,保境安民,造福一方。有明一代,城隍在国家信仰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洪武二年(1369年) 朱元璋诏封天下城隍神,封应天府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诸城隍皆封为王”,其他各府、州、县城隍分别封为公、侯、伯[7]。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又要求由京师到地方普建城隍庙,“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其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座,旧庙可用者修改为之”[8]。
明朝中央政府对风雨雷电山川城隍的祭祀仪式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要求,各地每年必须按期依规进行祭拜。
ATF压力将活塞移动至蓄能器缸筒内。活塞上的锁紧环穿过此时位于锁止器锁销中的球头(因为锁子球刚好在凹槽中不影响HIS活塞的继续移动),如图7所示。
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孔子及无祀鬼神等,有司务要每岁依期致祭、其坛埠、庙宇、制度、牲醴、祭器体式具载……风云雷雨帛四,山川帛二,城隍帛一,俱白色,附郭府州县官,止随班行礼。不必别祭,其祭物、祭器、献官及斋戒、省牲、陈设、正祭、迎神,并与社稷礼同。莫帛、初献,先诣风云雷雨神位前,次诣山川神位前,次诣城隍神位前,次诣读祝所。亚献、终献同初献,饮福受胙,其胙于风云雷雨神位前取羊一脚。彻馔、送神、望燎亦同社稷仪。[9]
达斡尔传说中认为除夕的夜晚已故亲人的灵魂会回家来探访,其它游魂也会回到人间到处游串。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把门窗上的缝隙封好堵严,以防游魂野鬼进入家中;除夕夜晚与该年同属相的人不准出门;除夕夜晚不准在室外呼叫孩子的名字,怕被鬼魂带走;除夕一整夜不许关灯,要放置长明灯。
河湟卫所相继设立后,国家信仰体系也随之“嵌入”这一地区,成为中央权力持续深入河湟地区的集中体现。河州卫的旗纛庙“在州西,洪武十二年建”,“卫掌印等官,以时致祭”。除此之外,河州还有社稷坛、风云雷电山川坛和郡厉坛,均系洪武初年建造。城隍庙在河州城内西北隅,元末即已建成,后多次重修(1) 参见吴祯撰:《河州志·卷二·典礼志》。 。岷州自设卫之后,指挥使马烨也相继设立了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坛等(2) 参见余谠纂辑:《岷州卫志·城池》、《岷州卫志·公署》及《岷州卫志·坛庙》。 。国家信仰代表着中央和皇权,是通过信仰文化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正如 Chidester 和Linenthal 所言,“神圣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被发现、建造或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正被某些拥有特殊利益的人所主导与操纵着”[11]。河湟卫所国家信仰体系的建立依靠的是中央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是明政府在精神信仰领域加强边疆统治的重要举措,彰显了国家主权和王朝权威。
在卫所之中,军礼是最正统的官方礼仪,祃祭成为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明政府规定:“凡各处守御官俱于公廨后筑台,立旗纛庙,设军牙、六纛神位……若出师,则取旗纛以祭。班师,则仍置于庙。”祭祀过程分为斋戒、省牲、迎神、三献礼、饮福、彻豆、送神、望燎等步骤。旗纛庙祭祀的神袛为:“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袛五昌神众”[10]。
2.宗教信仰体系——多族群多文化的交流碰撞。河湟地区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至明代时,已有汉、藏、蒙、回等族在此定居,民族的多样带来了当地宗教信仰的多元,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在此得到广泛传播。河湟卫所宗教信仰体系的建构不同于国家信仰体系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而是具有“自发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在多民族迁徙、定居、繁衍、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也是因河湟地处儒、藏、伊斯兰等三大文化传播的交汇处而自然形成。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河湟地区与道教渊源极深。“在《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等古籍中都记载有道教管理天上、地下女仙的最高女神西王母的住所,如湟水源头的西王母石窟、祁连山上的西王母祠、昆仑山上的琼楼仙阁等。青海境内的昆仑山与昆仑神话结合在一起,历来是道教信奉者寻根探源的神秘仙境。”(3) 参见张有厚:《道教文化在青海》,载《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第12辑),2000年. 早在魏晋时期,道教就已传入河湟地区。至明代,道教达到鼎盛,三清观、真武观、玉皇庙、魁星阁等道教场所广泛建立,仅嘉靖《河州志》记载的在河州卫建立的道教宫观就达8所(4) 参见吴祯撰:《河州志·卷二·典礼志》。 ,正如史书所述:“明代,甘宁青一代尊崇道教。”[12]河湟卫所也涌现出了一些享誉全国的著名宫观。如明宣德初年,青海土司、西宁卫指挥使李英奏请在西宁卫建立真武庙,后明宣宗御赐“广福”观名,并令道士孙思忠等管理观内事务。明朝末年,皇室成员朱清真几经辗转来到西宁卫,出家修道,并募资建成塔院,朱清真去世后,为表对其缅怀之情,广大信众多次对塔院进行修缮扩建,并更名为朱仙塔院。
东汉初年,佛教从中亚经新疆、甘肃而传入内地。因此,河湟地区成为佛教较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唐朝时期,朗达玛灭佛和吐蕃的动乱,迫使大量僧侣从卫藏地区迁入安多藏区,推动安多藏区的佛教走向繁荣。明代时,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藏传佛教寺院在河湟卫所大量设立,著名的有塔尔寺、佑宁寺、瞿昙寺、炳林寺、弘化寺、灵藏寺等。同时,河湟卫所中的土司也大力资助修建藏传佛教寺院,有的直接兼任寺院堪布。如洮州卫世袭指挥佥事杨土司,大力支持增修禅定寺,使其成为了河湟地区三大佛教寺院之一,并形成“兄为土司,弟为僧纲”的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伊始就已进入河湟地区,经蒙元时期的多次西征带来的大量穆斯林留居河湟地区,使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得到了快速发展。明代,又有大批江南回族移民迁居河湟地区,穆斯林人口显著增加,清真寺在这一时期得以广泛修建,仅西宁卫始建于明代的清真寺就有31座[17]之多。河州“八坊”的南关大寺、老王寺、老华寺、城角寺等都是在明代初建成或扩建。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在明代河湟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在西宁卫东关清真大寺已实行世袭三掌教制,在循化撒拉族清真寺中实行哈最制度。也正是从明代开始,河湟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3.民间信仰体系——相互采借、和合共存。河湟卫所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信众广泛,异常兴盛,成为河湟卫所信仰空间中最基层、最活跃的信仰体系。除了典型的山神、水神、泉神等自然崇拜以外,这里还形成了湫神崇拜、猫鬼神崇拜等独特的民间信仰。
沥青路面作为公路工程最常采用的结构形式之一,其是所处地区道路交通系统网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施工实践过程中,其基层施工技术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沥青路面基层施工材料使用不合理密切相关。为此,施工技术人员应从问题角度出发,即在明确技术应用缺陷的基础上,提高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措施运用的针对性与可靠性。如此,公路沥青路面的施工建设就能以可持续与耐久性的状态作用于地区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背景下所提出的道路交通网路系统建设。
山神、水神崇拜在河湟地区源远流长、非常普遍,几乎每个村落都有自己信仰的神山、神水,且神圣不可侵犯,他们不仅掌管着一个地区的风雨和祸福,而且主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火神、马神、龙神崇拜也较为普遍,这些都是基于万物有灵而产生的自然崇拜。从对青海、甘肃地方志史料的统计来看,明代河湟卫所的自然神庙不少于93座[14]。除此之外,人格化神灵崇拜也是河湟卫所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文昌神崇拜、关公崇拜、东岳大帝崇拜等。
笔者认为,河湟卫所的湫神崇拜最初应源于功臣祭祀。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为表彰和激励将士,从统一全国的战略需要出发,钦定功臣位次,并敕命在江宁府东北的鸡笼山建立功臣庙,“序其封爵,为像以祀”[16]。在全国统一后,朱元璋又将开国功臣奉于功臣庙,“死者塑像,生者序其位”[17],并将这些功臣封为神,命全国各地立庙祭祀。在今陕西华阴县华阴庙内的碑林中,现存有朱元璋的“封神碑”。碑文中就明确写道:“于民有功者神之,于民无功者不祀”。《明史》卷50《礼四》“功臣庙”条记载这21位功臣分别是:
中山武宁王徐达、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阳武靖王李文忠、宁河武顺王邓愈、东瓯襄武王汤和、黔宁昭靖王沐英。越国武庄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巢国武庄公华高、虢国忠烈公俞通海、江国襄烈公吴良、安国忠烈公曹良臣、黔国武毅公吴复、燕山忠愍侯孙兴祖、郢国公冯国用、西海武壮公耿再成、济国公丁德兴、蔡国忠毅公张德胜、海国襄毅公吴桢、蕲国武毅公康茂才、东海郡公茅成。[17]
河湟卫所“相互采借、和合共存”民间信仰特征的形成,首先是基于该地区多民族迁徙所带来的多元文化,而文化的多元又形成了当地群众“求同存异”的民族心理。河湟卫所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艰险,让普通群众更易相互理解,也更需要“灵验”神祗的保佑。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类别、民族差异、区域不同已不再重要,能够保境安民风调雨顺就会被普通群众所供奉。
二、信仰空间的演化:军事移民的地方认同
明朝初期,功臣祭祀在激励戍边将士扎根边疆、精忠报国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河湟卫所得到了较好的宣扬。但伴随着河湟地区政局的日益稳定,军事战争的日益减少,尤其是时间的推移,普通百姓对当年的血雨腥风和将领的卓著功勋也渐渐淡忘,这种带有浓厚“忠君报国、勇武奉献”思想的功臣祭祀必然会走向衰落。再加之,功臣祭祀的影响力主要在军队和军属范围之内,而明代中期以后,国势衰微,大量戍边将士逃亡或转民,如果功臣祭祀再不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关联,与民间宗教相结合,就会因缺乏有效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难以被社会认同和继承,功臣祭祀的嬗变与发展在所难免。于是,除了明初的开国功勋,河湟百姓又把明代以前的英雄人物和当地的神话传说人物加入其中,共同奉为“湫神”。而此时,湫神的神学意义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只是代表“忠君勇武”等国家意志,而成为保佑一方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的神灵。显然,这里经历了一场由功臣祭祀向湫神崇拜、由国家祭祀向民间信仰深刻变革的历程。
湫神崇拜本是指对民间信仰的水神、泉神、雷神、龙神等的崇拜,但河湟卫所崇拜的湫神主要是以明代的功臣将领为原型,又加入了当地人民敬仰的英雄人物和神话传说人物而最终形成。在这些湫神中,有常遇春、徐达、李文忠等人,故一般认为河湟湫神是源于戍边将士拥戴旧主为“神”,但这一观点并不全面。一方面,邓愈、宁正等将领曾直接参与了率兵征战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与戍边将士的感情联系应该更为深厚紧密,但却不在湫神之列;另一方面,张德胜、胡大海、赵德胜、康茂才等明代功臣都未来过河湟地区,却被奉为湫神崇拜。显然,湫神祭祀不仅仅是戍边将士拥戴崇拜旧主的结果。
宗教往往具有排他性,但河湟卫所的民间信仰却具有“跨族群、跨文化、跨祭祀圈”的鲜明特征,呈现出“相互采借、和合共存”的信仰特征。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宗教建筑艺术、宗教礼仪规程等形式上的互融,还体现在宗教信仰对象、宗教信仰空间等深层次的共享。
文昌神本是北斗星,后被人格化为主宰文运的神灵,受到汉族的广泛信仰。但在河湟卫所,文昌信仰不仅跨越空间、跨越地域,而且跨越族群、跨越文化,也被藏族群众所供奉。建于明代西宁卫的文昌宫,整体呈汉藏文化融合式的建筑风格,“依山傍水,河流索绕,汉番信仰,士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盛,有事祈祷,灵应显著,久为汉番信仰祈福消灾之所。”[15]又如,河湟卫所土族每年四月至六月都会举行隆重的“浪青苗”仪式和“插牌”仪式,祈求一年风调雨顺,驱除各种自然灾害,而仪式供奉的主神正是广受汉族信仰的二郎神。主持仪式的神职人员既有法拉,也有阴阳先生。
功臣祭祀在明代已经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配享太庙,而且还在全国各地被供奉崇拜。《明一统志》卷32《西安府》载:“开平忠武王庙,在长安县治西。王本朝常遇春也,以开陕功,朝廷敕有司立庙,岁时致祭。”[18]功臣祭祀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忠君”、“勇武”精神的推崇和宣教。正如朱元璋曾在《祭岷山天女洮河诸神文》中称:“神钟灵秀,机莫人知,然福善祸淫,以教人聪明正直之为也,朕命将指挥聂纬等帅兵守御是方,是方乃神所居之处,兵既临此就命聂纬等代朕会神以祀。神其无私,尚飨。”(5) 参见昇允、长庚撰:《甘肃新通志:卷93·艺文志》。
随着科技的进步,辅导员对学生的管理不再局限于开班会、查寝等。辅导员可以充分利用科技条件,通过微信、讯息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及时了解情况,当有问题出现时,能够迅速解决,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河湟卫所军户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身处异乡,远离故土,思乡之情和精神世界的空虚需要宗教信仰的慰藉和支撑。同时,这些移民中不乏有很多士兵曾追随这些功臣将领征战沙场、开疆拓土,这种崇拜和敬畏更增添了他们对功臣祭祀的信奉和推崇。于是,代表中央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臣祭祀在河湟卫所得到了广泛传播。
明代中期以后,国家的控制力有所减弱,戍边军士大量逃亡,军屯走向荒废。在这种情况下,河湟卫所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民化”成为大势所趋。在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中,国家信仰体系渐于衰微,旗纛庙、城隍庙、风雨雷电坛等有所荒废,这为民间信仰腾出了精神空间,民间信仰由此走向兴盛,甚至有的国家祭祀向民间信仰演化。在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这场变革中,最为典型的当是湫神崇拜的形成和发展。
正是这场变革,让发端于国家祭祀,兴盛为民间信仰的“湫神崇拜”,成为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一朵靓丽的奇葩。《岷州志》卷7《合祀》附《民间赛会》载:“诸湫神庙,每岁五月十七,众里民各奉其湫神像,大会于二郎山,各备祭羊一,请官主祭。”卷11《岁时》亦称:“然岷境称湫神者甚众,惟经长吏给帖者为正神,其他为草野之神。十六日会正神于城南古刹,计十有九位。”(6) 参见甘肃省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岷州志校注·岷州志·卷7·合祀》,《岷州志校注·岷州志·卷11·岁时》,1988年。 《洮州厅志》卷2《风俗》亦载:“五月五日……择月厌日,由官给箚,请十八位龙神,上朵山禳雹,回至西关外赛会,男女皆喜赴之。”卷3《建置·寺观》载:“龙王庙,邑龙神有十八位,庙宇建造极多,几乎庄堡皆有。天旱禳雨于神池,其应如响,乃一方之神福也。”(7) 参见张彦笃修,包永昌等纂:《洮州厅志·卷2·风俗》、《洮州厅志·卷3·建置》。 关于湫神的记载在河湟地区地方志中俯拾即来,可见当时湫神崇拜之兴盛。
可以说,小虫的这次行动计划非常缜密。在姑妈进了水池后,玉敏迅速给小虫发了信息,告诉他钻戒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小虫早就到了姑妈家的小区,候在大门外。接到了信息,小虫才进去。小虫知道姑父肯定不在家,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编好借口,然后才上了电梯。敲了半天的门,确认姑父家里没人了,小虫又向对门看了看,然后开门进去了。进了屋,小虫叫了声姑父,无人回应。小虫直接进了卧室,小心地取出钻戒,放在兜里。出门时见对门的门仍关着,小虫放心地进了电梯,下了楼,骑上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走了。
这一演化过程,既体现了河湟卫所权力文化网络的演进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相互博弈,也是卫所不断“民化”而成为当地社会组成部分的一个缩影,展现了军士移民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地方认同不断增强的历史进程。
木地板的主要劣化问题包括表层污染、漆层脱落、木板条表层磨损、劈裂、受潮变形弯曲、缺失、基层支撑不足导致塌陷等(图10).
三、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文化涵义和历史思考
1.信仰空间成为国家权力文化网络建构的重要内容。河湟地区地处边疆,远离中原,长期游离于中原王朝边缘。“历代以来,屡收屡弃。唐陷吐蕃,宋没西夏,其中隶中国之版宇者,十曾不得二三焉。”[19]但河湟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使得加强对河湟地区的有效统治势在必行。然而,河湟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民族成分复杂,风土人情又异于中原,如何建构适合于该地区的稳定有效的权力文化网络是摆在中央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明朝采取军政合一的卫所管理体制,并将流官和土官“参治”于卫所,以流管土,以土治番,从而达到了长治久安、稳固边疆的预期效果。但稳定和谐秩序的建立,除了需要构建严密完备的政治体制,还需要社会教化的维持,信仰则是其灵魂。尤其在笃信宗教的边疆民族地区,信仰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方面,河湟卫所的宗教复杂,信仰多样,价值取向多元,特别是基于内生的地方秩序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这与国家权力试图整合当地文化认同的初衷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河湟卫所“土流参治”的二元化权力架构,不同于内地的府县制,中央政府尚未对该地区实现直接管理。因此,采用行政权力强势整合当地的信仰空间,不仅会力不从心,还可能导致当地社会的分裂与动荡。面对这一形势,中央政府采取“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策略,在尊重当地原有信仰的基础上,将体现国家意志的信仰体系强势“嵌入”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之中,形成国家、宗教、民间信仰体系“三足鼎立”的格局。
实际上,明代对地方信仰空间的建构有着严格规定。据明实录记载:“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祗、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20]又有“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无得致祭”[21]。于是大量鬼神祭祀被排除出宗教信仰体系。而在河湟卫所中,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民间信仰几乎未进行任何限制,这种“妥协”,正是适应河湟卫所二元化权力文化网络的体现。国家信仰的强势“嵌入”,不仅仅是简单的祀神仪式,而喻示着一种国家在场的符号,与帝国的权威相呼应,成为国家权力文化网络建构的重要内容,以超越现实的存在来弥补国家机器力量之不及。
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建构也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反映。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明朝初期,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相对均衡,是中央、地方和基层权力相互制衡的客观结果。而到了明朝后期,国家信仰体系的衰微,民间信仰的兴盛,也是明朝中央政府国力衰微、力所不及的真实体现。
2.信仰空间的建构成为增强国家认同、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文化心理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文化往往具有其固定特征,在该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宗教也是如此,多种宗教是很难统一于一种文化的。在多民族聚居、多文化并存、多宗教共生的河湟卫所,这种矛盾尤为突出。但河湟卫所国家、宗教、民间三位一体的信仰空间建构,恰好成为中央政府增强国家认同、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具有明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信仰体系,每次祭祀仪式都是对社会大众国家意识的唤醒,促进了普通民众在文化心理层面对国家的深层次认同,实现了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相互建构。同时,河湟卫所信仰空间互相制衡的稳定状态也有力地保证了各民族间关系的稳定。
正如前文所论,河湟卫所民间信仰有一鲜明特点就是不同信仰的重叠与文化涵化。它们不仅相互采借文化符号,相互模仿宗教仪式,而且不计较神职人员的宗教身份,不计较信仰神灵的族属背景,这种“包容性”不仅有利于不同民族的联系交流,并且让国家意识和王朝权威的渗入更加顺利而有效,不会因信仰的不同而被抗拒或排斥。例如,带有浓厚忠君爱国思想的关公信仰,不但兴盛于河湟卫所的汉族之中,在藏、土等少数民族中也被极力推崇,关公还被藏族群众视为藏传佛教密宗的护法神而深受崇拜。这种“跨族群”的信仰,不仅打破了族际边界,而且让“神化”了的国家意识深入人心。
河湟卫所信仰空间还有一特点,即以湫神崇拜为代表的国家祭祀向民间信仰的转化,这一转化让湫神崇拜的受众大大增多,影响力也大大增强。河湟卫所远离中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普通百姓对明朝中央政府的了解少之又少,所以当地会出现只知“土司”,不知“皇帝”的情况。虽然湫神崇拜中“忠君爱国”的神学意义已被淡化,但对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开国将领的崇拜,他们英雄事迹的传颂与传承,大大彰显了国家的权威。增进了民众对国家的崇敬,在一次次民众“自发”的祭祀仪式中,国家认同被潜移默化地“植入”民众的心里,达到了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
在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中,无论是民间信仰的“包容”,还是国家祭祀向民间信仰的“转化”,往往表达的是王朝和国家的观念,成为边陲文化和中心文化弥合的重要方式,也是河湟卫所民族和谐的重要表现,他们让边陲与国家文化相通、紧密相连,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基于上述的当前各类研究中的不足,本文试图更多的从城市居民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社会距离的问题。因为一个城市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外来迁移者的进入无疑会影响到城市原有居民的生活,但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迁移者的影响肯定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本文要探讨的是城市居民身上的哪些因素会造成他们对于迁移者的态度的差异,即社会距离的差异。根据我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以下假设:
3.信仰空间的建构反映了多族群多文化危机下的调适策略。在河湟卫所信仰空间建构的过程中,族群差异所带来的信仰文化不同,成为边疆地区相较中原内地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因此,在淡化族群边界的基础上实现信仰共建,通过信仰自身的调适以适应河湟卫所多民族的现状,成为多元宗教和合共存的策略机制。不同族群的民众“巧妙”地运用不同的话语解释,有效地消除了不同信仰间的隔阂与抗拒,客观上增强了宗教信仰自身的文化张力,为信仰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便利。例如在河湟卫所就流传有这样的故事,洮州十八湫神之一的原型常遇春曾娶康多“六十家”部落的女子为妻,故当地藏族群众把常遇春称为姑父。另有传说,常遇春也曾娶土族女子为妻。常遇春和另一位洮州湫神的原型胡大海被认为是回族……这些传说故事本身的真假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有效地解决了不同族群对他族信仰的抵制和反感,维护了信仰空间的和谐稳定。又如每年四月初八,塔尔寺的藏族僧侣都要前往位于湟中县的道教名山南通山诵经祈祷。面对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同样有一段神话故事,传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途径南佛山,被漂游在外的孤魂野鬼拦截,请求设坛超度,宗喀巴大师因有急务在身,遂许诺待其回到塔尔寺后派喇嘛、阿卡每逢四月初八上山诵经超度。自此之后,便形成惯例,沿袭至今。这样的话语诠释,增进了不同族群对他族信仰的认可和包容,反映了多族群危机下的调适策略。
另外,河湟卫所恰好处于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的交汇处,三大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似乎会导致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支离破碎,而难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但实际上,河湟卫所的信仰空间不仅自成体系,相互制衡,有机统一,还有效维护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统一和长治久安。究其原因,与河湟地区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不无关系。河湟地区既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又是重要的民族走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东进西出、南来北往,再加之明政府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使这里成为重要的民族迁徙和移民聚居的地区。正是这种“迁徙文化”、“移民文化”,造就了河湟地区特有的文化心理,使这里虽然相对闭塞,却更易接受外来事物,这让不同宗教在这里都能找到自身的发展空间,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多文化背景下的信仰危机,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共建。
通过对河湟卫所信仰空间的考察,展现了西北边疆卫所独特的多元文化场景,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卫所百姓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了解到卫所移民由故乡情结到认同新家乡的心理变迁,看到了王朝国家的整合过程和河湟地区内地化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意识到,卫所的建立不仅仅加强了对边疆的有效管理,而且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钢芯高强度耐热铝合金导线是在钢芯铝合金导线的基础上将其钢芯加强采用高强度钢芯,同时在铝合金中加入金属锆(Zr)元素后制造出的一种新型导线,在低海拔地区钢芯高强度耐热铝合金导线由于其连续运行温度及短时容许温度比常规钢芯铝绞线(ACSR)高60 ℃,分别达到150 ℃及180 ℃,从而大大提高了输电能力,同时其机械特性也较常规钢芯铝绞线(ACSR)大大提高。
步骤4 对计算的幅度和相位误差平均值和进行平滑以滤出坏值,通过调整平滑窗的大小,使得平滑误差曲线补偿效果比较好,确定最终的误差补偿曲线。
参考文献:
[1] 武沐.明代河岷洮三卫戍边军屯研究[M]//暨南史学(第九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 先巴.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3] 骆桂花,高永久.明朝西宁卫的军事戍防与政治管控[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
[4] 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庚戌[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
[5] 张廷玉,等.明史:卷330西域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李东阳,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关给须知[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
[7] 张廷玉,等.明史:卷137礼制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寅[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
[9] 李东阳,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九十四群祀四[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
[10] 李东阳,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八十四祭祀五[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
[11] Chidester D, Linenthal E T. American Sacred Space[M].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15-17.
[12]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1[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3] 李兴华.西宁伊斯兰教研究[J].回族研究,2008(4).
[14] 朱普选,姬梅.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5] 王昱.青海方志资料类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1088.
[16] 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乙巳[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
[17] 张廷玉,等.明史:卷50礼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李贤,彭时,等.明一统志:卷32西安府[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19] 邓承伟,张价卿,来维礼,基生兰,等.西宁府续志:卷10[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20] 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十月丙子[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
[21] 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癸亥[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6- 0061- 06
收稿日期 :2019-03-10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明清时期甘青土司家族文化研究”(2016M592274)。
作者简介: 何威,男,河南大学副教授、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民族学、边疆学。
(责任编辑 程 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