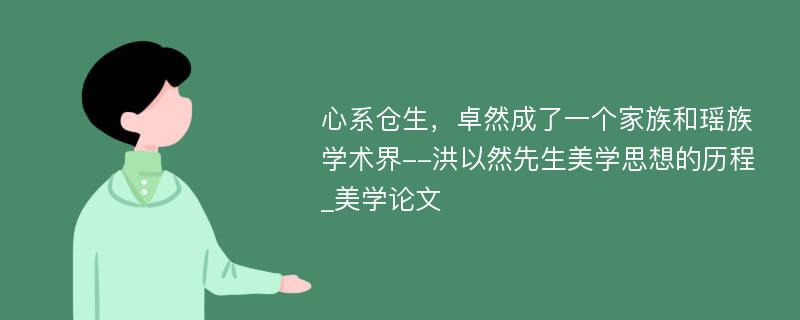
心系苍生建大厦,卓然成家耀学界——洪毅然先生美学思想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美学论文,心系论文,历程论文,大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4-0252-04
洪毅然(1913-1989),原名洪徵厚,字季远,号达人,四川达县人。20世纪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画家。1927年春,洪先生赴成都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普通师范科,开始正式学习绘画。1931年秋,考入国立杭州艺专(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绘画系,专攻素描与油画。1937年艺专毕业,先后任教于西南美专分校、成都南虹工艺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等。1949年5月,洪先生第一本美学专著《新美学评论》问世,这本书为他以后的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教授。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美学学会会长、中央美院艺术研究所校外研究员等职,同时还担任过甘肃省五届人大常委、甘肃省五届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常委等职务。洪先生前期学术方向以美术创作和艺术理论为主,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主要以美学研究闻名于学界,后期兼顾艺术理论及美术创作。先后创作了《水灾》《战后》《铁匠》《湖滨》《乞丐》《到前线去》《草》等大量绘画作品。发表了《论常书鸿的艺术及其他》《评岭南派的新国画》《再评张大千》《论傅抱石先生之艺术》《徐悲鸿批判》《评冯友兰先生论艺术》等大量艺术评论文章。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有:《艺术家修养论》《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新美学纲要》《大众美学》《艺术教育学引论》等,未出版的有《矿阴集》《艺术论大纲》《美学文钞》《美学笔记类钞》《美学论辩续编》《生活美琐谈》《艺术心理学教学大纲》《国画论丛》《艺术概论》《敦煌艺术初探》等以及大量零散的手稿和诗词作品。洪先生在绘画、艺术评论以及美学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为20世纪中国美学、美术的现代理论建构和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洪毅然先生一生于绘画、艺术评论、美学研究多有建树,尤以美学研究见长,在美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新美学纲要》《大众美学》奠定了先生在美学界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论辩使洪先生在美学界声名鹊起,在几次美学大讨论中,“洪毅然均以雄厚的学术实力和主将的姿态出现,成为自成一家的重量级美学家。他的观点有根有据,不看风使舵;他的学风扎扎实实,不欺世媚俗。”[1]与著名美学家蔡仪、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蒋孔阳、刘刚纪、高尔泰等多有美学交流便是明证,生前就被誉为“大众美学的开拓者”和“社会功利学派”。
洪先生的美学思想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思想之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等人著作的影响,他从绘画实践开始,深入探讨艺术理论领域,然后转入美学研究的殿堂,终其一生都在构建自己的美学大厦,在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洪先生提出了美学就是“关于美的科学”的观点,主张美学的研究领域不能局限于研究艺术美,而要扩展到现实美(包括自然美和社会生活美)。他系统回答了“美是什么?美在哪里?美从何来?”的美学元问题,界定了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美感的产生、种类和发展等基本问题。洪先生心系苍生,其美学研究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他大力提倡大众美学和美育教育,主张普及美学,强调美学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洪毅然的主张则具有把美学探索的井架直接架设在现实生活之上的性质”[2],形成“实用美学”的独特风景。洪先生诗画兼工,学力深厚,论域广阔,观点独到。高尔泰评价说:“他很正统,很主流,很美学界”,“是少有的学者型画家”,“正派学人”[3]。洪先生去世后,被王朝闻等人誉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忠实代表”[4]。
洪先生的美学研究是其学术生涯最辉煌的片段,其美学思想历程,可以分四个阶段来把握。
一、洪毅然美学思想的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学才以独立“学科”的面目进入思想知识界的视野,美学各流派面对西学东渐的背景要反映时代精神,普遍认为,建构美学“学科”体系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美学观点。
其时,洪先生怀着“多年来学习美学而试欲建立一新美学系统”的强烈愿望,于1949年写下了《新美学评论》这本“首次初步研究报告”[5]。《新美学评论》是洪先生最早的一部美学专著,是他由绘画、艺术评论转向美学研究后首次尝试构建新美学体系的一个研究报告式著作。“新美学”之新,一方面在于评论蔡仪《新美学》,另一方面在于建立自己不同于蔡仪《新美学》的新的美学——真正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即对观念论旧美学和唯物论美学的辩证发展之后的美学。
在这本小册子中,洪先生试探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观点,初步勾画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他的美学观点是在对蔡仪的美学观点的批判中得以展开的。蔡仪的《新美学》是较早地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力作,他力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美学》体系,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来考察美学诸问题,其美学思想的核心论点是“美即典型”,这根源于对艺术反映现实规律的提炼。在艺术领域,可以说具有真理性,但推及自然和社会现象,则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和片面性。洪先生则是较早对蔡仪《新美学》作出理论反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蔡仪的《新美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表明“惟与蔡先生所见,颇有出入,特草此评论,藉与高明一商榷之。”[6]他首先表明自己和蔡仪关于新美学在美学本身的认识、思想观点、治学态度以及建立新美学的方法方面的基本分歧;其次重点和蔡仪商榷美的定义之典型说、美的认识之观念说、美的分类之单向美等问题;最后表明自己关于新美学的美的本质、美的经验、真善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洪先生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事物相接之一种偏于感觉上的评价,是一种“价值”而不是一种“实体”。这种价值是起于形相直觉,通过联想交替,而仍归于形相直觉所证悟到的,足以唤起种种情绪反应之一种偏于感觉上的价值;美学研究的问题“第一是美的本质——即何谓美?第二是美的构成——即怎样才美?第三是美的效用——即美与人生之关系,诸问题。”[7]美感是起于形相直觉,通过联想交替,而仍归于形相直觉,并伴生一种积极的情绪反应的证悟心理活动(凡伴生消极的情绪反应者,为丑感);美的构成要素有九种;美学的性质是哲学规范之学与科学说明之学兼而有之的学科,美学与艺术学、艺术哲学、艺术科学各有界说,不容牵混;在美学研究方法上,对观念派美学、实验派美学等美学流派应该采取兼容并包、谨慎取舍的态度,避免“划地自限”、“惧越雷池”。他坚定地认为,真正的新美学“应不只是与观念论的美学相对待之唯物论的美学而已,并且还要必须是观念论美学与唯物论美学两相化裁、升高以后的新形态。”[8]
《新美学评论》是洪先生美学研究的处女作,鲜明地表达了洪先生早期的美学思想,标志着洪先生美学生涯的起步。但正如后来洪先生自谦的那样,“可见过去我对蔡仪美学的那些批评,实际仍是不自觉地在为旧美学张目,而对新美学实行抵抗,不过不是采取直接反对,而乃采取的是调和、折衷和杂糅的办法罢了。”[9]看似纠正蔡仪美学的机械性和烦琐性,及至20世纪50年代的辩论,对一些美学问题进一步明确以后,洪先生才看到了这本书矫枉过正的局限性。
二、洪毅然美学思想的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
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现代中国美学初步建构体系的时代,那么到了50年代,各派则忙于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新的生活需要新的审美标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与之相应的各学科的理论改造。在美学界,美及与美有关的名词术语、概念范畴确需明确,这是学科想象得以实质展开的前提。由于这时的美学学科建设和其它学科一样,必须表达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古今中西、唯物唯心,必须旗帜鲜明;说马列、行马列,向马列靠近,必须真诚而严厉,使得美学总的研究往往在概念上兜圈子,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问题是,朱光潜等美学大家虽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并真诚检讨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的错误,但是,在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回答美学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上,他则坚持己见;蔡仪等美学家虽则高举唯物主义美学旗帜,但被指为缺乏辩证思想。而中国的美学家毫无疑问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体系,那么,一切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学观点都要接受审视,都要放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实践和“思想改造”运动序列中表达话语,这种表达受意识形态的严格规定,基于此,美学研究者大多都乐于倾向唯物主义美学,都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美学者,都极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各自流派的哲学根据,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解决美学中的重大问题,但对这一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则各有不同,这就使美学在实质性的研究上观点对立,派别分明,令人眼花缭乱。因此,一场美学大讨论、美学理论转化就在所难免。
洪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就契入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大约与他幼年时受的教育有关。他后来虽多涉及古今中西美学思想,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心则直接导致把自己的理想和时代精神结合,并进而转化为一种学术追求的动力,这使得洪先生的美学之路一开始就获得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洪先生以主将的身份积极参与美学大论辩,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扎实的基础和进一步的理解,在思想方法上避免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影响,因此,在美学论辩上而多有独到的见解,可谓左右开弓,斩获颇丰。他借鉴前苏联美学研究方法,纠正美学与艺术学关系上的混乱和其相互替代的研究方法,围绕美学的研究对象、美的性质、美感实质及美与艺术的关系等美学问题来研究人类生活实践中一切审美意识及客观事物的美的实质、性质和功能,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从对朱光潜主观唯心主义美学的三个基本命题和蔡仪“美即典型”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美学的机械性以及李泽厚、高尔泰等某些美学理论的片面性的批判中,以严格扎实的逻辑批判和心理学分析,阐明了自己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即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美学领域的生根和发展。
洪先生将论辩所陆续撰写的论文,结集成《美学论辩》一书。该书主要从前述几个问题入手,阐明自己的美学观点。概言之,洪先生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的存在和审美意识诸规律;美感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现实界事物具体形象的感性直观的感受,但不仅限于那个简单的直接感觉,而是以此为基础并且是与那种直接感觉的快适与否基本一致的。美感过程中直接感觉和联想均具有重要作用。一切美感就其为感性的直观而言,诚然是个人主观的,但就其有生活的联想说来,却又同时是社会客观的;美的基本种类可分为现实美和艺术美、壮美和优美、悲剧的美和笑剧的美;美感的基本种类可分为惊赞和喜悦、哀矜和幽默;美感和美的认识,属于意识范畴;事物的美,就是其事物本身自己具有的、“充实而有光辉”的形象;美是存在于客观现实事物中,不是存在于主观意识里面;美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而以社会性为决定因素;艺术的本质是现实之形象的审美反映,既包括美的事物,也包括丑的事物;艺术的职能是“为美而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是辩证过程,是维护和发扬美的事物,克服和消灭丑的事物,使美的愈美,丑的变美。方法就是典型化,即把典型的事物或事物的典型方面提高加强为、概括熔铸为典型的艺术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其时美学界四大流派的形成来简单概括这次辩论的成果,无疑,洪先生是站在李泽厚客观社会派一边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就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而言,洪先生和李泽厚都认为美是事物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但洪先生不同意李泽厚对美的决定因素的社会性的过分强调而放松自然性的观点。洪先生正确地指出了这种观点很可能导致“美成为非直观的”;就美感的心理过程而言,洪先生和李泽厚都强调美感与单纯感觉的区别,但洪先生同时看到了两者联系的重要性,并对美感的心理过程作了精彩的分析。
洪先生所参与的美学论辩,讨论问题涉及美学各方面,通过论辩,洪先生对美学任务、对象、本质和框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的彻底唯物主义美学诸观点全面展开,“新美学”的较为系统的体系基本形成,他的美学思想由唯物的向辩证唯物的方向逐步靠拢,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三、洪毅然美学思想的深化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美学研究历经长期的思想桎梏逐渐走向突破。经过“文化大革命”,美学家逐渐成熟起来,洪先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全面反思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现状。
他认为,对于古代美学思想史,“惟多尚未加以批判整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几限于西方各派学说之译述与介绍”;20世纪40年代蔡仪的《新美学》确实是真诚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并力求向辩证唯物主义靠近。但在洪先生看来,相对于一般唯心主义美学而言,不失有某种程度“新”的一面,但“图以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之(可惜陷入形而上学唯物论)”[10];朱光潜的美学则被一致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洪先生认为,“解放后经过1956-1961年全国报刊大讨论,已被提上日程的总课题是:美学怎样始可成为‘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解决这一研究任务,自当坚持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根本指导下,进行严谨科学探索,方能有成。兹事体大,亟待有志于斯者共同努力……”[11]的确,“50年代的大辩论,实际是用马克思主义在奠定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基础”[12]。这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激烈争鸣过程,一些具体的美学理论得到了展现和讨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总的体系并没有得以扎实奠基。洪先生是较早反思这一大讨论并延展自己观点的学者。
基于此,洪先生于1975-1976年间,写成《新美学纲要》(出版于1982年)一书,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是其孜孜以求的“新美学”思想的简明纲要。也可以看作是洪先生美学思想的成熟代表作,标志着洪先生美学思想进一步得到深化。
在这本书里,洪先生以简明的方式阐述了自己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首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理解。洪先生认为,美学作为一门关于美的科学,它的特定研究对象,就是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诸领域中所特有的美与丑的矛盾,以及与之相关和派生的一系列矛盾(例如美感和丑感之间的矛盾等),就是对于美与丑的运动形式及其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之分析;“美学是关于美的一门独立科学”,美学实质上是美丑学;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主要有:“采风”,即调查,应当成为今日及今后美学研究大不同于以往的一项特宜首先加以重视的基本研究方法,阅读和审辩、实验和测验以及适当利用文字语言学,并结合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其次,分美、美感、美育三块回答了美学基本理论问题。最后,归结到一点,“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规律及相应理想的那些事物,以其相关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社会性为决定因素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与此相反者为‘丑’)”[13]。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至此,洪先生的美丑学理论全部奠基。
四、洪毅然美学思想的实践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春天业已来临,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得到关怀。迷茫和兴奋的青年们对美学的热情重新燃起,洪先生时刻关注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并思忖解决途径。于1981年出版了《大众美学》一书(该书写成于1979年),实际是通俗美学,即以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或俗语作标题,旨在把深奥的美学理论通俗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大众美学》甫一出版,群众纷纷抢购,一时洛阳纸贵,取得了异常轰动的社会效应。事实上,这是学术功夫的体现,一切人文学科,若不能最终接触实际,不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注定只能被关在象牙塔里。
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这是美学应用的要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显著特点。洪先生牢牢抓住这一点,一直致力于把美学研究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主张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实际中调查研究,归纳演绎美学原理,总结美学规律。洪先生认为,美是事物之一切好的内在品质之有诸内而形诸外的外部表征,即美是一种功利形态,美丑是一种社会物质实体,即社会功利关系形态。这种界定,联系了美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使美及美学研究能够真正面向生活本身;事实上,美学理论是美学实践的总结提升,作为唯物主义美学家,洪先生的美学研究回归实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求美从全部生活中获得,又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检验。洪先生坚信,美渗透在生活中,有生活就必有美的要求,既然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的美丑,那么美学研究方法就必须联系实际社会生活,只有这样的美学,才能培养和提高主体的审美素质和审美境界,也才能构建真正的美学大厦。“美的内容即生活的内容,但生活的内容要成为美的内容,必首先是好的。不过其好的生活内容本身也还不就是美。一切好的生活内容要成为美,必须体现为具体可感觉的和恰与其好的内容相适应的形象,这样的美一方面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一方面也包含社会功利的意义。”[14]在洪先生看来,任何个人都不能不是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社会中的个人,所以一切个人的生活实践关系,其实都是一定社会中的生活实践关系,其美感经验的记忆联想内容,必然具有一定社会功利的性质。他还认为,实用美学范畴涵盖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领域,生活有多丰富,实用美学也就有多繁杂。因此,他从生活实践,从老百姓的切身体验中谈美学问题,把美学从玄学中解放出来,对于美学大众化,对技术美学和技术美术多有启发,同时对于进行美育、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能力、美化世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洪先生也因此被同道称为“社会功利派”,其美学思想被称为“实用美学”。
8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自然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观点被再次关注,“实践美学”逐渐取得学术优势,“美学热”再次兴起。此时的中国美学界已积淀了足够的底气,学者们多以研究成果表态。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独树一帜,颇为瞩目。洪先生自然十分关注,虽年届古稀,仍笔耕不辍,发表多篇文章参与实践美学的讨论。洪先生认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一体两面,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但不是主体客体化;“人化的自然”并不就是“美的自然”,要成为“美的”自然,必须符合“美的”规律。洪先生的这些观点,为实践美学——“中国的本土美学”流派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最后的智慧。
一般认为,美学的理论框架都是遵循美、审美、艺术、美育的基本顺序,只有在这样的审美历程中,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模式和框架中,美学思想才能得以奠基,美学体系才能得以完整。洪先生的美学理论亦然。总起来看,洪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厦。《新美学评论》是洪先生美学思想的憧憬和美学大厦规划,是初步框架的搭建;《美学论辩》是洪先生对自己美学大厦砖瓦用料的斟辨取舍;《新美学纲要》标志洪先生美学大厦的建成;《大众美学》是洪先生美学思想的实践,它表明,这个大厦是为人民大众建立的。
纵观洪先生一生学术追求,诚如其自述:“我自青年时期所习专业为绘画。习画固非兼习相关理论不可。于是,由绘画艺术理论而旁参各门艺术理论,进而升入一般艺术理论,终于涉足艺术哲学与美学。当我对于美学研究深感迫切需要、具有浓厚兴趣、并正泛舟中外古今各派著述,且已倾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时,30年代得读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40年代得读蔡仪同志《新美学》,虽于两家观点皆尽未苟同,而受影响殊多;固尝徘徊、摇摆、折衷于其间。直至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李泽厚同志左右开弓,我与他不少见解基本一致,可谓不谋而所见略同。然大同中仍存小异,幸小异无碍于大同。果欲别泾渭,实亦无非为其共同所属一大派中之小支流耳。同道或竞加号曰‘社会功利学派’,似乎居然也算独树一帜,则不胜惶悚!”[15]诚哉斯言!
洪先生是国内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的学者,是学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忠实代表”。“但是,由于洪毅然先生当时身居西部,也由于出版经费等经济条件所限,他的这种美学思想被大家了解的还不够全面,这不得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16]不可否认,洪先生对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美学自身发展方面的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美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致力于马克思话语的中国语境表达;他始终能够立足于中国实际,密切联系现实的社会生活,从古今中外和同时代美学成果中批判地汲取营养,并努力体现时代精神;他力倡美育,践行美学实践,并能一以贯之,立场鲜明,不动摇,从一开始就能自觉地承担历史使命,积极追求一种体系化的思想、逻辑性的理论和严谨的科学方法并竭力形成自己的美学观点。他自由理智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严谨宽容的论辩原则和心系苍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尤其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重温他的思想,既是对洪先生的缅怀,也是一种学人效法先贤,反思自己的洗礼!
本文摘自《陇上学人文存·洪毅然卷〈编选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