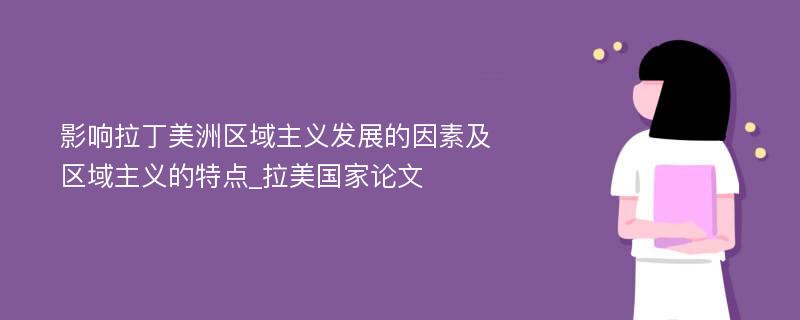
影响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因素及区域主义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区域论文,拉美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主义是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系指国家间以区域为基础的合作与联合。拉美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地区,其区域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由于受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拉美的区域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区域组织是区域主义的载体,在拉美区域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区域组织。比较而言,安第斯集团存在的时间较长,执行的政策较连贯,取得的成绩也较突出,在拉美具有代表性。
影响区域主义的因素
拉美历史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里蕴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印第安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拉美又是殖民地化时间最长的地区,自1492年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先后入侵“新大陆”,并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19世纪初,拉美大多数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独立后,它们一直为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实现民族昌盛和国家繁荣而进行了长期斗争。但是,拉美地区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1、殖民统治的遗害
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疯狂掠夺拉美的自然资源,将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农产品源源不断运往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同时,殖民统治者残酷奴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及从非洲运进的黑人奴隶,破坏当地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控制和垄断当地的工业、农业和商业。300多年的殖民统治虽然最终被推翻了,但其在拉美的影响根深蒂固。
一是边界纷争。如同在亚洲和非洲一样,在拉美也存在殖民统治造成的边界划分问题。在原属西班牙的拉美国家,“18个新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与其邻国有过明确的边疆划界,这必然造成战争、流血以及自此之后不断出现的敌意。”(注:〔美〕E·布拉德福德:《简明拉丁美洲史》,中译本,第13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二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拉美的经济发展。大庄园制和单一作物种植制使拉美经济发展迟缓。大庄园制是殖民者从宗主国移入的。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大畜牧业主等少数人手中。在世界各地区中,拉美的土地集中程度最高。大庄园制阻碍了拉美生产的发展。为了攫取财富,宗主国强迫殖民地只生产一二种能在国际市场上牟取巨额利润的产品,禁止其生产宗主国已经生产或可以提供的产品。在拉美国家盛行的单一产品制严重阻碍了拉美经济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殖民者还禁止殖民地间的相互贸易。
2、经济依附加深
在获得政治独立后,拉美国家开始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机器的使用,交通运输与通讯的发展等)。但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经济上对宗主国的依附性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依然是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这种单一经济结构加深了拉美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法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勒内·杜蒙教授把拉美的这种经济称作“病态经济”,其发展称为“病态发展”。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国家普遍以争取经济的独立自主为基本目标,改造单一经济结构,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试图以此振兴民族经济,摆脱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依附地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6%,高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平均增长率。
但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拉美经济的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未能得到相应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工业生产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其出口能力有限。保护主义政策使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质量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工业化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却需大量进口,致使对外贸易不平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多数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举借外债的办法,则使拉美经济的依附性加深。
美国的拉美问题研究专家E·布拉德福德教授在谈到拉美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状况时指出:“独立之后,依附性不但没有减弱,相反加强了。拉丁美洲的繁荣取决于向工业化国家出口天然产品和原料产品。另外,它的繁荣还取决于外国的借款、投资、发明、技术、技术人员、商船、中间商和意识形态。正是拉美现代化的装备加强了其依附性。拉丁美洲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增长,但几乎没有发展。”(注:〔美〕E·布拉德福德:《简明拉丁美洲史》,中译本,第20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美国的渗透
美国是拉美的近邻,从19世纪上半叶起,它便开始向拉美渗透和扩张。1823年12月2日,美国发表的《门罗宣言》,实际上是以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拉美国家独立为幌子,实现其把美洲变成美国人的美洲的野心,成为以后美国侵略拉美的理论依据。
二战结束后,美国加紧对拉美的渗透。在经济上,美国通过《美洲经济宪章》,加强对拉美各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在政治上,美国强化泛美体系,扼杀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把原先较为松散的泛美组织改组为由美国严密控制下的美洲国家组织。在军事上,美国借助与18个拉美国家签署的《泛美互助条约》,成为拉美国家的军事盟主。
虽然存在上述不利因素,“但拉丁美洲至今一直保持着统一和一体化的愿望”(注:〔委〕D.博埃斯内尔:《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中译本,第2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这种愿望早在拉美如火如荼的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期间就已萌发,其中以独立战争的杰出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表达得最为强烈。玻利瓦尔为防止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抵御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的侵略,提出了在拉美国家中建立政治联盟的设想。他认为,只有西属美洲各国团结起来,结成政治上的联盟,才能保障拉美的自由和独立。1826年年初,玻利瓦尔草拟了一份“关于巴拿马大会的设想”的文件,要求将分散的弱小的独立国家联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或最强大的联盟”。他满怀希望地憧憬:“新世界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语言、相同的习惯和宗教,”可以组成一个国家。(注:“牙买加来信”,《玻利瓦尔文选》,第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在玻利瓦尔的积极推动下,1826年6月,美洲国家国际会议在巴拿马召开,并达成了若干项协议。但由于英、美等国的挑拨离间和拉美国家的内部矛盾,玻利瓦尔的这一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然而,在拉美人民的心中一直珍藏着玻利瓦尔的理想,“组成一个民主的、进步的拉丁美洲国家大联盟,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体面的一席”(注:〔委〕D.博埃斯内尔:《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中译本,第2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此后出现的发展民族主义理论对拉美区域主义产生较大影响。发展民族主义,亦称经济民族主义,简要地说,是指一国希望在经济领域里自主行使主权,独立做出开发自然资源和从事经济活动的决定,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牢牢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发展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颇为流行,但对拉美尤具影响力。它在拉美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外国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渗透和控制。发展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正是外国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才使拉美的经济不发达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的统计数字,1960~1966年,流入拉美的私人投资达28亿美元,而外商赚取的利润和收入达83亿美元。因此,发展民族主义主张采取措施限制外国资本,增强经济的活力。与反对外国资本渗透相应的是,拉美的发展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反美色彩。如前所述,美国力图全面控制拉美国家。在经济方面,美国更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自己的经济繁荣置于其邻国的经济发展之上”(注:〔美〕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独立的探求》,中译本,第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美国是拉美国家最大的投资者和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企业遍布拉美各地,但它们是以牺牲拉美国家的利益来牟取巨额利润的。据美国商业部1970年发表的数字,美国在拉美的投资总额为3.02亿美元,赚取的利润则高达13亿美元,其比例为1:4(注:〔美〕E·布拉德福德:《简明拉丁美洲史》,中译本,第26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另外,发展民族主义主张在拉美实现工业化。发展民族主义认识到,主权国家不仅是政治单位,同时也是经济单位;政治独立并不代表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最终也会失去政治独立。因此,发展民族主义要求实现工业化,进口替代战略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许多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不足以支持现代化的工厂生产,必须建立共同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效益,增强工业化的动力。因而,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发展理论,强烈主张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
区域主义的特点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拉美的区域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拉美区域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强烈的发展民族主义。拉美的区域合作以经济为主,以一体化为宗旨。以安第斯集团为例,其成员希望实现区域一体化,力求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达到经济上的独立,在经济上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这正是发展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安第斯集团通过的控制外资的24号决议,“被认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使安第斯集团通过加强成员国面对多国公司时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具有了一种新的特性。”(注:Alicia Puyana de Palacios,Economic In-tegration among Unequal Partners,the Case of the Andes Croup,p.181,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2.)这种特性突出地表现在要求规范外商的投资行为,使其服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24号决议的本意是想将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与安第斯国家的发展利益相协调,通过吸引外资来克服国内资金的不足,并通过适当的方式,使外资流入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国民经济部门,从而服从于安第斯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但由于它把拉美在没收外资和国有化方面的经验与长期政策的定义合在一起,造成一些安第斯国家发起国有化运动,结果使得进口替代模式所必需的外来投资及进口受到阻碍。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从中得到了启示,“地区一体化的努力不仅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正是由于它们缺乏成就,而促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有制度的不平等,从而在拉美国家之间产生了更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注:〔美〕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独立的探求》,中译本,第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不仅仅是安第斯集团,整个拉美都奉行发展民族主义以解决本区域经济持续欠发达的问题。1974年12月在秘鲁召开的纪念阿亚库乔战役150周年会议发表的《阿亚库乔宣言》指出,虽然“我们的国家赢得了政治独立,但是它们在结合进世界经济之后,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依附,成为我们发展的阻碍。我们必须火速完成我们的解放,使我们的命运在社会经济领域内获得改善。”而“一体化是各国通过经济上相互补充的共同努力,以达到发展和保证经济独立的最有效的工具。”(注:〔美〕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独立的探求》,中译本,第314~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拉美区域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实行集体发展战略。安第斯集团执行委员会在1972年发布了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文件,以工业的发展为准绳,为达到就业最低目标、增加各国效益要求和减少外贸逆差,确定了该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安第斯集团为此还在两个方面采取了具体措施。一是部门工业发展计划,主要是为单个国家因市场规模狭小而无法建立的工业部门创造区域联合发展的能力。部门工业发展计划根据轻重缓急来确定产业和产品,并对工厂的位置、共同对外税率、自由贸易计划、成员国为完成这一计划必须采取的措施、共同的投资规划等予以全盘考虑。二是扶持本区域多国公司的发展。1971年通过的46号决议,将安第斯多国公司定义为:其主要地点在一个成员国内,其资本来自不止一个成员国,参与投资的每个成员国所拥有的股份不少于15%。由安第斯集团成员国组建的多国公司享受所在国的同等国民待遇。这一决议在拉美是史无前例的,它第一次将区域工业发展计划、外资管理和取消贸易障碍结合在一起。拉美其他区域组织虽然没有成立多国公司,但是集体发展战略同样也是它们进行合作的战略考虑。
集体发展战略还表现在帮助更不发达的成员国加快经济发展上,主要是在经济合作中给予它们优惠照顾,以防止或补偿一体化带来的影响。《卡塔赫纳协议》专门给予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特惠待遇,以缩小它们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该协议的第3部分规定的各项条款,使这两个国家通过有效和直接地参与区域的工业化和贸易自由化而获得利益,从而实现经济的加快发展。除了安第斯集团外,拉美其他区域也对经济更不发达国家给予优惠。如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在《蒙得维的亚条约》中规定,向更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的贸易优惠,允许这些国家延长实行进口减税计划的期限。各国可向任何被视为更不发达的成员国提供不能延伸给别国的贸易优惠;每个更不发达国家可列出享受这种优惠的“特殊货单”。通过这种方式,使拉美各区域组织中的更不发达的成员国感受到了区域合作的好处。
激烈的反美情绪,是拉美区域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也是与上述两个特点密切相联的。安第斯集团在对外方面,特别是在同大国打交道时,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尤其对美国在拉美的霸道行径予以严厉谴责。自二战以来,包括安第斯集团各国在内的拉美国家一直受美国的控制。安第斯集团认为,通过一体化,建立一支与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不仅能控制和引导外国的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以及外国技术的转让,实现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且还能保障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自主,维护参与一体化的国家的利益。1981年,安第斯集团迫使美国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取消其对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实施的限制性贸易措施。目前,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南方共同市场要求美国率先取消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然后再讨论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合理建议虽遭美国拒绝,但显示了该组织对超级大国美国毫不畏惧的坚强意志。就连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也开始向拉美靠拢。近年来,拉美虽然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然而在独立自主和反对外来干涉等问题上绝不退让。拉美国家清楚地看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阻止美国的霸权,维护自己的各项权益。因此,它们强调以“拉丁美洲的观点、拉丁美洲的方式、拉丁美洲的特点和拉丁美洲的力量解决拉丁美洲的自身问题”。(注:戈登·康内尔—史密斯:《美国和拉丁美洲:泛美关系的历史分析》,第120页,伦敦,1974。转引自曹远征:《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达与不发达关系》,第12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拉美的区域主义虽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与区域主义在当地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相比,差距还很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利益关系难以平衡。仍以安第斯集团为例。安第斯集团各成员国的领土面积大小不一,人口数量悬殊,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1969年,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两国的出口额占安第斯区域出口总额的66.9%,而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国只占9.5%;1975年,智利和秘鲁出口额占安第斯区域出口总额的53.4%,而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国仅占16.3%。(注:陈芝芸等:《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第243~24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按安第斯集团成员最多时6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具体划分,它们可以分为3个类别:哥伦比亚和智利是经济最发达的,属于第一类;委内瑞拉和秘鲁次之,为第二类;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为最贫困的,为第三类。它们的国家利益由此互不相同,因而对安第斯集团的要求及期望值也迥然有异。但在区域合作中,通常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能同步发展,要想使整个区域的政策协调一致,总会有一些成员国不得不牺牲本国的利益。这在安第斯集团成员国中引起了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拉美其他区域组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是国内问题经常影响整个组织的运转。每当国内政局不稳时,成员国政府往往以牺牲区域合作为代价,来平息和缓和国内矛盾。但这种做法往往引起其他成员国的不满,激化彼此间的矛盾。安第斯集团原定于1992年1月1日起实行共同关税,然而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由于国内原因,在1991年年底表示不能按时取消其对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关税。1992年,秘鲁总统藤森颁布法令,宣布取消对本区域产品的关税优惠,哥伦比亚立即决定对从秘鲁进口的产品征税,委内瑞拉则干脆与秘鲁断交。这不仅使安第斯集团原定的实行共同关税计划濒于破产,还使整个组织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鲍里斯·塞泽尔基认为,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的政治因素,在这个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安第斯条约组织内存在某种政治上一致性时,区域一体化进程就获得进展;当面临政治分歧时,安第斯条约组织的一体化进程就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并且改变了它的特征。(注:鲍里斯·塞泽尔基:“区域间合作的因素”,载布雷达·帕夫里奇等主编:《南南合作的挑战》,中译本,第23~24页,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7。)
三是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也给区域合作增加了困难。殖民统治时期遗留的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成为今日区域合作的严重障碍。有的学者在分析拉美的情况时说,“外者看来,拉丁美洲有一个所有国家都赞同的利益的共同体,但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该区域所有的毗邻国家实际上都有关系到其边界的争端”。(注:Brian Blouitt and Olwin Blo-uitt,Latin America:An Introduction Survey,p.283,New York,John willey Co.,1982.)安第斯集团的每个成员国都卷入了某种形式的领土纠纷,其中最重要的纠纷涉及3个国家: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为取得出海口,同智利摩擦很多,外交关系也经常中断。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委内瑞拉湾水域的划界问题上时有争执。秘鲁同厄瓜多尔的领土纷争也不断爆发,1981年两国甚至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四是美国的影响和干扰。美国一向将拉美视作其“后院”,在那里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政策。先是“门罗主义”,继有“睦邻政策”,直至“美洲事业倡议”,无一不表明了美国对拉美控制的企图。它一方面打着援助的幌子,使用金钱向拉美各国施加影响,力图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另一方面使用离间手法,破坏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智利于1976年退出安第斯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种干扰的结果。因此,美国的作用对区域主义在拉美的发展起着不利影响。
尽管存在上述不利因素,但拉美国家仍决心推动区域主义的发展,建立一个独立运动的先辈们所盼望的“共和国的联盟”。因为它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谋求区域一体化,才能使整个拉美置身于新的国际秩序中,从而有组织和有序地进入21世纪。拉美的一体化是这一区域历史进程的延续,玻利瓦尔的梦想将会逐步地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