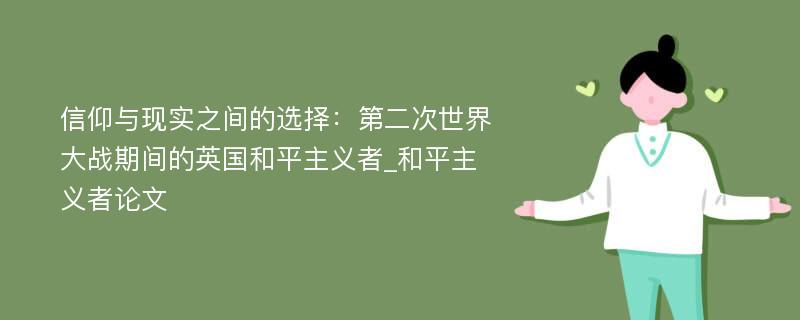
信仰与现实间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世界大战论文,现实论文,和平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2-0112-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和平主义者来说是一种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既没有能够 防止战争的发生,又没有使英国避免卷入一场新的欧洲冲突。新的形势下,是继续坚持 自己的和平主义信仰、反对政府的战争努力,还是同政府合作承担一个普通国民的责任 和义务?和平主义者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他们对战争的回应方式,不仅反映出和平主 义者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取向,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社会即使在战争形势下的 政治氛围。这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英国的政治生活,也许并不是没有帮助的。
一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是对的,30年代,“支持妥协”是大多数英国 人的一致意见。有的人(比如他自己)甚至进一步主张:“不管受到怎样的挑衅,战争在 当时都必须避免”。[1](P467)为什么这样呢?和平主义者的解释颇令人惊讶——尽管他 们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侵略行径同样表示厌恶和愤慨——一场“保卫民主的战争”实 际上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因为“如果要战胜法西斯,这就需要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越它… …而为着要打败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里(英国)就有必要推行法西斯主义”。[2](P146 -147)
不管这种逻辑是多么的混乱和荒唐,和平主义者拥有广泛市场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实的动力。英国的岛国地位,使她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地 ,很少有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因此,和平时期常备军数量比较少。在中世纪,国王主 要依靠民兵作战。1181年的《武器法》规定:“每个(自由民)应当起誓,……他将以手 中之武器,效忠国王亨利陛下……他将佩带这些武器,应召服役,效忠国王陛下和王国 。”[3](P2)《武器法》要求每一个自由民自备武器,定期在当地民兵军官的指挥下受 训,并时刻响应国王号召而服役。17世纪英国的民兵制遭到破坏,19世纪以后又得到恢 复。近代英国的殖民活动和维护领土安全的责任主要依靠一支无与伦比的海军力量。海 军基地靠近港口,主要用于对海外作战,并且人数相对有限。所以,人们不怎么害怕海 军力量的扩张,对陆军常备军力量的发展却比较敏感。一支相当数量的常备军的存在, 对和平生活和国内政治总是一种潜在威胁。人们担心政治家将其作为手中的工具对付竞 争对手和强奸民意。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和立宪君主制形成的过程中,议会制定 了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国王扩充武装和招募军队的权利,体现的正是一种反常备军和反军 国主义的情绪。
与这种反常备军传统相适应的是近代英国和平运动的兴起。17世纪中叶,乔治·福克 斯的公谊会教派,宣称以反对任何战争和暴力作为信仰的宗旨。1816年,英国诞生了第 一个和平主义团体——伦敦和平协会(the London Peace Society),这被认为是英国近 代和平运动的开端。此后,和平运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社会 势力。
从现实的角度讲,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主要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遭受的巨大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经历,它影响到英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给各阶层人们在精神上 和心理上以强大冲击。避免战争,反对军备,成为一种普遍愿望,这为30年代和平运动 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也是英国政府长期推行绥靖政策的社会基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引起英国和平主义者的关 注。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莫德·罗伊登(Maude Royden)女士发起组织非武装的和平军团(t he Peace Army),有800人响应号召。罗伊登准备将其派到中日军队正激烈交战的上海 ,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人道主义的人墙,想以此来阻止战争。但因得不到国联支持,只 好作罢。不过,她的计划也实在太天真了。
希特勒上台后,和平主义者纷纷表示,不仅他们自己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而 且“要以一切合法的方法去劝阻其他人诉诸于战争”,特别是“吸引最大量的年轻人拒 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4](P137)。这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1934年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组织的关于“国王与国家”的讨论,正是这种影响的 回应。因为“为了国王与国家”,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有力 口号。结果,俱乐部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决不为国王和国家战 斗”。[5](P314-315)其他大学起而仿效。动议传到美国,同样引起美国校园的一片喧 嚣。
通过集体安全体制制止战争,是30年代英国和平主义者的积极主张。1935年,由国际 联盟协会(the League of Nations Union)等和平主义团体共同组织的“和平投票”, 有1154万人参与,结果,90%以上的人赞成通过集体安全体制来避免战争。[6](P265)30 年代中期以后,由狄克·谢泼德(Dick Sheppard)领导的“新和平主义”或“和平誓约 同盟”(Peace Pledge Union)成为英国和平运动的旗帜和象征。他们积极支持张伯伦政 府的绥靖政策,鼓吹不惜代价的单方面裁军和妥协。[7](P10-11)
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始终应该看作一种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目标。但是,在30年代 的背景之下,英国和平运动所起的作用却是消极的。因为它在事实上纵容了希特勒的侵 略,妨碍了政府正当的军备努力,错误地引导了舆论,因而应该予以否定。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和平主义者陷入了难堪和被动的境地。但从和平誓约同盟 会员人数的发展情况看,战争爆发之后,和平运动并没有立即受到冲击,它的会员人数 还在增加,1940年4月才达到了它的顶峰规模13600人。
对于和平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40年5~6月间。这同时也是英国进行这 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希特勒的军队在西北欧取得决定性突破。法国沦陷,退出战争。 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单独承受着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且享有苏联支持的纳粹德国 的压力,英伦三岛岌岌可危,“一千多年来正第一次面临遭受入侵的危险。”[8](P52) 丘吉尔的讲话响彻云霄,整个国家被要求动员起来投入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
作为英国社会的一员,和平主义者同样负有国民保家卫国的义务。从良心上讲,当邻 居和同胞在危险面前奋起抵抗之时,如果和平主义者回避这种现实,那很容易背上一种 道德上的负罪感。但宗教的信仰和政治的信仰又使他们十分地厌恶战争。他们承认:“ 希特勒也许是比战争这个罪恶更坏的罪恶”,但同时又觉得:“试图以一种罪恶去克服 另一种罪恶,不仅在道义上是无法忍受的,而且这只能导致更大的罪恶。”[2](P146) 因此,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如果自己依从于社会大流,卷入战争的狂热之中,那也就是 自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在人格上,并非是体面和受人尊敬的行为。
好在英国社会对自己的和平主义者同胞是相对宽容的。政府并没有利用手中权力来取 缔和平主义宣传或大张挞伐和平主义者。自然,免除兵役义务的裁定制度依然存在,只 是似乎变得比上次战争中宽松和民主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裁定团由法官、当地名 流和穿制服的陆军部代表组成。军官的行为特别严厉,像是提起公诉的检察官,给申请 免役的人以一种心理上的压抑和威慑的感受。现在,陆军部的代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劳工部的官员,他们的处事方式倒像教堂的牧师,显得比较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政府规定只有那些因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原因的战争反对者有资格申请免除兵役,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条件有所放宽,因政治原因反对战争的人也获取了这种申请资格。当然 ,申请是否被接受那是另外一码事。此外,政府为那些拒服兵役者提供的替换服务也更 灵活,被监禁者的生活境地也大有改善。
1916年,英国政府实行征兵制,引发和平主义者的抵抗,提出申请免除兵役义务的总 共有16500人,他们中64%的人采取了与法官的裁定进行合作的态度,包括那些无条件免 除服役义务的和平主义者。但36%的人即5944人不服从法官的裁决。他们都经历了一段 与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相对抗的艰难时期,通常被判处禁闭的惩罚,更严厉的是蹲监狱 ,甚至威胁要处以绞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共有59192人申请免除服役,6.04%的申 请者被授予无条件的免除服役义务,20.62%的人被裁定适应在非武装部队中服役,24.8 2%的人被裁定适应在武装部队中服役,拒服兵役者的大多数即48.52%为有条件的免役。 [9](P12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政府对待和平主义者较为宽容,同时,也是由于战争的性质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和平主义者在公众中造成的影响倒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公 众中同情和平主义者的倾向不甚明显,而和平主义者也采取了较现实一些的态度,结果 ,遭禁闭或被判入狱的人只占到整个免役申请者人数的3%,其中一些还是因为不遵守军 队纪律造成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比例占到了30%以上。[4](P302)到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末期,在所有被征募者中只有0.2%的人申请免除服役义务,这从反面说明第二 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而和平主义者对于他们在战 争中所受到的对待似乎也颇为满意。著名和平主义者兰斯伯里(Lansbury)不无自豪地说 :“我们享有其他国家的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时期所不能享有的权利和特权。”[4](P301 )
不过,这些事实不应该掩盖另外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在许多场合和平主义者受到社 会的冷漠拒绝仍然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是那些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 一种本能反应。战争爆发后,和平主义的宣传仍然有相当力度,这与政府的努力和社会 主流意识不协调,不仅受到舆论的批评,同时也使和平主义者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19 40年5~6月间,加入和平誓约同盟的人数明显少于退出同盟的人数。《和平新闻》杂志 并没有被政府取缔,但英法军队在法国受到德军沉重打击以后,全国各地的代理销售商 自发联合进行抵制。被法官宣布免除兵役义务的和平主义者,突然间发现自己被雇主莫 名其妙地解除工作,而要重新寻找一份工作则又非常困难。整个国家的气氛是全面动员 起来,投入抵抗希特勒的战争,和平主义的信条和和平主义者自然不会被社会信任。正 如1941年2月21日出版的《和平新闻》所指出的:大多数和平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感觉 到,他们与社会之间错了位,变得很孤立,以致于在与别人交往时,不得不小心谨慎, 甚或缺乏信心。和平主义者赫伯特·格雷(Herbert Gray)承认:他发现和平主义者的处 境“几乎是不可忍受的”,“唯一两全其美的结论是自杀。不幸的是,这是一条怯懦和 逃避的道路”[4](P305)。
这种氛围导致和平主义者修正原有立场。和平誓约同盟没有像往日那样对征兵政策进 行攻击,它声明,会员是否拒绝服兵役那完全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信念和自由的选择,同 盟不作统一的要求。当1940年5月有人指控同盟的口号——当人们拒绝战斗时,战争就 停止了,你将怎样行动?——之时,同盟马上同意撤回这一口号,并且解释,这是一些 旧的标语宣传。而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和平主义者公开宣布放弃自己原有的和平主义 信仰,转而支持政府的战争努力。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恐怕要算伯特兰·罗素了。他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较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因此而进了班房。30年代后期,他加 入和平誓约同盟,做了一些和平主义的宣传,但当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英国本土面临 入侵危险的时候,他的立场发生了改变。1940年6月,他写信给朋友说:“自从战争爆 发后,我就感到不可能再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了。但由于牵涉到责任问题,我当时没有立 即明言。如果我处于可以上战场的年龄,我会明确表示我的立场的;但说服他人走上战 场则是另一回事。不过在现在,我感到有必要公开我的立场。”[1](P469)罗素公开宣 布退出和平誓约同盟。不过,从1940年6月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来看,放弃自己的和 平主义立场仍然是被迫的和痛苦的,他这样写道:“总的说来,我相信不抵抗便不能保 全纳粹企图摧毁的任何美好的东西。他们办事彻底,极富效率,技术上也很精明,因此 落入他们之手的任何国家,不但在技术上被征服,在精神上也会被征服。因此我们别无 选择,只能以暴抗暴。这是一个残酷的结论,而且与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是相冲突的 ;但我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它。”[1](P470)这似乎表明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为他生活中最抑郁的一页。其他宣布放弃原有立场的著名 和平主义者——如芒福德(Mumford)、马格丽特·斯汤姆·詹姆森(Margaret Storm Jam son)、西里尔·乔德(Cyril Joad)等——也同罗素的感受一样吗?
三
那些没有到战斗部队中去的和平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被无条件免除服役义务和有条件 免除服役义务的和平主义者,在战争中的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那些被裁定适应于非武 装部队中服役的和平主义者,行动要受到一些束缚。被免役和有条件免役的和平主义者 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范围和形式,大体有如下3种:
1.积极从事救护性工作或直接参加生产劳动
主要是抢救伤病员,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救济;或是遵从当地法官的安排,参加城市消 防队,到工厂、矿山、农场劳动。但农场主和工厂老板往往不愿接受这些“拒服兵役者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和平主义者便成立了基督教和平主义农林队(the Chistian Pa cifist Forestry and Land Units)和和平主义者服务局(the Pacifist Servie Bureau ),把那些找不到合适事情的和平主义者组织起来,做一些服务于战争的工作。参加这 两个团体的和平主义者很踊跃,一是因为可以提供替代军事服役的机会,二是不会像在 社会其他单位一样,受到冷漠和歧视。
一些和平主义者在救护队的表现还非常勇敢和积极。战前对政府的空防措施尖锐批评 的人,面对纳粹空军的狂轰滥炸竟毫无惧色。空袭的警报尚未解除,他们就冲到了被炸 的现场,或是参予扑灭大火,或是从瓦砾中寻找受伤的居民。他们几乎是抱着一种道歉 的心态来工作的,并同时想用自己的勇敢行为来证明:和平主义者既不是懦夫,也不是 某些人指责的“第五纵队”。
2.致力于尽快结束战争的努力
这与战前那种反对政府正当的战争准备和消极被动地避免战争的宣传不同。这是在面 对战争现实、不妨碍政府的战争努力、不影响整个国民抗战精神的前提下,寻找一条尽 快结束战争的途径,避免因持久战争所造成的更多人员和财产方面的伤亡。这些被称为 “先锋派”(the Forward Group)的和平主义者,都来自和平誓约同盟。在1941年4月的 和平誓约同盟的年会上,他们的代表罗伊·沃克(Roy Walker)指出:面对国家进行战争 的需要,同盟除了一系列退却外,再无什么主动的行动,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宗旨, 完全变成了政府的应声工具。他表示对此感到遗憾。他敦促同盟采取一项争取实现和平 目标的明确政策,力求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他承认,在没有打败法西斯的情况下寻求 和谈,对那些正遭受纳粹蹂躏的民族和人民来说,也许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但继续进 行战争则是更大的罪孽。因此,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和平是 可取的。[2](P149)他们向交战各方发出呼吁,敦促英国政府采取切实步骤结束战争。 他们还通过中立国有关人士与各交战方面联系,试探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处于力量优势地位的纳粹根本 不可能退却。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即使到了他的末日,也是不会做出任何妥协的,他宁 愿让德国毁灭,变成一片焦土,也不会向英美、更不会向苏联寻求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 的途径。因此,和平主义者的努力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 训。当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和平主义者又开展了一场所谓的“停战运动”的宣传,反 对签订惩罚性的条约。这仍然是一种不识时务的呼吁,自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影响。鉴 于在较短时间内德国策划和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以及法西斯主义野蛮的非人道的行 径,根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德日意三国实行民主改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要求, 和平主义者的微弱呼声,淹没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惩罚浪潮中。
3.从事道德重建的实践活动
这种活动不是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批评和抗议,而是强调道德的传统救赎作用,向人类 展示一种更高的道德水准,指出一条通向新的共同生活秩序的途径。他们将和平主义者 比作一种“新的基督教派的原材料”,在引导人们去建立基督教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过程 中,他们的生活应该像中世纪修道院神职人员的生活一样,在新的基督教社会中起到核 心作用。[2](P148-150)也就是说,在战争期间,和平主义者的真正作用,是在野蛮而 疯狂的世界中播撒新的文明种子。如果他们这种文明种子不能对病态的世界产生立即的 效果,和平主义者就应该把这项工作引向长远的未来。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示范作用 和个人人格影响,总有一天能够将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虽然从事这种道德建设的和平主义者人数不多,但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战争期间和平运 动的一个新趋向。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一批农业共同体的建立。一些感觉到不能适应于 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的和平主义者,也被劝说通过建立共享收入的生活来同朋友 们培养起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理想化的和平主义者试图于战争之中建立起一个新的基督 教社会。[10](P79)
参加农业共同体的和平主义者主要是三种人:确实热衷于与其他人在农业生产中合作 的人;企图逃避现实的人;战争时期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的人。共同体的规模 从几十英亩到上千英亩不等,这些土地大多数是较为富有的和平主义者出资购买的。
东安格里亚(East Anglia)的埃美斯特共同体(Elmsett Community),是个只有41英亩 土地的农场,大约有12个和平主义者在这里劳作和生活,但他们的宣言却冠冕堂皇,颇 具道德诱惑力:“为着一个建立在兄弟原则和人类合作基础之上的新秩序奠基,我们将 抛弃旧秩序中的个人主义,而这只有通过不为个人的利益而为全体利益的劳动以及共同 享有财富的生活才能实现。这样,个人的野心由于更高理想的追求而消逝。从商业主义 的偏颇影响中获得解放的人格将会在对那种理想的追求中升华。”[2](P151)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建立在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没有剥削压迫、充满田 园诗情趣的乌托邦理想。刚开始一段时期,大家对这种新玩艺儿的热情很高,能够很好 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是刻意将自私心掩藏起来,共同体生活较为和谐平静。但随着时 间的流逝,新鲜的感觉没有了,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各种自私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比如北 德文郡(North Devon)的罗纳德·邓肯共同体(Ronald Duncan's Community),其成员不 断寻找机会以逃避脏活重活,对集体的利益和财产不甚关心,结果,猪栏没有人打扫, 劳动工具没有人修补或是被随便丢弃;奶牛的挤奶不及时,劳动时偷工减料。邓肯试图 对这些现象加以管理,以保证共同体的正常运转。但他很快受到指责,说他像特务一样 窥视别人的生活和工作,这与共同体的真正精神相对立。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和平 主义者,不愿接受任何外在的强制和纪律规章的约束,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良好行为, 只不过是自我压抑的表现。邓肯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被称作“自由骑手”(Free Riders)的食客们。他们慕名而来,吃喝都由共同体包下,走时分文不给。这是一笔沉 重的负担,几乎把共同体压垮。最后,邓肯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实验看来 是失败的”。[11](P249)当然,其他共同体的情况也一样。英国和平主义者重复了他们 的前辈欧文在前一个世纪的失败经历。“最好的思想者,往往是最不成功的实践者”, 大抵如此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战争现实,英国和平主义者修正了30年代坚决反战的立场, 基本上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至少没有妨碍政府的战争努力,这与他们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的和平信仰,表达了一种人类的美好追求和愿望, 但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因而只会碰得头破血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和平主义 者改造了社会,而是社会改造了和平主义者。战争期间各种血腥大屠杀事件的逐渐暴露 ,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核武器的威胁,现代国家对市民社会控制的加强以及东西方之间的 冷战,使和平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传统信仰,非暴力立场适应于对付专制独裁 吗?个人拒绝卷入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核战争?和平主义者的结论是悲观的,前景似 乎一片黑暗。其影响是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的和平运动进一步瓦解,在很长时间里再也听 不到英国和平主义者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