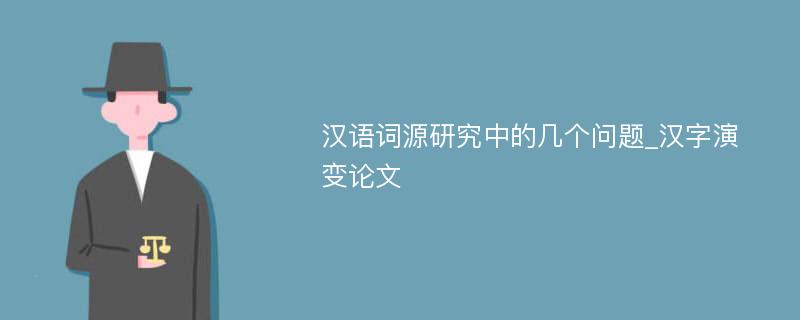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源论文,汉语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 (2001)01—0063—05
一、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的两个学术渊源
当代汉语词源研究,是从两个学术源头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研究;另一个是基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研究。二者的研究任务本来是一样的,但观念和方法均有较大差别。
西方词源学研究在方法上重视活的语言材料,采用方言、亲属语言的比较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以寻求词的早期语音形式和音义结合的理据。传统词源学则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以汉字为线索,以古音音系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工具,采取系联的办法,立足汉语内部词的同源关系,来探讨汉语词的构词理据。从他们工作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任务虽然都是要探讨语言中的词在发生时的状态,但西方语源学着眼语音更多一些,传统词源学着眼意义更多一些。之所以有这样的侧重,是由于语言发生久远,人类对词的原初状态的探讨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靠的材料必定是有文字记载的材料。西方的语言学大国多半使用拼音文字,语音信息保留较全面、准确,所以西方语言学家对语音十分敏感。语音不只是保留在拼音文字里,更重要的是保留在活的口语里。亲属语言和方言都是现存的语言,都有口语形式,它们又是源语言分化的结果,它们的共时状态,反映的是源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的面貌。建立在这个原理和事实上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把探讨音系演变作为探究词源的手段,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汉语的相应文字是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保留意义信息比声音信息要准确得多,所以,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自古对意义就十分重视。汉字的表音机制极不完善,但是,在周秦时代,汉语词汇的分化是伴随着形声造字的。表意汉字能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意义。传统训诂学对意义问题和形体问题的重视自然也很有道理。其实,这两种不同方法的侧重并不意味着西方不重视意义、中国不重视语音。研究词源问题必须语音与词义并重,这一点恐怕东西方没有区别。二者的区别只是取材的着眼点和由哪里起步的问题。
正因为两个学术渊源在对基本原理的认识上并无对立,因此,当代的两个渊源在学术上是完全可以相互影响、互相充实的。但由于学术史上的一些原因,两种学术渊源至今没有相互吸收。不是大家不想把二者结合起来,而是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大家的知识结构都有不足。从学者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们更偏重于接受哪个学术渊源的影响。明白这两个学术渊源是很重要的,当代汉语词源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都与两个学术渊源并存有关。不明白这一点,便难以吸收两个学术渊源的优点,寻找适合汉语实际的方法,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汉语词源学。
二、汉语词源研究中的音义关系问题
词的同源关系以音近为必要条件,判断音近必须运用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可是,判断同源词的音近关系谈何容易!
第一,“音近”是一个模糊概念,什么叫“近”,近到什么程度可以列入同源探讨的范围,都难以定出一个标准。传统词源学的大家们定了一些条例,诸如“旁转”、“对转”、“同纽”、“同类”……不一而足,可一旦操作起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不可避免“无所不转”。
第二,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特别是古音构拟,都带有一定的“假说”性质,有些结论属于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疑案,这就必然影响“音近”的判定。
第三,同源孳生呈网络状,既多层,又多向,演变层次越多,轨迹越长,距离越远。如分化孳乳,声音肯定是近的,但把漫长岁月的多层次演变的头尾衔接起来,还能保证音近吗?
第四,个别词音变化的原因含偶然因素,任何条例都难以穷尽概括。也就是说,都有例外。
基于以上四个原因,纯粹用音系研究的成果来判断音近,又用语音为纲来进行同源系联,免不了滥与漏并存。为此,词源研究必须关注另一个条件,即义通的条件。意义的内在性、个体化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它无规律可寻,所以有些研究者不但不把它作为系联同源词的纲,连纬都不予考虑。的确,义通规律由于意义研究的薄弱、演变轨迹的难以把握、偶然因素的存在,比音近更容易有例外,探讨起来更容易带随意性。但它有规律可寻是不能否认的。避免随意性的出路在于音近和义通两个条件并重,两个条件互相制约,两维交叉。
在词源研究中,义通的探讨有不少误区,影响系联准确性的有两点:一是把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汉语的造词理据混同;另一个是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混同。造词理据、词源意义,传统词源学又称“意义特点”,它带有具象性,居于义素这个层次上,是与词汇意义不同的概念。
吸取传统词源学义通研究的成果,将传统词源学已有的理论阐发清楚,同时将其经验升为理论,是使汉语词源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
三、汉语词源问题的历史时代特征
汉语词汇的积累大约经历过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派生阶段与合成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没有绝然分清的界限,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各以一种造词方式为主要方式。
汉语和世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有过一段为时很长的原生造词时期。这是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词汇如何从无到有,呈现什么状态,这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反复探讨而又难以确证的命题。章太炎先生以为语言最初的发生与人的触受有关;也就是说,原生造词是源于自然之声的揭示。这一说法在某些词上或可得到证实。例如,“蛙”、“鸡”、“鸭”、“鹅”、“鸦”、“猫”、“蟋蟀”等动物是以他们的鸣叫之声来为之命名的;又如,“淋”、“沥”、“流”、“涝”、“潦”等词的词音似与水的滴沥声相关;“软”、“蠕”、“柔”、“茸”等词的声母上古音都为“日”纽,发音时舌面腻黏,似能给人柔软的感觉等等。但是,这些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理性的必然?在天籁与人语之间存在着哪些规律性的联系?在已被记录下来的亿万词汇中哪些词属于原生造词的根词?由于语言发生的历史过于久远,不要说穷尽性的测查无法进行,就连一定数量的抽样测查和局部语料的归纳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关于原生造词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原生词的音义结合不能从语言内部寻找理据,它们遵循的原则即所谓“约定俗成”。
派生阶段是汉语词汇积累最重要的阶段。在原生阶段的晚期,就已产生了少量的源生造词。而当词汇的原始积累接近完成时,派生造词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造词方式。这一阶段,汉语已有的旧词大量源生出单音节的新词,并促进了汉字的迅速累增。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纷繁的派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同源词。
合成阶段的到来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结果。汉语词汇在原生与派生造词阶段都是以单音节为主的。由于音节数是有限的,区别同音词的手段必然非常贫乏。而且,派生造词阶段正是古代汉语文献大量产生的时期。在书面语里,孳乳造字伴随派生造词,成为区别同源词与同音词的一种措施,这便使汉字的造字速度也极快增长。词与字的增长一旦超越了人的记忆可能有的负荷,凭借音变与字变而进行的派生造词便不能符合词汇继续增长的需要。恰好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数量,为合成造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于是,在两汉以后,合成造词取代了派生造词,成为汉语主要的造词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同时,大规模造字的阶段也就随之结束了。
汉语同源词系联主要系联单音节词和语素,这就是为什么词源研究一直属于先秦汉语研究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源词系联都用《诗经》音系为线索。特别要提出的是,汉语的派生阶段,是与汉字的孳乳造字同步发生的;所以,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早就发现了“右文”现象,非常重视形声字声符的同源词系联上的线索作用,而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历史上的“右文说”,由于缺乏理论阐释,话说得片面一些,语例举得不一定全对,接受这个说法确实需要分析;但是,有一些偏重接受西方学术渊源的学者只相信声音,全盘否定字形的作用,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与拼音文字和它记录的语言的关系确有不同的地方,中国词源学的传统还是要有分析地继承,不能丢掉。
汉藏语系中语种的分化、汉语中方言变体的分化,应早于汉语标准语内部单音词的分化,所以,要想把词源探讨的历史时代再行推前,必须学习西方语源学的历史比较方法,进行民族语言的比较、方言的比较。这种比较可能会得到早于周秦的语音和词义状况。这就是两个学术渊源必须相互补充的原因。
汉语词汇的派生分化,主要是在周秦阶段,少数是在其他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的。因此,解决词源问题还要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问题。探求词源,逐一分析可能追寻到的造词理据,在具有大量成果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个局部的词族系统,这属于语言词汇的本体研究;而词源,对这些造词理据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从文化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证明和阐发,这已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阐释词源的诸多成果集中起来,可能大致看出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网络,形成语言与其他文化的互证关系。这就超出了语言的本体研究,具有了宏观语言学的意义与价值。
这一步工作必须涉足民族文化的大网络、巨系统,不应当简单化。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是对词源与文化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找到由语言本体出发深入到民族文化历史总体的可靠途径;还必须从分析微观事实入手,继而达到宏观认识的目的。这是词源研究中难度更大又不可缺少、必须面对的课题。
四、关于汉语词源词典的编写
近年来,有些人想编汉语词源辞典——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构想。章太炎先生的《文始》、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作为近似词源词典的个人专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词源辞典应当贮存汉语个体词的早期语音形式和造词理据,反映汉语词际的同源关系。而且辞典的词条必须是模式化了的。词源辞典与以反映词汇意义为中心的词汇辞典在编则与编例上必然是不同的。要编好这样的辞典,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最基础的条件:
1.科学汉语词源理论及可操作方法的初步完善的系统化。2.已被证实的个体词的词源积累到足够的数量。3.词的词源意义、文化阐释都有一种模式化的表述形式。4.词的原初语音形式构拟有了共识,不再众说纷纭。
编这样一部词典不只需要人力,更需要较强的学术功力。应当说,就目前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看,编写这样一部词典的队伍还没有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似乎还没有到位:
第一,语料的准备工作。汉语词源的探求,同源词的系联,现在已是语言学界的课题之一,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成果,但是现在经过系联的语料,大多是用单一的方法作出来的,因为参与工作的学者,熟悉亲属语言的,不一定熟悉方言;亲属语言和方言都能把握一些的,又不熟悉训诂学;传统训诂学和古韵学都通的,掌握亲属语言和方言又太少……这其实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两种学术渊源尚未综合在一起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语料的准备难以全面。再加上,词源学的基础理论尚未普及,个别词源的考据往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前面说到的那些理论混乱使有些考据难以成为的证确考。而词典是不能搜集未定论的语料的,明显错误的更得抛弃。即使想编一部局部的词典,搜集和选择材料的工作也还有相当的难度。
第二,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看到,有些正在操作的、被称作“词源词典”的项目,由于理论原理尚未理清,总体的编则和编例都很缺乏科学性,有把词源词典与词义词典混同之嫌。例如,有人编写的词源词典按现代音序编排,把同源词分置各汉语拼音音头之下。这种作法说明,编写者不懂得汉语词源据音系联的“音”必须是上古音系而绝非现代普通话音系。他们也不懂得,同源词的音近是用音节为单位来衡量的。用现代普通话的音名为序来编词源词典,把同源词搞得支离破碎,失根失据,对学术是个扰乱。而且,凡是这种“词典”,许多词条都分不清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甚至把纯粹解释造字意图的形源也混迹其中。这种编法,反映出主编或编写者恐怕对两种学术渊源哪一种都没有入门。
第三,编写体例的设计问题。由于系联同源词的实际工作尚未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编例很难设计。现有的几种编排方法对于一般的专著而言,虽都有优点,但是作为模式固定的词源词典都不够理想:
第一,用“声母”为纲,也就是用形声字的声符系统为纲。这符合汉语词汇发展历程中派生造词伴随孳乳造字的部分事实。但造词与造字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仅有一部分重合。传统训诂学家对“右文”涉及形声字的数量估计很高,认为在《说文解字》中有示源作用的声符可以占到90%以上,这个估计是否符合事实?在同源字系联尚未达到一定数量时,还不能得到进一步证明。因此,以字形为纲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让人接受,在事实上也总有点让人不放心。
第二,按上古音为纲来编排。这似乎体现了“音近”的原则,但正如前面所说,“音近”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汉语的“音近”以音节作为单位,顾了声纽,顾不了韵部;顾了韵部,又忽略了声纽。何况前面说过,有些同源词由于分化的轨迹较长,声音不一定很近,以古音为纲,免不了把本来是同源的词隔离起来;如果不想隔离而硬置于同条,则弄得一个词条中“无所不转”,使既定的编例不成其为编例。
第三,按词族类聚,找一个代表字为首。此法看起来很全面;但是词族是呈网络状的、有层次的,用此办法,在哪个层次分条是不好处理的。在系联未能穷尽或者准确系联尚未达到一定数量时,一旦该分的合了或者该合的分了,涉及到的就不是一个词两个词,而是一大串。
所以我主张,要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一批知识结构比较完备的人才队伍。不同领域、不同学术渊源的学者不要互相排斥,要优势互补。在经过一个积极的、有意识的准备工作之后,大型的汉语词源词典的编写才可以提到日程上来。在此之前,要鼓励局部和小型的专书多出一些,只是要尽量避免那些混乱的作法扰乱视听。
收稿日期:2000—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