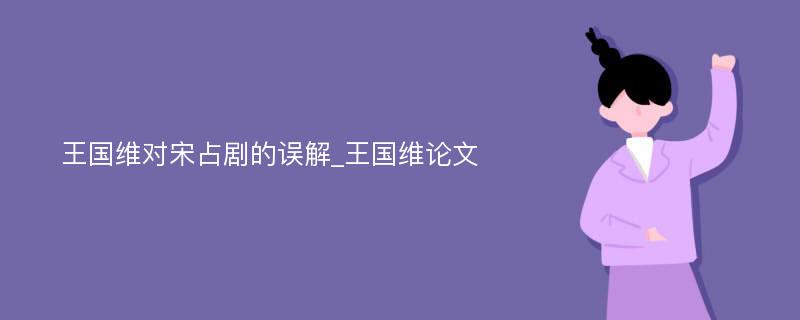
王国维对宋杂剧的误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剧论文,误解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09 文献标识码:A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等一系列戏曲论著以科学的方法与严谨的态度对中国古剧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开辟了古典戏曲研究的全新局面,其慧眼卓识,为世所公认。不过,正因为草莱初创,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有时也难免疏漏纰缪。王国维对宋杂剧的论述即存在多种误解,尤以对宋杂剧结构、脚色及表演体制诸方面问题的论述误解较深,影响亦大。故此本文拟结合有关材料,予以集中辨析。
在《宋元戏曲考》第七章《古剧之结构》中,王国维如是说:
即以杂剧言,其种类亦不一。正杂剧之前,有艳段,其后散段谓之杂扮,二者皆较正杂剧为简易。此种简易之剧,当以滑稽戏竞技游戏充之,故此等亦时冒杂剧之名,此在后世犹然……至正杂剧之数,每次所演,亦复不多。《东京梦华录》谓:“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梦粱录》亦云:“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武林旧事》(卷一)所载“天基圣节排当乐次”,亦皇帝初坐,进杂剧两段,再坐,复进两段。此可以例其余矣。
按:文中所引“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之“两段”并不是所谓“正杂剧之数”,“杂剧入场,一场两段”也非不变之制,《武林旧事》之“天基圣节排当乐次”中,皇帝初坐与再坐之时,更不是各进杂剧两段。王国维在这里误解了宋杂剧的结构与表演体制。
关于宋杂剧的结构,《梦粱录》与《都城纪胜》两部宋人笔记有内容相符的记载。《梦粱录》卷二十之“妓乐”条载:
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或作‘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篇的相关内容与此符合,仅文字表述略有差异。)
尽管如王国维所说,艳段和散段都算不上“纯正之剧”,只不过“冒杂剧之名”而已。然而在戏剧艺术还不十分成熟的宋代,艳段和散段事实上都是杂剧表演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宋杂剧在结构上由三大部分即艳段、正杂剧和散段组成(冯沅君《古剧说汇》以艳段、正杂剧与“把色”为宋杂剧结构之三部分,亦属误解),只不过这种组合并不严格,而是比较灵活随机。按照《梦粱录》和《都城纪胜》中关于宋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的逻辑去分析,当是艳段与正杂剧相继而做的这种组合“通名两段”(这可能是由于宋杂剧演出时艳段与正杂剧搭配表演的情形较为普遍的原因)。可是王国维从该段文字中单独摘取“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一句以资论述,就使得所谓“两段”成了“正杂剧之数”,即王国维认为在每次杂剧演出中,表演两段正杂剧。而事实并非如此。
据《宋史·礼志》《宋史·乐志》、陈旸《乐书》以及上述宋人笔记所载,两宋宫廷每遇重大节庆宴飨,都要举行包括杂剧在内的综合伎艺演出。这些宫廷宴仪通常以皇帝御酒一盏的工夫作为基本的时间和仪秩单元来安排各种表演活动。《东京梦华录》卷九天宁节“宰执亲王百官入内上寿”条、《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宋史·礼志》(志第六十六)之“大观三年,议礼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仪”等材料均明确显示,宋人宫廷大宴之仪一般共进御酒九盏,初坐五盏,再坐四盏。陈旸《乐书》卷一九九“天宁节宴”与《武林旧事》卷八“皇后归谒家庙”等所载亦与此相符。《宋史·乐志》(志第九十五)“春秋圣节三大宴”虽然定宴仪之数为十九项,其次第则完全吻合初坐五盏、再坐四盏共进九盏御酒之例。在这各种名目的宴乐活动中,杂剧表演通常每宴两场,安排在第五盏御酒和第七盏御酒时进行。《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百官入内上寿”条载“第五盏御酒……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第七盏御酒……勾杂戏入场,亦一场两段讫”。《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谓“第五盏进御酒……参军色执竿奏数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第七盏进御酒……参军色作语,勾杂剧入场,三段。”陈旸《乐书》卷一九九“天宁节宴”所载亦同。由此可见,宫廷宴会上的杂剧表演虽仪制明确,而每场演出的具体段数并无严格限定,一般为一场两段,也有一场三段的情况。但是,无论“一场两段”或者“一场三段”,所表演的并不像王国维所理解的那样全是正杂剧。因为:如果“一场两段”表演的都是正杂剧的话,那么“一场三段”自然也应当都是正杂剧,这就已经与王国维的论述不符,而且,说“一场两段”或“一场三段”所表演的都是正杂剧,实际上等于把艳段和散段都排除在了具体的杂剧表演活动之外,这又与《梦粱录》等书中的材料相矛盾了。结合《梦粱录》卷二十之“妓乐”条与《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篇以及《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百官入内上寿”条的材料分析,这种“一场两段”的杂剧表演应当是艳段与正杂剧的两项组合,“一场三段”则当为艳段、正杂剧和散段的三项搭配。换言之,在具体的每场杂剧演出中,“正杂剧之数”只有一段。
《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条中“天基圣节排当乐次”的内容比较细致详明,是我们研究宋代杂剧发展演变的难得的资料。但这一乐单无论就其宴乐仪制而论,还是从其杂剧表演体制来看,均与前述各种文献的记载有很大差异。该宴仪进御酒之数多达四十以上,实非宋制通例。其杂剧表演的次数也远远超过他书所载,共达四场之多,分别在初坐的第四盏、第五盏,再坐的第四盏、第六盏,即初坐两场,两坐两场。这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诸书所载的每次大宴表演两场杂剧的情况可谓大相径庭。不是王国维所说的“皇帝初坐,进杂剧两段,再坐,复进杂剧两段”(王国维在这里忽略了宋杂剧的“场”、“段”之别)。其具体所演,则如初坐第五盏之“杂剧,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书》,断送《绕池游》”。《三京下书》见于“官本杂剧段数”,自然是所谓“正杂剧”。可见在这一场表演中,正杂剧也只有一段。至于其前后是否还有艳段或者散段,书未详载,不敢妄下结论。
在《唐宋大曲考》的篇末,王国维以南宋史浩《觺峰真隐漫录》中的《剑舞》为例分析宋代大曲演故事的情况,最后推论说:
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于此可见。又一曲之中演二故事,《东京梦华录》所谓“杂剧入场,一场两段”也。
这种以大曲一曲之中演二故事的特点对应杂剧“一场两段”情形的说法是不适当的。结合前面的论述可知,这实际上是因王国维没有注意到宋杂剧“一场三段”的演出情况,误以为“一场两段”即杂剧表演的不变定制,又错把“一场两段”的“两段”当成了正杂剧之两部分而引起的误解(胡忌著《宋金杂剧考》曾指出这一误解,惜未予以充分论述)。
在《古剧脚色考》与《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对宋杂剧的脚色体制作了系统的探究,其中,对“参军”、“净”、“副净”的考察尤为着力。王国维认为:
净者,参军之促音,宋代演剧时,参军色手执竹竿子以句之,亦如唐代协律郎之举麾乐作,偃麾乐止相似,故参军亦谓之竹竿子,由是观之,则末泥色以主张为职,参军色以指麾为职,不亲在搬演之列。(《宋元戏曲考》第七章《古剧之结构》)
唐之参军、苍鹘,至宋而为副净、副末二色。夫上既言净为参军之促音,兹何故复以副净为参军也?曰:副净本净之副,故宋人亦谓之参军。《梦华录》中执竹竿子之参军,当为净;而第二章滑稽剧中所屡见之参军,则副净也。(《宋元戏曲考》第七章《古剧之结构》)唐时,(参军)则手执木简,宋则手执竹竿子,或执杖,故亦谓之竹竿子,又谓之副净。(《古剧脚色考》)
且不论王国维关于“净”与“副净”的解释是否准确(因为至今尚无定论),单就其论述行文本身而言,不难看出,王国维是把“参军”与“参军色”当作同义称谓来使用的。然而实际上,宋代的“参军”与“参军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作为唐代参军戏主要脚色的“参军”,亦屡见于宋人关于杂剧活动的记载,这是宋杂剧上承唐代参军戏的结果。从宋杂剧演出活动的有关记载中“参军”这一脚色的表演特征看,它基本上与后来的杂剧脚色“副净”一致(这也正是戏曲史家们多从“参军”出发去寻求关于“副净”及“净”的解释的原因所在)。“参军色”则不同,《都城纪胜》之“瓦舍众伎”篇谓: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色有色长,部有部头。(《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所载与此相符,仅文字表述略有差异)
可见,“参军色”是宋代教坊十三部色中的一个独立部色。又据《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百官入内上寿”条、《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十五中《采莲舞》《剑舞》等大曲以及《武林旧事》卷一“恭谢”等条的内容可知,“参军色”在教坊演出活动中的职责是致诵教坊词(乐语的一种,如苏轼《集英殿春宴教坊词》等)、勾遣乐工、组织大曲、队舞与杂剧表演,并在其他随驾用乐的场合诵念致语口号、赞拜导引。由于“参军色”在上述活动中通常手执竹竿拂子,故又被称作“竹竿子”。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确证“参军色”这一称谓是否与唐代参军戏中的脚色“参军”之名具有渊源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宋代的教坊体制下,参军色是不参与具体的杂剧表演的,即王国维所意识到的参军色“不亲在搬演之列”。司职杂剧搬演的是另一教坊部色——杂剧色。(孙楷第著《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胡忌著《宋金杂剧考》均明确区分“参军”与“参军色”之别,澄清了王国维、徐筱汀等人有关“参军”之论中因混淆“参军”与“参军色”两个概念而导致的误解。而五十年代末周贻白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仍基本循着王国维的思路,称“参军色”在北宋还是杂剧中主要脚色、至南宋始成为一个单独的部色,显然不确。最近,黄竹三先生撰《“参军色”与“致语”考》一文又据《武林旧事》卷一“天基圣节排当乐次”中乐工时和既念教坊词又演杂剧的现象推论“参军色”有时也亲自参加杂剧表演。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天基圣节排当乐次”所反映的是南宋蠲罢教坊以后的情况,在该乐次的“祗应人”名单里,原教坊其他各部色俱全,唯独不见“参军色”)。
收稿日期:2001-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