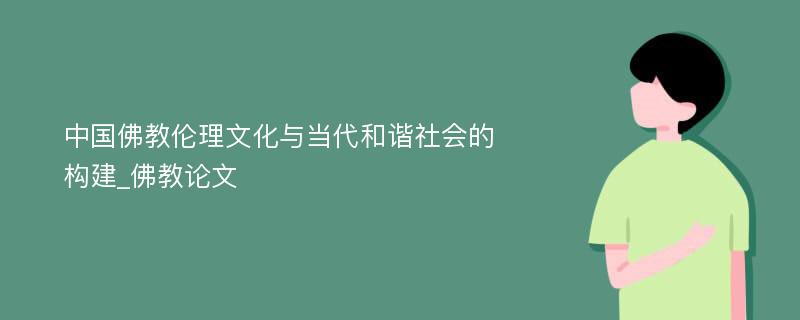
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文化与论文,中国佛教论文,当代论文,和谐社会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6)06-0027-05
如果说中国佛教文化是指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那么中国佛教伦理文化[1]则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中国佛教伦理与中国佛教道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经过必要的转化,可以在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佛教伦理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伦理文化的部分内涵和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和积极精神。
从原始佛教至大乘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印度佛教伦理文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原始佛教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重视对人生问题的探讨,重视对人的解脱的追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为了寻求人生解脱之道和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而出家修行。在修行过程中,他对人生问题进行了主动、积极的探讨,而将有关世界的本体等抽象的哲学问题悬置起来,如著名的“十四无记”和“剑喻”就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也反映了原始佛教的基本特点。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中道观”和“种姓平等观”。释迦牟尼在初转法轮时就明确提出,享乐和苦行都是过分的极端行为,只有“离此两边取中道”,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按照婆罗门教的说法,在当时的印度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通过修行才能获得解脱,而首陀罗种姓则不可能得到解脱,也永无再生的希望。佛教自创立之日起,就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不平等理论,强调各个种姓在尊奉佛教获得解脱方面是平等的,指出:“不应问生出,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2]释迦牟尼去世后100年至400年间,佛教教团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并进而分裂至十八部(南传说)或二十部(北传说),这个时期被称为部派佛教时期。在部派佛教时期,不同佛教派别在继承原始佛教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日益系统化、完备化。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正式形成。大乘佛教主张在修“三学”(戒、定、慧)和“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同时,要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四摄”(布施摄、爱语摄、利行摄、同事摄),认为在追求个人解脱的同时,更应致力于普度众生。由此,自利利他、自觉觉人成为大乘伦理文化的旗帜,普度众生的菩萨人格成为大乘伦理文化的理想人格,世间求解脱成为大乘伦理文化的践行路径。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佛教由南亚次大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在公元1-2世纪,佛教进一步走向世界,佛教伦理文化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中国本土伦理文化与印度佛教伦理文化冲突、调适与融合的过程。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自此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佛教伦理文化的传入,一方面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本土伦理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印度佛教伦理文化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人生态度的冲突。在人生观上,佛教从无常、无我的基本教义出发,认为人生是苦的,并指出只有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修行,灭尽贪、瞋、痴,才能摆脱种种痛苦,因而佛教伦理文化主张放弃世俗生活,追求轮回解脱。与之相对,“自强不息”、“制天命而用之”的文化精神则体现了中国本土伦理文化中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其次是政治和家庭伦理的冲突。佛教伦理文化主张沙门不敬王者,倡导弃家削发,这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中的“忠孝”伦理观直接冲突。最后是道德理想的冲突。佛教伦理文化所向往的寂静永恒的涅槃境界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所推崇的“圣贤”人格相冲突。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圣贤即道德完人,如《孟子·离娄上》中有言“圣人,人伦之至也”,同时,道德修行的目标、人生的崇高理想也是成为像尧舜禹文武周公那样的道德楷模。
魏晋时期,中国佛教初具规模;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趋于兴盛;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向鼎盛。可以说,从两汉时的传入到隋唐时的鼎盛,佛教伦理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是不断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从不承认世俗的伦理到承认并为世俗的伦理作注疏,再进而完全融入中国的伦理文化,这就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也是佛教伦理文化逐步实现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融合的过程。自宋朝以后,中国佛教趋于衰微,但其伦理文化在经过中国化的改造之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近代以来,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改革佛教,倡导人间佛教运动。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些高僧和居士倡导人间佛教理想,主张充分发挥佛教在社会伦理教化中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化,使佛教在近现代社会得到重兴。
由此可见,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出世型宗教伦理文化逐步世俗化的过程。
二、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佛教伦理文化逐步形成了克己、去恶行善、慈悲利他、孝亲等基本内涵。
(一)克己
在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所谓克己就是要求信徒严格修习“戒定慧”三学和大乘六度,以消除“贪嗔痴”三种“烦恼”状态。
克己主要是指克制自己,以消除“烦恼”和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由于无知或无明,人往往会认为“有我”,从而贪恋和追求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物,进而进入烦恼状态。在佛教理论中,人的烦恼主要有贪、瞋和痴三种,即“三毒”。贪、瞋、痴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这三毒即是消除烦恼,也就是说克己。首先,要克“贪”,就是克制对外物的贪欲,放弃对财富、权力、地位、名声、荣誉等的贪欲。其次,要克“瞋”,贪欲没有满足,往往会使人产生愤恨之心,使人对阻碍自己贪欲实现的人、物产生憎恨,从而无法摆脱轮回,所以佛教进一步要求人们克制、消除憎恨之心,即灭“瞋”。再次,要克“痴”,佛教要求人们消除无明,摆脱生死轮回,即灭“痴”。
克己观又与佛教的修身观直接相连。所谓修身,既包括以个体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又包括具有广泛社会伦理内容的“菩萨行”,即大乘六度。
在“戒定慧”三学中,“戒”是指佛教的戒律、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规范。佛教的戒规很多,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如《四分律》中就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信奉者通过对这些戒律、戒条的遵从,就可以克制自己的贪欲,避免不道德的行为。“定”是指安定身心,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的方法。“慧”是指克制自己的错误、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特殊智慧的方法。可见,“戒定慧”三学是佛教信徒修行的方法,是克己的具体方法。
六度亦称六波罗密,是指六种从生死此岸抵达涅槃彼岸的修行方法或途径,也是大乘菩萨达到涅槃境界的六种修习德目。在六度中,布施是指施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等,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功德以至解脱的一种修行方法;持戒即遵守佛教教义、教规,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手段和修习方法;忍辱包括耐怨害忍、安受苦忍和谛察法忍三种,主要是要求人们安于苦难和耻辱的修习方法;精进是指按照佛教教义、教规,在修善断恶、去污转净的修行过程中,不懈怠地努力的修习方法;禅定是指为获得佛教智慧或功德、神通而专心一致的修习方法;智慧则是指以“假有性空”理论去观察、认识一切现象的特殊观点和修习方法。可见,六度都要求人们在实践上克制欲求,牺牲自我,服务他人。
(二)去恶行善
不论在宗教伦理还是在世俗伦理中,善与恶都是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范畴。在佛教理论中,区分善恶的标准就是污净论,即清净无染、去除烦恼无明的就是善,反之,即为恶。佛教的善恶观与因果报应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因果报应论看来,善业恶业在因果律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善恶报应。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因果报应论便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相调适与融合。首先,印度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论与中国本土伦理文化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赏善而罚淫”、“祸福随善恶”等道德观念相互激荡,从而一方面化解了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部分地改变了佛教以超越生死的寂灭为解脱的思想,使得中国佛教伦理文化更具功利性和世俗性,其影响日隆。其次,“三报”和“神不灭思想”渗入并改造了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东晋的佛学大师慧远通过作《三报论》、《明报应论》和《形尽而神不灭》等文,改造了“现实受报说”,指出报应有“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的“现报”,“来生便受”的“生报”,“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的“后报”[3]。慧远的这种形尽神不灭论,改造了印度佛教的“无我”说,从而巩固了来生受报的理论基础[4]。再次,道德行为主体由众生转变为人类自身。在印度佛教伦理文化中,众生都是道德行为的主体,而中国佛教伦理一般只将人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正如宗密在《原人论》中指出的“人是唯一能心神交合的生灵”,这样就使得佛教伦理与世俗生活具有更紧密的联系。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5]这一名偈集中体现了去恶行善观,彰显了佛家戒律的基本精神,被称之为“通偈”。从内容上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诸恶莫作”,是指佛教信徒不得违背佛教的戒律、戒条,也就是要“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即“五戒”;二是“众善奉行”,是指佛教信徒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怒、不邪见”,即“十善”,其中前三条是身体方面的善行,中间四条是语言方面的善行,最后三条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善行;三是“自净其意”,指佛教信徒要在体悟自性清净的基础上,清除内心的无明、烦恼,达到驱除任何烦恼、超越善恶对立的境地。
(三)慈悲利他
慈悲是中国佛教最为根本的价值指向。中国佛教的慈悲观念,以同情、怜悯、利乐众生为前提,指出菩萨见众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苦、后世苦而生大慈悲,并强调“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并进一步将慈悲观念理想化、人格化,视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以普度众生为最高愿望。正如唐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所认为的:“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6]在慈悲观念中,中国佛教伦理文化尤其重视放生与布施。放生不仅要求信徒不伤害众生,而且要求他们保护众生。布施不仅包括财施(布施衣、食、财、物),还包括法施(对人进行说法教化)与无畏施(要有助人为乐、解人困惑的精神)。作为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慈悲观念已经超出宗教的范围,深深影响了广大的世俗民众。
在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慈悲主要包含三种:第一种是视众生犹如赤子,而“与乐拔苦”的“小慈悲”乃凡夫的慈悲。第二种是指开悟“诸法无我”的“中慈悲”,即阿罗汉与初地以上菩萨的慈悲。第三种是指由无分别心而升起的平等无差别的绝对慈悲,是远离“一切差别”的慈悲,只在诸佛之中的慈悲,即“大慈悲”、“大慈大悲”。
由慈悲观念可直接导出利他观念。大乘佛教反对小乘佛教的自利精神,尤其倡导利他观念,倡导自度度人、自觉觉人、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大乘佛教以慈悲为首,以度人为念,从而与儒家的仁爱之心形成共通。由此,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价值观念就不仅成为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且也对人们的世俗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孝亲
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与印度佛教伦理文化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体现在孝亲观念上。中国本土伦理尤为重视人伦、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奉养、敬重与服从。所以,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就受到中土深厚的重孝传统的压力和挑战,受到儒、道两家的指责:如佛教徒出家,与父母断绝关系,是不孝之举;僧人削发,违反了将身体发肤完整归与祖宗的孝道要求;独身无后是大不孝;不拜父母是违反尊亲的原则等。
面对强烈的指责和巨大的挑战,佛教较快地吸纳了中土的孝亲观念,并使之成为自己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隋唐之前,汉魏的牟子、东晋的孙绰与慧远等都就孝亲问题为佛教进行了辩护。其中,牟子用“苟有大德不拘于小”、“见其大不拘于小”的理由为佛教作辩护,从而为以后中国佛教的“大孝”说开启了先河,为中国佛教的孝亲观奠定了基调。隋唐时期,面对以傅奕为代表的反佛者的责难,以法琳为代表的护法者,一方面为佛教作了积极的辩护,另一方面又继承前人的理论思路,对佛教的孝亲观作了初步的系统阐释。法琳不仅指出“广仁弘济”的佛教与儒家纲常并行不悖,而且强调佛教的孝高出儒道两家,是“大孝”。宋元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中国佛教孝亲观实现了系统化。宋代禅僧契嵩在《孝论》的开篇处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7]通过劝佛行孝、助世行孝、以佛言孝,契嵩旨在培养佛教在中土的世俗之本和信仰之根。宋元之后,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主张持戒与孝行的统一,注重孝顺与念佛的统一。正如明代禅僧永觉元贤指出的:“甚矣,孝之为义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无上至真等正觉,非孝亦无由致,是知世出世间之福田,实无有逾于孝者。”[8]近代以来,中国佛教逐步由出世的佛教改造为入世的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孝亲观念。正如太虚大师所言,培本报恩、孝顺父母是“人生应做的第一要事”。
三、中国佛教伦理文化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历史阶段。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经过必要的转化,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
(一)中国佛教伦理文化有利于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
具有较高道德素质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依靠力量,因此,增强公民的道德自律,不仅是建立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点。在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名偈,就指出持戒的重点不在外而在内,即“自净其意”。在此精神的指导下,佛教的克己观念要求人们修习“戒定慧”三学,并兼修大乘六度,以期消除“烦恼”和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由此可见,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的克己观念,有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而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的增强又会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
(二)中国佛教伦理文化有利于和谐家庭的构建
孝亲观念有助于促进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在现代社会,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一,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的孝亲观,强调了以佛言孝、劝佛行孝与助世行孝的统一,包含了父慈子孝、知恩报恩的家庭伦理观。显然,积极倡导父慈子孝、知恩报恩的家庭伦理观,有助于家庭上下代之间的和谐相处,有助于促进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优化,形成其乐融融、相敬如宾的和谐家庭。
(三)中国佛教伦理文化有利于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
去恶行善的价值观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当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出现了价值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弘扬主导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去恶行善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因此,积极倡导去恶行善的价值观,一方面会有助于人们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有助于弘扬社会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社会风气净化,保证人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慈悲利他观念有助于促进个人与他人或集体关系的和谐。一方面,许多佛教僧侣、居士将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发扬慈悲利他精神,利乐有情,造福社会。如近代著名的圆瑛法师,于1917年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了大量孤儿;20年代初,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另一方面,在慈悲利他观念熏陶下的广大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就能造福社会,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今天,慈悲利他的伦理观念仍具有积极意义。
(四)中国佛教伦理文化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
慈悲利他观念、克己观念对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工业文明以来,技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已经充斥在现代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技术带来的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每一个人而言,其“行为必须是行为后果不能破坏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来的可能性”[9]。也就是说,人类再也不能将其他生命简单地对象化了。佛教慈悲利他观念本着慈爱众生、悲悯众生的精神,要求信众将自己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克己观念则告诉人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控制自己对外在物欲的追求,从而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与烦恼。可见,中国佛教伦理文化中的慈悲利他观念、克己观念,能够使广大民众产生“敬畏生命”之感,这对于化解当前的生态矛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以克己、去恶行善、慈悲利他和孝亲等观念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