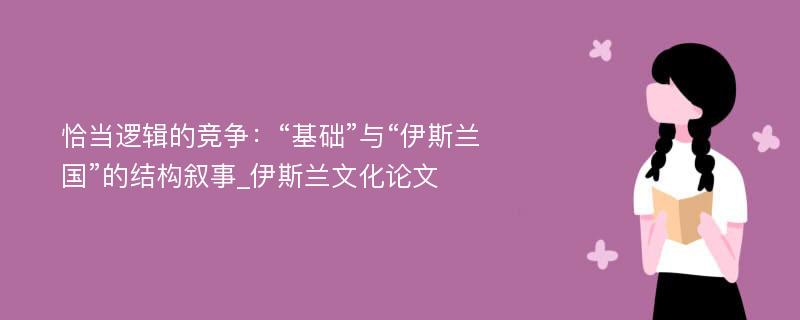
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架构论文,逻辑论文,竞争论文,基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04-0080-32 一 前言 “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是当前国际社会中影响和破坏力最大的恐怖组织,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①这种竞争不仅影响两个恐怖组织的战略战术和叙事体系及其发展演变,已经而且将继续对中东局势和全球反恐战争产生深远影响。在研究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复杂影响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两者的异同进行深入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要,除了可以借此探索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发展趋势外,还可以通过了解两个组织的异同以便对它们实施有效应对提供建议。诚如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指出的:“我们未能预见到‘伊斯兰国’与‘基地’之间的裂缝,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以致带来了危险的决策。”②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有关“基地”的成果相当丰富,③但对“伊斯兰国”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如自“伊斯兰国”2014年6月29日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以来,“伊斯兰国”的演变历程、行动战略与策略、意识形态的源流与特征、国际社会的应对等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果,④但大都集中研究该组织,未与其他恐怖组织(如“基地”)进行比较。⑤这类成果对于了解“伊斯兰国”必不可少,而且的确为人们了解该组织提供了诸多洞见;然而,由于缺乏比较对象,有可能导致关于该组织的部分观点或结论存在一定偏差。例如,认为“伊斯兰国”的政治目标在于建立“哈里发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提出了重要挑战、依赖于社交网络开展活动等观点,在不经意间忽视了“基地”及其下属机构或多或少也具有这些特征,只是程度上有异而已。因此,将“伊斯兰国”与“基地”进行比较研究,是对两者进行较为准确认识的一种有效方式,进而可为国际社会更为有效地应对它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将集中对“基地”与“伊斯兰国”的公开叙事及其差异进行研究。“基地”与“伊斯兰国”的差异和竞争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文只选择公开叙事进行比较,这涉及它们在“适当性逻辑”上的竞争。由于“基地”与“伊斯兰国”的公开叙事极其繁杂,为了研究的方便和保证结论的科学性,本文通过运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架构视角(framing perspective)”进行研究,归纳出两者对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如何动员潜在支持者支持或参与其鼓吹的“圣战”事业等方面观点的差异。从架构视角来看,提出并完成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恐怖组织在公开叙事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三项主要工作——“诊断式架构(diagnostic framing)”、“处方式架构(prognostic framing)”与“促发式架构(motivational framing)”。通过对“基地”与“伊斯兰国”的这三种架构工作进行比较分析,大致可以发现它们在公开叙事上的重要差异。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阐述从架构视角研究恐怖组织公开叙事的可行性,其次对“基地”与“伊斯兰国”所建构的三种框架——诊断式框架(diagnostic frame)、处方式框架(prognostic frame)与促发式框架(motivational frame)——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再次对两个恐怖组织在三种框架上的主要差异进行总结,最后对本文的发现及其启示进行简要讨论。 二 恐怖组织的公开叙事与架构视角 作为恐怖组织,无论“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都希望自身的奋斗目标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同,并积极支持甚至参与它们所鼓吹的“圣战”事业。因此,对于恐怖组织而言,它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于将其理念、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等信息传递给支持者、同情者乃至对手,以塑造自身行动与所追求政治目标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威慑、警告或胁迫对手。就此而言,与其他政治行为体相似,恐怖组织遵循并致力于重塑“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这种逻辑与恐怖组织试图通过其战略战术和具体的恐怖活动以扩大其影响力或实现其政治目标时所遵循的“后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恐怖组织所推动的活动得到支持,并为其暴力行为提供论证。⑥按照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n Olsen)的观点:“适当性无需专注于后果,但有着认知和道德的特征,也包含目标和志向。作为一种认知问题,适当行为是对特定自我概念至关重要的行为。作为一个道德问题,适当行为是合乎伦理的行为。”⑦对于恐怖组织而言,由于其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主要在于通过指使其成员或潜在支持者袭击无辜平民,这需要克服道德、伦理、法律、心理、情感等方面的障碍。⑧因此,恐怖组织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削减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心理成本”。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恐怖组织必须重构关于暴力恐怖活动的话语系统,以突破日常生活中惯常的“适当性逻辑”——如不许伤害他人等,重塑有关从事恐怖活动的新的“适当性逻辑”。 恐怖组织重构有关暴力恐怖活动的“适当性逻辑”主要是通过公开叙事(public narrative)进行的。叙事往往源自特定的信念体系,并以这种信念体系作为参照,不过,为了取得更大程度的动员效果,它们往往用一种简化和线性化的方式解读世界。⑩具体而言,一种有效的叙事不仅要构建一种具有可信性的故事,而且要为这一故事提供具有可行性的行动计划。前者意味着公开叙事不只是提供某些基本事实,而且需要以一种简化和具有说服力的方式提供对一种或某些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诊断,如不平等、不正义现象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根源;而后者需要为根治这些现象提供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以此激励潜在的听众或观众为实现替代性的社会秩序采取行动。(11)无论是“基地”还是“伊斯兰国”,都非常重视将其各种理念成分整合在一起,并将其具有内在连贯性、可行性和简明性的“故事”和“解决方法”兜售给潜在的支持者,同时对对手构成话语上的牵制甚至反击。换言之,恐怖组织试图通过公开叙事实现三个方面的目的:其一,为自身的暴力行动提供合法性。其二,吸引潜在同情者的支持并投身到暴力行为中。其三,胁迫对手并使其暴力恐怖活动获得最大程度的影响。(12) 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架构视角可为研究“基地”和“伊斯兰国”的公开叙事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基地”和“伊斯兰国”与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一样,在提出、建构并阐发其公开叙事的过程中,不只是利用既有的社会或宗教观念,而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事态的演变、自身的发展状况及不同恐怖组织之间的竞合关系,积极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它们有选择性地对事务进行解读,以构建契合自身政治目标、资源基础、思想理念和发展方向的叙事内容。这种密切涉及观念、意义、信念重组和完善的过程,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可被称为架构(framing)过程,而其产生的成果即为社会运动框架(frame)。不过,架构还具有更具体的内涵。按照架构视角的主要提出者戴维·斯诺(David A.Snow)与罗伯特·本福德(Robert D.Benford)的观点,社会运动组织主要通过框架“就某些需要加以变革的特定状况或情势达成共识、对谁或由什么对这些形势负责进行归因,并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安排,劝导他人协调行动以促成改变”。(13)根据上述界定,架构工作至少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诊断问题,二是提出替代性方案,三是动员潜在支持者(或同情者)与旁观者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围绕这三个方面内容而建构起来的框架,架构视角研究者分别将其称为诊断式框架、处方式框架与促发式框架。 不同的框架所承担的功能有所不同。例如,诊断式框架的任务在于“通过确定某些事件、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政府体系内部的某些系统是存在问题和需要修补或变革的,并找出失误方或责任方”。换句话说,诊断式框架需要回答“问题出在哪里,谁应该为此负责”这一问题。(14)通过该框架,社会运动组织者试图向其听者传达这种信息,即原本视为理所当然或不可变革的现状,实际上是不可忍受或不公正的,从而为人们尝试改变现状奠定基础,至少为实现人们的“认知解放”提供条件。(15)而处方式框架在诊断式框架的基础上,就“所诊断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并指出具体的需要完成的行动”,这些行动涉及社会运动组织尝试贯彻的战略、策略与目标等内容。(16)根据处方式框架的内容与特征,可以发现该框架的主要功能在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17)在回答上述问题后,还需进一步解决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即“怎样使人们行动起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是由促发式框架承担的。如何诱导社会运动参与者或潜在支持者克服恐惧与风险参与集体行动是非常关键的一项任务。通过提供各种激励、警示拒绝参与的后果,促发式框架试图尽可能多地动员潜在支持者与旁观者参与社会运动,以维持运动的持续或推进其政治目标。(18) 因架构视角注意到恐怖主义公开叙事内部的矛盾与多样性、强调社会运动组织在面对内外部形势时进行诠释并建构意义的过程、关注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革等,这些特点有助于较为准确地把握恐怖主义叙事的发展脉络及恐怖活动参与者在其中的能动性。(19)如此,近年来国外学术界不乏从架构视角对恐怖组织(尤其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的叙事进行研究的成果。(20)不过,由于“伊斯兰国”崛起时日尚短,运用该视角对其公开叙事进行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本文在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运用该视角对“基地”和“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framing narratives)(21)及其差异进行分析。 三 “重建乌玛的圣战先锋”——“基地”组织的架构叙事 自20世纪80年代形成以来至今,(22)“基地”组织通过其公开叙事已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架构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基地”,它致力于改变伊斯兰世界的现状,以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宗教与政治秩序。而这种理想中的秩序是基于“基地”领导人——如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等人——通过对伊斯兰教经典文本(如《古兰经》、《圣训》等)的选择性解读构建起来的,其中的核心概念为“乌玛(Umma)”“吉哈德(Jihad)”“塔维德(Tawhid或Tawheed)”“希吉拉(Hijra)”等。(23)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结合“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论述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24)对“基地”架构叙事进行简要的梳理。这种梳理不可避免地会以线性论述为特征,而且有可能对其叙事中的断裂和矛盾关注不够,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一)“基地”叙事中的诊断式框架 “基地”的诊断式框架始终围绕其建构的怨恨叙事而展开。这种怨恨既指伊斯兰世界所遭受的具体苦难和蒙受的羞辱,也指“基地”基于自身规范期待遭遇挫折衍生的怨恨。“基地”表达或提及的一些具体怨恨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沙特阿拉伯、也门、埃及等腐败的阿拉伯国家压迫本国穆斯林;西方帝国主义在殖民主义时代通过各种手段征服伊斯兰世界、随意划分边界,如迫使中东国家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破坏了“乌玛”的完整;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伊斯兰国家的石油,窃取了伊斯兰世界的财富;某些中东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等)的政府与西方国家合作,对捍卫“乌玛”的“圣战者”进行打击与迫害;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建立,并通过《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等所谓的“条约”侵犯巴勒斯坦的土地并迫害穆斯林;以维护人权为由攻击伊斯兰世界,如进攻阿富汗、伊拉克,干预达尔富尔等;鼓吹人权、提倡选举,试图以人造之法凌驾在沙里亚法(shariah)即伊斯兰教法之上,侵蚀真主的权威,伊斯兰世界已经堕落到了类似先知出现前的“宗教无知”或“愚昧(Jahiliyya)”状态;人为创立的法律替代了沙里亚法,严重亵渎了真主的权威;缺乏一个哈里发国家,偏离了先知的道路;在“两圣城(即麦加、麦地那)之地”驻扎有异教徒(infidel)的军队;外来思想观念的渗透和传播使穆斯林不再虔诚,反而追求物质享受,以致堕落成为非真正的穆斯林;等等。(25)总而言之,在“基地”的怨恨叙事中,“乌玛”是一个核心概念。乌玛被认为是由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一“认主独一(tawheed)”原则的虔诚穆斯林所组成的单一全球共同体,它超越了伊斯兰世界内部民族、国家、宗教派别、地域、部落等的分野,是一种纯粹基于“认主独一”原则而得以形成的信仰共同体。而乌玛遭遇破坏,则是“基地”各种怨恨的主要由来。 “基地”领导人之所以强调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上述问题,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表达普通穆斯林对伊斯兰世界所面临问题的关切,以期引发穆斯林对其诊断式框架的共鸣。毫无疑问,由于国际局势始终在变化,而且怨恨事由繁多,“基地”的诊断式框架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进行调整。如在1998年2月宣布创建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圣战国际阵线(International Front for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以下简称“圣战国际阵线”)时,本·拉登着重论述了伊斯兰世界存在的三种怨恨: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Zionist-Crusader alliance)占领了阿拉伯半岛、伊拉克人民因遭遇该联盟的制裁而蒙受苦难、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未获解放。(26)基于此,本·拉登宣布圣战国际阵线将作为阿拉伯地区所有穆斯林的先锋,号召各国穆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进行反击。在此之后,随着伊斯兰世界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基地”扩大了关注的范围,并将其诊断性框架的关注对象延伸到包括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地区、俄罗斯的车臣等地区的事务上。随着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基地”诊断式框架对问题的诊断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不公现象。 在对伊斯兰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后,诊断式框架在逻辑上自然需要找出导致这些问题出现或持久存在的原因,即寻找责任方。在此方面,“基地”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世俗阿拉伯国家应该对此负责。其中,“基地”更多地强调西方国家是导致乌玛遭到破坏、伊斯兰世界无法建立虔诚哈里发国家的罪魁祸首。在“基地”领导人看来,乌玛正在遭遇的各类危机,包括领土、经济、信仰和价值观上的,最主要的原因都源自西方世界的压迫和侵略,其中美国扮演的角色尤为险恶。如1997年3月本·拉登如此评价美国:“美国想占领我们的国家,偷窃我们的资源,扶持那些用人造之法统治我们的合作者,希望我们对所有问题都表示同意。如果我们拒绝服从,美国就说我们是恐怖分子。”(27)1998年成立圣战国际阵线时,本·拉登等人控诉美国:“过去7年,美国占领了圣城之地的伊斯兰土地——阿拉伯半岛,掠夺其财富,支配其统治者、羞辱其人民、恐吓其邻人、利用在阿拉伯半岛的基地作为打击临近穆斯林的先锋……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给伊拉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屠杀了上百万人,美国仍在重复这样恐怖的屠杀。”(28)基于对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的仇视,“基地”不仅将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其主要的目标,而且还对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民主和人权等规范标准均大加鞭挞。(29) 当然,除了将矛头对准“异教徒”,“基地”同样强调“叛教者(apostate)”在导致乌玛衰落过程中的责任。在“基地”领导人看来,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和乌玛之所以能造成巨大的伤害,离不开阿拉伯国家的为虎作伥。在“基地”的公开叙事中,腐朽的阿拉伯政府不再是真正的穆斯林,而是“卡菲尔(Kufr)”的代理人或“叛教者”,是需要打击或推翻的对象。如在2006年公布的一个视频中,扎瓦赫里号召“圣战者”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政府,指出“致力于改革是乌玛先锋的义务,因为消灭这些傀儡是实现拯救的切入口,也是抵抗十字军联盟入侵的开端”。(30)在批判阿拉伯政权罔顾民众诉求的过程中,“基地”领导人也对服务于政权的宗教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批判,认为他们服从当局的意志,无视现代伊斯兰社会面临的道德堕落,对西方价值观对伊斯兰原则的侵蚀视而不见,无意向穆斯林宣讲真正的伊斯兰教义,因此,他们必须为伊斯兰世界堕入“宗教愚昧”负责。(31)不过,虽然都主张向与西方合作的伊斯兰政权及其爪牙宣战,但因为出生地和经历的不同,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的关注点有所差异。本·拉登更关注阿拉伯半岛地区(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形势,而扎瓦赫里则强调在埃及推翻世俗政府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必要性。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基地”领导人虽然在话语上一贯强调打击腐败的阿拉伯政权的必要性,但在行动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其斗争重点和首要敌人始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32) (二)“基地”叙事中的处方式框架 在其诊断式框架的基础上,“基地”领导人构建了相应的处方式框架。“基地”认为,由于现有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在于“乌玛”遭到破坏并陷入“宗教无知”状态,那么伊斯兰世界当前的迫切任务就在于通过对异教徒或“卡菲尔”进行“圣战”以摆脱外来的影响,并通过实施沙里亚法以摆脱当前这种宗教无知的状态,最终重建乌玛。换言之,乌玛的重建构成“基地”构想中的理想状态,(33)而“圣战”与严格贯彻沙里亚法构成达至这种状态的途径。“基地”领导人对当前伊斯兰世界不复先知时代的荣光痛心疾首,致力于虔诚和严格地践行先知时期的宗教教义与习惯,尤其是《古兰经》和《圣训》,以恢复先知时代尤其是先知及其后的前三代哈里发时代的伟大。正因如此,“基地”为这种构想进行辩护的话语体系被视为具有“萨拉菲主义(Salafism)”的内涵,(34)而由于其暴力取向,更具体地被视为“萨拉菲主义”的分支——“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 Salafism)”的一部分。(35)“基地”领导人认为,一旦恢复到伊斯兰世界的辉煌,“乌玛”就能有效地得以重建。 由此不难理解,“基地”领导人为何在其公共叙事体系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强调建立乌玛和实施沙里亚法的必要性。由于认定所有的穆斯林均属于同一个乌玛,“基地”的公共叙事从根本上否定了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从而对构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的民族国家彼此独立这一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基地”还否认世俗权威,认为真主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权威。基于这一原则,“基地”领导人认为,为了重建乌玛,需要严格执行沙里亚法。如本·拉登2004年时曾表示:“伊斯兰法涵盖了所有的生活领域,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领域,比如经济、军事和政治事务,同时也涵盖了我们权衡人们——如统治者、乌里玛及其他人——行动的各种尺度以及根据真主为统治者确立的、不能违背的规则对其进行处理。”(36)按照这一逻辑,无论是重建乌玛,还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伟大,其根本途径在于严格遵循先知及其亲密追随者的道路,严格按照沙里亚法治理伊斯兰世界的事务。 针对横亘在重建乌玛道路上的障碍或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与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基地”领导人提供的处方是对前者开展“圣战”,而对后者实施“塔克菲尔(Takfir)”原则。在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方面,美国是“基地”开展“圣战”的首要对象。在“基地”的叙事体系中,美国是造成伊斯兰世界诸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也是破坏乌玛的主要力量,因此,对美国进行“圣战”,是对其罪恶进行反击的一种适当方式。如在1998年2月成立圣战国际阵线时,本·拉登宣称:“我们,在真主的帮助下,呼吁每位真主的信徒和期望因遵循真主的命令而获得恩宠的人,去杀死美国人并掠夺其财物,无论美国人身在何处。我们也呼唤穆斯林乌里玛、领导人、年轻人、士兵,对撒旦的美国军队与恶魔的支持者展开攻击,并驱逐它们背后的追随者,以给它们一个教训。”(37)2001年9月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本·拉登如此解释选择攻击美国的原因:“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巴勒斯坦、克什米尔与伊拉克屠杀我们。作为报复,我们有权利攻击美国人。九一一攻击并非针对妇女与儿童。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美国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象征。”(38)需要注意的是,“基地”鼓吹的“圣战”不局限于军事攻击一途,而是涵盖了经济抵制、践行信仰、抵御西方文化渗透、拒绝参与世俗选举等多种方式,这是一种立体而非单一的“圣战”。(39) 在进攻西方的同时,“基地”认为,要重建乌玛,同样需要对腐化堕落的阿拉伯政权展开攻击。(40)对于这些偏离了先知道路的政权及其追随者、不重视履行伊斯兰信仰和实践的人,“基地”宣布他们为“卡菲尔”,可以对其适用塔克菲尔原则,即他们不受乌玛的保护,可以根据沙里亚法实施死刑。(41)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治活动家、当代伊斯兰运动理论家萨伊迪·库特布(Sayyid Qutb)曾对塔克菲尔原则做过系统的论述。(42)库特布认为,由于现代的集权主义国家通过强力机关维持着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无知”状态,因此虔诚的信教者应该通过诉诸暴力以捍卫伊斯兰信仰,并对这些伊斯兰国家进行攻击,以恢复一种“伊斯兰秩序”。受到库特布上述思想的影响,“基地”领导人坚信对“卡菲尔”实现塔克菲尔原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换言之,塔克菲尔原则构成“基地”组织及其他类似恐怖主义团体针对穆斯林平民进行攻击的论证理由。(43)在“基地”领导人的公开叙事中,可以适用塔克菲尔原则的“卡菲尔”包括四类人:一是不赞成“基地”世界观的穆斯林;二是不执行伊斯兰教法的阿拉伯政权;三是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合作的穆斯林;四是质疑“圣战”重要性与必要性的人。(44)通过选择性地借鉴伊斯兰教的经文和不同时代伊斯兰运动理论家的阐释,“基地”领导人就如何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及重建乌玛给出了替代性的社会秩序方案以及实现这种秩序的途径。这种针对西方、伊斯兰政权甚至普通穆斯林实施暴力恐怖行为的论述,构成“基地”叙事中的处方式框架。 (三)“基地”叙事中的促发式框架 “基地”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也许其主要围绕怨恨叙事而展开的诊断式框架和主要围绕辩护叙事展开的处方式框架能够在伊斯兰世界产生一定的共鸣,但“圣战”的成败和乌玛重建的前景最终取决于其促发式框架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异教徒”势力仍然强大、“卡菲尔”控制着伊斯兰政权的背景下,“基地”主张全面实施沙里亚法的建议与呼吁缺乏现实性。故实施“圣战”构成了“基地”加以强调和鼓吹的首要斗争方式。因此,在“基地”的叙事中,有关“圣战”必要性、可行性、实施方式与策略等问题耗费了“基地”领导人的许多精力,此类叙事也非常丰富。大体而言,“基地”领导人的架构叙事主要通过重组宗教话语、提供思想激励、进行宗教或道德谴责、诉求伊斯兰教义中的“迁徙”等方式来构建促发式框架。 首先,激发普通穆斯林的危机感,鼓吹履行“圣战”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在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中,穆斯林必须履行的神圣义务和功修课程为念功、拜功、课功、斋功与朝功,也即通常所说的“五功”。通过重组宗教话语,“基地”把向异教徒发动“圣战”构建为穆斯林需要履行的“第六功”。其理由在于:如果穆斯林不为重建乌玛贡献力量,那么乌玛将永失荣光。通过强调伊斯兰世界正在遭遇的危机,“基地”领导人希望以此激发普通穆斯林献身“圣战”的意愿和热情。本·拉登强调:“在任何国家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是每个能如此行事的穆斯林的义务……这也是符合全能的真主的指示的。”(45)本·拉登不断强调,向全球的“异教徒”进行“圣战”,是“我们当前整个乌玛的义务,对乌玛而言,如果要战胜罪恶,那么整个乌玛需要献出它的孩子、财物、精力以开展‘圣战’,以抵御‘异教徒’施加的罪恶,避免他们伤害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46)在“基地”领导人看来,开展“圣战”是实现乌玛这一崇高目标的唯一和光荣的途径,不仅仅因为包括“布道(da'wa)”在内的其他路径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一方面是因为精英们受到玷污,另一方面也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过于强大,更重要的是因为“关于圣战的学说是在遵循真主之路,因为真主的指示和信仰至高无上”。(47)把“圣战”比附为真主的指示和先知之路,“基地”领导人尝试引导穆斯林基于对乌玛的信仰和对真主的虔诚而去履行“圣战”的义务。 其次,承诺精神和部分物质激励。仅仅诉诸宗教或道德上的义务,往往不足以吸引普通人参与暴力行动。因为根据伊斯兰教义,袭击无辜者或实施自杀性行为均是伊斯兰经典明令禁止的。为了突破这些禁忌,除了篡改或重组教义,“基地”领导人还鼓吹参与“圣战”能带来精神和物质激励,以吸引穆斯林献身“圣战”。(48)在精神方面,“基地”叙事鼓吹“殉道者永居乐园”,甚至诱以“殉道者”在天堂可享受“72位美目的处女(72 black-eyed virgins)”之类的话语。(49)在“基地”构建的话语体系中,以自杀的方式发动“圣战”而“殉道的战士”被称为“烈士”,享有崇高的地位。为“圣战”而死,不仅被塑造为最荣耀的死亡,而且也是进入“永生天堂”的一种门径。(50)这种在挪用相关宗教教义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烈士”叙事,“讲述了英雄般行动,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且经常与具有众多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的特定地方相联系,如天堂、地狱或耶路撒冷;或与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特定时代相联系,如处于重大危机的文化或时代的开端与结束,从而为自杀性攻击赋予一种‘超验基础(transcendent grounding)’”。(51)就“基地”的叙事而言,这个时代就是乌玛的衰落。如“基地”领导人强调,那些对当前乌玛所面临的危机视而不见的人,“将会受到真主最严厉的惩罚”。(52)当然,除了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激励,“基地”也会向那些参加“圣战”的战士提供一定的尘世激励。有幸生还,可以提高社会地位,获得一份好的工作或娶得配偶;(53)一旦“殉道”,将会给家庭带来荣光,从而提升其亲属在社区中的地位;将其肖像描绘在墙壁上或公布在媒体和出版物上,以庆祝其荣升天堂;有时会向家属提供抚恤金、关照其子女等。(54) 最后,对于拒不响应号召开展“圣战”的穆斯林,“基地”领导人则会提出警告,甚至威胁对他们实施塔克菲尔原则。“基地”领导人一开始对普通穆斯林响应号召攻击“异教徒”和反抗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寄予厚望,然而,响应号召的穆斯林远低于预期的事实,侵蚀着“基地”领导人对普通穆斯林履行其宗教义务的耐心。“基地”领导人认为,普通穆斯林过于在乎自己的安全和福利,并受到阿拉伯政权精英的误导,导致他们对乌玛面临的危机视而不见。“基地”领导人担心,穆斯林对“圣战”事业的冷漠和误解将导致驱逐外敌、重建乌玛的神圣事业获胜希望渺茫。大致自2005年开始,“基地”领导人严重不满于穆斯林对“圣战”表现出来的冷漠。如扎瓦赫里2008年以严厉的口气批评穆斯林:“我提醒伊斯兰国(Islamic nation)民众,他们需要对当真主问起他们为何不对穆贾西丁(mujahideen,即‘圣战者’)兄弟提供支持这一问题感到担心……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为未向塔利班提供支持感到懊悔,他们会醒悟到,真主终会问及他们为何不支持塔利班。”(55)事实上,按照扎瓦赫里的观点,穆斯林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对“圣战”事业无动于衷,而且是因为他们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犹豫不决、沉迷于自身安全,以致独裁者攻击我们、取悦他们,导致我们的事业停滞不前”。再比如,在批评巴基斯坦民众未对巴政府打击“基地”做出有力反应时,扎瓦赫里直言巴基斯坦人民“没有了荣誉感,泯灭了神圣性,缺乏自豪感,丧失了其价值”。(56)按照这种叙事,扎瓦赫里已将普通穆斯林视为难以动员的“外群体”,而且是导致其“圣战”事业举步维艰的障碍。如此严厉的言辞,一方面反映了“基地”领导人对穆斯林未积极响应“圣战”号召的挫败感,另一方面也为其警示乃至攻击穆斯林提供了理由。 四 “恢复哈里发的逊尼派卫士”——“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 相对于“基地”已有2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国”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恐怖组织。即使从“伊斯兰国”最早的组织形态——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2000年开始创立的“认主独一与圣战(Jamaat al-Tawhid wal-Jihad)”——开始算起,其历史也不过16年。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伊斯兰国”的名称却几经变化。(57)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涉及“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时,除非必要,均使用“伊斯兰国”这一名称。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伊斯兰国”非常重视建构架构叙事。有论者如此评价媒体宣传在“伊斯兰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相应的媒体内容与之伴随,‘伊斯兰国’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只会一事无成。”(58)在发展过程中,“伊斯兰国”同样构建了一套涵盖诊断式框架、处方式框架与促发式框架的叙事体系。由于“伊斯兰国”部分衍生于“基地”(2004年10月至2006年10月名字即为“基地”伊拉克分支),且其公开叙事体系的主要创立者扎卡维自称受到“基地”第一任领导人阿卜杜拉·阿萨姆(Abdullah Azzam)的影响,(59)因此,“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伊斯兰国”叙事中的诊断式框架 由于“伊斯兰国”与“基地”一样同属于“圣战萨拉菲主义”,而且均属于伊斯兰教义中的逊尼派,因此,对于伊斯兰世界所面临问题的诊断,“伊斯兰国”沿袭了“基地”的主要观点,如对西方的仇恨、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不满、对乌玛不复历史荣光的怨恨等。如在2014年7月1日,也即“伊斯兰国”宣告成立几天之后的第一个斋月,“伊斯兰国”“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其著名的“摩苏尔布道”中对伊斯兰世界的悲惨处境做了详细的论述,指出“乌玛”的穆斯林“正遭遇最为糟糕的迫害:他们的荣誉受损;他们的鲜血直流;被囚之人悲泣求助;孤儿寡母处境艰难;失去儿女的母亲悲伤垂泪;清真寺(Masājid)被弃,家园被毁”。(60)相对于巴格达迪的怨恨叙事较为抽象,“伊斯兰国”所掌握的宣传机器的怨恨叙事则更为具体。如“伊斯兰国”发行的电子刊物《达比克》(Dabiq)、建立的“中央媒体中心(Al Hayat Media Centre)”以及各省媒体分支机构大量散布有关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迫害、遭遇不公正的具体事例,试图以此引发普通穆斯林对其诊断式框架的共鸣。(61) 在“伊斯兰国”领导人看来,穆斯林所遭遇的不幸并非自然,而是敌视穆斯林的势力和“伊斯兰国”的敌人造成的。这种敌人并非特定的单个行为体,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及其支持者。如此一来,“伊斯兰国”的叙事构建了截然对立的二元化世界,乌玛是“自群体(in-group)”,敌人则是“他群体(out-group)”,两者处于不懈斗争的状态与过程中。2014年7月1日巴格达迪表示:“当前的世界已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两个战壕,不存在第三个阵营:一个是信仰伊斯兰的信众阵营,另一个是不信道者(卡菲尔)和伪信者(hypocrisy)组成的阵营;前一个阵营由全世界的穆斯林与穆贾西丁组成,后一个阵营则是由犹太人、十字军与其盟友以及其余的卡菲尔国家与宗教组成。后一个阵营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由犹太人进行动员。”(62)按照这种叙事,由美国和俄罗斯所领导的“他群体”是造成乌玛世界种种危机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也是“伊斯兰国”致力摧毁的世界。(63)巴格达迪在2014年7月1日曾指出,乌玛世界面临的困难就是上述他群体造成的:“不信道者削弱并羞辱穆斯林,在世界各地区宰制他们,掠夺其财富与资源,剥夺其权利。”(64)这种表述可以看出,“伊斯兰国”不仅对各种敌对势力充满愤懑,而且从根本上拒绝现代国际体系及其理念。 “伊斯兰国”诊断式框架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将什叶派穆斯林视为非真正的穆斯林。“伊斯兰国”架构叙事的特征自扎卡维时期即已形成,“伊斯兰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承续了这一观点。2004年2月,扎卡维宣称什叶派穆斯林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潜伏爬行的毒蛇、是狡诈邪恶的毒蝎、是刺探情报的敌人”。(65)扎卡维坚持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是拒绝信教者(rejectionists)和“叛教者”,相对于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打击什叶派穆斯林是更为紧迫的任务。他在2006年时指出,“什叶派首先开启了敌对,因为他们夺走了逊尼派的家园和清真寺,并在大街上对其进行攻击”。(66)“伊斯兰国”宣告成立后,该组织对什叶派的敌对态度并未有所变化,而是变本加厉地渲染并刻意挑起中东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试图从中渔利。如在2016年1月19日发行的《达比克》第13期中,“伊斯兰国”长篇引用扎卡维关于什叶派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以号召逊尼派穆斯林全力攻击什叶派。(67)“伊斯兰国”认同扎卡维的判断:“什叶派是背叛者和胆小鬼,他们只会恃强凌弱,只会攻击无依无靠者。”(68)由此可见,在延续“基地”话语框架的基础上,“伊斯兰国”构建的诊断式框架结合形势的发展也做了一些调整,以反映并操纵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教派冲突,这体现了其架构叙事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趋势,其目的在于试图巩固并推进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获得的据点。 (二)“伊斯兰国”叙事中的处方式框架 在诊断式框架的基础上,“伊斯兰国”构建了相应的处方式框架。由于将伊斯兰世界存在的非正义和苦难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等“异教徒”以及伊斯兰世界腐败的国家政权等“叛教者”,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国”顺理成章地要求对这些敌对力量发动“圣战”或实施塔克菲尔原则。不过,“伊斯兰国”脱离“基地”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前者在处方式架构上有其特别之处。这种特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伊斯兰国”的生存和崛起背景——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动荡局势和叙利亚内战——的影响,而且与“伊斯兰国”的发起人扎卡维的思维和行事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前者令“伊斯兰国”在提供替代性社会秩序时,主要着眼于中东地区的发展局势,而扎卡维的“前瞻性”眼光直接影响到“伊斯兰国”处方式框架的关注重点和“圣战”方向。相较之下,扎卡维对“伊斯兰国”处方式框架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更为显著和深远。(69) 需要追问的是,扎卡维到底为“伊斯兰国”应对伊斯兰世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处方呢?早在2006年,扎卡维如此描绘“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的战略目标和恢复伊斯兰世界荣光的途径:“我们将战斗不止,直到真主的沙里亚法所向披靡。第一步是驱逐敌人(系指入侵伊拉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者注)并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the state of Islam)。然后,我们将重新征服穆斯林土地,并将它们收归穆斯林治下……直到万能真主的沙里亚法盛行于全世界……我们将全力在整个世界实现伊斯兰正义并摧毁不信教者的非正义以及其他宗教的邪恶,这并非秘密。”(70)按照扎卡维的设想,“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的目标在于:对伊斯兰的敌人实施“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是仅次于遵循沙里亚法的义务;而拒绝“认主独一”原则的力量,均是异教徒,是实施塔克菲尔原则的对象;除了什叶派外的穆斯林共属一个国家,不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在世界范围内普及“认主独一”的精神并消除多神论、建设“哈里发国家”、全面实施沙里亚法。(71)从“伊斯兰国”后来的发展轨迹和行事方式来看,扎卡维的处方式框架很大程度上得到遵循。 扎卡维另一个应对伊斯兰世界问题、恢复乌玛荣光的必要条件同样得到了“伊斯兰国”的认同和继承,即攻击什叶派穆斯林。扎卡维曾言:“我们要进行两个层面的战争:一种战争是公开的,即与侵略者敌人公开作战,以清除卡菲尔;另一种是与扮成朋友的诡计多端的敌人作战,这种战争困难而且尖锐,他们展示同意,呼吁团结,但不断地掩盖其邪恶与阴谋”,(72)从而给战争制造了诸多障碍。而第二场战争的敌人就是什叶派穆斯林。扎卡维甚至认为,对于乌玛来说,什叶派是比美国更为严重、危险和残暴的敌人。(73)基于这种认识,无论是扎卡维还是后来的“伊斯兰国”,都将攻击什叶派穆斯林、挑起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作为增强组织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扎卡维如此规划利用教派冲突推进“圣战”事业的方式:“什叶派是促成改变的关键。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将他们作为攻击目标,而且对其宗教、政治与军事核心进行打击。这将挑衅他们将怨恨的矛头指向逊尼派,从而暴露出他们的内部矛盾并引发内讧。一旦成功,我们将能唤醒那些无动于衷的逊尼派,使他们意识到近在咫尺的危险和迫在眉睫的死亡。”(74)“伊斯兰国”不断在什叶派人群密集区域发动恐怖袭击,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激发教派矛盾,并从中牟利。 当然,“伊斯兰国”领导人在继承了扎卡维处方式框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其做出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为典型的变化是规划了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五个具体阶段。这五个阶段分别为“迁徙”“集合(Jama'ah)”“摧毁非法统治者(Destabilize Taghut)”“巩固(Tamkin)”以及“建立哈里发国家”。按照“伊斯兰国”的规划,这五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具有各自不同的任务:“迁徙”在于将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召集到特定的“圣战”据点,以扩充力量;“集合”在于将这些迁徙者进行“圣战”前的培训,以提高他们从事“圣战”的技能;“摧毁非法统治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叛教者”和“卡菲尔”发动暴力攻击,尤其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攻击,以制造尽可能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巩固”则力图填补暴恐活动留下的权力和秩序真空,以巩固其治下领土、扩充支持基础;“建立哈里发”是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此时,可以严格执行沙里亚法,贯彻“认主独一”的原则。(75)相对于扎卡维较为模糊的规划,“伊斯兰国”的处方式框架更为具体,也更具可操作性。“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发国家”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上述路径加以推进的。 (三)“伊斯兰国”叙事中的促发式框架 与“基地”一样,“伊斯兰国”同样需要解决如何动员穆斯林(逊尼派)支持“圣战”和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事业的问题。在此方面,“伊斯兰国”与“基地”一样,首先强调穆斯林参与“圣战”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这一点是“伊斯兰国”对“基地”促发式框架的继承。巴格达迪强调:“真主接受我们作为烈士的举动,并迅速医治我们的创伤,真主将穆斯林从囚笼中释放出来,并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避难所。”(76)与“基地”一样,“伊斯兰国”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认为穆斯林通过自杀性袭击针对无辜者发动“圣战”不仅无罪,而且是穆斯林的一种神圣义务,甚至是一项得到真主祝福的事业。如巴格达迪宣称,“圣战”团体事业的兴衰,均由真主决定,“圣战组织从虚弱走向兴盛,受到了真主的赐福;而它们趋于衰落和溃败,则是它们出现了病症的证据,我们须向真主寻求庇护”。(77)既然“圣战”的胜利是真主早就设定了的、无法更改,那么对于穆斯林来说,参与“圣战”不仅可以赎罪,而且还可以因此获得荣光。(78)穆贾西丁只要遵循真主的指示,不眷恋自己的生命和财富,他们不仅能收获胜利,而且还能进入天堂,得享彼岸的荣耀和辉煌。 为了进一步激发穆斯林献身“圣战”,“伊斯兰国”还号召他们进行迁徙,并将之改造为普通穆斯林应为真主履行的义务。“迁徙”同样是“基地”处方式框架的重要内容。(79)“基地”领导人构建的迁徙叙事强调,当代穆斯林应效仿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从麦加迁往麦地那,以摆脱困境,实现斗争事业的逆转。在本·拉登等人的操纵下,迁徙、服从真主及其使者、进行“圣战”构成虔诚穆斯林的三大标准。(80)而且,按照宗教极端主义者的阐释,迁徙是为“圣战”所做的准备,因为只有逃离“宗教无知”之地,才能为开展“圣战”提供条件。(81)不过,与“基地”不同,“伊斯兰国”甚至将迁徙提升至高于“圣战”的地位。如“伊斯兰国”强调,“迁徙是内在于圣战的一个支柱,在缺乏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时代尤其如此。真主的使者曾说:‘只要还有圣战,迁徙就不能停止。’他还说:‘只要仍在与卡菲尔作战,迁徙就不能停止。’因为在地球上不存在穆贾西丁的容身之所,故理想的迁徙之地只能是不存在强有力警察国家之处”。(82)毫无疑问,在“伊斯兰国”看来,穆斯林最为理想的迁徙之地自然是伊拉克与叙利亚。 除了阐发迁徙的重要性,“伊斯兰国”的宣传机构还详细说明了迁徙的必要性与目的。如“伊斯兰国”指出,迁徙具有多重目的:其一,逃避苦难,并避免与不信道者同流合污。其二,避免被异教徒或叛教者所玷污,以致认识不到自己的信仰和同胞。其三,对“伊斯兰国”而言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加入“圣战者”的队伍中,“支持他们,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对真主的敌人及他们自己的敌人发动圣战”。(83)为了吸引更多的穆斯林迁徙至“伊斯兰国”,该组织还提供了具体的指南,以指导他们完成迁徙之旅。(84)而对那些身处“十字军”或“卡菲尔”掌权国度的穆斯林,即使他们支持“圣战”事业,但由于他们对迁徙号召无动于衷,“伊斯兰国”严厉加以警告,指控他们是“失败分子”,“违背了真主的最高指示”,“毫无疑问,他们的信仰已被玷污,并且往往是在穆贾西丁打击十字军时最先跳出来予以批评的人,他们试图以维护伊斯兰教形象为由,掩饰他们对穆贾西丁的批评”。(85)按照“伊斯兰国”的理解,这类穆斯林并非虔诚的穆斯林,针对他们可以实施塔克菲尔原则。由此,通过提供激励或惩罚,“伊斯兰国”试图最大限度地动员穆斯林参加“圣战”,而且是希望他们到“伊斯兰国”土地上进行“圣战”。 “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并对此大肆宣传,则是其促发式框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2014年6月29日,“伊斯兰国”正式宣布成立。事实上,该组织此前的名字,无论是“伊拉克伊斯兰国”还是“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均模糊地含有该组织构成一个“哈里发国家”的含义。“伊斯兰国”希望利用名字上的含混之处,以期实现最大程度的动员效果。这主要是基于普通穆斯林怀念哈里发时代的心理。自从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924年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并将土耳其最后一代哈里发驱逐出境后,许多穆斯林对于源自西方的主权概念并不认同,而且期望重新恢复哈里发制度。(86)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甚至对哈里发的不复存在心怀怨恨,“在他们眼中,哈里发的消失意味着穆斯林政治权力的终结和西方的胜出,毫不夸张地说,逊尼派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就是一种重建哈里发的努力”。(87)而宣布“哈里发国家”重又出现,“伊斯兰国”可以宣称它能够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代表,并带领全世界的穆斯林重获伊斯兰世界的荣光。(88)巴格达迪认为,“伊斯兰国”的成立重新实现了乌玛世界的团结和统一,因为“叙利亚人不再是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不再是伊拉克人。地球是真主的……这是一个属于所有穆斯林的国家”。而有了自己的“哈里发”,履行迁徙义务自然也就成为每个穆斯林必须完成的使命:“所有的穆斯林,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有能力迁徙,那么就应该这么做,因为迁徙至伊斯兰之地是义务。”(89) 五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架构叙事的差异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架构叙事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逻辑上而言,这种现象都是正常的。从时间上来讲,“伊斯兰国”曾作为“基地”的分支机构存在过一段时间,它继承了“基地”的部分话语体系,包括对西方势力的仇视、观察世界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对构成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提出根本挑战等;从逻辑上来讲,“伊斯兰国”与“基地”均是恐怖主义势力,且主要为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都受到“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深刻影响,它们对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的认知存在公约数。正因如此,对它们架构叙事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尤有必要,这是对它们进行有效打击的前提。故下文将对它们在架构叙事上的差异进行简要分析。 (一)优先关注“远敌”还是“近敌”——诊断式框架的差异 “基地”与“伊斯兰国”的诊断式框架对于伊斯兰世界存在的屈辱和苦难的归因对象相同,即以美国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联盟以及与之合作的腐败阿拉伯政权及其他“叛教者”。这两种敌人被极端宗教主义者区分为“远敌(far enemy)”与“近敌(near enemy)”。(90)“基地”与“伊斯兰国”的诊断式框架均关注远敌和近敌。不过,两者的重点关注对象有所不同。 “基地”优先关注的是远敌。“基地”领导人认为,伊斯兰世界腐败的统治者固然需要推翻,但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打击和消灭它们的支持者——以美国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不消灭后者,那么严格实施沙里亚法、建立“哈里发国家”等就无法实现。鉴于此,“基地”致力于在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恐怖袭击,试图迫使它们改变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91)如扎瓦赫里2002年鼓励穆斯林对美国发动自杀性恐怖袭击,“这是遵循真主路上对死亡的热爱,也是用以毁灭(annihilate)美国的武器”。(92)由于美国及其盟友遍布全球,因此,在“基地”的架构叙事中,其活动范围也是全球性的。它宣称不仅希望解放中东,而且还希望解放高加索地区、阿富汗、克什米尔、东帝汶、达尔富尔等一系列地区。换言之,“基地”领导人对自身的定位是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的“圣战”团体,其优先目标在于打击西方。至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的阿拉伯政权,虽然也是需要斗争的对象,但不是“基地”当前的主要斗争目标。(93)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基地”的架构叙事优先关注远敌,但这一特征有时会有所变化。在此方面,本·拉登的立场只是偶尔有所游移,但扎瓦赫里的观点就有相当的模糊之处。扎瓦赫里总体认同“基地”应优先关注远敌,不过,由于对攻击近敌念念不忘,因此有时不愿在远敌与近敌之间做出优先等级上的区分。(94) 与“基地”不同,“伊斯兰国”的诊断性框架优先关注近敌,而非远敌。“伊斯兰国”的前身之一为“基地”伊拉克分支。与“基地”的其他分支一样,“基地”伊拉克分支起初为获得“基地”这一品牌带来的人员招募、资金筹措等方面的便利,名义上表示愿意采纳“基地”中央及其领导人优先关注远敌的叙事。不过,实际上,“基地”伊拉克分支及后来“伊斯兰国”的重点关注方向始终是近敌。如从扎卡维开始,“伊斯兰国”一方面主张打击以美国为首的驻伊拉克盟军,另一方面则竭力煽动伊拉克内部教派冲突,希望扩大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而为其攻城略地、扩充实力提供机会。(95)对于扎卡维肆意攻击穆斯林(主要是什叶派),扎瓦赫里曾表达过严重不满。扎瓦赫里先承认什叶派穆斯林的确不可信任,不过,他随后质疑攻击什叶派的效果和由此带来的道德问题:“鉴于什叶派的无知情有可原,为何要杀害普通的什叶派信徒呢?即使我们不攻击什叶派,又会遭遇什么损失呢?”(96)扎瓦赫里认为,屠杀什叶派不利于乌玛内部的团结,分散了本应一致针对美国的“圣战”力量,无助于“圣战”事业的推进。(97)扎瓦赫里对扎卡维的质疑不仅暴露了“基地”与“伊斯兰国”在诊断式框架上存在的分歧,而且也佐证了“基地”优先关注远敌的叙事特征。 “伊斯兰国”继承了扎卡维优先关注近敌的架构叙事。如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间,在伊斯兰“圣战者”内部流传一份题为《加强伊拉克伊斯兰国政治地位的战略计划》的文件。该文件的作者认为,“伊斯兰国”攻击美国纯属浪费时间,因为美军正准备从伊拉克撤军。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应采取的战略是全力攻击伊拉克的强力部门,包括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因为美国指望这些力量维持撤军后伊拉克的稳定与安全。攻击它们,更有利于“伊斯兰国”应对危机,拓展实力。(98)尽管这份文件是否得到“伊斯兰国”的采用不得而知,但“伊斯兰国”的叙事体系和战略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该文件的精神。如巴布尔·巴格达迪2014年11月表示,“伊斯兰国”的行动顺序为:首先打击什叶派,然后再针对支持沙特王室的逊尼派,最后才轮到十字军及其基地。(99)很显然,在“伊斯兰国”的诊断式框架中,美国等远敌并不居于前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以及雅兹迪人(Yazidi)、库尔德人等才是“伊斯兰国”最应关注的敌人。 事实上,“伊斯兰国”优先关注近敌并在行动上实践这一理念,构成其与“基地”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为了以示区别,“基地”与“伊斯兰国”在当前的叙事体系和实践行动中均强化自身的特征。如“基地”长期以来主要在西方国家发动攻击,即使是在伊斯兰世界发起恐怖袭击,其目标主要也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异教徒”,而“伊斯兰国”则主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尤其是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区)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如此带来的实践结果是:“基地”在打击穆斯林时有所顾忌,担心恐怖活动伤害穆斯林,进而引发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弹,故“基地”尽量避免在发动恐怖袭击时伤害无辜穆斯林,并在话语上为这种行为进行大量论证;(100)而“伊斯兰国”则无此顾忌,由此能看到“伊斯兰国”不仅大肆攻击什叶派和雅兹迪派等穆斯林,而且手段极为残酷。当然,出于战略上维持和扩大自身影响的考虑,两者也不排斥分别攻击近敌或远敌。如“伊斯兰国”于2015年11月13日在法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是其攻击远敌的一种体现。至少在诊断式框架的叙事上,“基地”优先关注远敌、“伊斯兰国”优先关注近敌的区分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在行动中它们是否实践这一特征,需要结合两者能力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做出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二)立即还是延迟建立“哈里发国家”——处方式框架的差异 在诊断式框架上对远敌与近敌赋予不同的优先性,影响到“基地”与“伊斯兰国”对于处方式框架的构建。在此方面,两个恐怖组织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它们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哈里发国家”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议上。虽然“基地”和“伊斯兰国”都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圣战”的终极目标,不过,对于是否需要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家”,两个恐怖组织存在重大差别。 “基地”领导人在公开叙事中较少提及建立“哈里发国家”这一问题。在“基地”的叙事中,“哈里发国家”是“基地”长期奋斗以追求的目标,“基地”领导人并未进行大量阐释并特别予以强调。如在2001年年初时发布的一封题为《建立一个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呼吁》(Calling for a Global Islamic State)的公开信中,本·拉登表示:“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每位成员都同意,目前被各种地理边界——基于民族、地理、宗教差异、颜色和种族——分割的世界所有伊斯兰国家应该合并为一个伊斯兰国家,那时将不再是人治人。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哈里发,其首都应设在麦加……这个庞大国家的名字应为全球伊斯兰国。”(101)不过,本·拉登并不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基地”迫在眉睫的任务。在2010年回答“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领导人纳西尔·乌哈什(Nasir al-Wuhayshi)有关是否需要在也门首都萨那(Sana'a)建立一个国家时,本·拉登如此回答,只要“美国还有能力摧毁任何我们建立的国家”,那么就没有必要如此做。他提醒乌哈什:“我们必须记住,美国这一敌人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102)在本·拉登看来,只要未战胜美国,那么建立“哈里发国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无法避免被美国颠覆或消灭的命运。只有当普通穆斯林对美国的怨恨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圣战”事业获得足够普遍的支持时,才是讨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恰当时机。扎瓦赫里也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并非“基地”当前的工作重点。(103)如在九一一事件后发表的一份公报中,扎瓦赫里承诺复兴哈里发,因为“正如本·拉登所说,这是真主的旨意”,不过,这项工作“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104)由于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在何时建立“哈里发”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等重大问题上含糊其辞,以致“基地”的处方式框架中有关替代性秩序的设计被认为是相当模糊的。(105) 与“基地”不同,“伊斯兰国”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解决现有伊斯兰世界问题的现实途径。扎卡维对于“圣战”能否获得普通穆斯林的充分支持并不十分关心,而“基地”的两位领导人始终强调建立“哈里发国家”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获得普通穆斯林的支持。为此,扎卡维坚持认为,不管其治下的民众如何看待,他都可以建立“哈里发国家”。(106)扎卡维对于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执着,构成他与“基地”领导人在架构叙事上存在的两个重大差别(另一个为反什叶派)之一。(107)受扎卡维的影响,“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也继承了这种狂热。如在2014年7月的摩苏尔布道中,巴格达迪强调建立“哈里发国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认为这是一种公共义务,“是穆斯林的责任——是一种已被遗弃几个世纪的责任……穆斯林因遗弃哈里发而获罪,必须竭力重建哈里发”。(108) 在宣布“哈里发国家”正式成立之后,“伊斯兰国”更是开足马力宣传“伊斯兰国”的相关信息,以吸引更多的穆斯林迁徙至这一“哈里发国家”之中。如“伊斯兰国”发行的电子刊物《达比克》第1期的封面文章题目即为《哈里发的回归》(The Return of Caliphate),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建立“哈里发国家”是“伊斯兰国”非常倚重的处方式叙事。另据学者统计,在2015年7月17日至8月15日“伊斯兰国”“官方机构”公布的1146件事件中,关于描述“哈里发国家”这一“乌托邦”的叙事占到总事件的52.57%,超过了其对“仁慈”(0.45%)、“战士的休闲生活”(0.89%)、“苦难”(6.84%)、“残暴”(2.13%)、“战争”(37.12%)五个方面描述的总和,“伊斯兰国”对于“哈里发国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09)很显然,巴格达迪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的行为,违背了传统“圣战”组织有关哈里发国家的建立应该延后并获得全体穆斯林的支持、乌里玛的同意等条件,自然引发了“基地”领导人的不满,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辩。(110)“基地”对“伊斯兰国”这一“哈里发国家”持严厉谴责的态度,意味着它又回到了建立“哈里发国家”是一项长远事业的立场上。(111) (三)是否渲染世界末日论——促发式框架的差异 “基地”与“伊斯兰国”诊断式和处方式框架的重大差异进而影响到两者促发式框架的不同。在此方面,是否鼓吹天启(Apocalypse)中的“末日决战(an End-Times Battle)”理念,并以此吸引潜在支持者甚至旁观者参与“圣战”事业,构成“基地”与“伊斯兰国”促发式框架的最大差别。 对于类似于“末日决战”之类的天启式话语,“基地”即使不是敬而远之,至少也是相当冷漠。“基地”组织的促发式框架主要诉诸的是动员对象的认知性和情感性需求,偶尔也会提供工具性的激励;即使使用天堂之类的话语,也很少征用天启式的象征。“基地”组织促发式框架的这些特征受到该组织领导人的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本·拉登很少谈论天启,即使偶尔提及,也倾向于认定在神的惩罚(divine comeuppance)这一壮丽时刻到来之前,他早已命丧黄泉。”(112)另一位对伊斯兰教中天启叙事做过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就所能获得的内部通信来判断,基地长期以来对天启式诱惑(apocalyptic temptation)无动于衷。”(113)虽然“基地”与“伊斯兰国”一样构建了一个善恶对决的世界,不过,“基地”似乎并未看到末日决战的迹象,似乎也不相信真主预先决定了“圣战”事业会在短期内成功,否则本·拉登和扎瓦赫里也不会对穆斯林不积极参与或支持“圣战”事业气急败坏。 除此之外,本·拉登和扎瓦赫里的经历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天启式叙事的态度。(114)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出生于精英穆斯林家庭,尽管本·拉登获得的是工商管理学位、扎瓦赫里不过是牙医出身,他们的宗教学素养有限,(115)但他们均认为沉溺于弥赛亚式的沉思不过是市井小民的无聊之举。此外,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属于逊尼派,而什叶派热衷于天启叙事,这进一步使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对天启叙事心生厌恶。尽管出于“圣战”大业的考虑,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往往不突出强调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以尽可能维系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团结,但长期的教派冲突史影响到他们对天启叙事的认知,本·拉登的个人经历则进一步使其对天启叙事和“末日决战”之类的理念充满警惕。1979年,一群逊尼派激进分子攻占了麦加大清真寺,并在其中卡巴神殿(Kaba)进行仪式,称其中一名激进分子为“救世主”马赫迪(Mahdi)。结果,在沙特士兵经过数周的围攻并最终攻入麦加大清真寺后发现,那位“救世主马赫迪”已一命呜呼。本·拉登对天启叙事敬而远之,或许与这位“救世主马赫迪”的屈辱之死有一定关系。虽然本·拉登与扎瓦赫里的部分手下也接受了末日决战或救世主之类的说法,但这些声音在“基地”的叙事中可以忽略不计。“基地”的态度非常明确:“许多穆斯林认为,只有当马赫迪出现,伊斯兰国(State of Islam)才能建立。这不过是纸上谈兵,以为举起双手向真主祷告,就会加速马赫迪的来临。”(116) 与“基地”不同,“伊斯兰国”热衷于宣传“末日决战”叙事。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扎卡维。扎卡维时期较早地在哈里发国家的建立和天启之间建立起来联系,并认为建立哈里发国家是在遵循真主的启示。如在2004年7月,扎卡维表示:“预示古兰经式的国家(Qur'anic state)的迹象已经出现”;2004年10月在向本·拉登宣誓效忠时,扎卡维再次强调“哈里发国家”即将出现,并表示它“需要通过我们的双手加以创立”。(117)从上述表述来看,“伊斯兰国”的处方式框架与促发式框架之间存在相互构成的关系:建立“哈里发国家”是天启预定的,而其建立则证明了天启正确无误。由此带来的逻辑后果是:既然天启正确无误,那么天启中有关大决战和末日审判的内容应是毋庸置疑的。上述逻辑关系一旦被确立并被接受,也就成为“伊斯兰国”独特的叙事体系,并使之与其他恐怖组织区分开来。从2014年开始,扎卡维的天启叙事被“伊斯兰国”系统加以利用,并成为其吸引穆斯林与外籍“圣战者”迁徙至“哈里发国家”参战的重要方式。“伊斯兰国”发言人2014年4月利用天启叙事宣称:“你们已被许诺了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麦加与麦地那,也被许诺了达比克、古塔(Ghouta,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引者注)与罗马。”(118)巴格达迪为了吸引更多人迁徙至“伊斯兰国”参战,同样以末日决战的话语蛊惑穆斯林:“伊斯兰教的青年们,去往应许的沙姆之地”,“来到你们自己的国家,托起你们的家园(edifice)……因为大决战即将展开”。(119) 总之,与“基地”不同,“伊斯兰国”大肆挪用并鼓吹伊斯兰教中有关天启和末日决战的相关象征,以此吸引追随者实现自己的野心。“伊斯兰国”较为系统地重构了《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末日决战”的天启叙事。由于《圣训》中有末日审判之前将在一处名为“达比克”的地方发生穆斯林与罗马军队进行末日决战的经文,“伊斯兰国”不仅竭力攻取了叙利亚西北部的城镇达比克,而且将其官方杂志命名为《达比克》。根据“伊斯兰国”的叙事,真主已经预设了所有的“异教徒”和“叛教者”均会在末日决战中被消灭,故“伊斯兰国”在占领了达比克后,只需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并接受末日决战的胜利。(120)“伊斯兰国”对于天启叙事的狂热,超越了他们对经典文本与形势变化之间错位的关注,也导致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叙事内部存在的逻辑或事实错误。(121)由此可见,在选择性地继承“基地”叙事体系的基础上,“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又糅合了教派主义、许诺哈里发国家、天启主义等因素,使之成为一个颇为另类同时又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恐怖组织。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架构视角出发,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及其异同做了简要的研究。由于两者在组织上存在过联系,这决定了它们在架构叙事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在诊断式框架上,两者均将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归咎于西方国家等“异教徒”以及专制的阿拉伯国家等“叛教者”;在处方式框架上,均主张建立“哈里发国家”,并对异教徒和叛教者们开展“圣战”;在促发式框架上,都强调穆斯林参与“圣战”的必要性,并认为“迁徙”至特定的“圣战”据点是一种义务。不过,由于组织演变路径与领导人理念的差异,导致它们的架构叙事也存在明显不同。如在诊断式框架上,“基地”组织优先关注西方国家等远敌,认为远敌是导致乌玛世界不复历史荣光的主要敌人;而“伊斯兰国”则优先关注什叶派穆斯林等近敌,认为它们是建立“哈里发国家”最主要的障碍。在处方式框架上,“基地”虽然坚持建立“哈里发国家”,但认为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在此之前“圣战”的主要任务是获得穆斯林大众的支持;而“伊斯兰国”则认为可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家”,这是确立认主独一原则和重建乌玛的有效途径。在促发式框架上,“基地”主要诉诸潜在支持者的认知、情感乃至工具性等层面,较少涉及天启叙事和末日决战的理念;而“伊斯兰国”则系统重构了伊斯兰经典文本中的天启叙事,并大肆鼓吹末日决战,以此作为动员世界逊尼派穆斯林参与“圣战”的主要话语手段。 对“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及其差异进行研究,至少能带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反击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是一项长期工作。(122)恐怖主义有自身的行动逻辑,而架构叙事就是了解其活动逻辑的一种方式。虽然恐怖组织的叙事体系与其行动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滞后于具体行动,但叙事体系毕竟是了解恐怖组织行动的重要指南或线索。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伊斯兰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按照其架构叙事构建的框架在执行。如果国际社会能较早地对“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形成较为深入的研究,或许可以拟定更富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其予以打击。此外,即使“基地”和“伊斯兰国”的组织形态不复存在,它们的架构叙事将对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产生持久和深远的影响。如“基地”经过多年的演变,已成为一个“品牌”、一种“意识形态”,即使组织本身消亡,其理念仍对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观念和行动带来启发。(123)基于此也可以推测,即使国际社会有朝一日从战场上摧毁了“伊斯兰国”,也无法保证其天启理念和末日决战论会随风飘散。不排除将来某种势力借尸还魂,重拾这套架构叙事并建立类似的组织。鉴于此,国际社会需尽快发动广大的穆斯林和学者构建反击“基地”和“伊斯兰国”架构叙事的反叙事,澄清它们的反人类、反文明特征,进而削弱其叙事的吸引力和动员能力。(124) 第二,通过了解恐怖组织在适当性逻辑上的竞争历程,我们可以展望它们的演变趋势。“基地”和“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在逻辑上相对连贯,而且具有不同的特征。出现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的竞争促使它们不得不完善各自的架构叙事,以争取与对手区分开来并在竞争中胜出。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两个恐怖组织在叙事体系上的竞争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条件。相对于“基地”,“伊斯兰国”的残酷、狂热和处心积虑挑起教派冲突并在话语上系统加以论证,使其比前者更为激进,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也更大。虽然国际社会不可能与“基地”合作打击“伊斯兰国”,但需要密切关注“基地”在叙事体系和行动上对“伊斯兰国”所做的反击及其叙事体系是否会与“伊斯兰国”趋同。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基地”虽然尝试在组织与叙事层面上实现与“伊斯兰国”的切割,但其分支机构与部分追随者开始采用“伊斯兰国”叙事体系中的象征——如“伊斯兰国”设计的黑旗、“末日决战”理念等。(12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伊斯兰国”叙事的动员能力尤其是吸引外籍人士参战的能力要强于“基地”。无论是吸引外籍人士前往所谓的“哈里发国家”参战,还是激励极端分子在西方国家等地开展“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均说明“伊斯兰国”架构叙事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再加上有部分原本效忠“基地”的分支机构转向“伊斯兰国”效忠,为了扭转颓势,不排除“基地”借鉴甚至向“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靠拢。 第三,需做好应对“伊斯兰国”外籍人员回流的准备,并尽早研究针对回流人员的去极端化、去激进化措施。随着“伊斯兰国”在战场上的失利,许多外籍“战士”很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回流本国。虽然此前“伊斯兰国”架构叙事中的诊断式框架优先关注近敌,然而战场上的失利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促使它转变进攻方向,将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人员投入到筹划在远敌领土上发动恐怖袭击上。当前遭遇严重难民危机困扰的西欧发生此类恐怖袭击的风险最大,因为据称有不少“伊斯兰国”的参战人员混在难民之中,试图进入欧洲开展暴恐行动。(126)对于这一趋势,首先,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伊斯兰国”外籍人员回流的管理,并深化在情报、反恐等领域上的真诚合作,尽可能截断“伊斯兰国”外籍人员回流的渠道。其次,需要加快研究更有效的去激进化、去极端化的措施。(127)由于“回流”人员接受了“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这给将他们拘捕后开展的去极端化、去激进化工作提出严峻挑战。因为“伊斯兰国”架构叙事的超残暴性、超保守性导致各国现有的去极端化措施有效程度如何存在诸多疑问。为此,国际社会应尽早就此开展研究,以探索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和杨恕教授、清华大学沈晓晨博士等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误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可参见Daveed Gartenstein-Ross,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The Islamic State vs.Al-Qaeda:The War Within the Jihadist Movement," January 13,2016,http://warontherocks.com/2016/01/the-islamic-state-vs-al-qaeda-the-war-within-the-jihadist-movement/,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Daniel L.Byman and Jennifer R.Williams,"ISIS vs.Al Qaeda:Jihadism's Global Civil War," February 24,2015,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sis-vs-al-qaeda-jihadism's-global-civil-war-12304? page =show,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②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March 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features/archive/2015/02/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③可参考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13-116页。 ④国外学术界的学术性成果已有不少,如粗略统计,关于“伊斯兰国”的学术专著就有20余部。不过,这些专著大多以资料性和介绍性为主,有深度的成果不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参见Benjamin Hall,Inside ISIS:The Brutal Rise of a Terrorist Army,New York:Hachette Book Group,2015; Loretta Napoleoni,The Islamist Phoenix:The Islamic State(ISIS) and the Redrawing of the Middle East,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15; Anna Erelle,In The Skin of a Jihadist:Inside Islamic State's Recruitment Network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2015; Phyllis Bennis,Understanding ISIS and the New Global War on Terror,Massachusetts:Interlink Books,2015。中国学术界关于“伊斯兰国”的成果主要以论文为主,可参考董漫远:《“伊斯兰国”的崛起与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51-61页;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24-30页;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38-156页;张金平:《“伊斯兰国”武装活动特点及走向》,载《国际论坛》,2015年第2期,第124-137页;谢许潭:《国际反恐新战场:应对“伊斯兰国”媒体宣传的挑战》,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82-103页;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4-27页;刘乐:《社会网络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动员》,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第82-109页。 ⑤不多的例外参见John Turner,"Strategic Differences:Al Qaeda's Split with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Vol.26,No.2,2015,pp.208-225; Celine Marie I.Novenario,"Differentiating Al 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rough Strategies Publicized in Jihadist Magazine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2016,DOI:10.1080/1057610X.2016.1151679; Daniel Byman and Jennifer Williams,"Jihadism's Civil War:The Islamic State Versus Al Qaeda," The National Interest,2015,pp.10-18; Daveed Gartenstein-Ros,Jason Fritz,Bridget Moreng and Nathaniel Barr,Islamic State vs.al-Qaeda:Strategic Dimensions of a Patricidal Conflict,New America Report,December 2015,https://static.newamerica.org/attachments/12103-islamic-state-vs-al-qaeda/ISISvAQ_Final.e68fdd22a90e49c4af1d4cd0dc9e3651.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⑥两种逻辑的区分,可参见James G.March,A Primer on Decision Making:How Decisions Happen,NeW York:Free Press,1994。 ⑦詹姆斯·G.马奇、约翰·奥尔森:《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69页。 ⑧Bert Klandermans and Dirk Oegema,"Potentials,Networks,Motivations,and Barriers: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01.52,No.4,1987,p.520. ⑨Donatella Della Porta,"Left-Wing Terrorism in Italy," in Martha Crenshaw,ed.,Terrorism in Context,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9. ⑩Milebna Uhlmann,"Challenges and Possibl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Counter-Narrative Measures vis-à-vis the 'Islamic State' Movement," in Jean-Luc Marret and Gonul Tol,eds.,Understanding Deradicalisation:Pathways to Enhance Transatlantic Common Perception and Practices,Washington,D.C.:Middle East Institute,2015. (11)Jennifer Jeffris,"A Fight for Narratives in the Battle Against Extremism," Small Wars Journal,August 1,2014,http://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a-fight-for-narratives-in-the-battle-against-extremism? utm_source,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12)Alex P.Schmid,"Terrorism and the Media:The Ethics of Publicity,"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1,No.4,1989,pp.539-565; Alex P.Schmid,"Terrorism as Psychological Warfare," Democracy and Security,Vol.1,No.2,2005,pp.137-146; Thomas H.Johnson,"The Taliban Insurgency and an Analysis of Shabnamah,"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Vol.18,No.3,2007,pp.317-344. (13)Robert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p.613. (14)David A.Snow and Scott C.Byrd,"Ideology,Framing Processes,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Mobilization:A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Review,Vol.12,No.1,2007,p.124. (15)Dang McAdam,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51. (16) David A.Snow and Richard D.Benford,"Ideology,Frame Resonance,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Vol.1,No.1,1988,p.199. (17)David A.Snow and Scott C.Byrd,"Ideology,Framing Processes,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pp.126-127. (18)David A.Snow and Scott C.Byrd,"Ideology,Framing Processes,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p.128. (19)Donald Holbrook,The A1-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2014,pp.36-49. (20)相关成果可参见David A.Snow and Scott C.Byrd,"Ideology,Framing Processes,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pp.119-136; 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2014; Quintan Wiktorowicz,"Framing Jihad:Intramovement Framing Contests and Al-Qaeda's Struggle for Sacred Author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49,No.Supplement S12,2004,pp.159-177。 (21)该概念源自Michael Page,Lara Challita and Alistair Harris,"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Framing Narratives and Prescription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3,No.2,2011,pp.150-172。 (22)“基地”的前身源自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参与抗苏战争的穆斯林志愿者(Mujahideen)所组建的“阿拉伯服务局”。一开始领导人为阿普杜拉·阿萨姆(Abdullah Azzam),本·拉登为其副手;1998年11月,阿萨姆遇刺身亡,本·拉登随即成为“基地”领导人。参见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17页;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p.11-12。 (23)“乌玛”意指“伊斯兰世界”或“伊斯兰共同体”,“吉哈德”意指“圣战”,“塔维德”意指“信主独一”,“希吉拉”(国内亦译作伊吉拉特)意指“迁徙”。关于这些核心概念的内涵,可参考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13-135页;John Turner,"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The Evolution of Salafi-Jihad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Al Qaeda Ideology,"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2,No.4,2010,pp.541-558。 (24)为了尽量避免出现误读,本文对“基地”架构叙事的研究参考了唐纳德·霍尔布洛克的研究,其从架构角度对“基地”叙事的内容及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参见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e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2014。 (25)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怨恨,可参见Thomas R.Mockaitis,Osama bin Laden:A Biography,Santa Barbara:Greenwood,2010; Peter L.Bergen,Holy War Inc.: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bin Laden,New York:Free Press,2000; Peter L.Bergen,The Osama bin Laden I Know:An Oral History of Al-Qaeda's Leader,New York:Free Press,2006; Steve Coll,The Bin Ladens:An Arabian Family in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Penguin Press,2008; 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Al-Qaeda in Its Own Words,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26)Osama bin Laden,"Osarna bin Laden's World Islamic Front Statement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Febmary 23,1998,http://www.fas.org/irp/world/para/does/980223-fatwa.htm,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27)Osama bin Laden,"From Somalia to Afghanistan," in Osama bin Laden,Messages to the World:The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edited by Bruce Lawrence and translated by James Howarth),London:Verso,2005,p.51. (28)Osama bin Laden,"Osama bin Laden's World Islamic Front Statement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http://www.fas.org/irp/world/para/docs/980223-fatwa.htm,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29)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Barak Mendelsohn,"Al Qaeda and Global Governance:When Ideology Clashes with Political Expediency,"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6,No.3,2014,pp.470-487。 (30)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72. (31)Osama bin Laden,Messages to the World,pp.3-15. (32)Fawaz A.Gerges,The Far Enemy:Why Jihad Went Glob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3)关于“乌玛”在“基地”叙事中的重要地位,可参见Fred Halliday,"The Politics of the Umma:States and Community in Islamic Movements," Mediterranean Politics,Vol.7,No.3,2002,pp.20-41。 (34)Salaf一词原为阿拉伯文,其意为“祖先”,具体指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时期。参见Christina Hellmich,"Creating the Ideology of Al Qaeda:From Hypocrites to Salafi-Jihadists," p.115。 (35)关于“萨拉菲主义”的分类,可参见Quintan Wiktorowicz,"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Vol.29,No.3,2006,pp.207-239。关于“圣战萨拉菲主义”及其与“基地”之间实践的研究,可参见Frazer Egerton,Jihad in the West:The Rise of Militant Salaf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Jeevan Deol and Zaheer Kazmi,eds.,Contextualising Jihadi Thought,London:Hurst and Company,2011; Mitchell D.Silber,The Al Qaeda Factor:Plots Against the We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1。 (36)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78. (37)Osama bin Laden,"Osama bin Laden's World Islamic Front Statement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http://www.fas.org/irp/world/para/docs/980223-fatwa.htm,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38)Hamid Mir,"Interview with Osama bin Laden," Dawn,November 9,2001,quoted in John Turner,"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pp.544-545. (39)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p.103-104;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6页。 (40)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72. (41)相关讨论参见Alia Brahimi,"Crushed in the Shadows:Why Al Qaede Will Lose the War of Idea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Vol.33,No.2,2010,pp.101-104。据称,七世纪中叶的哈瓦利吉派(Khawarij)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适用塔克菲尔原则的宗教派别。参见Emmanuel Karagiannis,"Defi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Jihadi-Salafi Movement," Asian Security,Vol.10,No.2,2014,p.198。 (42)库特布曾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高级成员。因筹谋刺杀埃及萨达特而被捕入狱期间,库特布在一系列信件中集中阐述了塔克菲尔原则,后被收录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路标》一书中。参见Shireen K.Burki,"Jihad or Qatal? Examining Al Qaeda's Modus Operandi,"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Vol.29,No.3,2013,p.241。 (43)Mohammad Hafez,"Takfir and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Assaf Moghadem and Brian Fishman,eds.,Fault Lines in the Global Jihad:Organizational,Strategic,and Ideological Fissures,New York:Routledge,2011,pp.25-46. (44)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8页。 (45)Osama bin Laden,"Osama bin Laden's World Islamic Front Statement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 http://www.fas.org/irp/world/para/docs/980223-fatwa.htm,登录时间:2016年3月1日。 (46)Osama bin Laden,Messages to the World,p.202. (47)Osama bin Laden,Messages to the World,p.69. (48)Akil Awan,"Spurning This Worldly Life:Martyrdom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in Dominic Janes and Alex Houen,eds.,Martyrdom and Terrorism:Pre-Modern to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223-225. (49)David A.Snow and Scott C.Byrd,"Ideology,Framing Processes,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p.129. (50)Samuel P.Perry and Jerry Mark Long,"'Why Would Anyone Sell Paradise?':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Making of a Martyr,"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Vol.81,No.1,2016,pp.1-17; Yuval Neria,et Al.,"The Al Qaeda 9/11 Instruction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Martyrdom," Religion,Vol.35,No.1,pp.1-11. (51)Robert Rowland and Kirsten Theye,"The Symbolic DNA of Terroris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Vol.75,No.1,2008,p.58. (52)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7页。 (53)Daniel Byman,"The Homecomings:What Happens When Arab 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Retur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Vol.38,No.8,2015,p.584. (54)David A.Snow and Scott C.Byrd,"Ideology,Framing Processes,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p.129. (55)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p.131-132. (56)参见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132,p.133。 (57)2004年10月,扎卡维写信向“基地”领导人宣誓效忠,该组织随即成为“基地”伊拉克分支(al-Qaeda in Iraq);2006年10月至2013年4月,该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或Islamic State in Iraq)”;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为“伊拉克与萨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ham)”或“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2014年6月至今更为现名——“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58)Dan Milton,"The Islamic State:An Adaptive Organization Facing Increasing Challenges," in Bryan Price,et al.,eds.,The Group That Calls Itself a State: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Islamic State,West Point: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2014,p.75. (59)扎卡维曾表示:“阿萨姆对我参加圣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转引自Ahmed S.Hashim,"The Islamic State:From al-Qaeda Affiliate to Caliphate," Middle East Policy,Vol.21,No.4,2014,p.70。 (60)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roadan," Al Hayat Media Centre,July 1,2014,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docuro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61)如研究者指出,在2015年7月17日至8月15日一个月时间内“伊斯兰国”的“中央”媒体办公室及各省媒体办公室共发布的1146件事件(包括图片新闻、电视录像、音频声明、新闻公告、海报、神学短论等)中,描述穆斯林所遭遇困难的事件比例占其中的6.84%。参见Charlie Winter,"Documenting the Virtual 'Caliphate'," The Quilliam Foundation,October 2015,pp.22-24,http://www.quilliamfoundation.org/wp/wp-content/uploads/2015/10/FINAL-documenting-the-virtual-caliphate.pdf,登录时间:2015年3月4日。该研究者所使用的术语为“受害者叙事(victimhood narrative)”。 (62)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docum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63)也可参考Haroro J.Ingrain,"The Strategic Logic of Islamic Stat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9,No.6,2015,pp.741-743。 (64)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decum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65)Ahmed S.Hashim,"The Islamic State:From al-Qaeda Affiliate to Caliphate," Middle East Policy,Vol.21,No.4,2014,p.70. (66)Isaac Kfir,"Social Identity Group and Human(In) Security:The Case of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ISIL),"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zm,Vol.38,No.4,2015,p.241. (67)如《达比克》表示:“在本政府(即指‘伊斯兰国’——引者注)成立之前,什叶派针对逊尼派犯下了诸多罪行,不过往往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他们杀害了许多穆贾西丁、学者、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不像明火执仗的美国人,什叶派说阿拉伯语,看似伊拉克人,熟知伊拉克领土。这使得他们是比美国人还要巨大的障碍,也是更为危险的敌人……因为其阴谋诡计,许多在美国入侵之初被杀害的穆贾西丁,实际上是被什叶派杀害的。”参见Islamic State,"The Rafidah: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Dabiq,No.13,2016,p.41。 (68)Islamic State,"The Rafidah: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p.42. (69)对于卡扎维对“伊斯兰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用一个例子做出较为生动的说明:在其发行的每一期《达比克》电子刊物的目录页,均会记下扎卡维的一句话,即“火星已在伊拉克燃起,其烈焰将持续加强——在真主的许可下,直至在达比克将全部十字军烧成灰烬”。参见Islamic State,"From Hijrah to Khilafah," Dabiq,No.1,2014,p.2。也可参考Haroro J.Ingram,"The Strategic Logic of Islamic Stat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p.737。 (70)Ahmed S.Hashim,"The Islamie State:From al-Qaeda Affiliate to Caliphate," p.70. (71)Ahmed S.Hashim,"The Islamic State:From al-Qaeda Affiliate to Caliphate," p.71. (72)Islamic State,"The Rafidah: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Dabiq,No.13,2016,p.41. (73)Islamic State,"The Rafidah: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p.42. (74)Islamic State,"The Rafidah: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pp.41-42. (75)参见Islamic State,"From Hijrah to Khilafah," pp.34-41。 (76)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docum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77)Abu Bakr al-Baghdadi,"Announcement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April 9,2013,http://triceratops.brynmawr.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066/16497/ABB20130409.pdf? sequence=1,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78)巴格达迪劝诫穆斯林:“你们只有一个灵魂,死亡时间前定,既不会提前也不能延后。不过,其间有天堂与地狱之火、平安喜乐和惨不堪言之别。对于真主的信徒,那将是大获全胜……真主的礼物是天堂。就灵魂而言,如果不明白真主并支持其宗教,那么只能是低贱的、痛苦不堪的、惨不忍睹的灵魂。”参见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www.gatestoneinstiture.org/docum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79)无论是在阿富汗抗苏期间,还是在与塔利班勾结和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抗,“基地”招募人员、保持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号召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迁徙到阿富汗参加“圣战”。 (80)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9页。 (81)参见John Turner,"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pp.545-547。 (82)Islamic State,"From Hijrah to Khilafah," p.36. (83)Islamic State,"To Our Sisters:The Twin Halves of the Muhajirin," Dabiq,No.8,2015,p.32. (84)Islamic State,"Fnroward," Dabiq,No.2,2014,p.3. (85)Islamic State,"The Burning of the Murtadd Pilot," Dabiq,No.7,2015,p.6. (86)John Turner,"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p.542,p.548. (87)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15,p.122. (88)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docum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89)Abu Bakr al-Baghdadi,"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documents/baghdadicaliph.pdf,登录时间:2016年3月3日。 (90)关于这种区分的起源,可参考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p.15-16。 (91)对这种战略的效果的评估,可参见Max Abrahms,"Al Qaeda's Miscommunication War:The Terrorism Paradox,"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17,No.4,2005,pp.529-549。 (92)Brian Whitaker,"Egyptian Doctor Who Laid Foundations of Global Islamist Offensive," Guardian,March 20,2004,quoted in Jeffrey Haynes,"Al Qaeda:Ideology and Action,"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8,No.2,2005,p.183. (93)Daniel Byman,"The Homecomings:What Happens When Arab 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Return?" p.589. (94)虽然扎瓦赫里的许多讲话明确地将伊斯兰世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并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掌权者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故打击美国是“基地”的重要目标;但与此同时,扎瓦赫里有时又会将这些问题归因为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发展状况。如埃及作为扎瓦赫里的故乡,他始终关注着埃及的国内局势发展及其国内敌人,并认为除非由穆贾西丁在埃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那么解放巴勒斯坦和其他穆斯林的土地、取消伊斯兰世界的腐败、恢复埃及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等问题,就无法得到圆满解决。参见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38,pp.70-72,p.146,p.150。 (95)Daniel Byman,"The Homecomings:What Happens When Arab 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Return?" pp.588-589. (96)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13. (97)也可参见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121; Ahmed S.Hashim,"The Islamic State:From al-Qaeda Affiliate to Caliphate," Middle East Policy,Vol.21,No.4,2014,p.72。 (98)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p.79-80. (99)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March 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features/archive/2015/02/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登录时间:2016年3月4日。 (100)据统计,本·拉登和扎瓦赫里所发表的声明中,有1/6的声明在于说明为了获得普通穆斯林支持的重要性以及使用暴力的局限性和风险。参见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92。 (101)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82. (102)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52. (103)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150. (104)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67. (105)John Turner,"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p.553. (106)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11. (107)Cole Bunzel,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p.13. (108)James Kitfield,"How to Stop Islamic State's Escalation Dominance," December 23,2015,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5/12/how-to-stop-islamic-states-escalation-dominance/,登录时间:2016年3月7日。不知为何,“伊斯兰国”官方发布的巴格达迪摩苏尔布道全文中缺失了这种文字。 (109)Charlie Winter,"Documenting the Virtual 'Caliphate'," The Quilliam Foundation,October 2015,pp.22-24. (110)相关情况的介绍可参见Cole Bunzel,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pp.32-34。 (111)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129. (112)Graeme Wood,"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March 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features/archive/2015/02/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登录时间:2016年3月4日。 (113)Jean-Pierre Tiliu,Apocalypse in Isl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p.186,quoted in 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28. (114)这里的讨论主要参考了威廉·马凯茨的研究成果,参见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p.28-29。 (115)Christina Hellmich,"Creating the Ideology of A1 Qaeda:From Hypocrites to Salafi-Jihadists," p.120. (116)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28. (117)Cole Bunzel,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p.15. (118)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103. (119)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100. (120)关于“伊斯兰国”“末日决战”叙事的内容、演变与存在的问题等的深入研究,可参见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2015。也可参见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16-17页。 (121)对此的解释,可参见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105,pp.142-144。 (122)Christina Hellmich,"Creating the Ideology of Al Qaeda:From Hypocrites to Salafi-Jihadists," p.121. (123)Olivier Roy,"Al-Qaeda Brand Name Ready for Franchise:The Business of Terror," Le Monde Diplomatique,September 1,2004. (124)关于构建针对恐怖组织的反叙事体系的重要性,可参见Daniel Byman,"The Homecomings:What Happens When Arab 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Return?" p.596; Donald Holbrook,The Al-Qaeda Doctrine:The Fram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dership's Public Discourse,p.69。 (125)可参见William McCants,The ISIS Apocalypse:The History,Strategy,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p.49,p.70;陶短房:《“伊斯兰国”黑旗的来龙去脉》,2015年6月2日,http://www.mzread.com/posts/s/2krgrezyk6kt,登录时间:2015年3月10日。 (126)Aaron Brown,"'Just Wait…' Islamic State Reveals It Has Smuggled Thousands of Extremists into Europe," November 18,2015,http://www.express.co.uk/news/world/555434/Islamic-State-ISIS-Smuggler-THOU-SANDS-Extremists-into-Europe-Refugees,登录时间:2016年3月10日。 (127)关于去极端化与去激进化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学术界一个亟待加以跟进和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现有成果可参见胡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研究——以沙特PRAC战略为个案分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第19-25页;沈晓晨、杨恕:《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激进化研究主要路径述评》,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6-43页;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