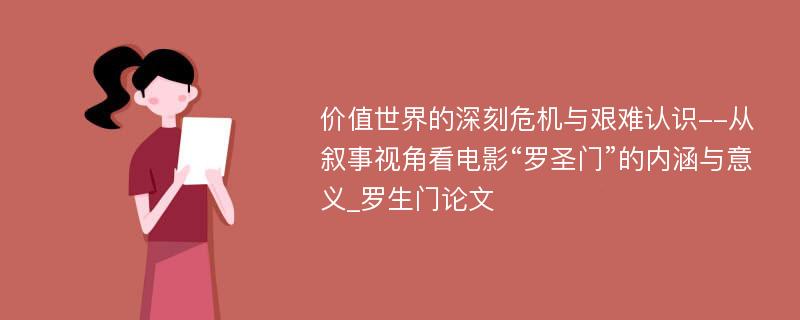
价值世界的深刻危机与艰难重认——从叙事方式看电影《罗生门》的内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看电影论文,深刻论文,艰难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57(2003)07-0015-04
1950年,黑泽明完成了电影《罗生门》。这部根据芥川龙之介小说改编的影片随后在 第12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这是日本电影首次获得这一大奖),引起了国际影坛 的极大瞩目,日本电影——也是整个亚洲电影由此真正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程。在今天 ,《罗生门》已被公认为是日本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现代主义电 影的起点,它对此后世界影坛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由于它成功 地将深沉的精神力量溶入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极富开创性的然而又是出奇简捷、朴素的 美学形式之中,而这个美学形式的关键则是一个叙事方式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选 择叙事学的角度作为分析这一作品的切入点无疑是恰当的。当然,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 将不止于叙事的层面本身,而是要力求达到对其意义内核的深入把握。
关于剧情的简短梗概
倾盆大雨中,灰暗阴沉的罗生门下,行脚僧和卖柴人一边避雨一边议论着一件关于强 奸和谋杀的案件。这时一个打杂的也来门洞下避雨,两人遂向他讲述此事。
案件发生于三日前,一名武士与其妻路遇强盗多襄丸,强盗强奸(?)了这位女子,武士 也陈尸林中。作为目击者和证人,卖柴人和行脚僧被传到公堂上,强盗和女子在这里分 别对案情作了陈述,两人的说法彼此矛盾。随后,在为死者举行的法事上,武士借巫婆 之口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而他(她)的讲述只是使事情显得更为复杂。最后,卖柴人承 认自己实际上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并对其余二人作了讲述——他的说法与以上三者均不 相同。
雨停了。残阳下,卖柴人抱着一个城门下的弃婴离去。
叙事方式
美国学者戴维·波德威尔在《虚构电影中的叙事》(1983)中提出了艺术电影叙事的三 种程序模式:“客观的”现实主义、“表现的”或主观的现实主义和叙事中的评述(注 :戴维·波德威尔.艺术电影的叙事[J].世界电影,2000,(6).(以下引用的波德威尔的 有关论述均见此文)),很显然,在《罗生门》中,“表现的”或主观的现实主义是一种 主导性的方式(四段特定人物视角的叙事构成了影片的主体部分),此外,叙事中的评论 也是其结构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波德威尔的看法,“表现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 点是将“休热特”(syuzhet,俄国形式主义术语,一译情节)限定在某种“临界处境” 中,它提供了一个符合传统习惯的中心点,使心理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得以承袭,而“ 针对某种处境的存在主义的意义,人物被赋予表达和解释自身精神状态的动机”。波德 威尔认为这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现实主义,因为休热特能够通过电影技巧将个体的心 路历程戏剧化。……法布拉(fabula,俄国形式主义术语,又译“故事”或“素材”— —引者注)世界和休热特戏剧化都凝聚在人物的行为和感情的困扰上;这也就是说,‘ 探究人物’不仅成为最基本的主题材料而且还是期待、好奇、悬念和惊异的主要来源” (这里的“人物中心论”主要是相对于好莱坞对“故事”的集中关注来说的)。波德威尔 同时指出,“表现现实主义”的程式可以构成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以及揭示人物内心 世界的一套“场面调度法”等等。与此相对,叙事中的评论凸显的是叙事的自我意识, “强调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这种法布拉的行为”,常表现出故事模式本身的混乱(藐 视叙事常规的倾向),从而“使叙事结构成为观者揣测的对象:故事是怎样讲的?为什么 这样讲?”而这种叙事中的自我意识往往又是与将导演视为创作者的观点并行不悖的。
以下是对《罗生门》叙事的一些主要层面的具体分析:
不可靠的叙述者与多重式内聚焦叙事
《罗生门》的叙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在罗生门下避雨的卖柴人、行脚僧和打杂的讲 述、议论构成超叙述层次,在他们的转述中出现的强盗、女子和鬼魂(由巫婆代表的武 士)的叙述构成主叙述层次(关于叙述分层的问题依赵毅衡说(注: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 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8,119,175,93-194,199 -201.)),超叙述层次的作用是自然而然地引出主叙述层,并构成一种叙事评论的手段 。影片中的主要叙述者是卖柴人、强盗、女子和武士(鬼魂)四个人,他们对同一故事的 各自叙述就构成了影片的主体部分。
这四个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在强盗多襄丸的叙述中,他在设下圈套把武士绑在树上 并把女子弄到手之后,正要离去却被她阻拦,她说无法忍受自己的丑事同时被两个男人 看见,要求两人中一定要死一个,强盗因此解开武士的绳索,与他展开了一场公平的决 斗(其间女子因恐惧而逃走),终于凭着过人的武艺用长刀杀死了他;在女人的叙述中, 自己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形象:强盗强奸她以后就逃走了。她抱着丈夫痛哭,却 看到对方用极其轻蔑冷酷的目光盯着她。她羞恨难当,终于昏了过去,醒来却发现丈夫 已断了气,胸前插着自己那把短刀……;鬼魂讲述的是故事的第三个版本:强盗得手后 ,劝诱女子随他而去,女子答应了,但要强盗先杀了绑在树上的武士;强盗怒其心肠之 狠毒,转而欲交由武士处置她。女子趁其不备逃走,强盗追赶不获,回来为武士松绑后 离去。武士万念俱灰,取短刀自尽(死后短刀为人所拔);在卖柴人的陈述中,先是说自 己只是看到死尸并报了官,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最后又承认偷偷看到了事情的经过。 这个经过在他的陈述中是这样的:强盗请求女子跟他走,女子未做答复,暗示二人决斗 。在丈夫拒绝决斗并斥责她的时候,她激烈地反唇相讥并刺激两个男人的自尊心,终于 使二人拿起了武器。决斗的过程毫无精彩之处,只是惨暴的乱斗而已。最后强盗杀了武 士,女子逃走。
四个叙述者彼此互相矛盾,每个叙述者都与其他主体意识发生冲突,无法纳入一个统 一的整体,更无法与隐含作者或作品总的价值观一致。他们出于各种复杂隐秘的利益动 机或更深层的心理原因,各各从自身的角度掩盖、歪曲或篡改事实真相。卖柴人作为一 个超叙述层次的局外人,本来似乎应该是最能做到公正客观的,但讲述开头的谎言(据 他后来说是“怕受牵连”)和最后被打杂的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就是盗走短刀(那是一把镶 螺钿的精美短刀)的人——这些使他的叙述也不能不变得可疑了。
在《罗生门》中,叙述者被特意安排成不可靠,一方面是用来达到明确的反讽效果, 即揭示人性本身的复杂和鄙陋;另一方面也隐含作者自身的怀疑和迷惘的流露。
不可靠的叙述产生于叙述主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罗生门》中,这种关 系是通过对同一故事(亦即每个人物所面临的“临界处境”)的“复述”或者叫做多重式 内聚焦叙事体现出来的。四个主要叙事段落都采用了一个特定叙述者的视角,并由这个 视角的持有者把自己的经历叙述出来。正如赵毅衡所说:“特定叙述角度把叙述者对故 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 力范围之内。”(注: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8.58,119,175,93-194,199-201.)每一段叙事都浸透了聚焦人物有意无 意的谎言、偏见和幻象。由于四段叙事之间明显的矛盾抵牾,用它们来重建统一的法布 拉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就促使观者把目光转向叙述本身而不是被叙述的故事,因为叙述 本身由于叙述者的自我限制而被戏剧化了。
情节
情节即被叙述的事件。如上所说,《罗生门》把重点放在叙述方式而不是故事本身, 或者说,是“讲故事”而不是“讲故事”,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从所指转向 表义过程本身”。(注: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8.58,119,175,93-194,199-201.)情节中的因果关系和与之紧密相联 的时序关系变得疑窦丛生、混乱不堪,由此产生的悬疑构成情节推进的基本动力,但这 种悬疑只是不断地使问题复杂化,却并不给予一个合理的最终解答。
赵毅衡指出,述本(叙述文本)对底本(大致相当于“故事”)所做的时间变形有两种, 一种变形的目的“是使底本中的事件以更方便的叙述形式出现”,可称为“再时间化” ,它保存了底本时序的基本形态;另一种时间变形则对底本时间作了根本性的破坏性的 改变,使述本中的事件无法按底本中的时间顺序复原,这种变形可称为“非时间化”。 由于时序与因果关系在叙述中密不可分,所以“非时间化”实际上也就是“非因果化” 。(注: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8,119,175,93-194,199-201.)《罗生门》通过四个不可靠叙述者的多重复述,不 仅在数量上大规模地分割重组底本时间,而且在根本上使事件脱离了底本时间的延续性 和顺序性的链条,这正是一种典型的“非时间化”或“非因果化”的方式。这种方式不 再需要观者对“本义”的理解,而是要求对隐含意义的读解——一种更高层次的阐释, 它建立在作品本身的歧义性或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歧义性——既体现在故事中,也体现 在故事的讲述中。正如波德威尔所说:“不确定性不仅只被理解为不确定,还要求被理 解为明显的不确定。……阐释影片,就是按照其最大限度的歧义解释它。”如果说“再 时间化”往往代表了传统作者与读者对叙述中因果关系的兴趣,对历史(或现实/底本) 的必然因果关系的信赖,并因此用自己的稳定价值体系和规范去抽取、删剪历史事件, 使之被叙述化或纳入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的框子的话(它往往产生于这种社会文化形态的 稳定时期或出于“稳定派”的手笔);“非时间化”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现 实并不服从一个必然的因果规律,其复杂性无法纳入任何现存的价值规范的体系。非时 间化是历史现实的非叙述化或无法被纳入一定的解释性体系的表现。它往往出现于旧的 社会文化形态体系崩解的时代,或出于“崩解派”的手笔。本雅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小说的(这也完全适用于电影——引者注)作者和读者对情节和故事失去兴趣时,他 们就显得对行为的意义和道德价值失去了信心。”(注: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8,119,175,93-194,199-201.)这 正是《罗生门》得以产生的深层思想背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上说,日本战败、帝 国神话的崩溃以及长期的破坏性战争引起的经济困难、社会混乱等问题(可能为了避免 过于近距离的直接影射当代社会,《罗生门》有意把故事的时代放在一个没有具体指明 的“前现代”时期,但城门下诸人谈论中透露出的信息[兵荒马乱、瘟疫、灾荒、盗贼 横行、人命如草等等]已经清楚地点明了这是一个危机深重的“乱世”)以及随之而来的 对旧有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普遍认同危机,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成为时代的突出特征——这些为这个背景提供了直接的注脚。而如果把这种状况放在一 个世界性的、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更广阔时代的背景中来看,那么它又不过是普遍意义 上的现代生活和人类状况的一个突出的缩影或隐喻而已。
叙事中的评论
除了直接的叙事之外,《罗生门》还运用叙事中的评论来突出叙事的差异、间离和歧 义性,并引导观者走向对叙述背后的隐含意义的读解。这种评论主要是通过超叙述层次 的三个叙述者(行脚僧、卖柴人和打杂的)在罗生门下的交谈议论来进行的。从这些谈论 中可以看出:三个人分别代表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与隐 含作者的倾向不相一致;但如果更深入一步来看,他们又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隐含作 者自身思想的某些层面。
打杂的代表着一种持彻底怀疑和否定立场的虚无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他对人 世的苦难漠然视之(影片开头卖柴人和行脚僧提起杀人案时,他表现得不屑一顾:“这 年头,杀死个把人算得了什么呀!”),在议论案情时断言人人都自私自利,“根本没有 什么老实人”,“人不能相信人”,从一种毫不掩饰的冷酷的利己主义立场出发,他发 现弃婴时公然地剥走婴儿的衣服,并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在这个人不如狗的世界 上,谁不替自己想呢?”这是一个极其尖刻、粗野、冷酷无情的形象,但同时他又是相 当敏锐和强有力的。正是他,从卖柴人叙述的漏洞中一下子看出了他是盗走短刀的人, 在因为剥弃婴的衣服而遭到指责和阻拦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这小衣服反正早晚 一定会叫人剥了去的,……我拿走又有什么不对?”并用偷刀的事实证明卖柴人也不是 什么好人,弄得对方哑口无言,终于让他剥走了弃婴的衣服。
与此相对,行脚僧无疑代表着一个传统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他高尚、纯洁,悲天悯 人而且多愁善感,但是却显得软弱无力,面对行将倾覆的价值世界只能发出绝望而无奈 的哀鸣。他看到了案子的可怕之处在于“世道人心,简直就没法让人相信了”,而这是 比什么强盗、灾荒、瘟疫等等都更可怕的事情。在案情被陈述的中间,他不断慨叹人的 自私自利,不可信任,感到这样的现实象地狱一样恐怖,但对此他除了哀叹以外却做不 出任何有意义的举动。
卖柴人则是间于以上二者之间的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他既是善良的,又不能摆脱人性 固有的各种弱点。他被亲身经历的事件所震撼,感觉到了价值世界行将崩溃的切肤之痛 ,在矛盾彷徨之后终于作出自己的努力去拯救那些可珍视的东西。他承认“如今在这个 世界上,人不能不怀疑”,感到“自己也摸不透自己”,但最终还是肯定要“相信人” 。尽管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隐含作者的否定和批判,但他最后对案情经过的陈述可 能仍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而在影片末尾他收养弃婴的举动则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的一抹 亮色。这个细节的象征意义是明显的。
通过这些多种声部共存的“复调”式评述,观者所感觉到的正是隐含作者——或者在 这里不如说,就是黑泽明本人内心的激烈矛盾、迷茫和挣扎。
诸种电影元素在叙事中的运用
《罗生门》的叙事是通过对多种电影元素的出色而协调的运用来实现的。这些丰富的 元素以十分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使整部影片的叙事给人以既生动、丰满又十分简捷 、朴素的印象。例如,就人物和表演来说,处于主叙述层次的强盗、武士和女子是影片 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人物都表现得充满活力、栩栩如生,从而使影 片真正具备了力度感和鲜明性。三船敏郎(日本战后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扮演的强盗 多襄丸初看起来(尤其是在强盗自己供述的部分)桀骜不逊而又胆力过人,充满了一种邪 恶的魅力,完全是个我行我素、放浪不羁的绿林好汉的形象;但在卖柴人的讲述中,特 别是在其中和武士决斗的一场,他却暴露出了色厉内荏的面目,显得十分的虚弱和怯懦 ,他和武士一样由于紧张、恐惧而不停地发抖,象野兽一样没命地喘着粗气,两个人在 滚爬跌打中胡乱地抓扯、扭斗,场面极其狼狈。前后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使他前面的自 吹自擂产生了一种漫画式的效果,由此也部分地暗示了这个人物撒谎的心理动机;而京 町子饰演的女子有时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可怜巴巴的弱女子(在她对案情的供述中),有时 却显示出刚强果敢的气质和几乎是恶毒的意志力;另一位出色的演员志村乔饰演的武士 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复杂形象,在不同的叙事段落中,他在观者眼前也交替表现出抑郁 、刚强、贪婪、正直、多情、狠毒、冷酷等等面貌。所有这些生动而复杂的形象被一并 呈现给观者,而影片本身并不告诉我们哪一个更真实,它把这个问题交给观者自己去判 断,而这一点正是和作品整体的叙事结构和意图相一致的。
在叙事结构方面:《罗生门》的叙事结构是建立在若干个倒叙(闪回镜头)的基础上的 。通过这种打乱时间顺序,不断地将描述中的过去渗入现在的手法,《罗生门》成功地 表现了不同人物各自主观视角中的经验,并使这些矛盾的经验之间形成强烈的冲突和对 比,而复杂可疑的人物——叙述者自身由此成为反讽的对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种 叙述方式使重点由所指转向表义过程本身,由确定的“本义”转向不确定的“歧义性” ,由统一和谐的价值规范走向其怀疑和崩解。
《罗生门》对光线、色调、音响和运动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例如,暴雨中的罗生 门一直笼罩在一种阴沉黯淡的色调中,而各个叙事段落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的布景 范围(林中)进行,其色调也以灰暗为主,但也时常有所变化,这完视情节发展和人物心 理的氛围而定。在运动方面:《罗生门》是一部富于强烈戏剧色彩和动作性的影片,而 这种风格的表现是与摄影机变幻不定的运动和精当的推拉镜头分不开的,这在行走、追 逐、格斗等场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一点也是历来备受电影史家们推崇赞誉的。另 外,影片的配乐和特定镜头等方面的处理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 不再展开了。
总之,各种电影元素的协调运用使《罗生门》的整个叙事过程既生动精彩、扣人心弦 ,又复杂多变、扑朔迷离,并最终自然地把观者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完美地实现 了创作的意图。
结论
《罗生门》产生于一个怀疑、虚无和崩溃的时代。故事本身所直接提出的可以说是这 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有没有可能找到终极意义上的真实?答案是否定的。这否定让 人痛苦,却又不得不如此。
当一个社会尚处于一套共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规范的有效控制下时,某种公认的“现实 ”或真实很难受到根本性的质疑;但一旦这个控制性的价值规范本身开始受到怀疑甚至 分崩离析,它控制下的“现实”或真实也就不复存在。人们发现,所谓唯一的、永恒确 定的“客观现实”或真实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虚构,它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 权力构造的产物。现实或真实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无数种——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构 建出(仅仅)属于自己的现实或真实,但是它们将不再可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价值规范体 系。
当真实被证明为并不存在或者是因太过复杂而无法为人所把握的时候,一切绝对价值 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成了问题。黑泽明借卖柴人的口说道:“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人不能 不怀疑”。怀疑什么呢?一切既存的价值观念。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再享有天然的合法 性或豁免权,人不得不象尼采那样进行“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并以此作为重新审视 世界与人本身的前提。而在这样做的时候,黑泽明就不自觉地接近了现代存在主义的起 点:彻底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写道:‘如果上帝不存 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这对存在主义说来,就是起点。”(注:萨特.存在主义 是一种人道主义[A].周煦良译,萨特哲学论文集[C].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因为存在 先于本质,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所以“人性是没有的”。萨 特承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 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但是,他鼓励人们通过“承担责任”的“自 由选择”来重新确定自己,从而“建立一个价值模式的人的王国”。(注:萨特.存在主 义是一种人道主义[A].周煦良译,萨特哲学论文集[C].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然而,黑泽明拒绝了这条道路。在影片的末尾,打杂的剥掉弃婴的衣物扬长而去以后 ,卖柴人决定收养这个孩子。当他伸手想接过行脚僧抱着的婴儿时,行脚僧竟错以为他 要剥掉小孩子的贴身内衣,待弄清其意图以后,他感到十分安慰,他说:“啊,你做了 件好事……多亏了你,我还是可以相信人了。”这是一个几乎过于直白的象征性细节。 “相信人”,意味着对基本的人道主义信念的重新肯定,而这里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 善性、良知、责任感及利他精神等最基本的伦理价值的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这种重认 不能不让人感到是勉强而缺乏说服力的。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 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在深刻矛盾中的痛苦煎熬和不灭的理想信念。毕竟,对一般人来说 ,“自由选择”是太过艰难因而也太虚妄无力了,人终究不能没有上帝或绝对价值的支 撑,否则就只有回到“人对人是狼”的野蛮战争状态或陷于荒诞的无意义生存,而这是 黑泽明所绝对不能认同的,所以,他别无选择。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结局……这是黑泽明的失败吗?面对这种苦涩(有时 甚至显得幼稚)的乌托邦式的梦幻,我们到底应该誉之为崇高悲壮还是斥之为荒谬可笑 呢?
我怀疑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学理的范围。在理性冷冷地拒绝的地方,是信仰,而且 惟有信仰仍在苦苦地坚持着。而在这一切背后,在所在矛盾、怀疑和失败的背后,我看 到了伟大的艺术家那悲天悯人的苍凉目光,这目光是那样的深沉、凝重、焦虑而又绝望 ,在这样的目光面前,不再需要任何的言说,因为它已经静静地穿透了观者的灵魂。
收稿日期:2003-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