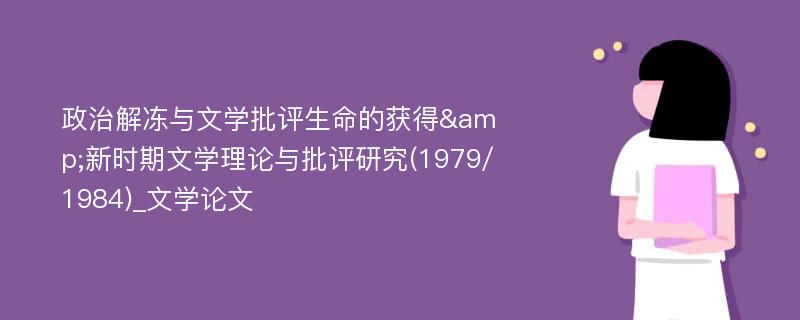
政治解冻与文学批评生命的获得——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1979-198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之初论文,新时期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2-0101-06
1978年,中国结束了癫狂荒诞的年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对“四人帮”的“左”倾理论进行了清算。邓小平同志在大会祝词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2](P3)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掀开了中国文艺事业新的一页,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下重获新生的。
一、批判与反思:文学批评观念的回归
(一)人学观念的确立
1.人学观念的历史来源
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源自高尔基。1928年,高尔基被选为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成员,他在庆祝大会上解释自己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时说:“我毕生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3](P102)。后来他在《论文学》中谈到苏联文学应该越过以前“贵族文学”的窄狭地域,把视野扩大到过去专制制度所压迫的其他地域的人民生活时说:“我并不是要强迫文学担负地方志和人种学的任务,然而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还指出,“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多变的趣味和情绪。”[4](P316)高尔基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始终弘扬人道主义精神,高唱人的赞歌,文学要塑造、赞美大写的人,要把普通人提高到大写的人的境界。这就是高尔基人学的基本含义。
由于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新中国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都深受另一位苏联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影响。他认为:“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5](P24)因此,当时的文艺理论批评界主要强调文学反映和认识外在现实的功能,而写人不过是为了写现实,以至于一些作品见物不见人,注重描写特定的生产过程、战斗场面,而在人的性格塑造上极少下工夫。
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以高尔基的“文学就是人学”为开篇之句,批驳当时流行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说法,认为“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在于揭示生活的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须要扼杀文学的生命。”[6](P140)而“高尔基把文学当作‘人学’就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6](P170)
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还提出了“在文学领域,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6](P142)也就是说,在50年代那样一个“左”倾思想蔓延的环境中,他提出了我们今天在文学批评中所推崇的理念: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钱谷融还对人道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把人当作人,承认人的正当权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最深的根底,最广的基础的。”[6](P156)
但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一片批驳声,他本人也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钱谷融后来回忆时说:“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对我的批判,却大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罪行来批的,并且不由分说的。现在回头去看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似乎有许多现象居然能够发生与存在,都会使人感到无限惊诧,甚至简直不可思议”。[7](P119)在此后的近20年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在“左”倾思想横行的日子里被文艺界抛在了脑后。
2.人性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
1979年,文艺界在一片拨乱反正声中重新探讨有关“人学”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依附的是文艺创作中的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性”的讨论,一个是“人道主义”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性”在“阶级性”、“工具论”的压抑之下被埋没达10年之久,突然在1978年重见天日,“我是人”的呐喊,必然成为这一特定时期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进行政治及历史反思的出发点。正如何西来指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野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8]同年,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感》一文中,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指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古希腊有一句著名的文艺信条:‘艺术模仿自然,也就是模仿人性’。”他还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指出:“马克思正是从人性出发去论证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发展私有制。”[9]朱光潜的观点在当时遭到了反驳:“朱光潜同志用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10]虽然朱光潜的观点遭到了批判,但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又被重新提出来。
在“人性”问题上,围绕什么是“人性”,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的联系与区别展开讨论。“人性就是保存生命欲望以及同人类繁衍有关的性的欲望”。[11]“人具有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本质是由这两方面关系决定的”。[12]与此同时,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79年到1980年,全国20多家报刊共发表关于“人道主义”讨论的文章80余篇;截至1983年4月,相关文章超过了600篇。[13]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是围绕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展开的,代表性的观点是汝信、王若水对“人道主义”的深化。汝信从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的人道精神”,以及“人道主义”要求“人的充分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内涵入手,确认了“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是不可或缺的”。[14]王若水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是一些道德规范,而且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15](PP.241-253)更值得一提的是,周扬、胡乔木在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也发表了重要文章,虽然二人在有关“人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文章在当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当时主要是不同观点的争鸣,最终也是一个“未完的文学预案”。[2](P4)但是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为中国文艺学以人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的重新确立,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度张扬,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哲学基础”。[2](P4)
3.人学观念的回归与张扬
1981年,国家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表示了理论界对其基本观点的认同。在此前后,一些报刊杂志业已发表了钱谷融的相关文章。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发表了他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这篇文章是他在1957年受到批判以后的自我辩护。1983年,《书林》又发表了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说明该文章写作、发表和受到批判的一些情况。随着钱谷融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伴随着“人性”、“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有关“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又重新回到了文艺界,这一观点在经过理论家的深刻探讨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吴元迈和李辉凡二位学者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尔基当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思想,以及提出这个命题的文化思想背景之后,对“文学是人学”提出了新的见解。“文学是人学,更正确的说,文学是艺术领域的人学。……我们只有把文学看成艺术领域的人学,才能深刻揭示出它的特殊本质和特殊意义”。[16]李劼在《文学是人学新论》一文中说:“‘文学是人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意味着相当具体的规定:对人的规定,对文学的规定,对‘文学是人学’的规定。也即是说,在这个看来空泛的概念之下,显示出了许多生动实在的内容,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文学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学。而‘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则意味着一种人类的自我生成过程。”[17]对“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当时理论界基本上保持了一致“赞同”的声音。正如刘再复在1985年提到,“‘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几乎是不待论证的,这一命题的深刻性在于,它在文学领域中,恢复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18]
对于“文学是人学”观念的重新探讨,创作界与批评界是同步进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以关注人、关注人性、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成为社会和时代思潮的代言人,刘心武的《班主任》、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人生》都描写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作品批评方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如朱寨的《留给读者的思考——读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曾文渊的《透视和描绘复杂的人生——读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等批评文章,传达出了当时“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正如后来理论家所评价的,“批评界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分析,并以这些形象为据,打破了那种简单狭隘的正面典型的观念,呼唤着更多不同个性的典型形象的破土萌生。”[19]
通过批评界和创作界的共同努力,“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并在80年代后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历史地看,‘文学是人学’观念的确立展现了命题本身的生命力和理论概括力,把人作为文学的出发点,从而牢固确立‘文学是人学’基础,并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和对于文学审美本质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为文艺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突破创新清理出了必须的场地,是新时期文艺学的第一个重大收获。”[20]
(二)为文艺正名
1.为文艺正名的前声
早在40年代,冯雪峰就曾在重庆提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不能分开、必须统一。1954年胡风“万言书”中的“五把刀子”说,更是对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的不满。1962年4月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起草的《文艺八条》,以及同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中,出现了文艺要“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提法,实际上这都是在当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某种匡正。[21]今天看来上述说法只是稍稍说了些不同意见,却在当时遭到了严厉甚至残酷的讨伐。到后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变得越来越神圣,越来越碰不得。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圣旨”供奉起来,当作在文艺上鉴别“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的试金石。
1979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人们开始重新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9年初,吴元迈在《略论文艺的人民性》中指出,“文艺的人民性概念始于十九世纪初,她的提出是文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并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被证明是一个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民性获得了新的科学基石。……今天,当我们在文艺领域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时候,有必要给人民性恢复名誉,以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22](P444)1979年3月,上海《戏剧艺术》杂志第1期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对流行的“工具论”发难,在肯定“反映论”的大前提下,批判“工具论”。这些文章的发表可以看作是为文艺正名的前声。
2.为文艺正名
明确提出为文艺正名观点的是《上海文学》。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十分流行、无人敢碰、碰则遭难的一个权威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进一步驳斥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文章指出:“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就会抹杀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和文艺的样式做出不适当的限制和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文艺的百花齐放”。[23](P38)并大声疾呼“为文艺正名”。更为可贵的是,这篇文章开始探讨“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求的真的价值,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求的善的价值,在真和善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是为了求的美的价值。”[23](P39)
这篇文章发表后,《上海文学》连续发表几篇为文艺正名的文章,拉开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学术论争的序幕。《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等国家核心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参与到这场为文艺正名的讨论中。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多次举行学术研讨会,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论断“我们的文艺从属于人民”。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且客观地分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纠正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极端化的思想偏颇。[24](P6)这样,文艺终于摘掉了“政治婢女”的帽子,在当时所能许可的限度内、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为文艺“正”了“名”。
二、走向审美化的文学批评
1.审美化文学批评的历史
20世纪,从王国维开始,经过蔡元培、周作人,至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朱光潜,形成了以审美文化为批评特色的文艺思潮脉络。与启蒙文学批评、政治文学批评不同,现代中国的审美文学批评自始至终矢志不移地恪守着文学审美活动的超现实功利性。从王国维主张的“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矣”到五四退潮期的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再到沈从文超然于党派政治与商业利益之外的文学观念、朱光潜“美感不沾实用”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学审美的自律性、超现实功利性,一直是中国现代审美文学批评的思维起点与价值底线。
然而由于救亡和启蒙的需要,文学批评从它诞生之初起就受到了文学启蒙和救亡作用的冲击而主要以社会学批评为主。此后又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文学批评主要为政治服务。文革十年,文学批评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评的审美化更无从谈起。
2.审美化文学批评的复苏
1979年以后,“人性”、“人道主义”禁区的逐渐突破以及文学的人学基础的牢固确立,促使文艺理论努力挣脱政治工具主义的枷锁,逐步从机械反映论走向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并进一步通过对于艺术反映论、艺术生产论的思考与探索,恢复了文艺的审美特性而使文学真正回归自身。1981年,《文艺研究》第2期发表的《从美学的角度加强文艺批评的讨论》一文中提出,“要提高文艺批评的质量,就必须把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进一步结合起来”。“文艺批评应该注意从美学的角度,深入地进行规律性的探讨”,“把真善美的高度统一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要注意“客观生活的美和作家主观审美意识的辩证统一”以及“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辩证统一”等等。虽然这些论述今天看来稍嫌稚嫩,但却走出了开拓性的一步,为美学批评的真正实现扫清了道路。
蒋孔阳的《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指出文艺创作要遵循“美的规律”。杜书瀛的《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论艺术的特性》提出艺术的感染力一是真实,再一个是炽热的情感。胡经之的《论艺术形象——兼论艺术的审美本质》提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本质问题。童庆炳的《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对文学的美学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与探讨。这些理论家们试图以他们对于文学审美的自觉意识推动新时期初期的文论由“他律”认识论向“自律”认识论转化。
80年代初,周来祥、栾贻信、王元骧等人就明确提出了文艺的情感特性,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是在认识过程中产生的、以人们对对象性质与自身需要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情感,文艺的生命主要在于审美特性。对艺术情感特性的强调必然导致对以往的机械反映论提出质疑,进而重新思考艺术反映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学术界普遍接受把文艺的审美特性纳入到艺术反映论之中,突出了艺术反映的审美特征或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并逐步形成了审美反映论。童庆炳提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25](P46)。钱中文也认为“如果把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改称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由此被纳入了审美的轨道,更符合创作实际”[26]。王元骧在论述文学的本质时确立了“文学的特殊本质是审美反映”,即“文学是以审美情感与心理中介来反映现实”[27],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作为形象艺术和语言艺术的本质特性。可以看出,“审美反映论”更贴近文艺的本质,它不但恢复了长期以来被扭曲、篡改的“反映论”文艺观的本来面貌,而且克服了其全面政治化的偏向,给它注入了审美的新鲜血液,使“反映论”文艺观获得了新生。但同时也应看到,以“审美反映”来概括文学的本质还略显不足,对此学界在90年代进行了深刻反思。总体看来,“审美反映论”的提出凸显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质,推动文艺理论研究由一般走向特殊,由僵化走向生动具体,由封闭走向开放,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探索改造和超越传统文艺理论的新水平和新成果。
在文艺理论界对文学的审美本质进行探讨的同时,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批评也迅速繁荣起来。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完全走出了“社会—历史的”批评的单一模式,开始寻找属于文学本体性的“美的”批评模式。评论家们开始从美学角度衡量文艺作品,把其作为审美对象进行研究和评价,并按照文学艺术应有的面貌和美的规律进行批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更多的文艺评论家在实践的过程中则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美学—历史批评”范式。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28]无疑凸现了作者批评胸怀的开放性、宽容性与超越性,而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29]是自朦胧诗讨论以来“较为系统全面阐述作者理论观点”[30]而从美学角度看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文章。另外,杨匡汉的诗歌美学批评也相当独到活跃,而蔡翔的《野蛮与文明——当代小说中的一种审美形象》[31]则是一篇既关注艺术作品本身,又从文化和“当代性”角度进行提升的美学批评论。《论阿城的美学追求》是从文化寻根角度论述阿城强化民族文化意识的独特“审美意识、情调和风格”。[32]正如陈骏涛后来所提到的,“‘新的美学—历史批评’范式不仅适合王晓明、陈思和、黄子平、季红真、南帆等青年批评家,也适合谢冕等一批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品格的中老年批评家。它异于传统之处在于更看重形式问题,更看重对美感形式与社会内容的有机整体把握,更看重对其他学科思维成果的借鉴”。[33]
1985年以后,审美化的文学批评走向式微。但是对文学作品审美特质的研究却在进一步的深化当中。
经过对“审美反映论”的讨论,学术界对文艺的审美特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注意到了“反映论”框架对文艺本质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人们力图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考察文艺现象,推进对文艺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到80年代中后期,学界就提出了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标志着对文艺本质认识的重大突破。审美化的文学批评也必将走上一个新台阶。
结语
1978年以后,政治环境逐渐改善,文学批评也重获新生。“文学是人学”、“为文艺正名”、“走向审美化的文学批评”等一系列观念的确立,使得文学批评一步步回归自身,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为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开局,是新时期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百家争鸣”、追求真理的批评精神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批评界。今天,批评界也应该进一步发扬这种精神,使得文学批评能够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9-07-06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文艺研究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上海文学论文; 文艺论文; 美学论文; 人性论文; 钱谷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