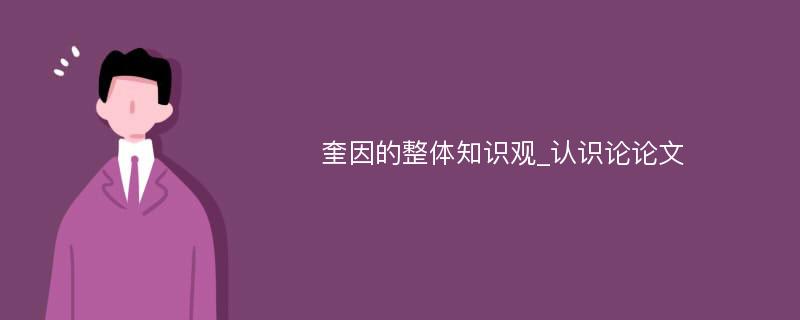
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蒯因从对基础论或还原论的批判中,引出了整体主义知识观,它包括下述要点:(1)我们的信念或知识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法庭的,接受经验检验的是知识总体,而不仅是整体边缘或离边缘较近的陈述,如直接观察陈述,各门具体科学的陈述等。(2)对整体内部的某些陈述的再评价必将引起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对其真值的重新分配。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而逻辑规律也不过是系统内的另外某些陈述,并不具有特殊地位。(3)在任何情况下整体内部的陈述都可以免受修正,假如在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4)基于同样的原因,在顽强不屈的经验面前,整体内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甚至逻辑和数学规律也不例外。(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验证据对于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6)所以,在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上,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标准,而受是否方便和有用这样一些实用主义考虑所支配,同时还要顾及该理论是否具有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精确性这样一些特性。这里,(1)-(2)点可概括为“整体论论题”,亦称“迪昂—蒯因论题”;(3)-(4)点可概括为“理论内陈述的可任意修正性原则”;(5)即是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论题,它在这里成为支持整体论论题和可修正性论题的逻辑依据,第(6)点充分展现了蒯因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
关于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我想着重论述以下几点:
一、整体主义知识观的理论基础与支持论证
假如不是从历史发展的秩序上看,而是从理论的逻辑关系上看,究竟是何种理论原因导致蒯因形成了整体主义知识观?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蒯因支持它的论证有哪些?我通过研究发现,整体主义知识观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即蒯因的不够彻底和不够一贯的实在论立场和他的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论题,支持它的论证则有三个:科学实践论证、语言学习论证与归谬论证。
蒯因作为一名极其推崇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哲学家,作出了明确的实在论承诺,即承认四维时空中的物理对象和数学中的类独立于研究主体而存在。但他同时又具有约定论和工具主义的倾向,这表现在他把物理对象和数学中的类看作是人为设定物,并且把科学理论看做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不过,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中,蒯因的实在论倾向更强烈一些,这表现在他坚持认为:科学理论归根结底起源于经验,即起源于外部对象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感官刺激,并且始终以错综复杂的形式保持着与经验的联系,在原则上可以或者应该在经验的反证面前得到修正或者辩护。独立存在的外部实体始终是我们所要认识和把握的对象。蒯因还认为,我们的整个科学尽管具有经验的起源,但它却超越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因此从同一组经验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是被我们所有可能的经验所不充分决定的,我们注定有在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理论。由于经验对理论有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又不是直接的和充分的,因此理论就象一个悬浮在经验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经验内容和经验意义在其中不能孤立地和确定地加以分配。实际上是科学理论整体面对着感觉经验法庭,遇到顽强不屈的经验反证时,究竟去修正或调整科学理论中的哪一个部分或哪些语句,是有很大选择自由的。而这正是蒯因整体论论题所要说的。因此,蒯因的实在论立场和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论题就是其整体论论题的理论基础。并且,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与整体论论题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
对于一个好的科学理论而言,仅有恰当的观察证据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构造和发展科学理论的活动就是同时对观察与系统的追求。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否则所得到的就“仅仅是观察记录,或只是无根据的神话”。①科学理论是一个在某些点上通过观察句与观察相联系的句子系统。或者,用蒯因自己的话来说,“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是被条件反射机制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而与非言语刺激相联系的句子之网”,②这就是他所谓的“信念网”,具体说来,科学理论系统是“那些在科学中被作为真的而接受下来的——尽管是暂时的——句子之网,在边缘上的是场合句,而且,这是一种特殊的场合句,即在任何给定场合对相关联的诸组或诸种感觉器的刺激会导致在那个场合接受这些句子为真句子。”③因此,一个科学理论的确立,需要有理论与证据之间精巧的相互调整,这种调整着受着除观察之外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
通过仔细的研究,可以把蒯因支持其整体论论题的论证归结为下述三个:
(i)科学实践论证。科学家在检验假说H时,必定还要肯定一组辅助性假设A的真。于是,在面对否定的观察结果时,科学家可以在A中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从而拯救待验证假说H。蒯因认为,以上情形是毋庸质疑的经验事实。
(ii)语言学习论证。蒯因相信语言的基本部分如观察句可以实指地学会,而语言的大部分则超出了可观察事物及其类似性的范围,需凭借类比综合才能学会。科学理论作为一笨重的语言结构,由理论词项编织而成,后者又由编织的假说相连接;它只在某些地方与观察相关联。当它作出一虚假预言时,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去修正该理论,以便它今后不再作此类虚假预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理论的语言除场合句之外,还包括了并不直接与观察相关联的语句,这些语句只能凭借一系列不可还原的类比跃跳才能学会,这就是说,当向回追溯时,不可能在观察语言的基础上顺利地导出理论语言。这就是蒯因所给出的关于整体论的自然主义解释:它源自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类比综合对于经验证据的超越。
(iii)归谬论证。蒯因论证说,如果整体论论题是假的,即一理论的每一句子都有其唯一确定的经验意义和经验蕴涵,那么,我们应该能达到一可接受的关于个别句子的证实理论,并且我们也应能够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划出绝对分明的界限。但事实上,后面这两点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并非一理论的每一句子都有其确定的经验内容,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法庭的。相反,如果整体论是正确的,则认识论上的还原论不可能是正确的,并且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绝对分明的界限也是不存在的。蒯因本人严格论证了这后两点。
二、整体主义知识观的本义和主旨
蒯因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整体论已被正确地叫做迪昂论题,并且还被相当慷慨地叫做迪昂一蒯因论题。它所说的是:科学陈述并不是孤立的受到相反的观察责难的,因为唯有共同地作为一个理论,它们才蕴涵其观察结构。面对相反的观察,通过修正其他的陈述,可以坚持任何一个陈述。”④但这种整体论学说过支于极端,它一方面受到了许多外来的批评,另一方面也与蒯因自己的其他学说相矛盾,因此蒯因后来力求将其“温和化”,具体说来,就是给它增加两个保留条件:(1)承认观察句的特殊地位;(2)缩小受观察诘难的理论整体的范围。蒯因说:
“一个保留与下述事实有关,即某些陈述是通过语言学习过程与观察紧密连接的。这些陈述确实是分别地接受观察检验的;它们同时又并不独立于理论,因为它们也含有更遥远的理论陈述的许多词汇。正是它们将理论与观察连接,起来。给理论提供其经验内容。即使对于这些观察陈述,……迪昂论题现在也仍然成立。因为科学家甚至偶尔也会取消一观察陈述,如果它与一个受到很好证实的理论相冲突,并且如果该科学家再现该实验的尝试归于失败。但是,若把迪昂论题理解为给一科学理论内的所有陈述以同等地位,并因此否认有利于观察陈述的那个强假定,则它就是错误的。正是这种(对观察陈述的)偏好使科学成为经验的。”
“另一个保留……与范围有关。如果科学语句只有共同作为一个理论才蕴涵其观察结论,那么该理论的范围必须是多大?它必须是被看作关于世界的综合理论的整个科学吗?
“……科学既不是非连续的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以不同的方式相连接,并且其连接点在不同程度上是松散的。面对顽强不屈的观察,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修正什么陈述和坚持什么陈述,并且这些选择将以不同的方式毁坏科学理论的不同范围,其毁坏在严重性程序上也不相同。整体在原则上是整个科学这一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可以用合法的方式为它辩护。”⑤
这就是说,蒯因整体论论题的两个重要保留是:(1)某些陈述如观察句可以分别地接受观察的检验,语句受观察检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2)科学的一个充分包容的部分,而不是整个科学,具有观察结果。经如此温和化之后,蒯因的整体论现在所要说的是:一个正待验证的理论“推出”了一个假的观察假言,但这并不是否定该理论的充足理由,因为不单单是那个理论本身,而是它和许多其他的理论一起,才作出了那个假的观察预言。因此,我们可以有多种办法去拯救那个理论:修正其他的观察证据,修正与该理论一起蕴涵假观察预言的其他理论和常识,甚至包括修正逻辑和数学。总之,在原则上面对顽强不屈的观察反例,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当然也可以不被修正;但在实践中,我们总是遵循最小代价最大收益准则,力争以最小的修正使从该理论到假观察预言的蕴涵关系失效,从而拯救该理论。
蒯因整体论的主旨或意图是什么?我认为,施太格缪勒的下述看法对于弄清楚这一点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蒯因的整体论包含有两种主要成分:(1)我们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可避免经验反驳的句子(拒斥先验认识)。(2)但是在理论和预言矛盾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指出某些引起这些矛盾的句子(拒斥孤立主义);相反,始终是作为整体的系统要么是受到怀疑,要么是又被调整好。”⑥受施太格缪勒观点的启发,我认为,蒯因整体论的主旨或真正目标是:
(i)拒斥先验认识,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使科学理论永远面对反面证据和批评。尽管蒯因对经验论的某种或某些形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名坚定的经验论者。在他看来,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关于词语意义的一切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认识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凡是在思维中的无不是先在感觉中。只不过蒯因强调感觉经验是行为意义上,它表现于外在的言语行为倾向,或者从对后者的观察中得到。因而,没有任何必然的、不可错的、不能被修正的先验知识,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经验知识,只是它们中有些离感觉经验近些,有些离感觉经验远些。也就是说,一切知识在经验内容方面只有多少的区别,而不是有无的区别,或者说只是程度之差,而不是种类不同。既然一切知识都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与经验的联系,因而面对顽强不屈的经验反例,我们理论的任何部分、任何陈述在原则上都可以被修正,甚至包括逻辑数学命题。就这样,蒯因通过拒斥先验知识、拒斥分析命题,给逻辑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以经验论说明,从而扫荡一切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使科学理论(尽管是受到很好证实的理论)永远面对经验,面对批评开放,以此为科学进步扫清道路。
(ii)强调科学家主体在提出或修正理论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尽管任何理论都有其经验起源,都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与经验的联系,但是,理论是由经验不充分决定的。这就是说,理论不是经验的函数,科学家不是一台接受经验输入而产生出固定的理论输出的机器。相反,科学家在接受经验刺激而产生理论输出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选择自由,从而表现出极大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这里,科学家的先天禀赋、性格特点、已有知识、理论偏好,甚至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等等方面的因素都会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由于科学家们在上述背景因素方面差别殊异,因而不同的科学家就可以由同一组观察发展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面对同样的经验反证,不同的科学家可以作出不同的修正,使已有理论获得与经验的协调一致。“这里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暗示”!蒯因就这样在经验论传统中,高扬了科学家的主体性因素,充分揭示了科学家主体在理论的创造、评价与选择活动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可以这样说,蒯因整体论是对于科学家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曲赞歌!
三、整体主义知识的内在矛盾及其理论归宿
我认为,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观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矛盾,并且最终必然导致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
1.整体论与蒯因隐含的基础论立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蒯因持有明确的整体立场。在他看来,科学双重地依赖语言和经验,但这个两重性不是可以有意义地追溯到每一个单独陈述的;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整个科学,其中的单个语句并不具有自己的唯一确定的经验意义或经验蕴涵,也就是不能被单独地证实或证伪。另一方面,尽管蒯因对基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名基础论者。这是因为基础论者有一个双层结构的理论模型: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和需要由基本信念来证明其自身的真伪或有效性的非基本信念,这里证明关系是单向的,非对称的。在蒯因哲学中,观察语句就扮演了无需证明或自我证明的基本信念的角色。蒯因认为,观察语句的证据是主体间可观察的,并且是主体间一致同意的,因而具有公共的和确定的经验意义,并且是单个地具有这种意义的。正是具有此种意义的观察句,才成为儿童和专业语言学家学习语言的出发点。否则的话,如果整体论是对的,并且每个句子的意义依赖于其他句子的意义,那么我们的语言学习似乎没有出发点,似乎没有一个句子的意义好象是自我包含和可学习的,因而可以作为学习其他句子的第一步。但是,必须有某种出发点,学习者(不管是儿童还是语言学家)能够在他已往的经验中获得,并把它作为检验关于随后一些句子的意义是什么的假设的有力证据。因此,在意义论的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是原子论者,因为不如此,我们就会使基本的语言学习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一来,整体论就必须考虑语言学习者的需要而有所缓和。蒯因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说他所奉行的只是一种“相对的或温和的整体论”。但不管相对、温和到何种地步,只要还是整体论,就是与语言学习的基础论要求相矛盾的。
2.逻辑可修正论与不同逻辑不可比较论题之间的冲突。蒯因从其整体主义知识观出发,得出了逻辑真理可错,逻辑本身可被修正的结论。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把多值逻辑、量子逻辑等异常逻辑(deviant logics)的出现当做是逻辑真理可修改、不牢靠的证据。但蒯因自己后来就否认了这一点。例如他在《逻辑哲学》(1970)一书中,指出:不同逻辑系统中逻辑联结词的意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逻辑系统(特别是标准逻辑和异常逻辑)之间就谈不上什么竞争或对抗了。因为“当一个人放弃了古典排中律时,他实际上放弃了古典的否定或析取,或同时放弃了这两者。”⑦蒯因由此得出结论说:异常逻辑改变了逻辑词汇或记法的通常意义,因而改变了论题,所以与标准逻辑是不可比较的。假如不可比较论题真的成立的话,它将把逻辑可修正论置于危险的境地:按一种解释,可以说修正过的逻辑与原有逻辑并无实质性区别,而只有记法的不同。这样一来,逻辑的修正就成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按另一种更可接受的解释,可以真正地改变逻辑而不只是改变记法,但是经修改得到的新逻辑与旧逻辑是不可比较的。因为如果人们改变了逻辑规律,那么他们也就相应地改变了逻辑常项的意义,从而改变了论题。于是,在新逻辑与旧逻辑之间就没有接触之点,所以也就没有冲突之点。这同样使逻辑的修正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如果要一贯地坚持整体论和作为其推论的逻辑可修正论,就要全部或至少部分地放弃不可比较论题。
由于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理论本身包含对经验证据的超越与突破,在行为证据的基础上我们无法唯一地确定理论内各孤立陈述甚至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的经验内容与经验蕴涵,因此,“关于我们的科学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物自体相符合的问题”是一个“超验的问题”,在自然化认识论中是“消失掉了的”。⑧这样一来,我们在评价与选择理论进时,就不应以是否与实在相一致或符合为标准,而应以是否方便和有用为标准:“每个人都被给予一份科学遗产,加上感官刺激的不断的袭击;在修改他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他的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⑨于是,实用主义成为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最高准则与最后归宿。
不过,在“实用主义”这个总原则之下,还是可以分离出下面一些成份与要素:
(1)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
蒯因认为,人们在作出本体论承诺,承认某事物如物理对象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作出的一种理论假定,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约定。科学理论也不是什么客观实在的反映,只不过是人们为了便于预测未来经验而主观创造出来的工具。例如,他明确断言“大大小小的物理对象不是唯一的设定物。力是另一个例子;……作为数学内容的抽象物——最终是类、类的类,如此等等——是同样性质的另一种设定物。”⑩既然物理对象只是设定,科学理论只是工具,当然它们无所谓真假对错之分,关于是否方便、有用的实用主义考虑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可以说,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逻辑后果就是狭义的实用主义;更精确的说法是,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乎就是一回事。
(2)突出逻辑标准,淡化以至取消客观真理标准。
既然我们的科学理论与物自体“符合”的问题,从蒯因认识论中消失,于是,如果还能谈理论或语句的真假对错的话,其标准肯定不再取决于理论或语句是否符合对象,而是取决于理论与理论、语句与语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它们是否自身融洽和相互融洽,凡融洽者即是真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而不融洽者则肯定不真或至少不可接受。于是,在理论的评价与选择中,客观的真理标准几乎不起作用,逻辑标准占据了首要地位。蒯因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合理假说的六大特征,其中保守性和温和性涉及新假说与先前已有信念的逻辑关系,简单性和精确性涉及理论的逻辑结构及表达方式,普遍性和可反驳性涉及假说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六大特征中至少有四大特征是属于逻辑方面的。
(3)相对主义
蒯因由否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不可修正的绝对真理,进而实际否认了人的认识的客观真理性,从而最终陷入相对主义。因为他认为,个别陈述不具有自己唯一确定的经验内容与经验蕴涵,只有科学理论整体才直接接受经验证据的经验,但是经验证据对于理论的决定是不充分的,因此翻译、指称、本体论等等在单纯的行为证据的基础上都不能确定地把握与测知,而具有不确定性;它们只有相对于一定的背景语言、翻译手册,且指称和本体论甚至要相对于关于量词的指称解释,才能确定地理解和测知,因而具有相对性。并且由于符合问题和真假问题从蒯因的认识论中消失,因此人的认识很难绝对地区分为真假对错,而只能相对地区分为是否方便、有用和有效。这样,蒯因最终必须陷入相对主义。但蒯因本人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他甚至严厉抨击了认识论中的虚无主义浪潮,明确与波拉尼、库恩、汉森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划清界限。这一事实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位著名的逻辑学家不承认自己理论的逻辑后果,并对自己的精神遗产继承人的与之一脉相承的观点大加挞伐。
四、整体主义知识观缺陷的根源
之所以产生上述这些矛盾与失误,我认为,其理论根源有两个:一是蒯因不彻底,不一贯的实在论立场,使他不能明确,一贯地坚持认识论上的反映论,最终滑入了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二是蒯因弄不清楚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之间的关系,夸大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完全否认了其绝对性、客观性的一面,最终事实上陷入相对主义。
1.蒯因始终动摇、徘徊于实在论与工具主义之间,从而不能明确一贯地坚持反映论立场。
这里的“实在论”一词不是用于与唯名论相对的意义上,而是用于与唯物主义近似的意义上。
总的来说,蒯因是一位具有强烈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作出了明确的实在论承诺,即承认四维时空中物理对象和数学中的类独立于我们而存在。蒯因在回答他人提问时说:“我站在唯物主义一边。我认为物体是实在的,永恒的和独立于我们的。我认为不仅存在这些物体,而且存在一些抽象的对象物,如数学的抽象对象物似乎需要用来充填世界系统。但我并不承认思想实体的存在,因为它们不是物质体,而是物体主要是人体的属性和活动。”(11)由于蒯因的实在论立场的不一贯与不彻底,由于他始终在实在论与工具主义之间动摇和徘徊,这在他的自然化认识论中造成了下述严重后果:
(1)蒯因不能明确一贯地坚持反映论立场。
据我所知,蒯因曾声言自己是一位唯物论者,但从未声言他是一名认识论上的反映论者,即他从未明确断言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科学理论是对于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反映。他一再肯定,我们的知识、理论具有感觉经验起源,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关于词语意义的一切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这些感觉经验,感觉证据是来自外部对象的对于我们感官的剌激,至于它们是不是对于这些外部对象的反映,蒯因似乎从不涉及这一问题。蒯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感觉论者和经验论者,但后两者并不一定就是反映论者。反映论总是与唯物主义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而感觉论和经验论既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也可以是唯心主义的。蒯因之所以不能坚持明确一贯的反映论,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的实在论立场总是不彻底且不一贯的,与真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有重大差别,具体表现在:(1)如前所述,蒯因的本体论观点具有明显的约定论和工具主义色彩。(2)他承认数学中的类或集合作为抽象实体而独立存在。(3)因为性质、关系、事实、可能个体等不能作为实体而存在,他就完全否认它们的客观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不相容的,其中存在唯心主义因素或滑向唯心主义的可能。正因如此,蒯因才从不明确支持认识论上的反映论。
(2)蒯因完全抛弃了符合真理论,而实际走向了融洽真理说。
由于蒯因的不彻底且不一贯的实在论立场,并且由于他从不明确一贯地坚持认识论上的反映论,于是,“关于我们的科学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物自体相符合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超验的问题”,从而在蒯因的认识论中“消失掉了”。这样一来,如果科学理论或其中的语句还有真假问题可言的话,那么真假就不再取决于理论与相应的外部对象之间的符合与对应,而是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理论自身是否融洽,即是否无逻辑矛盾而自身一致。凡融洽者就是真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而不融洽者则不真,或至少是不可接受的。蒯因就这样实际上走向了融洽真理说。
2.蒯因不懂得真理问题上绝对与相对关系的辨证法,严重夸大了认识中的相对性因素,其理论中潜伏着相对主义的暗流。
如所周告,蒯因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现代逻辑学家。受现代逻辑的深刻影响,他在方法论上追求严格,追求精确,追求纯粹。关于这一点,曾指出,蒯因把力求形式的精确性与偏爱接近主义结合起来。力求精确要求偏爱指称而不重视意义,偏爱外延对象而不重视内涵对象,偏爱语言则不重视思想和概念。(12)由于对形式精确性的过分追求,使蒯因的思维方法显得有些呆板,有些僵硬,缺乏辩证精神,这突出表现在他不懂得真理问题上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是一种理性的事业,它的目标是科学真理,即获得对自然的本质或规律的正确的认识或理论。科学事业是对真理的不断深入的无穷探索,而真理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在科学发展的特定阶段上获得的被事实所证实的科学理论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它必须随科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被检验、修改或发展,不断增加它对自然规律反映的逼真性。另一方面,任何被证实的理论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种成分是对认识对象的真实反映,不会被以后的发展所否定和推翻。科学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尽管每代人受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对自然界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带有局限性,但也具有相对真理性,为绝对真理的长河增添了一滴水珠。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发展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地向绝对真理逼近。
可以这样说,蒯因几乎完全不懂得上述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法。他出于科学家的本性与直觉,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认为在顽强不屈的经验反证面前,表达我们认识的任何陈述和命题都可以被修正,甚至包括逻辑和数学命题;不存在必然为真的先验知识,不存在不可错的分析命题。就此而言,蒯因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还指出,由于经验对于理论的决定是不充分的,理论存在对感觉经验和行为证据的超越,因此它实际上就无所谓真假,而只是是否方便、有用的工具。这样,蒯因就由于夸大人的认识中的主观性、相对性因素,进而否认了其中的客观性、绝对性成分,从而滑入了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这是由于不懂得辩证思维而在理论上付出的代价。
注释:
①②W.V.Quine:Theories and Thing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1,P.31,P.40.
③W.V.Quine:Word and Object,Cambridge:MIT,1960,P,11.
④⑤W.V.Quine:"On Empirical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Erkenntnis 9(1975),PP.313-315。
⑥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页。
⑦蒯因:《逻辑哲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5页。
⑧⑨⑩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第42页。
(11)麦基编:《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5页。
(12)Hao Wang: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The MIL Press 1986,P.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