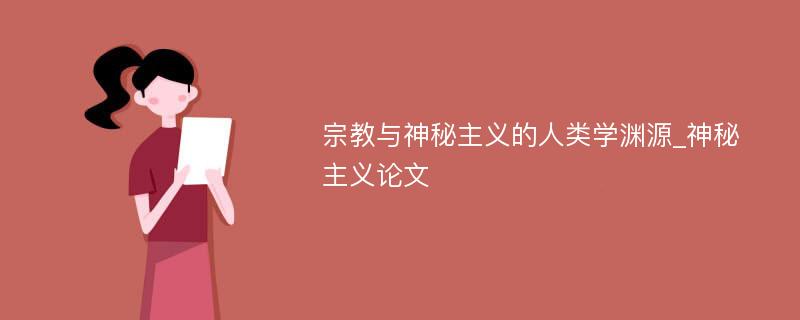
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人类学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秘主义论文,人类学论文,根源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两个哲学人类学讲演之二(注:本文最初以西班牙文写成,题为Las raíces antropológicas de la religion y de la mística,收录于文集Problemas,Barcelona,2002。曾译为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发表。中文翻译以作者自己翻译的德文本为依据,并获发表授权。第一个演讲题为《尼采与哲学人类学:内在超验的问题》,也收录于文集Problemas。相关文集尚有《自我中心状态与神秘主义:人类学研究》,慕尼黑2003。(译者注))。哲学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怎样从结构上区别于动物。在第一个讲演中,我赞同亚里士多德和一些现代哲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类基本的特征在于,他们说一种谓语性的直言式(praedikativ-propositionale)语言。这种语言结构中根植着我们客观化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以及追问理由的能力。现在这个演讲的主题是,宗教与神秘主义作为现象,是否也可由这种语言的功能来解释。两种现象无疑都具有人类学根源,因为:那种认为动物也能祈祷的设想是可笑的;而两种现象渊源于某种特定人类文化的设想,并无说服力。
我认为宗教性冲动以人类意愿(注:几个意义相近的德语词Wollen,wille,Wunsch分别视上下文语境译为意愿,愿望,希望等;拉丁文词源的das Voluntative译为意志。(译者注))的反思结构为基础,而这反思结构又根植于语言的直言式结构。第一个讨论人类意愿结构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区分了两种意愿,一种是反思的,经过考虑的意愿,另一种是直接的、感性的意愿。后者指动物性的,取决于感觉喜好的意愿。人类也有这种感性意愿,然而到一定的年龄后,会有反思自己感性意愿的能力。有了这种反思的能力后,人类的意愿就取决于他们认为这好还是不好。在追问什么好或更好时,我们在自由的空间内思考:首先,为达目的,最好的手段是什么;然后更进一步,在联系自身的基础上思考,对我和我自身的生活而言,更好的目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精神论》[1]的一句名言里说,人类的时间意识使人不得不考虑未来的生活,所以人类的意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类的意愿就是“烦”,烦生活怎样延续,烦生活的质量如何。以我所知,哈里·法兰克福1971年的论文《意愿自由与个人的观念》[2]是当代就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研究。法兰克福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不仅有愿望,而且还可能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些特定的愿望。因此必须区分愿望的两个层次:在第一层次上,我们简单地想要什么;在第二层次上,我们想要接受或拒绝某种愿望。例如,一个人想吸毒,同时又希望自己不要有这样的愿望。这个第二层次的愿望概念可视作对亚里士多德反思性的,经过考虑的意愿概念的复活。在这个层次的意愿中,我们似乎搁置起第一层次意愿,考虑同意或否定第一层次意愿的理由。
所有实践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样进行的。然而在搁置的过程中,如果追问我们想怎样生活时,这种考虑便有了特殊的意义。为突出这样追问的可能性,我称其为第三层次的意愿。因为在第二层次的意愿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即在自身感性意愿的随意性中建立一定的秩序;而第三层次的意愿面对的是人生,与前者不但不同,且深入得多。这个问题可称作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在这样追问时,我们试图找到一种超越具体意愿的,能够回答为什么我们宁愿生而不宁愿死这类问题的关键。有些人永不会迈出这一步,另一些人走到这一步只因为相信,死亡已经临头。通常在青春期,在人们有能力爱的时候,这个问题首次出现。严肃的爱情意味着人们将另一个人对自己的意义和自己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因此可以理解,恰恰在一个人获得爱的能力时,他同时遭遇死亡——生命问题。一般而言,在幼童身上是看不到第三层次意愿的。
我首先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观念为例,阐释这个第三层次的意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观念就是希望在始终如一的安宁的情绪中生活。这样的愿望显然超越于对实际生活中具体愿望的考虑。在第三层次上做出抉择意味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满足当下的愿望,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希望怎样生活。这个“怎样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人们希望怎样对待自己的情绪。所有道德行为的动机都可以在两种方式上得到理解:如果道德行为就是我自身意愿的对象,目的之一,那么对道德行为的考虑是在第二层次上的;而如果一个人在思考人生意义的基础上将道德理解为不言自明的,那么就是在第三层次上进行考虑。
我认为,就第三层次的问题而言,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比亚里士多德在安宁的情绪中生活的愿望更为基本,即人们如何对待自身愿望遭致的失望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所有宗教以及神秘主义的基础。
首先要注意的是,对愿望未能实现的预期是实践思考直接的后果。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由于人们的愿望总是和时间相关的,人们便有了自己可能死去的忧虑。对每个人而言,死亡都是最大的、最极端的失望。这一普遍现象就是不幸,而对这个词的理解,例如在英语中,然而也在其他所有我熟悉的语言中,——德语除外,都是在和“好运”对立的“厄运”意义上的。动物不可能在“运气”的意义上意识到幸运。“运气”是人的筹划中那不可预期者,那酝酿“偶然”的东西。拥有实践思考能力的存在,总要筹划将来,而在“可能计划”中蕴藏着对“偶然”在“运气”意义上的意识。所有技术——无论如何原始——的意义,就是设法将偶然性尽可能地减低。今天我们的技术虽然相当发达了,但是却不能克服偶然,正如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一样。既然人的意愿是对将来的筹划,那么人人都不断遭遇到意愿未能实现的可能性。这个“未能”意味着,那个不利于己的偶然:厄运。因此死亡,今天人们乐于推到边缘的死亡,曾经作为中心主题出现在几乎所有文化中。然而比死亡更基本的是这个更普遍的问题:如何才能将失望整合到人生中?所以人们如何对待失望的问题,不仅是第三层次意志的一个例子,而且根本就是这个问题的中心所在。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如何能接受失望的问题。
小结:直言式语言的直接结果是,在人类意愿结构中出现反思性考虑。法兰克福称反思性的意愿为第二层次的意志。由于直言式语言的结构,我们明确地遇到是与否的矛盾,即愿望和计划得到实现与遭致失望的矛盾,最后产生了第三层次的意志:对于人生的反思,其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整合失望与愿望。当然,无论是如何整合的问题还是追问人生意义的问题,对人而言都不是必要的,没有它人们也可以过得不错。只是这样的生活缺乏一致性:人们过着被动的生活,是幸运或不幸玩弄的对象;如果不寻求一种持久的人生观念的话,甚至自身愿望也成为偶然的了。第三层次的意志最重要的载体曾经是宗教和神秘主义。
如果问宗教性是什么,可能鲁道夫·奥托的《神圣性》[3]是就这个问题影响最大的著作。奥托认为,宗教性最本质性的范畴就是神圣性,而神圣性就是他称作“神秘的颤栗”的经验。稍后米尔克雅·艾利亚德的著作《神圣性与世俗性》[4],在我看来,是从奥托的观念出发的,所以两位学者都因其观点不具有普适性受到批评,而最有力的批评是,他们都以直接经验“神的在场”为出发点。
奥托的观点来源于施莱尔马赫,而后者认为宗教性产生于一种绝对依赖性的感觉的观点更为合理。如果我对施莱尔马赫的理解正确的话,他的观点之重要不在于区分了依赖性的相对与绝对两方面,而在于指出这个事实:每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力量,并因此在怎样的程度上独立于他人力量的影响,却还总是要遭遇他的能力所及范围之外者,因而总处于对幸运与不幸,好“运”与厄“运”的恐惧中。
我并不相信所有宗教现象可由某一种特定的观念来解释。我的意思是,施莱尔马赫指出的是宗教现象普遍的关键所在。因为,笃信神的力量的原因,根植于人人都有过的自己力所不及的经验,计划与偶然的冲突,而偶然总是意味着好“运”和厄“运”的对立。认为动物也体验神性的想法之所以可笑,不仅因为动物不能说话,还因为动物不能思考他们的意愿,因此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界限。此外,人们总以人格化的形式来设想神性的存在。
典型的宗教性行为大概是祈祷。在祈祷中,人们或祈求未来的幸运(好“运”),或感谢神曾赐予的幸运,或赞美神。第三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赞美神时,人们不仅承认神是有力的,强大的,而自己是弱小的,而且还在感谢与赞美中,在实用的意义上说出了自己要求帮助的愿望。当人们在神面前屈膝时,不仅知道自己依赖于一位伟大力量的存在,而且知道神高高在上,比自己或其他人都更有价值(过去君主可获得一个中间位置,人们在他面前也屈膝)。接近于高高在上的表达是崇高,——两者都不见得恰当,可惜我目前为止找不到更好的词汇。要完全地理解这里的意思,不可忘记宗教与信仰的联系,而信仰指出,神是道德的源泉。尽管恶神也不是没有,但人们却不会向他祈祷;一般而言,神都被认为是善的本质。这部分是由于神被视作赐福幸运的缘故,因此人们才能向神祈求幸运;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在宗教精神中克服了自我中心主义。
尽管人们的祈祷行为在时间上的三个发展阶段极易混淆,但也并非没有区分的可能。首先,人们试图在一种奇妙的过程中影响神的力量,对神使用第三人称,仿佛他是某种自然的生物。再来,笃信神者使用第二人称,请求神的意愿帮助自己。我认为这是本真的宗教性行为。然而在第三种行为可能性中,人们用“我们的父,你的旨意将实现”这样的表达展示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为宗教立场所成就的行为。在此,笃信神者自己的意愿显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不再设法影响神的意愿,不再要求神做我想做的事,而是屈服于神的意愿,并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承受。在人们将不幸理解为神的意愿的过程中,将坏事变成了好事。笃信神者成功地通过其行为的改变重新理解了“好事”。本来,他的愿望实现才是“好事”,而现在,“好事”已和他的愿望无关了。这就是说,通过建立同神的联系,他重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成功地将“失望”整合到自己的人生中来:他将所有发生的事理解为神的赐予,既然神的赐予总是好的,因而所有发生的事也是好的。
宗教性怎样获得这种与其开始完全相反的意义的呢?显然通过人们对神的赞美,对神的善的本质坚定不移的信仰。例如,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亲人死去时这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圣经·约伯书》第一章,21行以下)。这段文字中重要的倒转在于,失望被整合进人生中,而人在这种条件下获得了对自己人生坚实地掌握。因为失望是神所赐予,所以被视作“好的”,作为“好的”被接受,受到自己意愿的认同。于是人生获得了完整的意义。身患重病的笃信神者会说:尽管病痛是糟糕的,然既是神的赐予,自有其意义。在此可清楚地看到,第二和第三种宗教性行为的作用:缓解人生的不幸,使人生变得可以忍受,只是“缓解”不再是从失望中获得拯救,而是使接受失望成为可能。因此“缓解”达到的是灵魂的安宁,即,如此对待人生,使得人生中的失望也成为人生的一部分。
第三种行为似乎是人们在宗教范畴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因此有人坦言,担心这将导致寂静主义(注:Oietismus,基督教神学流派之一,主张灵魂放弃自身力量,完全受上帝的指导,如同“将自己献给风儿指引的帆船”(P.Segneri,Lettera di risposta al signor Ignazio Bartalini Sopra L'ccezioni che da un difensor de'moderni quietistis a Chi ha impugnate le loro leggi in orare,Venedig 1681)。)。然而,耶稣在克西马尼花园中的祈祷证明实情并非如此:“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39行以下)。可以看到,第三层次并没有放弃第二层次中的意愿,耶稣的祈祷准备接受神赐予的厄运,同时又请求,不要赐予这个厄运。一般而言,人的意愿是双重的:他想要幸运,但也接受不幸;他尽一切努力避免不幸,然而,如厄运果真降临,他也积极地接受。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对神的信仰不再可能时,宗教性行为如何自处。这就是尼采指出的“上帝之死”。以我所知,指明了现代宗教困境的最佳著作是弗洛伊德的《幻觉的未来》[5]。对神的信仰在弗洛伊德看来,不仅是个错误,更糟的是,这是个幻觉。幻觉就是人们出于希望而产生的非现实的信念,也可说是由于意愿的动机而产生的信念。当人们对一种观念无法给出理由,而只能给出主观性的原因时,这种观念的真实性就更加不可信了。所以宗教是孩子气的幼稚病,圣父就是现实中父亲的投影。弗洛伊德认为,信仰的错误甚至不值得证明,因为众所周知,信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希望决定的。
认为宗教是一种幼稚病的说法未免夸张。神圣性作为那超越一切人类力量的崇高被经验到,这样的经验如何能等同于孩子对待父亲的态度?弗洛伊德只是不想给任何能证明信仰合法的立场以辩解的余地,因此他甚至忽略了将失望整合人愿望这个行为的问题。尽管弗洛伊德对绝望这个问题钻研之深,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但他的答案居然是,一个成年人对于现实的,深沉的失望惟一能做的仅是:咬紧牙关,默默忍受。这就是说,我们应学会忍受绝望,无法将之整合,也无法给予人生以意义。他似乎还说过,追问生的意义问题也是幼稚病——然而,人生的意义毕竟不是儿童能够提出的问题啊。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现代人回避宗教呢?这似乎能支持弗洛伊德,实际却不然。回避宗教的动机首先是,今天,生活普遍比过去容易多了,因而深沉的失望很容易被推到生活的边缘:遥远未来的死亡是模糊不清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理论上的:今天的人们难以摆脱科学的世界观,而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里没有容纳纯粹精神性存在的空间。神的理念,作为在生物进化之前即已存在的精神与道德性存在,与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如此格格不入,老实说,即使没有弗洛伊德的意识形态批判,我们也应抛弃宗教信仰。哲学上那种“我们既无法证明神存在,也无法证明神不存在”的论辩,合乎逻辑却空泛,因为在纯粹逻辑理念——其惟一的合理性就是其不可证否性——上建造人生,即使帕斯卡尔也会感到荒谬。何况,仅凭弗洛伊德的意识形态批判,也能驳斥哲学上最后的怀疑。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今天惟一一种真诚的无神论立场,而我与他的区别仅在于,我不相信内情如此简单。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宗教信仰有深沉的人类学根基,而不能被简单地贬低为幼稚病。因此当信仰不再可能时,就出现了真空状态。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可以说,人类本质上就有进化而来的,将自己与更高的存在相联系的能力,因而一个没有信念的人一定程度上是不完全的存在。
尤其是如何接受死亡与其他失望的问题悬而未决。弗洛伊德那今天被广泛接纳的观点,即一个人在最深沉的失望中只能“咬紧牙关”,令人不满是因为,它不允许在变幻不定的人生中完整意志的可能性。正因为死亡的关系,人们才想要一个合乎理性的人生观念。尽管断断续续地生活,今日一步登天,明朝凄凄惶惶,——这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然而却是值得置疑的。在引入第三层次的意志这个概念时,作为例子我曾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安宁的情绪中生活的观念。这个观念虽然深刻,然而却将死亡和失望这些问题抛在了一边。惟一整合负面与正面的古希腊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但斯多葛派认为道德上的卓越足以对抗失望的看法,并不可信,因为问题在于坚持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如何能不仅忍受,还要接受痛苦。在宗教之外还有与第三层次的意志相当的学说吗?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神秘主义。在东方,在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神秘主义显得比宗教更为重要,因为是神秘主义而非宗教,起着整合生活观念,引导灵魂归于平静的作用。
首要问题当然是,如何理解神秘主义。对此可谓众说纷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囊括人们所知的所有流派。然而我们还是想得到一个能够多少囊括印度教,佛家与道家的冥想的不同形式,以及至少一部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的概念。有一种观念将神秘主义描述为一种意识状态,在其中主体意识到自己与万物的整体,或存在,或神合为一体。这种被称为与神一体的状态,经常被描述为冥想,或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经验。雅斯贝尔斯有一个概念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在神秘主义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消失了。赫拉克利特以多种方式表达的公式是hen pan,“万物归一”。所有这些表达的重要特征是,“我”消失了,或者说至少不再重要了。
然而,有的神秘主义并不在上述之列。例如印度教的神秘主义,在Samkhya瑜伽中,主体只沉入自身之中,并无与客体合为一体的要求。在佛家中主体既不沉入自身,也不进入与世界同一的状态,其理想境界是“空”。而在道家与赫拉克利特,主体与事物的多样性都没有消失:万物归一是说,万物都具有同样的产生与消失的结构。
神秘主义最普遍的一致之处或许是,意识、自我消失了或变得相对了。甚至在Samkhya瑜伽中,当个体沉入自己灵魂深处时,经验的自我也消失了。因此所有神秘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自我要么消失要么成为相对的了。我认为,要理解神秘主义,必须从实践的动机着手,而所有神秘主义的思想或理论部分相对而言都是次要的。这里的动机指的是,从实践上讲,主体自身如何从其自我解脱。听来似乎自相矛盾,难道主体不是自我吗?主体怎能从自我解脱?但神秘主义者指的是,自身从自己的“我要”得到解脱,从自己的愿望束缚中获得自由。并非所有神秘主义都以沉思或冥想的形式表现,然而,在神秘主义以沉思或冥想的形式表现时,神秘主义者就不再关注对具体意愿的负面预期。当神秘主义者将自身从其束缚在某个客体上的愿望解脱时,他将此经验为从“我要”的自我解脱。
所以我倾向于这样定义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就是通过这种从“我要”的自我解脱,达到一种灵魂的平静和情绪上的安宁的实践活动。这样看来,神秘主义也是对于如何对待人生中的厄运的回答。不同于宗教的是,神秘主义没有为了对抗厄运而寻求神的帮助,而是建立一种生活观念,以便在厄运降临时,自己能够不受影响。
神秘主义者要么进入一种类似佛家的空的状态,要么进入一种为存在所充满(摆脱了任何一个特定的客体)的状态,要么进入一种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中为神所充满的状态。如果神秘主义的动机在于弃绝或至少相对化所有具体意愿的对象,那么什么使得人们想要弃绝自己被愿望所束缚的存在状态呢?
我认为,这里的基础概念是灵魂的宁静,也就是那在所有神秘主义流派中都出现过的安然、淡泊的状态,被称为“神秘”的经验。这种状态是人们在实现愿望时无法经历的,因为,愿望总是变幻不定的,而且总要为幸或不幸所左右。这是一种人们在放弃或将所有愿望相对化时体会到的安然,远离所有情绪与所有变化的淡泊,也即人们称为灵魂的宁静的东西。无论结果如何,到来的是幸运还是厄运,这种情绪状态是惟一不为之左右的。
各种神秘主义流派从愿望束缚中得到解脱的动因大相径庭。在佛家与印度教神秘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从苦难中得到解放。按佛的说法,人生就是苦,而如果能做到无欲无求的话,苦也就没有了。人相对于动物的特殊能力就在于能放弃愿望,这样就能得到解脱。我加上一句,人有这种能力是因为人类的这种直言式语言,因此否定愿望成为可能。
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代表埃克哈特大师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的中心观念是与神或存在神秘的合一,然而对他来说放弃自身的愿望也是最基本的。对于人们应如何对待自己的愿望问题,埃克哈特大师著有一本题为《指导论》的小册子。他写道:“灵魂只有在没有为自我所束缚,放弃自我,服从于神的愿望时才是完美的。”所以,良好的愿望就在于放弃自己的愿望。这种立场同宗教的第三层次是一样的。在此,宗教与神秘主义合二为一。
道家的观念比佛家和基督教更复杂,而我将诠释得详尽一些;因为道家既不同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又不同于佛家建立在悲观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对于我们是最容易通达的。我的资料来源是传说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和庄子名下的集子。
在道家思想中也有冥想和沉思,却不似印度教那样据有中心地位。道家的方法并不试图从情绪的自我中解脱出来,而是放松情绪的自我。道家并不似佛家那样,在世界之外,情绪之外寻找灵魂的安宁,而是坚信,生与死、愿望的满足与失望不过是一件事的两面,正如阴与阳。道家也是一种神秘主义,因为道家也相信“一”,道,以及在其中获得自我的自由;然而不同于佛家与印度教的是,道家并不试图在生活的彼岸解决问题。道,或者一,应理解为相对的两面之统一,如庄子所说,“其名为撄宁”(《庄子·大宗师》)。道家思想同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有共同之处,而印度教的观念更接近巴门尼德。
这种观念首先并非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矛盾统一:原初的统一性存在于生与死,上升与下降之间。赫拉克利特残篇所言,向上的道路与向下的道路是同一条,也应首先从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
“万物归一”在道家思想中获得了这样的意义:首先,每个人愿望的满足与失望都同属一体。在次一层的意义上才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产生与消失的结构。“道”在中文里的意思是“道路”,然而在道家的理论中具有特殊含义,即所有从其中产生又从其中消失的东西。第一个含义显然是就实践而言,第二个含义是就理论而言。在中国,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追问道的第一个含义:哪一条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应当怎样生活?这也是儒家的问题,但唯有道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一半理论上的意义,即道是一切的基础。与统一性相联系是道家和其他神秘主义的共同之处,然而道家将统一性视作所有的发生都共有的、结构上的根源。那意识到统一性的智者,并不陷入冥想中,或并不仅仅陷入冥想中,他并没有因此脱离具体的存在状态。所以他并未使自己放弃对普通对象的愿望,而是使自己放松。
放松愿望在不同的层面上产生了后果。一方面,智者接受变化与发生——道家甚至说,人们在下降中上升,在损失中获取。另一方面,放松愿望的后果和我们在分析第三种宗教行为时看到的极其相似,不同点仅在于,道家不说“你的愿望将实现”,因为道家并没有设想神。庄子说,智者可以区分,什么是他能做的,什么是天意,“天”不是神,而是对自己能力之外的力量的表达。天意毋须与我必须做的事一致;因此我做必须要做的事,但不应试图影响天意。我应当接受自己能力的界限,然而这却不意味着,我在“咬紧牙关,默默忍受”,而是,我回到自身的界限中,意识到自己的相对性。
最后,放松愿望还有第三个道家特有的含义,即“无为”。“无为”字面意思是“不要行动”。然而道家的意思不是说,人们不应积极行为,而是,人们不应为要做的事不择手段,尤其不应忽视名誉和声望。老子认为,人们应当回到“赤子”的状态,而庄子则强调回归动物似的主动状态:不要过度意识到自身,即没有人们在英文中所说的那种自我意识,如此回到与动物类似的主动状态。庄子举例说,喝醉的人从马车上摔下来不会受伤,与其说人以酒达到这样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人顺应了天道。这个思想,即疏离自我中心的反思,无忧虑地行动,不考虑他人如何反应,后来被中国佛家思想吸收,再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禅宗思想的重要部分。
无为的思想并不是否定自己的行动,而是回到自己的意愿中。人的意愿与动物或小孩的意愿不同之处在于,这是经过思考的意愿,而这反思是对未来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在他人眼中是否有价值的考虑。正是由于这种反思,人们产生了其他动物不具备的各种焦虑和情绪。人们陷入自身的混乱中:他们自身反思的意愿成为其行动的负担。
道家寻求的灵魂的宁静不再是一般性的对自身情绪的泰然处之,而是淡化那种由于反思和期待他人肯定的焦虑而产生的情绪。道家认为这种情绪是一种错误,而想要回到类似动物的主动状态。思考的反思状态导致一种特殊的人类自我中心状态,其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动物并不关注它的自我,因此谈不上自我中心。然而,道家的观点并不是说,人们确实应当退化到动物或小孩的状态。正相反,人只能在超越了他经过考虑的反思,也就是说,更进一步之后,才能再度接近动物的主动状态:人只能在了悟天道时才能获得从自身的混乱中解放出来的灵魂的宁静。反思使每个人将自己看作中心,看作所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成为对自己而言绝对性的东西;然而,同样正是这种反思的能力,使人能更进一步意识到自己面对世界时的局限性。在人们对道家称为天,或宗教称为神者敞开心灵时,人们说出了:重要的并不是我,而是这个。而对于动物来说,并没有与我们用“重要”这个词表达出来的东西相当者。人的愿望首先将自己作为所有对于他重要的东西的最后参照点,而进一步将其“重要性”相对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对世界敞开心灵,意识到自己渺小若尘,与别的物体并无不同。正如相对化的可能性一样,灵魂的宁静也是人类特有的。只是,道家对于未经反思的动物或小孩的主动性活动的惊叹,使那种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反思才能达到的境界,看起来似乎是退回到反思前的状态。
详细阐述道家思想的原因在于,一来这大概是最易通达的神秘主义形式,二来因为道家及其无为思想在实践的层面上,看问题的方法与我在本文开头试图理论性地加以描述的东西一致。在这个角度下,我认为人的“烦”这种存在现象是反思意愿的后果。然而,道家终究也是一种神秘主义。所有神秘主义都解答人生的意义问题,而这总是对人生的失望这个问题的回应。在每种神秘主义中都能找到第三层次的意愿,而所有的神秘主义都建立在第二层次的反思基础上,这种反思使人能够退出由于对自身愿望的忧虑而产生的自我中心状态。所有神秘主义都认为,赢得人生的意义超越了单个的愿望或目的。神秘主义的一类如印度教,认为这种意义只有在现世的人生之外;而道家认为人生就是如此,在顺其自然中找到了这种意义。两者的目的都是灵魂的宁静。灵魂的宁静作为人最高的至善,作为惟一持续的满足状态,是人类意愿的反思结构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是高层次的反思的结果。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远东文化为这类追寻神秘的道路所主导,而是这种文化存在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文化中,那种认为人生无需这样的观念的想法最好的反证。
最后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宗教和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偶然与在“厄运”这个意义上的不幸是考虑意愿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宗教与神秘主义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甚至在一种宗教之内,也会出现接近我称为第三种宗教行为的神秘主义。如果将我称为第二种宗教行为的东西视作原初意义上的宗教立场,那么在宗教内部,这个问题通过人们投射神性的存在,并向之祈求帮助得到解决,而在神秘主义中则通过一种人生观得到回答。在这种人生观中,人们或是通过忽视失望的可能性,或是通过寻找一条能够整合失望的道路,来赢得内在的宁静。为此神秘主义也必须求助于非同寻常的东西,在人生彼岸的东西,这可能,然而并非必要,投射为神。无论巴门尼德理解的存在,还是佛教的涅槃,或是道家的“道”,都不是神性意义上的东西。或许,那种崇高的观念,即在我们彼岸,使我们感到自己渺小的东西,是宗教和神秘主义所共有的吧。然而,表达这个崇高的概念是很困难的,我已声明自己缺乏正确的词汇。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赞同维特根斯坦,认为崇高超越了人类语言的界限;反而应该认识到,恰恰是人类语言功能的结果,使得人类无法轻易在缺乏崇高观念的情况下理解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