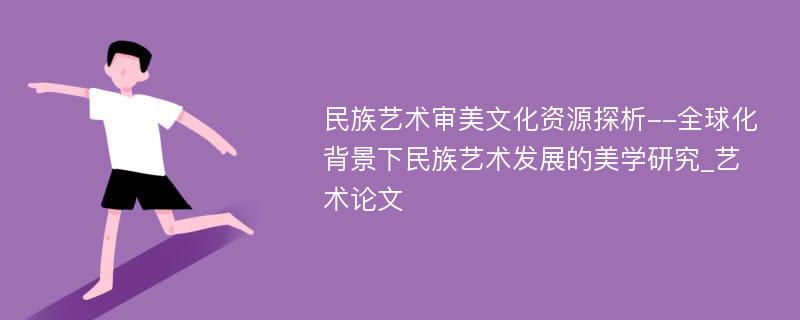
开掘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艺术论文,美学论文,文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存在及意义,已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当然不只是从发展文化产业角度的确认,而且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有关。艺术,历来是文化的突出体现方式与重要组成内容,因而,其文化资源特性及价值,也便愈来愈为人所重视,并不断进行着多视角的发现与多层次的阐释。
每个民族的传统艺术都是一座审美文化资源的富矿。在当代经济、文化呈“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民族艺术而言,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含量及其被开掘的成功与否,则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其生存与发展。就中国的各少数民族艺术而言,在古往的历史进程中,其生成与发展往往是一种自然状态,且与各自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融;而在当代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有的甚至是根本性变化),因而,对其进行包括审美文化资源在内的自觉调适与开掘是必需的和重要的。
所谓自觉开掘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实际上主要是在寻求与激活在当代新的背景之下发展民族艺术的因子和机缘,是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生长点。概而言之,自觉开掘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至少有如下三层意思:其一,是民族艺术在当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二,是在当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以使其在营造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显示自身价值;其三,对于民族艺术资源进行当代新的文化阐释,并使之焕发出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新的美学品质。
一
我们知道,中国每一个少数民族特色鲜明的传统艺术,说到底是该民族在特定环境中生存和生活方式及状态的生动体现,是凝结了群体意识和生存智慧的精神寄寓。譬如,位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曾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个辽远而神奇的地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曲《敕勒歌》的生动写照,更唤起人无尽的遐想。在这令人心驰神往的天地间,飘荡着如同天籁般的歌声——蒙古族长调民歌。它是伴随着草原游牧文明的产生而产生,孕育于草原深处,生发于牧人心田。若诗意地看,它可谓是蓝天上翱翔的雄鹰,是马背上颠簸的传奇,是毡包里醇香的奶酒,是草原上飘散着的乳香……然而,如今游牧这一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已逐渐淡出草原,而现代文明则不同程度地进入到了这块神奇土地的方方面面。据调查了解,到2003年底,人均收入达到3000多元的内蒙古自治区牧民家庭中,每百户拥有电视机近100台、摩托车90多辆,电冰箱、洗衣机、摄像机、电话、 手机等也越来越多地悄然进入牧民家中。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机制的出现,“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207) 这样,昔日“野茫茫”的草原已不再显得遥远,而种种信息的互联沟通已不再存在域限。那么,从古往传到今天的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当下境况如何呢?从多方面的信息得知,由于蒙古族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曾经哺育了无数长调歌手的草原文化环境的变化,如今,在内蒙古草原上民间演唱长调的人越来越少;曾经一度繁荣的东土默特部、科尔沁部、蒙郭勒斤部,长调已基本消失,只有少数老人略有所知。而且,有的长调歌手认为:长调是草原上的歌,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就找不到长调的感觉;坐在沙发上是难以体会到长调的意境的。那么,蒙古族长调的生存与发展前景何在?显然,这个问题既很严肃,又很现实。
以上举出的是个案,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当下所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问题的焦点显而易见,那就是:独具魅力的各少数民族艺术怎样在当代新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得到有效的生存与发展。近年来,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者有之,呼吁采取措施传承、保护者有之,其情之切,可感且亦可知可解。但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即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保护原有的文化艺术遗产而要求停止现代文明进程,当然也不能为保持某种民族艺术的原位性和原生性而让那里的人们再返回到古往的生活之中(事实上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而,我们的探索和努力应当在发展的大前提下进行。
中国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深入研究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作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1) 的论断,成为鲜明的文学发展观的突出体现,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很有积极意义。之后,胡适先生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因为“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3](21) 因此文学也必然随之而变。而且,合规律的变化也正是发展的需要,《易·系辞下》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后人论及文学的发展时,便常以通变理论来阐释之。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也?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即,随着时代而变化是其发展的常情常态。笔者以为,我们所论及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在当今新的时代背景中的进路选择,当然也应该是随着时代而发展。其中,大力开掘其审美文化资源,可谓是实现民族艺术在当代背景下有效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此实践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充分认识与提升民族艺术在民族文化谱系中的内涵与意义,以彰显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与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利用其特有资源而进行适时的新的创造,以有效拓展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焕发新的美学品质。
二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都具有显著的地域特性,而且在以往特定历史条件下,都经历了长时期的相对封闭与自适、自足,以及族群生活与生存中多因素濡染的过程,所以,往往既特色鲜明,又极富自然与人文内涵,当然,也必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差异。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大趋势的到来,现代交通、通讯迅捷发展,原有的地域阻隔被打通,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并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渗透,这对于具有地域特性的少数民族艺术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主要是,一方面其原生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本民族中的审美群体(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需求发生变化——突显现代性和丰富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关系到其生存,又关系到其发展。其机遇在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为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多种可能,因而,一方面可以在交流中丰富自己并获得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种种现代性传播方式与途径大大超越原有域限,走向广阔的世界。因此,地域性的民族艺术要在当代背景下获得良性的、不失主动性的发展,故步自封不可取,只求外在表现形式花样变化无关根本、特别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和增值,而只有深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层面,开掘其内在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继而藉此进行新的、相适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创造,才可能使之不断焕发生机。
据有关资料介绍,2001年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来自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族山歌表演队以其独特的山歌演唱吸引了观众,此后,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报道,“黑衣壮”这一壮族支系逐渐为世人所知。在当地政府和文化界人士的策划与操作下,通过发展旅游业、吸引学术界对当地“传统壮族文化”的关注,其民歌、服饰、建筑艺术得以充分展示。在此过程中,以民歌为代表的黑衣壮传统文化的形象也日益丰富与完善。而且当地人在对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回忆与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既强化了对于自身群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又激发了新的创造热情和审美追求。其间,民歌本身与当地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很大变化。这一事例比较突出地证明了在当代背景下开掘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可行及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内蒙古自治区于2004年举办的首届草原国际文化节以及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许多举措,也都体现出了这方面的特点并有收效。
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历史客观性,它是人们在民族文化及民族艺术的对话与交流中的主题,同时也便自然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石。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任何民族文化的内涵又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静态,它具有时间性,只要时间在流动,这一内涵就在变化与更新之中,它从来就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民族艺术中的审美文化资源也是如此。这便意味着,开掘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本身即是一种深层的发现与交流,需要有开放的视野。有的学者曾主张把握少数民族艺术的美学精神,就应该首先剔除外来的或现代的文化成分,构建出某种纯粹的、原生态的、未受“污染”的民族传统文化,然后再从中归纳整理出被认为是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长久不变的审美文化特征。这是秉承了古典人类学的民族文化观。而事实上只要有可能,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互渗是必然的。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4](426) 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一少数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特质对于“他者”文化而言,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同样适于在交流与互动中发掘并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而且开掘可以是多向度、多层面的。在某种意义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其是否以开放的心态去开发和吸收。
另外,实现对于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开掘与利用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还与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及创造能力相关。因为一切过去时代的文化资源,都有在当下文化语境中重新阐释和创造开掘、利用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资源要想成为生动、鲜活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都必须与当代及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包括文艺审美)相联系。所以,一切传统的文化资源要想在当代发挥作用,都要经历现代转换。其中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或资源,其本身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新的艺术产品,只有经过一定形式的再创造,才能成为具有丰富的当代审美意味的作品。二是虽然艺术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其所依赖的资源可以反复使用,而不是越用越少,但由于其具有拒绝模仿和复制的特性,故尤其需要创新。在此方面中国当代作曲家谭盾的实践可谓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在自己的家乡,用现代的眼睛从湖南古老的巫文化和傩艺术中探索新的意义。他由此而创作的组曲《地图》演出时,波士顿交响乐团设立网站介绍楚文化的根源,短短时间内就有20万人次上网阅读。他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作曲家竞技,在国际大舞台展示风采,又极具有现代精神,但却不是美国现代艺术的模仿,也不是廉价的东方情调,而是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现代性独创。的确,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解析与利用传统的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并以新思想、新形式以及新技术进行新的创造,是大有可为的,近年备受人关注的舞蹈艺术创作《云南映象》也正是这方面的突出体现。
三
在当代背景下进行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开掘、利用与藉此而进行新的创造活动中,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对它的认识和研究。从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到现代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认识与评判是不尽一致的,微妙之别不说,极端性的则是欢呼者有之,诅咒者亦有之。就关于民族艺术而言,便有人指责是现代技术的出现及被广泛运用而毁坏了传统艺术赖以生存的家园,是现代传媒夺走了传统艺术的欣赏者并使之流于浅俗,等等。而我们现在必须明白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演进发展的必然,无论是否愿意,都不可能无视其存在及作用,况且,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至若其利害所向,完全在于运用它的人,以及它被如何运用。汤因比说:一切力量——也包括进步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在伦理上都是中性的。因使用方法的不同,它可以成为善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恶的东西。事实也是如此,譬如,重核裂变被发现之后,很快出现了“原子弹”与“核电站”;人工合成氨技术成功后,同时生产出农业化肥与制造炸弹的炸药;药物合成技术既产生了治病救人的临床药物,又产生了危害生命的海洛因……所以说,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责难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应该首先追问运用这些技术的人,以及其运用目的。诗人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乃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关于技术方面出现的善恶得失应该追问到“目的”的层面。我们现在讨论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媒体与开掘、利用民族传统艺术审美文化资源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当然首先是从积极的、善意的目的出发,但同时也要做客观的认识与分析。
媒介的变化及作用是不可小觑的,这一点已为人类文化发展史所充分证实。现在,艺术与媒体的联系更出现了前所未及的情形。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一书的导言中所讲:“一种媒体文化已然出现,而其中的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身身份的材料等,从而促进日常生活的结构的形成。”[5](29) 与现代媒体相联系的艺术往往可能变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强势力量,在广泛的受众之中产生很大影响,从积极方面看,由于艺术的媒体化调用了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因素和手段,使艺术的影响可以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因如此,现在与现代科技相联系的艺术表现及传播越来越多,包括各少数民族艺术的开掘、展示及传播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从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西部民歌大赛,到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歌舞活动,都借助于高科技的声、光、电等手段来表达与强化其审美效果,艺术的技术化、技术的艺术化二者的共生表现十分显然。如今,连同草原上的“那达慕”活动中的艺术表演也都普遍运用到现代科技手段。笔者曾于2003年秋季与美学界几位朋友到贵州黔东南地区进行文化考察,那里的一个苗寨组织了男女老少近百人,以本民族的传统歌舞表演盛情欢迎我们,在此看来很传统的表演中,歌者却也在使用了现代扩音设备。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各少数民族艺术而言,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表现与传播,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其“原生态”与“原位性”,但其表现力与影响力却会显著增强,扩展受众面,并产生新的审美价值。如前所述,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有着明显的地域特性,即,生成于特定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中,同时也主要在此环境中展示与传承,这样,便于在本民族的稳态化文化结构中保持其原生性与原位性,但同时造成传播与交流上的局限性,而现代科技手段使之得到极大超越。如,一台在彩云之南昆明演出的反映当地少数民族风情的《云南映象》,一次在塞外青城呼和浩特进行的“成吉思汗杯”国际蒙古舞大赛,一届在中国东南边疆南宁举办的国际民歌艺术节,都通过现代视听传媒可以及时将现场表演展现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无数受众面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科技手段和与之相协调的大众文化运作程序,使当代大众可以享受到传统社会中无法获得的丰富的民族艺术及审美文化资源。的确,如今无论我们走到全国各地多么偏僻的地方——包括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而且欣赏港台和海外电视剧或流行歌曲成为备受欢迎的消闲方式之一。有人因此而认为这是民族传统艺术与文化衰落的表现。可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就是在民族地区、乡村牧区的人们通过电视机欣赏域外的时尚艺术之时,现代都市乃至海外的人们也正在现代传媒前观赏蒙古舞表演,或聆听壮族歌谣,亦或品鉴正在云南古镇丽江演奏着的纳西古乐等。现代媒介的传播可以是多纬度和多方向的,可以形成交流与互通之便。“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为不同族群提供了一套交流的‘元语言’或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才得以呈现自身。”[6](5) 当然, 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与在大众文化平台上的表现,必然会导致民族艺术本身的某些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失落或消亡,而只能是对于其审美文化资源的适时性开掘和创造性利用,这可以使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既获得新的机缘,又为更多的人所领受。
四
在当代背景下开掘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自然会关系到文化产业。这中间既有一定必然性,也有一定必要性。关于必然性,笔者以为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受当代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其二,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主导传媒形式变化而引起的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变化在民族艺术生存和发展上的体现。关于必要性,也应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使民族艺术置于大众文化的平台而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并产生一定影响,则需形成一定规模并有持续性;二是需要有适于自身发展的保障机制,为此,开掘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并使之形成产业化机制则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当然必须明确,我们这里所谈的产业问题,其主旨依然是在民族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上,而并非要讨论艺术在经济意义上的利益得失。
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艺术从其生成到传承表现,更主要的体现为一种自然状态,并是日常生产、生活与生存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具有自在性与自适性。但这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环境的原生稳态性。可是,如前所述,现在从大背景到小环境都在发生着很大变化,特别是从自然到人文严格的传统意义上的“原生态”已留存甚少,因此,其民族艺术便很难再以传统的“自然状态”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若仍依赖那种“自然状态”,很可能会自生自灭),而是需要有自觉的意识和作为,其中当然包括开掘、创新,为其注入新的生机,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为此,就需要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组织、营造,其中包括通过产业性的策划和实施,使之形成新的规模,拓展新的传播(艺术被消费)领域。这种实践,一方面可以在各民族地区本土营造出适于本民族文化艺术生存和发展的、具有新的“生态”意义的环境与气候,以吸引世人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现代媒介的强势,成体系、成规模地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
笔者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于本世纪初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方略,其中,大力开掘蒙古族艺术的文化资源,全面开拓文化市场,已基本形成了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良性态势。即,一方面,对于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开掘和利用大大丰富了文化市场,并形成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文化市场的形成,又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艺术在新的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并在更大范围获得新的价值确认。
另外,笔者曾两次游历云南丽江并两次观赏纳西古乐演出,其间,对其步入市场与自身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初浅的调研。大研镇是云南丽江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全镇范围内有五个民间艺术团,没有正式人事编制、不拿国家的工资,全部从事商业演出,走市场化的道路。演出内容多数为洞经音乐、白沙细乐和纳西民族歌舞。应该说,这些演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丽江传统音乐在当今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里的“大研古乐会”和“东巴宫古乐会”隔街相对,是丽江地区水平最高、阵容最强,同时也是声誉远播的两家演出团体,这里每晚演出几乎都座无虚席(主要是外地游人)。在观赏者看来,这是一台风格浓郁而又地道的纳西族音乐会,很有民族文化内涵。有游人说:“到丽江不听纳西古乐等于白来。”可见,走向市场的纳西古乐会已经成为丽江的一道具有标志性的风景,也是这里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从其生成及原初形态看,各少数民族艺术原本就是与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的。回溯以往,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也无论是在草原还是在水乡,许多少数民族的歌舞等艺术都是伴随着民族民间宗教、节庆、商贸活动而存在的。而且多方面的实践证明,过去的这样自然而然的结合,对于艺术的交流与提升、对于商贸体系的形成等,都产生过积极作用。这也表明,民族艺术与产业结合是有其独特基础或曰基因的。当然,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已完全不同于以往,因而不能照搬古往那朴素的模式,但这对于积极开掘民族艺术内在的文化资源而使其在当代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却是很有启迪性的。可我们也了解到当下有些人确有一种担忧,即忧虑民族艺术进入到文化产业的运作,会影响甚至毁坏传统的经典艺术和具有特色的新的经典性创造,或使那些无法进行市场化经营的民族艺术种类和非盈利性的民族艺术活动遭受灭顶之灾。应该说,这主要还是站在原有的计划经济角度的思考与认识。这里的关键是,当代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民族艺术保护也必须以与市场相适应的思路与方式来建构。当代新的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将艺术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种,在建立市场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互补的民族艺术保护方式,使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有益于民族艺术发展及文化产业建设的合理架构。另外,在当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它高度依赖文化的创新意识,所以,民族艺术为文化产业所关注与开掘,有益于其不断产生新意与新值。不过,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即,要坚决摒弃庸俗化和唯利是图,而始终保持并突出民族文化精神的鲜活性。
收稿日期:2005—03—30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全球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