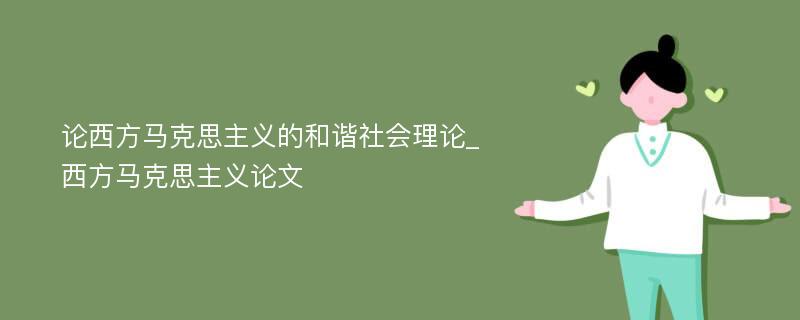
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现代化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西方社会和西方人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全面和谐发展,相反,西方社会和西方人却越来越走向了片面畸形发展。对于西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重从社会对人的总体统治和社会发展与人的价值下降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因此而得到了自由和全面发展,恰恰相反,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从过去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进一步发展为包括政治、经济和精神在内的总体统治,西方人变得更加不自由,西方人的发展因此更加畸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分析尤有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揭示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背离这一现实,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人的价值的上升和价值的实现,相反,还使得人的价值下降和人的破碎化。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人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物化带来的后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物化导致人的破碎化和原子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日益机械化、专业化和合理化,人的创造性的劳动不得不服从机器生产体系运行的规律,破碎化为机械的操作活动,工人也不再参与劳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从而丧失了和产品的有机联系。人的破碎化也导致了人的原子化,人丧失了生产过程的主体地位,并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原子、一个零件。其次,物化现象掩盖了现象和本质的区别,使人们只能拘泥于眼前的事物,人的行为仅仅只在于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规律,看到的只能是历史运动中的个别、偶然的规律,人们丧失了对整体景象把握的能力,更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而丧失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最后,物化现象导致了物化意识的盛行。所谓物化意识,在卢卡奇那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专门化需要的各门具体实证科学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些具体实证科学之所以是物化意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从而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认识。其二是指人们把机械化和操作化的异化工作方式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伦理,这表明物化意识已经侵入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二
西方社会现代化必然带来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文化的发展是否和谐,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所探讨的另一重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着重从如下三个方面揭示西方文化价值的危机。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析了西方哲学从辨证理性转化为实证理性的历程以及实证理性的本质。在他们看来,西方哲学思想传统是包含着肯定性的实证思维和否定性的辨证思维双重向度的,这种双重向度体现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矛盾。辨证矛盾把“是”和“应该”之间的紧张状态理解为一种本体论条件,使得既定现实本身表现为虚假的和否定的。建立在这种辩证逻辑基础上的哲学形而上学尽管包含着经验无法证实的所谓“虚构和幻想”,但是它总是力图区分真实和虚幻、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区别,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强调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联系,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向度和超越精神。与此相反,形式逻辑则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关注的只是抽去其对象内容的形式规律,其结果必然会忽视或取消本质和现象的冲突,导致同一原则和矛盾原则相分离,使哲学走向了抽象化、数学化和实证化,割裂了哲学和价值之间内在关联,从而放弃了哲学的批判性思维,起着维护现实的肯定功能。因为实证理性借口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把哲学对意义的追求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幻想,并把凡是不合计算和使用规则的东西都看作是可疑的。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分析大众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揭示了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文化和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针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产品出现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和复制的特点,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工业论”,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文化的异化。第一,他们指认由文化工业所创造出的文化产品同人处在一种外在的疏离关系中。在他们看来,文化的本义在于培育和提升人性,但是由文化工业所创造出的文化产品不过是特殊的商品,它关注的并非是如何实现人的价值,而是关注如何获得利润,文化已经沦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计算放在首位”。第二,他们指认了文化本身的异化和文化产品消费的异化,这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文化工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分散和个体性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大规模的流水线和机械复制的方式,这必然会抹杀文化的一切个性。文化的异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产品消费的异化。文化工业虽然从表面上看制造了各种富有个性的明星的形象,但实际上这些明星的所谓个性不过是一种伪个性,因为他们都不过是为了获得利润被非人化,并服从商品规律的具有完全内在一致性质的商品。第三,文化工业不仅服从商品运行的规律,而且还具有控制和操纵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职能,其方式是通过它向人们所提供的整齐划一和无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来实现的。这些无深度的、平面化的文化产品虽然具有使人们在娱乐中忘却一切痛苦和忧伤的功能,但它同时也使人们丢弃了一切思想和反抗社会现实的能力。“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欺骗。这种娱乐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固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正是由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文化的异化,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同一,人完全被社会总体所吞食。
三
西方现代化发展不仅造成了人和社会、人和人关系的不和谐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和谐,同时也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体现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哲学世界观、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等方面揭示了人和自然关系不和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他们指出,近代启蒙理性的宗旨是将人从神话的压迫中摆脱出来成为主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人,其关键在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这里所讲的知识并非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概念或观念,而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技术,由此知识就被归结为技术。而启蒙运动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得以确立,人们深信,依靠科学技术就可以控制和主宰自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把自然看作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异化。不仅如此,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又是同一历史过程,因为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必然会对自然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世界。但是一方面自然界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的非理性欲望也会受到自然的限制,一当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则必然会导致自然的反抗,体现为生态危机的爆发。
四
那么,如何才能使西方社会发展走向和谐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革与人的微观心理变革两个向度入手探讨这一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正是由于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社会发展的后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社会发展不仅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一致,而且人的片面畸形发展、文化和自然的异化在资本的奴役下具有必然性,因此,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是首先进行宏观的社会结构变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两个方面论述了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变革。
从社会制度的变革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集权社会,个人都被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工业体系所操纵而变成丧失个性、独立人格的机器人,因此这两种社会都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其社会制度的性质看,是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它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抗议。……是对人剥削人的抗议,是对人以牺牲今天的和尤其是后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滥用自然、浪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抗议。……非异化的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这种非异化的人并不‘统治’自然,而是跟自然合而为一,是跟对象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以致对象对于他来说成为生命”。而这样的社会也必须实现管理方式的变革,从过去的官僚式管理转向民主制管理。具体而言,在生产领域应该让工人参与生产的管理和决策,确立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消除异化劳动;在消费领域既应该满足人们基本的和必要的需要,同时又应该从被社会和广告所操纵的需要和消费中摆脱出来,避免异化和非人的消费;在文化伦理价值领域应该用以“爱”为中心的和谐伦理代替市场伦理,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植根于友爱和团结。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人之所以处于片面和畸形发展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人的心灵世界已经被当代西方社会所支配和控制,导致了人的自主意识的丧失,人的一切意识和情感都是由外部世界所强加和给予的。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它必然会造成社会和人的同一以及人的人格分裂,自然也就谈不上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因此,实现人的微观心理革命,使西方人从被支配和被奴役状态下摆脱出来,培育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总的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与人的不和谐状态、文化的不和谐状态以及人和自然的不和谐状态,并且从社会制度、哲学世界观、文化伦理价值观等方面分析了这些不和谐状态产生的根源,提出了通过社会结构和人的微观心理的双重变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其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取向看,它强调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并且要求社会发展始终应该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上;从其和谐社会理论的具体内容看,它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性和反生态性质、科学技术理性的合理性问题、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问题,提出了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人的微观心理变革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现实、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实践精神;从其探索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看,虽然他们也注意到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性,但总的看他们更加注重抽象的文化价值批判和伦理批判,因而他们的理论带有抽象的伦理说教和乌托邦的缺陷。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建构和谐社会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具体体现在:(1)建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西方社会的发展之所以不和谐,一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在于其发展不是立足于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这种发展方向的偏离,直接导致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背离,也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以及生态问题的产生。科学的发展观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同时,科学发展观还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和谐正体现在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不平衡,这样的发展只能导致片面、畸形的发展;(2)建构和谐社会离不开制度的正义性。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和谐根本原因在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它维护的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而不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也存在若干缺陷,导致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如何使发展的成果为广大劳动者共同享受,这是我们应当研究和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3)建构和谐社会离不开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正确的科技观、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幸福观和自然观。如何正确处理价值理性和科学技术理性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非理性消费观、幸福观,如何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建构和谐社会的和谐伦理,这也是当前我们应当注重解决的重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上述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是我们应该加以认真消化吸收的宝贵理论财富和思想资源。
摘自《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5.6.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