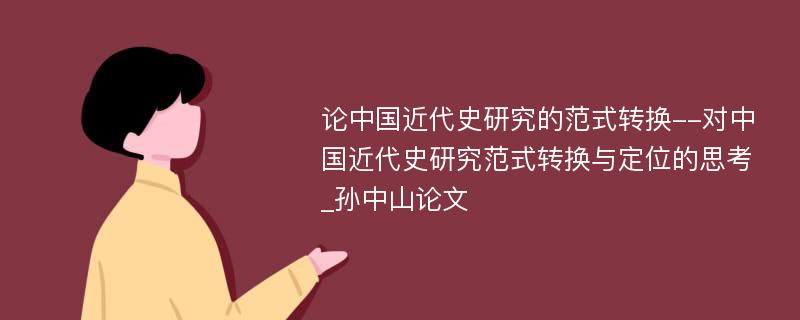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笔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与取向转换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现代史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在我看来,这种挑战和机遇主要归因于中国终将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文化必将走向“充分的世界化”(胡适语)。富有学术理性的史学工作者,应当结合我国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误区,深刻反思既定的史学研究规范,对中国史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认真的、深入的分析。
这里,我想从思维方式、认识取向入手,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谈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随着“冷战”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史研究见长的黄宗智在美国汉学界独树一帜,提出了“反思研究规范”的理性命题。他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1]。我很赞赏黄宗智的这个见解。大洋两岸的学人确实有必要思索一下长期以来双方所信守的、约束自我认识能力的“规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自觉挣脱它的束缚。就我的理解,黄宗智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就在于告诫研究者: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同时,必须转变认识取向,摒弃先入之见,构建悖论思维,去探求和发现那些长期以来所根本“不想”的东西。
就我个人的学术理路而言,我从事美国汉学的研究已多年,如果说在研究中有什么反思性的感悟的话,那就是要从跨文化的视野中,挣脱“规范认识”的束缚,努力寻找我们所根本“不想”的东西,从而弥补我们思维中的缺失,更真实、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
其实,反思是相互的,美国学者也在反思。因为他们同样受到特定的“规范认识”的束缚。提出“亚洲农业社会范型理论”的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就认为,在美国,很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是美国中国研究存在的最大的弊端。针对于此,保罗·柯文(Paul A.Cohen)曾经提出了中国研究的基本取向——“中国中心观”。但是,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很多美国学者那里,“西方的历史起点又是英国,因而往往是把英国与中国相对应,将研究英国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套用到中国,用以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可想而知了,那将是一个‘英国式的中国’”[2]。利特尔的这番话值得中国学者深思,他抨击的这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不也正是中国学者所始终加以遵循的吗?如果仍然恪守这一规范,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根本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与认识取向的转换相联系,我们应当提倡史学研究的跨学科化,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手段,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我在分析美国汉学研究的基本性质时曾经指出了这一点。这里,我想结合“文化大革命”研究来做进一步个案分析。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敏感、复杂而困难的研究课题。目前,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政治史范畴,特别是党的历史范畴。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放在更广阔的领域中间去研究,宁可失之于宽,不可失之于狭。6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20周年之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与社会现代化》。表面看来,“文化大革命”与“社会现代化”似乎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概念,实际则不然,两者确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在文章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震撼全球、激荡中国的‘革命’仍需要做出深入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思考。特别是应当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来认真梳理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还提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总结需要有新的认识角度和取向。在我看来,应该审视当时‘局外人’(特指外国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分析‘文化大革命’所试图提出、解决的问题,探究这些问题的取向及其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过去很少触及的领域。”[3]多年过去了,我所提出的这些取向,对于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仍有着不容忽视的方法论意义。我的初衷在于:只有真正超越所谓“权力斗争”的解读框架的窠臼,才能更理性、更全面地认识“文化大革命”。恰恰在这里,中外学者又同样受到“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的约束,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了令人费解的“默契”。
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研究也就是对人的研究。在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也同样涉及认识取向的转换问题。这里,我仅想结合对《建国方略》的再认识,谈谈孙中山研究,因为我们对他有诸多的误读和误解。
应该说,我是带着一种重新解读的取向来理解《建国方略》的。兴趣所至,我很想客观地破解一下孙中山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的内在特点。因为在以往对孙中山的研究(特别是思想研究)中,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过深,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附加的条件亦多,以至于研究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他们往往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规范孙中山的思想,寻找他的思想“误区”,在肯定中加以否定,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以及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已经成为一种“规范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是很看重他的《建国方略》的,将其视为自己对辛亥革命的反思的结果(在既定的思维定势之下,人们很难看得出这一点)。这一点在他的“自序”中有十分清楚的表白。在孙中山眼中,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那么,其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之说。
应该说,对孙中山在认识论问题上的这种看法,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理解有误。我们甚至认为,孙中山孤立地用难易来识别知与行的关系没有太大意义(也有人认为是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行的基础作用、认识的来源,以及真理的标准,等等。通常的说法就是,认识绝不能离开实践,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在这里,行是难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一认识论主张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尤其是突出强调了科学、理论、逻辑推理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实践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我们经常讲理论联系实际,但似乎着重点是放在实际上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是基础。孙中山就专门从最实际的生活范例入手,“以饮食为证”(中国有饮食文化闻名于世,但却没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以金钱为证”(中国需要经济学、金融学)、“以作文为证”(虽文字历史悠久,但也更需要文法、逻辑学)来说明科学、理论和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孙中山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此外,孙中山还一一提到,中国也十分需要建筑之学、工程之学、电学、化学,需要各种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等等。
其实,我们无须讳言,科学、理论、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之中缺少积累的东西。这一关键的缺失,确被孙中山抓准了。这正是孙中山的伟大过人之处。
孙中山还从反对封建政治统治的角度抨击了“知易行难”说。在他看来,封建政治的愚民政策,孔子的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好反证了“知难行易”。
与此相联系,我们还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孙中山是把解决认识论问题作为建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其意义非同寻常(我们经常讲,思想路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其中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他特殊的考虑而已)。这就是他在《建国方略》中首先涉及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问题,而后他才谈“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社会建设”(民权初步)。“心理建设”被孙中山看作“非常之建设”,因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孙中山提出:不仅要有“破坏的革命”,还要有“建设的革命”。就我的理解,孙中山提出的“心理建设”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孙中山的文化思想的缩影。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孙中山的思维方式也是独特的,他的文化思想正是其思维方式的真实反映。为了佐证“知难行易”,孙中山特别举出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例子,用以证明他和杜威是相通的。
在《建国方略》第一版准备付梓之际,恰好杜威博士抵沪。孙中山便请其质证自己的观点。杜威对此回答说:“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由此,孙中山感叹道:“此足见行易知难,欧美已成为常识矣。”中国的落伍,由此可见一斑。
收稿日期:2002-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