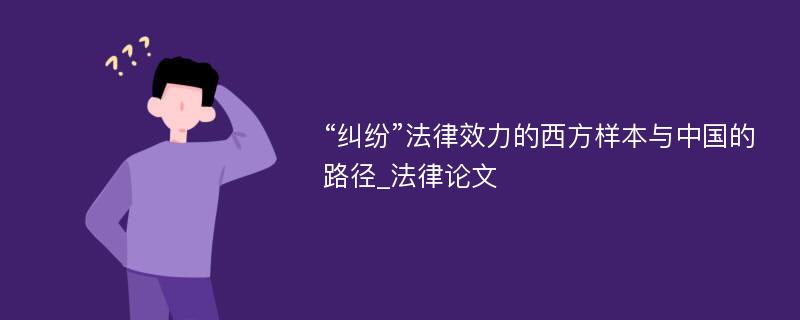
“争点”法律效力的西方样本与中国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样本论文,中国论文,法律效力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既判力的存在,使得法院对于诉讼标的的判断获得程序上的稳定性。但是,判决中对诉讼标的判断部分,即原告获得的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的判断,主要记载于判决书的主文之中。判决书主文之外的,法院对于争议事实(即争点)的认定由于不属于判决书主文,因此不在既判力的覆盖的范围内。从各国立法的情况看,事实争点的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间接禁反言或争点禁反言效力,赋予争点以确定的法律效力,不允许后诉当事人提出不同的主张;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公文书”的证明力,即将前判对于争点的判断作为效力较高的证据使用,但是允许当事人对前判事实认定的结论提出异议。
一、间接禁反言:以“程序公正”为核心的英美法模式
按照当代英美法理论与判例,当某一争点或事实已经被实际审理并被终局性的或有效的判决所确定,且该争点对于判决而言是必要的,该争点在接下来双方的诉讼中,具有终局性效力,无论是否基于同样的诉求。①英美法系的间接禁反言规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以“程序公正”而非“真实性”为基础。法官在考虑是否应该适用该原则阻止当事人对某一问题的再次争议时,不会考虑对该事实争点的第一次认定是否正确。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前诉对某一特定争点的认定是否经过充分的争议以及对前诉整个诉讼的决定而言,该争点是否必要。②
2.在“争点”遮断力作用的程度上,赋予前诉争点判断确定的遮断效果。只要符合适用条件,前诉案件中法院对某一事实的认定将对后诉法院产生确定的遮断效果。当事人不能再行争议。
3.在效力范围上,从“主体”与“事实”两个维度定义“争点”排除的范围,并通过判例极力扩大其作用力。
4.法官在间接禁反言的适用方面具有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争点禁反言适用要件中的“决定性事实”、“充分的诉讼机会”等极具弹性的概念,赋予了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加以解释的空间。③
二、公文书的证明力:以“真实性”为核心的大陆法模式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规定,判决中,只有对于以诉或反诉而提起的请求所为的裁判,有确定力。该法第325条规定,确定判决的效力,利与不利,及于当事人、在诉讼系属发生后当事人的继承人以及作为当事人或其继承人的间接占有人而占有系争物的人。④由此可见,按照德国立法对判决既判力问题的规定。既判力只拘束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非当事人不受既判力的拘束。同时,既判力仅及于争议的对象,当事人未提交裁判的请求也不会受到既判力的影响。由于德国法明确区分判决主文和事实与法律部分。前诉判决的效力仅及于裁判的主文,对于事实认定的部分,则不认为具有遮断效果。也就是说“只有法院确认了的法律后果才发生既判力”。⑤在德国诉讼理论上,如果某文书直接包含了应被证明的事件的过程(例如,判决、行政文书、遗嘱),该文书即属于要件文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7条规定,由官署制作的,载有公务上的命令、处分或裁判的公文书,对于其中的内容,提供完全的证明。⑥对于要件文书,法律推定其为真实,但是允许当事人提出相反的证据推翻此推定。法国的情况与德国相似,判决的既判力原则被限定于判决书主文中,判决的理由部分没有既判力。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争点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从证据法角度理解先前判决事实认定部分的法律效力。赋予“争点”以公文书的证明力。但是,允许当事人用相反的证据证明先前判决对于“争点”的判断是错误的。
2.在效力强度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虽然普遍赋予了前判事实认定以公文书的证明力,但是该证明效果可能由于当事人的反证而被削弱甚至推翻。
3.在“争点”证明力作用的范围上,以“事实”为中心圈定证明力的范围。证明力不可能波及前判中未出现的事实。证明力不可能波及前判中未出现的事实。
4.在判断前诉事实认定结论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方面,法官的裁量空间有限。立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的裁判属于公文书,提供“完全的证明”,对于法官而言,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该事实认定的结论是否被记载于判决书中。
三、不同的争点效力规则构建的依据
1.扩大争点效力范围或赋予其确定拘束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节约司法资源。英美法系各国通过间接禁反言规则,竭力扩大前判事实认定结论的效力范围,使“争点”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拘束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处于稳定状态。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在此问题上则显得更为谨慎,甚至保守,仅将前判的事实认定作为证据使用,而没有赋予其确定的拘束力。这种差异的产生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即赋予争点以确定的约束力在英美法系国家可以节约更多的司法资源,因此对他们而言是更为经济的。然而对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同样的作法却并不能产生同样的收益。
2.事实被探究和审理的深度与范围。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开示程序使得当事人得以充分收集证据,也使审理者获得充分接触证据的机会。事实被探究和审理的深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无法比拟的。在英美法系国家,“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理念在司法制度中得到了严格的贯彻。这些国家几乎所有的诉讼制度都致力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一次诉讼程序尽可能合并更多的请求和事项。体现为在对待争点效力的问题上,允许非诉讼当事人寻求排除先前争点的利益。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分别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被允许的。
3.利用先前诉讼资料的可能性及便利性。在英美法系国家,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使得法官在利用先前诉讼资料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而言,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使得他们可以取得前判中的内容,包括前判的决定以及记录,并将它们用作新案件中的证据。
4.重新审理产生不一致判决的可能性。英美法系国家由陪审团单独负责对事实的认定。陪审团的成员来源广泛,是同质化程度较低的审判集体。因此,可以推知,即便面对同样的证据,不同的陪审团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事实认定。但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集体却是由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职业法官组成。重新审理产生不同的事实认定结果的风险大大地降低。同时也不必担心职业法官不能恰当地对待先前判决事实认定的结果。
综上,两大法系在争点的法律效力的问题上,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规则,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因素决定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两大法系国家不同的争点效力理论在适用的效果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种不同的争点效力模式也没有优劣之分,总体而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四、我国的争点效力规则
1.基本模式的选择
英美法系国家以“程序公正”为基础的间接禁反言规则并不适合我国国情,移植英美法系国家的争点效力理论在我国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而大陆法系国家对待争点效力的证据法视角则更适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理由如下:移植间接禁反言规则在我国并不能起到大幅度地提升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的作用;“公文书”的证明力有利于弥补事实审理不充分的不足;与“禁反言”规则相比,“公文书”的证明力更易理解和把握,也更具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传闻排除规则的缺失进一步削弱了移植“争点禁反言”规则的必要性;赋予前判事实认定以何种法律效力与维护司法权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2.具体规则的设计
(1)对不同裁判文书中“争点”的证据效力做出区分,不应一概地赋予“免于证明”的法律效力。建议对不同的诉讼程序产生的事实认定结论分别赋予“绝对免证”的事实、“相对免证”的事实和“公文书”的证明力三种法律效力。“绝对免证”的先前判决主要指刑事有罪判决,“相对免证”的效力主要适用于行政诉讼判决,由于其事实认定的结论涉及对国家行政权运行合法性的审查,因此确保裁判结果的稳定性具有非常的法律意义,所以行政裁判中事实认定的结论也应被视为免证事实,主张事实存在的当事人不承担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是应当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充分的证据推翻事实认定的结论;“公文书”的证明力主要适用于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结论。“公文书”的证明力与“相对免证”事实的区别在于,“免证事实”较之于“公文书”的证明力更加稳定,否定方应当承担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本证责任,而非反证责任。具有公文书的证明力意味着对于文书内容真实性的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仍由提出公文书的一方负担。但是,由于公文书具有更高的证明力,举证方的证明负担较轻。对于民事诉讼的判决,无论产生于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无论是否经过二审程序,无论基于对席审理或缺席审理,均具有公文书的证明力。
(2)法院在不具有事实“认定”功能的程序中所做的裁判记录的事实,不具有公文书的证明力。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程序、财产保全程序、先于执行程序即不具有事实“认定”的功能。产生于此类程序的法律文书对某些事实的记载很可能仅建立在当事人合意或妥协的基础上或者未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法院严格审查的证据的基础上,事实的结论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因此不得认为具有公文书的证明力。
(3)除了对主要事实的认定,前判中对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应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赋予不同的效力。如果前诉与后诉基于相同的主要事实,前诉法院对于用于认定该事实的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具有公文书的证明力。如果前诉与后诉具有不同的主要事实,仅在某些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和证据方面有重合之处,此时不宜认为前诉判决对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也具有公文书的证明力,理由是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在诉讼中的作用类似于证据,在主要事实不同的情况下,赋予前诉法院对个别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以公文书的证明力,无异于剥夺了后诉法院对证据进行评价的权利,这样做是违反自由心证的基本规律的。
(4)在法律发生变化,证据发生变化,证明标准发生变化,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发生变化或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等原因,可能影响事实认定的结果时,应当允许后诉法院不受前诉判决结论的拘束,做出不同的事实认定。同时在出现上述情形时,无需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后诉法院应当在后诉案件证据的基础上重新认定事实。
①The American Law of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 Second,Judgments 2d(Volume 1I),American Law of Institute Publisher,1982,249.
②Jack H.Friedenthal,Mary Kay Kane,Arthur R.Miller,《民事诉讼法》,夏登峻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页。
③Meiring de Villiers,Technological Risk and Issue Preclusion:A Legal and Policy Critique,9 Cornell J.L.& Pub.Pol'y 523(2000).
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谢怀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⑤[德]汉斯—约阿西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26页。
⑥前引(17),谢怀栻译书,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