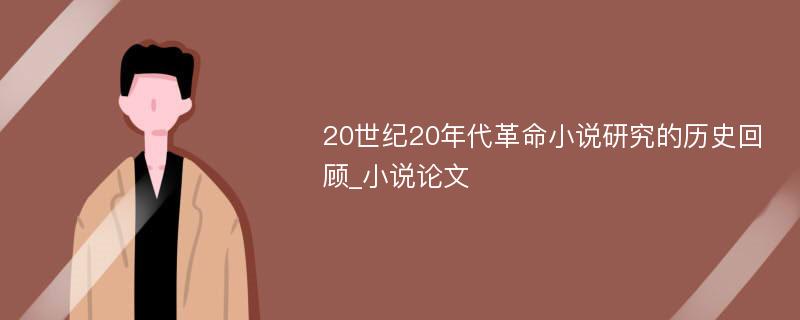
20年代革命小说研究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历史回顾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20~30年代阶段,革命小说的艺术价值遭到否定
在《太阳月刊》刚出世的时候,茅盾就撰文表示不满,认为其中作者没有“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化为文艺作品。”[1]1928年7月,他在东京又批评革命小说“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2]1932年,他为《地泉》重版作序,再次指出《地泉》代表革命小说的一般倾向,即“‘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和“‘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3]茅盾坚持不懈地同革命小说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作斗争,虽确实揭示出革命小说中存在的缺陷,但他指责革命小说缺少“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3]却有欠公允。众所周知,蒋光慈的小说曾风靡一时,不断被重版、盗版,洪灵菲的《流亡》出版后也打开了销路。另外,茅盾的批评也显得 过于责备求全,蒋光慈、钱杏邨等都认为“没有一个阶级的文学,不是经过‘ 幼稚’的一个阶段的”。[4]
左联时期,革命文学界也开始对革命小说进行批判。1932年,瞿秋白等左翼人士借《地泉》重版之机,对革命小说的“浪漫谛克”风格进行清算,明确指出“普洛的先进的艺术家不走浪漫谛克的路线”。[5]这明显受到苏联“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法”的影响。左联批评家教条主义地接受国际左翼文学理论,不仅否定革命小说的价值,而且对革命小说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在革命小说刚兴起的20年代,茅盾、鲁迅等就认为它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手段幼稚,而瞿秋白等左联理论家也自我批判。这些批评虽然含有“门户之见”及外来文学的影响,却对革命小说的发展和研究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它们被过早、轻率地贴上“浪漫谛克”的艺术标签。
二 50年代阶段,基本继承20~30年代的认识观念,但研究视角发生鲜明变 化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预示着50年代革命小说研究的特征。他认为“浪漫谛克”倾向和“革命与恋爱”公式,“虽然在当时曾引起一些青年的爱好,但经得起时代磨练的作品就很少。”[6](第243页)但他又指出革命小说“反映了历史性的斗争,是有意义的。”[6](第240页)这句简短的话,隐含着革命小说研究另一价值标准的萌芽,即以反映党的革命历史作为革命小说艺术价值的批评标准。在50年代中后期,这一价值标准被有些研究者推到显著的位置,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提出要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上认识新文学,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都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史作为新文学的首要批评标准。
这种新标准,构成对20~30年代审美批评的相对否定,形成50年代研究的特征,既树 立政治标准的批评视角但也相对坚守审美标准,并造成革命小说价值评判的矛盾冲突。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把这种情况鲜明表现出来。他一方面从政治立场出发, 认为20~30年代对蒋光慈的批评“有好多地方是不公允的”,[7]另方面他又认为蒋光 慈的小说艺术上粗糙。这种矛盾是审美和政治双重标准导致的。
50年代末,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斗争的日趋激进,王瑶、张毕来、李何林等新文学史家确立的政治批评标准,被一些研究者推向极端并成为批评的“唯一”标准。北京大学1956级鲁迅文学社撰写的论文《蒋光慈的小说》(注:《文学评论》1960年2期)就明 确指出,蒋光慈跟唯美派资产阶级作家根本不同,他自觉把文学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 他的全部创作都体现着服务政治的态度;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学者自20年代以来一直贬 低蒋光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无产阶级的早期作家,而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者攻击他就证明他的正确。在这种政治唯一的批评视角下,该文反驳了蒋光慈 小说“人物形象不丰满”、“概念化的倾向严重”等论调,认为它不符合事实、是一种 恶意的夸大,蒋光慈的一些作品艺术上虽有些粗糙但却是作者为政治服务的激情产物, 因此“必须充分肯定”蒋光慈小说的价值。这样,50年代末就逐渐把政治价值作为革命 小说批评的唯一标准。
三 80年代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统一的范式取代了政治批评, 革命小说研究逐渐走向客观、深入和开阔
80年代,由于受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热潮的影响,人们开始从流派角度审视革命小说,将其放在现代文学史的背景上研究,并摈弃50年代左倾理论、确立社会历史与审美批评相结合的范式,革命小说及其流派的思想、艺术成就得到“更为科学的说明,重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8]这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研究者把它放在无产阶级文学初创期和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价值阐释,既不“过低估计它的历史功绩”也“不致讳言它的严重失误和明显的缺点”,[9]取得不少较为客观、公正的成果。
赵园的《大革命后小说关于知识青年“个人与革命”关系的思考及新人形象的诞生》,(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4年2期)对大革命后小说“恋爱与革命”的流行主题重新进行反思,认为它不是所谓的“虚伪”题材,而是时代生活与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变更中的产物,“应当实事求是地被看作知识者、小说家寻求个人与革命之间的联系的一个认识阶段上必然发生的现象,联系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史来评价和认识”。该文还从现代文学题材演变的角度,论述这种小说冲突出现的文学史原因,认为它象征着历史意识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进步,也是新文学艺术手段与表现技巧“积习”的流露,但作者借此却“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徘徊于知识分子贯常的生活轨道和革命斗争对于参加者的严苛要求之间,沉醉于浪漫谛克的爱情生活,同时又受到对于事业的责任感、义务感的鞭策的游移彷徨中的革命者的形象”。在肯定“恋爱与革命”出现与流行的社会与文学的必然性、现实性的同时,赵园还深入剖析它的流弊及其根源,认为它所表现的革命转向“与具体的日常的生活过程割裂了,与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脱节了”,指出30年代批评所蕴涵的错误在于“以为革命者必须尽善尽美的见解”。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以“浪漫谛克”为研究对象,明确表示30年代左联的批评“很不公道”, 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历史主义造成的”,其中也含有“‘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尚未褪 尽的门户之见和偏激情绪”。他们既肯定“浪漫谛克”思想上和文学史的意义,又分析 它“为什么会招致人们相当普遍的非议”的原因,认为这类小说“确有它幼稚、粗糙的 一面”。
倪婷婷的论文《现代文学史上个性解放主题的淡化》,(注:《文学评论》1987年3期)则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题的角度,重新探讨“革命与恋爱”的文学价值与意义,认为它是“五四”文学主题的“一个补充和开拓”,但它把个性主题引入阶级解放主题并显示出进步性的同时,却忽视“这一主题下也应具有的个性问题”而表现出“致命性的流弊”,革命战胜恋爱的艺术方式不仅“幼稚、粗暴、简单化”,而且形成革命工作与个性意识“不正常的局面”。在《‘光赤式的陷阱’——革命 + 恋爱》(注:《江海学刊》1988年1期)这篇文章中,她又集中分析“革命 + 恋爱”“为什么在大革命以后出现”和它的“得失处何在”等问题,认为革命加恋爱的冲突既来自革命者对革命幼稚、偏颇理解和普遍浪漫谛克精神气质的主观因素,又来自革命本身的特点和缺陷给革命者带来的过分的献身要求等客观因素,其致命弱点不在于公式化、概念化,而在于对革命加恋爱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即将二者置于“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的两端”。
这些研究都以革命小说的“革命 + 恋爱”为对象,并把它放在现代文学史和大革命时代的语境内,企图为它的产生找到社会现实的根据或历史必然性,从而充分肯定它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即它“提供了一幅大革命时代知识者投身革命前后的时代图画”,成为“了解当时革命者以及革命作家的某些真实思想状况”[10]的历史镜像。
1986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审美批评的范式,分析了革命小说“粗率和强烈”的风格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导致的“以力伤美的艺术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他运用比较文学的批评方法,论述革命小说浪漫谛克情调跟浪漫抒情小说流派的关系,指出洪灵菲、钱杏邨等小说“风格上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阐述蒋光慈小说跟拜仑、高尔基、别得内依、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外国作家的影响关系。杨义以审美风格为研究对象,冲破了20~30年代批评表现出的写实主义的独尊意识与束缚,避免了50年代政治批评标准的态度偏激,弥补了80年代社会历史批评中审美分析的不足;他将革命小说放在中、外文学影响的背景上,探讨其风格跟中外文学的关系,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新空间。但杨义的研究与阐释尚显单薄,论述的对象仅限于蒋光慈、洪灵菲、华汉等几位重要革命作家的创作,影响关系的探讨仅限于在郁达夫、俄国文学之间,日本革命小说对我国革命小说的影响则没有触及,对革命小说跟社会历史、时代思潮之间关系的论述也缺乏新意。
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革命小说流派进行整体评判的研究趋势。夏德勇《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普罗小说派》(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3期)的论文,分析了整体创作特点,认为“强烈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与“反映工农疾苦和革命斗争方面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其突出的特征,但也有公式化、概念化、思想意识不纯粹等不足。他认为革命小说流派有一定的价值,一些作品有相当的艺术魅力,歌颂革命、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斗志,开拓了现代小说的题材并把阶级分析引进文学领域。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注:1989年)认为它重要的功绩与特色“就是站在鲜明的革命立场上,反映属于时代尖端的现实革命斗争题材,将革命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引进了小说创作的领域”,它的风格表现为“浪漫主义的抒情气质”和“注意塑造群像”;他还指出了革命小说流派的“弱点和不健康倾向”,即“浪漫谛克倾向”与“概念化”等缺陷。与80年代中前期相比,这些整体、宏观的批评和价值评判,无论研究方法还是价值观念都缺乏创见,这也许和80年代后期时代与思想的变化有关。
总之,80年代的革命小说及其流派的研究,在50年代的观念基础上完善了历史与审美的批评范式,并在80年代“启蒙话语”与文学审美研究的双重影响下,赋予一定的价值,基本改变了20~30年代完全否定的批评。但80年代的研究没有带来批评标准的新突破,无法跟20~30年代偏激的“片面深刻”和50年代悄然的变化相媲美。
四 寻觅突破的90年代,一些新研究方法被运用到革命小说研究领域
90年代的革命小说研究,汲取西方60年代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及文化批评等新方法,表现出抛却历史与审美批评的鲜明姿态。王一川的论文《浪漫乌托邦与父子冲突——从沈之菲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忧》(注:《文艺争鸣》1992年2期)和《“革命 + 恋爱”与再生焦虑——论20年代末几位革命知识分子典型》,(注:《戏剧》1993年2期)都运用“文化修辞学”的批评方法,分析革命小说中“革命 + 恋爱”所呈现出的表层“叙述”特征与深层意义结构。他认为,沈之菲革命与恋爱紧密相连的美好梦想中,流露出“父子冲突”的不和谐声音,造成了对浪漫乌托邦的拆解;丁玲的小说《韦护》对主人公内心焦虑的反复叙述,表明叙述者所关注的并非是革命战胜爱情的结局,而是革命最终战胜爱情的“艰难程度”与“艰苦过程”;王曼英(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革命与恋爱中所焦虑的中心问题,是“一个沉沦的女青年还能再次获得革命者资格吗”,因此文本叙述的中心是王曼英的“双重资格认同”问题。这种建立在结构主义、叙述学、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基础上的文本分析,打破80年代以前对“革命加恋爱”的忽视,发现“革命 + 恋爱”所隐喻的不同意义,其研究方法与问题剖析都具有开创意义。他还把“革命 + 恋爱”放在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宏观背景上,“从艺术符号系统与文化语境的互赖关系角度”,[10]分析它的表层叙述结构特征跟文化深层结构的隐喻关系,认为“革命 + 恋爱”隐喻文化语境内现代革命知识分子“原忧”和“再生”的两种心理焦虑,改变了80年代研究将此置在20年代政治与文化背景上的阐释方式。
旷新年的《革命文学》(注:1998年)一书,打破以往把革命小说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 政治语境内阐释的思维惯性,首次把它放在都市社会与文化语境内,认为它是都市中的 先锋文学,并在都市语境中经历由先锋到流行的变化过程。旷新年的大胆尝试,不仅恢 复了革命小说与都市语境的历史关系,也打开新前景。比如,该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方 法,粗略描述革命文学的社会生产情况,从作者的群体分化到上海文学报刊的兴旺等角 度,对产生环境和状况进行考察,弥补了以往的不足。如果说王一川、旷新年两人的研 究,都试图摆脱80年代的研究形式,那么朱彤《左翼小说叙事模式的流变》、(注:《 南开学报》1994年3期)杜显志、薛传之《高下文野之别(对两个小说流派相近审美追求 的辨析)》,(注:《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6期)王烨《现代革命的意识形态焦虑与叙事 策略》(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2期)等论文,都在研究角度上进行革新 ,或从叙事模式、叙事形式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开拓了革命小说研究的批评模式。尽 管如此,90年代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对象和问题仍局限在“革命 + 恋爱”和 “浪漫谛克倾向”等老问题上,虽有推陈出新之感,但却局限研究走向宽广、深入和突 破;视点、视角单一,无法反映革命小说与社会、政治、外来文学影响等的复杂关系。
今后,革命小说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和坚实的成果,还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努力:(1)资料的整理、编目工作,为研究提供全面、丰富、详实的资料保证。(2)主题、结构类型的研究工作,打破仅将研究局限在“革命加恋爱”或“浪漫谛克”问题上。(3)与俄国、日本等外国无产阶级小说的影响、比较研究,以此探讨我国革命小说与国际左翼文学的异同。(4)与现代革命、文化、都市—乡村社会、出版业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探究 革命小说在当时流行的社会原因。
收稿日期:2003-12-09
修回日期:2004-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