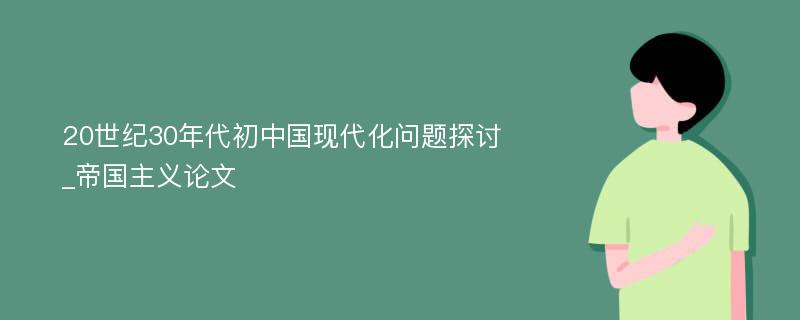
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探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初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是我国知识界首次以现代化为题展开的一次探讨。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多偏重于政治、文化思想的研究,忽视了现代化思想的探讨,因而这次现代化讨论也随之湮没,不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有关专著。笔者不揣浅陋,就这场现代化讨论予以评述。
一、现代化讨论的缘起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既有当时国内外社会经济巨变的历史背景,又有现代化理论演变的思想渊源。
1.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两者适成强烈反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的评判、选择、取舍,从而诱发了这场现代化讨论。
当时各大报刊如《申报月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生活》等竞先刊登有关经济危机、苏联建设成就的文章。一时间,人们竟以谈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为时髦。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现代化的思想转折:从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到认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则后者之不及前者,证明目下资本主义国之老衰,与社会主义国之生气蓬勃,确无置疑之处。”因而强烈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能够早一天到一个新形式的组织(社会主义),便早一天好”(1)。但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2)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并未形成共识,因而也就成为这场现代化讨论所要回答的主要内容。
2.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也是知识界对30年代初国内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的一种意识回应,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之心。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迅即占领东北;尔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长城沿线,不断制造事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与民族危机接踵而至的是30年代初中国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国民党政府保护大地主利益,广大农村土地兼并剧烈,加之苛捐杂税、天灾战乱,造成中国农村经济大破产。“农民破产之普遍,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3)。中国民族工业亦陷窘境。1930年冬,上海106家丝厂,停业者达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约40家。“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罕见”(4)。棉纱厂也不景气,“纱布愈贱,愈无销路”(5)。
目睹时艰,中国知识分子无不痛入心肺。《申报月刊》编辑提出了一个痛苦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如此步履艰难,“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呢?!他们觉得“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陶汰、万劫不复的厄运”(6)。沉重的危机促使他们发起了这场现代化讨论,以便“以各家对此问题的意见为药石,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7)。
3.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五四”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影响,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有三种倾向:一种是“俄化”派,以陈独秀为代表,从西欧文明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8)。从而告别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求索,“走俄国人的路”即其主张。一种是“西化”派,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仍迷恋于西方文明,继续鼓吹西洋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9)。一种是“东方文化”派,既反对社会主义新文明,也反对资本主义文明,而主张回归、复兴中国固有之文明。梁启超旅欧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便欲请出孔、老、墨三位大圣,去拯救西方文明。这种“以中补西”论即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10)。而梁漱溟则发挥了梁启超的这一思想,首开儒学现代化转换之先河,以文化多元的宏阔视野昭示了最近未来将为“中国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化复兴”的瑰丽图景(11)。“俄化”派、“西化”派、“东方文化”派互相论战,具体表现在20年代初关于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来开发实业的论战,以及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从五四到2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主要从文化领域探求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反差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强化了五四后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讴歌社会主义文明的思想倾向,并且进一步把中国现代化的探求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之所以有这一延伸,主要是因为“九·一八”后带来的深重国难与国民经济危机,使知识分子把救亡图强摆在首位:如何提高国防力与经济力,成为现代化追求的首要目标。“国家强弱的问题,应当与文化高低的问题分开。一个国家强,不必定文化高;一个国家弱,不必定文化劣”(12)。文化的现代化变革在火烧眉毛的救亡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某种程度上,为了凝聚全民族救亡力量还须向传统文化复归。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探求现代化领域的转变,而且还表现在这时已提出“现代化”概念来代替以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西化”或“欧化”。1927年柳克述著《新土耳其》一书,已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即“Whole heanted modernization”(13)。而该词大规模披之于报端的则是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特辑。但须指出,胡适与《申报》所使用的“现代化”概念,内涵有别:前者侧重于政治、文化上的理解——“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14),而后者注重于经济上的把握——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15)。这也恰好吻合了30年代初知识界探讨现代化视角从文化到经济的转变。
由上可见,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是五四以来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现代化道路论争的深入与发展,是知识界对现代化的探讨从文化领域转入经济领域的结果。
二、现代化前提与模式的探讨
1933年7月,《申报月刊》编辑为该刊周年纪念特地组织《中国现代化问题》专辑,向当时知名人士征稿。陶孟如、樊仲云、吴泽霖、金仲华、郑学稼、罗吟圃、周宪文等纷纷撰文,各抒己见。《申报》共收集26篇文章,其中短论10篇,专论16篇,论者大多应编者要求,从经济方面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主要讨论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何种方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16)征文观点五花八门,但多数人都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中国现代化道路应是非资本主义,持该观点的文章有7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的较少,各为3篇、2篇。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者兼采的有4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的文章也有5篇。笔者欲就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应走道路对各派所持观点予以评述。
(一)中国现代化的前提
中国现代化的困难、障碍是什么,亦即中国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多数论者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张良辅、陈彬和、孙静生、郑学稼、亦英、董之学、杨幸之、罗吟圃、吴觉农、陈高佣等10位作者持这一观点。杨幸之详细论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造成今日中国落后的两大根源。他从金融、交通、矿产各方面叙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状况。他得出结论:中国若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重恶势力,解决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那么“中国民族将永远落后,永远无法前进,其前途将更黝黑如漆不堪设想”(17)。罗吟圃也论述了“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压迫”及“政治的脱轨与军阀的混战”,指出“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18)。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在这前提下,才能谈得上现代化的建设。因此,该观点无疑抓住了根本问题,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论者一叶障目,只看到一些细枝末节的具体问题而忽略了根本东西,抓不到主要矛盾。张素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在于“励行法治”,“中国各种企业和其它一切事业之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执法者之不守法”(19)。杨端六、陶孟如、程振基、金仲华等人则认为政治腐败、教育不普及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二大因素。政治腐败表现在政府要员“思想陈旧至于诵经念佛”,“道德堕落至于贪赃枉法”(20);而教育则内容“空疏呆板”,又不普及,“怎样使我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受到健全的教育”,“乃是我国的现代化的途中的一个切要问题”(21)。诸青来则别出异议,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实业不振,是“利源未浚,地方未尽”,“技术幼稚,方法陈旧”,“工厂管理殊欠完密”(22)等种种失政所致,不能全诿诸外人侵略。诚然,缺乏法治、政府腐败、教育不发达、企业管理落后、技术低劣、交通不畅等因素,都对中国现代化进展起着或大或小的阻碍作用。但它们决不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反帝反封建面前,这些问题全属次要了。因而以上观点,混淆了主次,犯了因小失大的错误。
(二)中国现代化的模式
1.非资本主义模式:先进行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扫除障碍,并改造小农经济,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后再进入社会主义。董之学、杨幸之、罗吟圃、亦英、樊仲云、张良辅、郑学稼等7人持这观点。其理由是:第一,中国不能马上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只能支配国内市场到50%以内。而中国各银行的资本之额,只能占外国驻华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一弱”。“真是‘藐乎小矣’”(23)。因此,搞社会主义是超时代的。第二,资本主义化也行不通。因为“资本主义这个进程,在中国要碰着两个大的障碍,即:愈加依赖殖民地市场的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式的剥削制度”。更何况,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陷入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中了”(24),不足效法。第三,在当时历史阶段,只有采用非资本主义发展之一途。在这阶段,“不仅在凭借广泛的政治力量来扫除封建势力掩护下的残酷剥削与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支配,而且还要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25)。由此可见,非资本主义有四个特点:一是不马上搞社会主义。二是不搞资本主义。三是有一个扫除障碍、发展经济的过渡时期。四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即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横亘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集中力量,砸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现代工业,准备物质条件,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然而其也有缺陷:并未提出如何才能保障沿着非资本主义方向前进以便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不懂得要实现他们的主张,必须要有一个以共产党领导的各进步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同时利用、改造私营经济、小农经济,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
2.社会主义模式:对当时经济结构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方式的改造,以实现中国现代化。李圣五、陈彬和、闰年等人持这一观点。李圣五提出要“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26),亦即走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陈彬和提出了走社会主义的时代理由,是“因为现在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时代了”(27)。闰年则从道德价值取向上提出社会主义方式的必要,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就是“要打倒功利的经济活动的经济人,而去结实的树立个保证各个人的经济生存社会”(28)。不管怎样,他们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动机是美好的;其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看不到在中国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更看不到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不可能“一夜飞渡镜湖月”,直接跃入社会主义。故该主张无疑是一个魂丽的幻想。
3.混合现代化模式: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注入某些社会主义的血液以图拯救。诸青来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优点。兼采二者之长,不宜有所偏倚。全国实业可分别其性质,孰宜私有,孰宜公有,须先划定范围,不可漫无标准。私有者决非只谋私利不顾公益,官办者亦决非尽谋公益不图私利”(29)。郑林庄主张在“不十分变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内,采行计划经济”(30)。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其途径应是融和了生产机械化、合理化、计划化三原则”(31)。这是企图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嫁接到资本主义制度上。张素民亦然,主张“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32),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传统资本主义。他们企图在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下,对某些弊病,作一社会主义的改良修正,以求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这显然是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产物,是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要根治经济危机这一顽症,只有砸碎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之一途。任何形式的改良、修正,都只能暂时缓和矛盾的激化,不能根本解决。
4.资本主义模式。陶孟如、唐庆增二人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运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而我国当前之问题乃属生产”。要实现生产现代化,“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富力”,这就必须采用资本主义,才能增加财富。实行资本主义,人们便从中获利,而“获利愈多,则人民皆自动投资,不患资本之无着”;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之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莫能自拔矣。”他们还为个人主义正名,认为它并非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行为”,其真谛是“注重同情,决不希望他人之失败”(33)云云。这种远远落伍于时代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注定要遭破产。这是因为其根本就认识不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内外夹击下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三、历史与现代的检视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这次现代化讨论是知识分子对30年代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双重打击的一个思想回应,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基础因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导致的内部分化、动摇、离析,体现了知识分子企图寻求现代化以摆脱危机的殷殷爱国之情,因而是爱国进步的。其次,这次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必须首先扫除这两大障碍,才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并且在现代化模式取向上,多数知识分子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走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与我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相比,固然幼稚不足;但与同期仍执迷于“全盘西化”的胡适、陈序经相比,是一大进步,也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认识上的一大跃进,应予充分肯定。再次,从经济视野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跳出了习惯于从文化角度讨论现代化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一个进步。近代中西交接,给中国人带来的震动,最大的莫过于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感”(34)。因此,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能否延续、统一。自然,人们就习惯于过分夸大文化的功能,视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救国救民的根本。胡适说:“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35)。这种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在文化上探寻中国现代化本无可厚非,但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就是一个思维误区了。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则是五四以来从经济方面探讨现代化的较难得的一次。编者在前言中特地要求作者“注重于经济方面”,“集中讨论生产现代化”。26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经济上探讨现代化问题的。最后,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为稍后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提供了取代“西化”的“现代化”概念,进而使其内涵得到丰富、完善,加深了对现代化的理解。1935年爆发了“中国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的大论战,最终,多数论者渐渐摒弃“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转而采用“现代化”概念。这表明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深化了。冯友兰指出:“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我们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36)。论战中,人们不仅较多地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且对其含义在1933年初步界定为工业化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增加了科学化、合理化的内容。张熙若指出:“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代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化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从发展自然科学、促进工业发达、提倡各种现代学术、讲求科学方法等四个方面去努力争取。(37)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完善了现代化的内涵,提出了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等要素。这比较接近于战后西方学者提出的现代化概念,且要比他们早约20年。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迫在眉睫的抗日救亡,由于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贫弱,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箝制民主,也由于中国圆熟的传统农业文化所具有的抗拒现代化的惰性等多种因素,便得这次现代化讨论没有充分展开,理论水平不高,存在着严重的时代局限。首先,现代化讨论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当时知识分子多从经济方面来理解现代化,几乎把它等同于“工业化”、“产业革命”。这就阉割了现代化概念的丰富内涵,失之于偏狭。现代化是一个触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各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因此,这场现代化讨论只谈经济上的现代化而不谈政治、社会、文化、人的现代化,就显得严重不足,没有充分展开。其次,这次现代化讨论,虽然多数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但并没有解决过渡时期如何保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关键问题,比如领导权、经济制度等问题,又使其在40年代偏离了方向,为政治上取美国式民主,经济上取苏联计划经济的“中间路线”埋下了伏笔。再次,30年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认识也是肤浅表面的。他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批判也失于形而上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在当时人心目中简单地等同于国营经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公有制,有的甚至混同于法西斯主义(如谷春帆)。他们仅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表面成就,看不到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他们也认识不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文明类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诸如两者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都立足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等等。
统而言之,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从中国现代思想史角度看,它毕竟提出了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深化,为以后迅速接受社会主义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因此,这场讨论在基本方面应予肯定。
注释:
(1)江公怀:《中国经济路向的转变》,《东方杂志》1932年11月1日
(2)(6)(7)(16)《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申报月刊》,1933年7月,第2卷,第7号
(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第143—144页。
(4)(5)王方中:《1927—1937年间的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8)《〈新青年〉宣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9)(10)(11)(13)(14)(35)(36)(37)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7—168、47、71、361、366、631、338、458—459页。
(12)佛泉:《几条必经之路》,《大公报》1932年7月2日
(15)(17)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
(18)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之我见》,同上
(19)(32)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同上
(20)杨端六《中国现代化之先决问题》,同上
(21)金仲华《现代化的关键在普及教育》,同上
(22)(29)诸青来《中国实业现代化问题》,同上
(23)(24)(25)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同上
(26)李圣五《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同上
(27)陈彬和《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同上
(28)闰年《国民经济原理之改造与中国现代化》,同上
(30)(31)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同上
(33)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同上
(34)《梁漱溟全集》第二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